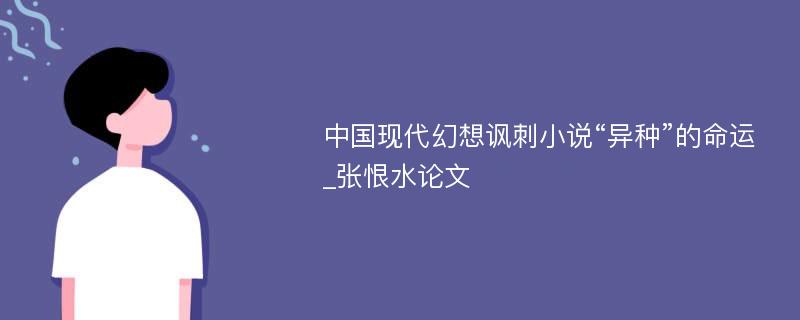
“异类”的命运——中国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类论文,中国论文,命运论文,小说论文,幻设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批在荒唐的时代产生的荒唐的作品。对于它们,我们很难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这些现成名词来进行简易的归纳,因而在评价之时也就倍感为难,或者从单纯的政治观念出发大张挞伐,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结果,这批作品长期被视为“异类”(也许连整体的“类”都算不上),备受歧视。
然而,一旦把它们聚拢过来,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其中的波澜迭起、五色斑斓: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张天翼的《鬼土日记》(1930)、老舍的《猎城记》(1932)、张恨水的《新斩鬼传》(1926)及《八十一梦》(1941)、王任叔的《证章》、钱钟书的《灵感》、许钦文的《猴子的悲哀》、周文的《吃表的故事》……既有精心结构的长篇巨制,也有随意挥毫的游戏之作,甚至还有一些可冠以“杂文”、“散文”名目的作品(如鲁迅的《智识即罪恶》、钱钟书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个个熟悉的作家大名与一篇篇陌生的作品名称之间异乎导常的组合,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而在这些“错位”之后,则是值得我们沉思的一连串问题。
这批作品最明显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其幻设性。“幻设”一词,出自明故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曰“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八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先生亦称“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潜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指出其特征为“寓言为本,文词为末”,并认为所谓“幻设”者,“即意识之创造”(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更准确地说,“幻设”应该说是有虚构的“变异之谈”,体现在《阿丽思中国游记》这一批现代作品中,便是其荒诞无稽的文体形式:在一段遥不可及或者故意含糊其辞的时间里,如《证章》中的“中华民国三千年”,《鬼土日记》中千篇一律的“某日”“某日”;在一些绝不可能的地方,如《八十一梦》中的“天堂”与“狗头国”,《灵感》中推翻了帝制的“地府”,《智识即罪恶》中的“油豆滑跌小地狱”;由一些身份或相互关系相当奇特的人物,如《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英国兔子傩喜先生,《八十一梦》中伯夷叔齐、潘金莲、猪八戒不拘上下古今的齐聚一堂,参予演出;连故事情节也故意荒而诞之,神而奇之,如《猫城记》中乘坐飞机降落火星上的“猫国”,《鬼土日记》中阳世之人凭“走阴术”游览“鬼土”。乍看之下,简直可以“童话”视之。
然而,揭开这层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我们却不难发现有阴惨惨的鬼魂肃立在马戏团的帷幕之后。那些纯属“幻设”的千奇百怪,与我们身周的社会现实忽然都有了千丝万缕、割舍不尽的联系,尽管经过了明显的漫画化、陌生化,它们骨子里仍然潜藏着沉重得令人不安的“过度真实”,各式各样的夸张、变形、修辞杂耍令人捧腹,与此同时,影射、暴露、不加掩饰的政治控诉却又时时溢出故事的文本之外,穿透了笑的烟幕,使笑声背后混杂着苦涩、轻蔑、厌恶、憎恨等等无法一笑置之的情绪:“猫城”里的猫人劣根千年如一;“鬼土”中高低两层界限森严;兔子绅士所持为宝典的《中国旅行指南》其实是本中国人的“恶习大全”(《阿丽思中国游记》);“天堂”里“有的兽头人身,有的人头兽身”,“兽头们大摇大摆,……人头的总透着寒酸些。”(《八十一梦》)……这一切都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司空见惯的现实,种种早已习以为常的不合理事物一旦配上了“猫城”“鬼土”种种不可思议之背景,便有了所谓“疏离认知”(Unfamiliarization)的效果,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注意。在这里,幻设的“滑稽”上升到了现实的“讽刺”,现实缺陷借幻景而凸现,使幻境比现实更加现实。显然,这才是这批作品本质上的共通之点——讽刺性,或者说,用幽默的手法表达出来的道德义愤。
与《儒林外史》、《阿Q正传》等近乎写实性的讽刺小说相比较,《猫城记》这一类小说有着怪诞不经的“超现实”艺术样式;与一般的幻想小说(如科幻小说、乌托邦小说)相比较,它则更具“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幻设性特征,主观的讽刺意图极其鲜明,强化了“反现实”意味;与纯幻想的神话、传说乃至寓言、童话相比较,它则舍弃了对神仙、法宝等超自然力的崇拜,也舍弃了简单明白的正面的道德训诫。事实上,这类作品中的幻想天地,正如张天翼所说,“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不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只是形式,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无论人,无论事,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注:张天翼:《鬼土日记·关于〈鬼土日记〉的一封信》。)超现实、反现实,与现实“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真实”,这些因素极其微妙的渗透结合构成了此类小说鲜明的特质。如果勉强给它立个名目的话,或许应称之为——幻设型讽刺小说。
二
联想到中国传统“不言怪力乱神”的实用理性精神与平和中庸讲恕道的价值体系,那么怪诞的幻设与辛辣的讽刺的产生其实都可算“异类”,这就是为什么此类作品不发达且大多命运不济的原因。但是,中国民族性中同样也有喜象征、好讽喻的一面,故“异类”的产生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异类”与“异类”之间的结合更是早已有之,甚至不可避免的。
追溯幻设与讽刺这两种“异类”思维相撞击的历史源头,我们碰到的第一座里程碑,就是《庄子》: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角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遂北,旬有五日而后反。(《杂篇·则阳》)
“微缩式”设想之怪诞已令人称奇,而大国争战的惨烈程度与所争领土之间不成比例的反差更构成了绝妙的反讽。难怪有识者曰:“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注:〔宋〕黄震:《黄氏日抄·读诸子·庄子》。)幻设型讽刺小说,也在这里找到了它的直接原型。
幻设型讽刺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则应归功于唐传奇,其艺术性较高的典型之作首推沈既济的《枕中记》及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前者叙少年卢生于邯郸道中逢道士吕翁,得其囊中枕而寝,遂于梦中历尽荣华衰败,醒来则邸舍黄粱未熟;后者叙处士淳于棼梦中被邀至槐安国,拜附马,复出为南柯郡太守,威福日盛,遂被国王疑惮送归,醒来之后方知所谓槐安国者,实乃自家宅南大槐树下蚁聚之穴。两文皆讽世之作,而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已由寓言的简单形式演进到“有意为小说”的阶段,“邯郸梦”、“黄粱梦”、“槐安国”、“南柯梦”均成无人不知之典故,开创了“梦游型”的幻设模式,影响尤大。另如李玫《纂异记》中的《徐玄之》、《浮梁张令》等篇,也都是以冷嘲热讽为主要特色的幻设型作品。
明清两代长篇小说的繁荣促进了幻设型讽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西游补》、《斩鬼传》、《镜花缘》、《何典》等作品的出现,即为标志。虽然它们多非全篇讽刺之作品,但讽刺的因素却占有相当的比重,较诸子书中的寓言及唐传奇微妙的讽喻来,锋芒也增强了许多,讽刺甚至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核心部分。《西游补》的镜中世界,《斩鬼传》“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3篇《清之讽刺小说》。)的人间戏拟,《镜花缘》的遨游海外、历诸异境的游记体裁,《何典》“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旧典”(注:鲁迅:《何典·题记》。)的幽冥戏拟,对后世幻设型作品的思维模式都颇有影响,并最终导致了清末民初幻设型讽刺小说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高潮的标志是所谓“拟旧小说”(又称翻新小说)的风行,它们大多袭用旧的书名人名而写当时新事,如冷血与煮梦的两部同名作品《新西游记》,不约而同地借助唐僧师徒(尤其是猪八戒)的视角来透视当时社会的千疮百孔。另有葛啸侬《地府志》、女奴《地下旅行》、老谈《痴人梦》等非“梦”即“鬼”之作,亦皆讥弹世风的滑稽小说。虽然阿英在其《晚清小说史》中曾斥之为“晚清小说之末流”,并称“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注:阿英:《晚清小说史》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但究其实,此类小说亦谴责小说之一支,属于晚清大变局中“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的产物,“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运笔行文,则诙谐处中破积闷,爽快处足匡钝疾,也自有一份不可抹杀之功劳。
理清了幻设型讽刺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之后,我们或许更为容易理解“幻设性”与“讽刺性”这两种民族文化的“异类”相结合的支点: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思维倾向于拒绝对宇宙作超自然解释,民族审美想象力的创造激情必然要在理性限制之内寻找出口,事尽可固无,理却须必有,任何“超现实”“反现实”都摆脱不了“现实”的原则,一旦幻设者对现实采取了否定态度之时,针砭性的讽刺便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特定历史环境及具体场合的制约,作家们往往无法直言不讳,只好被迫采取“譬喻不斥言”的委婉方式,为自己对现实的讽刺影射寻求一件“防弹衣”;同时,在讽刺中,批判性的力量也往往要求与夸张、变形、譬喻、戏拟等幻设性因素结盟,以使自身艺术化、幽默化,在总体上避免简单化、粗俗化、谩骂化的不良倾向,加强对生活形象概括的穿透力。诚如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所言——
寓言家是说教者,期望灌输一种道德训戒。人们并不十分喜欢道德说教,因此,这颗苦药就得裹上糖衣,必须妙语惊人,情趣横溢,或在某种意义上引人入胜。……假如这颗苦药上糖衣裹得不够份量,就不会有人把它吞下。倘若说教的寓义过狠,人们就会把说教者看成毫无人性,如果寓言的利刃刺得太深,他就会被送上十字架钉死。(注:见王宁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9页。)
最能理解戈尔丁笔下的“寓言家”的困境的,或许就是中国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的作者们了。与本国的前辈们相比,他们有幸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在一个优劣利弊一目了然的参照系中将国家、民族的病症看得更深更透;而西方同类小说的被译介引入,也让他们在表现技法上受益非浅,如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之于英国卡罗尔的童话《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之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小人国中的政党依鞋跟高度分为“高跟党”与“低跟党”,鬼土中的政党则依出恭方式分为“坐社”与“蹲社”),老舍《猫城记》之于威尔斯的《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两者同具“异星探险”的框架,猫国的“迷叶”与月球蘑菇的作用也颇为类似);然而,不幸的是,在接受了西式的“新武器”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比前辈们所处的更加无法自由表达的世界,他们的口诛笔伐往往一不小心就会堕入“寓义过狠”或“利刃太深”的陷阱,从而面对承受别人的斧劈刀戕的命运。
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的作家们所处的,是一个特别合适于讽刺的时代。风雨飘摇,鸡鸣不已,外敌侵凌,内患频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实的沉重几乎让人无法直面。作为置身于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中的启蒙者,“五四”时代理想化的精神投影在他们身上早已褪色,他们所面对的,是漫长得令人疲惫的“壕堑战”。向上看,统治阶层醉生梦死,其朽腐无可避免;向下看,众多民众却依然昏沉愚昧,又仿佛无可救药。上层是一场闹剧,下层则是一场悲剧,身处夹缝中的作家们,既感到了旧的罪恶怨鬼般的纠缠,又目睹了新型的罪恶饿蚊般的孳生;既无法看到新的曙光的上升,又无法阻止旧的有价值的伦理道德的沦丧。他们注定了是无法超越的,尽管他们的认识其实相当清醒。这种心态投射到他们笔端,便带来了“鬼气森森”的忧患感。鲁迅写道: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注:鲁迅:《华盖集·“碰壁”之后》。)
老舍则道:
我所见到的鬼都是鼻眼俱全,带着腿儿,白天在街上蹓跶的。……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变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注:老舍:《鬼与狐》,《论语》1936年7月号。)
鲁迅的“鬼”是现实中的受苦者,分明是人,却被剥夺了“人”的资格,诚属可悯;老舍的“鬼”却是使世界受其苦者,同样是人,贬之为鬼,增其可鄙。然而,“现实=地狱”这一公式,对于他们却都是适用的,对于“见了不少的人中之鬼,随手拈来,便是(写作)绝好材料”(注:张恨水:《新斩鬼传·自序》。)的张恨水,对于认为“鬼土”和阳世社会“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张天翼,甚至对于只是借助天真无邪的兔子和小女孩的眼光来“格格不入”地透视中国的沈从文,也都是适用的。
有了这样的共同认识心态,再想在笔下用简短的篇幅来概括变幻无定的末世闹剧,表现它们在人们心灵中所引发的喧哗与骚乱,那么,“寓言十九,托之以梦”就自然不失为一种有力且方便的创作手法。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在现实之前的退缩,恰恰相反,现实性正是这批小说中最不可剥离的部份。沈从文面对的是20年代末军阀混战的现实,张天翼面对的是30年代初劳资矛盾激化的现实,老舍面对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现实,张恨水面对的是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现实,这些现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一一打下了最鲜明不过的烙印。事实上,这些作品泰半都是现实刺激的产物。惯于冷潮热讽的老舍承认,他写《猫城记》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象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注: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宇宙风》1935年第6期。)以新闻记者为职业的张恨水也同样承认:“我为什么要写这本小说(指《八十一梦》)呢?说起来原也简单,只因那个时期重庆的一片乌烟瘴气,实在让人看不下去。”(注:张恨水:《八十一梦·前记》,载《八十一梦》,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抱有明确的讽刺、谴责意图的作家们,并不以单纯抨击某种社会风习或政治恶弊为满足,而是将讽刺对象定位为整个社会的全部病症,这样一来,但丁游地狱式的“游记体”便成为他们最常用的工具,叙述者往往同时兼任目击者、参与者,甚至评论者,仿佛一架移动的摄像机,对“活地狱”式的世界进行走马观花的扫描,恶劣的众生相也由此得以一一暴露。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小女孩阿丽思与兔子绅士足迹所及,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横行到军阀的以内战为赌博,以官僚政客绅士的结党营私到文坛的勾心斗角,从“人肉市场”上论斤两买卖儿童到随地吐痰、收小费等一般陋习,都被主人公(因而也被读者)一一摄入眼中,丑态毕露。在《八十一梦》中,“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将军’们,压在人民头上无恶不作的豪门,不顾死活只知道抢钱的贪官污吏,在官僚资本豢养下囤积居奇、跑‘滇缅路线’,发‘国难财’的商人,无耻下作的文化特务,地主型的房东,大大小小的‘裙带官’,‘拳头也是外国的好’的美国生活崇拜者……”(注:张恨水:《八十一梦·前记》,载《八十一梦》,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也都在梦游者的眼前暴露无遗。这类作品批判视野之广阔,并不在任何现实主义作品之下,它们的现实性是和寓言性并行而不悖的。
当然,以全景式的扫描速写为手段来追求作品的现实性,往往是以某些艺术性与深刻性的丧失为代价的,这一点也正是幻设型讽刺小说的大多数长篇作品最致命的弱点,而最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在这一点上作出弥补,在“拓广”的同时“深挖”,在把握全局全景的同时发掘这一切的总的根源,将批判的锋芒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直指国民劣根性的高度。在某些作品中,这只是偶一为之的闪光,如《八十一梦》中批评狗头国人“上自国王,下室穷百姓,都以私相授受为亲爱”;在某些作品中,闪光点便汇聚成了有意串连起来的长链,如《阿丽思中国游记》便是“对中国民族性弱点的一次大展览”(注: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在某些作品中,这根长链更被铸造成了自觉射向民族病根的支支利箭,最好的例子就是老舍的《猫城记》,他在谴责猫国的国王、政客、地主、学者这些上层人物的腐化无耻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刻划下层百姓的愚昧、自私与盲动,而这后者正是前者最适宜生长的土壤。猫人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自由”是猫人自有史以来的最高理想,但这个所谓“自由”在猫语中的含义却等同于“欺侮别人,不合作,捣乱”。“(对下等人)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也是下等猫人认为正当的态度。”而自相残杀的本事,却“一天比一天大,杀人的方法差不多与作诗一样巧妙了。”面对着这样的国家与民族,难怪老舍叹息道:“这个文明快要灭绝!”“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不良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有研究者总结了猫人的八大特性,一曰贪懒,一曰自私,三曰愚昧,四曰肮脏,五曰好色,六曰勾心斗角,自相残杀,七曰害怕外国人,八曰极端不重视教育,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讽刺杰作。其历久弥新、发人深省、尖锐辛辣、耐人寻味的程度,足可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媲美。”(注:袁良骏:《讽刺杰作〈猫城记〉》,《齐鲁学刊》1997年5月。)显然,正是在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与鞭挞中所达到的深刻性,才奠定在《猫城记》在同类作品中独一无二的杰作地位。
与现实性、深刻性共同构成了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对以往同类作品的突破的还有它的悲剧性特征。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坚持着“壕堑战”,相信着道德至上的寓言家,他们的心态是成熟的,同时又是沉重的;他们早已出离了本世纪初梁启超们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这一类空想政治小说时的幼稚激情,却又对近代谴责小说的前辈们那种“闹剧欣赏者”式的态度作出了自觉的摈弃。这或许正是现代幻设型讽刺小说与近代作品最鲜明的区别所在:同样是面对一幕幕闹剧,现代作品的处理基本上是悲剧性的笔调,而近代作品(包括幻设型讽刺小说及其他谴责小说)却“恰恰是广泛的、激烈的社会谴责和社会暴露与高度的对社会人生的冷漠旁观态度相结合的产物”,“对社会丑闻的展览与谴责是与作者内在情绪上的自我满足感相偕相生的……普遍的道德沦丧加强了作者自我道德的完善感,自我道德的完善感更使作者感到周围社会的道德沦丧。”(注:王富仁:《弗·伊·谢曼诺夫和他的鲁迅研究》,载《历史的沉思》,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365页。)
近代幻设型讽刺小说的作者是以“看戏的人”自居的,而现代的作者却因无法保持这样的袖手旁观态度而成了“戏中人”。在他们笔下,对社会病症的全面展示与对民族劣根的深入解剖往往伴随着他们要求改革现状的强烈愿望以及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还有情绪上的苦痛激愤。沈从文写道:
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但……所有心上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象没有法子使它融化成圆软一点。(注: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
同样的“得了讽刺而失了幽默”的情形,也出现在老舍的《猫城记》中,出现在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中……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甚至很难找到能起积极作用的正面形象,即使有,也逃不脱毁灭的命运,连带全书的结局也毫无例外地伴随着末世感与幻灭感:天真的阿丽思在目睹了一场奴隶买卖后满腹疑问地返回英国;鬼土里“改朝换代”,黑暗却一仍其旧;英雄的大鹰与小蝎双双自杀,猫人们被亡国灭种;一心铲恶扬善的孙悟空惨遭败绩(《八十一梦》)……而那些被讽刺的对象,尽管看起来多么的可笑、愚蠢与无价值,本来早应“毁灭给人看”,却又是如此顽固地存活着,而且注定了还要长久地存活下去。作为读者,我们不再看到“大团圆”,不再感受到以往滑稽讽刺小说阅读经验中曾有的美对于丑的绝对优势,不再有站在道德胜利一方的优越的快感,一旦领悟到那种种“有中国特色”的丑陋现象原来都出自民族性痼疾的根源,我们也笑不起来,压倒一切的,只是悲剧性的苦涩感。“虽然再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换三打国务总理,换十五打军人首领,换一百次顶时髦的政治主义,换一万次顶好的口号,中国还是往日那个中国。”这就是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结论。“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了五光十色的大笑话……我和猫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无隐的攻击他们,而后再给他们出好主意,他们很会把我偷偷的弄死。”(注: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宇宙风》1935年第6期。)这就是老舍“怯懦”地只能选择“讽刺”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这些到底是绝望的讽刺呢,还是愤激的警告,或者仅仅预示了作家们要与整个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文化心态?
三
“在最优秀的讽刺家的作品中,循规蹈矩的成分最少,真实的成分最多。”(注:(美)吉尔伯特·哈特:《讽刺论》,万书元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中国现代的幻设型讽刺小说往往就具有这种品格,它的现实性、深刻性以及悲剧性都标志着对以往模式的突破,即使由其提供的艺术画面有时仍难免粗糙浮浅,但它浓烈而刺目的色彩,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粗放生动的语言却都令人印象难忘。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幻境,而且是针对这个黑暗世界的颠覆,作为过往的传统型讽刺作品与当代“黑色幽默”的反讽体作品(譬如王小波的《2010》)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在文学史上也自应有其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始终找不到与之相契合的解读方式,忘记了它的对民族未来表示忧虑的“预言书”性质,忘记了它的“反面乌托邦”精神,忘记了它的幻设性所应具有的独特审美思维,而只是一味采取政治视角进行解读,或者认为它攻击黑暗不力,甚至否定其作为讽刺文学的价值,如瞿秋白、冯乃超对《鬼土日记》的批评(注:瞿秋白〈董龙〉:《画狗罢》,冯乃超(李易水):《新人张天翼的作品》,周载于《北斗》1931年9月创刊号。);或者认为它的影射太过激烈,对之罗织罪名,大肆批判,如沈从文因其《阿丽思中国游记》而被人别有用心地冠以“革命文学家”这一在当时可以杀头的头衔,老舍的《猫城记》更因“影射革命政党”而被打成“大毒草”;或者因为这类文学作品没能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或“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而加以否定(这一点有时甚至连作者本人也惴惴不安)。即如一致予以好评者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虽然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同样大受欢迎(国民政府大员们当然是例外),但到了1954年准备重版此书时,他也不得不删改其中不少篇目,承认这部他的最畅销作品其实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气力地在发他的‘牢骚’!”(注:张恨水:《八十一梦·前记》,载《八十一梦》,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幻设型讽刺小说这一“异类”,从此在这些优秀作家的创作中成为后无所继的“异数”,除了张天翼还能将这种幻设与讽刺相结合的才能转移一些到童话创作中之外,其他作家都在这条道路上放弃了进一步的探索,老舍甚至还搁置了一部同类型作品《鬼曲》的创作。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坛上的一大遗憾,而在这遗憾背后,则是关于“异类”作品在我们的文学创作、批评中的命运的未完的思索。
标签:张恨水论文; 小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小说史略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寓言论文; 老舍论文; 沈从文论文; 猫城记论文; 张天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