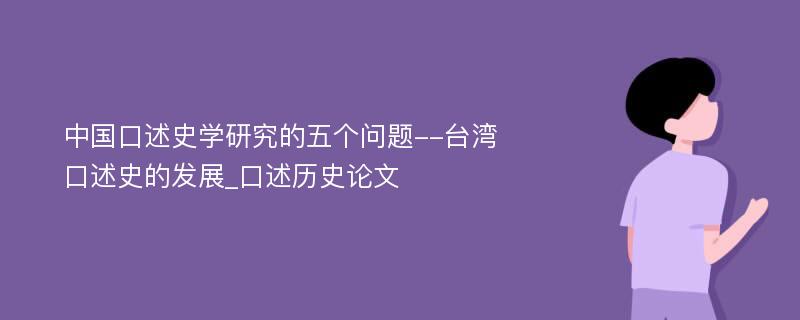
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五题——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台湾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讨论台湾口述历史的进行与刊布,都以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为其嚆矢,而订在1959年12月;然而如果将口述访谈包括座谈会、座谈会记录(以第一人称表示)这一宽广的定义来看,则应以1952年台北市文献会成立后,以《台北文物》为其机关刊物,在翌年1月(1953.1,2/3)刊登《大稻埕耆宿座谈会记录》一文为最早。可惜此一工作在1956年以后即停止。此外早期的《台湾风物》也在1954年5月刊出《士林镇乡土座谈会》为第二篇。虽然如此,但因学术机构有专才、预算,因此学术机构对口述历史的探讨虽较晚进行,但其规模成果却是地方文献机构、私人创办的杂志所难望其项背的。本文首先探讨台湾口述历史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是“中研院”近史所、台史所、国史馆、党(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军(史政编译局)为主;另一条路线自始即以台湾本土人物为访谈对象,自台湾大学、各省县市文献会、文化中心(后改为文化局)乃至于文化工作者。而后者在解严后,其发展更为快速,以地方文史工作室为其主力。其次谈及台湾口述历史的推动给台湾各界尤其是史学界带来的影响。再次谈及台湾口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面对的问题。
一、台湾口述历史的缘起与进行
(一)近史所既开风气又为先
口述历史是藉受访者的叙述,保留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记录,它为社会变迁保留史料,也提供历史研究或直接运用在个人传记与地方史的书写中。台湾口述历史的发端与实践,都不能不由1957年“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所长开始积极推动口述历史开始说起。
郭廷以所长认为只要每位重要人物都能留下一份详尽的传记记录,再与其他史料相对照,就能解决、澄清若干历史问题,遂在1959年10月拟订“民国口述史访问大纲”,于12月正式展开党、政、军重要人士的访谈。之所以在1959年展开这项工作,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1949年来台重要人士,有部分已退出政坛,有足够的人物可以选择;第二,中华民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到1945年抗战胜利,可说历经了15年战争,因而史料征集及历史书写两相缺乏,有待补充;第三,受到欧美各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影响,其中受到美国的影响较大。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早进行相关口述历史研究的大学,而该校东亚研究所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何廉(Franklin L.Ho)等教授,已在1958年进行“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访问因国共内战而迁徙美国的李宗仁、孔祥熙等中国重要的政经人物。
不过郭廷以所带领的口述历史与当时口述历史的潮流和台湾社会的变迁未能完全符合。首先是口述历史之所以在欧美产生,最主要的是替没有书写能力或不识字的弱势个人、族群发声,记录他们的历史。但近史所一开始就定格在“重要当事人”、“军政、外交、经济、文化、社会重要人士”,反而是为强者发言;其次访谈对象丝毫未把台湾人放入访谈名单,只重视迁徙来台、过去曾闪亮一时的政、军人物。经过近史所的提倡与实际进行,自1959年开始,经过一年多的日子,共访问了11人,到1960-1962年乃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各自进行中国重要人物的口述访问计划;此后10年间(1962-1972)接受美国Luce Foundation资助,成稿480万字。这是该所发展的第一阶段之历史。由于当时政治上未解严,受访者个人尚有顾虑,因此出版的脚步异常缓慢,直到1982年台湾第一本口述历史专书《凌鸿勋先生访问记录》才出版;也由于未能在较合理(尽早)的时间出版,反而使得早期从事的口述史不再新鲜;另一个原因是当事人已过世,难以找到合适的出版授权人,导致不少这时完成的访谈记录不能出版。
近史所第二阶段的口述访谈于1984年展开,所长吕实强为加强征集史料,成立了口述历史组迄今。这一阶段不论是访谈者、受访谈人还是访谈的形式、出版的状况都有明显的改变。在访谈者来说,不再如前期委托所外人士进行,而是由所里同仁组成团队,或由同仁找院外的合作者来进行;在受访者方面,不仅不再局限于军、政人物,反而扩大到教育、经济、企业史及相关领域的杰出人士,也开始为弱势者发声,或对政治受难者做大规模的访谈。此外在访问形式上也有了突破,此即原来都是个人生平式的访谈(即将受访者自从有记忆起一直到访问当时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改为以专题式的为多。比如《都市计划前辈人物口述历史》、《东北道德会相关人物》等访谈,亦即以某一共同主题为主。往后的专题,大半配合访谈者的研究计划,如《唐荣铁工厂相关人物访谈记录》、《台南帮企业相关人物》、《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在出版方面,为了及时出版,也在短短20多年内出版口述历史专书100多本,诚然是非常亮丽的成绩。本期在经费上,还有来自委托单位如台湾高速铁路建设相关人物就是委托案。经由这些委托案,结合更多对口述史有兴趣者的加入,就近史所本身而言,也是个扩大领域、接触社会的好机会。
除了出版专书外,1989年近史所也出版了《口述历史》期刊,这是年刊,旨在容纳篇幅较小的访问稿以及刊登探讨口述史理论、方法的相关文章,是全台湾唯一的口述历史刊物,2004年出版到第12期,现已停刊。
总之,近史所自1959-1972年进行第一期口述历史,至1984年迄今进行第二阶段的口述访谈,已留下千万字以上的史料,出版100多本专书,还有《口述历史》不定期期刊12期,成果丰硕。目前该所仍在进行院士访谈或接受委托案,但已不如之前积极。
(二)国史馆等单位的继起实践
“中研院”各所(包括近史所、台史所)的口述访谈,仅被定位为数据搜集,虽有任务编组,但不列入考绩;且口述访谈是费时、费力、费钱的工作,除非特别有使命感或者和自己的研究主题有关,很难强迫研究同仁进行。国史馆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作为一个学术、行政双重任务的单位,反而可以有专职人员来大规模的进行。当国史馆于1991年开始进行口述访谈时,聘近史所的研究员刘凤翰为顾问,以访问军政、财经、教育、医学、学术精英为主,也以重要人物生平式的访谈为主;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全力推动台独人物、民主运动人士的访谈;2009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则以蒋经国身边的相关人物为访谈对象,政党轮替也多少影响到受访人物之挑选。除了生平式的访谈外,也从事一些主题性、专题性的访谈,如对香港调景岭营、忠贞新村、眷村、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事件等做专题访谈。近20年来,该馆已出版52种口述历史丛书,其基础反而比近史所稳固,往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比国史馆更早发展的为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目前已缩编为党史馆),其访谈的对象以政治、军事等重要人物为主,自1977年起,党史会每年均针对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举办口述座谈会,结集整理成文字稿刊载于该会主编的《近代中国》中,如孙科、蒋经国等,选择座谈的时机为逝世周年或百年诞辰,邀请其同乡、故旧、部属为座谈者来谈其生平。另有以事件为主的,如“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对日抗战”或者国民党认为对台湾贡献最大的“台湾土地改革”。由于编制、经费的关系,1993年已暂停口述史的访问,但仍可见该会的出版品,如有8种个人口述专书,还有座谈会记录如《百年忆述》等。
另一个单位则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原称史政局,因缩编而改成“室”)。该局自1982年起对在台军事人物展开口述访谈,由近史所研究员王聿均、陈存恭、刘凤翰指导,主题以“战争”为主,如东征、北伐、抗日战争等为主轴,访问军官亦及于下属士兵。此后也逐渐进行专题式访谈,如滇印缅作战、青年军、陆军官校等,因此也有访问记录6种、专题访问记录8种。目前史政编译室已因人员缩编不再能积极进行访谈,甚至已退出每两年进行的口述历史工作会议。
(三)台大锁定本地人士的访谈及相关文献单位的继起
战后台湾史研究虽经台大教授杨云萍大力倡导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1965年台湾大学陈奇禄与许倬云教授在台大校庆20周年纪念时,举办“台湾研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的演讲与相关座谈会,台湾学界才渐渐推广有关台湾史的研究。1967年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下进行“台湾口述历史计划”,由王世庆、王诗琅负责主访经历日本统治的耆宿,且以板桥、雾峰林家这两大家族相关人物为主,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一计划到1969年不再继续。此一访谈成果,因当时访谈尚不普遍、整稿体例未能确定以致到1991年才出版《近现代台湾口述历史》,大半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整稿。此后台大零星的口述历史,主要是针对杰出校友的访谈。
前曾述及台北市文献会(分成省辖市、直辖市两个时期),于1983年恢复早期的传统,以座谈会的方式对改制的12个行政区展开访谈,不仅对人物也对地名沿革、行政区域、归属沿革进行采集,完成于1991年。紧接着于1992年起展开专题的口述历史座谈,针对各行各业的耆老、达人进行座谈,其内容包括茶叶、布业、传统糕饼、摄影业,后来台湾文化协会、五四新文化运动、台湾民众对中日战争的参与和看法、抗战胜利纪念等政治味十足的专题逐渐展开,甚至还对至今超过百年以上的人物如刘铭传与台湾现代化等举行座谈。为了较快地取得口述访谈的成果,亦有委托学术单位进行访谈的,如白色恐怖案件、历届市长、议长口述史、台北第十四、十五号公园口述史、大台北都会区原住民口述历史、台北市台籍日本兵等专题,这些议题能贴近弱势族群,为他们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成为首善之区台北的重要文化资产。
台湾省文献会(今改称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是早期研究台湾史、搜集保存台湾史料最重要的机构,1949年成立的该会,到1981年才开始展开闽南、客家及原住民婚丧习俗的口述历史座谈,而后借着纂修《台湾原住民史》、《台湾客家族群史》,还辅导各县市修志,而在1991年开始进行各县市耆老的口述座谈。该会较值得一提的是自1988年起在省议会和各界的期待下展开政治事件相关人物的访谈,如二二八、白色恐怖,而后又有八二三战役口述历史、传统技艺匠师、台湾人的战争经历等。
相对于台北市、台湾省两个文献会,高雄市文献会成立较晚,口述访谈也较晚展开。它先是在1991年委托“中研院”近史所展开“高雄二二八事件相关人物访谈计划”,翌年则积极展开有关民俗调查,如俚语、典故、歌谣、聚落发展的座谈,又针对高雄港和工业城的属性对该地工业界、工厂展开座谈,最后及于党、政、军、人文科学等相关人物访谈,出版了余光中、王家骥、赵耀东等人的访谈记录,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中。
至于台湾十八个县市,都有各自的文化中心(后改为文化局)开展访谈,且各有特色。如台中县则有《台中县口述历史》不定期刊物进行街庄行政、雾峰林家相关人物、妇女生活口述访谈;宜兰县则对日治下的产业、军事、教育、白色恐怖进行访谈;身处离岛的澎湖县也对职业妇女、马公要港部从业人员进行访谈。这些县市各擅胜场,成果丰硕。
至于私人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的更是不胜枚举,有些已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好书,如林忠胜、吴君莹夫妻完成的《陈逸松回忆录:日据时代篇:太阳旗下风满台》等四本;又如张炎宪担任国史馆馆长任内大力提倡口述史,亲自访谈,又在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下出版他的分区二二八访谈记录,可以说是最多产的访谈者;此外经由口述而为受访者写传的也不少,不赘。
二、台湾口述历史的特色
虽然台北市文献会1953年已在《台北文物》刊出第一篇座谈会记录,而“中研院”近史所于1959年底展开口述访谈,但一开始因政治氛围及口述访谈的风气未开,因此早期访谈不成功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直到台湾于1987年解严后,政治逐渐民主化,口述访谈乃得以趁势而起并快速推动。如果要说其特色,则有如下几点:
(一)搜集生活在跨越两个时代者日治时期的经历,得以展开日治时期的相关研究。由于研究台湾殖民地时期历史的主要材料来自于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等台湾总督府保存的相关档案,但作为被殖民的台湾人却没有相对的史料可以使用,因此访谈取得当时民间普通人的记录,就成为现在研究日治时期台湾史不可或缺的手段。
(二)对政治运动的平反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台湾因历经不同政权的统治,在改朝换代之际难免引发政治案件,而在执政者有意掩饰和抹黑下,一手资料、关键史料难以取得。以二二八事件为例,早期的观点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上,经对受难者家属、受害者本人及见证者的访谈后,颇能理解部分真相,成为平反运动的史实根据。
(三)保留传统匠师、艺人的生命史。由于社会变迁很快,一些传统的工艺、技术逐渐有失传断层的危险,经由访谈,忠实地记录他们的生命史,有助于了解过去,并保留资料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四)修志传统的延续亦有赖于口述访谈取得地方史料。90年代台湾兴起一股修志热,全台319个乡镇莫不卯足全力,但因地方史料少及能运用到的古文书、族谱有限,因此以口述访谈取得数据就成为修志的一个重要方法,尤其是“大家来修村史”将“乡”又向下修正到以“村”作为修史志的单位时,口述访谈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
(五)由口述访谈当事人而为之作传。虽然史学界仍谨慎地将史料、史学做很严格的分际,如写传记将口述历史仅视为史料的一部分,但其他学门的人则直接将访谈加上部分数据即成为一本传记,成为传主和作者两人密切合作下的产物,如朱瑞镛为其父朱江淮写的传、蔡笃坚为施纯仁写的传都是如此。
(六)由成立口述史工作会议到成立口述历史学会。由于各单位或个人进行口述访谈的愈来愈多,1991年近史所建议召开口述历史工作会议,经各单位同意而召开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一开始每年一次,而后两年一次,由各个公家单位轮流主持,主要协调访问对象、交换工作经验、介绍工作成果;迄2010年为止,共召开十二届,虽然成果有限,但藉此也凝聚出成立口述历史学会的契机,2009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口述历史学会。
(七)培养访谈、整稿人才。进行口述访谈及整稿者都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早期大学院校并未有相关课程可以培育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就成为重要的工作,1999-2000年“中研院”近史所在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部办公室经费赞助下,承办六个梯次的口述历史研习营,课程中有理论、有专题、有实习,为其后的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之后为了进行不同主题的访谈,也都各自举办研习营。此外,口述历史也成为大学院校的正式课程,大部分的课名是“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际”,除历史系、所外,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淡江大学信息与图书馆研究所、高雄医学院等都有口述史的相关课程。
(八)2009年“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出版的《台湾口述历史书目》总结了四五十年来台湾口述历史的成果。本书收集了1953-2009年上半年的成果,并将之分成总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五类,各类下又分成“专书”、“单篇文章”两种,以中文书写、已出版的为主。其中较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正确了解台湾口述史的成果,因此“将汇集多篇个别访谈记录的专书,以单篇为单位逐条摘录,再以专书论文体例制作书目”,共取得有效条目5005条,这其中以政治事件最多、最值得注目。目前在区域研究、族群、妇女、宗教习俗、产业这几个部分,都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台湾口述史界虽然已做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但是此一工作仍有值得省思改善的部分。
三、台湾口述历史的省思
台湾的口述历史经过几十年的采集与应用,现今也面临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台湾口述历史的品质堪虑。何以近二十年来口述历史如此蓬勃的发展,主要在于取得容易,只要受访者同意即可进行,但事后成为文字稿,中间是否有失真?内容是否不尽正确反而有误导的现象?而访谈者是否作了进一步的查证?以目前来看,除了重要机关如“中研院”、国史馆有审查机制较为严谨外,即使连某些素有声望的基金会也因没有经过考订而出现不该有的错误。这些就牵涉到访谈、整稿者根本没有能力检证受访者所说的是否错误,而不知道错误当然就没有“查证”的问题。说得更清楚点就是访谈者只是谛听者,就受访者的问题谈问题,而没办法提出更深刻的问题。更令人吃惊的是,台湾社会造就不少没有整稿经验的访谈大师,所有稿子只先由助理整,甚至到出版前也不看稿。口述史的出版品其质量良莠不齐自然不在话下。
(二)口述历史是不是历史?一般历史学者认为通过受访者和访谈者所形成的文本,只是众多历史素材的一种,和任何史学数据一样,必须经过考订才能使用,对口述历史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口述历史就是历史本身,尤其若是进行生平式的访谈,那么口述历史就是他口说的传记,因而只要是受访者讲的,就是历史。这乃因不同的学门、训练所造成的不同看法。不过口述历史必须经过考订(即使是受访者本人讲自己的事也会出现错误),方是负责任的做法。
(三)口述历史如何呈现。目前因录像方便,在口述访谈时予以录音、录像,至于要如何呈现,有的人主张不必整成文本,否则因为只要下手整成文字稿,即便是原音重现也未必不失真,何况打散内容、分门别类、重下标题?然而未经整理成文本,则第三者要参阅往往得花相当长的时间,尤其做为某篇文章的重要引注时,除非做成文本,否则别人无法查证;而整成文本可以缩短阅看的时间,但因受访者用母语(不一定是北京话),语言如何转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有整完文稿后是否给对方看过再修改?但若修改、增添而不仅是勘误,则又和录音、录像的内容不尽相同,这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主访者在成稿中做语辞的修订或下注,是否也使口述历史不够“真实”?
(四)口述历史是谁的?受访者的?主访者的?口述访谈的版权属于谁?一般的解释是如果是受访者主动请人采访,并只谈自己想讲的,主访者只是被动谛听依实记录,则版权应属受访者;若是主访者拟订问题、主动邀约受访者,则版权属主访者。然而目前口述史的版权依“中研院”的处理方式是各拥一半,换句话说,此一访谈的成品,双方都各负一半责任,将来如果有法律问题,必须共同负责,主访者难以置身事外。
(五)口述历史不该以出版为唯一的成果展示方式。一般说来,口述史要能出版才能普及,才能显示出成果,但往往访谈稿中有相当私密性或政治性的内容尚须时间沉淀,或者明知内容有误必须查证,却碍于情面勉强出版。我个人认为口述历史不一定非要出版,因为若不经考订而引发法律问题,则有太多后遗症,然则已访谈过后的文本要如何流通,即经口述历史学会的中介,储存在数据库中,只要得到主访、受访者的同意,即可以参阅稿子;如在没有出版压力下从事口述访谈,且不至于因为没有出版而无法提供给需要参考的人使用,则口述历史可以应用的范围将更广。
四、结语
口述历史工作十分辛苦,它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首先是找不到合适的受访者,其次是访谈后因受访者主观性太强、记忆力不佳或批判性强烈,很难整稿,有时又经千辛万苦的整编、查证,却得不到受访者的授权书;或者整好稿后受访者不满意,甚至自己写一份稿以为替代;而出版后若有史实不符或毁谤到第三人,则又要面对法律问题。只有主访者的学养、训练足够,受访者记忆、口才皆好且记录忠实认真,才有可能完成一本好的口述史专著。
台湾的口述历史成果自1953年起即陆续以座谈会会议记录的形式呈现,到2009年上半年累积了5005本,也造就了不少主访者、记录者,更出版了不少相当精彩的口述史成果,不仅成为国民好的阅读刊物,而且在重建家族史、进行区域研究、修志方面也有不少贡献。目前整个口述访谈的风潮历久不衰,虽令人可喜,但是访谈者本人的学养对出版成刊物所要付的法律责任却要严肃面对。台湾有关口述史的进行虽然已注意为弱势者发声,也为带动台湾经济起飞的私人中小企业留下不少史料,更为即将失传的工艺、戏曲的从业人员保留其重要的经历,凡此种种均为可喜的现象,但因缺少针对内容的考订,或进一步探讨口述历史的理论、技艺、方法及与国外的口述历史研究交流,则是还应加强的部分。
选题策划 杨祥银/陈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