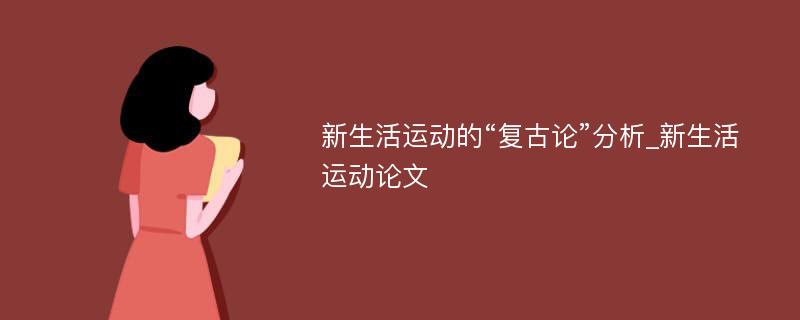
新生活运动“复古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就中华民国史还是蒋介石个人政治生涯来说,新生活运动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对于民国史其他领域,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直到近些年,随着民国史研究地位凸显,由“险学”变成“显学”,随着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整体研究水平的日益提高,新生活运动才逐渐成为史学界关注的话题。从已经问世的各类研究著述看,学界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许多见解读后颇有启迪。但在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笔者认为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很有商榷之必要,提出来求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
迄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新生活运动就其性质来讲,是“一股复古的逆流”;是“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和“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是“利用封建的道德与文化来麻醉人民群众,按照封建的‘礼义廉耻’准则,把全国人民变为四大家族统治下的顺民和奴隶”(注:见宋仲福等:《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王俯民:《蒋介石传》,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版;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笔者权且称此观点为新生活运动“复古论”。
平心而论,视新生活运动为封建复古运动,并非一点没有根据,因为无论从“礼义廉耻”被确立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还是从新运期间全国性尊孔读经逆流的出现来看,新生活运动与封建伦理道德之间的确有着密切联系。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当年说得很明确,“我们所谓新生活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凡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统统要照到我们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道德的习惯来做人”(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1934、3、19),《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第32页。)。现今台湾学者一般也认为,新生活运动其性质“是一种民族文化与道德复兴的运动”(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4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9页。)。但也正如人们所知,新生活运动历时长达15年,期间指导思想、主观意图与具体措施、客观效果之间的不一致性始终交织在一起,情况极为复杂,应作全面具体的分析。
其实,蒋介石等对所谓“固有道德”的热衷并非起于新生活运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传统的国家,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特别是那套等级、尊卑、服从基础上的忠君意识和“四维八德”为核心的伦理纲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久不衰、延绵不绝的重要精神支柱。虽经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封建幽魂总是驱之不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面貌依旧。作为封建买办势力的总代表,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前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十分注重利用封建意识形态维系政权统治。就蒋介石本人来讲,从30年代初开始,他就不断发表文章和演说,在“复兴民族”、“挽救国家”的旗号下鼓吹封建伦理道德。
对于“九·一八”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深刻危机,蒋介石不是从国民党自身找原因,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国民道德堕落,人心不古。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和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是由于老百姓们腐败、堕落,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不肯努力,丧失了固有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是由于“一般人都没有礼、义、廉、耻,都丧失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固有的德性”(注:蒋介石:《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1933、9、20),《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版,第790页。)。在他看来,个人道德的堕落必然导致民族道德的堕落,从而“使国家所赖以生存的东西——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坏,而致国家民族于灭亡”,因此,要抵御外侮,使国家复兴,“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1932、5、23),《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发行,第304页。)。为给自己的谬说寻找理论根据,蒋介石还搬出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作保护伞,称孙中山的思想“即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仁义道德思想”,“三民主义就是从仁义道德中发生出来的”(注: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1931、2),《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617页。)。
基于上述认识,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固有道德”的恢复和发扬,“礼义廉耻”被确立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
“礼义廉耻”作为重要道德规范,最早见于《管子·牧民》,即大家所熟知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当时提出“四维”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实现“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政治目标。封建伦理规范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特别看重“礼义廉耻”,则在于它具有直接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服务的实用性。
早在1932年4月16日国民党“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会上,蒋介石就提出过以“礼义廉耻”挽救人心的观点。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礼义廉耻”在他的文章、演说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对于恢复“礼义廉耻”等固有道德的必要性,蒋介石强调,无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机关,一个家庭以至每一个人,“要向上发展,要成功任何大小事业,都必须依据礼义廉耻的精神”,“这是我们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1934、3、5),《革命文献》第68辑,第24页。)。他还举日本、德国、意大利为例,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他甚至认定,在当时外敌入侵、国难日急的情况下,只要“礼义廉耻”这套东西能够恢复,“国家便可以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1934、3、19),《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第32页。)。宋美龄则认为,新生活运动致力复兴的“礼义廉耻”四种旧道德,“是提高人格的主要条件”,“是我国最可宝贵的美德,也就是中国立国的精神基础”(注:宋美龄:《新生活运动》(1936),《革命文献》第68辑,第109页。)。为证明恢复“礼义廉耻”生活的合理性,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干事的贺衷寒将新生活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这样的对比:“‘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像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过来”;而“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新生活运动,完全是那样绝对不同的东西”(注: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1934、2、26),《新生活月刊》(山东)第1卷创刊号。)。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新生活运动的保守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以“新”标榜的新生活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同时这也是新生活运动发动伊始,尊孔读经逆流接踵而至的原因所在。
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就已开始,但以政府名义在全国公开号召尊孔读经,是新生活运动发起以后的事情。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恢复祭孔(注: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发行,第371页。)。同年7月间,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于当年8月27日举行孔诞纪念活动。此后1935年和1936年,全国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祭孔活动。针对蒋介石集团把新生活运动说成是“救亡复兴的根本途径”,以及大搞复古尊孔的倒行逆施,舆论界曾予以尖锐批评。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同年9月《东方杂志》署名文章指出:“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中国的文化确有种种的特长,惟与西方各国来周旋,那根本无法可以抵抗他们的强力。所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条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国粹,而在怎样吸收一种文化使我们能抵抗他们的武力和经济侵略”(注:吴泽霖:《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胡适则把蒋介石集团导演的尊孔闹剧讥讽为“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可恕的;但在一个现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注: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独立评论》第117号。)。
上述情况说明,新生活运动与封建思想文化确有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内在联系。蒋介石集团通过发动新生活运动,尤其是着力倡导“四维八德”之类的封建伦理纲常,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统治服务,当为不争的事实。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复古论”有其一定道理。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生活运动在其实施过程中,除求助于传统道德、封建礼教外,也曾直接吸收和借鉴了当代西方国家的一些具体做法,制定了不少符合现代社会文明要求的生活目标和行为标准,从而派生出了改良社会习俗、提高国民生活素质和文明程度的积极功效,被后人称为“生活改造运动”。这一情况的出现,原因很复杂。
蒋介石等懂得,要稳固统治地位,必须借助于“礼义廉耻”之类的封建礼教,重新抬出孔夫子的牌位,但这并非易事。因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到了30年代,孔孟儒学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已没有太多的市场。因而需通过某种现实途径自上而下不断灌输,潜移默化,使人人都能“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前面提到,在蒋介石集团看来,国家危亡、民族衰弱的主要根源在于所谓“民族性的丧失”和“民族精神的堕落”,而民族性丧失、民族精神堕落的原因“又是由于构成民族分子的国民腐败,懒惰,苟且偷安,自私自利,不肯努力”。认为近代以来包括“九·一八”在内的一次次失败,“不是外国的军队打败的,也不是外国的兵舰、飞机打败的,而是自己不如人家,大家过的都是不合新时代的旧生活,所以才有失败(注: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1934、2、26),《新生活月刊》(山东)第1卷创刊号。)。这才引出“新生活”取代“旧生活”的必要性。基于这一逻辑,蒋介石手订之《新生活运动纲要》开宗明义指出:“新生活运动者,我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纲要还提到,新生活运动是一种“转移风气”的工作,“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这种工作“其力较政教为尤大,其用较政教为尤广,而其需要亦较政教为尤急也”(注:见《革命文献》第68辑,第1、3、4页。)。那么,怎样才能“转移风气”、实现“生活革命”呢?按照蒋介石的设计,须从国民最基本的生活即“食衣住行”的改造入手,“要使全体国民,凡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统统要照到我们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道德的习惯来做人。简言之,就是根据中国固有道德的习惯,来决定人人所必须的日常生活行动,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并没有旁的新花样”(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1934、3、19),《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第32页。)。如此方能“挽救国家,复兴民族”。
本着上述指导思想,新生活运动期间确实出台了不少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生活改良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新生活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总部先后设在南昌和南京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简称新运总会),会长和指导长分别由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担任。根据安排,新生活运动内容主要包括“经常中心工作”和“季节中心工作”两大类及其他相关活动。
“经常中心工作”指规矩与清洁运动。根据新运总会的解释,规矩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礼貌仪容、行为态度、社会秩序、办事条理等,要求做到服装整齐,珍惜时间,习礼义,守规矩等。目的在于矫正一般言语粗暴、行为鄙野、服装怪异、日用奢华、办事凌乱、秩序纷扰等现象,以养成重礼义守规矩的良好习惯,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和有条不紊的办事方法。清洁运动的内容分个人家庭和公共场所两方面。个人方面要求做到衣服整洁,食物清净,勤洗手脸,勤洗衣服,不随地吐痰等;家庭方面要求做到庭院洒扫,居室、厨房及饮食用具、雇佣工保持清洁等;社会方面要求车站、码头、公园、澡堂、饭馆、娱乐场所等保持清洁、灭蝇灭蚊等。据报导,当时南昌及各地新运促进会开展规矩、清洁运动比较认真,造成了很大声势,在南昌,市容“整齐清洁”,街道上很少有人吸烟、打赤膊或不扣纽扣,“街道特别清洁,店后或住宅之后,已无垃圾堆积”(注:HOlling·K·Tong:《新生活运动已有良好之进展》,1934年9月8日,上海《大陆报》。)。在新生活运动头一年里,规矩与清洁运动几乎成了新生活运动的代名词,是蒋介石集团最引以为骄傲的一项新运业绩。
“季节中心工作”包括春季植树、夏季卫生、秋季节约、冬季救济四项内容,1936年起正式推出。其中春季植树、冬季救济两项因各种原因“未及实施”,真正进行的是夏季卫生和秋季节约运动。据统计,从1936年5月20日到8月20日的卫生运动期间,全国共有473813人注射了防疫针,种痘人数129516人,清毒水井10839口,推广自来水用户6273家,消毒厕所4931处,整理沟渠928处,清理池塘774处,举行大扫除306次(注:见《二十五年度本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期。)。节约运动方面,主要实施项目为惜时、节用、爱物、乐业四项。惜时方面,提倡早睡早起,严守工作及约会时间,劝禁类似赌博的娱乐等;节用方面,费用俭省,馈赠酬答勿奢华等;爱物方面,要求爱惜公物,利用废物,提倡国货等;乐业方面,主张提高一般人对于职业的兴趣,闲暇时加入劳动服务团,从事筑路、造林、修堤及其他公共事业等(注:详见钱大均:《本会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新运导报》第2期。)。这项活动开始后,许多地方组织了节约运动委员会,按宣传、推行、检查的步骤开展工作,南京、浙江、广东、四川、安徽等省市执行比较认真。此外像劳动服务运动、推行“三化”(即生活的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方案、改革习俗运动、乡村服务工作等也都形成一定规模。
1934年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颁布过一个题为《新生活运动须知》的小册子,从不同侧面对“新生活”的标准作了界定,其内容对我们认识和了解新生活运动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礼貌方面,要求对于子孺要起让,集会场所要脱帽,公共场所不要叫喊、高声谈笑,不要酗酒,不要扰乱别人的作业等;整齐方面,强调衣服要整齐,纽扣要扣好,帽子要戴正,鞋子要穿好等;清洁方面,要求脸手要洗干净,要常常洗澡,不要随地吐痰或小便,墙壁不要胡乱涂贴等;守法方面,要求遵守国家法律,遵守公共秩序,遵行公民义务,不循私情不做伪证等;坚忍方面,主张做事要有毅力,失败不灰心;仁爱方面,提倡爱护生物,救护残废贫弱的人,爱惜公物;俭朴方面,提倡不浪费金钱,不作无谓应酬,婚丧喜庆要简省;廉洁方面,要求不接受贿赂,不接受公务关系的馈赠,不拿公家的物品来作私用,不舞弊不贪污等;名誉方面,要求不忘国耻,不要嫖赌,不要吸鸦片等(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4册,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6-2082页。)。
上述体现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系列做法和规定,并不只是为了装装门面,作为实施程序和步骤,实际构成新生活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其中有不少最后未能真正得到贯彻,但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无疑应当肯定。由此我们也可得出结论,把新生活运动简单定性为“复古逆流”和“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是说不通的。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中,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需要,蒋介石集团在鼓吹封建礼教的同时,也推出许多带有社会改良意义的举措,这一点是新生活运动“复古论”者们往往容易忽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