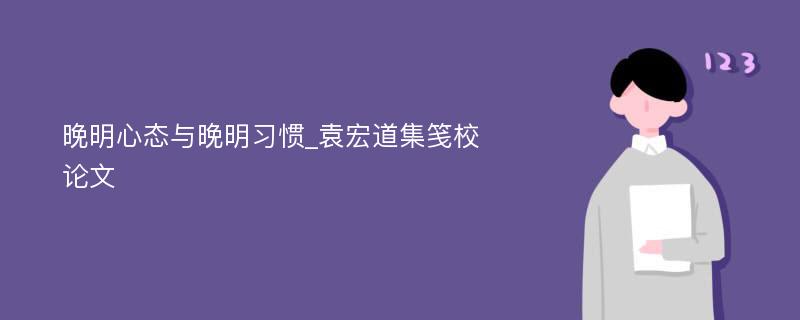
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气论文,明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总目》曾在论及明代士风变化时总结说:“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卷一三二“杂家类”存目)这段话固然反映出《四库》馆臣对于晚明士风与文风因轻蔑而略有偏颇的态度,但它指出晚明社会风气与文人思想的特点以及当时“小品日增,卮言叠煽”这种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历史氛围,却是相当准确的。因此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晚明小品可以说是我们认识晚明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个性的形象资料。
一
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自从宋代以后,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许多文人以儒学的圣人人格作为人生修养所追求的目标,力求获得尽善尽美的人格。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在他们看来,有弱点有缺陷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优点。张大复有《病》一文说:
木之有瘿,石之有鸲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传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吾每与圆熟之人处,则胶舌不能言;与鹜时者处,则唾;与迂癖者处则忘;至于歌谑巧捷之长,无所不处,亦无所不忘。盖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怜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梅花草堂笔谈》卷三)
所谓“病”就是超越正态、世俗、平庸、乡愿的“真”和“奇”,“病”者,才有特点,有个性,有锋芒,才有出类拔萃之处。故“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张大复如此多病,可谓“大佳”了。张大复这种观念非常有代表性,晚明人喜欢不同常态的“病”“癖”“痴”“狂”,故抱怨“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
有“病”,才有个性,有情趣,有锋芒,有不同世俗之处。这是晚明文人普遍的看法,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书》中认为:“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林和靖对于梅,米芾对于石,都有一种痴迷执着的爱恋之情,故成名士。因有“殊癖”才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有忘乎一切的执着之情。同样,张岱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琅嬛文集》卷四《五异人传》)“无癖”“无疵”之人不可作为朋友交往,因为他们缺少“深情”“真气”。晚明人推崇的是突出而又真实的个性,“癖”与“疵”其实就是那种不受世俗影响,没有世故之态的人格。人有“癖”有“疵”,才有执着的深情和真实的个性。蚌病成珠,文人之“病”则成为一种不同世俗的情致。晚明程羽文在《清闲供》的“刺约六”中详细论及文人的六种“病”以及这些“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六种“病”是癖、狂、懒、痴、拙、傲: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吟发生歧,呕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鹤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颇颇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风雨惊,啸长而天地窄。病可原也。
三曰懒。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病可原也。
四曰痴。春去诗惜,秋来赋悲。闻解佩而踟踌,听坠钗而惝恍。粉残脂剩,尽招青冢之魂;色艳香娇,愿结蓝桥之眷。病可原也。
五曰拙。学黜妖娆,才工软款。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悬孺子半榻,独卧元龙一楼。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病可原也。(《香艳丛书》三集卷二)
他们不理生计,不修边幅,傲对权贵,蔑视众生,多愁善感,行为古怪。这些“病”,其实正是文人名士的个性和习气。他们的感情与脾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方法,都与正常的俗人俗事不同。不同于世人,故称“病”。文人的生活情趣,都是由这种种“病”所生发的。有了病,才有诗意,才有意趣,才有不同寻常之处,这里所写,也正是对于种种“病”的赞歌。
晚明文人的精神受到当时思想界风气的浸染,他们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学的影子。王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而盛行于晚明,这种理论强调人的意识、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主张内省,由程朱的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反传统的精神。这种理论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吹进了清新的空气,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儒与禅,原来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自宋元以来,儒学本身受到禅学的更多影响。尤其陆九渊、王阳明一派,更是与禅宗有血肉关系。“狂禅”之风恰是从陆王的“心学”那里来的。不过,陆王“心学”的理论归宿是正心诚意,而到了李贽等人,则主要发扬了禅的诃祖骂佛的反传统精神,对于传统道德、儒学权威等等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蔑视一切世间礼法。他们的风格狂放执着,惊世骇俗,其思想行为对于传统的伦理纲常与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破坏性,故人们称之为“狂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论及“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明中叶之后,文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形成一种个性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如祝允明、唐寅等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对晚明文人有极大的影响。袁宏道曾赠给张幼于一首诗,诗中有“誉起为颠狂”之语,大概张幼于对“颠狂”二字的评价不满,袁宏道给他写了一信,信中说,“颠狂”两个字,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词:“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他引经据典来说明颠与狂的价值:“狂为仲丘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求之儒,有米颠焉。”实际上,孔子并不推崇“狂”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都违背了中庸之道,偏于一面,过于偏激。中郎借用孔子大旗来高度评价了“颠狂”的品格,接着说:“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张幼于》)可见“颠狂”不但是晚明文人喜欢的人品,而且是一种推崇的理想。
二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便宜。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
清供、清玩、清赏这类生活情趣,自宋代以后就开始了,如宋代的林洪就著有《山家清供》《山家清事》一类的书,但到了晚明,清玩清赏清供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就像沈仕《林下盟》中所说的,当时文人日常生活的“十供”是:“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奕棋。”(《说郛续》卷二十八)费元禄说士人的“游道”有三,即“天”“神”“人”,其中人的游道是“抗志绝俗,玩物采真”。(《晁采清课》)在晚明人看来,玩物不但没有“丧志”,而且能够“采真”,所谓“采真”就是获得人生的真谛。“玩物采真”四个字言简意赅地反映出晚明人清玩清赏的哲学。所谓清供、清玩和清赏其本质便是把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艺术化,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或寻找一种古雅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从山水园林、风花雪月、楼台馆阁,乃至膳食酒茶、文房四宝、草木虫鱼、博弈游戏、器物珍玩等事物上,获取清玩清赏的文化精神。晚明这类书籍很多,如屠隆的《考槃余事》、《山斋清供笺》、高濂《燕闲清赏笺》、陈继儒《岩栖幽事》、王象晋《清寤斋心赏编》、文震亨《长物志》、《清斋位置》等。
生活环境有多种多样,有在山水之间者,有在乡村者,有在远离车马的郊居者,但对于多数的士人来说,其生活环境却是“混迹廛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世俗生活也越来越喧嚣。于是,有必要在“廛市”中营造一个优雅清静的艺术环境,像陶潜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以清言的形式非常精辟地谈论说:“幽居虽非绝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对之事,似出世外。”于是人们大可不必车船劳顿,或艰难跋涉去游山玩水,寻幽访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自己的庭院、台阁、居室,水石、草木、蔬菜、门窗阶栏、书画古玩、坐几椅榻、车舟等等,都可以构成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比山水园林,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平和,也更为温馨,是人们最为寻常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生活环境。这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美学意识。
程羽文的《清闲供》是一部相当细致和别致地表现文人日常生活艺术的小品文。《清闲供》中的“小蓬莱”条说,蓬莱之所以是仙境,因为它虽处俗世,却隔谢了人世间的嚣尘浊土。对于士人而言,心远地自偏,“即尘土亦自有迥绝之场,正不必侈口白云乡也”。关键是自己建构一个清逸宁静的生活环境,下面便是程羽文对于生活环境的一些标准:
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桥,桥欲危。桥边有树,树欲高。树阴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细。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宽。圃中有鹤,鹤欲舞。鹤报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归。(《香艳丛书》三集卷二)
在这里,程羽文别出心裁地用顶针的修辞方式来写,这并非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体现了一种美学观念,即以这种环环相扣的语言建构了一个诸种要素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大体上构成了一幅当时文人理想的生活场景,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的生活美学观念: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与大自然的融合,以体现一种清雅的情调。
晚明有不少关于文人清玩的小品。所谓清玩,主要是指古钟鼎彝器、书画、石印、镌刻、窑器、漆器、琴、剑、镜、砚等。屠隆《考槃余事》一书中讲述了对于书版碑帖、书画琴纸、笔砚炉瓶和日用的器用服饰之物的鉴赏艺术。而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论骨董的类别、特点、形态和品赏方法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人们古玩清赏的文化分析。他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声色臭味之好,“故人情到富贵之地,必求珠宝锦绣、粉白黛绿、丝管羽毛、娇歌艳舞、嘉馐珍馔、异香奇臭,焚膏继晷,穷日夜之精神,耽乐无节,不复知有他好”。于是人们逐渐厌倦了这些新声艳色。“故浓艳之极,必趋平淡;热闹当场,忽思清虚。”他的结论是“好骨董,乃好声色之余也。”(《五说》)这是说,品鉴古玩,是为了在声色之外,找到一处清虚之地。所以品赏古玩也是一种闲适的人生修养,也可以进德修身,而且“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总之“有却病延年之助”。他认为,清玩的目的是“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是这种清玩便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意义。
晚明小品反映出文人们矛盾的生活倾向,一方面,他们鼓吹清心去欲,绝尘去俗,但另一方面追求声色极欲之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矛盾并存于晚明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中。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一信中描写了他心目中人生的真正幸福: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妇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龚惟长先生》)
陆云龙在翠娱阁选本中评此文说:“穷欢极乐,可比《七发》。”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之中,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如此直率,如此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鼓吹这种“恬不知耻”的生活理想。然而在晚明,这种放纵声色的生活,决不是“耻”,而是一种雅兴和荣耀。穷奢极欲、声色犬马、恬不知耻等,这些传统语言中的贬义词到了中郎笔下,却成了不可多得的褒义词。词义褒贬的转换意味着价值观的历史转换。中郎此牍,尽管加以艺术化与夸张,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出许多晚明文人的心声:人生就是充分地、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乐趣,尽可能地满足人的心灵与感官的所有欲望。在这里,中郎为晚明文人描绘了一幅生活理想的蓝图,它不但是对名教礼法的反叛,对中国传统文人那种重道义、重操持、自强不息的人格理想的一种背离,同时也是对陶潜式清高澹泊的隐逸之风的嘲弄。
中郎式的“穷欢极乐”的生活方式与晚明的社会潮流是一致的。张大复在《闻雁斋笔谈》中《戏书》二则也同样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理想:“一卷书,一麈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此处与袁宏道的《答林下先生》一文所写的五种“真乐”何其相似。这是当时文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普遍追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与精神的满足,向往着人生自由化与生活艺术化的理想,这种追求当然反映的是士大夫和贵族化的雅趣。张岱《自为墓志铭》说他少年时“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马,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琅嬛文集》卷之五)。从这真率得肆无忌惮的表白来看,说他们是一帮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大玩家”,恐怕正是他们乐于接受的雅号。
三
鲁迅先生曾在《杂谈小品文》中谈到明清小品有“赋得性灵”的特点,就是把“性灵”当作新的八股,为了表现“性灵”而制造“性灵”,敷衍“性灵”,鲁迅先生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明清小品的局限性。“性灵”本是与格套针锋相对的,但由于大多小品作者一味抒写性灵,性灵遂成为新的格套窠臼。从“独抒性灵”到“赋得性灵”,是晚明一些小品发展的艺术轨迹。
晚明小品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有时真率到喜欢自我暴露。如袁小修在《游高梁桥记》中检讨自己:“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珂雪斋集》卷之十二)检讨自己对于仕途的追求过分执着而成无耻。而《心律》更是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文中以佛家的十善十恶之说,进行反思。这十恶是: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五两舌;六恶口;七绮语;八贪欲;九嗔怒;十邪见。小修以虔诚的态度逐一用来对照自己的生活,恐怕在中国古代很少写得如此坦白的文章了。如他写到自己犯了“邪淫”之过,他承认自己冶游嫖娼,喜欢同性恋的劣迹,有改过之心而无坚持的意志。又如《心律》自我剖析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追思我自婴世网以来,止除睡着不作梦时,或忘却功名了也。”明人功名心炽热,却普遍喜欢自鸣清高,小修倒是相当老实坦率地承认自己功名心之强烈。他说自己对于功名,日思夜想,梦中也想,所以除了睡着不做梦时,才有片刻忘却“功名”二字。《心律》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的《忏悔录》。此外他在《答钱受之》信中也说:“自念生平无一事不被酒误,学道无成,读书不多,名行不立,皆此物为之祟也。甚者乘兴大饮后,兼之纵欲,因而发病,几不保躯命。”(《珂雪斋集》卷之二十四)像袁小修这种小品可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晚明文人的心态。
“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作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于是便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真”也就变味了。一些晚明小品作家所追求的雅人高致,因时代的关系,常常给人以一种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之感;而过分的清高自赏、自我表现,又容易“雅”极而俗,“真”而不挚,或弄“真”成假。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批评的晚明一些文人的通病是“矫言雅尚,反增俗态”。(卷一二三《长物志》提要)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局限。晚明小品在自由地抒发个性,真实地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世界方面,比传统古文更为灵活自如。抒发性灵,当然是文学创作题中应有之义;然“性灵”二字,固然重要,文学表现的对象却绝不止于此。若“独”抒性灵而不及其它,则窄矣。闲适固然也令人向往,但这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而绝不是一切。晚明的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是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而“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刘勰语),则几乎可以用来品评晚明许多名士的小品文。晚明小品的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不少晚明文人喜欢过分夸耀清高。不用说像陈眉公那样“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而像袁宏道那样过分渲染对于官场的厌恶,也多少有点虚情假意。在中郎的作品尤其是前期作品中,一个颇为集中的话题便是谈论当官之苦,这类作品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其尺牍更是常谈到做官之苦: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袁宏道集笺校》卷五《沈广乘》)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丘长孺》)
在这里,中郎夸张地把当官作为天下最痛苦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不做官,却与兄弟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但不久又辞官离职,游览江南佳山水。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但两年后又解官回乡,著书游览;万历三十四年,又入京补仪曹主事,但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后又迁稽勋郎中,最终还是请假归乡定居。历史上,像他这样屡官屡辞,屡辞屡官,屡辞屡迁的实在少见!辞官时截钉斩铁,似乎作官是天下最为痛苦的事,一刻也难以呆下去;但事过情迁,不久又还是照当不误。中郎的那些大叹当官苦的作品,偶尔读之,妙不可言;但他的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又不免过于渲染和夸张,他本人经历了辞官与任官的多次反复,有时其情感便不免显得有些轻浮,有些造作。
从艺术表现上看,许多晚明小品作家过于注意自己感情的细漪,却极少关注到外界社会的巨澜。如俞琬纶的一些小品,感情极为纤巧。他写的《祭桃影》《诔双梧》(《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七),悼念两棵死去的桃树与梧桐树,这些作品虽不可说纯然是嘲风弄月之作,文中也寄托某种感情,但这类文章多了,就叫人觉得有一种文人的酸气。又如他的《祭半齿文》,这篇小品是为了自己被蛀掉的半个牙齿而写,这里所包含的感情,难说是无病呻吟,但却有小病大吟之嫌。
晚明小品反映出晚明人风趣与儇薄的双重性,文章的风趣与儇薄之间有十分微妙的差别,风趣若稍过度便成为佻薄。如张应文《张氏藏书》的《箪瓢乐》中有一篇叫《粥经》的文章,内容是写吃稀饭的。全文摹仿《论语》的口气写成,如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而张应文的《粥经》则摹拟道:“小子何莫吃夫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腥,可以素。暑之代茶,寒之代酒,通行于富贵贫贱之人。”“子谓伯鱼曰:汝吃朝粥夜粥矣乎?人而不吃朝粥夜粥,其犹抱空腹而立也与。”全文生剥孔子,且不说这是对于儒家经典的大不敬,而行文轻佻,戏谑而成俗趣。再举一例。宋懋澄在《与家二兄》一札中在谈到自己的读书兴趣时说:“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九龠别集》卷之一)这里全是比喻,以经为妻,以史为妾,以稗为奴,以佛道为客。但日夕相处,最有感情的还是诗文辞赋一类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就像“外宅儿”非正式夫妻关系而与之同居的妇女(大概类似于情妇)。俗话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宋懋澄用明媒正娶的妻、妾比喻经史,而以婚外偷情的“外宅儿”比喻文学艺术,自然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倾心和偏爱。这比喻当然是相当新巧奇特,也比较幽默和风趣。但细细品味,总觉得相比之下宋懋澄的口吻新奇风趣但未免显得轻佻。虽然比喻毕竟只是比喻,不必求实,但它又的确折射了男权中心社会中封建文人的享受心态和猎艳口味。又如宋懋澄的尺牍《与白大》说:“我于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癖;譬如黄鸟,山中逢鲜荫木,辄税羽施声,须臾便翻然数岭,心境两忘。”(《九龠别集》卷之二)这种似乎风趣、潇洒而实际未免轻佻的口吻在晚明是相当普遍的。
晚明出现大量的艳情小品。如梅史的《燕都妓品》用科举取士的方式,来排列燕都妓女的等级,如状元郝筠、榜眼陈桂、探花李增等,并分别摘录唐诗和《世说新语》的名句加以品评。此外如潘之恒的《金陵妓品》、曹大章的《莲台仙会品》、《秦淮士女表》、萍乡花史的《金陵女士殿最》等,这些作品的情趣不能一概而论,但都颇能反映出当时文人的兴趣。最能代表晚明文人心态的是卫泳《悦容编》中《招隐》和《达观》二篇。古人说,小隐隐山林,大隐隐朝市,此外古人也有隐于书者,隐于吏者,隐于酒者,而卫泳《招隐》则匠心独运,开辟了隐的另一大途径,这就是隐于色。他认为色是最适宜隐的,人们一见美色冶容,名利心便都淡了,于是名缰利锁顿可挣脱。那些整天营营于名利场上的人,就因为他们胸中没有这种癖好,精神没有寄托。而英雄豪杰,有一个红粉佳人,便可以把臂入林,所以女色冶容可以让人忘却世事,这便达到隐居的目的。相比之下,那些寻找神仙者,禁欲寡欲者,或跑到深山去隐居者,那些隐居方法真笨,根本不能与隐于色的方式相比。美色,本身就是“桃源”,逃到里头,便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不是最好的隐居吗?“招隐”一词在古代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征召隐士出山,另一种是招人归隐,意思恰恰相反。卫泳当然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公开号召人们隐居到女色之中。《达观》一篇是晚明文人的“好色”宣言。这篇文章先是批驳好色有害的各种观点。先驳好色误国论,次驳好色妨德论,再驳好色伤生论。卫泳的结论是,好色不但无害,而且意义重大。“可以保身,可以乐天,可以忘忧,可以尽年”,加上《招隐》上说的,好色还可以隐,那么好色便应该成为人生修养的最佳必修课了,也就成为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修养了。中国古人总喜欢以女色为女祸,把历史上许多国破家亡的悲剧原因归结为女色作祟,卫泳的《达观》反其道而行之,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矫枉意义,但他把好色的益处提高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其本质也是为纵欲造足舆论的。卫泳的所谓“招隐”“达观”,即是把“色”与“隐”两者融合起来。既纵色欲,又可高隐;既快欲望,又可养生。鱼与熊掌,兼而得之,这样便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为了一个“高雅”的目的而放纵。
对晚明文人酷爱声色应作具体的分析,一方面当时有些文人可能是以纵情声色的方式来发泄苦闷和绝望,正如袁中道在《殷生当歌集小序》中说:“丈夫心力强盛时,既无所短长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块不平之气,古之文人皆然。”(《珂雪斋文集》卷之十)而钟惺《吴门悼王亦房》诗中说:“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隐秀轩集》卷第一三)恣情声色与恣情山水一样,也可以是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排遣方式。其中亦有一些文人确是借醇酒妇人来发泄精神上的苦闷,但多数只不过是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爱好,但他们往往以相当高雅的理由和理论来为自己解脱,以堂皇的借口巧饰渔色纵欲的放荡行径。曾异撰在《卓珂月〈蕊渊〉〈蟾台〉二集序》中说,他认为同是纵情声色,晚明人与古人是有所不同的,古代的英雄“则借以行其痛哭而消泄其无可如何之感愤”;而当时人却是“以为是得志而不可不为之乐事”(《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五)。
四
晚明文人复杂的心态与习气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晚明时代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崩溃,文人思想自由、行为放纵,但是政治的黑暗、功名的束缚与物欲的压迫同时又是相当严重。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行为的压抑两者矛盾相兼并存的特殊社会环境,导致晚明文人产生复杂与异常的心态。
由于程朱理学的衰落晚明文人思想相当活跃。程朱理学的初衷是要弘扬一种大同、和谐、亲情、友情的文化理想,弘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因此它注重人性的崇高和理性意志,追求理性升华。然而它一旦成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工具,也就逐渐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心学代替了理学,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的衰亡,不但对于统治者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引起人们强烈的幻灭感,人们否定了程朱理学的理性意志,并竭力消除了它的约束,必然带来感性和生理自然欲望方面的膨胀,因此整个社会风气正如张瀚所说的“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松窗梦语》卷七)
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在晚明小品中也同样反映出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
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冯梦龙则更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真”,他说:“古今来原无真可认也,无真可认,吾但有笑而已矣;无真可认,而强欲认真,吾益有笑而已矣。”(《古今笑自叙》)他还说:“碗大一片赤县神州,纵生塞满,原属假合,若复件件认真,争竞何已?”(《古今谭概·痴绝部序》)既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人生又何必那么认真呢?这种观念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了。
在这个封建晚期与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他们悠然的外表仍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正如黄汝亨《复吴用修》描绘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地,正是晚明文人理想的人格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冲突:一方面追求超越世俗的精神愉悦;一方面又处处摆脱不了人间物质需求和名利的羁绊。“两境递进,终归扰扰,半是阿堵小贼坐困英雄耳!”(《寓林集》卷二十四)自古以来,文人贫穷似乎成为天经地义,文人不但习惯,而且君子固穷,以之为荣,但在晚明这个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人欲横流的时代,清高的文人们时时遭受“阿堵小贼”的威胁,所以不免“终归扰扰”,难以保持内心的平衡。痛苦、烦躁、忧愁,对于生活的强烈欲望和难以实现的矛盾,造成晚明文人心灵的焦灼。
明代的八股取士对于文人的心态影响也是极大的。晚明的风气是个性的放纵,而八股恰好是最束缚个性与思想的一种文体。明人拿起八股文便要装出圣人道貌岸然的腔调,放下八股又露出放纵恣肆的文人习气,晚明人奔突于这两者之间,这种境地容易造成文人人格的两重性。晚明文人对于八股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他们既厌恶、轻蔑八股,但八股文又是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为了前途和生计,只好无奈地走上科举之路。于是大多文人读书的目的便是博取功名,正如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之十三所说:“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科举在当时也是一种社会对于文人的一种价值标准,袁中道中进士以后备选时写了一封《与梅长公书》:“看来世间自有一种世外之情,毕竟与世间应酬不来,弟才入仕途,已觉不堪矣。荣途无涯,年寿有限,弟自谓了却头巾债,足矣,足矣。升沉总不问也。”(《珂雪斋集》卷之二十五)从尺牍中流露的思想看,似乎科举是文人一生应该偿还的“债务”,文人奋斗的目的便是为了“了却头巾债”,他们的心态十分复杂,既悲哀,又无奈。
傅占衡的《吴、陈二子选文糊壁记》是一篇对于明代八股取士制度一种冷峻反思的作品(《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他以偶然看到二位旧友青年时为了准备科举考试的八股范文,如今被人用以糊壁御寒的事入手,沉痛地揭露科举制度对于当时士子的残害。二位文友曾与作者一起潜心研究八股文,但一位“飘零海上”,一位不能葬父,不能养母,自己也无家可归,他们的下场何其悲惨!文章也反映出八股文的本质,虽盛极一时,“房如蝶,社如蝗”,然八股文却是“不能丰稼穑,饱邦民”,“上不能当一城一堡之冲,次不足备一箭一炮之用,最下不可言”,可说是百无一用。作者日夕对着旧友抄录的八股文,“虽哑然笑而犹时郁然思也”,作者并非对这种现象作一般性的嘲笑,而是从根本上表示了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对受八股之害的文人深切的同情。作者最后说,这两位文友的八股文被人用来糊壁,终究发挥了某种作用,这其实还是幸事,因为它还不至于“以所学添祸人国”。从此看来,八股文不但无益,而且那些因八股文而高中入选,步上仕途者还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
曾异撰在《卓珂月〈蕊渊〉〈蟾台〉二集序》中激愤地指出:“今天下之人才,帖括养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国家,亦帖括撑持之国家也。吾观三岁取士,名为收天下豪俊,当事者舍经义而外弗阅。再三试闱牍,偶有通达慷慨之士,不以为触犯忌讳而不敢收,则谓是淹滞老生,反不如疏浅寡学者。”当时天下的人才,只不过是八股文养成的人才,而国家则是由八股文支撑着的国家。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因此他认为士人生于科举取士之时是一种“不幸”。(《明文海》二百五十五)在《答陈石丈》一信中,他又说:每次读科举之文,就不免感叹久之。他非常羡慕司马迁、杜甫诸君,因为他们用不着写八股文。他还夸口说,假如我无科举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然不能胜过他们,亦未必尽出其下。接着,他又写出自己矛盾心情:既想走仕途,但又明白写八股文纯粹是浪费时间精力的事。这种心情相当矛盾,“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这是时代给文人出了一个必须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回答的“极难题目”。(《尺牍新钞》卷一)无拘无束地思想、自由自在地抒发实感真情与现实生活中的名缰利锁之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在《与丘小鲁》一牍中,再次吐露了自己复杂与痛苦的心曲:
私念我辈,既用帖括应制,正如网中鱼鸟,度无脱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盎,蓄之樊笼,虽不有林壑之乐,犹庶几苟全鳞羽,得为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跃,几幸决网而出,其力愈大,其缚愈急,必至摧鳍损毛,只增窘苦。(《尺牍新钞》卷一)
这里说的是八股取士的制度为文人造成两难的困境,然而推之其它,何尝不是如此?文人们只是封建制度的“网中鱼鸟”,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顺从,那样能换来安全与适然,却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要么反抗,冲出樊笼,去追求个性的高扬,而那样又绝不可能成功,“必至摧鳍损毛”。曾异撰感觉到自己“缚急力倦,正不知出脱何时”。他自己一辈子的精神,大都消耗于此。在此之前,很少人对这种悲哀表达得如此真切。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周作人曾说过,小品文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近代散文抄〉序》)此语意味深长。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然而也反映出晚明某些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在我们看来,今天读者在阅读晚明文学时对于当时文人的心态与习气需要的首先不是欣赏,也不是指责,而是深切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