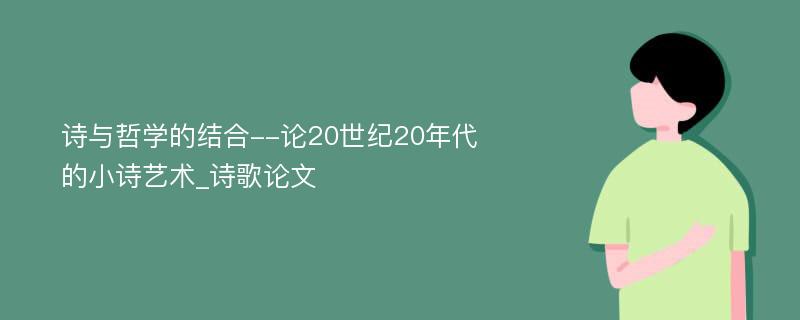
诗与哲理的遇合——二十年代小诗艺术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诗论文,哲理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的小诗以抒情写理为多,但其中又以写理为重。小诗的哲理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从对自然、人生的感悟中迸射出来的思想火花。冰心的小诗多表现自己内省的沉思和灵感的顿悟;宗白华的小诗多以哲学家的智慧和胸怀去把握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由于哲理与小诗的密切联系,并形成潮流,因而人们又把小诗派称为哲理诗派。小诗与哲理的成功结合,对于新诗是一种突破、一种创造。而小诗在内容与形式上所存在的种种弱点,则影响和限制了它的发展。
关键词 小诗的流行 小诗与哲理 小诗的中衰
梁实秋说过,“五四”时期“最流行的诗是‘自由诗’,和所谓的‘小诗’,这是两种最像白话的诗。”[①]实际上,“小诗”也是“自由诗”,只不过它作为一种“变异”的新诗形式,在1921年到1923年间的诗坛颇为盛行,以致被人们称作“小诗流行的时代”。
一、新诗坛上的宠儿
小诗随新诗一同诞生,在早期白话诗歌中,就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等写的小诗。不过,那时小诗的声音还很微弱。但到了1921年,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写起小诗来了。小诗跨越了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形成一种比较广泛的诗歌运动。确定小诗美学规范的是周作人、朱自清。文研会的冰心、朱自清、郭绍虞、徐玉诺、王统照、周作人、郑振铎、刘大白,创造社的郭沫若、邓均吾;湖畔诗派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此外还有宗白华、俞平伯、康白情、何植三等,都是小诗作者。由于众多诗人的推涌,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新诗坛上的宠儿”[②]。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其他许多诗人的诗集中也包含不少小诗作品,其中成绩最好、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宗白华。是他们把小诗创作推向高潮,奠定了中国新诗这种独特形式的艺术基础。
小诗之盛行,既是时代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也是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白话新诗的“尝试”运动为新诗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文研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诗歌进一步完善了新诗的诗质与诗形,以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为新诗的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奠基石。新诗已历史地完成了从旧诗到新诗的变革。但人们觉得文研会的现实主义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初期白话新诗缺少“余香和回味”的流弊,“女神”体虽擅长抒发火山迸发般的激情,但又有形式过于自由散漫,情感一览无余的毛病。于是,人们觉得诗坛应该有一种短小简炼、富于诗味的诗体来弥补诗坛的不足。正如周作人所说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感兴,自然便有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的小诗之需要。”[③]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情感“像电光的一闪,像燕子的疾飞”,[④]这种生活中真实、常见的瞬间即逝的情感用短可一行、长可三五行、七八行的小诗去表现再好不过。并且中国诗人向来喜欢短诗,中国诗人通常热衷于捕捉一个景色、一种情绪、一种境界的神髓,而不喜欢描绘五花八门的现象。因而,小诗的文体优势能够普遍满足人们抒情言志的需要,能够适应人们的某种审美心理定势。“五四”高潮期,像“女神”那洪钟般的巨响与写实主义的沉重叹息固然是诗坛的主色调,而“五四”退潮以后,由于社会的黑暗,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苦闷与彷徨,他们由感情的亢奋转向冷静的沉思,对社会、对人生勤于思考,敏于感受,偶有感兴,发而为诗;三言两语,道出某种哲理,写出某种感触,描画出某种景致,便为小诗。郭沫若在《女神》之后,写出了风格迥异的《星空》,其中就不乏优秀的小诗,这一事实,也正验证了小诗在诗坛的盛行。小诗的勃兴,实际也是应了诗体解放的要求,旧的镣铐打破以后,诗就呈现出自身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一些人生的感兴、内心的私语、景物的触动,都凭着那份天真烂漫率性为诗。即如周作人所说,“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⑤]可见,小诗这种灵动、活泼、完全开放的形式,体现了五四时期自由体诗的一种新的取向,它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那班新诗人的创造欲和表现欲。
小诗也是中外诗歌形式直接启发和借鉴的结果。从纵向考察,中国新诗中的小诗和《诗经》的部分作品、唐诗及其以后的绝句、散曲、小令和古代民歌中的子夜歌等有明显承继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小诗在中国文学史里也是‘古已有之’,只因它同别的诗词一样,被束缚在文言与韵的两重束缚里,不能自由发展,所以也不免和它们一样受到湮没的命运。”[⑥]“五四”新诗人丰富精深的古典诗词修养,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从古典诗词的短诗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来创造新的诗体。宗白华说“唐人的绝句……我顶喜欢,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是明白的事实。宗白华曾表示对郭沫若的一些短章的过于直露的不满,主张短诗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他的诗歌美学观点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推崇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结构,所谓“化景为情,融情于景,境与神会,美在神韵”,在他的诗中,“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理妙合无垠,具有齐整的短语、对句和对仗,这都是对古典诗词艺术尤其是唐人绝句的变化与发挥。冰心的小诗受到泰戈尔小诗的影响,但同时它还和中国传统诗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冰心自幼对对联、春联、联句、集句这类变形的古典诗尤为喜爱,而且对联这类短小的诗与泰戈尔的小诗在体裁的大小上已经很接近了。在她的诗中,能明显地感到她借用了对联的写作方式,难怪废名说:“打开《冰心诗集》一看,好像触目尽旧诗词的气氛。”[⑦]
当然,小诗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外国诗歌。在中国新诗的幼年时期,凡是有志于新诗的人们,莫不把输入外国诗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小诗在“五四”诗坛的兴盛,一方面是受翻译过来的日本短歌和俳句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印度泰戈尔小诗的影响。周作人说:“中国的新诗在各个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股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⑧]周作人与郑振铎是最初积极翻译日本或印度短诗并倡导小诗创作的诗人。从1921年5月起,周作人连续发表了译、论日本短诗的文章,对中国诗人借鉴日本俳句创造新诗中的小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诗坛对泰戈尔作了广泛的宣传。1918年前后,郑振铎对泰戈尔的诗发生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翻译。到1922年夏,他翻译的《飞鸟集》的出版,是小诗风靡中国新诗坛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郑振铎在《飞鸟集》序中所说:“近来小诗十分发达。它们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说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受泰戈尔的影响,已是众口一词。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⑨];徐志摩说她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⑩]。冰心在《繁星》序里曾说明了她的诗受泰戈尔的影响。在她80寿辰那天,她更有如下明白的承认:“那是1919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译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种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条,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11)在“五四”以后,一种完全不讲韵脚,不讲形式整齐,自由、短小的诗歌体裁——小诗,受到了诗人们的普遍重视。
“五四”时期的小诗,都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思索和感受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例如冰心的“小诗”,是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阅读新书、报刊,参加社会活动所得的收获。宗白华的“小诗”也是他留学法国时感受近代文明、思索宇宙人生所得的结果。小诗创作,并未经过作者严密的系统的总体构思与锤炼推敲,它只是及时地捕捉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并几乎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冰心的《繁星》就是“零星思想”的汇集,是她当时信手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三言两语”的编排,并未经过苦心的经营与构思。在诗人心中刹那间的情感、思想、观念,如不迅速捕捉、把握,就会一闪而逝,所以小诗创作的关键就是抓住“刹那”不放,“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12)冯文炳说冰心诗集“都是作者写刹那间的感觉,其表现方法犹之乎制造电影一样,把一刹那的影子留下来,然后给人一个活动的呈现。”(13)同时,小诗正因其“小”,所以“最重含蓄”,“重暗示、重弹性的表现”,通常只有三五行的小诗如几片花瓣,或缘事抒情,或因物起兴,或寄情于景,或不追求事、景、物的完整性;字句的省略、跳跃,形象、意境的“残缺”,意绪的“零碎”,正体现了小诗“有弹力的集中”的美学特征,因而虽短小而意蕴丰富。这些小诗虽然没有反映出时代风云,但却以精纯洗炼的语言,唱出了“五四”退潮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对时代、前途的新的期待、新的失望与悲观的意绪;对生命、人生、自然,对无限宇宙的新的发现、感受、倾慕与赞美的哲理情思,并且写得空灵、清新,诗意盎然。
二、诗与哲理的联姻
小诗作者甚众,色彩多样,风格各异。无论是蕴含乐府精神、俳句趣味、泰戈尔神韵的小诗,还是抒写内心的纤细感受与深邃的哲理的小诗,都有各自的风神和美趣。借用郑振铎赞美泰戈尔小诗的话来说,二十年代小诗“像山坡上的一丝丝的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来,随你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14)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小诗主要为写景抒情和偏于说理两类,而纯粹的写景,纯粹的抒情,纯粹的寓理,则并不多,而大多是写景、抒情与寓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写景时注重挖掘哲理,抒情时注重渗透理智,写哲理时注重借助于形象和比喻。小诗以抒情、写理为多,但其中又以写理为重。当时人们很自然地把小诗与哲理看作了“二而一”的东西,即成仿吾所说的,哲理诗是“与小诗凑成一对的”。(15)小诗中确有一些优美的写景抒情之作,但小诗的真价值主要不在这方面,他们不是以写景见长,而是以抒写哲理取胜,哲理小诗是他们对于新诗的独特贡献。
中国古代诗学有“诗中言理”、“以理为诗”之语;晚近有“说理诗”之说。“哲理诗”一词起自西方。亚里斯多德《诗学》所谓“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之说,成为后世哲理诗的滥觞。狄德罗《论戏剧诗》有“哲理剧”之说,黑格尔《美学》有“哲学诗”之说。“哲理诗”一词于本世纪初引入我国。哲理诗在中国古已有之,然而在中国古代诗史中几乎很少有哲理诗的地位,反而常常成为讥评的对象。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总是关注实际的人生经验而不是抽象的理念或哲理,即是“存在主义”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人生态度的缘故。在“五四”理性解放的启蒙主义时期,新文学作家摆脱了儒道思潮的束缚,借助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学说去思考宇宙、社会和人生,因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哲学热潮。许多新诗人都努力建立自己的哲学信仰,以解答他们觉醒之后面临的内心困惑。茅盾说:“那时大家正热衷于‘人生观’”(16),瞿世英说,对于当时的作家来说,“哲学是文学创作的本质”(17)。所以当时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哲理化倾向是十分突出的。在初期白话诗中,“说理是主调之一”,但说理诗往往太过于“晶莹透彻”,缺少“余香与回味”。文研会写实主义诗人也有说理倾向,但浑融精悍之作并不多。“五四”时期的小诗相当自觉地向哲理诗靠近,它的兴起,“一半是衔接着那以诗说理的风气”的。(18)冰心说:我写《繁星》,“因为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春水》“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19)从冰心着意强调《繁星》《春水》“不是诗”而是记录“零碎的思想”的见解,足见“哲理诗”的主张已在当时盛行。王统照在谈及泰戈尔时也说,“诗的本来目的,绝不是将哲学来教导我们,然而诗的灵魂,却是人生观的艺术化”,因此,“哲学使人知,诗歌使人感,然其发源则相同”。(20)可见,哲学对于诗及其它文体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五四”时期的作者中是多么牢固。小诗作品大都包含哲理,其所言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个人处世方面的种种智慧明达之理无所不包。小诗的哲理并非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以逻辑的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而是从对自然、人生的感悟中迸射出来的闪光的思想火花。
冰心的小诗受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以三言两语的格言、警句式的清丽诗句,表现自己内省的沉思和灵感的顿悟。但她的小诗并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和直接意义上,而是努力发掘事物所蕴含的哲理意蕴。这些哲理小诗或是人生真谛的发掘,或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或是人生哲学的诗意阐释。它对人的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对事物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进行深刻入微的探索。例如:“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他底下细小的泥沙。”(《繁星·三四》)“滚滚的波浪”来势迅猛,惊心动魄,而“细小的泥沙”则携裹在波浪之中,不为人所注意,这两个形象在大与小、巨与微、显与隐等方面形成鲜明对比,而对比的结果不是那巨大醒目、气势汹涌的波浪,反而是微小、不为人注意的泥沙创造出“新陆地”。在事物外在与内在的对比表现中,道出了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又如:“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繁星·五五》)诗人由花的明艳想到了芽儿长到花的艰难过程,从而揭示了任何成功都凝聚着奋斗和牺牲的深刻哲理。“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春水·三三》)借“墙角的花”嘲笑“孤芳自赏”,喻理警策,情景交融,启人深思。再如:“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繁星·四八》);“空中的鸟!/何必与笼里的同伴争噪呢?/你自有你的领地”(《繁星·七》):“经验的花/结了智慧的果,/智慧的果/却包着烦恼的核!”(《春水·一四六》)等等,都显露出朴素而深邃的道理,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和启迪。冰心哲理意味很浓的小诗所以被人们喜爱和称誉,关键在于他把这种哲理蕴含寄托在鲜明感人的形象之中,并且充溢着浓郁的诗情。有些哲理诗着一形象的比喻,有的通过形象表现哲理。诗的哲理几乎都是从一花一木一沙一石一人一事中引申出来的,并不流于空泛的说教,因而耐人咀嚼与回味。但也有一些哲理小诗,是采取问答式,直书其意,并没有借助多少形象,但仍让人觉得是诗,而不是纯粹的教义或学理。还有一些哲理小诗“造语平淡,用意艰深”,即用极其明朗而简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借日常事理以警世醒俗,晓喻众生。她告诫青年不要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那无希望的事实,/解答那难解答的问题,/便是青年的自杀!”(《繁星·五三》)劝嘱青年不要虚掷时光:“青年人!/珍重的描写罢;/时间正翻着书页/请你着笔!”(《春水·一七四》)教导青年不要过分看重荣誉:“冠冕?/是暂时的光辉,/是永久的束缚。”(《繁星·八八》)提醒青年不要空谈:“言论的花儿/开的愈大,/行为的果子/结的愈小。”(《繁星·四五》这些哲理小诗立片言而居要,寓警策于平淡,它是诗人高瞻远瞩而又洞察入微的心灵探索,含味隽永,内涵深刻,能启迪或深化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冰心的小诗的兴趣大都集中于事物或经验的本质而不是它们的细节的提炼和概括,因而颇具格言意味,饱含哲理光芒。《春水·一五》中说:“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一回头——/灵魂里潜藏的怯懦,/要你停留。”这里表明前进者不要轻易回头,因为一旦回头人的怯懦一面的本性就会使你停留不前。这是对人生的一种现象的感悟,这感悟是对事物本质的透示,因而具有哲理性。总之,冰心的小诗是用“智慧和情感的珠缀成的”,晶莹纯静,清新隽永,妙韵天成。
宗白华的小诗“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21),“他的诗,跟冰心比较起来,更是哲理”(22)。朱自清干脆说他的诗“全是哲理”(23)。当然,所谓“以哲理做骨子”,或诗歌哲理化,并不是用诗去宣扬哲学主张,而是用哲学家的智慧、哲学家的胸怀去把握自然,乃至把握整个宇宙。在这里,诗歌并不是简单的客观对象的描摹或浅薄的情感的宣泄,而是带着哲学内核的深刻观照和思索。1920年元月初,宗白华先生致信郭沫若君:“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这种对宇宙意识的自觉追求使他成为一名一往情深他吟唱自然的诗人,在他的诗中,“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歌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24)但这些诗,并非纯粹的自然诗,而是在丰富生动的自然景观中透射出深邃的哲理美。在《流云》集中,《夜》、《晨》、《绿阴》、《世界的花》、《彩虹》、《月夜海上》、《东海滨》、《月夜》、《孤舟的地球》等一批以自然物象命名的诗,弹奏出了纯真刻骨的爱和自然深静的美在他生命情绪中结成的微渺的节奏,以及在他理性世界中引发的深刻的哲理思考。他的《夜》这样写道:“黑夜深/万籁息/远寺的钟声俱寂/寂静——寂静——/微眇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尽。”这里情、景、理相互交融,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挣脱了地球的相对时间,于刹那间把握住了无限和永恒,获得了一种宇宙意识。还有一首《夜》:“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里星,/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里,/在里面灿着。”诗人以明快轻盈的笔调,表现了诗人一颗鲜洁晶莹的诗心和宇宙万物拥抱交汇在一起,而我的微躯化作一颗小星随着万星奔流的意象,又使人领悟到宇宙万物与人类在同一旋律里踏着相同的生命节奏于短暂的生命运动中共同实现着宇宙的无限。诗人把夏夜仰望星空时,人的自我感觉刹那间的微妙变化赋予诗意的表现,引起人们对于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悠长的哲学思索。不但写景诗常常蕴含诗意和哲理,即使是哲理诗,也写得有声有色。例如《生命的流》:“我生命的流/是琴弦上的音波/永远地绕住了松间的秋星明月。/我生命的流/是她心泉上的情波/永远地萦住了她胸中的昼夜思潮。”这里蕴含着诗人对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生命与爱情的关系的哲理性思索。再如《诗》:“啊,诗从何处寻?/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诗中写物象,清新生动,使人从中感到一种象外之意,一种令人神往、陶醉的审美情思,无形中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此外,《人生》、《宇宙的灵魂》、《断句》、《感谢》、《宇宙》等诗都在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深刻思索中传达出生命的奥秘,在有限的诗的本体中追求无限的审美哲学情趣。通读《流云》集中的一首首短小精粹、意味隽永的小诗,就可见到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诗情、诗意、诗美熔于一炉,达到水乳交融的和谐境界,也就是以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抒情式的,整体化的,诗意性的——去感知社会、人生,将哲理融于意象,让诗意蕴含哲理。他常常借助于比喻性、象征性的意象,以一些浸染诗人感情色彩的具体事物和生动画面为载体,形象贴切地表达思想与哲理,这就使他的诗具有了极强的诗性特征。仅从这里所举几首诗中,就足见诗人并不热衷于诗歌的教训意义,而是靠直觉和悟性,捕捉刹那间的心灵闪光;诗人准确把握自然景物的特征,经过心智的创造而表达出深刻的哲理意蕴;其诗中的形象既来自于平凡的大自然,又升华到极不平凡的哲理境界。
把小诗与哲理联系在一起,使小诗获得了一种鲜明的特色。小诗与哲理的成功结合,应当说是冰心、宗白华等诗人对于新诗的一种突破、一种创造。在中国诗学史上,一直把“诗中言理”、“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视为诗的弊端。而在近代和“五四”时期,所谓“说理诗”的称谓,多含贬意。不少人还把说理排斥在诗歌之外,极力主张“哲理本不宜入诗”。(25)而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作者取得了成功经验,为新诗开出一条崭新的艺术轨道。当然,以小诗形式抒写哲理并非是最理想的方式,即是说,它还有一些自身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即诗中哲理只是一闪而过,或点到为止,并极少涉及深层次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意识。此后哲理诗在形式上的进一步改观则证明了这一点。但无论怎样,这种哲理小诗却较早地突破了传统诗歌“以情为主”的规则,确立了“以智为主脑”的特征,它是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它不是使人动情而是使人深思。这种哲理小诗在诗坛的兴盛,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成仿吾公开宣称要打一场“诗之防御战”,就是针对小诗的哲理化倾向而来的。他认为,“诗也要人去思索,根本上便错了”;“带上了诗形而又自称哲理,我们只好取消它的诗的资格”;“把哲理夹入诗中,已经是不对的,而以哲理诗为目的去做,便更不对了”,其根本理由无外乎是:诗只可抒情而不可阐明哲理,诗只可诉之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理智的创造,所以在诗中,“要严防理智的叛逆”。(26)由于成仿吾是以主情派的理论武器来反对小诗的哲理性,因而其结论是偏激的,不可取的。虽然小诗抒写哲理还存在不少毛病,哲理与诗的完美结合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但要把哲理从诗中完全排斥出去,让诗只限于抒情,则是不可能了。小诗作者努力打开诗歌通向哲理的大门,建立哲理小诗艺术,正是要突破传统诗学的藩篱。他们的成功,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哲理美和诗意美的诗歌境界,而且证明哲理完全可以入诗,并且可以写很好的诗。从此以后,哲理诗在诗坛理直气壮地存在着,发展着。哲理不但为小诗表现得情有独钟,而更为一般诗歌所共有。尤其到了三四十年代,在各种艺术的激烈竞争中,诗歌的哲理化更趋明显,它对于民族智慧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闻一多说,“打破了一个固定的形式,目的是要得到许多变异的形式。”(27)小诗就是新诗取代旧诗后出现的一种“变异”的形式,这种变异的形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哲理化与简练化的统一。它在诗坛的风行,成就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短小精悍、清新隽永、活泼灵动的诗体形态。
三、小诗的中衰
自然,二十年代的小诗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当时成仿吾对小诗的偏激尖刻的批评集中于小诗的哲理化和诗体的“小”而“散”的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一些小诗作者“不注重感情在诗歌上的重要和它的效果”,而“用理论式的概念式的,与过于抽象的文字”“列为诗形”,“用过量的理智来破坏诗歌的效果”,结果使诗流于“浅薄”;还有些小诗因其“音数既经限定,字数自然甚少,结果难免不限于极端的点画派”和“极端的刹那主义”,“刹那主义与点画的结果”,使诗陷于“轻浮”。(28)还有不少诗评家也对小诗的缺点作了批评。朱自清说,一些小诗“不能把捉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余味”。(29)冯文炳说,一些小诗“把直接的诗感又直接的写在纸上了,其结果诗自然还是诗,而写诗的方法乃太像写散文了,即是照当时的情形直描,一杯凉开水就当作甜香的酒了。”(30)梁实秋后来批评这种“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的便成一集”的小诗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31)造成了诗歌上的很多杂草。事实上,如果小诗作者只一味地照直描写生活中的一鳞一爪、一时的片断印象和自我的琐屑感觉;或谈玄说道,无病呻吟,而不能用高远的眼光审视深广的社会生活,不懂得如何运用技巧,那么必然导致小诗视野越来越狭小,内容越来越贫乏无味,形式越来越粗制滥造。当时有这样一首小诗:“拦路睡着的黄狗/当我走过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惹它)/只是向我抬着头啊!”这首“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无一所取。随着平庸、拙劣的小诗的漫延,读者望而生厌,评论界一片斥责声。郭沫若当时就指出:“目今短诗流行,甚者乃小儿说话,殊非所取。简单的写生,平庸的感想,既不是令人感生美趣,复不是令人驰骋玄思,随随便便敷敷衍衍,在作者写出时或许真有实感随伴,但以无选择功夫,使读者全不能生丝毫影响,此种倾向我辈宁可避免。”(32)这确是对小诗的不良倾向的迎头棒喝!闻一多认为小诗的缺点在于“无形式”,“不仅没有形式,而且没有廓线”,因此他呼吁,新诗“已经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再受泰戈尔的影响,必有“不可救药的一天”。(33)闻一多后来倡导格律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无形式”的倾向的后拨!小诗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存在的种种弱点,无疑影响和限制了它的发展。
朱自清说:“《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34)这不仅与小诗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有关,也与现实生活的发展相联系。“五四”以后的一段沉寂很快过去,残酷的社会现实无情地撕碎了诗人们泰戈尔式的人生探索的梦幻。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后期曾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说道:“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像这样的幻美追求,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青年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不得不舍弃《繁星》《春水》《流云》式的博爱的幻想、哲理的探究,回归自然的憧憬……小诗“幽玄、静寂”的情趣已经无法吸引他们了。同时,1924年以后革命浪潮汹涌向前,1925年“五卅”惨案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逐渐淹没了一度兴起的小诗创作。时代呼唤“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小诗的体制与格调显然无法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小诗长于表达刹那间的内心生活的变迁,而不宜于表现壮阔的时代生活和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梁实秋认为,小诗的长度不够,容量小,不足以表达繁复深刻的思想与情绪。(35)因此,小诗作者也不得不放弃小诗的创作,去试验别种体裁,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生活的需要。
总而言之,二十年代上半期出现的小诗,以短小的篇幅捕捉刹那间的自我感受与哲理思考,变外部世界的客观描绘为内心感觉的主观表现,并且讲究锤炼趋于精致,无疑丰富和提高了新诗艺术的表现力,因此,我们说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运动有一个“奠定诗坛”的功劳,是并不为过的。尽管在1925年以后小诗不复受宠,但作为一种诗体形式却为多数诗人所接受,在新诗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了致力于小诗而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
注释:
①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日。
②(22)任钧《新诗话》,新中国出版社1946年6月版。
③⑤⑥⑧(12)周作人《论小诗》,1922年6月29日《觉悟》。
④(18)(23)(29)(3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⑦(13)(30)冯文炳《谈新诗·冰心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25)(27)(33) 闻一多《泰戈尔批评》,1932年12月3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9期。
⑩徐志摩《泰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11)卓如《访老诗人冰心》。
(14)郑振铎《〈飞鸟集〉全译本新序》。
(15)(26)(28)成仿吾《诗之防御战》,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1号。
(16)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7)瞿世英《创作与哲学》,《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19)《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
(20)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小说月报》第14卷第19号。
(21)《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版。
(24)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31)梁实秋《繁星与春水》,黄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印行。
(32)郭沫若致洪为法信,《心潮》1923年第1卷第2期。
(35)梁实秋《偏见集·论诗的大小长短》,正中书局1934年7月版。
标签:诗歌论文; 泰戈尔论文; 小诗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飞鸟集论文; 春水论文; 繁星论文; 冰心论文; 宗白华论文; 流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