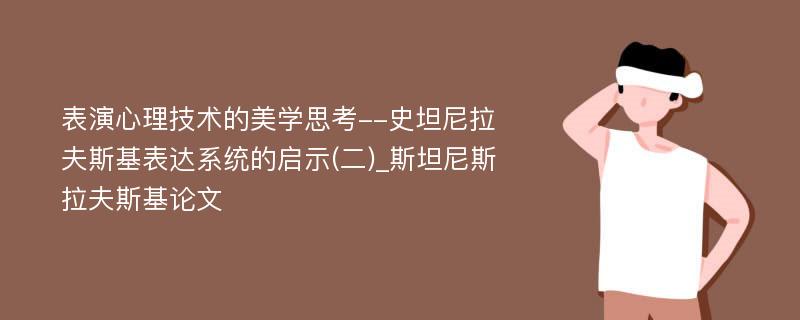
关于表演心理技术的美学思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现体系的启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斯基论文,美学论文,启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从内容到形式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从作品的形式进入作品内容的思维过程。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表演者从乐谱中“听”到的活生生的精神性的音调,要通过表演深深地打动观众的心灵,就必须通过表演者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形式这个中介。这里正好发生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运动——表演者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必须通过物质的形式才能传达给听众。
这里既有演奏技术问题,又有心理技术问题,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正是后者。假定表演者技术上已经不存在表演上的障碍,凡是表演者想要做到的,他一律都能做得到,按照这一假定,现在的问题,就不在于表演者手上的功夫是否做得到,而主要在于他的思维能力,即在于他是否想得到了。
理解与体验
许多听众都具有辨别音乐作品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的能力,但是,据此就认为表演者对作品的感情体验和体现是轻而易举的事,那就是一种误解。一个人能够辨别乐曲的感情色彩,也可以说他“听懂了”,他却可能仅只是理解了。尽管理解有助于体验,理解了却并不等于达到了深刻体验的层次。表演者在接触作品的时候,也会“知道了”这个作品的感情色彩,如果就满足于此,那就是误把“理性理解”当作了“感情体验”。尽管感情体验中包含着理性的理解,但是,一个人仅仅“知道”了别人的不幸遭遇,是一回事,是否对别人的辛酸感同身受?则是另一回事。前者就是理性理解,后者才是感情体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对:“用头脑去理解这些伟大传统的语言的含义并不难,然而,遗憾的是,要用演员的情感去感觉它们的精神实质却很困难(《戏剧》全集卷五541页)。
上面我们对《热情奏鸣曲》第一乐章所说的话,当然只是我们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不一定就符合贝多芬的理解,我们体验到的感情,也只是我们自己的感情。“现代的精神心理学十分确切地肯定,人根本不能生活在别人的情感里。他只能体验自己本人的情感。因此,演员说他自己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这只是欺人之谈,这是过去心理科学不发达的结果”(格.尼.古里叶夫《1955—1956年在中国所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讲座》。顺便说一句,这位古里叶夫不仅是列宁格勒普希金话剧院的导演,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副教授)。我想,这可能正是艺术表演中体验感情本身所包含的真实性与假定性的两重性的由来所在。对于我们的感情体验而言,它是真实的,也正因为是我们的体验,所以,对于作者而言,也正好是假定性。我们假定,我们是理解了作者的原意。至于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作者,可能是另一回事。但是,在艺术中,这种假定性不但是允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完全的真实性只存在于生活之中,艺术如果离不了假定性,艺术也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只能达到这样的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问题只在于:这种假定性是否与作品内涵的潜能范围相符合?
找到与丢掉
“在这种深夜的思想排演中,有多少种子、贯串动作和任务错综混杂在一起啊,有多少次琢磨、体验和检查着角色从头至尾整个发展过程啊。我多少次在思想和情感上度过对于骑士意义如此重大的一天;多少次我豁然开朗,有了发现,精神振奋,满怀希望,但白天排练时所有这些一概破灭,情感又被刻板手法和表演陈套所左右(《关于排戏和创造角色的札记》全集卷五587页)。 我们在音乐表演艺术中也遇到过相似的苦恼,多少次沉入艺术想像时,自己激动不已,演奏起来,却就是不激动别人。好象感觉找到了多少次,就又丢掉了多少次,甚至有时,自己觉得演奏得非常激动,观众却说演奏得缺乏感情。奇怪的是,当自己再听自己演奏的录音时,也得到与观众一样的印象:缺乏感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有过同样的经验:“须知我由于情感洋溢而出汗,心房跳动的次数都难于计算,还说我缺乏情感!”(《艺术手记》)这个问题曾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里至少涉及下列一些问题。
今天、此时、此地
在生活中,感情本来就是随时发生变化的,此一时不再是彼一时。这种只在一定具体情况下维持特定规格的心理状态,就是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心理场”,心理场本身就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一种“心理场”具有什么特定的性质和深度,又是与周围环境即“物理场”(它也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整体)相互作用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至整体的变化,就是说,任何一个子系统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母系统的整体变化。完全同一的心理场几乎不可能重复出现,至多是类似地再次发生。尤其是在舞台这个随时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的令人十分别扭的环境中,曾经发生过的心理场要在这种变化了的时间、地方再次出现,必须排除一切干扰,进行心理调整,重新进行创造。所以,斯氏要求演员必须做到“今天、此时、此地”,一个演员此时此刻的成败,就是他表演的成败,就如历史是暂时的一样,一切都是暂时的。
如果要问:在深夜冥想中,演员是怎样获得那千百次体验的呢?那时刻,演员思路的出发点并不是“寻找某种感情”,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艺术想象,从而进入了“规定情景”,那感情与感觉自然就出现了。而在排练和演出的时刻,主体脑子里不知充塞了多少问题:“我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之类,还要随时应对别人的谈话,随时改变着思路,即使非常想要进入“规定情景”,做起来也相当困难。那只能从“规定情景”中所能得到的感情和感觉,也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激发与抑制
感情这东西的发生与否,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是不能向它下命令的。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你愈是想进入什么感情状态,就愈是进入不成,你愈是要摆脱什么感情状态,也愈是摆脱不了。
“奇怪的是,当你实际感觉到在观众中的印象并不好的时候,当你控制着自己而不完全顺从角色的时候,——结果倒是更好。我开始懂得扮演角色方面的渐进性”(《艺术手记》全集卷五95页)。这里有一个译者加的注:“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谈的是角色的逐渐发展,以及演员为最充分深刻地展示形象而配置自己的表演手段和气质的能力。在他的“体系”中,有关于演员和角色的远景的篇章,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不敢说译者准是错了,这种解释却令我怀疑。关于斯氏的两种远景即角色远景与演员远景的理论,下面我们会来讨论,不过,与其说斯氏在这里谈的是角色的渐进性,还不如说是谈论的是感情自动化的渐进性。感情在人们愈是抑制它时,它就会自动反抗即愈加增强,这倒是感情发展的一种规律性。当你失去了亲人,你如果要想用大哭一场的办法,缓解一下痛苦,反而愈哭无泪;而别人越是劝你不要难过,就触动得你越发伤心。你越是要把眼泪强压下去,眼泪就越是要自动涌出来。当然,这是以首先已经触动了感情而感情尚未迸发的情况为前提的,并不是说,你越不难过就越难过。这一规律告诉我们,激发感情与控制感情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以为,斯氏说的正是这一感情发展的渐进性。这就是说,当你已经进入某种感情而尚未进入迸发状态的情况下,如果你想“让感情丰富一些吧”,感情就越不出来;恰恰相反,你如果要抑制它,结果,这感情就非迸发出来不可。
舞台语言
有人说:“善于将别人的意见化为自己的意见,是为民主作风。善于将自己的意见化为别人的意见,是为领导思想”。这两条似乎也应该是对于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表演艺术不是接受和传达意见,而是既要做到:以作品中的感情体现,启发自己的感情体验(这正是上文所说的“找到与丢掉”的东西);还要做到:以自己的感情体现,去启发别人的感情体验。
从作品的内容得到表演者的感受,这是一个从别人的体现转化为自己的体验的过程,如果在舞台上的瞬间,表演者缺乏体验,固然可能失败。即使在舞台上,表演者并不缺乏体验,表演者要想将自己的体验转化为体现,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舞台语言问题。
说到“舞台语言”,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艺术技巧,来表达什么感情。在设计表演的整体计划的时候,这些都曾是关键问题,但是,在舞台上执行计划时,关键就不再是记住应该使用什么舞台语言的问题,而转移到舞台语言是死是活方面来了。到了舞台上表演时,所有的应该如何如何的“规定”,都容易成为“套路”,把人引入“做戏的自我感觉”,你越是盼望某种感情来临,它就越不来临,心里的灵感没有了,就只剩下何时使用何种技巧了,所谓的舞台语言就像“背书”那样机械式地重复,结果竟是既无体验也无体现。
斯氏理论的精华,正在于以“创作的自我感觉”与“做戏的自我感觉”相对立。“我想学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在自己身上造成的不是灵感本身,而只是有利于灵感产生的土壤,也就是能使灵感降临到我们心灵中来的那种气氛”(《我的艺术生活》352页)。 这也正是优秀的演员似乎能够“呼唤”灵感的奥秘所在:表演者不是去寻找某种感情,而应该进入艺术想象即通过想象进入“规定情景”,合乎逻辑的感情就会自动发生,即进入了体验。这就为艺术体现创造了前提,要使舞台语言富于表现力,就要丢掉一切“牢记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枷锁,让被解除了压抑的下意识来执行甚至即兴修改贯串动作的计划。“真正的艺术则应该教导人怎样有意识地激发起自身的下意识创作天性,以进行超意识的有机创作”(《我的艺术生活》476页)。 “使我们的天性发挥它的作用,而天性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艺术家”(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17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来也不曾有意识地去注意自己的表情,只要有什么样的情绪,就自然会下意识地现出什么样的表情,这样自然就会仅仅留下那些恰如其分的舞台语言,一切动作也才会真正成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表情手段。
舞台时间
“舞台时间”区别于生活中的时间。也有人把这两种时间称为: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在生活中,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往往随着环境变化发生得比较迅速,而在艺术中,特别是在音乐中,心理变化的时间常比生活中感情变化的时间要长,与生活中的时间历程相比,大小高潮起伏的层次要多些,高潮持续得长久些,退潮较慢些,好象通过高倍的“显微镜”来观察内心世界,让听众来得及细细体验其中的“滋味”,这也是艺术感人至深的原因之一。
把生活的真实当作艺术的真实的人,常常一味要求生活的真实性。有人说:“还是话剧好,到了关键时刻,演员的动作和道白一下子就把高潮推上去了。歌剧不行,到了正需要快速推出高潮的关键时刻,他偏偏唱起来,矛盾的发展一下子就慢下来了”。看来,这位先生是只接受话剧的舞台时间,而不接受歌剧的舞台时间,实际上,就连话剧的舞台节奏也比生活节奏要“慢”,只是没有慢到他所不能容忍的程度罢了。“要遵守舞台时间,让观众细看并且明白脸上的表情,同样也要让意识来得及进入脑海并且反映在脸上”(《1904—1905年导演日记》)。“……舞台时间。它比生活中长久。必须给观众留出时间去欣赏演员,并把最主要最有特色的瞬间,把一个角色、一场戏的每个段落等等看清楚了,铭记在心中,留在记忆里带走。因此必须弄明白目前这场戏里什么是最有特点的,把它表现得更久些,更鲜明些”(同上)。我想,不善于掌握舞台时间或称舞台节奏,可能就是演员自己非常激动,而表演效果并不激动的原因。演员确实是激动过,但这个感情发展过程太快了,当观众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演员的感情高潮已经过去了,结果竟是给了观众以“缺乏感情”的印象。音乐中的舞台时间,比话剧中的舞台时间更具夸张性。如果不善于掌握舞台时间,很可能,演奏家的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快,听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或者没有来得及充分反应,就过去了,也就不可能在观众心中产生如演员所期望得到的那种强烈的效果。
要把心理变化的时间延长,对心理内容给以长足纵深地开挖,这本来就是不自然的,要做到让人感到非常自然,就需要与“不自然的感觉作斗争”的心理技术,使一切细微曲直的转折都给人以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感觉。顺便说一下,本来,在舞台上的一切感觉就都是不自然的,这很容易导致表演变形走样打折扣,斯氏强调用局部紧张(例如压紧脚的大拇指)来达到整体肌肉松弛,也是为了解除这种在舞台上的不自然的感觉。
角色远景与演员远景
所谓“角色远景”,就是按照作品所揭示的内容一步一步发展下去的角色的感情体验的单元构成的一条线。如果“演员远景”与“角色远景”是一回事,那也就不存在什么“演员远景”了。斯氏提出的在“角色远景”之外,另有一条“演员远景”的发展线索,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角色远景”中的自我是第二自我,即“忘我”的那个我。俗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话说对了一半,演戏的还有一半不是疯子,看戏的还有一半也不是傻子。演戏的还知道自己是在演,看戏的还知道自己是在看。这清醒的一半自我,就是第一自我。“演员远景”的一条线,就是第一自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一条线。除了作品内容要求的“角色远景”之外,当然还有许多要求:第二自我是不需要“背台词”的,对于音乐表演来说,就包括背谱和背歌词。角色根本就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他会遇到什么事情。可是,演员从一开始,就知道事情的结果。第二自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演出计划”,他根本就不该把自己设想为一个表演者,第一自我却不仅要执行演出计划,绝对不准忘记下面该做什么事,还有一个掌握观众心理的问题。
通常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按照音乐内容来设计表演计划,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善于掌握观众心理的问题,有时恰恰就是有意地做出似乎“背离”内容的抉择,反而能够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茅原先生在《人化的自然与音乐的耳朵》中,曾经谈到的陕北说书民间艺术家韩起祥演唱《刘巧团圆》的经验,就是典型的例子:表演者在音乐持续很长时间的悲哀情绪(弱唱弱奏)之后,突然把三弦伴奏过门弹得非常响亮,这显然与悲哀的情绪要求是不一致的,据韩起祥的解释(大意):这时,听众已经太难过了,再哭下去,听众将不能继续接受,所以,要唤醒听众:“这是在听说书”!这样,听众将从“书里”暂时退出去。然后,再回到悲哀的情绪中来演唱下去,听众才能继续接受。韩起祥提醒听众:这是在听说书:布莱希特提醒观众:这是在戏院里。行家里手所见何其相似乃尔!
言语与现实
巴甫洛夫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要使用言语,那么你就要时刻不停地想到言语之中的现实”。巴甫洛夫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相互作用的原理说明:人们在使用第二信号系统进行言语交流活动的时候,人们的第一信号系统中所得到的实物印象,作为想象(即被调动的信息储存),就同时被激活起来,比如,当人们在说“花”这个概念的时候,谁也没见过什么抽象的“花”,而只见过具体的花,或者是自己屋里摆过的花瓶里的梅花,或者是在公园里看过的月季花,诸如此类的生活印象就在言语活动时被激活起来。第一信号系统并不限于视觉范围,它包括听觉、触觉(甚至对温度的感觉记忆)等等在内,当我们看到“声嘶力竭”这个成语的时候,或者是某一泼妇骂街的声嘶力竭的感性印象,或者是某人装腔作势自我表白式的声嘶力竭的感性印象,即使它是已经抽象化的了(即有所扬弃的、不完整的)感性信号的储存,也会与第二信号系统的信号同时被激活。通常人们对于这种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的相互作用,是并不注意的,它自动化地在进行着,这些作为伴随物的第一信号的实物印象也未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但是,如果我们在读剧本或读乐谱(乐谱上所写的是作为思维活动的纪录的“符号”,也具有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的意义)的时候,有意识地进入想象,就能利用伴随出现的第一信号系统的实物信号作为“刺激物”,激发表演者的形象思维活动。在这种思维活动中的一切形象,也就是元素及其发展而成的“贯穿动作”中的一条“心理形体线”,它以元素为起点,以远景即最高目的为归宿。它贯穿于整个艺术表演的过程之中,它是沟通体验与体现的一条纽带。所以,人们就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斯氏的体系:“体系就是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古里叶夫)。
相互作用的三条线
心理形体线居于三条线的核心地位,另外的两条线,一条“感受线”,它是精神性的、内心体验性质的一条线;一条是“形体行为线”,它是物质性的、舞台语言式的、通过表演见之于外的、体验与体现统一的一条线。而心理形体线正是把感受线与形体行为线联接在一起的媒介或中心环节。
斯氏的学生、苏联人民艺术家华·托波尔科夫说:“在制定心理形体线的时候,我们又要首先确定感受线”(《演员的技术》107页)。 表演者的工作是从阅读开始的,也就是从感受作品开始的,不过,事实上,心理形体线也随之诞生,并立即反作用于感受线,而且,除了这个“启动”式开始之外,这三条线中的任何两条线都构成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生发、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
我们先来考察感受线与心理形体线的关系。感受的心理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产生心理表象的心理过程。托波尔科夫说:“每一个形体行动都是心理过程的表现。……行动的过程是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的:对周围世界的感受;由感受而引起的思维;相应的反应或者说对周围世界的反作用”(《演员的技术》61页)。这其实就是皮亚杰在修改心理学中的“刺激——反应”(S—R)公式时所提出来的“刺激——主体——反应”(即S.A.R)公式。外界的刺激,通过主体的思维,产生了反应, 而且,这个反应也构成对于主体的新的刺激,又引起思维进一步深化的运动。对于表演者的工作而言,作品就是外界的刺激,它引起主体的思维活动,这反应就是唤醒了对生活印象的记忆储存。而这些表象不但是心理形体的来源(它就是构成心理形体线的形象素材),而且,这表象也是激发进一步想像的刺激物,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不但新的刺激引起新的表象运动,已经唤起的表象也要具有更新即深化的意义。感受线促使心理形体线的建立与发展,同样,心理形体线也促使感受线进一步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以作品的体现为刺激,通过主体的思维,引发表演者的体验的过程。
我们再来考察心理形体线与形体行为线的关系。心理形体线已是第二次出现了,它第一次出现在它与感受线的相互作用之中,第二次就是出现在它与形体行为线的相互作用之中,并且是携带着它与感受线相互作用的全部财富来参与建构形体行为线(实际即是舞台语言线)的。这一次,S.A.R的公式的形式没有变,改变的只是内容, 心理行为线中的表象构成新的刺激物;经过主体的思维,找出的形体行为即舞台语言,就是主体作出的反应,而这反应也构成新的刺激物,促使思维主体的感受更加深刻,也促使主体思维对形体行为线建构的进一步深化。所以说,形体行为线一旦诞生,它也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它也转化为积极推动心理形体线发展的因素。这个形体行为线的整体,也就是体现着作品内涵的整个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也就是从内容到形式运动的最后结果。
四、互相渗透的三原则
斯氏体系的三个基本原则就是:能动性和行动的原则(有时也说“有机行动的原则”)、规定情景中热情真实的原则和意识地走向有机创作的原则。
能动性和行动的原则
这里涉及的是表演者需要凭藉什么手段来进行艺术创作的问题。行动的原文是деиствие,具有活动、做(相对于说)的意思,有人译为“行动”,有人译为“动作”,也就是上述行动线的“行动”,就由它构成从元素到贯串动作的三条相互作用的线。“心理技术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作器官的一切元素使之行动起来”(‘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61页)。
所谓“有机”的行动,指的是,无论在艺术想象中还是在舞台上,不必要也不允许存在任何多余的动作。所有的动作都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必要的合理组成部分。在戏剧中,一切都是靠“动作”来说明问题的。这一点,在音乐中,情况有所不同,音乐中主要的传达手段不是行动,无论是从作品获得的东西还是表演者提供给听众的东西,都只是关于行动的体验和感受。行动到哪里去了呢?是由表演者和欣赏者在艺术想象中予以补足的。与其说是“行动”,毋宁说,只是在艺术虚象中补足的关于行动的“想像”。
规定情景中热情真实的原则
这里涉及的是表演者主体的思维方法问题。主要是提醒演员,不要“舍本求末”。演员们往往过分把注意力放在舞台语言方面,着重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技法去表现自己用理智来理解的作品内容,或者努力用理智勉强自己进入某种感情状态。实际上,舞台语言只是一个结果,舞台语言来自于感情特质,感情特质又来自于规定情景。这种“不要去寻找感情,应该是寻找规定情景”的想法,本来是普希金提出来的。要点是:“纯真的热情,或者说真实的情感,是由规定情景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完全符合感情发展的规律性,无论对于文学还是艺术创作,确实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只有合乎逻辑地进入了规定情景,才能合乎逻辑地找到元素和建立行动的线。
意识地走向有机创作的的原则
这里涉及的是表演艺术中的操作标准的问题。整个斯坦尼斯拉夫斯表演体系贯穿着这样的要求:“通过有意识的技术,达到演员天性的下意识的创作”(《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29页)。
人是不能控制自己的下意识的,否则,它就不叫下意识了。怎么能够发挥下意识即天性这个“艺术家”的作用呢?诚然,就如我们骑自行车和游泳一样,经过反复训练,可以形成下意识的操作。这总不能是唯一的道路,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茅原先生在《音乐的可知性》一文(载于《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二期)中,有一个段落标题就叫作“在遗忘的背后”,原来,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在遗忘的背后”就是下意识的记忆储存库。人们把某些东西忘却了,这些东西就转移到下意识这记忆储存库中去了,遇到一定的契机,即遇到一定的“相似块”,这些被遗忘的东西就会自动化地(有时尽管是以变了形的姿态)浮现于人的脑海里。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即:人们究竟怎么能够通过意识来调动下意识的活动?
演员上台时脑子里应该想着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斯氏常说的演员脑子里必须有的那个“总谱”,就是一个表演者,在钻研作品的时候,下了很大功夫,连非常细微的地方都反复练习过的那些东西的总和。当他要登上舞台表演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是把整个“总谱”都装在脑子里吗?这很危险,脑子里也记不了这么多细节,思想负担太重,精神太紧张。演奏者们都知道,你越怕什么地方出错,就越是在什么地方出错。或者,是把准备得那么仔细的“总谱”都丢在脑后,豁出去了,闯它一番吗?这也危险,有时候就真的会在演奏中途“卡”住了。
斯氏主张用一种“表解”(尽管他也叫它“总谱”,却是非常简单浓缩过的东西)来代替整个“总谱”,比仿说,作品如果是一棵树,这表解就只是树干和大的树枝,不包括细枝、叶、花。这很像一个教师上课用的“教案”,提纲携领,却起着提示作用。“这一种总谱或你所遵循着前进的路线,应该是很简单的,不但如此,它还应该以自己的简单使你惊异。复杂的心理线索以及其中各种细微难辨的东西只会使你莫知所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演说、谈话书信集》1953年莫斯科版)。就是说,在演员登台时,心里应该只记住一个非常简单的纲要式的框架。这不危险吗?准备得那么丰富的许多细节,不是会忘掉吗?那不是白白地花了那么多力气吗?其实,一点也不危险,忘掉就让它忘掉好了,忘掉了,就把它们寄放到下意识那记忆储存库中去了。
上述的“表解”就是表演者有意识地留作启动下意识活动的“契机”或者叫“诱饵”。斯氏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对于在下意识中的人类感情的口袋,是不可以当作钱袋那样探进去搜索的;对待下意识应该用另一种办法,要像猎人对待他从丛林中用诱饵捕获的禽鸟一样。你是找不到这种鸟儿的,而如果你要找寻这种鸟儿,就需要布下这种狩猎的诱饵,让鸟儿自己飞来。我所要给你们的这种诱饵,就是形体的和初步心理的任务和动作”。他说的形体和初步心理的任务和动作就是指的上述“表解”即简化了的“总谱”。实际上,这一简单的“总谱”随处都埋伏着足以引起下意识创作的契机。所谓的“即兴”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下意识的活动。
天才与人材
表演艺术需要天才,但是,艺术教学总不能只寄希望于青年自身的天才。如果这青年只有才能而不是天才,那么,他就只好跟着天才走即去模仿天才,而实际上,天才能做到的事正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因此,这种模仿真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徒劳。
过去,人们总是期望和等待灵感的到来,斯氏的功绩正在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人训练成材,使之能够具有“呼唤”灵感的能力,使艺术教育和美学研究提高了“科学含量”。
科学的东西自然有其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它还在发展之中,与艺术结合的科学研究更有着其特殊的困难,它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能保证实践的必然成功,但是,这里也应该有更高的成功或然率,值得和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探索。我相信,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必将进一步加强艺术教育与美学研究的有效性。
标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