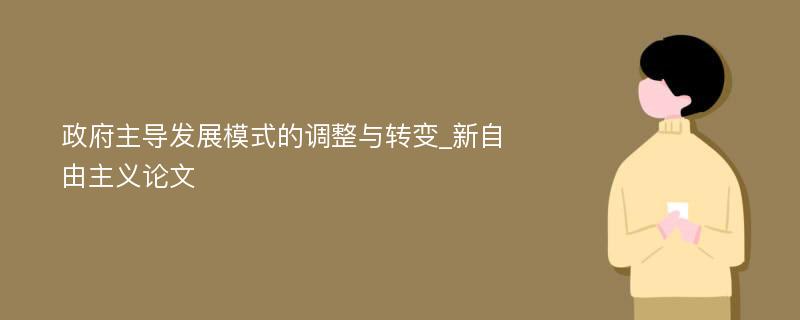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调适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论文,模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就在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共识已经历史性地载入了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中。然而,在这一表面性的“共识”之下,依然存在着巨大实质性的争议。最为核心的争议问题是:政府(或行政机制)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或者问,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究竟如何转型? 尽管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普遍遭到质疑,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成功案例似乎并不鲜见,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和普鲁士①,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东亚奇迹”②,再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持续30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③。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政府(或当年的朝廷)所实施的发展战略看起来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如何对此类现象给出理论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的一大挑战。面对现实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尤其是以政治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为主的比较发展研究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形成了一个名为“发展型政府”(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思潮。 “发展型政府”概念的诞生缘于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所谓“发展型政府”,意指通过产业政策推动经济成长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拥有一批具有强烈发展意愿的精英,他们超脱于社会力量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有能力自主地制定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并最终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所管辖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④。之后,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界,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北亚拓展到其他地区⑤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⑥,从而使发展型政府学派发展壮大。 从此,“发展型政府”这一标签不再专属于东北亚经济体,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2001年,发展型政府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出版了《“余者”的兴起:后发工业化经济体对西方的挑战》一书,将发展型政府进一步解读为对西方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挑战,也就是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有别于自由市场主导型之外的新发展模式,即她自称的“修正主义模式”⑦。 一、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面临挑战 然而,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一蹶不振以及东亚诸多经济体在1998年陷入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展型政府理论也陷入了信任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作为新自由主义重镇的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指出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蒙受了失去的十年,以“权贵资本主义”或“关系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日本模式”丧失了声望,其根源就在于弘扬政府主导型发展的人士迷信政府:相信政府能选出赢家,相信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以驾驭市场,相信政府能确保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永远屹立不倒。因此,发展型政府理论体现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即相信国家经济官僚高人一等的知识、洞察力和责任感。这篇题为“重访‘修正主义者’:日本经济模式的兴起与衰落”的文章高调宣布,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是没有出路的⑧。 实际上,更早发表的、也更有名的批判性评论,是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4年年末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出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克鲁格曼在这篇后来引证次数超过三千的著名文章中断言,亚洲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巨额投入而不是技术变革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会随着资本回报率的递减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依赖于强势政府动员资源以刺激经济成长的所谓“亚洲模式”,只不过是一种仅仅具有警示意义的神话,并不构成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质性挑战⑨。克鲁格曼后来因其在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获奖却强化了其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观点在大众媒体上的权威性。 当然,这些批判意味浓厚的文章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学术思潮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总是随着现实世界的变化潮起潮落。当新一波金融危机于2008年在新自由主义的家乡美国爆发之后,世界各地非学术媒体对发展型政府理论的热情又重新抬头。抛开相关的意识形态争论,有关发展型政府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究竟会有怎样的命运,也就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性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停止争论。 争论归争论。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化冲击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东亚发展型政府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动员和调配能力受到了极大的侵蚀。在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日趋走向制度化,原本颇具一些神秘色彩的政商关系也日渐公开,而大企业也在新政治舞台上有了新的角色,不再单纯是发展型政府的政策抓手。因此,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政府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就开始告别发展主义模式。无论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应对,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型,逐渐回到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的轨道上来。简而言之,乍看起来,发展型政府转型的方向似乎都是走向新自由主义,但转型的过程无疑是艰难曲折的。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各地政府在应对危机上出现进退失据的病症,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其发展型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漫长“阵痛”。这一“阵痛”的时间和烈度在不同的经济体呈现完全不同的格局。 就日本而言,发展型政府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之前就受到侵蚀了。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和国际学界关于发展型政府的讨论迅速降温,致使有关发展型政府与经济高速增长和泡沫迅速膨胀的关联性不明不白。部分针对这一问题,同时针对有关日本繁荣和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进行了少有的抽丝剥茧般的研究,给出了意涵丰富的解答。依据高柏的分析,发展型政府理论对于日本的描述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基于三大错误的假设:第一是认定政府主导了政策制定,而企业仅扮演从属性角色;第二是认定发展型政府的工作重心是挑选赢家;第三是认定政府有能力而且一定会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化地配置到最有效率的产业甚至企业之中。基于其本人的实地考察以及大量学术文献,高柏告诉读者,实情并非如此。发展型政府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计划者,而是私有企业的赞助者和保护者。在日本,政府组织、倡导和担保了私有部门中非常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大企业中的终身就业和小企业间的卡特尔,从而一方面推动经济成长,另一方面保护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型政府的工作不仅仅是挑出“赢家”予以扶持,而且也要保护经济效率意义上的“输家”,进而在福利国家建设不足的同时着力发展一种福利社会,让民间企业发挥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日本“发展型政府”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既促成了日本过去的成功,也导致了日本现在的停滞⑩。发展型政府对于日本来说,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发展型政府高度发达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也异常曲折。 发展型政府在台湾地区的转型也近乎失败。根据阿姆斯登的高足、台湾地区学者瞿宛文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共振型转型。在政治上,台湾地区逐渐走向了竞争性民主体制,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因素,两大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主导了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导致台湾地区在诸多发展战略的形成上出现党派极化现象。由此,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关涉到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方面,台湾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1)关于优先发展领域的共识无法形成;(2)台湾地区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定位无法厘清;(3)经济意识形态发生了从发展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然而,沿袭着发展型政府传统的台湾地区当局,无论由哪一个政党主政,都未能以有效的方式回应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行使适当经济职能的挑战。最后的结果,一方面,台湾在经济发展上欲振乏力;另一方面,台湾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和社会保障(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所认可的社会安全网)改善方面也进展迟缓,而这两方面恰恰应该成为发展型政府向新自由型政府转型过程中政府施政的着力点(11)。 相比较而言,韩国虽经阵痛,但其发展型政府的转型却相对平缓一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的中产阶级壮大,劳工阶级的政治力量也在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以及经济自由化的进展,政府与大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企业自主性加强,发展型政府的权力遭到侵蚀,强政府指导大企业的政商关系模式难以为继。发展型政府的遗产及其转型的“阵痛”,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导致韩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稳定,这也构成了亚洲金融危机重创韩国的内部因素。在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一方面在国际组织的压力下推进了新自由主义式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在金大中主政期间,军政府时期常规性使用的很多市场干预政策被取消,但另一方面由于路径依赖,其发展型政府依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 发展型政府的转型艰难,或者说发展型政府的韧性,主要缘于发展型政府所引发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发展型政府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催生新型产业的同时也保护缺乏竞争力或产能过剩的产业;更有甚者,发展型政府在推进经济成长的同时也滋生了裙带资本主义(13)。面对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压力,嵌入于传统政商关系的政府无力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发展主义国家、庇护主义国家、福利主义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并存导致政府转型的阻滞。新的经济增长点,即战略型产业,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恰在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优等生日本发生了。 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三种转型前景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勃兴的大背景下,发展型政府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本身的转型,正成为比较发展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之一。学者对发展型政府转型的不可避免性,一般没有异议,但对其方向和路径却有很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仔细分析,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但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研究文献并非只是表达其中的一类看法,更多的情况是其中两类甚至更多看法的组合或调和。 (一)新自由主义转型论 新自由主义转型论认为发展型政府将会或快或慢地转型为新自由主义政府,而新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唯一正常模式,尽管不排除在这一大同模式的内部存在一些小异。新自由主义转型论在众多经济学家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但亦有不少政治学家持此看法。有学者主张,在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压力下,发展型政府走向衰亡并走上新自由主义之路是不可避免的(14),而新自由型政府形态能否顺利形成并取代原来的发展型政府,是相关经济体能否走上社会经济发展新良性循环的关键(15)。 由于“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内涵过于丰富,“新自由主义政府”这一概念的外延自然也有些边界不清,因此有些学者倾向于更加具体地加以论述,认为发展型政府的转型方向是规制型政府(the regulatory state),即国家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基本上处于无为状态,但在完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制(尤其是社会性规制)方面理应也必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16)。亦有学者论证,新自由主义政府与规制型政府本身就不是一组对立的范畴,而在全球化解除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旗号中,无论是正在从发展型国家转型之中的日本,还是经受了撒切尔夫人新自由市场制度洗礼的英国,市场自由度无疑增加了,但解除管制的运动实际上走向了重新管制,规则增多了,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反而有了更多的保障(17)。 当然,有不少专门研究规制型政府的学者指出,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发展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的转型,并没有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快步前行,即政府在加强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和减少管制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性方面,进展十分缓慢。即便是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在银行管制领域,受制于政治压力的高度自由裁量性行为依然广泛存在。换言之,虽然发展型政府正在转型,但政府的发展型行为依然比比皆是,而规制型行为却常常疲软。因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发展型政府与规制型政府的混合体不具有可持续性(18)。 在发展型政府理论之中,发展型政府与规制型政府构成了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开山鼻祖、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指出,所有地方的政府都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只不过干预的理由和方式有所不同。在美国模式中,政府的规制型取向远远压倒了发展型取向。与关注哪些经济领域应该取得实质性发展的发展型政府有所不同,规制型政府主要关注如何建立客观的规则和程序,以确保经济竞争的充分(19)。针对这一点,有学者质疑,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发展型政府与规制型政府的二元对立还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两者并不是处在有你没我的二元对立格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点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发展中世界,都是一样的。因此,学术探究的重点并不是探究发展型政府如何向规制型政府转型的问题,而是应该研究两种政府类型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条件(20)。 (二)发展主义持久论 发展主义持久论强调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韧性,即认为各地的发展型政府将会在内外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下进行改革、调适、创新,也不排除某些地方会出现短时期内的政府崩溃现象,但是发展主义依然会展现其韧性和活力,而发展型政府向新自由主义政府转型从而走向“正常化”的论说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与此同时,也有众多学者,尤其是在发展型政府理论建设方面贡献卓著的学者,否认在全球化时代会必然出现发展型政府的衰亡,更不认为发展型政府必然会向新自由主义政府转型。这一点最为鲜明的表达来自澳大利亚学者琳达·维斯(Linda Weiss)。她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全面质疑全球化将导致世界各地的政府实现新自由主义式“正常化”的流行看法。此文提出了五大命题:1.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赶超永远存在,因此以制定和实施赶超战略为己任的发展型政府不可能退休;2.经济自由化固然不可避免,但新自由主义绝非各经济体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唯一路径,具体路径的选择无可避免地受到各地已有制度结构、社会结构和特定政治目标的制约;3.发展型政府受到冲击,尤其是其原有的一些政府能力受到侵蚀,并非全球化或经济自由化自然而然导致的结果,而是国内政治格局改变(例如在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均已出现的政党轮替)所导致的结果;4.亚洲金融危机本身并非发展型政府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确证,而只不过表明发展型政府自身需要更具有适应性而已;5.日本的停滞并不能证明发展型政府丧失活力,而是证明其原有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既不具有鲜明发展主义取向、也不具有强烈自主性的政府,这种软弱的政府只能屈从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制定并执行“没有输家”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成为输家。在她看来,世界各地的发展型政府处在改革和转型之中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有可能会强化适应性,有可能会进行自身的创新,也有可能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因自身疲软而衰落,但是绝不可能出现向新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趋同现象,而在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然呈现多样性(21)。2005年,维斯又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证全球化并不会使各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降低,反而全球化会产生一种“政府增强式效应”(state-augmenting effect),让各地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继续扮演核心角色(22)。 美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家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是发展型政府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2006年,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对发展型政府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进行了展望。2008年,他将这份演讲词进行改写,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的形式发表。这篇论文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在二十一世纪,发展型政府将继续在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上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其二,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型政府必须基本上走出既定的模式,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很显然,发展型政府自身的转型势在必行,而转型的核心在于发展战略不再以资本积累为中心,而是致力于能力建设。与此同时,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心也不再是政府与商界(或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的亲密关系(23)。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发展型政府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上,一大批参与建构发展型政府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的学者,修正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由于不再把研究重心放在详细分析政府发展主义意愿的来源以及夸大经济技术官僚接近韦伯主义理想类型的行为,不再强调发展型政府具有唯理性主义“官僚自主性”从而能高瞻远瞩地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经济政策(24),而是强调政府所嵌入的各种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强调政府行动所受到的历史和制度因素的制约,这些后期的研究与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早期成果拉开了距离。 (三)市场经济多元论 市场经济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体由于历史形成的制度、结构和文化的遗产,其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神级表现的发展型政府理论不具有解释力,而学术的发展重心应该转移到对多样性的研究上来。 在有关发展型政府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论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多样性”这个主题。事实上,所有不认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论述的学者,都反对市场经济体制唯一论,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多样性。在国际学术界,主要在经济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研究热潮,形成了所谓“VoC研究路径”(the VoC approach)。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了。 大体来说,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可分为两大学派:一是发展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二是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两派学者的共同点是认为市场经济绝非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刻画的一种模式,而是呈现多样性,其根源来自“制度的互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或“制度的嵌入性”(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前一种表述多为政治学家所使用,而后一种表述则为社会学家所偏好。两派的相异点在于其研究方法论,前者信奉方法论个人主义,后者尊崇方法论整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选择特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作为自变量,来解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包括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倾向于把所解释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置于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整体之中加以考察。 历史制度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考察,聚焦于两类市场经济体制,即自由型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和协调型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两者在四个维度上呈现显著地差别,即(1)在公司治理上,前者强调股东主权、职业管理者主导日常运营,而后者强调利益相关者主权,重视雇员的权益;(2)在金融结构上,前者是资本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投资银行发达,而商业银行相对边缘化,而后者商业银行发达并且在企业融资和股权中都占主导地位;(3)在劳资关系上,前者奉行市场自愿主义和有限度的政府规制,而后者社会法团主义、三边主义和企业经济民主或终身雇佣;(4)在社会保护上,前者倚重于自由主义型福利国家,而后者建设法团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型福利国家(25)。很显然,这两种市场经济理想类型的划分,多基于英美资本主义和德日资本主义的对比,而后者又被称为“非自由型资本主义”(26)。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将各类行动者(个体、公司、社团、政府等)的行为动机分为两种,即追求自我利益和履行义务责任,同时行动者之间权力配置和行动协调的机制分为五大类,即市场、社群、私立科层组织(大型公司或非营利性组织)、公立科层组织(政府机构、公立组织)以及协会或网络。由此,经济社会生活的协调机制可以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而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发展型政府理论所关心的经济发展的推动,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来解释(27)。由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28)。 无论哪一种版本,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吸收了发展型政府理论的部分成果,但其理论架构和探索视野比发展型政府理论更加宏大,更具有包容性,而且对政府以及经济官僚的假定已经不再具有唯理性主义和唯道德主义的色彩。正是在这一学术发展的背景下,有学者指出,发展型政府理论对东亚政治经济景象(尤其是政府的所作所为)的描绘是不完整的,如果要对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解释力,一个理论不仅需要聚焦于成功的产业政策,也需要覆盖其他政策领域,如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收入分配政策,同时在这一理论的研究框架中,必须把国家行动及其政治经济后果放在更大的社会网络和制度背景当中去分析(29)。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近来也破天荒地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200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领衔撰写的著作《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该书给出了四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即(1)寡头垄断型:其有弊无利,具体表现在高度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由少数企业主宰),以及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2)政府主导型(或国家导向型):其利在于有可能短期内提升企业、行业或国家的竞争力,其弊在于极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过度投资、资源配置扭曲)和大面积腐败,最后形成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3)大企业主导型:其利在于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也有助于提升本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但其弊在于创新不足,垄断加强,发展容易失去动力;(4)企业家型,其利在于拥有无穷的创新动力,其弊在于规模不经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论著,该书对企业家型资本主义赞赏有加,但同时认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应该也有大企业主导型资本主义的适当空间。至于具有短期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最好避而远之(30)。 三、简短的结语 国家与市场的何种关系以及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更加有利于经济成长,是经济学、政治学、发展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核心课题之一。从全球视野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并非罕见,发展型政府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模式不会终结,而发展主义理论自然也不会消退。但毫无疑问,发展主义理论本身需要发展,以新国家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发展型政府理论”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描绘为少数政治经济精英高瞻远瞩地引领市场前行的图景,不但没有说明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新的发展主义理论将重点放在制度的多样性,探究哪些种类的制度组合能以何种方式促进经济成长,这种新制度主义的思考路径有广阔的前景。 政府干预是否必要其实并不是有意义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干预,或者说政府干预能否以顺应市场机制甚至强化市场机制而不是破坏、扭曲甚至取代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进行。如果能超越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那么诺思关于国家的困惑,就会有全新的解答。也只有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新实证研究,不论是发展型政府理论还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才能有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前景。 注释: ①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②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Vol.24,No.1(1991),pp.109~126. ⑤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中译本参见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朱天飚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 ⑥Linda Weiss and John M.Hobson,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中译本参见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⑦Alice Amsden,The Rise of "the Rest":Challenge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⑧Brink Lindsey and Aaron Lucas,Revisiting the "Revisionist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conomic Model.Cato Institute:Trade Policy Analysis,No.3,1998. ⑨Paul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Vol.73,Issue 6(1994),pp.62~78. ⑩Bai Gao,Japan's Economic Dilemm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1)瞿宛文:《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台湾发展型国家的不成功转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84期(2011年9月),第243~288页。 (12)Yong Soo Park,"Revisiting the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5,No.5(2011),pp.590~606. (13)David C.Kang,"Bad Loans to Good Friends:Money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Issue 1(2002),pp.177~207. (14)Yun Tae Kim,"Neoliber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9,No.4(1999),pp.441~461. (15)Carlos Aguiar de Medeiro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al States",Panoeconomicus,No.1(2011),pp.43~56. (16)Giandomenico Majone,"From the Positive to the Regulatory State",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17,No.2(1997),pp.139~167. (17)Stephen K.Vogel,Free Markets,More Rules: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18)Andrew Walter,"From Developmental to Regulatory State? Japan's New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The Pacific Review,Vol.19,No.4(2006),pp.405~428. (19)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8. (20)David Levi-Faur,"State Making and Market Building for the Global South:The Developmental State vs.the Regulatory State?",Jerusalem Papers in Regulation & Governance,Working Paper No.44(July 2012). (21)Linda Weiss,"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Adapting,Dismantling,Innovating,Not 'Normalizing'",The Pacific Review,Vol.13,No.1(2000),pp.21~55. (22)Linda Weiss,"The State-augmenting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0,No.3(2005),pp.345~353. (23)Peter B.Evans,In Search of the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al State.Brighton:Centre for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iversity of Sussex,Working Paper,No.4,2008. (24)Vivek Chibber,"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7,No.4(2002),pp.951~989. (25)Peter A.Hall and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6)Wolfgang Streeck and Kozo Yamamura(eds.),The Origins of Non-liberal Capitalism:Germany and Japan in Comparison.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 (27)J.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eds.),Contemporary Capitalism: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8)Colin Crouch and Wolfgang Streeck(eds.),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 (29)Chung-in Moon and Rashemi Prasad,"Networks,Politics,and Institutions",in Steve Chan,Cal Clark,and Danny Lam(ed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p.9~24. (30)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和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标签: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全球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