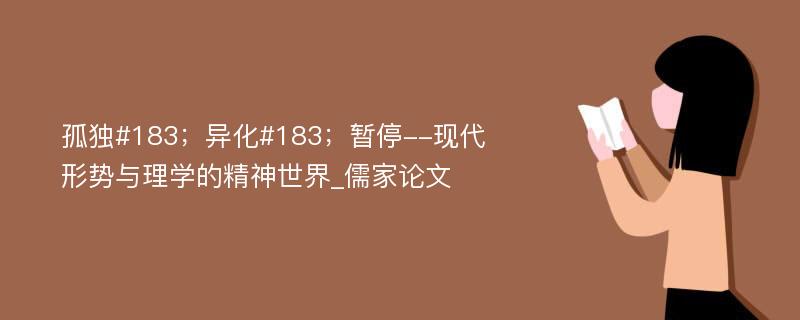
孤独#183;疏离#183;悬置——现代境遇与新儒家的精神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境遇论文,孤独论文,精神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些年来的当代儒学研究中,人们似乎多言“境界”,很少论及“境遇”。实际上,现代新儒家普遍的道德心性及其开显的形上境界要通过具体的、差别性的“境遇”来体现和落实(此“境遇”包括个体的、社会的和时代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个人遭遇又往往与社会、时代的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特别是对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更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与生活的关系也就是“境界”与“境遇”的关系。无视时代的特殊问题和每一位儒者独特的生命感受,片面强调儒家思想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则此“普遍性”至多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此“超越性”也只是一种虚设的(概念的)超越性。一个真正以儒家的圣贤理想为依归的人,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一个”儒家,在其希圣希贤的追求中,必然折射出时代的色彩和闪现出个体生命的光辉。
一
在叙述牟宗三生平学行的文字中,以蔡仁厚整理、撰著的最为集中、最为重要、最具有史料价值。从了解牟宗三生平的角度看,当属蔡仁厚在《鹅湖月刊》上连载的《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一文最重要。其中的基本材料来自牟本人的论著,特别是其《五十自述》,但在细节上有些考订和补充。
一部《五十自述》为了解牟宗三的生平学行提供了便利。依蔡仁厚所述,该书于1956年冬开始撰写,于次年完稿,时年49岁。(注: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行著述纪要》,《鹅湖月刊》第165期,第7页。)作为一部自传体的著作,《五十自述》极具特色,有人称它为“牟氏所有著作中最富色彩、最足以传世的一部”(注:林镇国:《当代儒家的自传世界》,《清华学报》新23卷第1期,第116页。)。
若把牟氏的《五十自述》与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作一比较,当饶有趣味。《三松堂自序》写得清醒、理智,不动声色,娓娓道来,其中大量述及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和事乃至社会、民情,作者本人的思想都被对象化了。《五十自述》所注重的不是编年式叙述,而是心路历程和存在感受。它在史学家的眼中或许称不上是一部传记,毋宁说它是一种心灵独白:无遮拦,无文饰,无做作,无自我标榜和自我美化,一任生命的本然挥发宣泄,将心灵裸露在世人面前。这确实是大手笔、大气魄,是当今所谓文人学者所不能、也不愿为的。
《五十自述》展露了牟宗三的心路历程,使我们看到他如何由一个淳朴的农村娃,一步步走入哲学的殿堂,又如何超越了理智分析和逻辑思辨而窥到了生命的底蕴。书中很大篇幅是抒发作者当下的生命感受。他在写于1988年该书的《序》中说:“此书为吾五十时之自述。当时意趣消沉,感触良多,并以此感印证许多真理,故愿记之以识不忘。……吾今忽忽不觉已八十矣。近三十年来之发展即是此自述中实感之发皇。”
依牟先生本人所述,50岁而后,其生命“集中于往学之表述”,于是有了《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以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的写作,牟先生也依此成为当代儒学的巨擘。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牟氏的学术造诣和义理规模主要表现在其50岁以后的著作中,世人也因此更看重这一时期的著作。而从主体生命的自我展开来看,牟先生在其50岁以后的著作中所表现的生命形态,似乎更为清澈、纯净、理性而圆融,而看不到《五十自述》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不过在我看来,在牟先生后期思想的发展中,《五十自述》所展露的诸种矛盾与问题并没有消解,只是没有再浮现于理论的层面,却仍然作为某种深层潜存的因素,制约着其思想的展开与理论的建构。
作为一位集深刻的思想洞见与丰富的感受力于一身的哲学家,牟先生《五十自述》中所作的抒发,实与当代儒家的客观境遇紧密地关联在一起;那些看来只是某种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折射出儒家在现时代所遭遇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从这一特定的角度解读牟先生的《五十自述》,乃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二
我也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注: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15页。)
我常下意识地不自觉地似睡非睡似梦非梦地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兄弟姐妹,觉得支解破碎,一无所有,全星散而撤离了。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彻里彻外,整个大地人间,全部气氛,是浸在那一叹的悲哀中。(注: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47页。)
家破、国亡,一切崩解。社会的、礼俗的、精神的、物质的,一切崩解。吾之生命亦因“离其自己”而破裂。此世界是一大病,我之一身即是此大病之反映。此世界是破裂的,我亦是破裂的;此世界是虚无的,我亦是虚无的;此世界人人失所受苦,我亦是“有情既病,我即随病”。但在我只是被动的反映,不是菩萨之“现身有疾”。世界病了,我亦病了。(注: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46页。)
《五十自述》中的这类文字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殊可惊异。几段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骨的孤独、悲苦和苍凉,这是我们在阅读传统儒家典籍时决然感受不到的。儒家心目中那个和谐、秩序、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世界及儒家所追求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从容洒脱等等,都一并退隐了、消散了、解构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破碎的、扭曲的、荒谬的世界和一个忧怨、无奈、失所归着的灵魂。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和对不被人理解的境遇的抗争。牟先生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与好坏;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96页。)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困厄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00页。)
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厄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02页。)此一阶段也是牟先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50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
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先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含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感受时代与社会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注:在有些论者那里,当代新儒学似乎可以等同于“宋明儒学+民主、科学”,这未免太简单化了。有的论者甚至以“现代宋明理学”界定“现代(当代)新儒学”。窃以为用“现代宋明理学”一语表述马一浮先生的理论学说,或许较之表述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更为妥帖。笔者曾从一个侧面论及熊、冯、唐、牟等人思想中“儒家”与“现代”的关系,指出:“在我们使用‘儒家’这一特殊的称谓来界定他们之前,应当首先考虑到他们同样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群,而这些知识分子乃是西风劲吹、文化失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批转型中的人物。也就是说,新儒家人物同样是生活在历史的夹缝中,同样难以摆脱心灵深处的种种彷徨、困扰、紧张与分裂。正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或许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现代’一样,新儒家人物或许也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传统’。”(《没有圣贤的时代》,《当代新儒学论衡·代序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页)事实上,在一个全新的“境遇中”,现代(当代)儒学较之传统儒学,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某种整体的、根本性的改变,此种改变在许多方面已远非宋明儒学的思想架构和话语系统所能包容。此方面《五十自述》这部著作恰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表露出来的牟宗三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固然可以从孔子反对“乡愿”及“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处得到解释,但同时亦可以成为一种当代儒家“艰难时事”之写照。当牟先生讲“我需要以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熊、牟等人的“狂傲”人所共知,人或以为其由于“狂傲”所以难为流俗接受,却忽视了其“狂傲”正是与现实中处处碰壁和不为人理解的境遇相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牟宗三之抒发既不能简单归于某种现代学人所共有的存在感受,也根本不同于佛家“人生皆苦”的体验,因而也就与向往“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先生有异。梁先生说:“我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版,第209-210页。)这其中没有历史意识,亦没有家国天下意识,直下便是个体的、宗教的感悟。牟氏所感受和抒发者,甚至与唐君毅著作中常表露出来的悲天悯人的情调亦不同。唐先生说:“忆吾年七八岁,吾父迪风公为讲一小说,谓地球一日将毁,日光渐淡,唯留一人与一犬相伴,即念之不忘;尝见天雨后地经日晒而裂,逐忧虑地球之将毁。”(注: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第1144页。)这其中所包涵的对于无常的感受和忧患,似乎更易于与佛教和基督教相契接。相比较而言,牟宗三的感受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式的”,因为其是与家国天下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
孤独根源于疏离。疏离即是脱离了自己的家,此所谓“家”当包括现实之家与精神之家。在儒家传统中,两者原是不可分的: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神之家必须在现实之家(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养育和滋润,离开后者,精神之家就无从安顿。这也是儒家区别于一般宗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家”的观念在牟先生的《五十自述》中居于中心的位置。前两章《在混沌中长成》和《生命之离其自己的发展》,可以说包含了理解牟氏思想的全部暗示,在其深层内涵上,都是与“家”的观念关联在一起的。
有趣的是,牟先生在《五十自述》中讲到少年生活,并不像早几年写作的《说“怀乡”》一文所描述的那样悲凉,相反,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种纯真自然的顺畅和谐:清明时节去扫墓,“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页。)“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页。)
四时递转,时光流逝,自然和谐中平添一份诗意的神秘与浪漫,此与牟先生在其后来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严刻、冷峻适成对照。此少年的生活意境,从年届“知天命”的牟宗三笔下写出,实际上已不是指谓一种原始的混沌,而是代表了某种生命理念,此生命理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浓厚的家园感:“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这谐和的根深蒂固的一套,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共十五年,我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那里生,在那里长,没有时间上的间隔,没有空间上的睽离,所以没有逆旅之感,也没有过客之感。”(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21页。)他甚至感叹:“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
《五十自述》的重心在于反观“生命之离其自己的发展”,此种反观同时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内省与转化,从中不难看出,牟氏皈依儒家的精神之旅远不似人们一般所描述的那样直接而平坦。
牟氏自述自15岁离开家乡到县城求学始,便开始了一种“耗费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扑着的一个对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这也就是所谓“生命之离其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相当漫长,它不仅包括牟先生早年的求学生活,而且原则上亦包括牟氏自我厘定的“直觉的解悟”、“架构的思辨”、“客观的悲情”几个思想发展阶段。我们来看下面两段话:
《历史哲学》(注:该书完稿于1952年,初版于1955年。)写成之时,吾已惫矣。纯理智思辨之《认识心之批判》是客观的,非存在的;《历史哲学》虽为“具体的解悟”,然亦是就历史文化而言,亦是客观的。此两部工作,就吾个人言,皆是发扬的,生命之耗散太甚。吾实感于疲惫。子贡曰:“赐倦于学矣”。吾实倦矣。倦而反观自己,无名的荒凉空虚之感突然来袭。由客观的转而为“主观的”,由“非存在的”转而为“存在的”,由客观存在的(“具体解悟”之用于历史文化)转而为主观的,个人地存在的。这方面出了问题,吾实难以为情,吾实无以自遣。这里不是任何发扬(思辨的或情感的)、理解(抽象的或具体的),所能解签,所能安服(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29页。)。
我无一种慰藉温暖足以苏醒吾之良知本体、天命之性,以现其主宰吾之“人的生活”之大用。我感觉到我平时所讲的良知本体天命之性,全是理解之解悟的,全是干枯的、外在的,即在人间的关系上、家国天下上、历史文化上,我有良知的表现,而这表现也是干枯的、客观的、外在的(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47页。)。
生命之“离其自己”即是生命的对象化、外在化,而对象化、外在化常常被视为“知识化”的同义语。牟先生这里说的则是另一种情况,即由于生命之一味扑着在“人间的关系上、家国天下上、历史文化上”所导致的一种对象化与外在化。这提醒我们应适度区分社会、历史层面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儒家与道德、宗教层面心性修养意义上的儒家——此在传统儒家那里可以说是二而一,而在儒家思想的现当代发展中却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笔者曾用“生命意义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张力”来表述梁漱溟在儒、佛之间所作出的取舍与抉择,认定梁先生乃是在关涉国家民族何去何从之历史文化的层面上认同于儒家,而在个体生命之终极托付的层面则认同于佛家,所以他申明自己之舍佛向儒是“替中国人设想应有的结论”的结果(注:参见郑家栋:《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拓展及其引发的问题》(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载李明辉主编:《当代新儒家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302-309页。)。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在新儒家思想的深层,民族文化之薪火传承或许较之生命意义的终极托付占有更突出的地位。与此相联系,与其说他们是道德心性、圣贤修养意义上的儒家,不如说他们是文化传承、继往开来意义上的儒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当意识(亦可以说是文化救亡意识)而非对生命意义的究极了悟和抉择决定了他们成为一名儒者,并自觉地去担当文化重建的使命。”(注:郑家栋:《没有圣贤的时代》,《当代新儒学论衡·代序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牟宗三的自我检省,至少提醒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社会、历史层面的文化使命感与主体生命的自我安顿混为一谈。
为中国文化诊病、治病的牟先生申明自己“惫矣”、“倦矣”、“病矣”,在他看来,因于某种“客观的悲情”从事历史文化之反省疏导,此仍然只是生命之“发扬”、“耗散”,是“智、仁、勇之外用”。牟先生写作《五十自述》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工夫,使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他说:
良知不但要在这些客观的外在的事上作干枯的表现,且亦要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如果这里挖了根,则良知就挂了空而为客观地非存在非个人地抽象表现,而不是真正个人地践履地具体表现。此仍是满足理解之要求,即属践履,是客观的外在的践履。外在地就客观之事说,虽属良知之理,而内在地就个人生活之情说,全是情识之激荡(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47-148页。)。
人们每每批评新儒家内倾过重,忽视且亦无力于回应“外王”层面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重蹈了宋、明儒家“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覆辙。此类批评尚不无道理,但若由此得出结论,说儒家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社会、历史的层面,内圣方面似乎不成问题,则不免失之乖离。事实上,对于当代儒家来说,最重要且亦最困难的,仍然是良知如何“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在自己生命上受用,亦即牟先生所说的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
儒学对于牟先生之为“生命的学问”,首先表现在他深切感受到“内圣”之旅的艰难。(注:儒学是否是“生命的学问”是一回事,如何把它讲成生命的学问又是另一回事。生命的学问不仅要展示生命的崇高、神圣和庄严,且亦必须体会到生命的限制、生命的无常和生命的可忧、可惧。牟宗三说:“生命虽可欣赏,亦可忧虑。若对此不能正视,则无由理解佛教之‘无明’,耶教之‘原罪’,乃至宋儒之‘气质之性’,而对于‘理性’、‘神性’以及‘佛性’之义蕴亦不能深切著明也。”(《才性与玄理·序》,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充分重视和理解牟先生的《五十自述》,不正视和理解《五十自述》所展示的生命的挣扎与奋进、生命中魔道相契的苦斗,生命中的空虚、无常和荒谬感,也就很难真正理解牟先生所讲的“生命的学问”。)应当说对于当代儒家而言,此种艰难更有过之,因为它不只是来自主体生命本身的限制,而且是来自伴随社会、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的改变所产生的诸多困扰与问题,因而它也就不仅关涉儒者的个人修为,而且关涉当代儒学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牟先生曾一再谈到现实伦理生活的匮乏对其精神生命的影响:
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注: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2页。)
苏醒良知本体以为“主观之润”之具体表现在个人践履发展过程中,是需要人伦生活之凭藉的。故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伦生活是维持“生命在自己”之生活之基础形态,亦是良知本体之具体表现而为主观之润之最直接而生根之凭藉。但是我在这里全撤了。我未过过家庭生活。孝悌在我这里成了不得具体表现的空概念(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48-149页。)。
如果认为牟氏所抒发者不过是一位早年便离乡背井、后来又飘泊于一隅的天涯游子所特有的感受,那未免太简单化了。这其中关键之点乃在于儒家之良知、心体、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在我们指出儒家之仁的普遍性、超越性的同时,切不要忘记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原本与产生、培育它的社会生活土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且良知、仁所包含的普遍性义理,必须经过具体而特殊的身心体验在现实的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体现和实现,所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一个已大大改变了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中,儒家之仁还能否落实以及如何落实?仁的普遍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意义上超越它的具体性、特殊性?此一问题并非是一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便可以了断的。
作为一种伦理象征,牟先生在《五十自述》中一再谈及他那位“白手起家”、“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的父亲,也一再谈到父亲的死去、家族的离析、兄弟姐妹的星散使他产生的“逆旅”、“过客之感”。问题在于:这并不只是在讲述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衰落的故事,因为传统的生活世界的塌陷乃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只是并非每个人都有某种自觉意识和痛切感受罢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情感“根本缺乏了培养”,“缺乏了陪衬”,“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人人都在游离中”,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家”成为一缕乡愁或一个抽象的概念。牟先生在《说“怀乡”》一文中指出:
我现在已无现实上的乡国人类之具体的怀念。我只有这么一个孤峭的、挂了空的生命,来从事一般的、抽象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之厘清。这只是抽象的怀念,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怀念(注: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5页。)。
此种抽象的、概念的、本质的“怀念”固然重要,但此抽象的、概念的东西又如何回到感性的、具体的、实际的生活、生命之中去呢?抽象的一般又如何得到生活的润泽而上升为具体的共相呢?如果没有后一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新儒家所成就者,就仍然只是某种“挂了空”的东西。
四
“挂了空”,是为“悬置”。这里使用“悬置”一语,主要是针对某种与现实生活相对待的形而上的拓展、开显和安置而言。新儒家的本意是要安顿社会人生。此安顿乃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性的、宗教性的安顿,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均可归于此列。此与历史上儒家那种彻上彻下、彻里彻外,贯通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安顿明显不同。相比较而言,或许只有梁漱溟先生早年的“乡村建设”接近于后者,却以失败告终。
从“五四”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儒家学者似乎越来越注重和凸显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层面。此一点可以说颇具深意。若从化民成俗、制礼作乐、建立日常生活的法规来看,传统儒学较之当代儒学无疑更具有宗教之实。但传统儒学之谓“宗教”乃是顺适平和、生活化的,是内在于现实生活而谋求提升、转化、点化,并不是要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有所标立,这也是儒家有别于一般之所谓宗教的重要之点。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新儒家的努力方向正是在于反抗流俗(亦可以说是反抗与批判现实),执持一种文化理想、理念,此理想、理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和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固然有理由批评新儒家“脱离实际”,但同时应当认识到,此所谓“脱离实际”乃是新儒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做出的自觉选择。牟宗三说:
我的依据不是现实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国家,华族的文化生命。一切都有不是,而这个不能有不是,一切都放弃,反对,而这个不能放弃,反对,我能拨开一切现实的牵连而直顶着这个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现实的污秽、禁忌、诬蔑、咒骂,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注: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16页。)。
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孤往的勇气和宗教的热诚,而此种勇气与热诚正是以“拨开一切现实的牵连”为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熊十力、牟宗三那里,儒家真正成为了一种宗教,成为了某种只有依赖于信息和执着加以支撑和维系的东西。
若是把熊、牟等人比喻为佛门所谓“行者”,人们定会斥为乖离,而笔者却分明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通之处。《释氏要览》卷上:“《善见律》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名畔头波罗娑。’今详,若此方行者也。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或许有人会说以“修行人”指谓牟先生并不恰当,牟先生自己曾说其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荡荡”;又说“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注:转引自唐亦男:《缺憾还诸天地》,《鹅湖月刊》第239期,第27-28页。)。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上面两段话连在一起,说牟宗三等不做修行,只是写书。殊不知对于熊、牟等人来说,写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苦行。儒家之价值系统所维系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熊、牟等人所阐发者已不再是某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处体认、加以落实的东西,因而也很难再有传统儒家那种“依于仁,游于艺”的怡然自得。“写书”同样成为一种困厄中的苦斗,成为他们追求理想的一种基本的方式(注:这里我们比较一下熊、牟两先生是饶有趣味的。就总体而言,牟先生当然更“现代”,但在某些方面,他又似乎更“传统”。熊先生以家庭生活为累赘,在早年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一封信中,他说:“昨年来忽增女儿外孙,顿令人感觉无味麻烦。老妇人性情又难说,往年,她住书院之下一室,我独住上,饭外不相见,我做我的事。今同住一屋,令人心烦。”(引自翟志成:《当代新儒学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3年版,第123页)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曾引熊氏1951年写给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其中更有“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的极端语(此信原刊于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号,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8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熊先生所言的“道德心”乃是一种孤峭的“道德心”,我们于其中似乎很难发现对传统的伦常生活(所谓“天伦之乐”)的依恋与感受。他把家庭生活与“担道”对立起来,且视著书立说为“担道”的同义语。牟宗三一生忙于著书立说,但他实际上并不以著书立说为满足。《五十自述》中始终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对传统伦理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渴求,并以自己“未过过家庭生活,孝悌在我这里成了不得具体表现的空概念”为一无法弥补的不足和缺憾。这表明他至少在思想理念上认为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应当是统一的,而这又恰恰是儒家传统的重要之点。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同时哀叹“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89页)。“安身地”乃阴宅也,足见其对于“家”的看重和渴求是贯穿其生命之始终的。)。
新儒家的兴起是以西风劲吹、儒家在现实层面惨遭失败为背景的,因而可以看作是儒家在理想层面的退守与坚持。从此种意义上说,新儒家必然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可以说,梁、熊、冯、牟等新儒家学者都是一些为理想献身的人,他们的贡献亦在于执持一种文化理想。若着眼于现实的层面,可以说他们是一些失败者。此所谓失败,主要的不是指外王事功方面的无能、无力(此在传统儒家亦属平常),而是指他们实际上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之中。此种冲突成为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冯友兰先生的悲剧正在于他曾试图通过与现实的妥协来调解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使新儒家学者常常与孤独、寂寞、焦虑相伴,也使得他们很难真正领悟和受用“从心所欲”的从容中道和“吾与点与”的自然洒脱。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安置国人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自己又似乎很难彻底摆脱“花果飘零”和无家可归的“逆旅”、“过客”之感。他们的理想及其坚忍、执着来自已经断裂的历史。他们坚信,此理想、历史与人道、人性一样具有普遍而永恒的价值,却又苦于红尘滚滚的现实中应者寥寥,使理想得不到现实的滋养和印证,这是他们种种苦闷与焦虑的根源。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熊、牟等新儒家一改传统儒家的平和中庸——他们愤世嫉俗,孤傲尖刻,怒气冲冲,动辄骂人。他们是现实的抗议者、批判者,却还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者。
熊、牟等人是一些殉道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殉道。他们的努力并非没有意义。今天新儒家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倾听者(还很难说是拥护者和追随者),其影响也早已超出了门人故旧的有限圈子。但理想的种子是否已真正获得了现实的土壤?又何时能够生根、发芽直至结出现实的果实?这其间恐怕还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和艰难不懈的努力,其中的首要之点在于:在已经大大改变甚至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体制、生活结构、文化环境中,儒家的人文理想还能否找到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能否重新建立起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