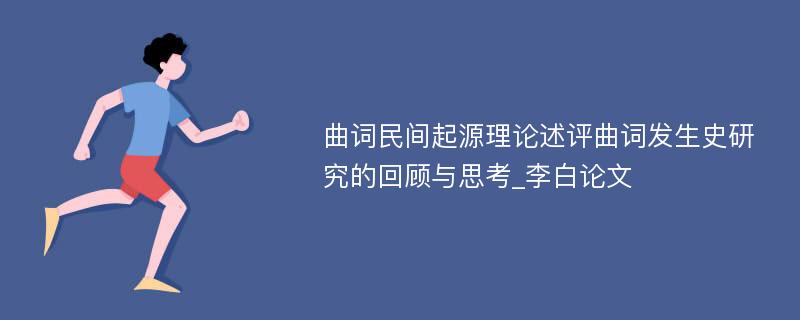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史研究论文,民间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曲词发生研究是唐宋词体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涉入一条新河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流淌?”[1]追溯一门学科的历史,对于其发生意义源流问题的追问,是探求未知的动力所在。关于曲词发生的问题,历来词家众说纷纭,迄今未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宋以降,或以为李白《菩萨蛮》及《忆秦娥》是“百代词曲之祖”;或以为词系乐府,源于六朝时梁武帝《江南弄》、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或以为词系长短句,起于《诗经》中《殷雷》、《鱼丽》等长短句之什,甚至有人认为词的始祖可追溯到唐虞时代《南风操》和《五子歌》。新词学研究认识到词的“倚声填词”属性,所以大多从词与乐关系出发对上述传统观点持否定态度,提出词起于隋代、初唐晚期、盛唐、中唐等说法。这在现代词学研究的初期,便受到了胡适、郑振铎等学者的重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个讨论的高峰。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有:姜亮夫《“词”的原始与形成》,较仔细地分别了“词”与“诗”及“胡乐”的关系;刘尧民《词与音乐》从词与音乐的关系入手,重点突破,追溯到词的源流演变。类似的文章还有胡云翼《词的起源》、霍世休的《词调的来历与佛教经唱》、田子贞《词调的来源与佛教舞曲》、卢季野《词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陈能群《论燕乐四声二十八调》、萧涤非《论词之起源》、杨宪益《论词的起源》、李嘉言《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等。当前学界关于词的发生起源问题的研究即承袭这些学术成果而来。其中两个最主流的观点便是:第一,词起源于民间;第二,词乐是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亦有学者不断对这样的观点进行反思,比如对燕乐问题的讨论,对宫廷词、文人词以及民间词问题的讨论等等。笔者对曲词发生起源问题的反思性研究也是针对这些主流观点来进行的。通过对词史发展的通观性思考和对史料的重新翻检爬梳,笔者以为词体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亦非燕乐的产物。这是我们曲词发生起源问题研究的核心观点。对此,主要是经过了如下的反思历程:
一、曲词的界定问题
“词的起源不明,主要源于对词的界说混乱。”[2]传统上对于词的界定是以词的参差句式为标准的,但是单是句式上的参差并不足以划清词与《诗经》中杂言诗、乐府之杂言句式的界限。对此唐圭璋先生较早提出了新的看法:“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词’,必然是起源于劳动人民,而绝不可能起源于梁武帝、隋炀帝或其他封建文人。其次,‘长短句’固然是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词的产生是与特定的音乐因素分不开的。而特定的音乐因素还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不把以上各点放入探讨范围之内,恐怕不易得出圆满的结果……我们知道,与‘词’相配合的乐曲,是隋唐时属于‘燕乐’系统的‘新声’。”[3]曲词源于燕乐之说,现代以来胡云翼《宋词研究》、刘尧民《词与音乐》等,已持此论。至此,则更进一步比较明确地提出用燕乐来界定词体文学。从此之后,凡是论词的起源,燕乐成为立论的源起,但是对于燕乐各人的理解又有不同。因此,燕乐界定标准的确立并没有终结词体起源的争论,反而让这一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自清季民初新词学的研究伊始,就有一块基石,即词与乐与歌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乐是词在当时存在的方式,歌则是词在当时的传播方式。如龙榆生先生在《词学研究之商榷》中说:“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4]可以说,当下的词学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来的。如“词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是隋唐燕乐,词乐是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5]虽然并不深究“燕乐”端是何物,但都承认了词与乐的关系。①肯定词与乐之间的联系,是新词学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与乐联系并不足以厘清词体,也即合乐对于词体不具有唯一性,不足以界说词体。“中国诗歌的传统就是合乐,从《诗经》到乐府,乃至后来的元曲,都是合乐演唱的,因此,‘合乐的歌词’并不能作为词体文学之专有。”[2]而词体的清晰界说,是讨论问题的基石,若没有一个对于词体的清晰界说,研究就会失之芜蔓最后无所得。
词并不是隋唐燕乐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曲子才产生的。从音乐因素来讲,乐府诗与词的关系最为密切,特别是那些与声乐歌曲直接发生关系的歌诗与词的起源应该具有亲缘关系,是清乐,而不是燕乐与曲子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的一种以律化形式来配乐的歌词。举如梁武帝《江南弄》之类虽然音乐属性上是清乐,但是由于它还不具备词的律化特征,所以还只是清乐歌诗。只有具备了律化的特征,词才能够定型化,才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被模仿和采用,成为体裁意义上的词体。词体的发生,就其音乐原因来说,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而形成的新曲子;就词体的文学建构因素言,是糅合偏取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熔铸近体诗的格律而为词律。[2]
对一贯所说的“词是配乐的歌词”,或说“词是音乐的文学”这种流行的说法要认清几个问题:第一,词的配乐性仅仅是词体漫长演变历程中某个历史时期的特质,但在这一过程中,词体的写作和传播,产生于曲却不断向脱离曲的方向发展。词体的写作与传播,脱离于曲,却又合于曲,靠的是词调,或说是格律化的词牌来保持。词的发生史,乃是近体诗格律化的结果。第二,词并不是隋唐燕乐的直接结果,而是通过曲子才产生的。就歌诗的系统来说,六朝乐府诗和初盛唐声诗,是词体发生的直接歌诗源头,而六朝乐府诗和唐声诗的音乐,是中国本土的,特别是具有江南特色的吴声西曲是其主体音乐构成②。两相比较,是中国本土来自于南朝的清乐,而不是主体来自于域外的胡乐与曲子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三,以“词是配乐的歌词”,或说是“以燕乐配乐的歌诗”来界说词,都是不够准确的。词的界说,应如此表述:词,是借鉴近体诗格律以词调来定型的一种诗歌体裁,以近体诗格律将其定型化,来表现其原本产生时期的音乐性,为其特征表现。[6]
对词体进行了初步界定之后,就可以对词的民间起源说进行考察。词起源于民间“胡夷里巷”和词源于燕乐说,是存在矛盾的。燕乐是隋唐宋时代宫廷所用俗乐的总称③,既然词乐是宫廷的,何以曲子词却又发生于民间呢?我们认为,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这是因为,初盛唐时期,朝廷对于民间乃至于中下层官员的音乐消费活动是有严格限制的,音乐歌舞享受一向是地位身份的象征,为宫廷贵族专有。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对于官员家庭中的丝竹欢娱,直到天宝十年才作为一项皇恩浩荡的新政而有所松动。这说明,士大夫官僚家庭中酒令歌唱和妓歌筵席的盛行,也是此后才开始的。依赖音乐成立的词体不可能产生于盛唐之前的民间甚至是一般士大夫阶层中。
二、词体发生前的音乐文学研究
词体的发生一方面是清乐发展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音乐文学不断律化的要求。若对词体发生前的音乐文学史进行一番考察,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清商乐发端于曹魏建安时期,而非一向所说的北魏时代。就其本质意义来说,可以视为建安之后隋唐之前也即魏晋南朝时期的宫廷俗乐。清商乐主要是由相和歌辞的清平瑟三调发展而来的本土俗乐(而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主要是外来民族的音乐),其发展线索主要是清商乐从曹魏政权的北方随着晋室东渡来到南方并与当地的吴声西曲融合,成为新的江南清乐。北魏时期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时,收其声伎,把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同时,南方的清乐继续发展,成为梁陈隋的清乐曲子,到隋代九部乐和初唐十部乐,清乐就成为其中一种,并入了燕乐的概念当中。我们可以将曹魏开创时期或说开创于北方的这种宫廷俗乐称为清商乐,将南朝的吴声西曲称为清乐,以区分这两种略有区别的音乐。曲词未能产生在清商乐、游宴诗、娱乐审美盛行的建安时代,而要到盛唐之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即是从建安到初唐之前都还是乐府诗的时代,乐府诗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制约着这种歌诗文学,同时对诗歌格律的认识还不成熟,还不具备一种从形式上加以定型化的方式和手段,而要等到近体诗格律完成,才有可能实现曲词创制和传播新的音乐消费和文学传播的方式。[7]
清乐和六朝乐府诗具有声乐属性、江南文化属性、精练属性、宫廷贵族属性和宫廷艳歌属性,而正是这些属性,使清乐和六朝乐府诗成为盛唐之际曲词发生的直接源头。具体来说,北朝、隋代与唐初的燕乐,乃是一种胡乐大曲并非歌唱之乐,构不成声乐演唱曲子的音乐形成基础,而南朝清乐是一种声乐表演的音乐。盛唐时代玄宗由燕乐大曲向声乐转变,使清乐获得了新生,而诗体格律的发展也日益成熟,此时,清乐歌词才脱离南朝乐府歌诗的外形,与近体诗声律结合,成为一代新的声乐歌唱形式,促成了曲词的诞生。清乐及与之相配的南朝乐府歌诗所具有的江南属性,在音乐体制上表现为短小灵活的情爱表达。也因此,曲词在发轫之初,就具有浓郁的江南色彩,也皆为短小灵活的小令。南朝乐府诗的精练短小特点,一方面是音乐上由大曲而走向短小灵活的曲子之趋势,另一方面则是诗歌史上近体诗发展过程中律绝句数、字数的限制。这种精练短小的特征也可视为其后近体诗和曲子词时代到来的一次预演。清乐及六朝乐府诗作为六朝宫廷文化和宫体诗的重要构成,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清乐经由法曲的中间环节,成为盛唐曲子的源头,从而奠定了词乐的基础;第二,清乐歌诗,经过音乐的约束,日益走向精练和格律化,从而成为近体诗形成的基础,并进一步成为曲词文学的基础。[8]隋代初唐时代的燕乐,其本质是舞乐和曲乐,而清乐的本质是声乐歌唱,这直接影响着以后曲子、曲词的发生。[9]
考察隋唐间音乐观念和音乐功能的变革,我们会发现隋炀帝的嗜好音声以及歌诗创作,到唐初作为易代反思的结果,并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相反,作为大曲音乐文化的九部乐十部乐以其宫廷宴乐的需要被承继下来。一直到中宗时代,音乐的纯娱乐性功能才得到发挥,即著辞歌舞作为演唱形式的发展,而这对于盛唐词体的产生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盛唐时代的音乐变革和乐舞制度变革对于曲词的发生发生了直接的作用。盛唐音乐变革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态为:1)唐玄宗由于对音乐的精深造诣和具有个性的艺术生活方式,将此前宫廷朝会的正式宴享音乐蜕变为个人私宴的新兴音乐消费形式;2)新的音乐消费形式,带动了音乐表演的小型化、娱乐化等特征,随之出现了以声乐化演出替代传统以舞曲、器乐曲为主要表演形式的音乐变革;3)唐玄宗喜爱的新兴音乐,并非传统的以胡乐为主体的所谓燕乐,而是以本土清乐为主体的法曲,法曲成为盛唐音乐的变革契机;4)初唐后期的音乐享乐观念和朝廷局部化声乐爱好的音乐消费形式,对于玄宗时期音乐思想的解放,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意义。④就盛唐法曲的本质来说,法曲是对燕乐的变异和对本土清商乐的回归,或说是在清商乐基础之上糅合里巷胡夷之曲,借鉴外来燕乐对传统清商乐的改造。法曲有如下的主要属性:
1)它是以清乐为主的宫廷音乐,所谓“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正说明其本身不是胡夷里巷之曲,才会去“杂用”之。2)这种法曲,应该不再是隋代初唐的杂糅歌舞、器乐的大型宫廷表演使用的大曲,而应该是声乐演唱性质的曲子:“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有“歌者”,说明是歌唱性质的曲子,既是唱曲,就需要歌词,没有合适的歌词,乐工就自行编撰一些歌词填入曲中。由于乐工不是专业的词人,因此,“其五调法曲,词多不经,不复载之”,歌词没有文学审美意义,也没有得到正式的记载,没有流传下来。3)这种法曲,与梁武帝时期的清乐性质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融合江南吴声音乐以及胡夷音乐。所谓“里巷”之曲,可能主要是指江南吴声西曲。4)正像梁氏法曲由梁武帝创制一样,开元法曲,应该也是主要由玄宗本人亲自创制的。《明皇杂录》记载:“上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10]63所谓“自教法曲”,充分说明此曲只应宫廷有,只有皇帝等少数人精通,因此,需要帝王等亲自教习。这条资料同时证明了,梨园是专为教习法曲而设立的。段安节《乐府杂录·雅乐》条:“次有登歌,皆奏法曲,近代内宴,即全不用法曲也”,而宫廷正式宴会是不能使用法曲的,仍旧使用十部乐。5)法曲和道曲是包含的关系:“梁武的法乐是佛曲,唐代的法乐是法曲。唐法曲中含有道曲成分,即含有佛曲的成分,事实上法曲中又直接含有佛曲的成分。”[11]556)法曲的音乐属性主要是清乐,而不是隋唐燕乐。这可以参看《燕乐探微》。
这样的音乐乐种变革,直接冲击了盛唐的音乐制度:将传统的按乐曲种类分类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彻底打乱,改为坐部乐和立部乐。具体的变革则包括了至少五个方面的内容:1)太常和鼓吹署的宫廷乐工;2)二部伎制度;3)梨园法部;4)内教坊;5)小部音声。这些变革标志着这一时期的乐舞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的胡乐到以清乐吴声的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乐歌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当然,这一过程中对胡乐因素的吸收,包括打击器乐进入到华夏本土音乐当中,则使得清淡素雅的清乐法曲增强了节奏感和音乐的约束性,为后来与之相配的词体文学的律化,创造了部分音乐条件。
前论可知,词乐发生史的演进过程,从六朝清乐到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盛唐法曲兴盛之后的声乐盛行,词乐方面已经基本完成了词体发生的准备工作。从乐府与音乐史相互吻合的乐府歌诗演变史视角来看,其实,长短不齐的歌辞形态早就在南朝梁武帝时代就已经具备了雏形,到隋炀帝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不论是从配乐歌辞的音乐角度,还是从长短不齐的外在歌辞形态,都已经具备了词体发生的条件。有声之乐的声乐史和有乐之声的歌辞史,两者都已经做好了诞生词体的孕育准备,那么曲词何以不能在梁武帝,或者是隋炀帝手中诞生呢?这是由于,作为曲词的一个重大因素,即供借鉴曲词进行格律化的近体诗因素,尚未准备完毕。万事俱备,唯欠东风,这近体诗的最后形成、成熟,就是等待或说是催生曲词生命诞生的第三个要素。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曲词发生之前的近体诗形成历程,即初盛唐时期的近体诗发展成熟历程。
初唐诗坛,主要由宫廷内外两部分诗人构成,其中宫廷诗人和宫廷诗占据主流,宫廷诗人的主要使命是完成了对诗歌本身的律化,而宫廷外诗人则完成了诗歌题材和诗风的转型,实现了诗歌由初唐向盛唐的转变。具体说来,初唐的近体诗律化成型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李世民为中心的第一代宫廷诗人的创作,从诗歌字数的精练,到对偶的广泛运用乃至声律的成型,都作出了贡献;上官仪代表的龙朔变体,将诗歌的词义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之对,已经从一般的词性音义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配置;文章四友和沈宋代表着近体诗格律的成型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近体诗在声律方面的渐进历程,同时,在近体诗的内在形式即表达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传统线性结构向对仗性结构的转型。从乐府的角度来看,由于音乐体制的变革、政治环境的变化等诸种因素,六朝乐府逐渐呈现出去声乐化的倾向,融合了一定律化因素的七言歌行反而盛行起来,体现出了律化近体化的时代精神。乐府七言歌行多不入乐,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的音乐消费之歌词形式以唐声诗为主,且多围绕宫廷来展开。[12]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倾向,乐府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歌词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用以满足音乐消费对声乐歌词的需求。曲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一直到中唐时代,词体形式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可以将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看做词体发生的前夜。
绝句声诗与长短句除了齐言与长短句的不同之外,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唐声诗还不是定型化的律词,但与乐府诗比较,唐声诗的定型化程度,已经远超乐府诗。可以说,唐声诗可以确认为词体发生前夜的一种配乐演唱的歌诗形式。在玄宗开天之际发生的音乐变革,词人的作者群体还没有及时产生,对于短小声乐歌词的需求便使得截句为词大受欢迎,同时,从盛唐到晚唐,亦不乏从六朝清乐或大曲中摘遍而为声乐歌诗的情况,这都可视做向曲子词转换的重要环节。声乐演唱对于声乐曲和声乐歌词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旺盛,使得盛唐以来的优秀诗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一时代的潮流之中,从而最终引发新兴曲词的发生和确立。
三、词体发生确立研究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确认,词体发生的音乐、诗史准备在开元天宝间已经完成。无论是词体发生的音乐条件还是其诗史准备均是以宫廷文化为核心产生的,与民间无涉。深刻的反思民间观,不仅对理解曲词,甚至理解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脉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在民间观支配下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一边断言民间文学如何如何,一边讲授一部以宫廷贵族文化为核心的上古中古诗史。面对着这样的矛盾而不进行反思,我们将不能还文学史以基本的真实。简言之,汉魏到盛唐,整个文化的中心在宫廷。汉魏时期的诗歌,常以帝王宫廷为中心而作;南朝以来,九品中正制带来的中央集权不得不退让为世族为中心的政治制度,世族文化成为六朝的文化中心所在。齐梁以降,帝王皆为世族,宫廷成为世族政治和文化的代表、代言,六朝仍然是宫廷文化为中心的时代。隋代以来,实行科举制,是对隋代以前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反拨,具有深远的影响。科举制所产生的强大的士大夫集团,势必成为下一时代新的文化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隋唐政治制度,科举与世族并存,世族势力更是大于新兴科举势力。因此,约略可以说,魏晋以来至盛唐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初唐后期,四杰、陈子昂这些原本是宫廷文化成员的诗人,由于政治斗争的倾轧,由宫廷而走向四野,遂为宫廷文化反拨之先驱。于是,盛唐发生第二次文学觉醒,诗词分野,诗渐次走出宫廷,曲词却在宫廷的温床上和摇篮里孕育诞生,先天地携带着宫廷文化享乐消费的性质。
词体并非发生于民间,而恰恰是发生于盛唐宫廷,并由李白完成了创制词体的历史使命。由大诗人李白首先创制,更进一步说明了词体与诗体,特别是与唐诗之间的血缘关系。[13]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清平乐》五首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为李白的应制词创作,而《菩萨蛮》、《忆秦娥》则是李白借词体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李白词确为词体发生的标志。当然,在李白完成创制词体文学形式之后,声诗形式依然流行,直到晚唐。
为何李白能够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而以王维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诗人群体却不加入到这种词体写作之中,甚至是在李白创制词体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词体亦没有被士大夫文化所接纳?在盛唐时代发生的文学与诗体自觉,可以说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和可能。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评,客观上要求出现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概言之,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多地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为李白的宫廷词创制提供了契机。王维的宫廷应制连同他的宫廷乐府歌诗,都只能是王维的应景与应酬之作而已,这与李白起自草莽而乍入宫廷的兴奋与得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李白与王维二人分野的本质所在。[14]
李白之后,词的诗史接纳过程是漫长的。应制、应歌体现了词的接受者对于词体产生和发展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早期应制词即席演唱,到太白体方具词体意义,太白体应制词奠定了早期文人词的女性化特征。词本体对其有个漫长的接纳过程,直到白乐天体、温飞卿体才实现对太白体的呼应和回归,标志着早期应制词历史使命的完成。[15]
中唐中前期的文人词写作有一个缓慢的演变历程。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刘长卿、王建的长短句词,是词体发生史中间的重要链条。此五位词人中,其中四人的人生经历都有着与宫廷生活密切相关的关系,张志和曾经待诏翰林,韦应物、戴叔伦有着早年在宫廷三卫、诸卫的人生经历,王建有过太常丞的仕宦经历。因此,他们成为李白宫廷应制词之后的传人,并连接着以后温庭筠和花间体的宫廷风格词体写作。[16]
中唐的俗文化对于曲词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安史之乱”极大地推动了包括音乐消费和诗词写作的世俗化、通俗化。“安史之乱”造成了数万宫廷乐工的四散逃亡,而这次动乱的深刻教训也使中唐宫廷有着弱化宫廷歌舞消费的趋势。包括佛教俗讲等在内的全方位的文学通俗化过程,对曲词的发展与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中唐元和、长庆时代,仍然是声诗与词体并行的时代,而且声诗仍然占据主流形态。这是我们对词体发生史演变到中唐时代的一个基本认知。这一时期,以白居易、刘禹锡为代表进行的词创作,是词体发生自李白创制之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志。白居易等人的词创作标志着词体阶段性地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17]
而词体写作到温庭筠,则标志着词体发生史阶段的初步完成。东坡之“以诗为词”,东坡之后(所谓后东坡时代)的诗化革新,倍受关注,却鲜有人注意到飞卿诗与飞卿词之间的关系。[18]其实,就唐宋词史的范畴来说,诗之于词体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飞卿体即是以晚唐诗风入词,以其特有的温李诗风入词。胡仔评曰:“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正指出了飞卿乐府诗与词所共有的“造语”“绮靡”等唯美倾向。陆时雍《唐诗镜》评飞卿《兰塘词》:“深着语,浅着情,是温家本色。”这些特色,正是飞卿词的典型特征。换言之,飞卿的乐府诗,正是飞卿词体形成的温床。⑤而应制应歌的大量飞卿词创作,构成了词体的基本特征,成为词体发生史阶段初步完成的标志。
此后,韦庄对词体有了进一步的推动,花间确立的词体范式,经由温韦而为士大夫文化所接纳,可以说花间词的结集是对词体产生的一次确认。[19]到南唐后主体,词体最终完成了其发生史意义上的完型。后主之词,罕有称之为“体”者,但后主词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堪称后主体。后主体形成的过程,大体经历了早期学花间、早期文人词两个阶段:960年左右开始学花间体,但又融入一些更为浓郁的宫廷气息;归为臣虏之后,写出悲天悯人的以血书者,形成后主体的特有风格。从词史的角度来看,《花间集》940年编辑问世,飞卿体香软华贵的文风,已经在西蜀君臣那里发挥到了极致,词为艳科的属性,词体的女性特征也已经基本奠定。词,这种中国所特有的诗体形式,一方面它具有“别是一家”的特性,不具备这种有别于诗的“歌”的特质,它就没有从诗体中分离出来的基本理由。因此,诗雅词俗,词为艳科,诗承载文学的政治道义,承载社会的男性功能,而词体则一切相反,承当文学的情爱本色,承载人类的女性功能。这一点,已经由花间体给予了确立。另一方面,花间之后,词本体已经在迫切地寻求着向诗本体的回归,就词史地位而言,温韦花间,在于对词体艳科等特质的奠定,而后主词,则在花间之后,实现一次向诗本体的回归和复位,可以视为后来北宋中期东坡体的一次预演,标志着词体作为诗体一种的最终确立。[20]
通观曲词发生研究,由于近百年来白话文学观念与平民文学观念的影响,要理清曲词发生发展脉络不经过这样的反思性研究是难以进行的。笔者认为,关于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的曲子之歌诗(曲词)转型的产物;词体发生的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
四、余论
近年来,笔者围绕五言诗和曲词的起源发生问题进行研究,都指向了对民间说和无名氏说的批判。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对传统学术的颠覆,其实,笔者所颠覆的,仅仅是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现当代学术话语。从词体起源发生的研究来看,笔者试图对胡适以来的民间学术史观进行反思,推翻所谓词是由民间先创造、文人后学习的民间词史观,建构以诗人为中心,特别是以卓越诗人以及士大夫精英为中心的文学史观、文化史观,而这一结论,恰恰与古人的诗余说、李白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等较早的说法是吻合的。从五言诗起源发生的研究来看,则是对古今以来两汉说的颠覆,重归钟嵘所说的“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最早说法。就本质而言,两大起源发生研究,都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疑古思潮、民间创造思潮的否定,其本质是对传统学术的回归。
注释:
①当然,学界对于这一观点也存有异议,比如音乐史家洛地先生的观点。洛地先生持“律词”观,认为词的产生是不断律化的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A.先是(唐代的)‘律诗入唱’——梨园采时人推崇的某些‘律诗’入‘教坊曲’而唱。B.随后,(唐、五代或至北宋)出现文人‘律曲’——文人直接写‘合律’的‘曲子’。C.随后,‘和声’之‘定语’消失,改为‘实字’进入本辞。D.‘律词’——‘格律化的长短句’——我特称之为‘律词’者出现了。”可以参见洛地先生的相关论著:《词乐曲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词之为词在其律》,《文学评论》1994年2期;《“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1期等。
②所说主体音乐构成,意味着并不排除对胡乐因素的继承和汲取。
③“俗”概念和“民间”、“平民”概念的混淆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④详见笔者《论唐代乐舞制度变革与曲词起源发生的关系》一文,拟刊于《文学评论》2011年5期。
⑤实际上,诗词的渊源不仅在词的起源时期,亦不仅“以诗为词”,而是在词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整个的诗体借鉴过程。参见木斋:《论唐宋词的诗体借鉴历程——以温韦、张先、晏欧、少游、美成体为中心线索的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3期。
标签:李白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近体诗论文; 文学论文; 声乐论文; 汉乐府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