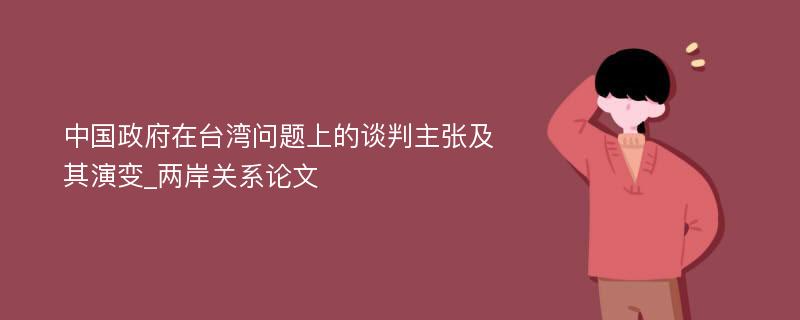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主张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在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谈判主张最早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中期。其时,着眼于远东紧张局势的缓和及维护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即由武力解决的一手准备转为既坚持武力解放又力争和平解放的两手准备。作为这种调整的体现,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注:见《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189、223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中美两国并经商定于同年8月起在日内瓦就此展开大使级会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呼吁: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央政府正式宣布: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注:见《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502、603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其后几经酝酿,到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初步形成了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案,这就是“一纲四目”。“一纲”指总的指导方针,即: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不接触中共的立场可以等待其转变,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但要逐步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四目”即: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注:陈立旭:《周恩来与“一国两制”构想》,《台湾研究》1998年第1期;陈保亮:《周恩来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统一论坛》杂志1998年第1期。)惟受限于国际国内及海峡两岸间的种种状况,中国政府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遇到了诸多阻力和干扰,在1949至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台海两岸基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重大转折是在七十年代末。其时,由于美国确认“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大陆在清算了“左倾”政治错误之后,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开始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海内外华侨华人都希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中国政府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确定了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实质内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从那时到现在,中国政府在和谈问题上的主张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1月到1991年5月,主要为推动国共和谈实现第三次合作的时期。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并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对台湾当局占领下的金门等外岛的炮击。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明确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一大学教授时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实现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的方式,所以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6月到1995年6月,主要为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以事务性商谈促进两岸交流,进而为政治商谈创造条件的时期。
1991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受权向台湾方面提出三项建议,其中第一项为:“由海峡两岸有关部门和授权团体或人士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问题,扩大交往,密切联系,繁荣民族经济,造福两岸人民。对于台湾当局有利于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主张和措施,我们都予以欢迎。”第二项为:由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进行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还可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讨论台当局关心的其它问题;在商谈中可邀请其他政党、团体有代表性人士参加。(注:见《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第658、877页,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项谈话表明,在两岸政治谈判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先“由两岸授权团体或人士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多进行一些事务性商谈,多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促进交流与合作,“增加相互了解,寻找共识,建立互信,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注:海协副会长唐树备在洛杉矶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1992年5月19日。)为此,大陆于同年12月16日,成立了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海峡交流协会”。在此后三年半的时间里,“海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态度,先后与台湾的半官半民组织“海峡交流基金会”进行了16次事务性会谈,谈判内容涉及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函件查询补偿、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渔事纠纷处理、遗产继承互助、两岸文化科技交流、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等,其中少部分议题在1993年4月底5月初两会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谈——“汪辜会谈”中达成协议(包括: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协议、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辜汪会谈共同协议),大部分议题则因两岸对“一个中国”内涵没有共识、在协议的定性上存在分歧,而无法获得具体进展。虽然如此,海协的成立及其与海基会之间进行的事务性接触和商谈,仍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席江泽民曾高度评价“汪辜会谈”的举行,认为会谈是成功的和有成果的,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注:《新华每日电讯》1993年5月7日。)
1993年8月3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布《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的白皮书,其中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指出“和平谈判”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点之一,为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注意:这里将两党谈判改为两岸谈判是考虑到台湾岛内情况的变化,对政策做了实事求是的重要调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题;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可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台湾问题不同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因此,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谈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八项看法和主张,其中第三条重申并进一步提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当局关心的各种问题;“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能就政治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找出双方都可在接受的解决办法。”(注: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本来,在这个阶段,两岸关系经过七、八年的互动和两会事务性接触、商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员往来空前频繁,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密切,交流交往的层次空前提高,两会会谈的议题也空前深入,如果循此途径发展下去,两岸一定会以和平、渐进方式最终达成国家统一目标。但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本质并非追求统一,而是确立两岸“对等政治实体”地位,实现台湾问题国际化、两岸分裂分治合法化,故而在两岸进行民间交流和事务性谈判的同时,他们极力在国际上大搞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目标的“务实外交”和重返联合国等活动,同时不断以政治问题干扰和阻挠两岸事务性谈判的进行,这就必然加剧了两岸政治上的紧张关系。随着两岸交流和两会商谈议题的日益深入,涉及的权限和范围越来越广,遇到的来自台方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最后终因两岸政治上南辕北辙而使两会的商谈触礁。1995年6月7日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关系恶化,同月16日大陆海协致函台海基会,宣布推迟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及其预备性磋商的时间,长达三年半之久的两会事务性商谈至此告一段落。
第三个阶段从1995年7月至今,为促进两岸政治谈判、以政治谈判带动事务谈判的时期。
1995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促使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重新认识台湾问题在发展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度,从而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更公开宣布遵守中美建交三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中美两国并达成了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这就大大压缩了台“务实外交”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两岸事务性谈判之所以举步维艰难以取得进展,关键在于“它已涉入政治问题而又没有条件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只有实现政治谈判,扫除两岸政治上的障碍,才可以为解决两岸经济性、事务性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鉴此,从这时起,中国政府在两岸谈判问题上的主张再次进行了调整。
1995年10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回答墨西哥记者提问时指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当局不断从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使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遭到破坏。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台湾当局。只有台湾当局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行动上放弃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搞台湾独立的活动,两岸关系才能得以改善和正常发展。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注:《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1996年1月31日,李鹏在纪念江泽民“95.1.30谈话”发表一周年的谈话中,除重由上述立场外,进一步指出:只要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一天不停止,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当然只能由那些搞分裂活动的台湾当局某些领导人来承担。(注:《人民日报》1996年1月31日。)同年6月22日,中台办和国台办发言人就李登辉“5.20讲话”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称:如果台湾当局确有谈判诚意,就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实际行动,就作为第一步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或两岸共同关切的其它政治议题与我们进行商谈。(注:《人民日报》1996年6月23日。)9月21日,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在美国侨界的一个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两岸关系的形势表明,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进行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尽快展开两岸间的政治商谈,特别是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才有可能消除影响两岸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障碍,恢复和促进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奠定稳固基础,维护和促进台湾的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注:《人民日报》1996年9月23日。)
1997年7月1日,香港结束英国百年殖民统治顺利回归中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底回归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台湾问题的解决更加突出地摆在中国政府的面前。9月12日,江泽民在中共15大报告中再次重申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再次表示“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回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注:见《台湾工作通讯》1997年第10期。)
1998年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95.1.30谈话”发表三周年时特就“一个中国”原则和政治谈判问题再加阐述。指出:为寻求和扩大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我们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经过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两岸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今后两岸关系要继续稳定发展和良性互动,必须通过政治谈判,共同承担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义务,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当前首先要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作出安排,通过这一会谈就政治谈判的议题、代表名义、方式等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两岸两会应当扩大交流和接触,为及早实现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寻求共识、创造条件。(注:见《台湾工作通讯》1998年第2期。)这里提到的两岸政治性谈判的程序性安排,是考虑到台湾当局对进行政治谈判疑虑重重的实际情况而表现出的耐心与灵活性。8月24日,中台办和国台办负责人再就两岸政治谈判问题发表谈话说:当前在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进行政治谈判已历史地提上了议程。“一个中国”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识,也得到举世公认。我们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第一步先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目前应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进行商谈,随之重新开始海协与台湾海基会的经济性、事务性商谈。这样安排正是为了满足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两岸关系发展的愿望,也考虑了台湾当局的有关意见。如果台湾当局确有诚意,就应当放弃实际上坚持搞“两个中国”的立场,就没有理由拖延进行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为了有利于增进了解、寻求共识,海协愿意和海其会进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对话。除了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的人以外,竭诚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就发展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与我们广泛交换意见。(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8月25日。)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主张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体现了锲而不舍地追求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从上述谈判主张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在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统一、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容分割、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始终是坦诚的和坚定的,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这些原则攸关民族情感、历史记忆、人民利益、国家安全与尊严等重大问题,任何人均无法改变;同时它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但在统一的步骤、方法、谈判的程序名义议题等问题上,中国政府则表现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耐心,不拒绝并认真听取和采纳任何有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有益建议,甚至宁可自己吃点亏,如在两岸经贸上年年背负近百亿美元的赤字,在谈判步骤宁可先经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谈判逐渐积累政治谈判的条件,在谈判的对手上务实地由国共两党谈判调整为两岸谈判,在谈判议题上除了“一个中国”原则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特别是和平统一主张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各方的利益,如“一国两制”的设计确保台湾在回归祖国后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特区政府并拥有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甚至港澳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自卫权和一定的外事权,除外,回归祖国后的台湾人民可以循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台湾特区可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国际活动并发挥作用,分享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耀;其次,两岸统一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有助于中华腾飞和民族振兴,使中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两岸统一排除了台海地区爆发战争的隐患,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定繁荣,也符合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利益。基于上述理由,可以说,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主张合情合理,深具诚意善意,并且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始终保持调整、充实和完善的弹性空间,因而是不惧怕挑战、经得起各方检验的,值得台湾当局认真考虑并作出积极的回应。
标签:两岸关系论文; 台当局论文; 台湾论文; 两岸政治论文; 台湾问题论文; 两岸经济论文; 一个中国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