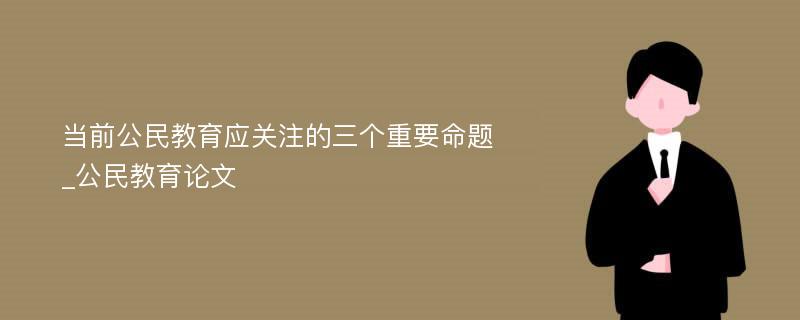
当前公民教育应当关切的三个重要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切论文,命题论文,公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公民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与教育课题,正在逐步重新进入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视野。这是中国社会与教育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对于公民教育的认识并不相同。因此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我们讨论公民教育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价值立场、秉承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成为我国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前提。我认为以下三点至关重要,值得特别注意:
一、公民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对公民教育的认识应当与时俱进。
就像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等并非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公民教育也并非西方社会的专属。与一些人对于公民教育的错误认知相反,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建国以后也都不止一次旗帜鲜明地使用过“公民教育”的概念,并且付诸过政策和教育的实践。
最明显的例证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都曾经开设过直接以“公民”为名称的课程。① 此外,在我国现行学校课程体系中,虽然我们并未使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早已涵括了一些重要的公民教育内容,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权利与义务教育、国家政治体制(含政党制度)教育、国际组织与国民身份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和平教育,等等。
这些现在存在于“政治”、“法律”、“道德”等课程模块下面的教育内容实际上就是国际上称之为“公民教育”的内容——尽管对这些课程内容及其教育的具体安排可能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些公民教育内容缺乏;一些公民教育内容需要调整;公民教育活动的形式急需改进)。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和谐社会建设对于社会公平、正义或者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迫切追求,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合理引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提高理性的公民素养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教育理所当然的重要任务。
国际上考虑加强公民教育的主要理由②通常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需要通过公民教育作为重要途径之一去加以克服;全球化与移民问题导致的多元化课题需要公民教育予以充分关注和应对;青年一代身上暴露出来的许多缺陷,例如政治冷漠等,是公民教育缺失或者无效所导致;反民主或者种族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抬头的趋势,需要教育系统高度警惕,等等。显然,上述很多理由在中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但是,中国大陆目前最突出的状况,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公民素质缺陷:一部分年轻人公民意识淡漠,缺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情,从而使得本来可以因为公民的有效参与而避免或降低的负面社会现象不能得到应有的、有效的遏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恰恰相反,许多人常常过激使用自己的民主权利,罔顾一些过激行为可能产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生活的伤害。因此,从社会心理层面确认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开展积极的公民教育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具有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质,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
许多人都认为在公民教育方面我们应具有开放的胸怀,向先进国家学习、借鉴。但是问题在于,关于公民教育的概念、内涵与重点等问题的理解,国际学术界有许多共识,也有许多分歧。即使是那些“共识”部分,大家的理解也并不相同。
比如在作为公民教育重要内容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方面,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可能更多强调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而另外一些个人权利意识过于膨胀的国家则在教育中更多地强调公民的义务。又比如,在世界、国家、社区与个人关系方面,一些国家由于公民的国家意识相对淡漠,可能更多强调民族或国家意识;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感到他们应更多强调个人权利、世界公民、社区参与,等等。至于课程名称,虽然欧洲国家普遍重视公民教育,但是仅仅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有关“公民教育”的课程称谓就包括:公民或公民教育、公民文化、公民资格教育、公民与法律教育、社会研究、社会科学、人与社会、生活技能、共同生活、“社会、个人与健康教育”、个人与社会发展、社会知识、“公民、社会与政治教育”、“公民、法律与社会教育”、民主与人权、人权与民主公民资格教育、政治教育、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公民社会的准则、宪法研究等。③
当我们准备认真开展公民教育的时候,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当然是: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认识中,什么是我们应该认定的“公民教育”尽管寻找共识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也存在一个比较绝对的共同点。那就是:不同社会基于各自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具体情况,思考各自公民教育的重点。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如此。
比如,2003~2004年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多元文化教育中心曾经研究过多元民主国家中公民教育基础性的4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学生应该了解本地社区中、国家与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④ 显然,这一观点与美、英等国学者对于全球化步伐加快和外来移民增加导致的若干社会问题的关注有关。而在北欧的瑞典,2001年通过了一个“反对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对同性恋的憎恶与歧视的国家行动计划”。瑞典政府坚持要求学校促进种族平等,规定教育活动的开展应该与基本的民主价值观相一致,学校中工作的每个人都必须促进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以及对共同生活环境的尊重。⑤瑞典公民教育的上述努力显然与北欧社会近年出现的聚众骚乱和种族主义行为有关。
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命题在我们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上仍然有效。中国人当然应当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基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考虑自己的公民教育设计。一方面我们应当鼓励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确立公民的主体意识,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让大家树立理性或辩证的权利与义务观念。一方面我们应当鼓励公民树立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而奋斗的意识,另外一方面,和平崛起又要求我们有正确的民族意识和国际观,学会从社区到全球社会生活的积极、有效的参与。我们既不能制造一个让别人完全不懂的公民教育概念,但是我们也要反对公民教育上可能存在的“文化殖民”。
总而言之,就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具有中国特色一样,我们也应当考虑根据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实际去建设自己的公民教育的新理念。那些脱离中国社会实际、似是而非的抽象和简单的思维方式和那些闭关自守、拒绝与外部世界对话交流的态度都应当坚决摒弃。
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生活同步建设,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理念。
公民教育属于广义的“德育”。但是许多人在潜意识或者思维定式中一直将学校德育等同于思想品德、政治课等直接的德育形态。实际上德育包括直接德育、间接德育与隐性课程三大形态。中国德育的问题不仅存在于直接德育,更多的也许是我们对间接德育与隐性课程等学校和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德育关注不够。于是在学校内部,德育往往成为少数人的事业,学校之外“5+2=0”的局面也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全部德育的进步都依赖于德育与学校和社会生活的合理连接,公民教育应当与生活的改进同行。
我的主张是:应当通过“公民生活”的建设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其要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营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舆论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潜意识里都将公民教育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像许多人曾经将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样。其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培养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这一点既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教育法》中,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实践之中。在公民意识淡漠、理性的公民行动能力缺失十分严重,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现实社会问题的今天,我们需要全社会在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必要性、迫切性上的共识。有了共识,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生活;有了公民生活,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
第二,成人社会应当做公民生活的表率。在所有价值教育领域,榜样学习都是极端重要的学习方式。尽管我们谈论公民教育时常常将重点放在未来公民的教育上,但是如果成人们都没有成为积极公民生活的榜样,我们是无法使得青少年真正相信公民教育专门课程所教导的一切的。即使我们成功地在学校和课堂上进行了象牙塔里的公民教育,当未成年人接触社会的时候,所有接受过的教育反而会让他们失落、失望,继而后退到比较保险的“臣民生活”、“私民生活”的惯性中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除了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之外,我们认为成人社会的公民教育和成年人关于公民生活的自我教育至少和校园里专门针对青少年的公民教育一样重要!
第三,学校生活应当改造成为“公民生活”。教育家杜威和陶行知先生都曾经强调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命题。当学校在管理制度上没有民主精神,当课程与教学一直采取强制灌输的模式,当师生关系、生生关系都被等级观念所浸透的时候,学生们根本没有成为公民的机会、基础,再好的公民教育课程也都会流于形式,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设计、开发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读本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应当是,让整个学校生活具有公民生活和公民教育的性质。对公民教育来说,让青少年生活在一个民主、公正、人道、受尊重、鼓励理性参与的教育环境里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可喜的形势是:最近几十年,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中国不仅经济进步迅速,社会与政治进步也是明显的。虽然由于历史与国情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但是从公民个人权利的确认、维护到国家政治生活体制上的民主化都为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环境。因此,除了必要的直接德育内容与形式的改革,强化更合理的公民教育内容之外,学校德育关注的重点之一应当是如何更多地将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落实到具体的校园生活的改造中去,让孩子们在一个和谐、民主的教育生活中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公民。
在真实和不断进步的公民生活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应当成为中国公民教育的最重要命题。
公民教育是一个老概念,也是一个新问题。同时公民教育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教育问题。我们由衷呼吁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认真关注、推进新时期中国公民教育的健康发展。我们更是由衷地希望,通过教育界和全社会的不懈努力,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概念能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建设同步,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地重建起来,并焕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注释:
① 张志建著:《中学思想政治课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Audrey Osler and Hugh Starkey:Education for Democratic Citizenship:a review of research,poliy and pracrice 1995—2005,BERA,Education volume 24(4).
③ Audrey Osler and Hugh Starkey:《公民教育的进展研究:发达国家的探索》,《中国德育》2007年第4期。
④ Banks,J.A.,Banks,C.A.,M.,Cortes,C.E.,Hahn,C.,Merryfield,M.,Moodley,K.A.,Murphy Shigematsu,S..Osler,A.,Park,C.and Parker,W.C.(2005)Democracy and Diversity:principles and concepts for educating citizens in a global age.Seattle,WA:Center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⑤ Government of Sweden (2001) National Action Plan to Combat Racism,Xenophobia,Homophobia and Discrimination.Stockholm:Written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2000/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