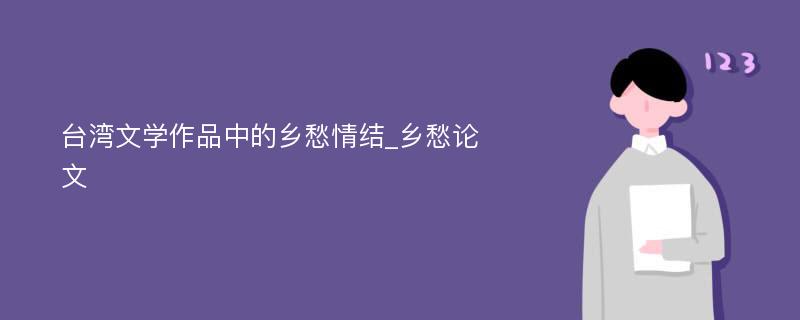
试论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台湾论文,文学作品论文,情结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乡愁;我们则认为,乡愁是台湾文学作品中一个魂牵梦绕、挥之难去的浓郁情结。
台湾作家有一首诗说得很到家,让人闻之心动,读之欲哭,感慨良多,久久难忘。它的名字就叫《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以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言浅意深,容量很大,我们似乎觉得它一语道尽了乡愁的诸多情感,万千意味,尽在其中了。
关于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乡愁,人们已经谈过许多,以至于有人坦言:不要一提起台湾作品就是乡愁。然而笔者以为,谈到台湾文学,你还真难彻底避开乡愁的影子。孤悬海外,云水茫茫,生活在宝岛上的炎黄子孙们,你能让他们的何种情感可以彻底摆脱乡愁的影响呢?是的,那儿也有人一再试图甩掉中国之根,但这“根”的存在却是连他们自己也难以否定的事实。说到底,只要有故乡,乡愁总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只不过言多言少、有形无形,其表达方式、外现形式不同罢了。而且,我们进一步认为,对台湾文学作品中乡愁情结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从广度上说,目前的研究不仅没有涵盖也难以全部涵盖乡愁的诸多领域,人们不知道在许多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一颗乡愁的心,研究者许多时候只是在肤浅的、表层的情感世界住足、徘徊,他们没有看到乡愁之中包容着极为丰富、广阔、极具变化色彩的内容;同样,从深度上说,人们往往罗列现象,泛泛而谈,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种种表象之中不仅蕴涵着乡愁的万千意味,而且常常积淀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思想。这也许就是到目前为止许多乡愁研究中的局限所在,也是造成一些人对此产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乡愁情结决不是台湾文学中的唯一情结,但它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那么,台湾文学作品中乡愁情结究竟有多重,乡愁的领域究竟有多广,乡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一、乡愁是一种滋养:大地山川
一个人,只要他离别故土,远走四方。故乡就会成为他永远的思念之乡、温暖之乡。故乡,无论是他的出生之地,还是他的成长、生活之地;无论曾经留下他的欢歌笑语,还是曾经带给他辛酸和悲伤,这个地方都会令他深深牵挂,依依难忘。因此,对故乡故土的思念无疑是乡愁中最常见、最直观、最强烈的一种。
捧读台湾的文学作品,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这种极具情感色彩的故土之思。台湾诗人梅新有一首小诗叫《中国的位置》:“中国的位置,位于东东东/恰好和狮子座的流星雨成垂直的垂点上/中国的位置,位于南南南/恰好和天狼星的雄姿成垂直的垂点上/中国的位置,位于西西西/恰好和猎户星的枪口成垂直的垂点上/中国的位置,位于北北北/恰好和牛郎织女星的年龄成垂直的垂点上……。”这首诗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以这种方式去抒写,特殊的方式强化了特殊的情感。诗的内容似乎很简单,但其意义却极为浓重,好似汉代乐府民歌《江南》,反反复复,回旋咏唱,极具特色地表达出漂泊流浪的炎黄子孙对祖国大陆的深切怀念。祖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这首小诗以其独特的形式告诉人们,她永远雕刻在普天下中国人的心中。台湾的中老年作家许多都是生于大陆,长于大陆,那儿曾经留下他们孩提的歌声和青春的足迹。那些梦幻般的记忆往往是难以磨灭的:郭枫梦中的北方,天高云淡,雄壮辽阔;白先勇笔下的南国,郁郁葱葱,如诗如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是林海音悄悄讲述的老北京的故事:一件件难忘的事,一个个多情的人,一处处充满神奇和梦幻色彩的景物,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可亲可爱的清末民初北京风情画。那色彩鲜明的红墙绿瓦,那令人陶醉的乡情乡音,蕴涵着童年的无尽回忆,映衬出作者的铭骨思恋。林海音诗意的描述为世人创造了一个美妙动人的童话世界,直让人觉得这似乎不是旧日故都,简直宛如人间天堂,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度闻?由于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分隔,使旧日的生活经历洒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夕阳余辉,情感的投入和想象的力量,极大地美化了过去的一切,梦中的世界是最美的天地。江山如斯,往事如斯,遥想大陆,人淡如烟,远在海岛的人们,怎能不涌起绵绵无尽的乡愁呢?还是诗人席慕容说得真切:“请为我唱一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都太悲凉/如果你不爱听/那是因为歌中没有你的渴望//而我们总要一唱再唱/想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岸啊 阴山旁/英雄骑马啊 骑马归故乡。”(注:席慕容《出塞曲》。)席慕容唱出了游子们心中对故土最真挚的情感。
大地不语,具有无尽的力量;江山无言,凝聚着永恒的呼唤。台湾作家们思念自己的故土,自然是怀念养育了他们的那山那水,那方土地,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但更为重要的,这乡愁中无疑还深深蕴涵着一种渴求的情感,一种寻找的意象,它在寻找一种故乡独有的难以替代的东西,寻找凝聚在风土人情中的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寻找一种生命的支柱。
以著名的散文家郭枫为例。郭枫回忆中的北方农村显然是贫穷和愁苦的,作者以多情的笔触深刻地描绘出那个忧患重重、民生多艰的年代。在郭枫作品中,民族危亡、苦难人生始终是一个持久而沉重的主题,但是我们通读他的作品,你却很难发现沮丧、阴郁和悲观失望的影子。他总是在苦难中展现希望,在重压下露出微笑,在忧患的土地上为人们树起一面理想的旗帜。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系列散文“怀乡散记”中的《老家的树》,这篇散文抒写了故乡土地上四种树木的自然形态:春天柳树的娇柔,夏天榆树的火热,秋天白杨的潇洒,冬日松树的峻拔。粗读此文,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树木;但细细想来,脑海中便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生活在树下北方之人,感受到一种以树木为象征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作者用北方之树撑起一方坚韧、顽强、生生不息的感人天地,折射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穷苦百姓的几种生命形态:春荒时的坚强、酷暑中的勤奋,秋收后抗击日寇的悲壮和冬日顶风斗雪的刚毅。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树,理想中的树,那一棵棵树的形象分明是人的生命意志的外化,是作者怀念、赞美、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笔者以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赞美树,不如说是赞美人,赞美一种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不如说是作者在寻求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寻求一眼极为可贵的生命源泉。古人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活水”也许是故乡独有的啊。
故乡是现实的,故乡又是精神的,乡愁不仅是对故乡绵绵不断的思念,还是天下游子与故乡终生不渝的维系。对广大的中国人而言,故乡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想起故乡,心里就踏实,奋斗就有力量;故乡是一种无言的关怀,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想起故乡,就会感到一种鼓舞和温暖,就会产生信心和勇气;故乡还是中国人生死相依的伴侣,“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在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故乡依然寄托了他无限的哀愁和最后的希望。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临终遗诗中深情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注:《于右任诗词曲选》第213页,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此情此景,此诗此意,多少故土之情,家国之念,都浓缩在这首短短的小诗里了。读懂了这首诗,也就真正明白故乡的山川大地在台湾作家心目中的特殊位置和重要作用。当然,这个故乡不仅仅指祖国大陆,也包括台湾在内,因为台湾本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说他无法选择自己的故乡,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的心目中重新创造一个充满个性的属于自己的故乡。那里既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亲人,也有自己现在、未来和理想。对故乡的思念是人生的重构,对生命家园的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滋养人的。因此,乡愁也不总是悲悲戚戚的,它无疑还有极为主动和积极的一面——它是作家们精神的需要,是心灵的滋润,也是他们人生和价值追求的重要表现。
二、乡愁是一种依恋:文化传统
香港作家董桥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话说得很重。何谓“文化乡愁”?在其著名的小书《乡愁的理念》中,他进一步解释道:“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
如果说对故乡的思念是和一个有形的世界的对视、联系的话,对文化传统的依恋则是和一个无形天地的沟通、交流。文化传统不像故乡那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承载物,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意象。但它的作用却一如故乡,对炎黄子孙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中,流淌在历史的长河里,无声无息但发挥着无比浓重的力量。文化乡愁也许没有故园乡愁那样强烈、火热,但却更加浓郁和持久,更加普遍和辽远。诚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言:“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注: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见《桥跨黄金城》第21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台湾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乡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源远流长的祖国文化的浓浓的爱;其二是对近百年来这种精致文化传统悄悄失落的深深遗憾。
与其大陆同仁一样,台湾作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并且,由于这些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台湾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在对文化传统的感受和把握上往往有其特殊和独到的一面。几个世纪以来,台湾几度漂离祖国大陆,由此造成了台湾社会较为普遍和长久的漂泊心态,特别是历史上残酷的殖民统治,使台湾沦为“弃儿”和“孤儿”。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向往、认同和爱戴,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因而成为台湾社会以及台湾文学的必然追求。这不仅表现在其创作精神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也表现在其大量文学作品洋溢着的极为浓郁的古典文化诗境之中,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许多台湾作家对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上。著名作家杨牧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曾一再指出,一个现代作家下笔时“必须领悟到诗经以降整个中国文学的存在。要让三千年的中国文学笼罩你虔敬创作的精神,也要让四百年的台湾经验刺激你的关注,体会到这些同时存在的,是构成一个并行共生的秩序。……历史意识教我们将永恒与现世结合看待。我们下笔顷刻,展开于心神系统前的是无垠漫漫的文学传统,我们纸上任何构造,任何点线面,任何内求和外发的痕迹,声音无论高低,色彩纵横是惊人的繁复,狂喜大悲,清明朗静,在在都有传统的印证。”(注:徐学《从古典到现代》,《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3期。)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验时,他不无惊奇地说到:“一种美学经验,恐惧和喜悦,丰富了我的幻想世界,在短期间内为我的文字染上某种诡异的色彩,沿着半规律化的铿锵声调向前延伸。”是老庄开拓了他的玄思和想象,是韩柳文引他走向风格体裁的殿堂,而读了《史记》“方才揣摩出什么叫做‘文章’”(注:徐学《从古典到现代》,《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3期。)。杨牧这番话当然不乏理性的分析和引导,但主观体验和情感色彩无疑是浓重的,颇有一种悠然神会、妙处难言的味道。他诗情画意地说出了文化传统的艺术魅力,也说出了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许多作家内心深处对古典文化深深的崇敬和热爱。著名作家吴浊流在《大地回春》一文中疾呼:“愿与三千士,振兴大雅风,试观沙漠地,跃出几英雄。”这里的“大雅风”,可以泛指民族传统,也可以指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及古典诗词,由此可见他对民族文化的依依深情。他们不只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翻读台湾的文学作品,我们能深深领悟到一种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东西,在小说的故事中,在散文的描写中,在诗歌的意境中,在
宝岛的那片青山绿水中,飘然时现,深蕴其踪。爱亦成愁,爱到极致,忧愁便会悄悄而生。透过浸透着古典诗意的台湾文学作品,我们既感觉到文化传播的强大力量,也深深体味到一种别有意味的文化乡愁。
文化乡愁的另一方面与上面的论述紧密相联。因为喜爱,所以常感到不满和失落;因为爱得深,所以失落感也就特别强烈。台湾中老年作家大多有过大陆生活的经历,而且常常往返于台湾和海外。这些背景往往使他们拥有较为丰厚的生活积累、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参照系统。正因为如此,他们笔下的乡愁住往显示着浓郁的回顾、对比、怅然失落等特点,有一种文化寻根的意味。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让他们自豪,中国近代悲惨屈辱的一页让他们悲哀,现代社会人格美人情味的丧失让他们感到惆怅,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往昔不再让他们深感忧虑。这一切汇集在一起,就形成文化乡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极为强烈的的落感。白先勇被余光中称为“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这“敏感”和“伤心”两个词无疑是对这种失落感最准确最精彩的概括和描述,而白先勇则是这方面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家。人们阅读白先勇的文学作品,时常感到一种思想的力量,感到一种象征的意义,这“力量”和“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他那宽广浓郁的“文化乡愁”。他认为,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继承与发展。而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化传统慢慢消失了,这是最让人感到遗憾、惋惜和痛心的。白先勇曾说:“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伤怀的追掉,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163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白先勇的许多作品就是以最大的努力来写这三个“感”,即苍凉感、历史感和无常感,《纽约客》是这样,《台北人》更是这样。作者正是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满怀感情地描述了广泛意义上的“台北人”由盛而衰直至没落、死亡的诸多过程;作者以一系列凄楚动人的故人往事,表现出他内心深处极为强烈的失落、惆怅和惋惜,表现出他极具特色的“敏感”与“伤心”。这种从悲剧故事及其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历史怅恨和寻根思旧的文化乡愁,是白先勇小说最具个人特色的悲剧主题。白先勇的系列小说固然写出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精神世界的广阔深邃,但它们又何尝不是一曲曲对美到极致而又衰落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哀歌呢!
总之,无论是爱也好,失落也好,其本质都是一种深深的依恋。“文化乡愁”说到底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一种依依深情,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环境中的一种极具温情色彩的精神寻求,是对知识分子心灵天地的一种珍惜和守护。白先勇在小说《台北人》的卷末,特意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令人叹息不已的《乌衣巷》,作为他“文化乡愁”主题的提示。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斜阳野草,诗意古深,只是不知台湾作家们的无边愁绪,一腔情怀,这首小诗可否容得下?
三、乡愁是一种审视:历史命运
乡愁,乡愁,一个关键的字眼是“愁”。对台湾作家而言,这个“愁”既来自对故乡的思念,对文化的依恋,更来自对祖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命运的反思和审视。经历了近百年的挫折失败、动荡战乱、内忧外患,广大台湾作家的心中留下了强烈的震憾和无数的疑问,这一切迫使他们回首过去,苦苦思索,站在历史的高度,立足于现代思想的深度,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心态进行严格的审视和反思。
他们把冷峻的目光首先投向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尊敬、学习、理解的同时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思考。他们以全新的观念和批判的态度叩问历史,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影响巨大的传统观念提出自己的疑问、思考和看法。比如对传统道德习俗,也就是那些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伦理道德,他们提出尖锐的批评的指责。他们认为,历代统治者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以及所谓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等等传统美德,实际上是中国人无穷无尽的社会人生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悲剧的描述和揭露在白先勇许多哀顽凄绝的小说故事中显得尤其触目惊心、动人心魄。再如对历史人物,他们以崭新的视角、语言和意象,对传统人物做了重新审视和思索,对许多世代流传的题材按自己的理解作了全新的创造和阐示。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光中的新诗《夸父》,这首小诗以其颇具特色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思维串联起种种意象,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为什么要苦苦去挽救黄昏呢?/那只是落日的背影/也不必吸尽大泽与江河/那只是落日的倒影/与其穷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霭的冷烬/——何不回身挥杖/迎面奔向新绽的旭日/去探千瓣之光的芯心/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而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诗人赋予夸父这一神话人物以崭新的内容和意义,在古老的题材中开掘出崭新的意蕴,在古老的人物身上升华出极具时代意义的思想,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和批判性。台湾作家在反思历史文化时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努力从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现象中追寻出不寻常的东西来,在这种寻找中,一方面不断研究、清除传统文化中的种种落后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断总结、阐发一些颇有价值的崭新命题,这种追寻往往给读者深深的启迪。
对社会现实、生存状态的审视和批判是乡愁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台湾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真实反映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台湾新文学从发生开始就确立了回归祖国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批判精神,作为台湾文学两大主要流派的乡士派与现代派,其绝大多数作家都是深深地关怀着脚下的土地和自己的民族,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深沉的民族情感,以笔为旗,发光发热:他们或通过对祖国宝岛苦难历程的追叙,反映了台湾同胞民族情感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或在对台湾以及大陆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社会弊端的展示中,表现对台湾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极大关切;或在异国他乡寄托怀念故土与亲人的缠绵情思;或面对海峡两岸的分离抒发对祖国母亲的一往深情。总之,他们以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热情关注着社会,参与着历史,贡献着力量。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奶母”的赖和,“以果戈理的讽刺描写了殖民地统治下本省农民的悲惨的生活情况,揭示了日本统治下本省人苦难的诸样相。他替本省乡土文学树起了第一面旗帜。”(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34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铁血诗人”吴浊流用他的小说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天地:各类人物的生沉起落、苦苦挣扎,各种道路的风雨泥泞,形形色色思想文化意识的相互冲击渗透,这是台湾日寇统治时代的众生相,是那段生活最为真实生动的写照。而名噪一时的现代主义作品,则由于注重心理写实,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台湾民众近几十年普遍存在的迷惘苦闷心态,透过这些,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社会转型期种种病态的现实,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西方腐朽文化对人们心灵的毒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现代派文学还是具有相当的认识作用的。在白先勇的短篇《夜曲》中,一对年轻时的恋人晚年相遇于美国街头,男的自责:“我现在是有名的心脏科医生了,可是一个中国人也没有医过,一个也没有……”。而来自大陆的女的却说:“中国人的病,恐怕你也医不好呢”。这极为沉重的对话中包含着另外一种审视,它曲折地折射出台湾作家对现实、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一种把握以及一种悲愤交加的复杂心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对文化传统、生存环境认真审视的同时,台湾作家以较为开阔的胸怀和全局性的目光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予以整体性思考和把握,并进行了极为可贵的研究和探索。在这方面,著名作家白先勇曾提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被放逐了。他在专文评价於梨华、聂华苓时,用的题目就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白先勇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一直处于一种流离状态,这种状态主要不是指逃难,而是指与现代文明的不即不离。他对处于流离状态的中国人,概括了一句极具感情色彩的话,说他们(我们)“成了精神上的孤儿,内心肩负着五千年回忆的重担。”他借助历史来描写心灵,着眼点主要在探索“放逐”对人及其心灵的巨大影响。在回顾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白先勇曾极为沉痛地说:“我们中国人在廿世纪很失败。”显然,他是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凝望二十世纪、反思国人命运的,此话准确与否大可商量,我们并不一定同意这个判断,但白先勇经这苦苦思索说出的这番话无疑是触目惊心、极具震憾力的。它是漫天乡愁的一种凝结,是无数疑问的一种升华,无论如何,它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可以视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人认识自己、总结自己极具特色的观点之一。探索民族命运,寻找知识分子的出路,乡土作家陈映真的思想见解也令人深思。面对台湾社会的急剧变化,面对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他更加紧迫地审视、探寻着知识分子生存的意义、责任和出路,他在化名写的《试论陈映真》中谈到: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必须“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作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诀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陈映真对自我的认识是透彻的,对知识分子“救赎之道”的论述也颇有见地和价值。台湾作家对中国人自身以及命运的认识是艰苦、坚韧和积极的,他们的努力显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高度。把握自己,把握命运,这种人生态度和可贵实践对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审视是台湾文学乡愁情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乡愁而去审视,而由于审视又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刻意义上的乡愁。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作家的责任感、参与精神、忧患意识十分充分地体现出来。从这个方面说,审视中的乡愁是最为沉重的。
四、乡愁是一种期待:民族未来
乡愁的核心是爱,对祖国的爱,对同胞的爱;而爱的核心则是一种深深的期待,对民族未来最美好的盼望和期待。钟肇政在其长篇小说《鲁冰花》的卷首题词中充满深情地写道:“希望着——永远希望着有更多的热爱,遍洒在大地上。”这是作者的心声,也是台湾作家们共同的心愿。他们热爱台湾,也热爱祖国,因为台湾本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对乡土的爱融入到对祖国、对民族的爱之中。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创作中找到确实的印证。钟肇政曾经说过:“我们盼望我们中国人以后有什么样的远景,我便在作品中间接地、隐含地表现我的观点。”(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97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他的这番话在台湾作家群中是颇有代表性的。那么,他们盼望中国人有一个怎样的远景,换句话说,台湾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作家们对未来有一种怎样的期待和渴望呢?
首先他们渴望祖国早日统一富强,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繁荣昌盛。这是他们最强烈的期望,也是台湾文学众多作品较为普遍、共同的主题。钟肇政借他作品人物之口明确而又诀绝地说:“……吾儿,你晓得你的祖国吗?他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的血液都是中国人的血液,骨头也是中国人的骨头。”(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124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字字千金,掷地有声。聂华苓小说中各种各色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们全都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41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在《台湾轶事》小说集中,她让人物以走了板的腔调唱了一段京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尽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情真意切,一唱三叹,不仅道出了去台大陆人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心理创伤,而且抒发了他们迫切要求回归祖国与亲人团聚的真挚情感。真可谓:酒入愁肠,化作思乡泪。在陈若曦的作品中,“回归”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作者为此使用了大量篇幅并显示出相当的艺术功力。她积极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渴望回归。她认为大陆、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爱大陆、爱台湾都是爱中国。她在作品中曾引用王粲《登楼赋》中的一句:“人情同于杯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表达了忠贞不渝的怀土感情。在其力作《向着太平洋彼岸》中,她煞费苦心地让主要人物一个回归大陆,一个回归台湾,让他们都回去建设“中国”,然后,通过其他人物之口,喊出大陆和台湾“公平竞赛”、“和平统一”的呼声,这构思是极为独到的,主题则是极为深刻的。这些渴望回归的文学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爱家的真挚情怀,它们顺应历史潮流,申明民族大义,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艺术再现。作品中所表现的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正是海峡两岸人民正在携手努力,力争早日实现的目标。
其次他们渴望在东西文化的撞击中寻求一个坚固的立足点,重建一个开放、健康、现代化的精神世界。数十年来,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严加防范、对西方全面仰赖,导致台湾社会深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此外,台湾作家又大多有着海外和台湾两地生活的经历,因而,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如何使古老的华夏文化焕发出青春活力,最为重要的,如何使新一代中国人以良好的心态和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台湾作家们时常面对、苦苦思索、不断探求、急于解决的问题。以於梨华为例,於梨华的作品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展现这种文化撞击和寻求的。首先在人生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极力倡导的是精忠报国的爱国热情和兼善天下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而在西方社会,人生的至高理想首先是个人生存意志的实现和物质欲望的需求。如何在东方民族的责任礼义与西方民族的人格独立、物质进取之间取得一种认同,这是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等小说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於梨华表现文化撞击主题的另一个贡献是对留美学生爱情悲剧的充分展示。爱情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选择,在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这成为於梨华精神探求的又一重要领域。再如三毛,这位风格卓异的女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寻找、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轨迹和艺术境界:在生活道路上,她追求一种融汇中外、自由开放的人生理想;在文学实践中,她创造出一种熔东西方审美理想于一炉的艺术精神。三毛以其短暂的一生,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个努力建构自由健康的新的文化人格的寻找者的感人形象。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台湾作家们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也只能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马上拿出一种肯定性的结论或答案,尤其不能奢求他们的实践尽善尽美。但他们已经开始的在中西文化交叉地带寻求一种博采众长的“超越性”努力,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展示出一种在自尊自爱的民族意识前提下走向世界的文化选择,以及他们的创作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较好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美感。这一切无论如何是极有意义和极有价值的。
第三,他们殷切地渴望炎黄子孙能够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能够振奋精神、博采众长,用自己的双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真正创造出一个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振兴中华”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更是台湾同胞内心深处的渴求和极为强烈的呼唤,因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心中聚集了太多的强烈的亡国之感和切肤之痛。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杨逵,一生坎坷,艰难困苦,但他以自己坚强不屈,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篇章。他曾说:“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与和平。我没有绝望过,也不曾被击倒过,主要由于我心中有这股能源,它使我在纠纷的人世中学会沉思,在挫折来时更加振作,在苦难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处碰壁,也不会被冻僵。”(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42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他的小说即使在描述最黑暗、最痛苦的年代时,依然充满着坚强的理想主义的光泽,表现出先进的理念和不屈的抗争精神。结局积极向上,具有一种催人奋起的力量,被誉为“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注:转引自《台湾新文学概观》第42页,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而钟理和的作品则刻意表现、极力弘扬一种默默的坚韧的精神。在含有自传性的小说《菸楼》中,每当主人公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起父亲在荒年里用绳子拴在患着疟疾的母亲腰间,把她拖到营材局做工的事,这让人永生难忘的一幕极大地激励着他生存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小说中最感人的一句话是:“父亲是倔强的,我也不能低下头来。”钟理和的作品以其众多的人物和故事显示出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尊严,显示出坚强不屈,奋勇进击,在奋斗中求生存的可贵精神。而余光中的作品中往往透露着另外一种坚强的意志,好像总有一种力量在激荡着读者的心情:“暴风雨之下,最宜独行/电会记录下雷殛的一瞬/凡我过处,必有血迹/一定,我不会失踪。”(注:余光中《天谴》。)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是余光中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总之,台湾作家们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一个共同的意愿,那就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一切有责任感的炎黄子孙们,要自强不息,苦苦进取,使中华民族有朝一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普天下中国人最强烈的心愿,也是一代代仁人志士最明确的奋斗目标。80年代初,身居台湾,已是古稀之年的文化老人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新论》中大声疾呼:“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这
是人世间最动情的呼唤,也是最有力的号召,黄钟大吕,感人不已!
乡愁是一种普遍的人文现象,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它不分国家、民族,也不分地域、时间。然而纵观世界文坛,却很少有地方能像中国的台湾地区近几十年文学发展那样,乡愁这个母题会在短时间内如此集中,如此强烈,呈现出如此丰富生动、绚丽多彩的艺术景象。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从中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也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特殊历史和环境的影响。家是中国人的第二生命,是炎黄子孙永远的温暖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漂泊流浪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因此也就“无奈归心,暗暗流水到天涯”。诚如台湾作家许达然所说:这归心在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上,也在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上(注:许达然《回家》,见《中国纯情随笔》第37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当然,更在千千万万奔波流浪的炎黄子孙内心深处。笔者以为,台湾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情结蕴涵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游子情怀的悠久神韵。从特殊环境上说,十六世纪以来,台湾岛十六次被列强侵略,两度沦为荷、日殖民地。四百万民众曾被“朝廷”履约出卖,她为祖国承担过巨大的牺牲,这对台湾社会和人心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以后,一批知识分子随之迁台,同时也带去了大陆失败后所产生的浓重的幻灭感和失落感;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急剧转型,造成农业凋敝,污染严重,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另外,台湾孤悬海外,与大陆母体文化隔绝,与生态环境污染的同时,精神生态环境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新一轮的幻灭与失落感正不断增强,这一切是造成台湾文学作品乡愁情结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当然,应当看到,在台湾的乡愁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分被国民党当局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尤其在所谓的“战斗文学”时期。这些作品以“时代歌咏”、“爱国爱民”相标榜,实质上不过是台湾当局“反共复国”的拙劣工具而已。尽管这部分作品影响不大,并且不久便烟消云散,但这种现象的存在依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
如前所述,乡愁问题是一个极为深厚、复杂的课题。坦率地讲,以有限的篇幅谈论这样一个课题是颇为吃力并且是难以尽如人意的。但是,笔者依然愿意为之努力,因为这毕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乡愁是一支血脉,它联结着祖国和世界各地的海外赤子;乡愁是一首老歌,它凝聚着普天下炎黄子孙的真挚情感;乡愁还是一件有力的武器,它维护着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并号召所有的华夏子孙为此目标,生生不息,顽强奋斗。捧读台湾同胞的乡愁文学作品,我们尤其深切地感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力量,特别是在祖国的宝岛上某些台独叫喊甚器尘上的今天。
行文至此,正值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重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时刻,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台北举行的一次庆回归的晚会。当与会同胞一同高呼:“祖国一定要统一,我们都是中国人”时,我们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们的耳旁再次回荡起钱穆先生那凝重、苍凉、雷霆万钧的声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标签:乡愁论文; 白先勇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台湾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故乡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