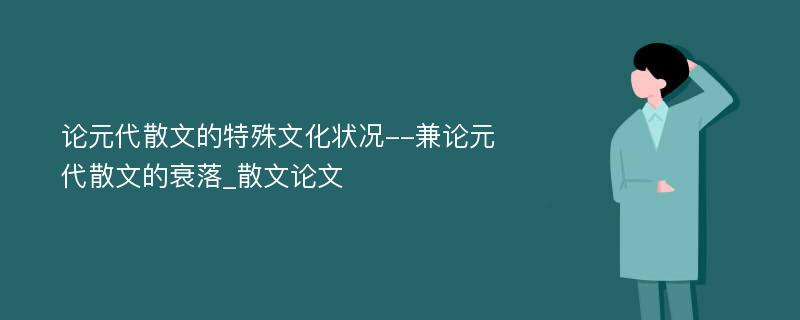
论元代散文的特殊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散文论文,境遇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1999)06—0126—05
元代散文,议者甚少。然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者,应不得不及;治散文史者,当更难逃避。但却曾见一号称《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者,竟也以“所占位置较轻”为由,对元代散文“略而不论”,径直从唐宋一跃而至明清[1], 而且这种操作法在一些涉及散文史的专著或论文中似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笔者以为,“所占位置较轻”,纵观前后,可能是事实,但“略而不论”却不是史家的正确态度,至于元代散文的成就和涉及的问题是不是轻微到了可以“略而不论”的程度,更当重估。我觉得,元代散文的实际成就应该得到实事求是地肯定,而其相对秦汉唐宋明清来说总体成就不高的情况,我们应该结合元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文化环境,作出合理的解释,相关的问题也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建构中国散文发展史的逻辑框架时,不至于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故就本文的题目略陈浅见,请教方家。
一
元代散文之所以遭后人轻视,并非全是偏见,实因其本身成就有限。但处于先秦两汉和唐宋两大辉煌时期的映照之下,元代散文为何突然跌落下来,失去了散文文体延续了好几千年的光彩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元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被置身于一个特殊的文化境遇之中。
境遇之一:散文文体向来居于文坛正统的地位,在获得先秦两汉及唐宋两大辉煌时期的成果之后,其历史之悠久和遗产之丰富,反因难于攀越而成为后代散文家而首先是元代散文家沉重的肩负。
当13世纪的元代散文家们操笔写作的时候,中国古代散文已经有了约三千年的演进历史,从殷商甲骨到汉简唐写宋刻,由简到繁,由质到文,不断丰富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萌芽最早、发展最为完善、体式最为完备的文体(注:古代诗歌萌芽亦早但体制上至少还缺散曲一式。),累积起巨量的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的优秀成果,并形成了秦汉和唐宋两大散文重镇,就正统正宗的散文观念来估价,已经登上了辉煌的顶点,此后的散文,似乎已没有超越的余地,也较少创新的可能,只剩下总结的任务和承续其传统的责任,至于写作实践,则尽力摹拟已力不从心矣。事实上,元明清散文的诸多流派,始终都困扰在继承与革新两大基本命题的矛盾斗争之中,不能自拔,最显要的成绩在于总结而不在于创造,在于理论而不在于写作,复古拟古的阴云始终笼罩文坛,辉煌的历史财富,反成为缠住后人前进脚步的绊索。
元代散文以不足百年的时间,徘徊在历史的夹缝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境界上不能超越前人,而叛逆革新的话题又未提上桌面,别开生面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尚未成熟,这就注定了元代散文的历史命运,上既不能摆脱秦汉唐宋阴影的覆盖,下又还未像明清那样开始了对散文传统的系统总结和创新努力,并已在反复古的斗争中萌芽了更加深刻的变革精神。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它不得不成为一个一切旧的传统都已变得十分沉重,而一切新的迹象还都不太分明的过渡时期。
境遇之二:通俗文艺的潮流,戏曲、小说新样式的崛起,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正宗的旧文体,虽然在正统观念里戏曲、小说仍然是小道末流,但市井细民的审美趣味和娱乐需求,以及通俗文艺作家们的卓越创造,实际上把散文文体逼进了一个狭小的划地为牢的空间,而不得不让出大片的领地让新体通俗文艺去驰骋。
文体的新陈代谢、此起彼伏、演变更迭,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规律。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段话启发我们去认识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每一特殊时期,都会有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产生,以取代前一时期的代表性文学样式的地位,因为旧文体已经在前代作家手里达到了最高境界,新一代的作家难以再有作为,只能借新文体而革新创造,而这种新文体又将在他们手里攀上绝峰,后代作家又只能再去弄一种新玩艺了。文学史于是以高峰并峙的形态和文体更迭的方式向前演进。
也许我们不宜过于执著王国维的具体描述,因为在他的描述中,散文似乎并没有置于文学史舞台的中心。而事实却是,先秦诸子、汉魏史家赋家所创造的秦汉散文既丰碑耸立,韩、柳、欧、苏所代表的唐宋散文也形势巍峨,令天下文人敬仰,它们还都能与同时代的诗歌媲美并肩,共享高誉。然而宋以后,情况真正变了。在市井民间说唱艺术的土壤里长期孕育的戏曲和白话小说,在宋元之际迅速走向成熟,特别是杂剧和散曲在元代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竟成为“一代之文学”而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并列,抢占了诗文的传统席位。更深刻的变化是,这意味着垄断了文坛两、三千年的抒情表现型、论理抽象型的诗文,一起被挤到了文学舞台的边沿,从此,长期遭受压抑的叙事再现型的戏剧和小说,将以其雅俗共赏的蓬勃生命力,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灾难性的后果还必然降临在元代散文作家队伍的素质构成方面。文体的革命性转换,裹挟着大批文学才俊精英,大步跨进了新体文学的广阔天地,有远见卓识的作家,纷纷从正统诗文划地为牢的狭小空间挣脱出来,在杂剧、散曲的创作中建树自己的文学功名。关、马、白、郑、王实甫等人从传统正统的文学世界的出走,让元代诗文的作家队伍,剩下的多是迂儒庸才,其间虽也偶现高人杰士,但队伍整体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准的平庸,使元代散文怎能继秦汉、唐宋以后再创辉煌,又无力与同时代的关汉卿们去比试高低。
境遇之三:随着忠臣陆秀夫迈进海水的脚步,最后一位赵家天子走向死亡。汉宋政权的彻底失败,元蒙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把占中华民族文人比重最大的汉族和南方各族文人,与全体汉族民众一起投入异族统治的特异环境,汉族文化遭受了血与火的严重考验,汉族读书人也饱受民族歧视和文人歧视。
起初,蒙古马铁蹄南下,一路掳掠屠杀。《金莲正宗记》卷四曾经这样描述:“当蒙古锐兵之南来也,饮马则黄河欲绝,鸣镝而华岳将崩。玉石俱焚,贤愚并戮。尸山积而依稀犯斗,血海涨而仿佛弥天。”文明程度很低的蒙古贵族,野蛮地践踏汉族文化。窝阔台时,竟有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2], 权臣伯颜也曾有过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议,要对汉族实行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据记载,当时的儒者士人很多沦为奴隶[3], 至于民间流传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则更夸张地形容了汉族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以“马上得天下”的元蒙统治者,初无所谓文化的概念,还曾经相信过“辽以释废,金以儒亡”[4]的流言, 故立朝前后约八十年废行科举,让隋唐以来走了六七百年科举路,笃信“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汉族儒生顿失前途,不得不另谋生计。这无疑会使大量可能成为散文作家的读书人流失,使元代散文的作家队伍大伤元气。“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的关汉卿们,一方面是他们具有更加超迈的文学识见,所以弃正统文体而创新声,另一方面,难道不也是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迫他们“沉抑下僚,志不得申,一寄之于声歌之末,以抒其抑郁感慨之情”(注:胡侍:《真珠船·元曲》。)吗?是元曲之大幸也,而元文之大不幸也。
如上所言,民族歧视与文人歧视及异族专政的压迫摧残,新兴文体与通俗文艺的剧烈冲击,先秦以来辉煌散文遗产之成为巨大历史重负,三大制约机制,置元代散文于不利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也许还可以加上立朝不足百年的时限,可能就是元代散文的成就上不能追唐宋,下不能比明清,而同时代也远不能与杂剧、散曲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
二
问题的深入,使我们还得研究元代散文作家队伍的素质构成,和他们的运作情况。
其实元蒙贵族的上层人物,一当意识到中原大地就要到手,即开始了谋求长治久安的思考,并相应有所动作。于是应该说某些读书人的处境似乎就有了改善,一批有社会声望的所谓大儒被搜罗重视,以备顾问。延祐二年(1315年)又恢复了科举,元代散文也因此而有所复苏,史称全盛。但幸事中却有大不幸在,从实质上说,元代散文一起步就掉进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深渊,初期大儒的恩遇,后来科举的终于恢复及所形成的热闹局面,仍只是这深渊里的舞蹈。这个深渊,就是道学。
由于元蒙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了,马上所得之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归顺的汉族儒生也努力向他们解释“辽非释废,金非儒亡”[4], 他们逐渐对他们将要统治的这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充满奥秘的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于是他们除了继续炫耀野蛮和暴力之外,也转而采取了以汉文化治汉人的基本国策。于是曾经被汉族统治者利用来有效地统治过汉人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又被元蒙统治者利用来有效地驾驭汉人。就这样,在搜罗到的一批所谓大儒的帮助下,儒学和程朱理学成了元代的官方哲学。顺理成章的是,儒学和程朱理学,也就成了元代散文法定的指导思想,成了元代散文终元之世也没能取下来的紧箍咒。
很明显,元蒙统治者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了汉族文化的优秀与伟大,而要来尽一分爱心。在这里,宋儒理学的被挑选是要用作一个大手段和大工具的,大儒的功用在于为其设计成熟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统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科举的恢复也是为了网罗更多的儒生人才,所以复科举的诏令中强调的是德行经术,而不要“浮华”“辞章”。也许在异族统治下如此因果地张扬民粹,虽有被利用的悲哀,但也有保存延续本民族文化的兴奋吧,不然大儒们何以那般投入?在这样的环境下,儒学本身已经工具化了,作为儒学运载工具的文章,当然更等而下之了。
文学的各种体式,与社会精神生活各个层面的联系,似乎各有分工。如果暂不考虑各种文体相互交叉嫁接而出现的复杂形态的话,那么一般说来,叙事再现型的戏剧、小说,更多地联系着民心,解剖着世情,其本性特色是真;抒情表现型的诗词歌赋,更多地联系着自我,抒发着主体情志,其风貌魅力是美;而散文文体因其较为直白的表达方式,必然更多地受着制度文化、君主意志、国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的控制,其思想素质应该是善。善是个好字眼。但是正因为它是个好字眼,所以古往今来的罪恶,都喜欢借它作掩护。这甚至已经成为一切专制统治者必须精通的法术。元代统治者显然也很精通这个法术,而且他们成功地利用了那些心甘情愿的读书人。
本来,文体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的内容,散文虽然更容易受到制度文化的挟迫、监控和利用,但那些具有奇胆奇识的作家,却可以挥动如椽大笔,写出惊世骇俗的警世奇文,宋末元初的邓牧,就是一位极有胆识的散文家。看来一个时代的散文成就如何,关键在散文家队伍的素质构成。于是我们还要来讨论讨论元代作家的整体状况和分布情况,才能继续这个话题。
戴不凡先生1958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过:“在关汉卿时代,文坛上存在着三种人。他们手里都掌握了文艺形式,却为着不同的目的服务。”第一种人是“卖身投靠的”,他举出王恽作代表,因为他不哭文天祥、陆秀夫,却给汉奸史天泽写祭诗;第二种人是“看破红尘的隐士”,举出胡紫山、卢疏斋、马致远为代表,他们是在唱着这样的歌曲:“门前栽柳,院后桑麻,有客来汲清泉,自煎茶芽。……无是无非,问什么富贵荣华!”第三种人自然是关汉卿们了,他们在那个“妄撰词曲”要处以严刑的时代, 以大无畏的精神,抒写受压迫者的愤怒, 为人民写作[5]p219。
戴先生的意见启发我们认识到,宋元易代的特殊写作环境,促使元代的作家队伍发生了三极分化,简言之:(一)归顺;(二)退隐;(三)入俗。极有意味的是,他们在文体上也形成了分工。归顺者们仍操传统文体,坚守诗文阵地,或及散曲,但一般拒绝杂剧,其思想是儒;隐士们以散曲为主,或兼作杂剧,间及诗文,其思想是道;偶倡优而不辞的入俗作家们则走进市井民间,以杂剧为主,亦作散曲,少涉甚至不及诗文,在思想上,他们是生活的杂色,进步开放,做小民的代言人。而其创作实绩之比较,是一个规律显现出来,那就是离长官意志、传统观念和正宗文体越远,甚至走上叛逆之路的,越富创造力,总体成就越高。从三支队伍的素质构成看,杂剧显然聚集了最多精英,其中还有文化巨人,散曲次之,亦多洁士高人,诗文作家整体看来较为平庸,迂儒居多。钟嗣成《录鬼簿序》曾经幽默地揶揄过那些迂儒,他为迂儒们所不齿的剧曲作家们立传,估计会遭非议,乃曰:“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是的,迂儒们哪能领略关汉卿、王实甫们的艺术趣味呢?钟嗣成的话,告诉我们元代作家队伍当时已经有了雅俗之争和门户之议。
值得进一步利用的是,钟氏所言“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圣门”之类,几乎正好是元代文论的几个中心词、关键词。元代散文的许多作家和论家,正是谨守孔孟的“圣门”,僵持程朱的“性理之学”,而自谓“高尚之士”的。试读一则当时有“北许南吴”之誉的大儒许衡的语录,其《鲁斋遗书》卷一有云:“凡无检束、无法度,艳丽不羁诸文字,皆不可读,大能移人性情。圣人以义理诲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语一见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古语有之,可不慎乎?”这样的迂论,在元代散文家的集子里是俯拾即是的。
鲁迅曾经指出:“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确实一语中的,十分深刻。这一点,在元代散文领域表现十分突出。元代散文的基本内容不出宋儒理学,而元代散文理论则终元之世,始终纠缠着文道关系。
元初,赵复、许衡、刘因、吴澄等鸿儒,倡导儒学,讲习程朱,他们承继宋儒,渐使理学成为道统,并成为统治者提倡推行的官方哲学。当时的散文家,多半就是理学家。由金入元的郝经,坚持着“不道德、不仁义而文章者,谓之逐末之士”[6]的观点,声称“不学无用学, 不读非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7], 他把元好问的写真实论改造成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散文观,以《原古录序》、《答友人论文法书》、《内游》等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道本文用、理自生法、悟道即文的文道关系论。在这样的理论中显然道学束缚文章。刘壎痛斥时文为“背时之文”,“亡国之具”,并欢呼“今幸科目废,时文无用,是殆天赐读书岁月矣。”[8]不可不谓有见识, 但他坚持的仍不过是“学以明理,文以载道”的常论。
当然后来也有论家在极力糅合文道关系的矛盾。如刘将孙在《赵青山先生墓表》、《题曾同公文后》等文章里,研究文道关系的融合问题,而提出一种理想的美学境界,叫做“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甚至有论家揭发道学对文章的压迫。戴表元与袁桷师生相继,就在文道关系上反对道学家排斥文章的观点,竟说出“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9]的大胆言论来,主张推翻理学对文章的压迫, 恢复文道并重的传统。
但是,道本文末也好,文道交融也好,文道并重也好,了不起是说文章也应受到重视,而道的内容则是一成不变地神圣着,不敢去碰的。甚至有些论者之所以敢于提高文章的地位,就是因为好文章才能更好地充当道学的运载工具。
没有新鲜思想的文章,就没有新鲜的活力、生命力,就走不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路。这可能是元代散文真正的悲哀。但同时代的杂剧作家和散曲作家们,却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收稿日期:1999—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