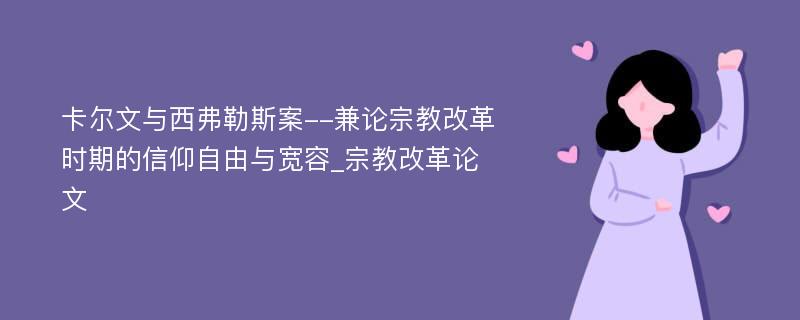
加尔文与塞维图斯案——兼论宗教改革时期的信仰自由与宽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尔文论文,宽容论文,宗教论文,时期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约翰·加尔文是16世纪欧洲新教改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新教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并没有像马丁·路德那样受到赞扬。相反,他却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被视为科学的反对者、信仰自由的敌人、宗教不宽容的代表,比罗马天主教会还要坏,“加尔文”一词甚至竟成了疾病、宿命论、罪行之类的代名词[1](p234)。加尔文的罪状主要是逮捕并处死西班牙人文主义者、著名的科学家塞维图斯,他的各种罪名也源于此,至今仍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加尔文究竟在塞维图斯一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反面形象又是如何确立的,该如何理解宗教改革与信仰自由乃至宗教宽容的关系?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
米盖尔·塞维图斯原名米圭尔·塞维托·科奈撒·阿里亚斯·利沃斯,西班牙人,于1509年或1511年的9月29日出生在阿拉贡王国距萨拉哥萨西北60英里的小村庄维兰纽瓦·德·锡耶纳,后来为躲避迫害,化名为米盖尔·维伦纽夫(维兰诺瓦努斯)。塞维图斯出身于传统的天主教贵族家庭,其父安东·塞维托是锡耶纳的书记员,母亲卡塔琳娜·科奈撒也是贵族家庭出身,塞维图斯家共有三兄弟,他是长子。
塞维图斯是在西班牙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的。16世纪初,人文主义传入西班牙并蓬勃发展起来,古典语言的学习与圣经的编辑整理成为热潮,伊拉斯谟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塞维图斯很早就接受教育,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莱文,13岁时,他入萨拉哥萨(或勒里达)大学学习,后来转到巴塞罗那大学,1528年,又入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塞维图斯深受方济各会修士尤安·德·昆塔纳的影响,并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昆塔纳是巴黎大学的博士,西班牙议会的议员,从1529年起担任皇帝查理五世的忏悔师,他实际是个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1525年到1526年,塞维图斯成为他的秘书。在图卢兹大学期间,塞维图斯除继续学习语言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著作,甚至阅读《古兰经》,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神学思想,同时看到了教会与政府对新思潮的镇压行为。他受人文主义方法的影响,把《圣经》作为考察乃至检验神学理论的依据,但是,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他发现基督教神学的主体——三位一体理论等在圣经中根本找不到依据,于是开始怀疑传统理论的正确性。1529年,已经荣升为查理五世忏悔师的昆塔纳再次召他作秘书,随后他与恩师一道在1530年亲历了皇帝在意大利的加冕仪式,使他对教会的腐败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教皇是“最邪恶的畜生,最无耻的娼妓”[2](p60)。
结束了意大利的旅程后,塞维图斯便前往日内瓦,途经里昂,后又前往巴塞尔、斯特拉斯堡等地,宣传自己的理论。1531年,他出版了《论三位一体之错误七书》,全面否定自尼西亚公会议以来的正统教会关于三位一体的理论。他指出,新约圣经里并没有“三位一体”、“位格”、“本体”、“本质”等字眼,这都是后来的杜撰,因而是错误的。耶稣基督是真人、上帝之子、救世主,虽然具有神性,但次于上帝,并不具有永恒性,道是永恒的,但子不是。圣灵也不是一个位格,它在基督升天后驻留在信徒的心中。1532年秋,他出版了《关于三位一体的对话》,再次系统阐述了反对三位一体的观点。
塞维图斯的言论遭到激烈反对。马丁·路德、梅兰希通以及瑞士各地的新教神学家纷纷撰文批判他,新教行政当局则开始禁毁他的著作。罗马教会的反应同样激烈。已经升任奥格斯堡禁书委员会首脑的昆塔纳对昔日得意门生的行为非常愤怒,立即下令查禁其书,同时上报帝国及教廷。教会随即组织人马对他的观点展开批判,下令全面禁毁其书,并扬言判处他火刑。1532年6月17日,教会发出逮捕令。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也开始调查此事,并向阿拉贡地区的宗教裁判员以及萨拉哥萨大主教和世俗政府发出通知,密谋逮捕他。
塞维图斯为了躲避迫害,化名米盖尔·维伦纽夫,隐居里昂。他在里昂的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先后编校过盖伦、希波克拉底、托勒密等人的著作,同时开始研究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并于1534年到巴黎大学学习医学。1538年3月毕业,随后到沙利厄镇居住行医。1540年,他在巴黎遇见了枢机主教皮埃尔·帕尔米耶,并成为后者的医生,随他入住维也纳的主教府。
隐居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神学,他一直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为此,他通过里昂的出版商让·弗莱隆与加尔文通信联系,讨论神学问题,并表达了到日内瓦来的愿望。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
加尔文与塞维图斯的交往始于1534年。加尔文非常熟悉塞维图斯的神学思想,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一直想劝其放弃错误主张。为此,当时双方约定在巴黎的圣安东尼大街面谈,但是塞维图斯并未履约。双方的通信交往并不愉快,加尔文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并送给他一本《基督教要义》,希望能劝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塞维图斯显然不同意加尔文的观点,他对《基督教要义》做了批注,对加尔文进行批判,同时送给他一些自己的著作。加尔文对他的执迷不悟及傲慢的态度非常生气,随即写信给弗莱隆表示不再努力争取说服他,与塞维图斯断绝往来[3](p153),并在1546年2月13日给法莱尔的信中说“如果他来的话,只要我还有点权威,就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3](p154)。1553年1月,塞维图斯又出版了《基督教的复原》,继续反对三位一体,并在神学论证中提出人体血液循环理论,还寄给加尔文一本。
《基督教的复原》一书出版后,加尔文在私下里曾向一些密友透露过此事,其中有一位名叫纪尧姆·德特里的法国难民,他是纪尧姆·比代的女婿。德特里有一位罗马天主教表兄安东尼·阿内伊斯住在维也纳,此时正是他要争取的对象。德特里在给阿内伊斯的信中陈述了实情,后者立即把信交给有关当局,天主教会开始调查此事,并将塞维图斯投入监狱。塞维图斯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说自己曾以塞维图斯的名义给加尔文写过信,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他本人已经放弃了那些错误的观点。为了逃避惩罚,他贿赂了狱官,从监狱里逃跑。法庭在6月17日缺席判处他火刑。
1553年8月13日,塞维图斯在逃亡过程中来到了日内瓦,在到教堂聆听加尔文的布道时,被人认出并被逮捕入狱。根据日内瓦的司法程序,加尔文先后指使其秘书尼古拉斯·德·拉·方丹和其弟安东尼·加尔文作为控告人,并亲自就神学问题起草了对塞维图斯的起诉书。市政府想把他引渡给罗马教廷,但塞维图斯表示宁愿接受日内瓦法庭的审判。日内瓦政府法庭经过几次审判,在征求了苏黎世、巴塞尔、沙夫豪森、伯尔尼等城市的意见后,以异端罪判处他火刑。加尔文等希望改判杀头,但遭到拒绝[3](p331)。1553年10月27日,塞维图斯被烧死,12月23日,维也纳宗教法庭追加了对他的火刑判罚。
二
纵观塞维图斯事件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他被处死并非加尔文一个人的愿望,实际上,无论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会都对判处死刑没有异议,而且,维也纳法庭早已经判处他火刑,加尔文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后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很大的变化,不但这份“功劳”归到他一个人身上,而且他也逐渐成为自由的敌人、不宽容的代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加尔文的反面形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的。
日内瓦政府处死塞维图斯的行为,引发了一场争论,该如何对待“异端”,世俗政府有没有权力武力惩罚异端。以卡斯特里奥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异端只应该由上帝本人来惩罚,世俗政府无权镇压[4](pp67—68)。卡斯特里奥虽然赞同宗教改革,但是在神学问题上却与加尔文有分歧,双方最后分道扬镳。塞维图斯一案过后,他匿名撰文攻击加尔文,提出宗教宽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矛头只指向加尔文,而多少忽略了负责审判的日内瓦市政府。卡斯特里奥的攻击赢得了一些人,尤其是加尔文的政敌的响应。加尔文在日内瓦一视同仁的改革措施引起了城里一些权势贵族的不满,这些人生活放荡、道德腐败,改革自然对他们不利,因此,他们一直以个人自由为借口,攻击加尔文。为了打击加尔文,他们还支持卡斯特里奥并联合另一位加尔文的论敌波尔塞克,进一步攻击他。波尔塞克因反对加尔文的预定论被逐出日内瓦,随后又回到天主教阵营。为了回应攻击,加尔文在1554年就塞维图斯一案发表文章予以驳斥,重申武力惩罚宗教犯罪是世俗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并得到多数新教神学家的支持与认可,1577年,波尔塞克出版了加尔文的传记,捏造事实攻击他。虽然这些来自对立面的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太大影响,但却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自由、理性、进步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内容。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当他们回顾16世纪,尤其是宗教改革的历史时,看到只有不自由、迷信、倒退,与中世纪没有区别。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严厉改革使他一直有个人自由的迫害者的嫌疑,随着有关材料的发现,他也成为最受“青睐”的对象。1730年,日内瓦政府秘书让·戈蒂埃在编撰日内瓦的历史时,首次对塞维图斯案表示异议,不久,有关塞维图斯的传记著作相继问世。1756年,伏尔泰在日内瓦发表了《风俗论》,从思想及良心自由乃天赋人权的角度,把加尔文定为处死塞维图斯的罪魁祸首,说他“自立为新教的教皇”,嫉妒心强,是个暴君[5](pp520—521)。爱德华·吉本认为宗教改革并没能使信仰自由,只不过用一种束缚取代了另一种。改革家们同样实行僭政,把各种严刑峻法加于人民,对宗教异端处以极刑,加尔文即是典型[6](pp334—335)。作为启蒙运动的殿军,伏尔泰的结论几乎成为普遍真理,被崇尚自由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下来。
19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仍是理性王国的天堂,加尔文的命运每况愈下。他不但反对自由,而且反对科学,因为他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曾经说过“谁敢斗胆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之类的话。此外,塞维图斯曾经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加尔文处死了他,因而也就成为科学的敌人。恩格斯指出:“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他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7](p446)。恩格斯的论断不但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以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论断也成为加尔文的一个代名词被接受下来。19世纪末,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的著作被学术界整理出版,更加深了人们的印象。加尔文的反面形象在美国得到进一步深化。美国教育的教科书要么根本不提加尔文,要么把他作为不宽容、精神迫害的典型、宗教不宽容的代表、自由的敌人甚至“恶魔”,作为塑造与旧欧洲不同的以自由与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的反面典型。
加尔文的反面形象在20世纪里继续延续着,先是被比作法西斯,后又成为影射共产主义的工具,房龙的通俗故事系列,是对大众观念的又一次强化。同一时期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和平主义者斯·茨威格的著作则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斯·茨威格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对于这位“从早年起,维护自由与独立就是最强列的本能”[8](p246)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异端的权利——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无疑就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对暴君的反抗与对自由的渴望再次通过对加尔文的鞭挞表达出来,加尔文这位被启蒙思想家称为“暴君”、“新教教皇”的改革家,在斯·茨威格笔下几乎就是希特勒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极权主义野心家、狂热分子、魔鬼、杀人狂、自由的天敌,“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为神权的专政”,“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9](p28;p2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再次祭出自由的大旗,作为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武器。对一些刚脱离社会主义、乍接触美国民主的知识分子来说,体验自由进而探讨其历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玛瑞安·希拉说:“我从波兰来到美国时,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一种体现在日常的意识形态、宗教以及哲学中的新精神。为了理解我的新的社会环境,我必须研究它的发展史,探寻确立美国民主制度的那些思想的根源。这使我研究塞维图斯,把他视为历史上的中心人物,正是他的殉道开启了宗教思想的新方向,激励着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对普遍压迫宗教思想以及知识探索做法的批判分析。最终,塞维图斯和卡斯特里奥播下的种子首先在索齐尼派宗教运动,然后在启蒙运动中生根发芽。”[10](preface)希拉的著作正是这种理念的产物。美国例外的民主论成为绝对标准,反面角色仍是加尔文,所不同的是,他代表已不再是传统的旧欧洲,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了。
三
在近代西方主流思想的视角下,加尔文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光环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反面的形象,由力主处死塞维图斯的群体中的一员,被逐渐从中剥离出来,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成了杀人犯、科学的敌人。在自由、宽容的标准下,他由一位追求自由的代表转变为自由的敌人、不宽容的君主;由一位接受世俗政府领导的市民变为实行“政教合一”的独裁暴君。
那么,这些对加尔文的指责是否属实呢?该如何来认识呢?
长期以来,加尔文反对哥白尼学说的这句话几乎成为他反对科学的铁证,但相关研究表明,这是后来学者的杜撰,他不但不反对科学,反而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
如果说反科学的指责是不真实的,自然无公正性可言;反自由、不宽容的指责倒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似乎不存在不公正问题。在塞维图斯案的前前后后,他确实是最积极的一个,从逮捕、指控、起诉书的起草、审讯到处死,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加尔文力主处死的是异端,但同时是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尔文对塞维图斯之死负有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为此受到谴责也是毋庸置疑的。
承认并批判加尔文的错误当然是必要的,但完全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把错误绝对化,也是不对的,必须用历史的态度,结合时代的特点进行分析与评价,看看那个时代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程度。
宗教改革对罗马教会独霸西欧的现实提出了挑战,良心自由成为新教反对罗马教会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的完全自由,无论罗马教会还是新教会都如此。对16世纪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对基督教及其信仰的理解在本质上与以前没有区别。基督教仍是最高真理,宗教上的得救仍是人生(人类)的最终目标,它关系到整个社会或世界,绝不是个人的私事,更不是个人道德生活的指南。对他们而言,基督徒有选择教派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考虑),但没有选择不作基督徒的自由。否定基督教或者其基本教义,都是异端,必须受到惩罚。新教反对罗马教会,并不是要否定它另立新宗教,而是要纠正错误与迷信,重新确立正确的信仰。信仰自由及良心自由是在这个逻辑前提下展开的。塞维图斯反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等理论,但他绝不反对基督教,他的目的同样是恢复早期的淳朴的基督教。
对于宗教改革时代的基督徒来说,所谓的信仰自由还是建立在遵守官方教义的前提之上的,任何超越这个前提的公开举动,都将受到惩罚,罗马教会和新教概莫能外。天主教会在宗教改革时期迫害的新教徒不计其数,新教同样对异端进行处罚。宗教上的罪行不仅仅违反了教会法,应当受到教会的处罚,而且违反了世俗的法律,因此,惩罚宗教犯罪是世俗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政府参与宗教乃至控制宗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1566年9月,伯尔尼政府处死了意大利人瓦伦丁·甄塔勒,新教处死异端的情况在英国也是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甚至在17世纪仍然存在,1632年,日内瓦政府以异端罪烧死尼古拉斯·安东尼,1652年,则以巫术罪吊死了肖德龙,1687年,德国的吕贝克政府处死了彼得·君特尔。对绝大多数宗教改革家而言,改革并非完全把世俗政权从宗教事务中排除出去,更不是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排除它的宗教责任,只是对它的权限进行重新界定,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教关系,实现分权与合作的模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新教的出现虽然有助于宗教信仰自由与宽容的进步,但是,在对信仰自由与宽容的理解上,基本上与传统的观念没有分别,不但未能实现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宽容,就连基督教内部在这方面也未完全实现。犹太教、伊斯兰教乃至其他宗教仍是“敌基督”的异教,要么接受归化,要么被彻底消灭[12](pp366—370);宗教异端、巫术迷信、不奉国教者都不是宽容的对象。甚至连呼吁宽容的最著名的代表约翰·洛克,也未能做到彻底的宽容,在他的《论宗教宽容》中,无神论者与不奉国教者是不在其中的[13](pp15—16)。
所以,总体而言,16世纪欧洲的宗教信仰自由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在这种前提下,所谓的宽容也具有很大的时代特点,远没有达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状态。有学者指出:“近代早期的宽容无疑要么……是失败者的信条,要么仅仅是局外者用宗教、政治及社会术语提倡的一种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许多本性上倾向于某种形式的宗教宽容的人,却激烈地反对宽容。”[14](p4)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宽容并非真正的理性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较量的后果,《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的“谁的领地,信仰谁的宗教”的原则是最好的证明。不仅如此,宗教自由与宽容在新教各派内部也没有完全实现。实际上,“至少到17世纪30年代,绝大多数撰文论述宽容的这个时期的作者,争取的仅仅是良心自由,偶尔涉及一些崇拜方面的有限的自由,他们的信念是,这种宽容最终有助于建立真正的和平与和谐。他们都认为,宗教上的多样性本身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能在短期内予以宽容,为的是正确的信仰最终获胜。”[14](p6)
加尔文应该受到谴责,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他的指责并不是完全公正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加尔文在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思想视野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顾此失彼的做法的结果,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处死塞维图斯既是加尔文个人的错误,又是他那个时代的错误与悲剧,让他一个人承受整个时代的错误,是不公正的。虽然进步,理性是启蒙思想家的大旗,但在自由宽容问题上,他们恰恰否定了它。自由与宽容在他们那里成了独立于历史之外的衡量一切的绝对不变的标准,加尔文自然成为它的牺牲品。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历史简单化了,以为新教就一定比罗马天主教进步,好像罗马天主教迫害镇压宗教异端是理所当然的,是无可指责的,新教的这些行为则是必遭谴责的。这不但歪曲了历史,同样曲解了自由、宽容、进步等理念。自由、宽容、进步的原则是绝对的,但其内涵却总是具体的,总是与具体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的。只有“抛弃永恒不变的也就是非历史的理性原则,代之以真实的历史环境及特殊的事件,”[13](p17)才能获得一种更真实、更客观、更公正的历史认识。
标签:宗教改革论文; 加尔文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罗马市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