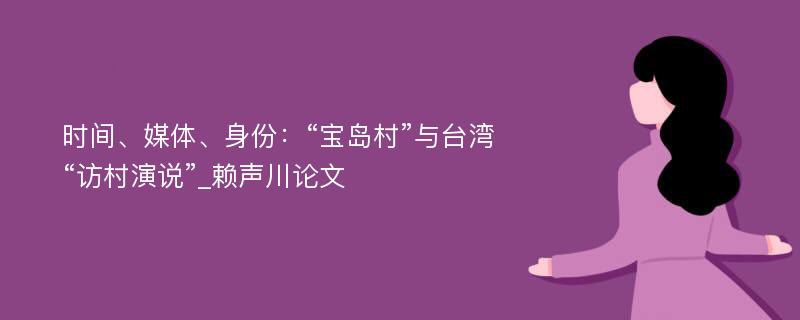
时间、媒介、身份:《宝岛一村》与台湾“眷村言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宝岛论文,台湾论文,媒介论文,一村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眷村二代子弟,王伟忠于2006年开始向赖声川讲述眷村故事时,他曾经居住过的台湾嘉义“建国二村”已于一年前拆除。尽管之前已经拍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在电视上播出过,也预备筹拍电视连续剧①,但在王伟忠看来:“电视讲求快速,必须不断制作‘产品’;舞台剧的艺术性格比较强烈,可以酝酿……舞台剧的影响力和时代意义不同……电视上什么东西都会过去,比较琐碎、冗长,有广告掺杂;舞台剧却能一直演,今年演、明年演、十年之后演,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完整的东西会留存下去……”②眷村的故事持续讲了两年,2008年,赖声川以王伟忠的讲述为主要素材,拟定大纲,得到王伟忠认同后,选定演员(其中约三分之二具有眷村背景),运用他所擅长的集体即兴创作方法创作出舞台剧《宝岛一村》。该剧于2008年12月5日首演于台北,第二年,正是国民党迁台60周年,《宝岛一村》在台湾的嘉义、台中、高雄、中坜、台北先后演出41场③,在台湾重新掀起眷村热潮。曾有人担心过它的政治危险性④,但这出戏非但没有挑起族群冲突,反而出人意料地产生了沟通蓝绿阵营的“桥梁”作用⑤。《宝岛一村》的台词与内容几乎没有经过什么调整,就于2010年1月启动大陆巡演之旅,先是登陆广州,之后一路北上,历经三轮先后演出54场遍及13个城市⑥,所到之处广受欢迎,丝毫没有接受的障碍。而在大陆的媒体看来,“该剧所反映的内容和剧中很多台词一样,多年以前是很难想象能在大陆出现的,其情其景格外令人感怀”⑦。
王伟忠找赖声川来创作这出眷村戏,当然首先缘于赖声川在剧场界业已取得的卓越成就。这位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戏剧学博士自1983年回到中国台湾之后,长期运用集体即兴创作方式,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融于一体,创作出24部⑧(至2006年)原创戏剧作品,其艺术影响力之深广使他两度(1988年,2001年)获得台湾政府颁发的文艺奖,而面广量稳的受众群体也使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表演工作坊成为台湾仅有的可以依靠票房生存的民间剧团。在中国内地、亚洲区域,甚至国际上,赖声川的声名同样不同凡响,对于他的各种赞誉臻至其极。除了艺术声望之外,王伟忠选择赖声川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两岸关系这一台湾社会逃不开的问题在赖声川多年来的戏剧表现中始终或显或隐,脉续不断。《暗恋桃花源》、《回头是彼岸》、《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先生,开个门》、《我和我和他和他》、《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等作品直接探讨两岸关系在社会政治、文化人心等层面的显现,而《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西游记》、《红色的天空》、《如梦之梦》等剧虽不是直接表现两岸关系,但大陆与台湾在文化源流、命运纠葛、艺术传承上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其中依然隐约可见。基于此,赖声川自然成为王伟忠心目中创作眷村素材剧场作品的不二人选。
赖声川的戏剧作品善于把捉时代精神脉搏,诞生于2008年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宝岛一村》与既往的“眷村言说”相比,也具有时代所生成于它的独特质感。在台湾,眷村文学的高潮发生于1980年代,朱天心的小说《未了》获得1981年《联合报》中篇小说奖,除此之外,较为读者熟知的还有朱天文的《小毕的故事》、《最想念的季节》,苏伟贞的《有缘千里》、《离开同方》,袁琼琼的《今生缘》,爱亚的《曾经》,张大春的《鸡翎图》,苦苓的《外省故乡》,萧飒的《如梦令》、《少年阿辛》等,1986年由希代公司出版、青夷主编、集合了十多位作家作品的《我从眷村来》,更可说是首部眷村文学大成之作⑨。在台湾研究者看来,眷村文学的高潮之所以在1980年代发生,是因为“此时的眷村住民同时遭遇着生活空间的瓦解与生活经验的转变,前者逼使其走出竹篱笆,与眷村外的台湾其他群体汇流,从而消解眷村身份殊异性;后者则动摇了他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使命和信念,重新思索‘我是谁’的课题。”“透过书写,他们一方面传达‘被边缘化’的焦虑不安,另一方面,则企望藉由书写‘我族’和‘我村’的集体记忆,留下属于他们的历史。”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本土化”、“去中国化”的言论立场与政治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加剧眷村群落的边缘化,相应地,“书写与关注眷村的热潮,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以降渐渐冷却”⑩。《宝岛一村》能够创造新一波的眷村言说热潮,与出现的时间点不无关系。2008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眷村改造限期临近(11),国民党迁台即将60年,都使这出戏在台湾的诞生不仅有了合宜的政治气候,更别具纪念的意义。
由于时间节点所生成的对眷村的纪念意味,也许还由于王伟忠持续讲了两年故事的行为给赖声川留下太深的印象,《宝岛一村》就由王伟忠扮演的说书人开启整个故事。接下来,从第二场开始,剧中的眷村二代轮流充当说书人角色。说书人的存在填补了长时段、多线索剧情在跨越间留下的空白,而其“口述历史”的形式亦创造出“故事”向“纪录”转化的幻觉。在台湾言说眷村的文艺系统中,《宝岛一村》的史传色彩最强,不仅因其采用近似于《茶馆》的史诗式结构,由三段眷村历史(1949-1950,1969-1975,1982-2006)串接而成,还因为,相较其他跨越长段时间进程的眷村作品,如小说《未了》、《有缘千里》、《离开同方》、《今生缘》,电影《竹篱笆外的春天》、《小毕的故事》(根据朱天文同名小说改编)等,它的时间刻度最清晰。在以上所列举的作品中,时间融解于人事更替、主体经验中,往往没有明确的年份标识。而在《宝岛一村》中,不仅有具体的年份作为时间印记,而且,蒋介石去世、李登辉当政、开放探亲、眷村拆迁,这些进入公众记忆的社会重要事件都在剧中人的生活、言论中一一呈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出富于纪念性的戏不仅可看作“故事”,亦可视为“文献”。
历史有其传承。本剧采用从头说起的叙述策略,便要将眷村的历史传承展示出来——不仅只是地理上的“从何处来”,还有文化与历史的渊源。第一幕第一场为“入住”,各种不同的口音——北京腔、天津腔、江浙腔、四川腔—表明这群人的来路;魏中解释冒名顶替的姓名为“宋朝”的宋、“仁爱”的仁,亦微妙地显现历史与人文的渊源。1950年元旦的升旗仪式上,老赵将一面残破的青天白日旗拿出,要求挂上,解释说:“这是抗日时,我一个弟兄背在身上的。”(12)这个场景在内地演出时,不仅自然地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传递出一个重要的政治讯号:这些国民党士兵即使败退台湾,他们心中作为军人的荣誉依然是抗日,而非剿共。在台湾过的第一个除夕,他们情不自禁唱起思乡之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种情感在接下来的两幕中或显或潜地延续。大树下是眷村一代的政治论坛,不管是讨论戴笠死没死,还是反攻内地应当采取何种路径,或者骂李登辉“小王八蛋”,都是故土情感、国族认同的曲折显现。而在1990年三户人家返回内地探亲时,40多年的悲情瞬间释放:奶奶突然打了小毛一巴掌,“这一巴掌是你代替你爸爸挨的。当年他骗我说去台湾玩玩就回来,这一玩就玩了40多年”;小朱与元配抱头痛哭,却又惊喜地发现他留在内地的儿子已经替他生出了孙子;周宁在内地除了有已逝的父母、健在的姐姐,还有一个关系非同寻常的战友——他在他墓前的哭诉,揭开其同性恋身份。骨肉分离、血脉传承、情感羁恋,两岸割不断的联系在这一场戏中得到极致的显现。
然而历史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以2008年的时间节点回溯眷村历程,《宝岛一村》对于“变化”的显现相较其他“眷村言说”尤显自觉与清晰。从入住到迁出宝岛一村,这是变化在50多年间的显现;小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朱建国(小名大牛),第二个儿子取名朱建台(小名大车),这是变化在一年间的显现。尽管眷村由于成分单一(由同一军种的军人及其眷属组成),管理严格(国民党在军中推行政工监视制度),也因为具有自足的供给保障系统(每月固定的食物配给、子女学费减免优惠、眷户的电费减半等措施,也搭配了军人的退役、抚恤制度、医疗补助等)(13),其一代住户很少与外界往来。然而眷村毕竟不是铁罐头,从本地人陈秀娥的嫁入,到老赵与本地木匠小黄的来往,都显现眷村与台湾社会互渗融合的客观存在。如果说眷村一代除了必要的事务,很少出村,眷村二代可大不一样,随着他们的成长,人生半径比起父辈显见扩大了。大牛、大毛、二毛、小毛、周胖都因各种因缘离开眷村,唯一留在眷村的只有大车。在宝岛一村的第一个除夕,围炉夜话的眷村一代中除了陈秀娥,清一色都是内地来的;在宝岛一村的最后一个除夕,眷村三代齐聚,成分复杂极了:内地来的眷村一代,嫁入眷村的台湾媳妇,他们生出的眷村二代,眷村二代的婚姻对象有美国人、越南人、中国台湾本地人,二毛的丈夫居然还是民进党官员,他们生出的眷村三代从血缘上来说,真是复杂极了。
蒋介石去世后,“反攻大陆梦”从此化为泡影,这些国民党老兵不得不在这片土地上安住下来。时间改变人事,1950年,老赵岳母在台湾去世时,内地人在台湾的坟墓屈指可数,这种情形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如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道:“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14)。1980年代,宝岛一村中的老赵在台湾去世,这是眷村一代加速凋零的开始,苏伟贞创作于1990年的《离开同方》中,奉磊也是捧着母亲的骨灰坛回到同方新村的。时间悬置身份,对于眷村一代的身份尴尬,朱天心有过悲情的陈述:“得以返乡探亲的那一刻,才发现在仅存的亲族眼中,原来自己是台胞、是台湾人,而回到活了40年的岛上,又动辄被指为‘你们外省人’,因此有为小孩说故事习惯的人,迟早会在伊索寓言故事里发现,自己正如那只徘徊于鸟类与兽类之间,无可归属的蝙蝠。”(15)时间养成习惯,在《宝岛一村》中,回乡探亲的周宁婉谢姐姐“来住”的邀请,“这么多年住在台湾习惯了。”宝岛一村要拆除了,对于眷村一代是二次离乡,对于眷村二代是伊甸不再,他们都有对眷村岁月的流恋与怀想,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家人、邻居、朋友一起举行的这场欢送会,其主调是迎向于新,而非踯躅于旧。
《宝岛一村》的开头与结束都是同样的场景:鹿奶奶缓缓走过正在拆除的眷村废墟……“剧中的鹿奶奶是我们小时候公认神奇的人,传说她是青帮子钗头凤。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传说,可是对赖老师来说,这占了很重要的象征位置。”(16)赖声川的戏剧惯于在虚实之间穿行,扮演者周妲吟认为,“整个《宝岛一村》是鹿奶奶在台湾的回忆。”(17)也许换个说法也可以成立:鹿奶奶的形象集中呈现了宝岛一村的人对自己村子的情感投射与历史记忆。苏伟贞在《台湾眷村小说选》的序言中写道:“这些人在原本应该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与冲突,漫无目的游荡,失去坐标,成为地球永远的飘浮者,切断在生命光谱的两极,恐怖到像无止尽的惩罚。时时刻刻宜乎问:乡关何处?”(18)这是眷村悲情最剀切的表达。回想鹿奶奶接唱大车在电视节目中未能接续的那首“郊道”:“风凄凄影摇摇,殒星曳落怪鸟长鸣,一路行来无人烟……”就可以看到失落家园无以自处的凄切是一切眷村言说共同的底色。鹿奶奶两次在眷村的断井残垣前走过,这个美丽优雅、永远不老的形象或可视作眷村人心中恒定的家园意识与变化的历史现实之间的对峙。
“常与变”的关系命题在赖声川的戏剧中并非首次出现,《暗恋桃花源》、《回头是彼岸》、《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我和我和他和他》等有关两岸题材的舞台剧都通过别具匠心的构思将这一关系命题融入多层次对位交错的情节结构中。以《暗恋桃花源》这部在内地传播最广的戏为例,该剧通过“暗恋”与“桃花源”两个故事各三段剧情的拼贴,呈现时间所带来的人事变迁与主体不变的追寻情结之间的映照与冲突,对古往今来恒常的“桃花源”情结进行政治、文化、人性等多层面的演绎,充满张力的拼贴性结构与寓义深刻的细节使该剧具备可供深入解读的艺术精致性。而在《宝岛一村》中,这种富于个人思维特质的设计不见了,结构演绎的是客观的历史时间行程,场景展现的也不过是客观的历史形貌,然而,如果细心追究其中的场面、细节、线索的处理,隐没在“客观”背后的“常”与“变”这一属于历史、哲学、现实人生等多种向度的关系命题将再一次浮现。正是在常与变的关系坐标下,《宝岛一村》对于历史性意识形态的言说才能跨越政治的樊篱,引导受众以更为理性的心态来审思这段历史及其人事。相对于台湾既有眷村言说所渲染的历史之变发生时的不可承受之“重”,《宝岛一村》对于悲情点到为止,更多着眼于乡愁对于文化的濡养以及小人物在困境中挣扎求活的韧性。而该剧所内含的另外一个命题同样不应为我们所忽视:人在急剧变化的历史中,该如何应对内心深处对母体文化的追忆与眷念?当血缘、文化的构成随着社会的变迁越来越趋向复杂化,个人的身份认同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困扰?也许赖声川对此并无答案,但如果我们仅仅陶醉于舞台上种种精彩场面所激发的笑声与泪水,而对这一命题毫无觉察与触动,那对于整出戏的观赏,无异于买椟还珠。
《宝岛一村》作为一个不很“象”的眷村名字显然有意为之。它虽然标明是“空军眷村”,但赵、朱、周三家代表着眷村常见的家庭形态:老赵从内地来时带着妻子与岳母,是单纯完整的家;小朱的家眷留在内地,来台后与本地女子结合,是族群融合的家;周宁独身,后来和遇难的战友家属成立家庭,是婚姻变异的家。发生在这三家的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眷村。由此可见,《宝岛一村》表现的不是眷村的个别形态,而是一般形态。
就“家庭”而言,运转其间的无非是衣食住行娱,如何呈现眷村特色?“一个地方的文化开展,一定是从‘吃’开始。眷村带来了各省吃的多元文化,象牛肉面是外省老兵带来的,传统菜市场里所贩售的各种馅饼、水煎包、烧饼、油条、卤菜,也陆续成为台湾一般民众熟悉的小吃。”(19)食物在散文随笔中可以随兴起笔,在戏剧中却不能孤立存在,而应成为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本剧中的天津包子就是作为贯串始终的剧情元素而存在的。天津包子的手艺由来自天津的钱老奶奶传给好学的本地媳妇朱嫂,之后成为朱家养家糊口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成为宝岛一村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钱老奶奶向朱嫂面授机宜:“做天津包子是有诀窍的,里面要包肥肉跟瘦肉,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调整的。”“这个天津包子就是让人家吃了什么味儿都有,但是你就是说不出是个什么味儿!这就是最地道的天津包子!”小小的天津包子包含着中华文化善于应变与化合的智慧精髓,当然它还是内地饮食文化在台湾得以传承的见证,也是台湾多元文化融合的一种象征。在眷村人的回忆中,眷村的“穿”颇多趣事:“美援物资也是不少人的衣着来源,‘净重五十公斤’的面粉袋内裤,如今早已成为怀想当年的经典笑料”(20)。因为不是情节的必然组成部分,这种笑料在该剧中没有用上,而旗袍却成为剧中富于特定文化内涵的穿着。在《宝岛一村》的舞台上,鹿奶奶的优雅、冷如云的美丽都由不离身的旗袍来体现。她们都是内地来的眷村一代,旗袍维系着对母体文化趣尚的情感与记忆,剧中的本地媳妇朱嫂不穿旗袍,眷村二代也不穿旗袍,文化与代际的分别在旗袍中得以展现。不管是吃,还是穿,只有传达出眷村生活所内蕴的文化信息,眷村的特质才真正地显露出来。
与小说的文字叙述、电影的平面影像相比,剧场表现眷村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对空间的立体呈现。居住特点对眷村人际关系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眷村的整体精华在于‘非常拥挤’——你家窗就是我家窗,他家在防火巷里,走到后院就通到别人家去。所以像伟忠就觉得,他是被很多人带大的,那种感情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力”(21)。由于你家窗就是我家窗,赵、朱、周三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剧中时常出现,两家或三家打开窗相互通话、递送食物、看电视的场景;也常常出现,这家发生了什么事,隔壁邻居侧耳窥听的场景。该剧在舞台上以只现梁柱的方式极简地勾勒出一字排开的三家住户,不仅让观众得以窥见户内居民的生活内容,而且生动地呈现三户之间极富眷村特色的互动交往。对于长大了的眷村二代来说,这样的空间有着逼促的另一面,他们渴望走出眷村,拥有自己的天地,缘于此,眷村二代不管命运形式如何,离开是普遍的选择。近邻既能成就大毛与大牛青梅竹马的恋情,亦让大毛的母亲觉得这样的婚姻太没出息。导演在表现因儿女恋情引发的纠纷时,充分利用了两家相邻、共用窗户这一居住特点,共时性地展开彼此家庭的声气互动。这场纠纷的高潮是,歇斯底里的赵嫂打破了两家共用的窗玻璃。眷村二代的恋情受挫唤起观众的悲剧性体验,然而紧接着的场景却具有出人意料的喜感,心烦意躁的老赵口渴想喝茶,茶壶却没水,他透过碎掉的窗玻璃问隔壁的小朱,“喂,有没酒?”剑拔弩张之后却以两家男人携手喝酒而结束。对于眷村居民来说,简陋、拥挤、时有纠纷的生活之所以在他们离开之后的情感记忆中总留有一抹温馨甜美,便因为这种难免龃龉却又不计小节的患难情义。眷村的居住特点是眷村人际关系乃至命运形式形成的基础,导演据此做足剧场的文章,可算切中眷村的精华,也使《宝岛一村》在“媒介”的表现力上,区别于以文字、影像来表现眷村的作品。
有关眷村的文艺作品总少不了音乐。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几首英文歌曲对于表现主人公命运、情感不可或缺。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中开篇就说:“读这篇小说之前……我恳请你放上一曲Stand by Me,对,就是史蒂芬·金的同名原著拍成的电影,我要的就是电影里的那一首主题曲……”(22)小说无法直接呈现歌曲的旋律,只有熟悉这首歌的人,或有心去找到这首歌仔细聆听的人,才能体会得出歌中“Stand by Me”的反复呼喊如此贴合好勇斗狠却又惶惑不安的眷村二代气质。由于剧场再现声象的特性,音乐成为《宝岛一村》重要的表意手段,不仅创造情绪氛围,更介入情节发展中,发挥着多向度的表意功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下,英文歌曲在台湾非常流行。“Que Sera Sera”是1956年美国电影《擒凶记》(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的插曲,歌词以我问母亲,我问爱人,儿子问我的形式,分别提出三个问题:将来我是否会变得美丽、富有?将来的生活每天都会美好吗?将来我是否会英俊、富有?不论是妈妈,还是爱人,还是长大后的我,对问题的回答都是“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这首歌在剧中共出现两次。第一次二毛在留声机上放出这首歌,大毛与大牛正在隔壁房间打牌,此时,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命运尚未显形,而门前走过穿着时尚的大辣、小辣姐妹花,也尚未下海当陪酒女。未来会是怎样?美好的幻想存留心间,此时的他们也许根本未曾留意歌中唱的是什么,更谈不上理解“世事不可强求,顺其自然吧!”的人生态度。而大牛对大辣、小辣开的轻薄玩笑引起大毛的不满:“那我穿那样你也要那样看啰?”这种认真的负气预埋了命运的伏笔。这首歌第二次出现于宝岛一村的告别联欢会上。已经人到中年的大辣、小辣唱起:“Whatever Will Be,Will Be(顺其自然吧!)”,她们已由当年的吧女发展成现在的piano bar老板,在座的大毛、二毛、大牛、大车们,命运各不一样,人生滋味也远非当初所能预料,从小生长于其间的宝岛一村也马上要拆了,再唱(听)这首歌,是无奈,是洒脱?其间况味远非当年。
导演将音乐植入剧情多有神来之笔。剧中,大车要去参加电视台的“三朵花”节目,邻居周宁先替他演练一番,起唱了一个字“我”,众人齐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周宁说:“错!这首现在是禁歌,全部带走!”接下来,二毛又接唱:“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周宁又说:“错。”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又错,周宁说“没有理由!就是错!”如果知道这是一首1930年代的上海老歌,诉尽爱情失意的哀怨,就理解深谙党国禁忌的周宁何以说“错”。接下来周宁自己对出了一首英文歌:“whoa,whoa,whoa,yea,yea,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这场对歌既传达出眷村邻里间亲密无间的情感,又不着痕迹地将那一时代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虚弱性暴露无遗。
剧场空间不仅能逼真地复现现实生活环境,更具有特殊的赋义能力。舞台与演区的分割、观众对演出的聚焦式欣赏、观演之间活生生的交流,生成剧场空间特有的仪式感。在赖声川的创作历程中,将剧场空间的仪式感发挥到极致的当属2000年问世于台北,2013年复排于内地的《如梦之梦》。受启于印度菩提迦叶的信徒绕塔仪式,赖声川将观众视同舍利塔,让演员在环绕观众的四面舞台上演出,配合着关于旅行、轮回的剧情线索,营造出川流不息的存在感与神圣而又梦幻的仪式感。贯通于“莲花池”(中心观众区)的纵轴,亦成为展示剧中人物心灵对话、命运转换的另一条仪式通道。《宝岛一村》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上演出,其仪式感没有《如梦之梦》鲜明,却仍可透过特定情境的设置生成。来到台湾的第一个元旦,宝岛一村人汇聚于广场上举行一场升旗仪式;第一个除夕夜,众人齐聚于老赵家围炉夜话、遥望故乡方向。透过这两个集体场面,眷村一代的家国情怀、思乡重负唤起观众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言的“怜悯”之情,经过剧场共同体的能量汇聚,升华为庄重、神圣的仪式感受。在台湾演出中,台下坐着老去的眷村一代,这种仪式感在他们心中更为强烈,其内涵也更加复杂。最后一场戏中,死去的老赵以魂灵的形式参与宝岛一村的告别会,他写于儿子出生满月时的一封信从家中房梁上取出,“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愿你此生一切平安。”平实的话语、超现实的画面使这个结尾不仅切合眷村的命运背景,更连接到人类共通的命运前景,成就一场共同的祈愿仪式。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点滴亦在剧场中传递出特定的含义,老赵的岳母在台湾去世,当棺材送到时,隔壁家的朱嫂正逢临盆,通过舞台上的巧妙衔接,这一场景延伸出生死交替、代际延续的象征意涵。赖声川充分地把握住剧场的特质,使有关眷村的点点滴滴既含有源于生活的日常性又不乏从具象中延伸、可供升华的象征性。由此反观2008年由王伟忠参与制作的表现眷村人事的54集电视连续剧《光阴的故事》,虽说故事的模型大同小异,但舞台的精炼与电视剧的琐碎、剧场中的神圣感与荧屏前的消遣性,使相近的眷村素材分野成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产品。
赖声川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台湾戏剧导演,实际上其身份构成远较此复杂。作为1954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的外交官子弟,他拥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整个童年时期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从1966年跟随父亲回到台湾到1978年留学美国,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又都在台湾形成;1978年到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接受完整的西方戏剧教育,1983年回到中国台湾以后,其绝大部分剧场作品都在台湾完成,因此台湾人的身份认知是相当自觉的;而赖声川的父母均来自内地,从小对他施予的身份教育是“中国人”;其祖籍在江西的会昌,在台湾填写身份信息时,籍贯一栏填的都是江西,因此,江西人的身份同样可以成立。而在《宝岛一村》的创作中,赖声川的身份更多了一层特殊性,即他是台湾眷村题材文艺作品中少见的非眷村出身的创作者,那么,身份构成的复杂性如何生成《宝岛一村》的言说特性?
眷村的形成源于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带来的大规模战争移民,《宝岛一村》对于迁移的表现既尊重历史的事实,又将“迁移”汇入人类历史恒常的变动经验中。1949那个时空发生的故事是因政治原因产生的迁移;而之后,这些移民一代的子女们由于各种因缘走出眷村或移居海外成为第二次的迁移;随着眷村的拆除,眷村居民们不得不迁居又是一次新的意义上的迁移。该剧一而再地重现“迁移”,可见赖声川已将迁移看成是变动不居的人生中的常态,其中不难发现他所经历的居所频移、身份叠变的经验投射。也正缘于自身迁移经验的深切,赖声川对移民心态的刻画尤为着力。每一次迁移都将遭遇情感的困境,该剧展示出克服这种困境的复杂心路历程,既可见到现在与过去的深层联系——“回归”的渴望,文化承传的自觉,又可见到在现实境遇中生存下来的多种心态——痛苦地,无奈地,务实地,达观地……这就可以理解,这出戏为什么可以超越眷村,跨越海峡,因为它原就是人类共通际遇、情感的显现。
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亲身的感受,又因频繁移居而不断改变人际交往圈子,赖声川对眷村居民所面对的族群融合、文化冲突命题有自己特有的理解。与既有的眷村言说相比,该剧在表现眷村的自成一体之外,还展示出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的实际存在:本地人陈秀娥嫁入眷村,向钱老奶奶学到了天津包子的手艺;老赵自觉走出眷村,与本地木匠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剧中眷村二代对于命运、婚姻的选择更显见地超脱于族群的概念:大毛嫁给了美国人,二毛嫁给本地民进党人,大车娶了越南媳妇,眷村二代的族群谱系已然同构于台湾社会。剧中眷村人与台湾本地人的文化差异主要通过语言来显现,但语言交流的困难又常在喜剧化的情境中消融。二代与一代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成为另一个表现重点,二毛讥讽父辈:“这围墙里都是假的,外面才是真的!”“这些墙壁上的字,反攻大陆!写得越大就是越大的谎言!就是做不到才写那么大!”吊诡的是,反攻复国梦未灭,眷村父母却反对内部的通婚,理由是,没出息。这也从客观上促成眷村二代离开眷村,融入台湾社会。对旧的守护维持与对新的向往接纳呈现奇妙的拉锯、悖反与交融,这也可视为赖声川以多元身份对眷村特质作出的独特观察。
出身眷村的作者在呈述眷村时,可能胶着于自身的感知视域,在深具眷村味的同时,也多少显现“当局者”视野与经验的局囿。赖声川的非眷村身份使他更可能关注眷村中存在的相通于人类一般处境的人和事。该剧中,周宁这样一个“同性恋者”身份的设置,即非眷村素材所“必需”。事实上,演员在创造这个角色的开始,并不清楚他的同性恋身份,一直排练到中途才知道,因此周宁一开始并不使观众觉察到他在性取向上的异常。不管导演是故意按下不表,还是真的临时起意,总之,它使人物的表现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他首先是人,而非特殊的一类人,当观众在人的层面接受他时,也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的同性恋者身份。该剧还有一个特别的人物——“纪怪”。眷村一代所背负的乡愁在他那里是双倍的,既失落了文化意义上的故乡,又失落了母语意义上的故乡,因为谁也听不懂他说的话,其早日还乡的愿望一定比他人更加迫切,却隐藏在一大串无法被聆听的古怪语音背后。这种悲剧况味比起“眷村言说”中常见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显得更为深沉,而其悲剧的意义也超出了眷村。
在眷村出身的作者眼中,眷村总是特别的。在朱天心看来,眷村二代有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23)的任性使气,经过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电影塑造,眷村二代拉帮结派、好勇斗狠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当然也不尽如此,朱天心不无深情地写道:“一名溷迹其中、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去跑船的沈家老大,二十年后,你不难在报上的访问他中,清楚嗅出他的眷村味儿,当大约举国都不相信他要把那块唐荣旧址变更为商业用地并非只为了赚取暴利,而是想盖一幢他做海员时在其它美丽的国家看到的美丽建筑时,大概只有你相信他所说的是真话,并惊叹且同情这名身价百亿的成功证券商,为何还可怜兮兮如你们十数年前、对国家如此抽象却又无法自拔的款款深情。”(24)但在《宝岛一村》,眷村二代的个性似乎没那么突出,或者说与以上形象构成反差。小毛向朋友们描述具有绝世武功的鹿奶奶如何传艺于他,然而这不过是幻想,到了真实世界,他带着大车、周胖去台中“蓝天使”酒吧找姐姐,发誓要砸店、放火、救姐姐回家,临到头却什么都没做,落荒而逃。该剧中眷村少年的造反仅止于偷偷地抽支烟,造假传单来领奖,唯一一次动真格的是小毛带着大车、大牛一路追打偷看了二毛洗澡的周胖,周胖逃脱后带村外一班人反扑。然而这只是一晃而过的场景,后事未提,可知这场架打得并不大。在这个村子里,最不驯的要算二毛。她穿超短裙,唱流行歌曲,和村外人交往,讥讽自己的父辈,最后和一位民进党官员结了婚,这也只算一般的人生轨迹,并非传奇。现实中的眷村有许多传奇,最令他们自豪的是,眷村二代中出了许多台湾各界的中流砥柱,剧中的大车却不属于此列。他虽然参加了电视台“三朵花”节目,有“出名”的机会,却没能抓住,最终留在村里继承了母亲的包子事业,这显然是对一飞冲天的眷村传奇的反写。
在最后的告别联欢会上,远在异国他乡的眷村二代纷纷回来向家园作最后一次道别,其中却不见周胖的身影。周胖是眷村二代中内心积压着许多负面情绪的一类人,抱怨父亲周宁对他不够好,质问母亲冷如云与黄将军的关系,埋怨她很少陪自己,追问自己是不是周宁的亲生儿子,这些都展示着心理压抑之“因”。他平时性格懦弱、顺从,唯其如此,环境中感受到的压抑才转化成出人头地的奋进,而偷看女生洗澡,带着外村人向追打他的小毛、大车、大牛反扑,出国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些都可视为心理压抑之“果”。周胖的成长轨迹让人想起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杨德昌在电影中用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解析小四向着小明的那一刀是怎么刺出的,这个小四,原先也是课业优秀的学生,这一刀结束了他象周胖那样的人生可能,而周胖则完成了小四未走完的那条路,学成留美。但他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疗治,再也不回眷村来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剧中的周胖并没有走上小四的路,但非极端化的境遇呈现出的却是更为普遍却又难以为人察觉的精神问题。《宝岛一村》对眷村二代的表现走的是反传奇,反高潮的路线,与导演的非眷村身份不无相关。这种身份使他在眷村素材中看到的人生常态更多于异态,对眷村的表现也相通于一般意义上对人的存在的表现,这或许就是王伟忠所言:“也看到有些赖老师自己的看法。”(25)然而这并不使作品失去眷村味,有了王伟忠的故事作为基础,再加上许多眷村出身的演员的真切演绎,《宝岛一村》对眷村的呈现并不走味。
探究身份对创作的影响,不能忽视赖声川长期以来的佛法修持经历。不难发现,其戏剧对社会人心的观察及艺术形式的创造大都渗透着佛法特有的智慧与方法。《暗恋桃花源》的自心与外境,《西游记》的名相与实相,《回头是彼岸》的无常与幻梦,《十三角关系》的我执与烦恼,《乱民全讲》的五阴炽盛以及他长期运用的集体即兴创作方式、拼贴式结构,无中生有的剧场创造,都显现出佛法的无常、空观、有漏皆苦、互即互入、安住于当下等思想的影响。1990年代后期,赖声川敏感地意识到,政治讽刺的边界已被电视、报纸等媒体扩张到极致,戏剧中的政治议题在社会引发的反响已难续辉煌,剧场该何去何从?2000年创作的《如梦之梦》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政治议题在其戏剧中淡去,精神如何得以解脱的心灵命题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梦之梦》、《如影随行》(2007)、《快乐不用学》(2010)(该剧香港版为《水中之书》,2009)等剧直接借用转世、业报、中阴、自他交换等来自佛教的宇宙观及修行方法来表现精神解脱命题,《宝岛一村》看起来没有如此鲜明的佛教色彩,但对眷村人事的表现依然贯通着佛教的精神理念。
相异于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之沉痛哀婉,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冷烈峻肃,苏伟贞《离开同方》之阴沉诡异,《宝岛一村》显得明朗而温暖。明朗源于对小人物“草根韧性”的突显,随顺命运,不将自己往绝处逼,这让生命有了喘息的空间,也使人心有了回旋的余地。冷如云活不下了,向嘉义铁轨倾出上半身,最终又收回到天后宫烧了一趟香后返回自己家;大毛的恋情受阻恋人离去自己赌气当了吧女,多年后与恋人重逢,话居然说得心平气和:“那艘船早就开走了……我们没搭上。没搭上就是没搭上。不然怎么办?”周宁多年之后回乡,在同性恋人的墓前喃喃自语:“在你出事那天,我也已经跟你一起死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活到今天?也是因为你说过的一句话:人生要开心,尽量开心……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开心。”这既可看成剧中人的精神特质,亦可视为赖声川个人的理念渗透,它与佛教所倡导的不追不迎,安住于当下,接受各种可能的思想显然是一致的。能够将就要脱轨的生命挽住,使已经临头的大祸化解,还因由于“人间情义”。要是没有周宁施以援手,冷如云当年怕就无法挺住丈夫被传“投匪”的那一关,而多年之后,她亦去向黄将军说情,将被诬成匪谍的老赵救回。相互施以援手的“人间情义”反映出受与施的正向因果循环,它温暖的不仅是宝岛一村,还有人情冷落的当代社会。赖声川曾说:“我在每次开始创作时,在工作的每一秒中都必须审视自己的动机,我在为观众包礼物还是向他们丢垃圾?检查动机虽然不能保证我的作品质量优良,至少能保证不会成为公害。”(26)创作上的“菩提心”既可反映在赋予眷村这样悲苦底色的素材以温暖的调子,让人相信人间真情的存在,亦可反映于对族群融合、文化互渗的可能性之表现上,这一切,皆缘于他认为“戏剧可以改变人心和社会”(27)。
佛教倡导不追不迎、安住于当下的生命态度,乡愁却是人类情感的共同基因。一如背井离乡的父辈难以止息对故土的思念,少小迫不及待要离开眷村的二代们老大时“最怀念的还是生长在眷村的日子”(28)。乡愁或可通过宗教理念的疏导得以纡解,但其存在并非没有正向的作用力。因为乡愁,眷村一代在他乡不断反刍故土的艺文习俗,从而使中华文化的精华与血脉得以延续;如今也因为乡愁,失掉了眷村故土的王伟忠坚持向赖声川说了两年的故事,终于促成《宝岛一村》的问世。当我们走进剧场,看到舞台上许多由眷村走出的演员以对眷村的记忆、对父辈的情感演绎出一幕幕鲜活的眷村人事,就会发现:眷村并没有被历史的废墟所掩埋。乡愁对文化的延续效力又一次显现了。
①《光阴的故事》是王伟忠、王佩华制作的54集眷村题材电视连续剧,2008年9月开拍,2009年1月杀青。台湾中视无线台自2008年11月10日至2009年2月17日首播。
②(16)(25)朱安如:《王伟忠:宝岛一村,故事未完》,《PAR表演艺术》,192期,2008年12月。
③⑥据“表演工作坊”官网(www.pwshop.com)数据统计。
④由于《宝岛一村》的资金投入很大,制作人丁乃竺当初想在台湾企业寻求赞助,“冲着‘表演工作坊’这张牌,台湾的很多企业都很感兴趣。但是当他们听完《宝岛一村》的故事后,都善意地回绝了:台湾人忘不了这段历史,但是在台湾的文化中,生意人不喜欢参与到政治中来。”参见朱耘:《〈宝岛一村〉为什么这么红》,《中国经营报》2010年3月1日。
⑤有一个不是外省人,也不是眷村人的观众写信给剧组,说他在看《宝岛一村》之前,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外省人来到台湾之后,就把所有的资源都抢为己有,让台湾人很可怜,可是看完《宝岛一村》发现,原来有一群外省人也过得这么苦。原来之前听到的历史好像不是真的,要开始重新做一些了解。资料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2010年2月21日(周日)20:30播出的《名人面对面——赖声川》。
⑦王润:《〈宝岛一村〉:开场浓情散场温情》,《北京晚报》2010年2月1日。
⑧截至2006年,赖声川的原创剧场作品有:《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984)、《摘星》(1984)、《过客》(1984)、《那一夜,我们说相声》(1985)、《变奏巴哈》(1985)、《暗恋桃花源》(1986)、《田园生活》(1985)、《圆环物语》(1987)、《西游记》(1987)、《回头是彼岸》(1989)、《这一夜,谁来说相声》(1989)、《台湾怪谭》(1991)、《红色的天空》(1994)、《又一夜,他们说相声》(1997)、《先生,开个门》(1998)、《我和我和他和他》(1998)、《十三角关系》(1999)、《菩萨之三十七种修行之李尔王》(2000)、《如梦之梦》(2000)、《千禧夜,我们说相声》(2000)、《新加坡即兴》(2002)、《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2003)、《乱民全讲》(2003)、《这一夜,Women说相声》(2005)。根据《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陶庆梅、侯叔仪编著,时报文化2003年版)中的《附录一:赖声川历年演出资料1984-2002》及表演工作坊官网资料统计。
⑨⑩赵庆华:《乡愁与离散——“眷村文学”在台湾》,张嫱主编:《宝岛眷村》,第115、116、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根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的规定,全台八百八十六座眷村预计将在2009年底前拆除完毕,代之以新式集合国宅或另有他用(如转作公园、标售土地等),届时眷村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地景将永远消失。”参见李广均《荣光眷影》,张嫱主编:《宝岛眷村》第26页。
(12)赖声川、王伟忠:《宝岛一村》,第52页,“国立”中正文化中心2011年版。(后文出自该剧本的台词与舞台说明不再另注。)
(13)参见张茂桂:《想象眷村》,张嫱主编:《宝岛眷村》,第41页。
(14)(15)(22)(23)(24)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苏伟贞主编:《台湾眷村小说选》,第44、56、39、57、58页,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
(17)《演员祝福》,赖声川、王伟忠:《宝岛一村》,第297页。
(18)苏伟贞:《眷村的尽头》,苏伟贞主编:《台湾眷村小说选》,第12页。
(19)王蓉蓉:《感情菜谱》,张嫱主编:《宝岛眷村》,第102页。
(20)李俊贤:《眷村走透透》,张嫱主编:《宝岛眷村》,第53页。
(21)廖俊逞、朱安如:《赖声川:让故事说自己的故事》,《PAR表演艺术》,192期,2008年12月。
(26)赖声川:《赖声川的创意学》,第151页,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27)郭佳:《赖声川:戏剧可以改变人心和社会》,《北京青年报》2013年2月7日。
(28)林青霞:《宝岛一村》,《苹果日报》2008年12月25日。
标签:赖声川论文; 宝岛一村论文; 台湾论文; 暗恋桃花源论文; 王伟忠论文; 如梦之梦论文; 剧场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