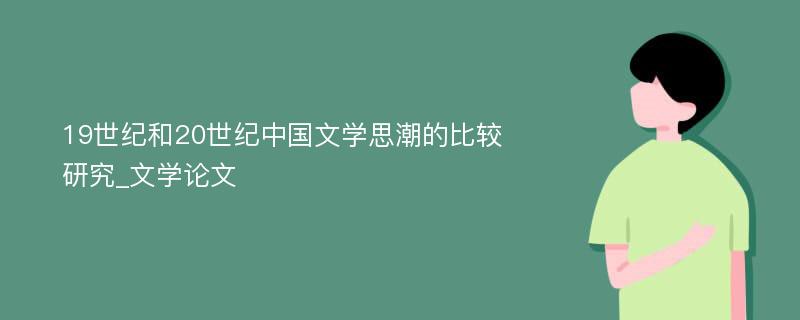
19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比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7278(2000)02—0070—(09)
中国文坛在20世纪可谓思潮迭起,热闹非凡,而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则是潮歇汐落,一派沉寂。不过这仅限于表面的热烈程度而言,其实19世纪的中国文坛不仅曾涌动过各类思潮,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开了20世纪文学思潮的先河,只是19世纪文学思潮更多地藏伏在平心静气的理论探讨和温柔敦厚的创作实践之中,多属于潜在的、隐性的思潮,同20世纪那种以声嘶力竭式的倡导和剑拔弩张式的论争为主体的显性的甚至是泛化的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19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与20世纪文学思潮的显泛性
从时代运行的基本状貌而言,中国的19世纪同20世纪一样充满内忧外患,频受外来的或内部发生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面临着政治转向、社会转轨的种种契机。有道是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按说这种板荡不定危机四伏的社会状态应该孕成花样繁多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正像人们在20世纪所强烈地感受到的那样。然而19世纪文学思潮从密度上远比20世纪稀疏,比较明显的似乎只有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萌芽状态的个性主义和变革、开放思潮,以宋诗派和同光体为代表的在拟古旗帜下作古典现实主义酝酿的宋诗运动,还有围绕着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兴起的成果了了的民族主义文学,伴随着近代启蒙主义而起的势单力薄的民俗主义文学倡导等等,除了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大张旗鼓地倡导并力行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等“跨世纪”运作而外,所有上述可被称为思潮的运作也仍是潜隐性的,潜隐到连学术研究界都加以忽略,因而有关这一时段文学思潮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时代性的差异。
20世纪的所有思想文化思潮或萦绕着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或者以此为基础,这场对传统文化形成结构性破坏的运动众所周知发生于五四,其端绪则直接上溯到19世纪末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然而不管怎样,它构成了这个世纪最有价值的时代内容。这一时代内容深刻地决定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运作的内涵、方式与特征。从人的文学,个性主义文学,到普罗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甚至连各种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在内,都搏动着强烈的批判和反叛的神经,透溢出清算传统和超越经典的勇气与魄力,并试图对文学的进化乃至社会的进步有所倡导与引领,这样的文学思潮每每以“运动”形态出现,无论其实在性如何,都彰显在历史的景幕,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这其中还不包括相当一些没有什么新鲜的特别的内容却被煞有介事地加以描画加以张扬的东西,例如田汉热情洋溢进行阐述的“新浪漫主义”,郑伯奇连篇累牍展开论证的“国民文学”等等,它们原本只是一种观点或径是对外来思潮进行译介的一些心得,远够不上一股思潮,却因其照例带有上述“运动”特性在实际的倡扬中被夸大为思潮类的东西。诸多如此这般的准思潮装点得20世纪更其思潮泛滥,思潮的所指也随即宽泛化了。总之,在以反思传统和超越传统为基本观念环境和时代思想基础的20世纪,传统在理论层次以及经验层次上都面临着被怀疑被解构的命运,而这种怀疑与解构同时又必须面对传统势力有形的或无形的压迫和挑战,故此必须以过于郑重其事的思潮形态显现出来,从而导致了这个时代思潮的普遍化、显泛化。同样在20世纪,即使有些时候有些舆论对之有所维护甚至有所坚守,也只能以显泛的思潮方式出之。所以,20世纪文学思潮的显泛性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这一时代背景大有关系。同样的意义上说,19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也导源于那个世纪缺少相当激烈的传统否定性文化运动作为中流砥柱,而且,构成这一时代文学主要思潮的思想观念及其主体文人不仅绝少发出反传统之倡,相反还都愿意祭起传统的旗帜,以作为张目。宋诗派以及后来的同光体、桐城派等拟古主义乃至于泥古主义文人自不必说,便是当时变革意识最强烈的龚自珍,其用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也还是春秋公羊学,[1](P138)对社会的批判也被他自己定位在“良史之忧”的意义上,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P6), 发表改革訾议时也常标榜古例,谓“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2](P6), 可见他基本上是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出发忧思天下抨击时事的,由此还能很自然地联想到他那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中“重”字的所指所示。在文学上,龚自珍虽有挣脱宋诗藩篱之举,时常流露出自我表现的热忱、兴趣与意志,但总体来说他更愿意将自己活跃的思想和炽热的情感通过正统乃至古雅的文学管道输送出来,或者喷发出来。他给自己取定的雅号用字是那么冷僻繁难似亦可佐证。当19世纪的文学家在尊崇传统的旗帜抑或是意识之下作倡新之语时,传统在被反复言说的状态中强化了自身的规范力,这种规范力至少会从外在的表述方式上将那些稍含锐意的新观念磨蚀殆尽,其内在的锐意亦须在传统化皈依的前提下得以有限地呈露,于是其作为思潮的潜隐性实属不可避免。
从文学思潮的潜隐性与显泛性的对比中,我们甚至能够反溯这两个世纪对待传统的态度竟是那么截然不同。19世纪对传统的普遍尊崇已经深刻地作用到龚自珍这类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他们发出的呼唤变革的声音本来最需要反传统的反冲力作用,但谁也没有想到将传统当作营制自己言论炮弹以助观念升腾的燃料,传统哪怕是在虚拟化的层面上也从没有失去定于一尊的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反传统意识几乎占据了20世纪主流话语的全部空间,即使是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紧急关头——通常在这样的关头人们更容易对民族赖以生息发展的传统产生温情脉脉的依恋情怀或宽容心性,民间化、民族化的呼声依旧没有能淹滞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代热情,无论那几方面的观点孰对孰错,但抗战初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关于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论争,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凸现了20世纪的这种时代热情。在一个普遍地寻求传统遮蔽的时代,各种各类思潮即使不偃旗息鼓也绝不至于剑拔弩张,这便是19世纪文学思潮呈现潜隐性风貌的根本原由;同样,在一个普遍地张扬反传统精神的时代,各种观念必然争相以夸大的形态出之,导致20世纪文学思潮呈显泛化态势。
导致20世纪文学思潮呈显泛化态势发展和蔓延的反传统意识,其勃然兴起以至如此普遍深入的原因殊为复杂,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固然十分关键,但来自传统内部崩坏灭裂的声音和信息不啻是给20世纪主流思想文化界注射了一副富有威力的兴奋剂。问题是20世纪的人们如何能够清晰地倾听到这样的声音并较为准确地把握到这类信息?显然,这与外国文化思潮的大量涌进及其集束性影响和恒久性比照有关。自19世纪末开始,早已被动地打开国门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普遍良心上已经意识到以前那种从“器”和“道”的层面倡导西学并进而“师夷”的观念对于医治“老大帝国”的痼疾难奏奇效,遂以严复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广泛译介以及林纾对西方文学的大规模输入为典型代表,一波接一波的引进、释绎及参照西方文化科学和文学的浪涛汇成时代潮汛,引领着中国进入了思潮迭起的20世纪。在人们的印象中,“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从没有做过有板有眼的“交接工作”,作为这种粗疏的交接的直接后果,20世纪最初的十多年在文学和文化上几乎乏善可陈,更谈不上什么思潮的涌动了。其实,西方的价值观念伴随着《天演论》等文化典籍进入中国,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文人群体中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反响和震撼力量,有关民权、自由、民主、科学等西学概念如黄钟大吕猛烈地撞击着文人的耳鼓并有力地打动着他们的心灵,于是连像鲁迅这样有着深沉内涵和思维定力的读书人都在这一时段加入了读解、阐释、宣传西学的行列,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科学史教篇》等宏篇巨论中,人们很容易感受到那个思潮涌动时代的良心与脉息。那时有代表性的文化杂志都在内容上甚至在名称上体现这样的时代良心与脉息,譬如《浙江潮》之类。当然还得将酿成辛亥革命之时代巨潮的此起彼伏的革命思潮作为文化时潮的硕大背景核计在内,无论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及其雏形还是陈天华的“猛回头”敲响“警世钟”作“民主政体”之倡,抑或是章太炎、邹容鼓吹的民族革命论,都展现了在西方政治观念和体制影响、感召之下的革命思潮之厚重。在这一意义上尤其不能忽略的是像南社之类兼具政治性质和文学品味的文化社团,它们的运作常常能使上述背景下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展开得有声有色。
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思潮运作的起点,也是这种运作的原初环境,包含着西方政治、文化和文学观念等冲击性因素的这种原初环境始终起着瓦解传统、刺激现实、激活思潮的作用,作为这番瓦解、刺激与激活的结果,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思潮从一开始便显现出显泛化的趋向。像是对外国政治、文化、文学思潮潮水般地涌进国内的生动情形的描摹与反馈,及至五四时代,“思潮”一词便在时代性表述中显泛到极点,除了诸如“时潮”、“时代潮”、“新潮”、“潮势”、“潮流”等名词术语泛滥不已而外,“新旧思潮之激战”之类的警策性、刺激性语汇亦耳熟能详。所有能够引起某种关注或者希望能引起某种关注的思想观念都有可能被理解为或竟至于被夸大为一股思潮。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被动地向西方打开国门,但真正称得上走向开放、吸纳外国思潮并自觉地以之作文化参照的时代远未在鸦片战争爆发之日到来。除了这个世纪末年由黄遵宪、梁启超等推波助澜的革新运动外,几乎整个19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话语都程度不同地疏隔于世界文化和文学思潮,当然更缺少世界性思潮、观念的参照,从而与20世纪经常面临着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冲击、挤逼及被动或主动选择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这种对照的另一番结果便是以19世纪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潜隐性比照20世纪同类思潮的显泛性。
人们已经注意到龚自珍、魏源等人锐利的改革呼唤对于19世纪末的文界革命乃至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动和招引作用,诚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中所总结的那样:“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曾朴在《译龚自珍〈病梅馆记〉题解》中则直称龚氏为“新文学的先驱者”。但由于缺少外国先进思潮的刺激与引领,他们的呼唤每常萧条于古圣先贤的“经典”之中,难以形成规模巨大、气势不凡或先声夺人的思潮气息。龚自珍的时论,哪怕是在推出最新锐学说之际,亦每以古风前制圣经贤传起笔,如倡言改革却以“夏之既夷”、“商之既夷”为绪引[2](P5), 议论田政农宗则以“古者未有……”“儒者曰……”为话题[2](P49),他如“闻之古史氏矣……”[2](P87)“中国自禹、箕子以来……”[2](P169)之类, 概以古训发凡,如此不一而足,即令思维开放,立论新颖,亦绝少融入海外讯息。既失外来思潮之冲涮,又蒙古史古训之遮掩,于是龚子之说,常常有思而少潮。自魏源始,所有著论,已颇多外来讯息,但这些讯息并没有作为思想者激活、振奋自己思想的激素,也似乎没能成为这些中国思想者思想和言论的重要参照,而较多地成了防范乃至克服的对象。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尽纳海国四方之讯息,但此书本“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P207 )所议皆在“患夷之强”,克服敌夷,故来自洋夷之邦的观点,哪怕是崇论宏议,也难以进入中国思想者的精神领地,当然更谈不上兴风作浪,掀起思想的潮讯。以夷为敌,作制夷议,虽是典型的时论,却并没有新思潮的峭拔警策之风,原因是这样的观点已深深地潜隐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之中,而这类情绪在相当的程度上已被传统的文化因素所漫漶。即使到了明确倡导西学的19世纪后期,西方思潮似乎在许多精英知识者那里获取了进入老大帝国的合法资格,但它们还是不能堂而皇之地作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运作,因为许多精英文人还是倾向于在“为用”的意义上对待西学,他们从感情上和操作方式上都防止和杜绝西学的冲击进入中国文化本体的神圣领地。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当时应是相当旗帜鲜明同时也是相当招摇的议论,但他一开篇还是“《传》称……”,还是“孔安国曰……”,从而在“伊古儒者”之语的荫拂之下消钝了言论的锐气;王韬的《变法上》更是直言不讳切中时弊之论,可也津津乐道于“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的变法经,从而在“道必大同”的传统命义上淡化了思想的时代光泽;薛福成提出《振百工说》,旨在介绍“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但其立论之基却在历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禹、周公以至张衡、诸葛亮等如何“神明于工政”,从而在“圣人之制,四民并重”的强调中将自己的见解依托到了“古者圣人”的旗下。如此这般的理论操作,大大缓解了外来思潮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并自处于传统文明的厚重包装之中,因而销蚀了新思想本来可能具有的极富锐意的潮势,终至于在整体上造成了这一时代政治、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潜隐状态。
显然,19世纪传到中国的外来讯息已经拥有一定量的积累,但其中包含的理论成分还相当稀薄,即使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也没有为梁启超之前的文人学士所警觉和注意,这也是造成这个世纪文化和文学思潮潜隐不彰的重要原因。从19世纪末开始传入的西方思想、理论和观念,给中国20世纪的文学家带来了丰富的理论素养并锻炼了他们相应的表述技能,这就强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家酝酿思潮、操作思潮的兴趣与能力。不可否认,思潮的运作必须以理论的阐述为基本载体,理论兴趣的普遍缺乏和理论能力的相对萎缩势必导致文学思潮的潜隐不彰。这便是外来思潮冲击较缓、比照不力的条件下中国文坛的实际情形。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的论断表明当时人们对此情形应能有清晰的认知。王氏指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转于分类……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19世纪的“我国人”确实如此,而到了20世纪,在西方思潮和理论方法的刺激、诱导和引发下,情形已经发生改变。
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上述文士多为阁僚官宦,他们的新议常常出于其职分的考虑,囿于其身份的约束,依托古圣方可期安然自保,纵缘洋说难免不罹难惹祸,于是新见既出便设法涂抹其棱角,每有突破则惶惶然寻求规范,所思所议难以作思潮运作,即便汇成某种思潮也必呈潜隐状态。在政治领域是这样,在文学领域亦复如此。阁僚官宦之辈治文学,即使不将它当作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亦难免不从传统的诗教观念出发,担负起士大夫阶层的应分之职,于是阐幽发微原本就慎之又慎,斟酌再三,倡言出新则更加会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因而文学观念虽常有翻新,文学思潮则趋于潜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的文人(尤其是进入我们话题的代表着这个世纪文学主体的文人)一般都与官场无缘——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或许会想起曾在教育部里做过佥事的周树人,显然,这一区区文职无论如何不能与19世纪文士的官职相提并论,而周氏又恰曾敢于在任上跟上司总长章士钊过不去乃至打官司,其实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从来就没有认同过自己一度厕身其间的官场。不用说像鲁迅这样的精英文人,更不用说大量的平民主义者和革命文学家,便是对“政府”保持某种兴趣的胡适之流也常是如此:他们更多地站立在并坚守着民间化的立场,在许多情形下对于官方往往取一种相悖逆、相抗衡或者不合作的态度,于是他们的所思及所议不仅无需多虑传统教化与规范秩序,而且要抗议、挑战这类东西,他们的申言与倡导不仅不必因顾及自己的身份操守而钝其棱角,掩藏锋芒,而且须为突出自己的角色崭露棱角,毕现锋芒,甚至有些文人故作反叛之态,漫出惊人之语,从而将哪怕是相当有限的新思想新观念都夸大为一种新思潮甚至是新的时潮,由此可见,20世纪文学思潮的显泛性尤其是在前半期乃属于一种必然。
二、19世纪古典现实主义主潮与20世纪宽泛的现实主义
19世纪与20世纪的文学思潮在其展示形态上固然显现出潜隐化与显泛化的巨大差异,但是在主导倾向上又无不紧密而切近地回应着现实的吁求,反映着现实的脉搏,显现着类现实主义的总体时代风貌。20世纪文学始终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从早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倡导到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流行,从左翼文艺中普罗现实主义的张扬到延安时期甚至新中国阶段革命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运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复归到90年代初的“新写实”以及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宽泛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汇合成整个世纪蔚为大观的文学主潮。19世纪的文学思潮虽较多地取其潜隐的姿态,却也始终贴近着纷乱而严酷的现实,时隐时现或彰或显地推涌着关怀现实、批判现实、作用于现实文坛、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思想潮流,无论是桐城派的余绪还是宋诗派的主干,无论是龚自珍、魏源这类先觉者还是黄遵宪、梁启超这类启蒙者,都无不在这种痛心疾首的现实关怀中展示其思想魅力,凸显其时代价值,从而汇聚成这一世纪类现实主义的思潮主线。展示在中国文人面前的这两个世纪都充满着包括变革欲望、拯救需要和发展吁求在内的现实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注定不能剥离于这样的力量,也无法拒绝这种力量的吸引,便纷纷以自己全部或部分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性投入其中,其结果又特别加强了这种现实的力度。由此可以说,在急切地需要现实主义的19、20世纪,中国文坛上正姿态各异地勃兴着富有时代特征的现实主义主潮。
或许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的现实主义概括19世纪尚处于传统文学模态下的观念思潮多少有些冒失,但现实主义除了作西方文学史的阶段性标识而外,确乎可以当作一种艺术方法和艺术处理的原则来理解,这种方法和原则在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中自有着无可否认的普遍性,于是王国维在著名的《人间词话》中就将诗学的“写境”一翼名之以“写实派”,这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最正宗也是最完整的运用。应该承认19世纪文学思潮在总体上确曾强调摹写、表现现实,主张文学的服务功能和诗教作用,比较多地鼓励文学者的理性批判精神,这些内容都与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内涵相通,而且也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呼应。只不过进入我们视野的19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与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学参照背景,以西方的价值、方法和理念为基本依据、策略和准则的20世纪现实主义还是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的参照面在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传统,它常常以古典的价值作为关注现实的观念依据,以古典的方式作为服务现实的艺术策略,以古典的理念作为批判现实的基本准则,因而可以说是一种古典化的现实主义,或径称为古典现实主义。1952年,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写出《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曾使用过“古典现实主义”的概念,不过他强调的是“中国宋代以后‘平民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是这一因素中包含的“近代的性质和色彩,即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性质和色彩”,与我们的论述中强调参照面,强调古典化的依据、策略和准则的侧重点并不一样。
20世纪现实主义的宽泛化在现实性的强调方面有着具足的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简言之就是在近代启蒙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现实化的结果。《青年杂志》最先提醒青年们注意的便是处在“世界关系”中的“今后时会”,[4]一如孙中山彻悟到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这样的观念基点上,新文学倡导者大力提倡“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反对文学的“瞒和骗”,将对现实的反映和表现视为时代文学的真谛。无论是新青年先驱者还是新潮社后进,都将现实的关注当作阐发议论和从事创作的先决条件,自文学研究会重申新潮社时代“为人生”的价值观以后,哪怕是有意与之闹龃龉的创造社文人也不得不将“人生”当作法宝来祭——郁达夫反诘道:“古来哪种文学不是为人生的?”于是连向被认为代表着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文学其实也在表现现实人生方面显示着写实文学的质地感。自此以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在主流话语层面就几乎被固定为密不可分,任何在观念上对这种关系提出挑战、修正乃至怀疑的企图都会遭到密集的诘难甚至群体的围攻,当然,这样的诘难和围攻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是相当合理的,事实是,从20年代初期的“为艺术而艺术”观念,30年代初期的“艺术非至下”观念,40年代初期的“与抗战无关”论到80—90年代的“绿洲说”和“向内转”论等,这些试图让文学同现实(甚至只是时事)有所脱节的主张无不都是迎头遭遇这样的命运。一个容不得任何有关文学疏离现实的观念抬头的时代当然是宽泛的现实主义的时代,20世纪正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仍在继续着类似的操作,无序地推涌着“现实”情结的人们还煞费苦心地引入了“当下”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将“现实”的强调变得复杂化了。无论怎样评价这种复杂化,它将“现实”的关注引入现代化话题的矢向是非常清楚的。
19世纪古典现实主义主潮也突出地展示了现实主义注重现实、强调现实的通性,不过它倡导着从古典价值观出发认知现实、反映现实。龚自珍作为19世纪启蒙文化的先驱者所显露出来的思想成果和精神素质是多方面的,而关心时事,关注现实,“通经致用”,拯救时弊则是其文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文学活动的归趣点。张维屏曾明确地将近代以来士子文人对时事的关注归结为龚氏的导引:“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1](P6 )“诵史鉴”、“考掌故”既是“论天下事”的方式方法,也是“论天下事”的价值依据。“通经致用”是魏源对龚自珍文学的一种概括与评价,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文学价值观的间接表述。他的言论自免不了那个时代的“托古”之风,却能清醒地认识到古训不足以完全医治现实的痼疾,犹如“昨日之历,今岁而不可用”,然而他的思维焦点乃在现实,所谓“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3](P156 )王韬曾高度评价屈原的“忧世”情怀,并明确认为文章应是“载道之器”,须“思古伤今”,“悲天悯人”。黄遵宪对文学者提出了“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的要求,其现实的强调则伴之以泥古的否定,较之于前人显然更为大胆:“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1](PP172—173 )都说许多文人倡导古典现实主义往往以对桐城派的批判和否定为前提,殊不知桐城派中以类似的热忱关注现实者自有其人。隶属于这一派的梅曾亮就曾清醒地指出过“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作为桐城派的中兴柱石,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重新解释该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所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义,并赘加“经济”一科,而此“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其实就是经世济时的学问,反映到文学上,则无异于写实精神之倡。人称张之洞诚如己言“能将宋意入唐格”(《四声哀蕲水范昌棣》),其中“宋意”一词,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是“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的现实状况。19世纪是一个内忧外患日见其烈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国文士很容易将现实的关注理解为一种文人的操守和文章的基准,从而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中透溢出写实之趣;只不过他们关注现实的参照系是古人古事与古代经典,因而其写实之趣显露出来的便是古典现实主义的脉息。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要害是文学的“有用性”得到反复的确认与不断的强调。承继着19世纪末启蒙主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思想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文学在思想启蒙、唤起民众以及改造国民性等世纪性课题中的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即使是在最清醒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鲁迅那里也能以夸张的样态显现出来,鲁迅果断决绝的弃医从文这一历史性选择即可算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后来在《呐喊》自序中描述自己“听将令”的心态似乎对文学的作用又起了某种疑惑。文学研究会将文学定位成“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可以说是20世纪现实主义主潮中有关文学作用问题较为鲜明也最为稳健的观点,较之新文化先驱者对文学作用的夸大乃至迷信的情形,尤其是较之后来变态地理解文学的作用,甚至以为文学可以反党可以搞阴谋的种种庸俗观念来,则显得特别清醒而妥当。曾以异端者自任的创造社一度否认文学的有用性,甚至跟着唯美主义者叫喊“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5] 声言“毒草的彩色也有美的价值存在”,[6] 然而他们毕竟无法超越于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于是不得不迅速放弃高蹈的文学无用论,转而强调文学的“大用”,说是“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7] (P108)创造社的理论缴械在20世纪文坛上极富有象征意义,整个这一时代只要出现“艺术至上”之类的倡导者,现实都会逼迫他们仍然拿起艺术的武器挡住各方面的声讨,无论最后是否成功,总能让他们在一定的尴尬中领略文学的妙用。于是,文学的有用性和实用性仍旧汇成了这个世纪的观念主脉,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一大组成部分。
19世纪文坛在总体上亦倾向于文学有用性的确认,虽然无论是桐城派还是宋诗派,都是从“载道”、“义理”等特定的古典角度确认了文学的功用,但毕竟这种众口一词的确认形成了这个时代文学功利观念的主脉,更不用说有些相关的理论倡导还是那么切合于20世纪新文学家的现实主义口吻。魏源曾像胡适等人那样反对过文学中的无病呻吟,在《诗古微》序文中严肃地提出:“诗以言志,百世同揆,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吟者耶?”在这样的话题上他免不了要依托“古圣”,说是“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然而强调的却是“来世”的关注。魏源还认定文学可以起到“变古”、“便民”的作用,认为诗文具有“合听”、“合观”的功能,这些都是在发扬古贤“兴、观、群、怨”说的基础上确认了文学的功能价值。龚自珍的“尊情”、“宥情”说也包含了相当密实的古典现实主义内涵,特别是他确立的诗文标准,乃是超逸出古人思考范围的现实言说:“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汹,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2](P166)这番诗性的表述极富浪漫的激情,然而蕴涵其中的却是关怀“天下”的现实主义内核,尤其是“泄天下之拗怒”句,确能给人以丰富的现实主义启迪。
当然,除了19世纪末的改良主义者以偏激的持论和政治功利性观念强调文学之于现实改造的作用而外,处于古典化文学语境下的19世纪文人一般不可能完全脱离经典的“诗教”与“载道”观来确认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因而他们也就不可能通过显泛化的语言夸大文学的功能。兴起于19世纪末的一系列文学“革命”,则已在改良主义思潮的重重包围中坐实了文学硕大无朋的功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甚至认定文学可成为“智天下之具”(裘廷梁语),在“支配人道”方面具有“不可思议之力”(梁启超),这种夸张了的文学功能观对20世纪新文学的发动和新文学家的素质修养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在改良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脱离了古典的诗教传统,亦即脱离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轨道。
此外,现实主义天然地含有理性批判精神,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便是以“人生究竟”之类的理性思考求得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定型。19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包含着潜隐的理性精神,虽然这种理性精神更多地蕴籍着古典的成分,但它毕竟强化了古典现实主义主潮。在这样的话题上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世纪影响最大的宋诗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可以作多方面的理解,但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谓“本朝人尚理”,钱钟书的《谈艺录》称“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似应是理解宋诗精神和宋诗运动精髓的可靠门径。
收稿日期:199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