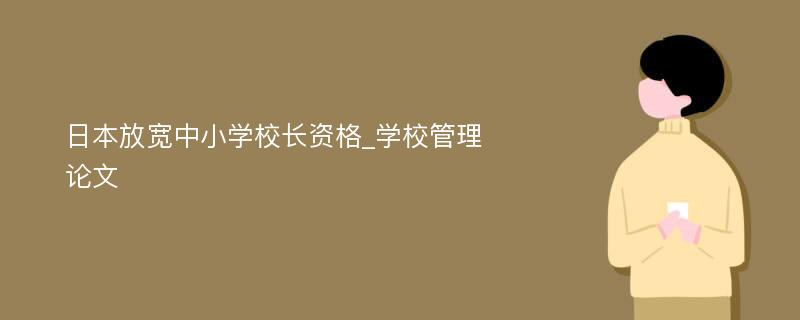
日本正在放宽中小学校长资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论文,日本论文,校长论文,资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国民教育中“不登校”(拒绝上学)、“异己灭”(欺侮同学)、校内暴力之三大病理现象的凸显,日本国民教育质量问题越来越多地遭到怀疑和批评,其中,以往常被称作“现代日本成功最根本原因”的教育制度之弊端最受指摘。为此,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教育改革来打破固定化教育模式。
传统上,日本中小学校长资格制度正是规制、保护、封闭、划一、僵硬的典型,校长普遍由教育行家担任,有的甚至由大学教授兼任。对于选拔校长的资格,有的地方教委,如日本高知县教委有更加严格的规定:校长要具有两年以上的教头(协助校长工作,通常主管教学)或相当于教头的职务经验。可见,原来的校长资格制度实质上强调的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提拔或调动,确立的是系统内部的“年功序列”,保障的是系统内部人员的职业生涯,而缺乏与外部人力资源间的互动。
对于拥有校长任命权的日本文部科学省来说,已逐步开始认识到优秀校长须具备以下能力:拥有一定教育方面的见闻与认知,对教育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能够确实把握所在地区以及学校的现状和课题,具备统领学校的领导能力,能够激发教职员工的工作潜能,与相关机构进行合作、协调的能力。而以往对于校长资格条件的要求绝非促成优秀校长能力的唯一途径,甚至还不一定称得上最佳途径和关键。不过由于其规制、保护、封闭、划一、僵硬的本质,排斥、挤占和覆盖其他途径,剥夺了更多社会精英担任中小学校长的权利。
法案出台
遵循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998年9月21日所作的《关于今后地方教育行政方式》报告精神,《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修订案出台。在修订案中,作为教育制度改革重要的一环,“校长资格缓和”被历史性地提出。修订后的《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重点对校长资格条件作出修改,主要体现在:把“五年以上相关职务经历”改为“十年以上教育相关职务经历”(《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第8条第2项);增加新条款“拥有国立及公立学校校长任命权者以及私立学校设立者,出于学校管理运营的特殊需要,可以任命及录用具备与第8条所规定之同等资质者”(《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第9条第2项)。
考查“与第8条所规定之同等资质者”的语义,可发现新增条款实际上是为“不持有教师资格证,并且不具备教育相关职务经历者”的民间人士任职开了绿灯,可以说是极大地缓和了校长任职资格。而继续推敲“同等资者”之内涵,在日本又大略可以将其具体分为两类对象:一是行政机构的管理层;二是民间企业的部长级管理层。而从实际任用情况来看,后者占了绝大多数,似乎拥有国立及公立学校校长任命权者以及私立学校设立者都更青睐那些在商场中摸爬滚打过的、具备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技能的人士,希望他们能够将企业中的管理运营方法引入学校中,给缺乏生机的学校管理运营改革带来新的增长点、契机和动力。鉴于该制度尚处于实验性导入阶段,笔者将针对该制度实施近期收效和存在问题提出观点并资我国借鉴。
实施状况
事物的发展是量与质的统一。这里依据量(在职人数)和质(管理效果)两个维度对“校长资格缓和”的开展状况进行解读。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年度调查,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在职人数变化情况如下——
民间人士校长在职人数变化情况
民间人士 其他 合计
2002年度214 25
2003年度
56 8 64
2004年度
76 9 85
2005年度
9211103
2006年度
8913102
可见,以2002年为开端,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在职人数逐年递增;但倘若排除离职、退休等因素,则各年度新入职的民间人士校长人数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当前日本中小学计四万余所,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制度历经五年之导入与发展,在日本38个县市中合计不过百余人,其所占比例仍然相当低。可见,多数学校设置者对于引入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并不持积极态度,或者说当前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制度尚处于实验性的导入阶段。
在管理效果方面,日本文部科学省初等教育局曾在2003年公布《民间人士担任校长任用之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六个任用民间校长的教育委员会均表示录用结果达到并超过预期目标,具体成果如下——
一是有明确学校经营目标和构想;二是能积极向学生监护人和地区居民提供信息;三是发挥了激活教师组织的作用。这些成果开拓了学校经营方面的新课题和领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困扰校长群体的难题。
综上所述,“校长资格缓和”在质上的表现获得一定认同,但在量上仍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那么,既然“校长资格缓和”能够带来裨益,为何其发展相对缓慢呢?这就涉及以下问题。
发展课题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体能力是这样,组织目标也如此。反映在校长资格上,首要的问题在于校长来源“多样化”和“专门性”的论争。而这除了需要校长个体实践自觉外,必然需要强化教育委员会的援助机制,如有专家指出要为校长提供有力的援助,教育委员会职员应当定期走访学校,根据现实状况为校长配置多个职务能力出众的副校长和教务主任。如果这些民间人士校长能够得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相信可以收获更大的成果。
其次,民间人士担任校长的问题势必牵涉到“学校”与“企业”在根本目标上的差异,因此,如何保障中小学校的组织目标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众所周知,民间校长制度的导入无非是为了在学校运营中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然而,企业经营管理毕竟只是作为学校运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两者不应混为一谈。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如果将教育目标简单等同于生产效率或是经济效益,与基础教育之宗旨乃至民间人士担任校长制度之本意都是南辕北辙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严格地区分目标与手段是相当困难、不尽现实甚至缺乏指导意义的。
启示
我国的教育界和业界的交流互助方面相对薄弱,工商企业界的管理运营策略迁移到学校管理中的成功案例尚不多见。而校长是学校最主要的管理者,是“教师的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更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表率以及学校发展的设计师和引路人。如何通过重新探讨和明确校长资格问题,吸引各界管理精英献身教育事业,将现代管理经验和成果融入学校管理中,提升学校经营管理水平,以应对信息科技的推广运用,聘任制度的不断深化以及校内外联携加强等给现代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已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应当反思以往的校长资格规定在运用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是否过于规制、保护、封闭、划一、僵硬,又如何向自由、竞争、公开、多样、柔性的资格制度进行转化,应当探究怎样通过政策支持和促进校长来源“多样化”和专业人才“专门性”之平衡,应当通过怎样的考核评价机制来缓和与克服以育人为本的学校与视绩效为生命的企业管理在根本目标上的差异性,这些都是今后值得思考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