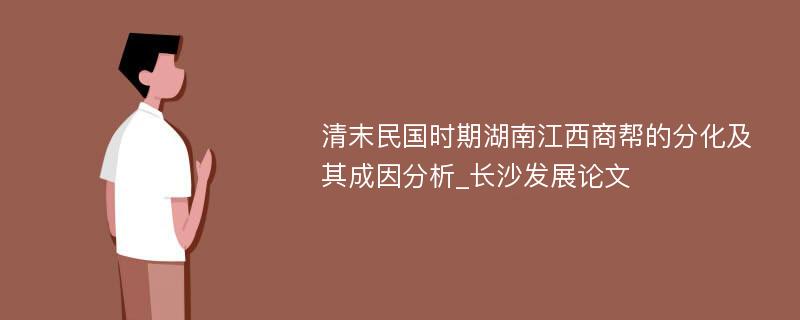
清末民国湘省江西商帮的分化及其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江西论文,清末论文,民国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5-0097-06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各区域市场联系的加强及大宗货物长途贩运的兴盛,使商业人口流动频繁。商人在利润的刺激下,千里跋涉,寄居异地,激烈的市场竞争、土著的排斥、文化上的隔膜,迫使同籍商人联络一气,走到一起,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不少地域商人抱成一团,“以众帮众”。这种组织特征在明清国内的地域商帮中,徽商与江右商的表现明显,徽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地也。近江右(商人)在外,亦多效之”。[1]货殖于湖南的江西商人在市场竞争与乡族联谊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商帮团体,湖南的地方文献上一般称之为西帮或江西帮,“夫所谓帮者,由同业联络而成,举其董事数人,立定条规,以执行其商务”。[2]91江西商人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使得江西商帮组织会馆——万寿宫遍布湘沅,“万寿宫之在湘川,几於各县皆有,西帮之名,震耀一时”。[3]盛极一时的江西商帮组织,晚清民国逐渐衰微,跨地域商人行业组织的勃兴及江西商人的融入,表明湖南的江西帮组织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分化演变过程。
一、同业组织的勃兴与江西帮的融入
在讨论江西帮分化演变融入同业组织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会馆组织与同业组织的简单区别。①首先,从其功能上看,会馆是外来同乡商人的组织和办公场所,代表地域商人的利益,同乡是加入这一商业团体的先决条件,乡土特征非常明显。同业组织则打破狭隘的地域概念,一般不分籍贯,不论土客,只要从事同一行业都可加入、甚至必须加入同一同业公所、公会,它代表的是整个行业的利益。其次,从其命名来看,会馆绝大多数以商人的籍贯为名,而同业公所、公会原则上以行业命名。再次,从其供奉的神祇来看,会馆一般主祀乡土神灵,配祀其他神灵,如观音等神祇;而同业公所、同业公会则多以行业神为主祀对象,如钱业俸财神,药业祀药王。总之,会馆与同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服务地域商帮组织为根本宗旨,而后者则以整合行业行为为最终目的。清末民国,同业商人组织兴起,作为地域性商人组织的江西帮,审时度势,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走出地域商帮局限,参与到同业组织中来,完成由血缘地缘团体向业缘组织的转变过程。
(一)长沙钱业江西帮与同业组织的创建
“银钱贸易,业冠百行”,钱业在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盖钱行一业,所为弁冕群商者,匪特造物盈虚之用愈演而愈繁,抑亦生人福禄之源可大可久也”,[2]233-237因而钱业的兴衰多被看作是一时商业凉热的风向标。湖南钱庄,“究始于何时,已远不可考,《湖南通志》所载咸丰六年湘抚骆秉章奏折,称‘湘省昔时营钱号者,多系江西人民,自粤匪窜湘,已相率歇业回籍’”。[4]由此可知,咸丰以前即有钱号,而且此业中以江西商人为主体。太平天国战乱平息后,湖南钱业迅速复苏,“颇称兴盛,其营业或发市票或铸铅丝银,获利者巨万”。在利润的驱使下,地域商人相互牵引,商帮组织迅速成长,“原最初在湘开设庄号者,多为赣籍人士,嗣后钱业既盛,获利颇丰,本省人士亦接踵而起,与赣人争衡,于是遂有江西人经营者为西帮,湖南人经营者为本帮,以示区别”。[4]行业内各家店号供奉同一行业神——财神菩萨,无所谓同业组织。本西两帮各不相关,互不统属,自定行业条规,相互竞争称雄。
光绪初年,社会风气渐开,市面金融活泼,钱店利润丰厚,小钱店乘机而起,遍布街巷。但这些小钱店多投机经营,资本不丰,无相当的银钱储备,信用不固,哄抢市场,倒骗潜逃之事时有发生,致使整个行业秩序混乱,声誉受损。于是“钱业中人见业务如此散漫无稽,遂开始组织同业财神会于福源巷”,并规定“凡挂‘钱店’二字招牌者,需各捐牌费银五十两于财神会,否则不许开设”。并呈请官府核准立案,以取得官方支持。在营业上商定,“每日钱价由财神会公议,上午一价,下午一价,凡营钱而不出牌费者,一律取消其营业权”。[5]此番整顿后,钱业秩序井然,经营也由此而扩张,但行业制度仍需健全。数年后,因票币滥用,金融市场动荡,钱店票币充斥市面,如部分中小钱店原资本不及一万,而出钱出票币却至数万之多,故市面票币通货膨胀,钱店资金周转不灵,不少钱店旋即倒闭。后官方插手此事,取缔钱庄数家,并规定“凡钱店须有五家同业联保,方准开设”。钱业同人受此金融风波打击,重新整理行规,考察各店号实在资本,资本不实者,不以连保;内部严格监管,遇有违规,立即整饬,“行业内又为之振兴,同业因此获益者甚多”。行业中出现多家大钱店,如汪咸裕、周集义、颜泰顺、德源长、朱乾升、蔡福泰、天咸丰、春和祥、泽春祥等店,且有不少兼营典当。钱业一时信用大昭,金融活泼。为适应行业发展需要,建财神殿,同时将福源巷财神会名义取消,财神殿成为钱业同行议事之所。
光绪二十三年(1897),财神殿更名为福禄宫,每日钱价限定同人早饭后齐集福禄宫公同议定,每日只出行市一次,最迟不得过上午十点。而此后行规亦更加具体,兹摘引如下。
关于两帮组合及行内事务的处理:
我行公庙新举总管四人,本籍客帮各二,敦请贤能练达事理精详者,会同每届总散值年经理同行要务。凡属有碍行规及紧要公件,值年即行会商总管,公议事应如何办理,然后出通知单知会同行,则事权归一,以免众心难齐,各怀异见。至总管更替,三年一届,满期仍由同行公议酌举总管两人接办,旧总管四人内、酌留客本两籍各一位,新旧各半,轮流交接,以资熟手而免误公。
关于同业开张:
嗣后凡欲开张,必先请至总值年处,登记新开牌名于总薄,说明店东何人、司事何人,别无胶葛,然后开张。系前曾关歇,店东该帐未清、银钱票据未能发讫,或本系无耻之徒,屡开屡歇,只图网利,不顾天良、乖我商体,均不得改牌复开,违者公同禀究。
关于行业结算:
同行所出除夕、年终、年底、腊底及三十等期银票,公议均由是日上午、下午将店内银票尽数赴公所,互相拨换。
关于钱业图章:
我行钱业各色图章,乃镇日必须之物,虽关紧要,不能有店主时刻收藏。且难杜监守自盗之弊。倘有店伙人等悄窃图章,盖用银钱票据,滥供嫖赌各用,该票一经上柜,或别经查出,概以做假票论,并追来手究系店伙何人所弊端,一面送县究办,一面投鸣值年,公同贴革,如或被其朦混兑去,银钱即著保人赔偿。
为免受社会上不正当势力的滋扰,规定:
同行不论何家有痞滋闹,一经得信,即著老成帮伙或亲往解散。如托故不前或令无知店徒前往充数,以致债事或该痞等内有与同行店主、帮伙谊涉族戚,因而不申公论,反而庇护,查出公罚。[2]233-237
从这些条规可以看出,本客两帮在行业组织构成上基本持衡,总管权限最大,两帮各二;业务上两帮已无隔阂;行业对外交往上也未有本客之别,如遇事端,均由行业组织出面照应。因而可以说两帮基本没有差别。民国初年,按照当时普遍的称谓,钱业同人将“福禄宫”三字改为“钱业公所”,增收牌费银六十洋元,创行业月捐年捐,以扩充公所公项,并由公所创办小学一所。同业中子弟不论本客帮均可入读,进一步淡化了两帮的地域差别。民国13年(1924),公所改为董事制,由本客两帮合组,票选董事九人,监察二人。公所除每日上午议钱价外,若同业中有亟须讨论之事,则及时通知各董事、监察召集,开会一经议决即发生效力。[5]至此,两帮已经完全融为一体,钱业中的江西帮也完成了地域商帮到同业组织的演变过程。
(二)长沙药业江西帮的基本演变
“省城药业开设最老、声名最著者,以外帮人居多。”[6]清前期,长沙大小药店有一百余家,分属江西、江苏、河南、山东、湖南五帮,其中湖南帮因属本土湘籍又称本帮。五帮各立条规,勿相水火,各自帮口极紧,严妨外帮势力渗透。如河南帮、山东帮,店中帮伙学徒非北方人不请,帮内人员约束极严,无事不许出店门一步,以防止在外冶游滋事。西帮秉承一贯传统,从帮伙、学徒到账房、管事均用江西人,且不许店内帮伙与本地女子通婚。[7]本帮亦有相应之条规:“各店只许雇请本帮客师,携带本帮徒弟,倘藐视违规,雇请外帮客师、携带外帮徒弟,使值年人等难以稽查,公同革退。”[2]446-448苏帮因与江西帮渊源较深,[8]所雇员工从掌柜至学徒多为江西人,“苏帮人开店,请的职工是西帮人,算是开明的了”,长沙著名药店劳九芝堂就是如此,部门负责人、技师、高级职员大都是江西人。[9]
各帮之间相互倾轧,竞争激烈,“其生意最大者,莫如江西帮之药材行,专做批发生意,不做门市零卖”。到咸同年间,江西帮见小药店零售获利不少,小药铺纷纷兴起,“各城门口、各僻街小巷,无不有江西小药店出现”。这些小药店多是西帮药材行帮伙所开,“因药材进手颇廉,又能向药材行赊帐,成本轻、开设亦易也”,经营灵活便利,有声有色。药店中生意最好的应属苏帮于乾隆年间开设的劳九芝堂,“一姓相承,获利甚巨,生意永久勿衰”;其次是山东、河南帮的东协盛、西协盛两大药铺。湖南帮最初药店极少,资本雄厚者亦寥寥无几。湖南帮见外帮药业团体巩固,生意发达,争衡市场,获利正丰,于是试图力挽狂澜,想方设法与外帮竞争,甚至采用“联络放价”手段,以夺取他帮生意,在药业中力量有所增强,出现颐寿堂、福芝堂、南协盛、北协盛、中协盛等大药店,有能力“与外帮药业比胜”。[6]但外帮行业资格老,市场较为巩固,生意并不因此减少。而在激烈的比拼过程中,为保证同行的一定利润空间,行业整体意识产生,商帮的地域界限开始淡化,以至于湖南帮内部也“人心渐将不一”。光绪十五年(1889),为强化地域观念,湖南帮只得“重整旧规事”,加强本帮内部团结合作,防止外帮渗透,在条规中强调:“凡新来客师、新来徒弟,务宜查明清楚,若有外帮潜混,来历不明等事,公同驱逐,不得徇情隐匿,亦不得临事抗传不到,违者公同议罚。”[2]446-448其目的便是整合本帮力量,号召同乡一致对外,与外帮争强比胜。
清末民初,湖南帮药业日见发达,营业日益扩张。各帮见湖南帮有死拼之势,为顾全资本起见,有意讲和。而频繁的商业往来,也使得湖南帮“彼时合志同心,无不踊跃”的局面难以维持,各帮药业同人要求停止恶性竞争协调商业利润的呼声高涨。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五帮药业联络一气,创设“五帮药业公会”,会址设在黎家坡仁寿宫(江西临江会馆②),并制定一系列共同遵循的同业条规。各帮公同推定总管二人,值年八人;公同议定药材价码,划一价格;不许私自涨跌、破坏行规,违者议罚。会内供奉名医孙思邈为祖师,并设神农皇帝像一座。会内常年经费,收取牌费捐每招牌二十洋元,如改牌加记则收十元,不足款项,另收月捐补助。[6]可见,尽管药业公所起始时较为松散,但药业同仁从本行业整体利益出发,要求打破地域界限、规范经营、共同获利的趋势明显。在此过程中,省城药业江西帮也逐渐走出相对封闭的地域行业商帮组织界限,向跨地域同业组织融入。
但是江西帮由地缘组织向跨地域同业组织的转变并非坦途,在某些情况下,地域商帮也可能固守抗争,极力维护其既有利益,省城长沙成衣店江西帮即是如此。内部的经营管理极为严格的长沙西帮,实际多为南昌府丰城县人,故亦称丰帮。最迟在咸丰年间,丰帮就已创立了自己的会馆“文昌阁”,奉轩辕神位,[10]并有规章沿袭。光绪年间,西帮面对“人心不测,紊乱条规”的形势,重整帮规,从其帮规内容来看,其地域色彩得到强化,进一步约束帮中同人对新条规 “均宜恪守,倘若犯者,内有知此情弊,隐瞒不报,罚戏一部。如不遵罚,革出三代不许入帮”。[2]385-386但这种固守一隅的做法最终证明还是徒劳,最迟在民国中期成立的该业同业组织即打破了地域帮派的限制。
从清末至民国中后期,打破的地域局限,融入跨地域行业组织是大势所趋。在这历史趋势下,江西帮或被动适应,或积极参与,或主动倡导,最终完成了由地域组织向行业组织的分化转变。
二、湘省江西帮分化演变的原因
清末民国湖南的江西帮组织经历了由最初的地域同乡组织会馆向同业组织公所、公会分化演变,归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行业竞争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相对活跃,在高额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不同地域商人商帮逐渐迈出其原有行业,插足利润丰厚的其他商业领域,使得竞争加剧,而市场上的优胜劣汰最终打破了原来各商帮固守一隅、条块分割的局面。同行之间为了保证一定的利润空间,不得不考虑规范经营,要求行业合作,地域商帮之间必然出现同业整合的局面。
以烟业为例,湖南省城烟业向来分为建(福建)帮、西帮和本帮,以建帮、西帮为最大,湖南本帮生意最为零落。后来本帮整合自身力量,成立本帮的行业组织,生意有所扩展。民国2年(1913),湖南帮烟业同行组织会董熊桂芳为倡合同业,创办湖南烟业公司,并设立分店,改进产品质量,与建、西两帮展开激烈竞争。因其产品不论种类、颜色、香位较之建条、西条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价格低廉,故销路极广,前往购烟者络绎不绝,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生意非常兴盛。建帮、西帮虽质量具有一定优势,但产品远道而来,关税极重而成本高,且不注重花色翻新,故生意日渐式微。为供市面需求,建、西两帮烟铺只得经常到湖南烟业公司购销本地货,而外界亦传闻说两帮均已入股湖南烟业公司。到民国6年(1917),三帮共同组织同业公所,“会中组织每年公举正副总管共二人,正总管管帐薄,副总管管银钱,又公举值年八人,照三帮店铺多少为分配,均系一年一任”。[11]
再如苏广业,光绪以前,长沙办广货者,都由湘潭批发而来,生意小,均由丝棉铺搭做,无专行,更无公会、公所。光绪初年,京苏货盛行,不少店铺装饰华丽,“获利者多,因而开设者亦众”。光绪十余年,洋货输入长沙,京苏洋广杂货店繁荣,江西人吴大茂开设苏广洋货号,“获利倍蓰,于是继而起者数十家”,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坡子街一带几乎遍地是苏广洋货号。货物日益丰盈,但“同业者虽多,而货价不一,无行规,亦无团体,抢行夺市斗巧争奇”,同业人士见各业皆有公所,惟本行业杂乱无章,“乃倡合同业集资购买青石井房屋三间,为每年办财神会及同业聚会之所,此苏广洋货业创立公所之始基也”。[12]
长沙旅馆业同业公会也是如此。清末民初,长沙旅馆业在竞争中,三大帮逐渐站稳脚跟,并各自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长沙帮为云集会,善化帮为东南会,江西帮为柔远会,三大帮势力相当。为避免进一步厮杀,三帮共建旅业公会,共议同业事项,公举总管执年管理会务。[13]重定行规:
窃商贾乃四民正业,无论生理大小,欲沾利益,必赖行规。兹我等贸易客栈,已历多年,前因试馆杂列,致价值高低不一,败坏难堪。爰集我行酌议,禀请出示立章,以昭划一,且使循规踏距,便易稽查,故迩来客栈一途,颇有条理。第沧桑时局,多有变迁,今特立约会商,续议数条,俾志合规同,合资遵守。[2]506
此后凡开业者必先入会,并遵行业条规,否则必遭同行抵制。
再如衡阳纱布业,民国初年江西帮资本雄厚,货源充裕,花色繁多,从批发到零售基本垄断衡阳纱布市场,冠盖同业,盛极一时。民国15年,本帮(衡阳商)力谋发展,整合本帮布店,与西帮对峙,逞雄争长,展开激烈的商战,或刺探对方适销纱布存量,研究推销策略,及时引进时新产品;或以棉纱换土布,白布易色布,扩大纱布、土布、色布品种;或以紧俏货搭配滞品;或放宽赊期扎卖途货;或封锁消息,制造假象。在相互竞争中,不仅西帮垄断局面被逐渐打破,而且数家资本雄厚的老店也因经营失策或管理不当而惨遭淘汰。[14]四年后即民国19年(1930),衡阳纱布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
(二)江西帮的“土著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宗法传统的国度,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在人脑海中根深蒂固,难以消弭。外来客民大多受土著的排挤,成为弱势的代表,而土著一般为霸道的代名词。异地商人来此经商,为避免受各方刁难,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必须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社会,尽力争取本地人的认同。其方式主要有:在客地置办家产,举室迁移,与土著通婚或进行资本交流,捐官谋取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商人的土著化过程其实就是商业移民过程,江西商人在湖南“土著化”现象极为普遍。先从小市镇看,如与江西萍乡接壤的醴陵县,市场上存在本帮和西帮之分,清末除红茶、夏布、土瓷、豆腐外,余如药材、南货、糕点、豆豉、杂货、银楼、布匹、钱庄、典当等各业,均属西帮;[15]587民国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以贸易置家产者亦不少。”[16]永顺府龙山县江西商人“其先服贾而来,或独身持襆被入境,转物候时,十余年间,即累赀钜万,置田庐,缔姻戚,子弟并入庠序”。[17]湖南汨罗杨氏由丰城贸易至汨罗,为免受当地恶棍的刁难,与当地名门结为亲家后,才免受挑衅。[18]大都会也不例外,清末,省城长沙钱业江西商人甚至可以左右市场,民国以来,“西帮人物多举室来湘,其经营之庄号亦多,年代甚久,与本帮商号形同一体”。[4]药业江西帮帮口极紧,凡药材生意之秘诀、行情信息严禁外传,不带本地徒弟,不与本地人通婚,否则就是“卖饭碗”,必被本行业革除。[19]而到民国年间,不少地方出现西帮与湖南本帮交融的局面,如湘乡,江西帮在此地定居,繁衍后代,与湘帮长期相处关系融洽,出现“转窝子”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帮中的谢太和药店老板谢孔昭、同济药号老板卢仁卿不顾帮派的阻力,招收湘乡籍学徒进店,“湘”、“西”两帮的传统界限被完全打破。[20]再看湘潭,这个曾经发生过大规模土客械斗、以至朝野震惊的商业都会,[21]西帮与本帮历来隔阂甚深。但经过数百年的磨合,虽依然摩擦不断,但双方剑拔弩张之势已消弭。至清末民国年间,两帮不仅互结儿女姻亲,而且在经营上互有资本往来,两帮之间多年的鸿沟被逐渐填平。[22]在凤凰,赣籍商民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谋求社会地位。清末国库亏空,重开捐纳之法,江西商民熊玉书、裴彤九等捐候补知县及监生等头衔。赣籍商民还通过送子弟入学登科举等途径步入政界,如裴三星商号送长子裴晴初入学中举,历任贵州、澧州知事,民国初期连任三届凤凰县长。商民子弟顾家齐、戴季韬曾任国民党师长和湖南省政府委员。[23]类似的情形在湖南不在少数,笔者翻阅大量湖南地方文史,发现湖南有一大批的工商联干部、工商业者是江西商民的后裔,他们在民国年间已经融入本地。
尽管阻力重重,但赣籍客商自始至终未曾放弃融入本地的努力,从最初的具有商业性质的建街市、修码头、设义渡到完全是社会公益性质的修桥、铺路、防灾、赈灾、建学校,江西商人可谓煞费苦心。在这种“土著化”过程中,原有商帮内部的乡土粘合力逐渐消减,商人的地域色彩慢慢淡化,并逐渐汇入到新的地域社会、新的商业团体组织中去,江西帮内部也随之逐渐发生着分化演变。
(三)晚清民国的时政导向
晚清民国的政策导向也为江西帮的分化演变推波助澜。这一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规为江西帮由地域商帮组织向跨地域行业商人组织演变提供了法律约束。清末,在帝国主义先军事入侵、后商业掠夺的打击下,清廷愈来愈感觉到商战的重要性。光绪29年(1903),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倡导华商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以期达到“保商利,通商情,讲信誉而无欺诈,有竞争而无倾轧,发展商业”的目的,并认为:“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24]在商部的劝导下,湖南颁行《湖南省商会试办章程》,并广为宣传:“愿来本会注册者,受本会开通、联络、保护、振兴之益……如不来本会注册者,有事则本会未便处理,以示限制。”[25]与此同时,湖南各商务繁庶之区如常德、岳阳、衡阳等地也相继成立商会,各地江西商人也纷纷加入其中,有的甚至被选为会长、副会长,在商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社会身份的变化,必然影响其地域角色作用的发挥。到宣统末年(1911),湖南各地共成立商会十五处,入会商号12665家,商会议事共达1498件,[26]商会影响日益扩大。
民国政府继承了晚清的商务政策,继民国4年(1915)颁布《商会法》之后,为矫正营业止的弊害,维护同业的公共利益,北京政府农商部于民国7年 (1918)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同一区域内之工商业者设立公会,以一会为限”,[27]这使得不同地域的商业团体在经营同一行业时,必然走到一起,原有的同一行业帮派林立,壁垒森严,相互争雄的局面被打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的颁布,为旧式商业组织的转变和新式工商同业组织的建设提供了法律规范。为进一步整合行业组织,南京政府于民国18年(1929)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并于次年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细则》,强调“同业之公司行号,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推派代表,出席于公会”。[28]在民国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加入同业组织成为工商界潮流。在湖南,民国18年(1929),长沙先后组织了国药、百货、旅馆、估衣、纸业、南货等同业公会70余个;至民国24年(1935),全省批准立案的同业公会有291个,入会商家13700余家;[29]至民国30年(1941),全省共建立商业同业公会1107个,入会商号25774家;[30]至民国36年(1947),全省同业公会组织发展到2124个。[31]同业公会组织基本覆盖了湖南的绝大部分行业门类,将各商家商号囊括其中。湖南省政府转令各地执行,省城长沙措施极为严厉,“不加入同业公会不准营业,限期更换会员证,无证者勒令停业”,[15]623迫使同业公司商号必须加入工商同业组织,最终促使了行业中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业组织的瓦解。
打破地域界限,走向行业联合,工商同业组织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正如吕作燮所指出:“地域商帮的会馆,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竞争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就暴露出他的先天不足,特别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入侵以后,竞争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就迫使地域性商帮逐步突破地域界限,向同业联合方向发展。会馆的衰落和同业公所的兴起,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自然趋势。”[32]清末民国湘省江西商帮的演变就是这种自然趋势下的一个典型缩影。
收稿日期:2008-06-15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对此争论太多,各执一词,本文仅以湘省范围内会馆、公所设置的一般情况而言。
②湖南《大公报》自民国14年6月3日起,连续十余日刊登“江西仁寿宫临江会馆启事”,而且临江以药业闻名,地方会馆亦称“仁寿宫”,故可推测此仁寿宫为江西临江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