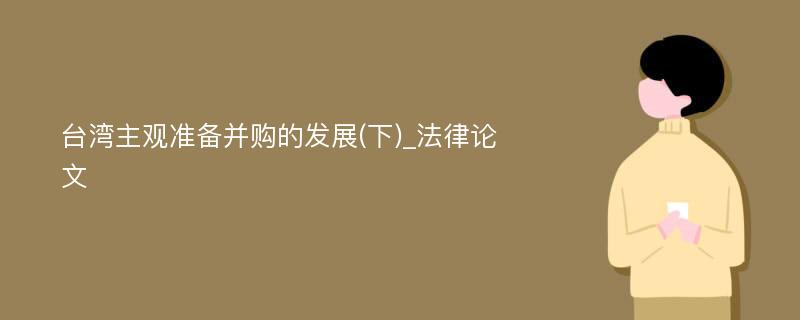
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在台湾地区的发展(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主观论文,地区论文,在台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实务状况
(一)案例一:“中央信托局”(以下简称“中信局”)诉请先位中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希公司”)后位香岛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岛公司”)损害赔偿事件(注:本案例《资料》,存于中央信托局。)
1.案情介绍
中信局与先位被告中希公司签约订购重石晶粉2000公吨,约定中希公司应以定期班轮载运,并须保证货品于交货时无瑕疵。讵中希公司未依约定,以后位被告香岛公司所属非定期班轮运送,惟运抵基隆后,发现破包甚多,须在船上重新包装,因请求中希公司赔偿损失。如法院认先位被告不负赔偿责任,则请判令运送人即后位被告香岛公司赔偿。第一审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罗时薰于1973年10月29 日以1973 年诉字第1481号判决,认原告先位之诉有理由,判决原告胜诉,至于后位之诉,则认“原告本位声明之请求既属有理由,关于预备声明部分,自无审酌之必要。”(见附件判决)
先位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三审判决及其后发回判决,均认原告先位之诉为有理由,而未再就后位之诉加以审理裁判,其诉讼程序因与本文无关,故不详述。
2.说明
(1)本事件为被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2)一审判决认先位之诉有理由,就后位之诉未予审酌。
(二)案例二:“中央信托局”诉请香岛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损害赔偿事件
1.案情介绍
“中央信托局”(以下简称“中信局”)就本件同一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在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973年度诉字第1481号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以香岛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岛公司”)为共同被告,在该案之本位声明(先位声明)系请求另一被告中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中希公司”)赔偿损害,备位声明(预备声明)则请求香岛公司赔偿损害。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受理该事件审判之结果,以本位声明为有理由,而仅就中希公司部分予以裁判,而就香岛公司部分未为审判,嗣仅中希公司对于该判决提起上诉,尚未确定,中信局乃另行对香岛公司提起本件诉讼。第一审认起诉合法而为实体判决,台湾地区高等法院1976年度上字第655号第二审判决,认为所谓备位声明, 系指同一原告对于同一被告将理论上相排斥之数个请求,以同一诉讼合并主张,预虑第一位之请求无理由时,要求就第二位之请求为裁判之意。因此,不同之被告即不能为备位声明。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就该事件之备位声明既未经裁判,备位之诉尚在诉讼系属中,中信局更行提起本件诉讼,有违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禁止重诉之规定,因此将第一审判决废弃, 改判驳回中信局之诉。中信局不服,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于1977年6月以1977 年度台上字第1722号判决(见注⑦),废弃上开二审判决,其理由为:“按在诉之合并之形态中,有所谓预备之合并,而预备之合并复有客观的预备之合并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之分。所谓客观的预备之合并,即同一原告预虑其对于同一被告提起之某诉(先位之诉)无理由,同时提起不能并存之他诉(预备之诉),以备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预备之诉审判。所谓主观的预备之合并,即在共同诉讼,或由共同原告对于同一被告为预备之合并,或由同一原告对于共同被告为预备之合并,前者原告甲预虑其对于被告之诉(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原告乙对于被告之诉(预备之诉)审判,后者原告预虑其对于被告甲之诉(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其对于被告乙之诉(预备之诉)审判。关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实系法院依原告所为先位声明及预备声明定审判之顺序,本于民事诉讼法系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尚非法所不许。此种诉讼,法院认先位之诉为有理由时,不必更就预备之诉审判,即以先位之诉有理由,为预备之诉之解除条件,预备之诉遂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亦即该部分之诉讼系属应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此后虽先位之诉受败诉判决之当事人提起上诉,于预备之诉已消灭之诉讼系属不生影响,在第二审程序除有诉之追加之情形外,不得更以在第一审预备之诉未受裁判之当事人为当事人。原审既谓另案第一审法院认上诉人对于中希公司之先位声明为有理由,而未就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之预备声明审判,此项预备声明应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从而上诉人于另案预备之诉之诉讼系属消灭后,更对被上诉人提起本诉,自不受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禁止重诉规定之限制。原审未见及此, 遽认上诉人另案预备声明之诉讼仍在系属中,不得更行起诉,殊有未洽。”
2.说明
(1)本事件台湾高等法院第二审判决,认:①预备合并之诉, 系指同一原告对于同一被告始得提起,对不同之被告即不能为备位声明,故对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采否定见解;②一审就先位之诉判决原告胜诉,未就后位之诉为裁判,先位被告上诉时,后位之诉之诉讼系属不消灭。
(2 )“最高法院”第三审判决则认:①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为合法而采肯定说;②如先位之诉获胜诉判决,后位之诉因解除条件成就而失其效力,亦即其诉讼系属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消灭;③此后虽先位之诉受败诉之当事人提起上诉,第二审法院不得更以后位之诉之当事人为当事人予以审理裁判。
(三)案例三:孙国风等对“国有”财产局台湾中区办事处(以下简称“国有财产局”)请求同意建筑房屋事件
1.案情介绍
孙国风等在第一审起诉,其先位声明以“中央兴业株式会社”为被告,后位声明以国有财产局为被告,请求同意建筑房屋。第一审法院认先位声明为有理由而未就后位声明为裁判。国有财产局竟对此判决提起第二审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二审判决(1976 年度上字第454号)以其上诉不合法予以驳回,(注:第二审法院如认上诉不合法,依民事诉讼法第444条规定,应以裁定驳回之, 本件二审法院以判决驳回,似有不当。)国有财产局不服提起第三审上诉,“最高法院”于1979年6月以1979年台上字第1727号判决,(注:见法律评论第46卷第3期第30页。)认第二审驳回其上诉,于法无违误。
2.说明
此一案例,为被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第一审法院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采肯定说之见解。第一审就先位声明为原告胜诉判决,而未就后位声明为裁判,后位之诉之被告能否对先位声明所为判决上诉?第二审、第三审法院均采否定见解。
(四)案例四:“中央信托局”、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公司”)诉请台湾西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伟公司”)给付买卖价金事件(注:本案例资料(附于万国法律事务所1982 年度711139号卷宗),请参见附件一——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983年度诉字第6178号判决。)
1.案情介绍
本事件先位原告中信局及后位原告中油公司以预备合并方式对西伟公司起诉,请求返还价金及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先位原告主张:(1 )先位原告虽系依行政院所颁布“统一国外购料办法”之规定,受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之托办理“无磁性钻管”之标购,先位原告系以自己之名义为当事人与被告订约,并非以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代理人名义订约,此观诸系争契约首页右下方买受人签名为先位原告中信局,而非备位原告中油公司,更未表明系为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之代理人即明,至于先位原告在招标书上记载受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之委托办理等字样,不过表明先位原告与备位原告之内部关系,系为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之计算标购无磁性钻管而已,对于先位原告系以自己名义与被告订约并无影响。先位原告既系以自己名义与被告订约,自属本件买卖契约之当事人。(2)本件买卖, 被告所交付之“无磁性钻管”具有重大瑕疵,根本不符合约定之规格所要求,但被告经原告催告后明白拒绝另行交付无瑕疵之货品,核其行为,显已构成不为给付或不为完全给付之状态,原告且已依约解除契约,从而原告不但得请求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且得请求返还价金。
后位之诉原告主张:(1 )万一法院不认先位原告为适格之原告而驳回起诉,则以中油公司为备位(后位)原告,本于与先位之诉相同之事实及理由,请求返还价金及损害赔偿。(2 )至于本件先后位原告所提起之“主观的预备之合并”,本于民事诉讼法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及“最高法院”1977年台上字第1722号判决之意旨,应为法律所准许。
被告西伟公司则抗辩:(1 )原告提起本件学说上所谓之“主观之预备合并之诉”,固以“最高法院”1977年台上字第1722号判决意旨为依据,惟该项判决意旨迄今尚未正式编为判例发表,自无拘束之效力,另查此种“主观之预备合并之诉”,应否准许?学说上及实务上尚有争执,况该判决之所以承认主观之预备合并之诉,在于便利当事人与防止裁判之抵触,然“最高法院”判决后段认为“此种诉讼,法院认为先位之诉为有理由时,不必更就预备之诉审判,即以先位之诉有理由,为预备之诉之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亦即该部分之诉讼系属应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从而上诉人于另案预备之诉讼系属消灭后,更提起本件诉讼,自不受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禁止重诉规定之限制。 ”云云,则备位原告于第一审判决后得重行对被告起诉,不但对被告之保护殊欠周到,抑且无法防止裁判之抵触,被告可能为重行给付,是以被告认为原告提起本件“主观之预备合并之诉”不应准许。(2 )先位原告中信局系受备位原告中油公司之委任,代办采购“无磁性钻管”之手续,先位原告中信局并非买受人,此观原证一号标书前言所称:“中信局购料处系受标单上所示当事人之委任,代理当事人办理招标采购;中信局为采购代理人”云云即可了解。先位原告并非买卖契约之买受人,自不得请求被告返还价金。(3)何况,本件买卖标的物并无瑕疵, 其品质规格完全符合契约的规定,先后位原告之主张无据,其请求殊不应准许。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李威廷于1983年6月22日以1983 年度诉字第6178号做成判决,先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是否合法论断,认为:“按在诉之合并之形态中有所谓预备之合并,而预备之合并复有客观的预备之合并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两种。关于后者,实系法院依原告所为先位声明及预备声明定审判之顺序,本于民事诉讼法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尚非法所不许。”并进而就实体为先位原告部分胜诉部分败诉之判决,至于后位原告之诉,则未予裁判。
被告不服,对先位之诉之判决提起第二审上诉,先位原告中信局及后位原告中油公司亦均提起先后位之附带上诉。其附带上诉之声明为:(一)原判决不利于上诉人之部分均废弃。(2 )废弃部分请判决:(先位声明)台湾西伟有限公司(即西伟公司)应给付中信局新台币(下同)8880元及自1983年5月14 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央银行核定放款利率1/2计算之利息。中信局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备位声明)西伟公司应给付中油公司8889元及自1983年5月14 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央银行核定放款利率1/2计算之利息,中油公司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关于后(备)位原告之提起附带上诉之依据,则主张:“预备诉之合并,固以先位声明合法并有理由为备位声明之解除条件,惟若嗣后先位声明变为败诉时,仍须就备位之诉为判决,因而解除条件应于判决确定时始成就,亦即备位声明之诉讼系属,必俟先位声明判决原告胜诉确定始消灭,今西伟公司提起上诉,先位声明因而不得确定,其备位声明即未消灭。又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于第二审采续审制,继续第一审诉讼程序,因之,事件经上诉于第二审法院,即发生全部移审之效果,备位之诉自当随先位之诉一并系属于上级法院,西伟公司虽于上诉时,仅就先位声明部分提出,其备位声明应并系属于第二审法院,故本件备位声明并未因原判决先位声明胜诉而消灭,且与先位声明并系属于第二审法院,因此倘认中信局非适格当事人,请就备位声明部分予以判决。”但被上诉人西伟公司对此则主张:“备位附带上诉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带上诉不合法:(1 )按先位附带上诉人中央信托局(即中信局及备位附带上诉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即中油公司)依据“最高法院”1977年上字第1722号判决提起所谓“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经查前开判决意旨称:“此种诉讼,法院认为先位之诉为有理由时,不必更就预备之诉审判,即以先位之诉有理由,为预备之诉之解除条件,预备之诉遂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亦即该部分之诉讼系属应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此后虽先位之诉受败诉之当事人提起上诉,于预备之诉已消灭诉讼系属不生影响。在第二审程序除有诉之追加之情形外,不得更以在第一审预备之诉未受裁判之当事人为当事人”。又“最高法院”1979年台上字第1727号判决亦同揭斯旨。依此可知,在所谓的“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受诉法院认先位之诉为有理由,备位之诉应即脱离诉讼,备位之诉当事人因未受裁判,自不得提起上诉。本件中油公司已因中信局之胜诉而脱离诉讼,其不得再行提起附带上诉,甚明。(2 )依民事诉讼法第437 条规定“对于第一审之终局判决得上诉于管辖之第二审法院”,须先有第一审终局判决,始有第二审上诉可言,且唯有受不利判决之当事人,始得提起上诉。就本件言,原审判决对中油公司之诉既未判决,自无所谓利益或不利益之存在,渠竟提起附带上诉,自与法不合。(3)依民事诉讼法第460条规定,附带上诉须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起始为合法,而本件原审法院既未对中油公司判决,尤其仅对中信局提起上诉,中油公司不与焉,中油公司并非被上诉人,自不得提起附带上诉。尤有进者,本件诉讼之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中信局及中油公司不但无法合一确定,抑且相互排斥,是本件应属普通共同诉讼。依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则原判决不利于中信局部分,其利害仍不及于中油公司,中油公司自不得因中信局提起附带上诉而藉此提起附带上诉。”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审判长法官苏士腾、法官吴仁、苏达志合议审判,于1984年3月19日以1983年上字第2921号判决, 该判决当事人栏除列先位之中信局为“被上诉人(即先位附带上诉人)”外,并列中油公司为“备位附带上诉人”。二审判决先论断系争买卖契约之当事人即买受人为先位之中信局,然后就后位中油公司之诉及附带上诉,认:“本件买卖当事人既为中信局与西伟公司,则中油公司列为备位原告或备位附带上诉人即无加以审酌之必要,本件所应审究者,仅中信局解除买卖契约是否合法,请求返还给付价金并赔偿损害是否有理由而已。”然后就先位原告部分之诉讼,为两造上诉均一部有理由,一部无理由之判决。
西伟公司不服上开二审判决提起第三审上诉,“最高法院”以1984年度台上字第2745号判决仅列先位原告中信局为被上诉人认上诉为有理由,废弃二审判决发回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亦仅列中信局为被上诉人及附带上诉人(未再列后位之中油公司为被上诉人及备位附带上诉人)而以1984年上更(一)字第500 号判决驳回上诉及附带上诉,嗣西伟公司再提起第三审上诉,“最高法院”认上诉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驳回(1985年度台上字第1934号),案归全部确定。
2.说明
(1)本件为原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认“本于民事诉讼法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应予准许。
(2)原告引用“辩论主义”之精神及“最高法院”第1722 号判决做为主张应准许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论据。
(3 )先位原告及后位原告不但所主张之起诉事实(除契约当事人部分外)及理由相同,且均委任相同之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可见先后位原告之地位系“协同”而不相冲突及对立(参见第122页注①)。
(4)第一审法院认先位之诉有理由判决先位原告胜诉, 但就后位之诉何以不加裁判,并未加以说明。
(5)被告西伟公司提起二审上诉, 先后位原告亦提起先后(备)位之附带上诉,但后位原告并未受一审裁判,其附带上诉是否合法?两造对此有所争议,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一方面仍列后位原告中油公司为“备位附带上诉人”,一方面未以“备位附带上诉”为不合法,以裁定驳回,而认:“本件买卖当事人即为中信局与西伟公司,则中油公司列为备位原告或备位附带上诉人即无加以审酌之必要。”其见解是否认为:①后位之诉虽未受一审裁判,但仍随先位之诉之上诉而移审于第二审,只因先位之诉有理由而“无加以审酌之必要”?②后位之诉之原告虽在第一审并未受不利之判决,但仍得对先位之诉原告所受之不利益判决提起上诉?此皆为值得进一步探究之问题。(注:如采当然诉讼参加之理论,则可能得此结论。)
(6)本事件被告西伟公司就其败诉部分提起第三审上诉后, 包括其后之二审更审程序,后位之诉似未再被提及而与先位之诉分离,其理由为何?是否合乎承认预备合并之诉之本意?均值探讨。
(五)案例五:“中央信托局”、高雄市立民生医院(以下简称“民生医院”)诉请科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公司”)返还价金等事件(注:本案例资料(附于万国法律事务所1984年度731083号卷宗),请参见附件二——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984年度诉字第1297号判决。)
1.案情介绍
本事件先位原告中信局及后位原告民生医院以预备合并方式对科华公司起诉,请求返还价金及损害赔偿。
先位原告主张:(1)本件原告中信局于1981年3月28日发出欲购买“实时心脏超音波扫描仪”一套招标之表示(要约之引诱), 被告于1981年5月13日以书面提出要约,原告中信局于1981年6月15日承诺,并与被告成立买卖契约,系争买卖契约之双方当事人应为中信局与被告,至于原告中信局虽受民生医院委托标购系争实时心脏超音波扫描仪,但原告中信局系以自己名义签约,并为民生医院之计算买受,买卖契约之买受人应为中信局。(2)系争实时心脏超音波扫描仪于1982年3月底运抵高雄,由高雄公证股份有限公司会同英国原厂技师及有关技术人员开箱检验结果,发现其品质与合约不符而有瑕疵,无法完成验收手续,其后原告中信局一再函催被告依约修理,更换新品,被告虽亦屡次派员前往修理,惟历经一年余系争扫描仪之瑕疵仍未获改善,乃不得已发函通知被告解除契约,请求退货还款并赔偿损害。
后位之诉原告主张:(1 )如钧院审理结果认原告中信局系代理原告民生医院标购系争扫描仪,系争买卖契约之买受人为民生医院,则以民生医院为备位原告。(2)除关于当事人适格部分之陈述外, 备位之诉之事实理由与先位之诉部分相同,兹引用之。(3 )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先后位原告主张:“关于‘主观的预备之合并’,实系法院依原告所为先位声明及预备声明定审判之顺序,本于民事诉讼法采辩论主义之立法精神,应为法律所准许,“最高法院”1977年度台上字第1722号著有判决。本件原告所提起者,即为‘主观的预备之合并’,亦即原告中信局预虑其对于被告之诉(先位之诉)无理由时,请求法院就原告民生医院对于被告之诉(预备之诉)审判。揆诸前开说明,自属合法。”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蔡日昇于1984年11月26日作成之1984 年度诉字第12979号一审判决,认系争买卖契约之买受人应为先位原告中信局,并认原告先位之诉有理由而为先位原告胜诉之判决。至于后位之诉,一审判决则认:“本件为主观的预备合并之诉,先位之诉有理由,为预备之诉之解除条件,本院既认原告中信局先位之诉为有理由,则预备之诉即原告民生医院之请求遂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失其效力,故该部分之诉讼系属应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此一判决因当事人未上诉而告确定。
2.说明
(1)本件为原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第一审判决认为应予准许。
(2)原告引用辩论主义精神及“最高法院”第1722 号判决做为主观应准许提起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之论据。
(3 )先位原告及后位原告不但所主张之起诉事实(除契约当事人部分外)及理由相同,且均委任相同之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可见先后位原告之地位系“协同”而不相冲突及对立。
(4)第一审判决认后位之诉因先位之诉有理由, 其诉讼系属因解除条件之成就而归于消灭,显系采“最高法院”第1722号判决之见解。
(六)案例六:托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福公司”)诉请先位被告阙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阙盟公司”)及后位被告林焕文给付买卖价金事件(注:本案例资料(附于万国法律事务所1988年度779119号卷宗),请参见附件三——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988年度诉字第6879号判决及台湾高等法院1989年度上字第736号判决。)1.案情介绍
本件原告托福公司以阙盟公司为先位被告,林焕文为后位被告,提起被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请求给付价金。
原告之主张为:(1 )关于先位声明部分, 先位被告阙盟公司于1988年3月5日由后位被告林焕文代理向原告订购电子测量仪器400台, 价金为美金102800元,原约定先位被告应于1988年6月30 日前交付货款予原告,后应先位被告要求,双方同意将上开期限延至1988年7月15 日。惟先位被告却始终未给付价金,而争执林焕文无代理权。然林焕文自1987年以来曾多次代表(或代理)先位被告与原告交易,且先位被告早已知悉林焕文为其代理人而始终不为反对之表示,足见其确系有权代理,至少,先位被告也应负表见代理人之责任,原告自得请求其依约给付价金。(2)关于备位声明部分, 本件买卖契约系由后位被告林焕文代理先位被告签订,原告主张以先位被告为买受人。惟若认为后位被告无权代理先位被告签订本契约, 则原告主张后位被告对原告应负民法第110条无权代理人之责任。 查原告因后位被告无权代理先位被告向原告订约,因而所支出之缔约费用,原料及其他准备交货之成本、费用及资金积压所损失之利息,与依契约原可预期收入之利润等损害,应得向后位被告请求赔偿。
先位被告主张:按本件系争之买卖,先位被告完全不知,更遑论有授权后位被告代理本公司或有任何应负表见代理人责任之情形存在,原告之请求显无理由。
后位被告主张:(1)本件主观预备之合并不合法。(2)备位被告系自己与原告成立买卖行为,并非有权代理或无权代理任何人为买卖行为,何来应负无权代理人之损害赔偿责任?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魏大喨于1989 年3 月24 日以1988年度诉字第6879号作成判决:(1 )首先就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是否合法之问题,认“此种诉之合并,系法院依原告所为先位声明及预备声明定审判顺序,依民事诉讼法采当事人进行主义,言词辩论精神,及避免判决先后矛盾言,非法之所不许。本件原告提起本诉,先以阙盟公司为被告,依买卖关系请求给付价金,并预虑其诉无理由时,请求就后位被告林焕文依无权代理法律关系请求赔偿损害,其诉之型态依前开说明,应无不合。”(2)就实体方面, 则认先位被告应负表见代理授权人之责任而判决原告先位之诉胜诉。(3)原告先位之诉既有理由, 即无就后位之诉部分为审理之必要。(4 )就先位之诉原告胜诉言后位之诉部分非为原告伸张或防卫权利所必要者,其所生之费用,本院酌量情形命原告负担其一部。
对于上开判决,先位被告不服而提起上诉,先位原告(被上诉人)除就先位之诉为声明请求驳回上诉外,并就后(备)位之诉而为声明。而后位被告林焕文亦于第二审提出答辩。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审判长法官温良瑞、法官徐定远、朱建男于1989年10月30日以1989年度上字第736号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而驳回上诉, 惟关于主观预备合并之诉是否准许及未裁判之后位之诉,是否随先位之诉上诉而移审之问题,则认:“本件被上诉人以诉之主观预备合并之关系在原审先位声明请求阙盟公司给付价金,复以备位声明请求林焕文赔偿损失,有起诉状在原审卷第517页可稽。而原审亦以之为审理, 而认为被上诉人之先位声明有理由,遂未再就备位之诉为审理,有判决正本附卷可佐。而本件于阙盟公司上诉后,被上诉人援引“最高法院”民刑庭会议决议之客观合并之诉之移审效力问题之决议,主张备位之诉应于先位之诉上诉时有生移审之效力。惟查,民事诉讼法第248 条所谓客观的诉之合并,系指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以数项法律关系为诉讼法标的,依同一诉讼程序提起之诉讼也。故称之为诉讼请求客体之合并。今被上诉人在原审先则请求阙盟公司给付价金,复备位请求林焕文赔偿损害,两者诉讼主体不同,此应为主观的诉之合并,而非客观的诉之合并甚明。原审既未就林焕文部分为审理判决,被上诉人复未就林焕文部分提起上诉,则无论阙盟公司之上诉是否有理由,本院应无就林焕文部分为并审之理。”
本事件于先位被告上诉第三审程序中,原告及先、后位被告达成和解,由先位被告撤回上诉而告终结。
2.说明
(1)本案例为被告多数之主观预备合并之诉, 第一审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依当事人进行主义,言词辩论精神及避免判决先后矛盾之理由,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非法之所不许,且认先后之诉既有理由,即无就后位之诉为审理之必要。
(2)关于后位之诉之诉讼费用, 第一审法院认非原告就先位之诉伸张或防卫权利所必要,故依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 酌量命原告负担其一部。
(3)第二审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决, 似仍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为合法,但是,于第一审先位之诉原告胜诉而未就后位之诉为裁判时,如先位之诉上诉到第二审,则认为后位之诉并不随同移审。因此,无论先位之诉有无理由,二审法院均不得就后位之诉加以审理。
(4)先后位被告不但所主张之事实及理由相同, 且均委任相同之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可见先后位被告之地位系“协同”而不相冲突及对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