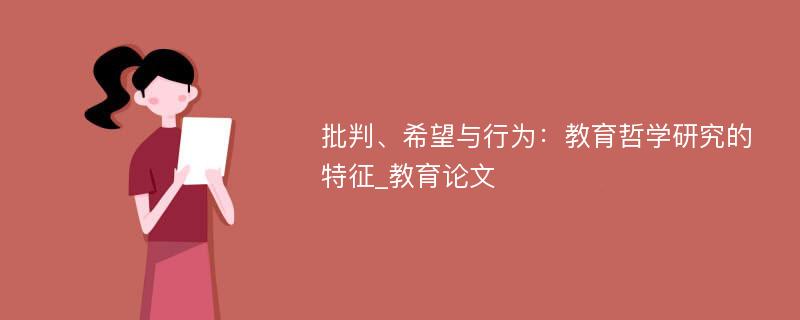
批判、希望和行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之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性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2)25-0003-05
今天,教育研究迅速地使自己服务于经济市场和资本运营之逻辑,“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供求关系”、“实用”等词语支配了教育研究者的世界。一种被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批判社会学正使教育研究患上“权力主义”、“批判主义”、“解构主义”的贫困。流行的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它们确实功效卓著,但“流行趋势”、“卓著功效”对发展一种健康的教育研究并不足够,且常常会行使一种“阻碍”健康发展之功能。流行的教育研究并不能让人们看到属于教育的希望,它们各执其一端,相互攻讦,为了战胜霸权而不是发展真知的目的阻碍了它们对自身缺陷的反思,它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贯穿着帮派学者的不逊和对“理性真诚”的背叛。它们的争论掩盖了教育中最根本的问题,教育成为各种研究方法、经济与商业、私人利益的试验田。愈来愈趋于“碎片化”的取向加大了教育及其研究的风险,祛除了“民主”、“正义”、“人性”等在教育中的魅力。教育研究者成为“目光短浅”的只懂得欢呼或悲叹的“庸人”。对流行教育研究的剖析能够产生一种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力量,同时会收获一种信心和自我认识的责任。教育哲学研究必须成为一种对美好生活和卓越人性的无条件关注,必须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思考的力量,赋予人类思维以尊严。它不仅必须批判诸多“压迫式”的教育研究形式,还必须重建一种对教育的深入而恒久的信心,并产生一种为了信心而不屈的行为。
一、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的批判,它含有对完美教育的希望,是一个独立自由与反对“碎片化”霸权的探寻教育之方式,其目的在于产生对美好教育的想象与捍卫
作为一种批判的教育哲学研究,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独立自由的品性。它不会为“美好的当下”而摇旗呐喊,却总会不断地挑当下教育的“刺”,怀疑当下的教育。思想的妥协和顺从从来都远离或背叛了这一品性。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哲学热衷于浅薄地吹毛求疵、爱逞能或者爱发牢骚,而是防止人们在现存教育研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方法中迷失自己。这种教育哲学相信,无论是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研究范型,我们都不应该盲目地加以接受或不加批判地效仿。流行的东西往往会使人们容易盲目、容易效仿,只有注入一种理性批判,才能使人们从流行中解放出来,降低教育的风险。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要抱守某个观念或者所谓的“哲学真理”,并以之来同化和审视教育研究。教育哲学研究并不提供这样的“真理”,它是一种“无立场的批判”、“自由的入思”。“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在上述东西的发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简言之,是真正认识事物的努力。”[1]批判表达了教育哲学研究对于真知寻求的无条件信守。这意味着,对于教育哲学研究而言,批判一定多于“批判”,批判是寻求真知的一种方式。离开了对真知的信仰,批判似乎是多余的。因此,批判不是一个否定,不是一个对教育的“真知”、“美好”、“卓越”之追求的否定;相反,它是对它们的捍卫,是对教育研究之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克服。
作为一种批判的教育哲学研究,它意味着需要寻求一个比较完整的视界去审视教育,需要追寻一个完整的教育之本相,以之来克服或取消一种片面性。尽管“片面化”已经成为教育研究大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教育哲学研究必须揭示这一趋势之后果。这预示着作为一种“批判”,它必须进行自我批判,要承认自己的局限。这是一个品质性的要求。批判包含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单纯的驳斥和否定。对自我无知的省思拒绝了一种“权威式的”、“居高临下的”斥责与批评,反对已经演化为派系之争的“科系之争”。在柏拉图的教育哲学中,那些对话者之所以最终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荒谬中,是因为他们过于坚持从某一个方面去看待教育。那些过于片面坚持自己观点的对话者并不真正明白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一个观点所包含的最适切的意义需要一个完整的背景和体系,这也就是柏拉图比那些对话者更加清楚他们自己立场的原因。批判不能迷失于某个观念中,以一种片面的观念来批判另一种片面的观念。教育哲学的批判要求一个更高的谨慎态度,而不是过于匆忙的论断。
作为一种批判的教育哲学研究,批判意味着对未来美好教育的一种期待或希望。批判并不只是解构一切,这样的批判并不能完成更加困难的教育理论研究任务。在批判之后,如何重建一种教育及其研究,批判主义教育社会学研究似乎消失了。批判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的自恋,不能拘泥于对现实教育犀利的揭露,因为教育不能在一种废墟之中进行。杜威这样说:“仅注意使教育不被一个阶级积极地用来作为更加容易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还不够。”[2]教育必须从追溯既往和展望未来两方面来解释。“长时期以来,人们表示有意识地利用教育,使青年人在不应产生社会弊病的道路上开始,以消除这些显著的社会弊病。同时,他们还设想使教育成为人类实现更好希望的工具。”[2]为何批判?何以批判?教育哲学研究必须拥有一种希望。只有在希望中,教育哲学研究才能对现实教育进行批判,才需要批判。离开了这一希望,批判将无法产生更大的力量,只是批判而已。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的批判,它并不做那个所谓的“客观的”、“中立性的”批判,因为“中立性的”、“客观的”批判也许并不存在。它必须提供一个“伦理”与“价值”上的判断,批判和“美好”相连。教育哲学的批判不是用某种具体的目的是否达成来进行批判,教育哲学的批判是“异质性的”。它必须产生一个对“异质性”教育的想象、一个好的教育的希望。教育哲学研究的批判必须不能加重人们的绝望,使他们成为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主义者。相反,只是为了那些绝望者,为了那个美好的教育,批判才被赐予教育哲学研究。彻底的绝望主义者也许并不会抱有希望,也就会丧失批判的欲望。只有有了希望,才有批判的动力。只有有希望的批判,才会有拯救。
二、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的希望,它在于以超越的视野关注现实教育,思索现实教育可能的完美性,拒绝绝望,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现实与学会希望,在于使一种美好的可能性之观念与有希望地对待现实教育之态度深入其心
如果教育哲学是一种希望,那么,它就必须关注现实、关注现实教育。只有在对现实教育的关注中,教育哲学才能摆脱一种浪漫主义的幼稚病,才能克服一种自我放纵和绝望,同时,也才不会牺牲在现实教育经验主义的祭坛上。正是对现实教育的关注,才使得希望能够产生。这并不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教育,人们希望美好的教育在某一天会实现,或者希望教育会不断地变好。既然困惑、不满和痛苦在今天还有许多,那么,没有希望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希望并不产生于一帆风顺之中,相反,希望蕴含在困境甚至失望之中。关注现实,承认现实的缺陷,这原本就是一种希望的行为。希望设定了对现实的不离不弃。当然,对现实的关注和承认并不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专利,它只是以一种有希望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它不是沉迷于当下,只凭冷静的头脑去分析现实教育、黏着于事实;亦不是拘执于虚构与幻想之中,只靠自我情绪而无视现实教育、脱离现实教育,习惯于糟糕地好高骛远与自说自话。有希望的关注意味着以一种完整的、超越的视野去思考,让人们从现实中找到希望或期盼。它不是以教育的当下、现代的面目来思索教育,而是按照教育更好地发展来把握教育。
为了现实教育的希望,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必须把“应该”和“是”统一起来。在《理想国》中,那个走出洞穴的有着超越性视野的哲人最终走入洞穴之中,将“美好的愿望”降落在现实之中。正是这个“下降”教育了这个哲人,使他有了“现实知识”与“自我知识”,不再那么“不顾现实”,他的知识因此更加成熟了。也正是为了那个现实,他下降到洞穴,他拒绝了“自我孤立”,避免了自我与现实的“天地两隔”。哲人苏格拉底的哲学存在于酒肆小巷之中,他的教育哲学是现实的教育哲学。《理想国》实为一本讽刺“那些不顾现实的理论家”的教育哲学著作,它是对空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教育的解构与超越。那个按照乌托邦主义构建起来的教育大厦最终是一种反讽,导致人的单一化与科学化之恶果。在《会饮》中,现实的具体的个人——阿尔西比亚得斯的最后出场预示着对苏格拉底疯狂阐述的纠偏和完善。在《斐德罗》中,那个关于爱欲的美好理想的谈论发生在城邦(洞穴)之外,最终,苏格拉底和斐德罗一起走回了城邦,因为“谁又能够离得开城邦呢?”苏格拉底的大部分对话都致力于教诲一种理性的“疯狂”:让那些“理想主义者”清醒一些,要有现实意识、现实感,要有实践之慎思。卢梭的《爱弥儿》重新思索这一问题,“理想主义”的教育体系带来的是惨淡的命运,它必须懂得如何在现实中生活[3]。
为了现实教育的希望,意味着教育哲学必须努力地而不是草率地去认识现实、理解现实。如果我们认同辩证法,那么,现实中就一定蕴含着更好的可能性,现实并不是被完全决定了的,现实有一个“现实可能性”寓于其中。现实与“发展”、“未来”相连,它不是一个“僵硬的事实”。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现实是一种“尚未”、“有待”、一个过程,因此,现实总能给予人以希望,它总是需要人们耐心地等待它自己最终得到破晓的时刻。“希望元素也是现实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4]“缺乏现实可能性的现实是不完整的,没有未来的现实是不值一瞥的。”[4]教育哲学反对简化过的现实,它思考的是更强大的现实,是现实过程想要的完美。这样的思索给予了它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使它总能够看到更多一点。更好地思考现实,必须成为教育哲学的一个品性。
为了现实教育的希望,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拥有希望,教育哲学研究者不能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者”,以一种消极的、不满的态度对待现实教育。教育哲学研究者需要理解的是,在我们称之为现实的教育条件下,教育中的希望是如何形成的。教育哲学研究者必须以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寻找现实教育的希望,使自己有一种对现实教育的真诚期待。尽管现实教育有可能在不断地令其失望,但教育哲学研究者也要以一种有希望的态度来对待现实教育。拥有希望,实则是拥有一种对现实教育的爱。
为了现实教育的希望,并非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提供给现实教育某种所谓的希望的方案,让现实教育符合其规范或安排;亦并非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希望现实教育达到某种未来的具体目标。教育哲学研究并没有这样的“权威”和能力,更不能强制现实教育。教育哲学研究是“产婆式的”、“启发性的”,其在于使我们看到教育的希望、抱有对教育的希望。在这里,教育哲学之“希望的功能”大于“希望的内容”。这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要求与自我限制。在柏拉图的教育哲学中,那个获得拯救的哲人并不能将“阳光”、“火光”(光明)带到洞穴中囚徒的面前,试图照亮洞穴的努力会弄巧成拙,他的工作只是教诲、指引他们渴望阳光,从而超越自身之现状。教育哲学研究的功效在于使我们有了对美好教育的热爱,如此,我们便不再局限于“坚硬的现状事实”。于是,现实教育便多了超越与崇高的因素。
为了现实教育的希望,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不仅必须拒绝绝望,而且必须学会希望。学会希望不等于学做白日梦,编制梦想;而在于更好地去理解希望,更深入地去思考希望,从而使得希望更加理性、更加完善,让这个希望能够有用,指向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学会希望要求教育哲学研究者要有清醒的头脑,让自己更加清楚希望的命运,不惧怕失败、歧视和他者的非议,在种种困境中使自己的希望更加明确、清晰、坚定。学会希望要求教育哲学研究应更少一些随意性、主观性,以沉思“现实之美好可能”为其基础,寻求现实中高于现实的东西。学会希望,就是学会思索一种现实的希望。学会希望,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将一种美好的可能性的观念深入其心。
三、作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之行为,它在于突破自身之局限以进行公共性对话,“介入”教育实践,让人们看到教育及其研究自身的权能,其目的在于使教育希望产生理性的力量,在于寻求更好的、更慎重的、有思的实践
希望不是逃避主义,希望预示着行为。希望不是概念性的,而是实践性的。教育哲学研究者不能成为一个庸人,从看来已经有些无法忍受的现实教育中隐退出来,拘泥于流行的专业性研究趋势,做一个为报社和升迁的撰写者,有着稳定收入的教授,使自己患上“直面教育问题的无能”。教育哲学研究者不能在一种安宁中、盛赞中获得自我认同,不能逃离到“看起来很美”的精神幻想之中,满足于在孤立的精神世界中遨游或自恋;或者,忽略这个现实教育世界,去热衷于一个曾经存在过的“黄金教育”。教育哲学研究不仅需要一种沉思理性,更需要一种参与理性。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它必须转化为一种希望的行为。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将一种为了美好教育而奋斗的精神贯注于其中。它必须让我们看到教育自身所具有的权能,并赋予这种权能以理性的活力,即用理性来激活这一权能,使其产生一种行动的力量。这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绝非一种狭隘的专业性教育研究,亦非一种所谓教育知识的探寻,而是对美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教育哲学研究者身上看到这样的实践,他们的行为服务于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追求,他们自身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和启动他人的力量,而非一个个犬儒主义者。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种自我的实践,涉及到教育哲学研究者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对于哲人苏格拉底和思想家孔子来说,他们的教育哲学就是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言行、生活表达自己的教育理念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需要承担更大的理论任务,让“斗争”与“人性解放”真正深入到人们对教育的观念之中。它使我们看到一种更加强大的教育,一个更加完整的教育。在教育服从于政治与经济的支配性权力的同时,教育能够起到一种抵制或反抗权力控制的作用,它能够成为我们争取正义、渴望真知和实践民主的一种有效力量。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教育必须成为一个实践民主和为了民主的阵地。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和把教育作为解放个人能力,朝向社会的向前生长的观点密切联系起来,杜威如是说[2]。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需要参与公共性教育问题的思索,在这个参与中使自己对于教育的理念能够成为一个公共性话题。这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让教育的希望转化为一种公共性的价值追求。这并非指将一个“私人性的”理想公共化,用这个理想来行使一种思想强制,而是指教育希望需要对那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有所担当,教育的希望必须饱含这些人类追求的公共性价值。如果按照杜威的观念,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实验民主。这也许要求教育哲学研究者绝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窠臼之中,他们必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类的命运、苦难与不幸,热爱正义、民主和自由,并能为了正义、民主和自由而寻求一种可能的实践。这也许要求教育研究者不能将自己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以获得专业性的认同、学者们的认同为其追求,他们需要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能够使人们去思想、去行为的理论力量。这就要求他们将思想作为一个“公器”,超越于佶屈聱牙的繁琐主义与在世界中摆弄、编织教育,探索与运用一种“公共性”的表达语言,而不是故弄玄虚地搬运“晦涩词”、“学术术语”把自己保护起来。教育哲学研究理应成为“最一般”的研究,它的思想的希望恰恰在于其是否能够“最一般”、“最普遍”,能够为人们所感触到,而不在于它是否使用了更加专业化的术语。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必须“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它没有那种摩西式或保罗式的启示权威,它真诚地寻求对话,在和他者的对话中与在认真对待他者的批评中获得一种对教育更全面的理解。这意味着它必须拒绝思想霸权,它必须和他者一起分享对一个共同的教育世界的理解和探索。因为只有在平等的对话中,那个“公共性价值”和共同的教育世界才能彰显出来。教育哲学研究认为,对希望造成威胁的绝非来自那些“更多地用麻烦制造谜团而不是驱散它的人”,而是来自那些“企图用自己的轭支配所有人的思考方式的人”[5]。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主动承认自己理解教育的有限性,它绝不能回避或杜绝争论,只与或者尽可能与那些和自己不会冲突的人们去交流。教育哲学研究者并不想要那种抹平异质性的、一团和气的兄弟般的亲热或亲密,他们想成为大家的真诚而有益的朋友,而不是哥们儿兄弟。教育哲学研究需要一个多元的他者的研究世界。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宽容品质。实际上,教育哲学研究者在许多教育研究者眼中非但不宽容,而且要求有些近乎苛刻。但是,这涉及到教育哲学研究者对其他研究的一种期待以及对自身作用的定位。尽管“对他者的期待”常常是一种危险、冒险的行为,会异化为强迫,但有时候“不冒险”比“冒险”更危险。教育哲学研究反对霸权、权威主义,但绝非表达一种虚无主义的存在,放弃对更好的教育的探究,使大家享受“你好、我好”的安宁快乐。“希望的行为”原本就表达了一个对“更好的”追求,表达了对现实的超越。让大家丧失希望,满足于成为友善的虚无主义者,对于教育研究而言,这也许是更大的危险。对话的民主化不等于麻木、迎合、容忍甚至纵容,对话的民主化在于“完善”、“超越”、“全面”,对话的民主化亦是一个“探究的民主化”。教育哲学研究需要一个多元的异质性的研究世界,但绝非放弃批判和对美好教育的希望与民主探究。杜威曾这样说自己主张的民主的教育哲学:它需要从那些在科学和探究方面有资格的人那里接受知识、原理,它也接受散布在人类经验中的好,但它却具有理智的权能,批判这些普通的知识、原理和自然的好[5]。也许,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苏格拉底的教育哲学是对话的实践,他热爱自由、民主、多元化的雅典社会生活,从未摒弃过雅典,认为自己是人们的“牛虻式”的朋友,而不是“投其所好”与“无关痛痒”的爬虫。教育哲学研究正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学会了如何做自己。
作为一种希望的行为,教育哲学研究并不能躲进书斋与咖啡吧之中,它必须有对实践的敏感力和丰富体验。这并非意味着它必须始终浸泡在实践之中,或者它放弃从书本中获得智力资源和启示。教育哲学研究看重问题和思索,但它的问题和思索是源于实践的,是关乎实践的。之所以教育哲学研究重视问题和思索,是因为为了更好地实践、保护实践,为了让教育实践成为一种有思的实践。教育哲学研究之所以被诟为“只说不做”,是因为它更需要一种谨慎的实践、理性的实践。对希望的坚守使它有着更强的实践欲望,正是为了实践,才使它拒绝风风火火的实践、异化的实践、被支配了的碎片化的实践。教育哲学研究绝不会放弃实践、不实践,不能实践的希望非但没有力量,还会使人们对希望失望或绝望。教育哲学研究要“介入”(而非简单地走入)教育实践,遭遇教育现实,思索它,发现与重构现实教育的希望。并能够在自我实践与教育实践中让人们感受到希望。这同时意味着为了希望,教育哲学研究必须反思希望,学习更好地希望。因为那些未经反思的、狂妄的、付诸实践的希望不仅会让人们对希望失望、绝望,而且会让人们对希望产生恐惧。
教育哲学研究要能够产生一种教育希望,要成为一种有希望的教育研究。它需要理性地实践这一希望,有希望地行为,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种实践的教育研究。它必须审视自己的存在状况,突破重围,使自己不再变得无人问津或多余。它必须批判现实,反抗霸权,在批判与反抗中抱有对现实教育的希望,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种批判的教育研究。批判、希望和行为必须成为一种教育哲学研究的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