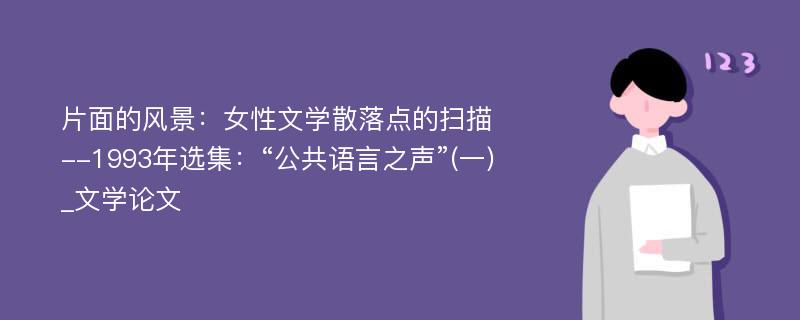
半边风景:女性文学的散点扫描——《1993:众语喧哗》选一(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边论文,风景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蜀中无大将 巾帼作先锋
“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人家对人类受难后孤苦情境的表达方式。”小林插嘴说。“纯粹二十世纪的,不流泪,不忏悔。哪像我们的作家,遇到点波析不是悲悲切切苦着个脸,就是硬挺着做外强中干的灵与肉的搏斗,累不累呀。”
“唉,什么时候,能让我们都脱去伪装恢复到原生态,痛痛快快做一把人就好了。”博士长叹一声。
“想返祖也没用,那块尾巴骨早让冷板凳给磨平了,长不出来喽。”王京东撇嘴。
“对你这号的,发多少指令也没用,脱掉表层的媚俗,里层还是媚俗。”
“对对对,我是媚俗里生,媚俗里长,媚俗里娶亲开俗花。只有博士您凌空出世,超凡脱俗,整个儿一个人间叛逆孙行者……”
“你们都快住嘴吧。”小林叫着。“都是俗人,谁能比谁雅多少?就这么个古老而又庸俗的话题,就引得你们吵来吵去,真够俗气的。都别争了,看月亮吧,这世界只剩她不媚俗了。”
我们都沉寂下来。远处广播局电视塔的灯光一闪一闪的。月亮依旧很不真实地浮在我们的头顶。一只猫悄无声息地从草垛上溜了过去。渠水好像是停滞不动了,仿佛在暗夜里谛听,期待着什么。
1993年第1期的《中国作家》,一份冯牧领衔、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文坛重镇,刊发一个鲜为人知的女性的一部中篇小说《白话》,描写一群到基层锻炼的硕士博士,无法真正地介入现实生活,也不能自主地选择和进行自己的研究,只能在百无聊赖中调侃生活,挖苦自己,发泄苦闷,打发光阴,又于心不甘,若有所待的荒诞却又真实的故事。我们很难揣测,编辑部的大小编辑们,是如何发现和推出这样一篇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字的,但是,它的作者徐坤,从此却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两三年间,先后发表《呓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游行》等作品,一跃而成为90年代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如果说,90年代产生了什么文学新人,那么,首当其冲的,一个是湖南的何顿,写《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和《我们像葵花》的那位就是,一个便是“白话”出一大批让人乐不可支又乐极生悲的文人小说的徐坤。
而且,徐坤的出现,似乎强化了我们对9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女性文学的日渐壮大,并且大有占据文坛半壁江山的气势——在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头货和辛辣明快愤世嫉俗的杂文领域里,女性似乎还不足以与男性抗衡,但是,在中篇小说这一长兴不衰的“当家菜”上,说女性作家已经领先,在散文天地里,女性散文也自成格局,撑起半边天,大约不为过分。在这一章里,我们就对90年代女性文学崛起的原因和态势,做一番粗浅的描述。
说我这悲欢说我这情
80年代的文学,曾经出尽风头,占尽春光。但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不可能无限制地澎湃下去,潮涨总有潮退时,加上突然事件对作家心态的影响,慷慨悲壮、激情奔涌的文学潮流,变得衰落和萧条。有人这样说,90年代初期的文坛,只有两部作品可言,一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一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话说得绝对了一些,却可以使人体会那种心灵的落寞。
说萧条,是说80年代的文学主潮,以思想启蒙和理性精神为涵,充满改变现实的激情的文学衰落了;但是,有失落,就有上升,有消退,就有替补,文化和文学是不会出现真空的。取代了壮怀激烈、宏伟崇高的悲壮感和使命感的,是90年代初期不期而然地产生的以闲情逸志、吟风弄月、品茶论酒、世道人情为主旨的散文热。
最初的缘起,也许只是几家出版社的出版策略。当代文坛一时间似乎失去了活力,许多知名作家又难以摆脱“自由化”之嫌;一味地保持激进态度,无论是谈历史还是谈生活,都显然不合时宜(请回想一下《坚硬的稀粥》的无头官司);于是,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徐志摩等现代作家的散文,被推向市场,并且受到意外的欢迎。
心潮跌宕的时代,似乎一下子消失,日常的、世俗的生活形态,自省的和内敛的情感方式,代替了外向的、热烈迸发的情感方式,那在80年代只占一个小角落的家务事、儿女情、琐碎生活和烦恼人生,以及在激流勇进的表层下面,那恒定的伦理内容,都集中地体现在《渴望》——一部产生相当影响的电视连续剧中。它或许是第一部定位于中年女性观众的文艺作品,并且是以具有东方女性美德的中年妇女刘慧芳为主人公。做出这种选择,策划者有自己的角度,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功,却具有多重启示:其一,它在不经意间,突出了性别意识,女性主演,又面向女性观众,这在当代文艺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其二,与男性所追求的不平凡的事业、大动荡的时代相比,女性更注意个人性的事务——爱情、婚姻、家庭、孩子,更看重个人性的生活——《渴望》恰恰是在大时代风雨的背景下,以刻画为丈夫、家庭、孩子等付出种种牺牲的女性。文革云烟可以淡忘,“留下真情从头说”,以往一向是以时代、民族、社会等为尺度,而把个人的命运和情感看得很轻很轻,在《渴望》中,却被翻转过来。普通女性,胡同人家,亲情、友情、爱情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风波,构成这部长达50集的作品的主调。
与此同时,一批女散文家,也占据了众多刊物的版面。她们以写身边事务、个人经历、童年记忆、儿女情长,情感波澜等见长,并且成为90年代初期文学的惨淡中一束温馨的花朵,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像唐敏的《女孩子的花》,池莉的《千古憾事》,赵玫的《四十岁女人的新梦想》,叶梦的《月之吻》,韩小蕙的《不喜欢作女人》,等等,都是抒写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怀的优秀之作。对当代散文研究颇深的刘锡庆在讲到女性散文的时候这样说:“男作家有男作家的优势,女作家有女作家的长处。人的大脑、性别决定了男女确实有些不同的优长,女性特别善于表达,善于裸露内心世界,情感比较细腻,男作家理性思考能力较强,更多关注社会,关注大的方面,对自己的关注比较少。女作家则对自我的情感体会比较细致,比较深,写的文笔也比较好,善于表达……我们现在的女作家,一批一批地出来,我觉得这很正常。‘十七年’时期,不准写‘小我’,写‘社会’写‘阶级’的多,而这不是女作家的所长。现在随着散文的定位,真正要通过自己的情感去表现内心,去折射世界,那么,女作家就显出了她们的优长。”其实,何止是“十七年”,就是80年代,“小我”仍然是居于次要地位的,80年代追求的是时代命题,宏大情感,关乎国家、民族的重大主题,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等,都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讨论问题,追求一种廓大的视野,一个重要表象就是以“大”字命名的文学作品特别多,比如《中国农民大趋势》、《世界大串连》、《兴安岭大山火》乃至《中国大流产》这样让人感到不伦不类的篇名。只有在从政治热情的低迷到商潮漫卷的惶惑,使得男性作家的社会关怀和理性思索一时陷入困境的时候,才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巾帼作先锋”的局面。当然,这也不排除那些在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女作家推出新作,不过,她们的作品,也显然有适应新的社会心理的改变,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苏叶的散文,带有江南女子的娟秀和精致,她的作品,在叙事抒情的结合,在结构的曲径通幽上,都可以见出其精心之处;在她的笔下,既有淡淡的沧桑感,更有对他人对生活的掩映不住的温馨。
她遇到一位被大火烧得容貌全非的陌生女性,便马上感到惶恐和自责,“我说着来意,似乎若无其事地望着这可怕的、被火舌舔卷了真实面目的脸。但其实我已神魂不定,我已无心关注朱契和他夫人的事,满心满怀只对眼前的这不幸女子充满了惶悚和难过。我惶悚于自己惊动了她,惶悚于自己在她眼前太过于健康。我难过的是谁都难以体验她克制着多少痛苦,多少无奈,克制着多少向往,多少寂寞!”(《烟语暗千家》)这种以己度人,却又最终感到无法体验到对方痛苦的心境,鲜明地表现出作家的情感深度;满腹感叹却又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则是她的许多散文的精到之处。《月照西窗》写刚参加工作的自己,在文革中因笔误而罹罪,这样的冤案和悲剧,可以说是司空见惯,难以有什么妙笔生花;被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所压倒的“我”,却突然注意到一片月光,并且沉浸于其中,得到心灵的解脱,焉能不倾其笔墨去描绘这明净的月色,并且再次传达出这种痛彻骨髓却若无其事的神态:“细细的眼泪像两条线,从腮上流下。我坐起来,倚靠着墙,看那月光,像一朵莲花,在满室暗涛中,斯文地浮游。温静的浅密色,像青苞米的穗儿,吐着还未成熟的消息。她轻轻地转过墙角,跃上门框,又跌落在枕畔上……”
苏叶还擅长于描写自然景物。她的《太湖烟雨》、《太阳湖》、《天子山之幻》等,都可以称作美文。她写太湖,是在夕阳残照里的壮丽图画,“我们站在高坡,向太湖投去最后一瞥。只见满眼光波鳞跃,一天斜阳醉红,浩淼的湖面,横着竖着几条细长的小船。一个打鱼人立在船头,向长天碧水抛去一张好大的黑网。它万孔千目,薄如蝉翼,烟一样没入淼淼水中……一时,我只觉得魂魄飞荡,痴呆中,满身裹的都是风,满手攥的都是夕阳的残红了……”(《太湖烟雨》)她写从湖面上升起的太阳,却又寓意着多情儿女的惨痛而决绝的别离:“太阳把刚强的头颅再一次浸埋在盈盈湖水,埋进清纯,埋进秀丽,太阳也沉迷啊!恨不能变一束七色花永留在湖底,又希望做一只大鹏鸟,把湖驮在自己的双翼,然而,湖怔忡着,黯淡了,面色灰沉,如失血的少女,睁大的瞳仁,散神地流淌着孩子般的求乞,太阳凝视着,凝视着湖,把逐渐变得冰凉的漾漾清波搂进自己的慈爱,而湖的泪水,就在日光猛地一震中,涕泗滂沱了。”(《太阳湖》)
斯妤的散文创作,也有过与苏叶相似的阶段,着力于表现对于爱、对于美的追求。她的早期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是对于少女情怀的抒发,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对于故乡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她带着脉脉温情去表现生活和大自然。她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等,在自然风光的描写上都是非常用力的,她笔下的月光,别有一番情致:“往回家的路上踱着的时候,偶一抬头,看见了极其动人的景致——半圈明晃晃的月丝,发着白金一样的光辉,静静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嵌在暗蓝色的天空!蓝天,银辉;月圈弯弯,天幕垂垂——多美丽的意境,多飘逸的月景!这月圈儿是这样细,又是这样柔,然而却明亮耀眼得令你不敢相信,几疑它是出现在你头顶的幻影!——看着它,我脑海中久久地浮起半只清辉四泄的白金镯子,眼前,则不时闪过一段亮闪闪的银丝线!”“我久久地在月下徘徊,久久不忍离去。我看着这绮丽的月丝终于渐渐丰腴起来,渐渐长成了半轮明月——是的,这月丝原只是残月的细细的外圈,刚才,是造物主划了火柴,先将它点亮了。”(《小窗日记》)
但是,进入90年代,斯妤的散文,出现一种新的面貌。对于人生的艰难困苦,现实的平庸猥琐,人性中冷峻严酷的感受,取代了她先前对于爱、对于美的孜孜以求。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于存在的荒诞感,对于“我是谁”的反省,对于个人内心的省视,成为她的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对于自我的关注,是90年代女性文学的基本倾向,那么,从对于生活的积极肯定到对于生命的怀疑和质询,则表现出斯妤的风格个性。她并没有诉说造成她的文风大变的原委——也许,同样经历过时代的风风雨雨的人们,也不需要更多的诉说——但是,却不难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那种内在的、铭心刻骨的悲怆。在《心灵速写》中,她感叹“柔情似乎渐渐被孤独与冷寂榨干。冷面冷心冷血冷泪”;在《流沙》中,她从时光的流转中领悟“有”的脆弱易逝和“无”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以及对爱情的幻灭感,“如果说爱情还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它是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它使你有机会看一个拙劣灵魂的全部表演,并且从中发掘人类的全部悲哀”;积郁的情感,投射到各种随机的景物上,从夏日的蝉鸣(《倾听蝉鸣》),到暖春的大雪(《我因为什么而孤独》),从北方的风雨(《风去风来》),到度假的海边(《在海边》),她的焦虑,因生存的虚无荒诞而产生的焦虑,萦绕胸中,盈满而溢。她反复地说,“丧失温馨情怀仿佛有一万年之久了”(《在海边》),“丧失温馨情怀其实并不久但感觉却有一万年了,一万年来只觉肃穆沉重只觉混沌迷蒙只觉雾气如网”(《烛光》),甚至,当别人称赞她是富于女性气质的作家,都会引发她的“不愿意生为女人”的叹息(《也是叹息》)。
也许是心灵的压迫过于沉重,迫使她寻找一种新倾诉方式,斯妤的散文中,出现了“荒诞系列”——表达的感觉是荒诞的,表达的方式也是荒诞的。90年代散文走俏,作家作品众多,风格各异,但是大都不脱离写实和实写路子,不知斯妤是否从鲁迅的《野草》、《狂人日记》中得到启悟,她采用了梦幻的片断、变形、怪异等方式,传达出她对生活的梦魇的恐惧和无法逃避的惶惑——《某年某月》、《并非梦幻》、《夜晚》、《真实梦境》等作品,可以看作当代散文的创新之作:
我惊恐地望着他们,他们却一齐吃吃地冷笑起来。你的戏该收场了!一个声音恶狠狠地掷向我。我的心猛跳了一下。我知道这是我的大弟弟。他曾经射杀了一群狼并且将狼心一个个掏出来吃了。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对待我。我说弟弟们别这样我是爱母亲爱大家的呀你们为什么这样围着我?你们还是不肯相信我是吗我要怎样才能使你们相信?那好我把心抠出来给你们看看这心是红还是白?
于是我把心提到嗓子眼,然后猛地一下将心抠了出来。我捧着自己的心感到一阵温热。我把这颗血淋淋活跳跳的心捧到每个兄弟的面前,哀哀地求他们明鉴求他们了解。
然而我的兄弟却一齐纵声大笑起来,他们不但笑着他们还往我的心上唾口水。
——《并非梦幻》
80年代初期,尚在大学读书的王英琦,就以电影剧本《李清照》而一举成名。后来,她转向散文创作。她的理性思索的深度和率真地表达自我的文笔,成为她独特的旗帜,迥异于别的女作家;但是,她的女性情怀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她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生活的选择,仍然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的;这二者间的张力,开阔了她的艺术空间,并且赋予她的作品以情致和力度。她似乎受法国的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波伏瓦——《第二性》的作者,萨特的终身伴侣的影响很深,在她的文字中反复地谈论过波伏瓦的思想和生平。她自己似乎也要像具有社会叛逆精神的波伏瓦一样,要同时在两个方面进行女性的抗争:一方面,她在诸多女作家中,对于时代的重要命题,是最为关注的,参与感最强的。另一方面,她又要在这个动荡和调整中的时代,对女性的命运表示特别的关怀。如她自己的自白所言,“我敢说我肯定类属那少数‘偏激地爱着与憎着’的作家——属于作家里的‘异端分子’。我的愤世抗俗和对绝对的追求,更带有女性的偏狭和‘吉诃德先生’式的盲冲。”
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似乎还没有看到别的女作家像她一样发表过直言不讳的观点(《沪上随笔》);对于处于文学论争的漩涡的张承志,赞扬者称赞他高举起批判拜金主义和精神沦丧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贬抑者指责他为文化冒险主义,像她这样做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却又具有相当透辟的分析的反响的女作家,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无需援助的思想——兼致张承志〈无援的思想〉》)。1993年以来,文坛上的论争层出不穷,但是,那好像是好勇斗狠的男人们的事情,女性作家大多是以恬静从容的心态,带着一份幽雅和宁静,作壁上观。只有王英琦以她的散文赤膊上阵,直抒己见。她称赞张承志说:“在张承志身上,你能嗅出‘狂飙突进’诗人的气质:你能看到凡·高和高更的偏执和极端,你能发现他像卢梭那样,善于把‘穷人表现的不同凡响’”。“在当代作家中,我还绝少看到内心搏斗有如张承志这样深刻旷久的,更绝少看到人格意识精神特征有如张承志这般执着专一的。尤其是他文化人格中那种异常深沉的‘宗教美’,确是很魅人的。”能作出这样的描述,已经是慧眼独具,要说出下面的话,则更需要深邃的思想能力:
体验过一切,对于张承志似乎是远不够的了,他还面临走向更高层次的理性成熟期(尽管他本身就是学者型的作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哲学气质理性色彩,但他的该死的偏执性格,往往又导致他的部分非理性)。
毕生忠于信仰是可贵的,但高于信仰之上的理性之花更其美丽,倘若没有科学理性的导航,则人和信仰便难能处于和谐之中,最终也难免出现信仰盲从,乃至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无需援助的思想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王英琦指出,“批判者最珍贵的品质是自我批判。张承志倘能在理性的深层次上,使二者更完美地统一,则他的人格魅力也就更其完美,张承志倘能在突破目前的心理重轭后,仍坚持自己的心灵,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命之路,则更显示出他主体力量的深厚和强大。”
如王英琦曾经讲到的,她自己和张承志在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但是,一心追求彻底的硬汉性格的张承志,在他的文章中,不能不总是做出某种强悍的姿态,难免有健美表演者四肢紧张地展现全身肌肉的表演性,而缺少必要的自省,作为女性的王英琦,在省察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又因为女性的柔韧和灵活性,而显示出适当的弹性和回转。她的散文,以豪放大气为主,却也可以深情依依,母性十足;她可以用波伏瓦的观点讨论妇女问题,写出《被“造成的”女人》,感慨“自从儿子入世后,我便不是我了”,批判男性的女性观,“人类历史已有千年万载保持男性支配男性优越的社会了,女人们的‘被造成’已非一朝一夕之功夫了。试看今日,女人不是仍被男人‘造成着’、‘雕塑着’吗?女人要想逃出男人的股掌,只怕生生世世休想了。”她也可以从儿子那里获得灵感,得到欣慰,把儿子比作一部“爱不释手,永读不倦”的书,以致“一切蠢血沸腾的文坛干戈,一切俗气冲天的营求头角峥嵘,都离我远去”,并且为自己从写社会写人生的豪放转向爱子心切的婉约辩护,“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没有微不足道的东西,家务事、儿女情尽可以放开胆子登上散文的殿堂”。(《生活的散文》)
王英琦还有一批散文是表达她对人类生存的哲学问题的思考的。她信守着女性的立场,但是,她的理性思辨,却没有为此而受到束缚。在《大师的弱点》中,她讲述雕塑大师罗丹和他的学生卡米尔的爱情悲剧。那位曾经被罗丹称作他“不朽的偶像”并且给他以很多艺术灵感的女性,在为罗丹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以后,最终离开罗丹,一个人在孤苦无助的状态中,在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并且在多年的苦难之后庾死在疯人院里,而罗丹此时却仍然在如云的美女陪伴下,继续自己的艺术创造,并且享受着极高的声誉。这样的故事,当然是令人在洒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谴责罗丹的绝情寡义的;但是,在思辨的时空里,王英琦由对罗丹的道德评价,进入对艺术创造与爱情追求的两难判断,“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不敢在爱情中追求人生的人,是人格不健全的人;在爱情中大胆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人,却又容易导向对人类文化总体上的不道德。或许,正是这种爱情与事业上的得与失,道德与不道德,痛苦与升华,才构成了一部可悲可泣的艺术史,才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灵与肉深刻磨难的艺术家。”在《求道者的悲歌》中,她把爱因斯坦后半生对统一场理论的求证,虽然倾尽心血却未能实现该命题的证明,这样在功利的角度看来是一无所获、枉费生命的悲剧。通常被理解为爱因斯坦的一个绝大错误抉择的事件,做出了新的理解:这是一次孤寂的、独立不倚的、漫长而又以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对人类理想秩序的存在为唯一内容唯一目的的追求,是通过伟大的失败而证明了的人类超越现实和功利性的永恒精神的英雄悲剧。爱因斯坦在统一场理论的证明上是失败者,但他所建立的人类精神的原则,却是人类的永恒财富。这样的哲理散文,可以说是王英琦对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贡献。
女性的天空
与女性散文的崛起相呼应的,是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依照我们的判断,女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中的实绩,是足以令众多男性作家相形见绌的。这里讨论的女性写作,已经不只是标明作家的性别,以取得特别的关照,而是指从中所表达出来的女性意识的自觉,并且产生出被称作私人化写作或者女性私人小说的作品。它的典型代表是近年活跃于文坛的陈染、林白、徐小斌等。
所谓私人化写作,批评家陈晓明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的妇女写作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女性文学’这门学科,所谓妇女写作归属于男性写作的总目之下,甚至完全被男性写作所淹没。尽管妇女写作的阵容庞大而有力,但她们一直是按照男性的格式,使用男性的语言写作。她们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直到80年代后期——我们称之为‘后新时期’,父权制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那种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非主体化的写作已经重新划定了文学的规则,这使女性写作可以比较自如去探究女性‘自我’的世界。一种真正反寓言的后个人主义式的写作开始酿就女性主义的叙事。90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调主观化视角,对于一部分女作家来说,那是纯粹个人的内心生活;而对于另一些女作家来说,则是个人与历史对话的一种姿态。不管如何,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人记忆,确实是进入90年代以来,文坛的新气象之一。
陈染、林白和小斌,这三位私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个人记忆”中某些共同的特征:她们和她们笔下的主人公,从幼小的年龄起,都具有某种自闭的倾向,又都感到了某些情感方面的匮乏——童心也罢,女性也罢,在社会生活中都属于弱者,都需要他人的保护和安慰,需要被别人所关心,但是,个人生活的环境,又是孩子所无法选择的。成长时期的心灵阴影,会笼罩一个人的一生,尤其是感情特别丰富的女性。因此,这成为她们的作品所反复倾诉的一个主题,并且推动她们向不同的方向去进行寻找,寻找自己所匮乏的情感的源泉。
在陈染和林白的带有很强的自述色彩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是残缺的家庭,父母亲的失和与离异,使她们很小就失去父亲,失去父爱,也失去女性生命中最早也最自然地接近作为男性代表的父亲的机会,失去与男性沟通的天然条件。母亲的工作繁忙或者感觉失察,又使她们对于母爱,也感到生疏和困惑,无法与自我以外的世界产生积极的联系。这样的个人记忆,在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都有明显的描写。
《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从小就感受到父母双亲之间的情感冷淡和对于自私父亲的厌恶,以致于仿佛不由自主地拿起剪刀,把父亲的裤子剪坏,对他进行报复。但是,这种恨,又是爱的情感的扭曲。正是这对于父亲的又爱又恨,成为陈染作品中的一种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作为父亲的替代物的、与作品中的青年女性相比,年龄要大出很多的男性,在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并且与女主人公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恋父情结与弑父情结,相反相成地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而且,这位男性,往往是以医生或者老师的身份出现——这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医生对于病人和老师对于学生,都是有关怀和爱护的责任的;在一个尽力把自己同社会和人们隔离开来的少女来说,医生和老师,又是她无法躲避、无法逃离开去,不能不与之打交道的极少数男性;医生需要接触病人的身体,老师则更像人生的第二个父亲,并且成为许多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的崇拜对象……于是,在《与往事干杯》、《嘴唇里的阳光》等作品中,是一个具有医生身份的年长男性,成为女主人公的爱慕对象,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和她的中学老师T先生,经过了相互对立和漠视以至仇恨,却又最终转化成为情人关系,其奥秘就在于此。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同样写出童年时代因父母离异给女主人公造成的感情创伤。长大后的多米,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作,而且,哪怕是在白天,她都习惯以厚厚的窗帘把门窗都堵起来,不透进任何光线,然后在灯光下写作——这是典型的自闭症,把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绝,然后向自己倾诉自己的情感。当然,人不可能完全遗世而独立,尤其是女性,她总是需要他人的支持,他人的关心。对于男性的失望以致于敌视,在林白那里表露无遗,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最后是为了解决一个户口问题而漫不经心地把自己嫁给一个年龄足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男人。在《致命的飞翔》中,在《猫的激情时代》中,北诺和猫两个女性,虽然她们都是有求于人而不拒绝以自己的肉体同男人作交换,却都因为不堪忍受男人的兽性虐待而杀死凌辱她们的男子。两性之间差距和敌对,迫使林白转向对于女性之间的情感、抚慰和帮助的关系的描写。这种同性恋或者准同性恋的倾向,在陈染那里也有所表现,不过,如同她在对男性的向往中是寻找父爱一样,陈染的女性之爱,也更多是母爱的一种补偿,她总是写一个女孩与一个年长寡妇之间母女与情人兼而有之的关系。林白笔下的女性,似乎更加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那在性格上更强悍的一方,则是要取男性的角色而代之,自觉地充当保护人。《回廊之椅》中的朱凉和七叶,娇弱的少奶奶和服侍她的身强力壮的女佣之间,“很难想象有哪两个女人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某个在西方通行的合法的词汇”——林白特意提示读者说——朱凉不只是在洗浴中要得到七叶的抚慰,她在午睡的时候,也要七叶守在她的身边;而七叶,在朱凉死去多年以后,仍然保留着对她的忠诚和深情。《瓶中之水》是同一主题的延伸,对于女同性恋者在相互间的处境、地位上做文章:生性孤僻的二帕,尽力躲避着来自同性的友谊和关怀,也躲避自己天性中具有的同性恋倾向;但是,她还是和主动关心她的意萍要好起来。然而,在许多事情上都一再忍让她的意萍,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优越感而严重地伤害了她,导致了两个人的关系破裂。那么,已经走上这条路,还能退得回去吗?这大约是林白下一批作品要解答的问题了吧。
自闭性的倾向,情感创伤的印记,在徐小斌的作品中同样存在。在她的作品中出现的,是作为既不美丽又不会讨人高兴的妹妹的主人公,在少年时代与得到父母宠爱的姐姐的对比中所感到的精神上的被遗弃,以及烧香拜佛的外婆带给她的神秘压抑的宗教氛围,像《末日的阳光》和《敦煌遗梦》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样。她的作品,同样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像《双鱼星座》在结尾处所嘲讽的那样,“也就是在这一瞬间,天边的一扇门悄悄地开了,上帝本人探出头来,上帝看见了那个不安分的夏娃的后裔。上帝隐约记起在伊甸园里夏娃的恶劣表现。为了偷吃智慧树的禁果,上帝给了她最严厉的惩罚,让她妊娠,让她流血,让她忍受比男人大得多的苦痛。但一切已经迟了,因为她已在男人之先吃了那禁果。上帝想到这里不免有些沮丧,他不再看那个不自量力的女人一眼就关上了天门。他把天门向女人永远关上了。”
不过,比起陈染和林白,徐小斌要大了几岁,她当过北大荒知青,有知青一代的命运感和更多的社会经历,正是这些经历,使她的眼界要比陈染、林白开阔许多——陈染的人物,总是恋父和恋母,林白的作品有同性恋倾向,徐小斌呢,似乎对于正常的两性之爱更加投入;尽管说,她笔下的女性,终归难以实现自己的爱情,但是,这对于克服其女性人物的自闭症,总是有所帮助的。陈染和林白的作品,同为过浓的精神自传性写作,而难免于某些情绪和意象的重复,作品中的环境空间,也较为局促,仅仅限于女主人公所存在的一座楼、一间房屋;徐小斌的作品,却既能抒写自我的情怀,也能构造传奇性的故事,既能在现实的氛围中铺排人物情节,也能在亦真亦幻的情境中去展示某种怪异;而且,她对于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民俗图画的展示,以及她在艺术与生活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都丰富了她作品的内涵。三个女性作家都不乏讲故事的才能,以明显的虚构方法讲故事,但是,陈染和林白,似乎在努力描棕一种虚构的现实,徐小斌却擅长于进行一种夸诞和变形,与斯妤的荒诞系列散文,同样具有某些怪诞色彩;在她的作品中,女巫的气息是最浓的。人们的存在和活动,仿佛都有特殊的意示,都想要印证什么同时又摆脱什么,从而造成一种费解的神秘感。
《敦煌遗梦》中的肖星星就是如此。她因为在梦幻中预感到一个大男孩子的死亡而前往敦煌,带着朦胧和无法把握的情致,是为了证明这梦境的实有,还是为了用事实否定它?在敦煌,她先后遇到两个富于魅力的男子,一个成熟稳健的中年和一个热情似火的青年,并且被两个男子所爱,但是,有意追求爱情的她,却又因为各种原因,逃避开去,再次远走他乡——远走他乡,也成为在爱情之外,进行解脱的另一种方式。肖星星从京城到敦煌,从敦煌到印度。在《双鱼星座》中,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卜零,则对古风犹存的云南边疆佤族山寨产生强烈认同。卜零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在爱情上又遭受挫伤,她把这些归诸她的血缘,把自己设想为没有被平庸的现实磨灭生命灵性和浪漫气质的少数民族后裔,而在佤寨感到“他们便是自己遥远的族人”;当她在现实中陷入内外交困时,她又重返佤寨,去寻找超度苦难的力量——这也许过于缥缈,却扩展了作品的生活蕴含。
从这些区别来看,徐小斌在私人化写作上,没有陈染和林白那样纯粹,她有着兼顾现实生活的一面;因为她的驳杂,在谈到女性主义写作时,人们更多地提及的,也是陈染和林白;不过,如果把旗帜和口号看得轻一些,而更重作品实际的话,那么,徐小斌的意义,大约不在陈染的林白之下。(待续)
标签:文学论文; 张承志论文; 散文论文; 小说论文; 女性文学论文; 一个人的战争论文; 风景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