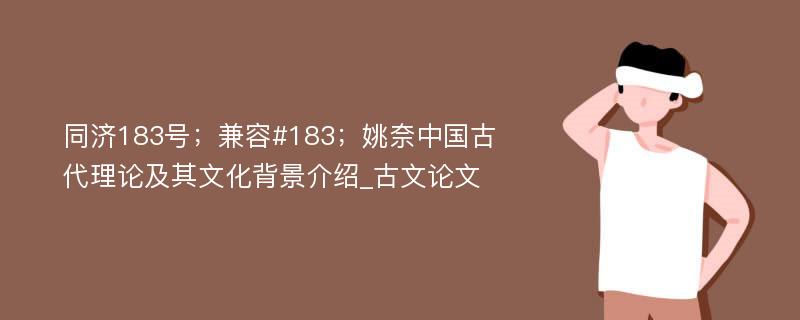
兼济#183;兼容#183;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古文论文,文化背景论文,理论论文,兼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4;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1999)06—0109—05
中国的散文发展源远流长,但作为艺术散文的自觉创作,则是自韩柳古文运动始。韩柳虽以其卓越的艺术实践,完成了对散文这种艺术形式的确立和建设,但他们对这种新文体的艺术特征,尚乏清晰的认识,因而也就提不出明确系统的艺术理论。归有光虽在散文创作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闻一多语),但也终未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桐城派”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终结,其在创作方面虽是强弩之末,无法与唐宋古文运动比拟,但在散文创作艺术理论方面,却是集大成者。它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论,尤其是对唐宋八大家和归有光的文论,加以总结和发展,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散文艺术理论。仅此一点,就值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书一笔。可惜学术界过去对桐城派文论视之过低,直到近年方有好转。笔者认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以后,深入到散文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散文艺术的总体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交融。由艺术技巧论,到艺术意境论,再到艺术风格论,这就是桐城派散文艺术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这是拙著《戴名世论稿》(黄山书社1985年版)中的一段话,旨在勾勒戴名世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曾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限于篇幅,对这一“发展脉络”本身却未作详细论述。为补此阙,笔者对方苞散文艺术技巧论、刘大櫆散文艺术意境论已分别撰文言之,此篇则对姚鼐散文艺术理论略事解说,以了前愿。
姚鼐散文艺术理论之核心自然是其风格论,但风格并非空中楼阁。无有效的创作途径,创作的不是真正的艺术散文,更无散文之艺术风格可言。因而在姚鼐,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逐步升级的三个台阶,是层层递进的一个较完整体系。遗憾的是,以往的有关论著对姚鼐文论似未作为一个完整之体系进行梳理,而多为零散的叙说,从中国古文论研究之先驱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到近来多种文学理论批评史莫不是如此。因而拙文论述虽极其简略,却力图着眼姚氏文论之体系。
一、三者兼济的创作论
姚鼐创作论的核心为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他在《述庵文钞序》中有云: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据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据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之贵。
姚氏生活的乾、嘉之际,汉学与宋学各立门户,相忤甚激。两派虽都宗经崇儒,但又都轻视词章,如姚氏所谓“言义理之过者”,其空疏不文为宋学之弊;“为考据之过者”,其繁碎不当为汉学之病。两者均属“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对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处理不当。方苞之“义法”说也有这种不当,所以姚鼐说:“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鉴于此,姚鼐则主张在古文创作中,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收并用,以期“能兼长者之贵”。
就义理与词章的关系而言,前者为精,后者为粗,精摄于粗,而粗饰于精。姚氏有云:“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与翁方纲》)因而为文不可单纯“饰其辞而遗其意”。但为文若徒有精干主躯而无粗枝大叶,也会“索然无生气”,因而姚氏又云:“达其词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复汪进士辉祖书》);古文词章美者,“即之而光升焉,诵之而声闳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气勃然动乎纸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异趣而横出焉”。只有这样,才能使古文获得艺术素质,以自立于文学之林。
就考据与词章的关系而言,姚氏既反对繁琐考证,又反对言之无物,他说:“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又云:“以考证累其文者,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议证考核,其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正是文之佳处。
姚氏之“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说,就作家的修养而言,是要才、学、识俱佳;就古文的创作而言,是要三途并进。有人称“义理、考据、词章”为古文的三要素,也有人仅视之为“学问之途”(当然也不排斥“学问”之途,此留待后文言之)。我则不以为然,而以为其为创作三途径或程序:确立命题、发掘素材、行文章法,故称之为创作论。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惜抱自守孤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是对其创作论的赞赏。
二、诸体兼容的文体论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可见有无精当的文体论,有关古文之命运;而精当的文体论,源于正确的古文观念。
姚鼐的文体论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其一,以“为用不同”,分古文为13类,即: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姚鼐对每类文体的源流、功能及其规范都有简明的论述,如在论辨类中指出,其“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其流则“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苏洵)杂以苏(秦)、张(仪)之流,子瞻(苏轼)兼得于《庄子》”。碑志与杂记虽均属歌功颂德,但有记事大小与是否施之金石之别,这样就各司其职了。序跋与赠序,似皆为序类,但前者系对正文“推论本原,广大其义”,后者则为“致敬爱,陈忠告之谊”。奏议自汉以后虽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却与书说有别:“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书说)。”是为各有规范。就具体类别而言,姚鼐枉正了欧阳修、茅顺甫对墓志、墓表司职不明之误,纠正了司马迁、刘向对辞赋虚实不辨之弊,使各类文体有了严格的界说。就整体而言,姚鼐的13类分法不简不繁,既不像《文选》那样“分体碎杂”,他不录子部、史传以及六朝古文,以纯洁古文家族(钱基博云:“此分文体为十三类,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视《昭明文选》分类碎琐、立名可笑者,为简当矣。”);也不像方苞《古文约选》之偏狭(方仅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且谓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垂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不可入古文)。姚鼐不墨守唐宋古文的樊篱,而对上自秦汉下迄本朝的古文都兼收并蓄,甚至对诗歌化的散文如辞赋,以及小说化的散文如韩愈之《毛颖传》等,都纳入古文王国。使后学既有章可循,又能自由驰骋,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诚如钱基博所言:“此书之善在于既分摄其英华”又“历代文章质变,各家面貌风格,罔不可以分别体认”,“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1](p.114)
其二,以“所以为文”,立古文“八要”说,即“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其精者指作品的内在因素:神(神韵)、理(事理)、气(气势)、味(韵味);粗者指作品的外在形式:格(格局)、律(法度)、声(音节)、色(文采)。只有精粗结合,内在因素与外在形式相辅相成,古文才能成其为古文。这八要素不仅综合、发展了方苞之“义法”说、刘大櫆之“神气”说,而且校正了他们各自的偏颇。一般论者多易舍粗而取精,忽视艺术形式,姚鼐则认为“诗文,皆技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与翁方纲》)13类中的文章,都以此八要素组成;“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因而以此八要素为标准,对13类中文各有取舍。如奏议、诏令、箴铭等,似难成艺术散文,但由于它们或“诵忠而辞美”,或“意与辞俱美”,或“辞尤质而意尤深”,符合上列精粗八要素,所以不仅可称为艺术散文,而且列入古文规范。而“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如此取舍,方能使古文得其“当”。
姚鼐将13类与八要素相结合,而成《古文辞类纂》,收文700 余篇,横呈古文家族全貌,纵显古文发展全程。其“蒐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不仅是姚氏文体论的实践产物,更成为桐城文派延绵久远、传薪接火之圭范。曾国藩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曾文正公杂著上》)吴汝纶更说:“姚选古文为古今第一善本。”(《与裴伯谦》)并一再倡言,尽废古籍,惟保存《古文辞类纂》一书为国粹精华。
三、阴阳兼美的风格论
古文既有八要素,其精者构成古文内在美,其粗者构成古文形式美,两美并存而构成古文风格美。姚氏将古文风格分为两极: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复鲁絜非书》)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虽为古文风格美之两极,但在姚氏看来,这两者非但不相互对立,反倒辩证统一。姚氏虽未挣脱阳上阴下的传统观念,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以为“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阳刚阴柔并行而不偏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皆不可以言文”:损害了和谐就无所谓美。他所说的“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遗意,有若自然生成者”,就是阴阳相济、刚柔浸透的自然中和之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仅是古文风格美最基本的两极,而非古文风格美之全部。在姚氏看来,由于阴阳刚柔的配伍不同,浸透不齐,偏胜不一,又能生成多种多样风格的古文。他说:“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
尤为可贵的是,姚氏不仅对古文风格美之两极和它们的交融、变化有精湛而形象的描写,更对其起因与形式有着较正确的论证。他说:“文章之原,来乎天地。天地之道,阳刚阴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而作家得乎阴阳刚柔之精而为文,“必由其人胸臆所蓄,履行为止,率然达之翰墨,扬其菁华,不可伪饰,故读其诗如见其人”。简而言之,“其诗即其人”;详言之,则风格即由自然因素(天地阴阳)与社会因素(作家其人)、精神修养(胸臆所蓄)与生活实践(履行所止)相结合的产物。
姚氏“阳刚阴柔”说,远可追溯到《周易》与《文心雕龙》,如《易·说卦传》云:“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文心雕龙·镕裁》云:“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定势》云:“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近则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和发展了方、刘之论,如刘大櫆有“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之见,近似阳刚阴柔说;方苞有“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质相类”之论,也近似“其诗即其人”说。只是他们都未将自己的观点系统化,亦不似姚鼐论述精湛。因而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阳刚阴柔”兼美的风格论,是姚鼐之首创。姚氏此论亦为尔后的桐城派作家广为接受,影响极大。如曾国藩之“古文四象”、“八字之赞”;张裕钊以“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与“味、韵、格、志、情、法、词、度、界、色”20字分配阴阳,均为姚氏之论的推衍,然他们化系统为琐屑,有失其精彩。
四、了得一个“兼”字
姚鼐古文理论之特征与魅力显然一个“兼”字:兼济的创作论、兼容的文体论、兼美的风格论,真可谓了得一个“兼”字。然这“兼”字的获得,自有其文化渊源。首先就师道而言,姚鼐为学是私淑方苞、亲炙姚范、刘大櫆,可谓转益多师。姚鼐有《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言及与方苞的关系,说:
计鼐少时,亦与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宁,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年乡试,一至江宁,未及谒,其后遂入都。又数年,先生没,遂至今以不见先生为恨矣。
可见姚鼐并未曾见过方苞,只是私淑之。而姚鼐之父季和同伯父姚范,皆与刘大櫆友善。姚范曾为翰林院编修,以贯通经史著名,于诸子侄中独爱姚鼐,每谈必令姚鼐傍侍,稍长即授以经学。姚鼐从18岁开始同时从刘大櫆学诗与古文辞,他有《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云: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
刘氏亦有《送姚姬传南归序》称道姚鼐:“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足见师徒情深。
姚鼐生活的时代,汉学、宋学壁垒森严。姚鼐却无门户之见,他曾欲拜汉学大家戴震为师,不意遭拒。戴震有《与姚孝廉姬传书》云:“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作为汉学代表人物戴震婉谢姚鼐,是视之为宋学中人,道不同不相谋。然姚鼐即使未入戴氏之门,但对戴氏之治学方法却能“兼收之”。戴氏治学之道:“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文章。”(《戴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对此,姚鼐能融合并加以改造以为己所用。姚氏云:“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相对而言,戴氏重考核,轻文章,以为“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有所偏废。姚氏则倡三者统一,相得益彰。诚如曾国藩所云: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以义理为质,而后词章有所附、考核有所归。(《欧阳生文集序》)
其次,就其司职而言,姚鼐乾隆二十八年以32岁中进士,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然到馆不到两年,即于冬季辞官归里。其辞官的原因是与同僚意见不合。姚莹《惜抱先生行状》云,当日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辩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馆内戴震、纪昀为著名汉学家,视姚鼐为宋学派代表而排斥之。叶昌炽云:“乾隆中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校书之列,其拟进书题,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文述(纪昀)不同,宜其枘凿也。”(《缘督庐日记》卷四)姚鼐自43岁乞归,至85岁去世,执教鞭长达40多年。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实则淡泊功名,只以文章传授弟子。以“惜抱”自名其轩,即取陶渊明《饮酒》“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诗意,作为精神写照。
以教书为终身职业的姚鼐,有憾于“四库全书”馆内门户之见,长期在其教席上坚守“有教无类”之准则的同时,对大江南北之文化从善如流,广为吸收,表现为极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这对其文论也有积极影响。如其在扬州梅花书院执教时,受“扬州八怪”遗风余韵熏陶,而提出“阳刚阴柔”说。因为艺术大师郑燮就有近于“阳刚、阴柔”的艺论(参郑燮《赠潘桐冈》诗)。
再次就其学风而言,姚鼐所处的乾隆时代是个“十全大武”的“极盛”时期。学界虽有汉、宋之争,朝廷却采取汉、宋调和政策。如《清史稿·儒林传序》云:“崇宋之性通,而以汉儒经义贯立。”文坛虽派别林立,但朝廷所要求的还是高文典册、炳炳琅琅的大块文章。姚鼐虽长期远离庙堂,却不能不受由朝廷倡导的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固而姚鼐为学就不同于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而能“上究孔、孟,旁参老、庄,百氏之书,诸家之作,皆为咀含其精蕴,而外沈浸其辞章。是以诠经注子,纂言述事,刻峭简切,和适斋庄。淡泊乎若无酒之絪蕴,希夷乎若古琴之抑扬。浏然而来,若幽泉之出于深涧;飘然而逝,若轻云之漾于大荒”(管同《因寄轩文集·公祭姚姬传先生文》)。其为文也不同于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而认为“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窥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而操笔而使吾手与吾所见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与张阮林》)。以思深功至为根本,抒写性灵,法有定而又无定。有定者,为一派之总脉;无定者,方显示作家之独创。
可见,姚鼐有开放之胸襟,有广阔的视野,转益多师,虚怀若谷,为学为文故能兼收并蓄。唯其能兼收并蓄,姚鼐才能继方、刘之后成为桐城文派之集大成者。姚莹《惜抱先生行状》云:
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为文章正轨,刘海峰继之益振,天下无异词矣。先生亲问法于海峰,海峰赠序许之。然先生自以所得为文,又不尽用海峰法。故世谓望溪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能,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刘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称桐城云。
可见姚鼐既兼方、刘之长,又能超越之,如吴德旋《古文绪论》云:“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刘海峰,而好学不倦,远出海峰之上,故当代罕有其伦;拣择之功,虽上继望溪,而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又望溪所无也。”而桐城后学多出姚门,桐城文派之门庭实亦自姚鼐而日益扩张。曾国藩于《欧阳生文集序》中更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田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金天翮在《皖志列传稿》中更突出了姚鼐作为通博之鸿儒、文章之泰斗的形象。他说姚鼐“宾接后进,气凝色怡,士守其教,咸端悫有文。桐城家法,至是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然鼐于文章、经术、义理之外,诗词书画,无不精究,尤精力之过绝人”。
凡此种种,足见那了得的一个“兼”字,不仅是姚鼐古文理论特色与基础,也造就了姚鼐作为一个集大成古文家的形象,更为姚鼐在桐城派发展史上争得一席何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1999—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