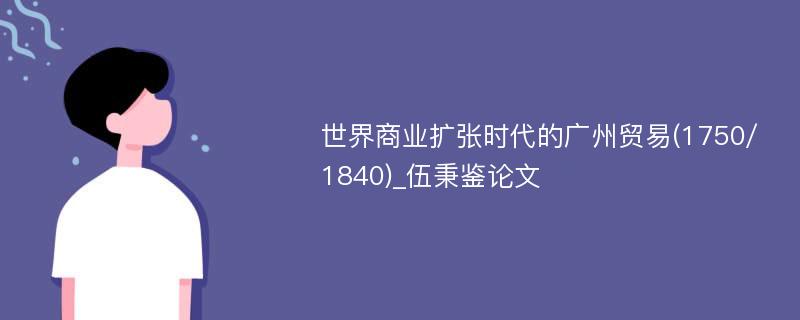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时代论文,商业论文,贸易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2-0105-08
由于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通,揭开了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海商的东来,传统南海(注:南海是中国五大海中最大的一个,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占五大海区面积的74%。中国古文献中的南海,初无明显的范围。元、明之际,才有东、西洋(东南海、西南海)之分。以文涞为界,其东为东洋(东南海),其西为西洋(西南海)。西洋(或称大西洋)有时也包括印度洋与东非沿岸。本文所说的南海是指明清时期习称的范围。)水域的贸易网络,已经西越印度洋,延及大西洋,东通太平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初步形成世界性的海洋贸易圈。
如果说16世纪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形成的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全球化商业扩张的时代,是一个商业竞争趋向激烈的时代。这一新世界贸易格局的出现,对于作为传统海贸中心的广州,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在全球化商业扩张时代形势下,广州贸易所作的回应。
一、南海贸易格局的变化
广州古来就是中国海贸的中心(除元代一度为泉州所取代外)。明代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明确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流求,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就是说,广州被指定为南海各国朝贡贸易的港口,所管辖的范围也最为广阔。南海贸易局势的变化与广州贸易息息相关。探讨广州贸易时,当应从南海贸易谈起。
环列南海的“南海诸蕃国”,已为华人所不断移居,明代更成为中国商民出没的地方。华侨在东南亚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海商于是16世纪先后前来,改变了南海政治与贸易的局势。
首先,中国与南海诸蕃国间传统的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华商的贸易网络受到冲击、削弱和破坏。葡人于1511年攻占满剌加(今的马来西亚,明末称麻六甲),是西方势力东渐的滥觞,也是宗藩关系受到冲击和破坏的开始。作为明帝国的藩属国满剌加,陷落达十年之久,明朝廷才得知。明帝国也曾严词申斥葡人,责令其退出,返回故土,并下诏谕近邻暹罗(今的泰国)诸夷救援,但未曾取得任何效果。从此起,明帝国与南海诸蕃的宗藩关系日渐式微,在南海的政治势力逐渐退出。尔后南海诸藩先后陷为西方的殖民地。
葡人继而前来中国沿海活动。先是勾同中国的海商、南海诸蕃的一些商人在杭州湾外的双屿岛建立国际性的市场(1548年明朱纨发兵捣毁),继而以租借占据澳门作贸易据点,并建立东亚与欧洲的贸易网络。
继葡人之后,西班牙人于16世纪中叶占据菲律宾,以马尼拉为贸易基地。16世纪末,荷兰人(16世纪时其领土包含今日的比利时、尼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兰德斯一带)也来到吕宋(菲律宾),由于遭到葡、西的抵制,于是荷兰国内的各公司联合起来,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并配有强大的武装舰队,以加强其在南海的竞争力。它极力排斥葡、西势力,甚至进攻其贸易殖民基地。17世纪初营建巴达维亚城(雅加达),作为为殖民统治的据点。继而侵占锡兰,并从葡人手中夺取麻六甲。又占据台湾,以大员(即今安平)作为贸易据点(1662年为郑成功所驱逐)。巴达维亚和大员两据点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奥援。继葡萄牙人之后称雄于东亚海域。
英国1600年组织的东印度公司,也前来加入南海水域的商战。由于其资本和武装力量处于劣势到17世纪20年代,把重点转移到印度和波斯。唯留下爪哇的万丹作为在南海的基地。
前来南海水域的葡、西、荷和英等国的贸易公司,不仅拥有以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的舰队,而且有本国政府作其政治与经济的坚强后盾,有垄断某一地区贸易的特许状,甚至享有殖民地军事和政治的全权。他们凭借其船坚炮利,一方面主张公平的贸易,另方面遇到失利时,则拦截掠夺海上商船,甚至烧杀掳掠沿海居民,无恶不作。他们在南海地区建立起各自的殖民基地,实行殖民统治,一改东亚海域由华商独领风骚的传统贸易局势。再是,西方各国海商的先后到来,导致出现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此时南海贸易的网络,既连结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又重新伸展到永乐之后中断往来的印度洋,并扩及大西洋,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各国间都需要交换各自的产品。荷兰人说:“中国人需要我们的白银,正如我们不能没有他们的商品一样。”(注: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斯》,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第216~221页。)可以说,16、17世纪的世界已经开始趋向一体化。
如果说16世纪是海洋时代,是世界趋向一体化的开端,那么,18世纪是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也是世界一体化加深而出现的贸易重新改组的时代。
1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是伴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取得成功而出现的。产业革命为市场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产品,迫切需要推向市场。从英国1700年至1800年一百年间的出口商船吨数、输入额和输出额成倍地增加中,可以看到产业革命带来的后果——工业产品对市场需求的迫切性。据统计,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1700年为31万多吨,1800年增至192万多吨,增加了五倍多;商品输出额,18世纪的首10年,为6至7百万磅,1800年却达到4187万多磅,增了约6倍;商品输入额,18世纪初为4百万磅,世纪末已增达约3千万磅,增加了6倍多。如果置于坐标图上,可以看出,这三项指标都在扶摇向上,世纪末的20年间更是几乎直线上升(注:参见(法)保尔.图芒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6~78页。)。18世纪的南海贸易,除老牌的葡、西、荷等国商人相互竞争外,又增添了英商这一强劲的对手。跟踪而来的还有欧美其他国家的商人,如法国、丹麦、瑞典和刚刚建国的美国等。此时,南海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化,而且更加带有疯狂性与倾轧性。
商业是以国家的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商业的竞争力。自重商主义流行以来,商业扩张的胜利就是市场、资本和政治权力结盟成功的结果。商业资本的张缩是与其国家权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从西方各国海商在南海势力的消长与其国家实力的隆替相一致,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取得产业革命成功的英国日益强大,其在南海贸易的地位也随之而与日俱增。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创立伊始,就以印度为掠夺对象进行蚕食。18世纪30年代起占据了马德拉斯等三个管区,并在其他地区建立了商栈。18世纪末,印度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有了印度作基地,更可以加强对南海水域作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756年,英商的通译员洪任辉(James Flint)秉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旨意,乘武装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等港口,提出诸多横蛮无理的要求。基于历史上“双屿岛”与“澳门”由洋人引诱而聚集成市的历史教训,洪任辉的举动引起了清朝廷的惊惕。为了“防微杜渐”,又顾及广州僻处南疆,其出海孔道的黄埔、虎门,“在在设有官兵”,可以保证安全,所以于次年,亦即乾隆22年(1757年),下诏令:“将来止许在广州收舶交易”(注:《高宗对训》卷281,“饬边疆”; 《东华续录》,乾隆,卷46。)。从此,只允许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不准再往其他三口(厦门、宁波、上海)从事商业活动。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规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
二、“独口通商”与广州贸易
广州被指定为中西贸易的独口通商口岸的由来,已简述如前。此事常为中外学人所称引,几乎已经成为常识。由于引述的太多,有时望文生义,以为其他口岸都关闭了,或认为东亚各国也一样止许来广州口岸通商。其实,独口通商仅限于对欧美各国商人而言,并不禁止他们在南海地区殖民地的商人前往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口岸贸易。
关于“独口通商”规定的利弊及其后果,尚待深入的研究。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对广州贸易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中西间的贸易,原主要是在南海区域内西方各国的殖民地或商业据点进行的;实行“独口通商”后的广州,成为中西直接贸易的市场。中西贸易也从原来的以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了。
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繁荣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各国来船显著地增多。据文献记载,在独口通商前10年,每年平均约近20艘,尔后不断上升。1833年竟达189艘。据统计,自1759年至1833年共来船5072艘,平均每年达67.6艘(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卷24,“市舶”。)。
18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中西贸易而言,主要对手是英国(包含其殖民地印度)。早在18世纪初,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主要职责的英东印度公司船舶,每年往返于中国东南沿岸港口。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的第3年(1759年)之后,英东印度公司每年来船约10艘左右,1770年以后有时增至20艘上下,1786年激增至62艘,1883年达107艘,其中港脚商人(散商)船82艘。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其来船之多却仅次于英国,跃居第二位。中英间的贸易:输往英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左右,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占总入口额的80~90%。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英属殖民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每年为3200万美元,而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1100万美元。另据同时代人菲普斯(Phipps)估计,认为中国与英国贸易达4445万美元,英属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为2743多万美元(注:穆素洁: 《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两者说法,对贸易额的估计差距甚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英国本土没有足够的受中国接受的商品与中国交换,只有以其殖民地印度的产品来与中国作三角贸易,而且以印度产品为主。
其次,广州出口产品多样化,增多商品种类。虽然不乏地方性的特产,但更多更大量的是普通的农产品。种类达80多种,其中以茶、生丝、绸缎、土布、糖等为主。从中国传往欧洲的饮茶风气,到18世纪已经养成习惯。从18世纪20年代起,茶叶已取代传统的商品丝货的地位;成为贸易额最大的单项商品。18世纪80年代,茶又成为美国的重要饮料,其需求量益增,需求量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土布(又称南京布)和食糖在18、19世纪之交以后,日显重要。从与英国的贸易看,土布的贸易额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糖和糖制品,也成为中国出口到英属印度市场的主要商品。早在1716年,马博罗(Marlborough)号船货的清单,糖和糖制品是主要的商品。前往印度的船只除载有数十万磅的中国糖(在大多数船的载量平均为400,000磅至800,000磅之间)之外,还装载有铜器、白铜(在印度用于铸造船的一种铜,锌和镍的合金)、水银和明矾。至1833年,糖占贸易总额将近四分之一(注:穆素洁: 《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各国用来与中国交换的产品主要是棉花,尤其是英属印度产的棉花。其次是英国的毛织品和其它工业产品。18世纪,广州贸易处于出超,各国的补偿物是白银。英国运来的毛织品赚不到什么钱,有时甚至亏本。但却可从出口棉花等得到盈利。例如,1796年,从伦敦来船18艘,运来毛织品成本价612464磅,售得款1666602两,亏损9.3%;运来的棉花5589担,成本103968卢比,售得款69858两,盈利105.3%;同时运来银元120960两,以作其入超的补偿。这一年,美国和丹麦的船只,除运来广州“微不足道”的货物外,差不多都是用白银补偿。两艘丹麦船运来的白银为650000元(注:参见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合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89~591页。)。据估计,从1784年至1844年间,美国商人把约有15亿美元到18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这有助于扩展国际的金融市场。18世纪中叶,鸦片贸易日益增长,且迅速扩展,各国来船尤其英船,往往夹带鸦片毒品来广州贩卖,19世纪后,数量剧增。据1818至1827年的统计,运进的鸦片已达6926箱,价值78224871元(注:参见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5合订本,第402页。)。
除中西贸易集中在广州以外,逐渐陷入西方殖民地的南海地区各国的商人,也来广州贸易。据1833年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的听证会记录,中国对东南亚和日本的帆船贸易估计每年的总额是令人印象深刻的7000万至8000万美元(注:修素洁:《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这一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中英贸易的两倍。可以想象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广州贸易的。
广州的贸易是在清政府制定的体制下进行的:由粤海关负责税收并管理行商,指定黄埔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广州十三行负责中外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这四个环节,又各自形成一套制度。目的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广州十三行是广州外贸体制中的重要环节。它原是广东巡抚李士桢在康熙25年(1686年)在广州设立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口贸易货物”的洋货行。有学者认为广州十三行的名称于晚明已经出现,清代的十三行源自于此(注: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充当广州十三行商者,需经政府特许并颁发执照。他们各自经营,难免出现彼此间的矛盾和倾轧。为了协调行内关系及处理行外事宜,以加强共同对外竞争力,于1720年成立公行。公行的成立被认为伤害了外商的利益,因而遭到英商的百般阻挠和要挟。次年于无形中宣告终止。乾隆25年(1760年),清朝廷允准行商潘振承等9家呈请,重建公行。嗣后分设外洋、本港、福潮三个名目,以分别办理欧洲、南洋以及福州、潮州的贸易和货税事宜。这样负责办理欧洲贸易、货税事宜的外洋行(即十三行),便成为垄断广州中西贸易的外贸机构。
应当指出,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不能以此推论当时整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程度。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毫无疑义,独口通商给广州带来的商业繁荣,对岭南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尤其强烈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是这一期间,珠江三角洲由于广州市场的需求而不断加深其商业化,从而跃居中国先进经济区的行列。各地通往广州商路沿边的市镇,也于此时勃兴。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商业,带来了西方商业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法,诸如理性主义、“有限负债责任(limited liability)”观念、复式会计法,等等。再是通过承充行商、买办等角色,培养出一批熟悉近代商业的人才,推动了中国商业的近代化。19世纪60年代,基于国内尚无以华商的名义自行投资的规章和经营环境,所以尽管以华商投资为主创办的公司,也不得不以外商之名注册挂牌。在上海的公正轮船公司即一例。它本来是由著名的广东香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和郭甘章等共同筹办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能与西商进行商战的如同我们下面将要谈及的豪商。他们长袖善舞,在与西商的竞争中不断增殖资本,并将其贸易网络伸展到欧美各地。
三、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与卷入世界市场
在1750年~1840年的世界商业扩张时代,大量的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商人的到来,并没有把广州的华商跻垮,反而造就了广州十三行商人商业资本的黄金时代。广州十三行商人(亦称行商、中介商)是政府特许的商人,又往往通过捐纳而取得虚职官衔。因此,一般也叫他们为官商。他们介乎外商、华商和官府的三角关系中,不仅享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且垄断着对外贸易。他们除包揽对外贸易外,负责把外商进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以防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负有管理、保护外商之责;居间办理广州官府与外商交涉、往来文件等事务,俨然兼办洋务了。他们垄断对外贸易,意味着垄断货源,垄断价格(名义上是广州的官员定价,由他们出面宣布),垄断利润。所以,行商往往短期内即可暴富。据怡和行商人伍秉鉴在道光14年(1834)自己统计,所有田地、房屋、铺店、钱庄,以及与英美两国贸易的商业资本共达2600万两。又据咸丰10年(1860)法国一家杂志的记载,同孚行商人潘正炜的家产总额也达一亿法郎以上,其财产已富于一国王之地产(注:亨特著,冯树铁译:《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行商这一商人集团继徽商、晋商之后称雄商界,其商业资本额也远超过徽、晋商(注:明代中叶的徽商有的商业资本已超过一百万,到了清前期达千万,这是其发展的顶峰。)。如果说徽、晋两大商人集团在明清时期,只涉足于东亚海域各国的话,那么,以广州行商为代表的商人于晚清已经走向世界,前往欧美作商业扩张了。
广州豪商的出现,是与世界商业扩张时代提供的舞台有密切联系。西欧各国原以享有垄断特权的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亚洲和广州市场出现的。18世纪出现了众多的散商(港脚商人),他们是一批在广州市场上越来越活跃的自由商人。1784年美国商人的到来,以及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的取消,更增添了商业自由竞争的活力。自由竞争不断地取代垄断,有利于商人精英脱颖而出。广州华人豪商如潘氏、伍氏等,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的。
广州华商的经营活动,因国内资料的阙如,有许多商情一直沉埋在黑暗之中。随着荷兰、丹麦、瑞典、印度和美国等国家档案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其鲜为人知的史实慢慢地浮出水面。据西方学者的研究,18世纪,广州华商已经经营广州与欧洲间货运的帆船贸易。据荷兰和瑞典有关1750年至1770年广州帆船贸易的档案记录,至少有27艘,多达37艘的中国帆船经常出入于广州。投资于这一帆船贸易的有广州十三行商人,也有外国商人。据瑞典档案记载,在37艘帆船中,有不少于9个华人商号和13个华商所投资。另外还有7位充当管理者。有的帆船是属于十三行商人所拥有,如潘振承、颜瑛舍、陈捷官等。帆船的货仓,往往为外商所租用。根据美国学者范达克(Paul A.Van Dyke)博士以1763年为例所作的估算,广州帆船所承担的广州对外贸易货运量已占总量的30%,约略与英国的货运量相等,余下的40%由各国来广州的货船分担。从此可见广州帆船货运在当时世界船运中的地位。
以行商为代表的广州豪商,已如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华商以输出中国的茶叶,棉、丝、糖等商品,而同各国的国际商人连结一起。同时利用他们的关系在亚洲以外的地区营运其商业资本。
18世纪中叶,广州十三行的主要商人之一同文行潘振承(1714~1788),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关系。他本人曾有几次马尼拉之行,并能用英语与西班牙语洽谈生意。他在东南亚其他港口也有贸易关系。早在1753年,潘振承已经与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往来,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这国际贸易关系中,瑞典的铜、铁和木材产品被销售,以换取在加地斯(西班牙西南部之一海港)的西班牙银,这些银后来流入广州。他与西班牙人也有过密切的合作联系。他死后其子继承了约二千万西班牙银元的财产。
19世纪初,丽泉行商潘长耀(1759~1823)租用美国的货船来进行贩运货物。中国和外国的商人都因期货交易体系中资产流动问题遭受过损失。许多美国商人因营运的需要而向中国人大量借钱。潘长耀是其债主之一。美商借债逾期不还。单在费城,便有21名商人欠他的债款达50万美元。为此,潘长耀在1815年曾写信给美国麦迪生总统,抱怨美国商人欠他一百万美元还没有偿还。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伍秉鉴(1769~1843)是19世纪最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人。他不仅通过充当美国人的代理商销售中国和欧洲的商品,而且仰仗他与各国商人的关系,建立起其庞大的世界性商业网络。美国学者穆素洁博士根据伍秉鉴写给他美国经理人的50多封信件(这些信件藏在哈佛大学贝克尔图书馆),以及他写给与之有密切商业联系的印度帕史(Parsee)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的信件(藏于孟买的Maharashtra邦档案馆),并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在她的近著《世界市场与中国蔗糖业》一书中,对伍秉鉴过去鲜为人知的商业关系和贸易网络,尤其在欧美经营商务的情况作了揭示,使我们对伍氏的商业活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伍秉鉴继承他的父亲伍国莹,(1731~1800)的商务而成为洋行商人。他商业的成功除他本身人格的魅力外,他的诚信、大度、富有同情心,亦大有关系。他广结善缘,与许多国家的商人都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他被美国商人认为是一位可充当可靠的商业合伙人,所以,乐于与之合伙经营。
伍秉鉴19世纪初,开始贩运茶叶到欧洲销售,租用的是美国货船。1810年,两艘美国船只被丹麦海盗劫掠后所提交的保险赔偿申请中显示,开往哥登堡的一艘船上除美国商人的货物外还装着属于广州华商价值38,000多美元的茶,而另一艘船上完全没有美国商人的货物,只有属于伍秉鉴的价值58,000美元的茶和属于潘长耀的32,000美元的茶。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的一名合伙人约翰P·库欣,在1833年作为一名代理人与伍秉鉴一起工作,伍秉鉴贩运他的茶叶到汉堡,租用的是一艘载重200吨的普鲁士货船。
伍秉鉴尽管已是耋耄之年,出自于对美商的信任,他决定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在美国作实业投资,条件是美方要把每年的利息支付给他的后裔。鸦片战争期间,他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约翰·默里·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投资于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默里·福布斯进一步将伍的基金使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以及包括如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的投资。
从现存的伍秉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与他保持通信的有在广州与他会见过,或有商业往来的美国商人,如约翰·库欣(John Cushing)、约翰·格林(John Green),以及拉尔夫·贝内特·福布斯(Ralph Bennet Forbes)的三个儿子,即托马斯、罗伯特和约翰(他们三人同伍氏都是旗昌洋行中的合作伙伴)。还有纽约商人洛(A.A.Low)和小约瑟夫·库利奇(Joseph Coolidge Jr)等。伍秉鉴正是通过这些人以及欧洲、印度的商人着手建造他在各国的贸易网络。
19世纪初,伍秉鉴就通过曾在广州营商的印度帕史商人默万吉·马尼克吉·塔巴克(Merwanjee Maneckjee Taback)等,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其他的印度商人如孟买的莫霍马达利·阿利·罗盖(Mohomadally Ally Bogay)、以澳门为基地的达达布霍伊·拉斯托姆吉(Dadabhoy Rustomjee)等,也都与伍氏有商务关系。伍氏在孟买的代理商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经营有方。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在一份1842年4月24日的帐单中显示,詹姆塞特吉受伍秉鉴之托,购买珍珠,送到旗昌洋行,所需的款项可用孟加拉政府的7000卢比支付。如果不够,再请旗昌洋行代垫。詹姆塞特吉还受托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丝和肉桂,并要求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帐目中。从此透露出,伍氏与各国商人,乃至与盂加拉政府间的复杂关系。
伍秉鉴还经营与美国和欧洲的直接贸易。我们从他给美国商人的通信中可以窥见一些信息。鸦片战争期间的1841年11月21日,他给已经从广州回到波士顿的库欣(Cushing)写信说:“四月和五月,我把价值约一百万美元的茶叶用船运到纽约和伦敦,我认为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两天后在写给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Forbes)的信中,则说他正将三、四百吨的茶叶,装船运往荷兰。信中还透露以前贩运的商货,已经取得约50%的利润等。
我们还可从些信件中,看到伍秉鉴对其国际上商业伙伴的关照和慷慨。在1840年6月1日写给库欣的信中说:我现在写这封信,主要为了说明,我已经把茶装上了“阿克巴(Akbar)”号,总额约五万美元,茶将随船前往新加坡,如果茶不能够在新加坡以40%的利润销售,它将随英国船只被运往伦敦的福布斯公司。同时,在得到8%的年利率后,我将把该次商业投机所得的全部利润给J·P·斯特奇斯(Sturgis)先生,倘使赔本,我将独自承担。我希望斯特奇斯先生今年将创造大约四万或五万美元,并且,我放弃他欠我的在老帐目上约三万美元的利息。
伍秉鉴似乎最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市场投机而大赚其钱。他从美国人取得现金,为美国和印度商人提供信用贷款,收取利息,之后又在美国投资而得益。这是他抓住美国在中国和印度洋的贸易扩张,以及新加坡港市于1819年的建立而出现的机遇而采取的举措。他投入的资金是相当巨大的。信件中就提及通过口头协约而借贷31020美元给予库利奇(Coolidge),又给予洛(A.A.Low)一笔25,000美元的信用贷款。1840年6月28日给约翰·福布斯的信中说,“我在美国和欧洲拥有大量基金,这些基金你必须尽可能谨慎管理,保证其安全,并让它产生利润;在英国商业确定以后,把我的所有基金以孟加拉的硬币或帐单的形式,送回中国我的朋友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那里”。伍秉鉴在1834年估约拥有2600万两银币(折约5600万美元)的财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本。
伍秉鉴于1843年逝世后,由其子伍崇曜(1810~1863)继承家业。伍崇曜与旗昌洋行合伙继续作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Baring Brothers)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似乎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当旗昌洋行于1891年宣布破产,约翰·默里·福布斯成为了伍氏家族的受托人时,记录显示旗昌洋行拥有属于伍氏家族的一百万多美元受托基金。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45000美元之间。从一些逸事趣闻的史实中表明,一些卷入世界市场的豪商是如此富裕,以致于他们能够一掷万金,以解人之困。伍秉鉴有一次就撕毁一份美国商人72000美元的借据,使这位商人能够返回家园。
从伍秉鉴与美商的关系中,已经不难看出,中美商人贸易网络的彼此交织。这种情况,从其他美商同广州华商的关系中也可得到说明。许多广州的华商与在波士顿设有商行的美商珀金斯(Perkins),都建立有密切的商务伙伴关系。华商中有一位名为叶盛(音译)的就因与珀金斯作丝货贸易而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在19世纪40年代爆发的鸦片战争期间,美商设在广州的公司也为华商所利用,以帮助中国商人坚持他们应得的权利。旗昌洋行的职员爱德华·德拉诺(Edward Delano)于1841年,留下这样的记录:“日日夜夜忙于为各洋行商人写委托书,以期他们有可能最后取回茶钱。这些茶是他们销售给自称美籍,名为T·W·斯蒂凡斯的商人。T·W·斯蒂凡斯在前往英、法途中,逃到了孟买”。这些在战争中给广州华商伸手相助的美国公司,很显然彼此间就本有商业上的伙伴关系。
从上可见,广州的豪商已经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之中,与传统的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不啻天壤之别。广州华商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