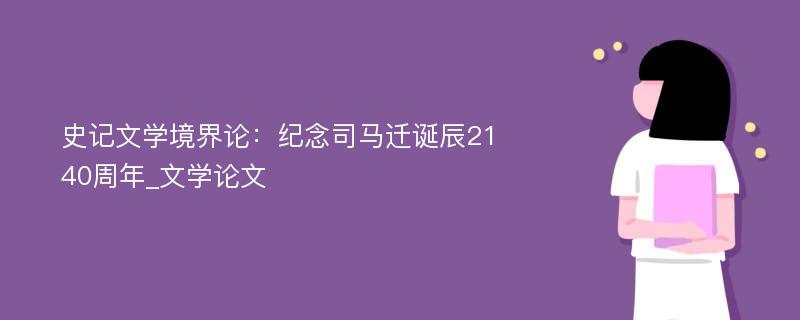
《史记》文学性界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诞辰论文,司马迁论文,周年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史记》文学性给予界定。它从前人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过程及今人对这一认识的分歧谈起,指出如今问题的症结和焦点已经不是《史记》是否使用了文学手法问题,而是《史记》是否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问题了。文章分别从道理上和实质上——着重从所写内容对象(以人物为中心,对人物“为人”特别关注,使笔下人物具有了文学上“人学”的人的特点;写进了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作者的理想、追求,是经过审美观照之后的审美创作)、作者的写作目的和动机(不但有历史家的强烈使命感,还有文学家的创作冲动;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把自己作为民族的良心)、作品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重点从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典型化考察分析)、以及将《史记》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那些先秦典籍中得到的实证几方面进行论证。同时,本文就《史记》文学性的概念、《史记》的文学创作性质与《史记》作为“实录”的关系作了简要界说。
[关键词]《史记》文学性 《史记》文学创作性质 《史记》文学性界说
由于《史记》本身所具有的不容争辩的艺术魅力,也由于历代学者的不断阐扬,如今,人们几乎都知道并且承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史记》的文学性,似乎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然而,从历史上来看,人们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却并不轻易,从只认为它是历史著作,到认识它是好文章,到进而承认它是文学作品,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史记》问世之后,西汉两位著名的学者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 这虽然是从史学角度讲的,毕竟称许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好。东汉班固,在《汉书》里把司马迁列为文章家。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2〕晋代张辅,称赞“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 “逞辞流离”。〔3〕南北朝时期, 刘勰在他那部著名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里,把“史传”作为一种文体,辟专章论述,已经把《史记》包括在广义的文学范围之内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都非常推崇司马迁的文章,韩愈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4〕; 柳宗元一则说“《谷梁》《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一则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5〕由于他们把司马迁的文章树为古文典范, 从而奠定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纵观自汉至唐人们对《史记》文学成就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从文章、古文(或说文章辞采、散文艺术),亦即从广义的文学这个层次的认识上,认识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古人之间以及古人与今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其二,但到这时为止,还只是把《史记》作为广义的文学看待,对于《史记》在写人、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就,根本没有涉及——刘勰这位文论家如此,韩愈、柳宗元这两位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如此。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的《昭明文选》不收《史记》的传记作品,也说明编者是把《史记》传记作品放在文学视野之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正象一些文艺理论家所指出的,这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长时期内不重视人物形象问题,甚至没有人物形象的概念有关。
到宋代,与话本小说的兴起和广泛流行相联系,有人开始从人物形象和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进行评论和研究。魏了翁在评论《高祖本纪》高祖还乡一段时指出:“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泣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6〕这里,评论家讲得很清楚,这种把生活细节、人物情味刻画得如此酣至、逼肖,并造成如此浓重的氛围、意境,已经超出了历史的需要,显然进入文学创作的范围了。刘辰翁在他的《班马异同评》这部评点著作中,指出《司马相如列传》的文君夜奔等于“一段小说”,指出司马迁为人作传,不只写人物的生平、功状,还注意写那些最能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象《绛侯周勃世家》狱吏书牍背、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等,用这些来为人物传神。他评《留侯世家》时,称赞“圯上老人又极从容,如同时亲见”,“妙处正在‘履我!’又业已如此。”批评班固对这些描写妄加删削,以致使作品“顿失数倍意态”。此后明清评点家,尤其是一些小说评点家,更进一步从《史记》的写人艺术、虚构、想象等文学创作特征,以及传记文学与一般小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论列,其中以金圣叹的评论最为深刻、独到。他说:“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计算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7〕又说:“司马迁之为文也, 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又见其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8〕金氏这两段论述, 实际上是最早对《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创作特点所作的概括和阐明,也是第一次对小说与传记文学之间区分所作的界定。此外,周亮工有“笔补造化,代为传神”〔9〕说, 姚苎田有“冥心独运之文”〔10〕说,郭嵩焘有“亦自喜其摹写曲折之工也”〔1〕说。这些说法都说明作者看出了《史记》具有文学创作的成分。
“五四”之后,鲁迅站在现代认识的高度,对《史记》有过两句著名的评语,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2〕。这一评语,是对《史记》文史结合特质的明确确认,也是对《史记》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标志着对《史记》的文学性已经从整体上获得了本质性的认识。
那么,至此,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是否就解决了、就统一了呢?并没有。只要稍加深究就会发现,人们承认《史记》是文学了,但是每个人头脑里那个“文学”的内涵却是各不相同的,有人承认它是文学,只是承认它运用了文学描写的手法,写得富有文彩,实质上就是不承认它是文学创作。即使如今,就以文史两界而论,看法仍有分歧,就连问题的提法都不一样:史学界同志提出,司马迁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呢,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文学界同志则问,《史记》仅仅是用了一些文学描写手法呢,还是包含文学创作成分,具有文学创作性质?
看来,对《史记》的文学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和给予科学的界定势在必行,它反映了《史记》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早在30年代初,有人就已专文探讨过这个问题——虽然没用“文学性界说”这样的词。袁菖1930年在中央大学半月刊一卷第十三期发表《史记之文学研究》,文章“导言”第一个问题讲的就是“史记何以为文学”?他主要讲了三点:(1)有感情;(2)有丰富的想象;(3)有个性描写。在第三部分,讲“史记文学的艺术特质”,列出七点:(1)个性的表现;(2)笑的描写艺术;(3)小说的艺术;(4)散文的艺术;(5)戏剧文学之艺术;(6)喜剧艺术之一瞥;(7)悲剧艺术之一瞥。
前人走过的路告诉我们,探究和界定《史记》的文学性,从《史记》具有哪些文学特征,运用了哪些文学手法着手是必要的,然而却远远不够,因为问题的症结和焦点已经不是手法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了。史学界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司马迁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呢,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或者更本质些说,《史记》的人物传记,是实录还是创作?
我们的话题不妨就此说起。在我看来,这个提法本身就有些毛病,因为从道理上讲:
第一,司马迁写《史记》的当时,还处于文史不分的时代,他并没有今人这样明晰的史学与文学的概念,他写《史记》,恐怕既不必明确也不会在意是用文学之笔写历史人物还是借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创作,既如此,我们又何必硬把两者对立起来?既是文史不分,就意味着其中有文有史(不管所占比例如何)。我们知道,在当时,在散文领域还没有纯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所以散文领域的文学创作常常是寓文于史、寓文于论——即寄体于史或寄体于论等等而出现。
第二,那么,能否把寓文于史的关系理解为、简化为、或对换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呢?内容是历史,文学只是表现形式,寓文于史就是以文学笔法写历史?这样的理解、简化或对换恐难说通,因为寓文于史是把文学创作寄寓在历史的记叙之中,是寄体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现出来。
第三,关于《史记》的性质,现在正进行着深入的讨论。阮芝生强调它的特质在于它是“百王大法”,是“横跨‘经史子集’四部为一书的绝无仅有的伟大作品”〔13〕。韩兆琦说司马迁著《史记》原意是要发表他的一家之言,是要使《史记》成为象《春秋》一样的“经”,是为后人开的“治世药方”,它“说道理是首要的,写人物,写故事,是为了讲道理服务的,是一种载体”。〔14〕不管这些说法能否成为定论,不管这个讨论结果如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果承认它的百科全书性质,就不能以某一种(即使主导的)性质而否定其他,排斥其他。多质并存,这正是《史记》的卓绝之处!当然,反过来说承认《史记》的百科全书性质,并不就否认《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主要是历史著作,因为《史记》毕竟主要写的是历史,而且司马迁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家来写它的。这一点,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特别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时所时刻不能忘记的。
在从道理上说明一些问题之后,让我们进入实质问题的考察。针对《史记》是否具有文学创作性质这个关键问题,我们试着从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这几个较为根本的方面着手探究,其它一般性问题从略。
一、从写什么,亦即所写内容对象上看。
(一)《史记》述史,与先秦史书有个根本区别,是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了以人物为中心;与后来其他同样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著作也有一个显著的差别,这就是它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写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的地方特别多。比如“禹为人……”、“始皇为人……”、“项王为人……”、“吕后为人……”、“子胥为人……”、“灌夫为人……”等等。象这样的字眼,不说篇篇都有吧,起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还不只一句两句。这“为人”的含义,首先是相对于“功业”而言的,就是说,司马迁写人,不单重视人物的历史功绩、功业表现及历史评价,同时还重视人物的品德节操和为人品行等道德评价;其次,“为人”的含义还包含着对人物性格和个性的体认和把握,也就是关注于探寻和表现每个人物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个性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不单是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待,也是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笔下的人,就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历史的人,而具有了文学上“人学”的人的特点。
(二)人们在说明《史记》具有文学创作特征时,常常强调它的“有感情”,它的“笔端挟带感情”,或说它“灌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强调它的“以情感人”。是的,感情是文学的重要特质,有无感情的投入是区分是不是文学的重要标志。可如果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容易和一般历史著作区别,因为写历史,写一般人物传记,是爱是憎,是褒是贬总有个主观态度,只不过有强弱、浓淡、隐显之分罢了。还有人强调,《史记》“不只叙事,兼能写情”,或说“不只叙事,而且传情”。如果前者所说“有感情”、“挟带感情”等所说的感情是指作者的感情的话,那么这里所说“写情”,“传情”的情,指的就是人物之情,事理之情,是人物、事理本身内在的情蕴了。这是《史记》“感情”的又一个层面。此外,古今许多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史记》“辞多寄托”、“寄兴深长”。也就是说,《史记》写的是历史人物,但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司马迁往往情不自禁地把他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以及自己的理想、愿望、希冀、追求等等,融注、渗透、寄寓在其中。譬如,《屈原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雎蔡泽列传》所阐发的“发愤著书”、“穷愁著书”说,《伍子胥列传》、《季布栾布列传》等所表达的“隐忍以就功名”的信念,难道不是凝注进了作者司马迁的人生体验?《外戚世家》所突现的“偶然性在人生命运中的作用”的主题,《万石张叔列传》所揭示的“万事唯谨”至于极点的这种家风世风对于人的智慧、才干的窒息与扭曲,难道不是闪耀着司马迁独特的人生发现?《魏公子列传》和《李将军列传》所表露的对于“谦恭下士”、“好客为国”的“翩翩佳公子”和“国士无双”的一代名将的崇慕与爱戴,难道不是明显地寄寓着司马迁的理想,甚至是按照他的理想塑造出来的吗?是啊,司马迁作为一个有崇高使命感的历史家,不但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拥有广泛的社会阅历,而诗人的气质,又使他对一切都保持特有的敏感。特别是李陵之祸的遭遇,更使他获得了比常人要入骨三分的人生体验。他写历史,不仅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且要“成一家之言”,他“述往事”是为“思来者”,他还“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那么,一部《史记》里,该有多少话要和时人讲和后人说呀!就如《报任少卿书》所显示的,他要向人们剖白、倾诉、传达的,他要告诉、提醒、警戒、激励、感动人们的,该有多少!所有这一切都要写进《史记》,事实上也已经写进了《史记》。那么《史记》的内蕴,单单一个“历史”怎能包容得了呢!
(三)《史记》还有一点与一般历史著作不同,这就是它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只是进行历史评价,而且是把它们当作审美对象来写来看待的。譬如《赵世家》所写赵氏孤儿的事,可以看得出来,作者绝不只是为了告诉人们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也不只是为了肯定和表彰公孙杵臼、程婴这样的人。他是觉得,这桩事,这些人,和他们的不平凡的作为,体现了人类一种崇高的精神,体现出了一种崇高的人格美——一种为救助被迫害的孤儿而慷慨献身的大义,是非常值得钦慕、咏叹和玩味的,所以才用饱蘸激情的笔,把它写出来,用以感染和激励人们。读《史记》,特别是读其中一些得意之作,往往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已经把他的人物理想化了,是按审美的要求、审美的理想来刻画和塑造他的人物的。象前面提到的《魏公子列传》,司马迁对信陵君“谦恭下士”、“好客为国”的人品崇慕之至,视为难得的理想,写来便无限低徊,无限唱叹,传中连称“公子”不绝于口,以至全传竟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还有,《史记》写易水送别、乌江自刎、过沛还乡这些著名场面,都着意经营,造成那样浓至的、令人唏嘘感叹的氛围意境。所有这些,都一在说明,作者所写,已不只是单纯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现象,而是经过了审美观照之后的审美创作。
综让所述,首先从所写内容对象上看,《史记》就已远远超出历史的范畴,进入文学领域了。
二、从为什么写,亦即从写作的目的动机上看。
(一)司马迁写历史,不但有历史家强烈的使命感,还时时有文学家的创作冲动。每当我们读起《史记》当中那些出色篇章的时候,常常会强烈地感到作者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他要把他的人生体验,把他的爱和恨,把他想要称扬和鞭挞的各式各样人物的思想性格、灵魂嘴脸,统统刻画出来。读着《史记》,我们常常会感到象归有光所讲到的那样:“太史公但若闹热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15〕
(二)司马迁的《史记》,不但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心。他写历史,不只是进行历史的评价和裁判,而且继承和发扬“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传统,把自己作为民族的良心。他在民族历史心灵的大海里遨游、巡礼,揭露不平,鞭笞罪恶,讽刺丑态,赞美英雄,颂扬美德,追求崇高,追求光辉理想的人格,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性,作出妍蚩必显的鉴镜。所以人们读《史记》,不仅可以读到历史,还能读到人的命运与人的心灵的历程。
三、从怎么写,亦即从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上看。
这里,我们不准备也觉得不必要再从描写的形象性以至夸张、想象等等再去全面论列,只想就心理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典型化几方面作些重点考察。
(一)古代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或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总之,所记重点在于“言”、“事”,至于帝王的言行动机,执笔史官无权、也不敢妄加推度。于是乎以史传为主体的先秦叙事文学,一向缺少心理描写。而《史记》由于司马迁重视人的历史作用,把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更由于他对人物“为人”的特别关注,就特别注重和加强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因此,《史记》比起其他史传作品,心理描写比重的加大便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五帝本纪》据《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加工改写虞舜孝亲的故事,重要增润之一就是加了“瞽叟、象喜,以为舜已死”的心理描写。《孔子世家》据《论语》刻画塑造孔子形象,也增加了不少象“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这类心理描写。这是有古代典籍作为素材凭借的,就是没有典籍作凭借,由作者自己搜集材料或完全自己创作的作品,也有不少出色的心理描写。譬如《赵世家》写“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淮阴侯列传》写“高祖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这些心理描写,一看就知道绝不是出于史官记载或别的什么史料提供,只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结合人物处境,详情度理,经过想象加工而创作出来的。
(二)《史记》的人物语言描写也大半出于“见象骨而想生象”,是“善设心处地,代作喉舌”〔16〕的主观营造。象《晋世家》写骊姬的谗言,由《左传》“贼由太子”一句而生发成一大篇固为显例,再如《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伏剑自裁前仰天长叹那段话:“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 我以死争之于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于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这段话把伍子胥一腔忠而见疑,有大功而遭谗陷的怨愤,一古脑儿倾泻而出,为自己,也为那些因耿介而获罪的人吐了一口长气。这番话,《左传》、《国语》里都没影,自然是出自作者的“杜撰”,然而就情理言,所有这些又都如水到渠成,是势所必发的。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吴见思《史记论文》评它“其写醉语、怒语、对薄语、忙语、闲语、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无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论,乃诸臣竟不做声,遂发作郑当时,是一肚皮不快话语,一一入妙”。即以东朝廷辩一场而论,田蚡伶牙利齿,血口喷人的话,韩安国圆滑世故,首鼠两端的话,郑当时局促嗫嚅的话,以及武帝这位少年天子失望负气既是发作又是发泄的话,种种声腔口吻,恐怕你就是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或高明的模拟演员,也难传达于万一。能写出这样的人物语言,靠的绝不是史官“记言”的本领,而只能是出自文学大师的呕心创作。
(三)《史记》人物典型化,有自己的特点,季镇淮把这个特点概括为“从‘实录’到典型化”〔17〕。他说:“司马迁写的是历史人物,他固然不能虚构事实,必须依据确信的事实。但是选择事实,剪裁和安排事实,突出地描写某些事实这一系列的思考过程之中,显然包含着他对事实的认识、想象和体会。上述方法的运用过程实在也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司马迁找到了一把通过特殊、个别来体现一般的钥匙。他塑造典型,既不能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不能用以一个生活原型为基础,再吸取他人材料加以融合的办法,而必须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进行艺术创作。因此,“实录”原则是司马迁塑造典型人物的基础。但是只有这一条还不能创造出典型人物,只有卓越的史识和高度艺术概括的完美结合才是达到典型化的途径。这卓越的史识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具体说来便体现在传主的选择以及事件的选择和描写上。司马迁凭着卓越的史识,从历史上真实人物中选择那些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人物,再从这些人物一生行事中选择那些有助于揭示人物本质的,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从而塑造出人物的典型形象。
前面说到,司马迁写《史记》,“辞多寄托”。就是说在写人当中往往把作者的人生体验、生活发现和理想愿望写进去。这些作者个人的东西,对于原本传主人物来说,是外加因素,两者之间如何统一?弄得不好会给人以生拉硬扯两张皮的感觉。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采取的是寻找两者“契合点”的办法——即凡所寄托,一定要是传主本身经历中确实具有,甚或是传主本人也体验到的,这样的寄托,对传记本身来说,等于是画龙点睛,往往能起到一种升华作用,象“隐忍以就功名”的论赞语对于《季布栾布列传》就是这样。还有,司马迁有时为了把人物理想化和典型化,也为了使人物性格保持统一,使一篇作品主题统一,风格完整,常常把传主的一些和传主主导性格不一致,和作品主题不一致的事迹不在本传中写,而以他传见之。这种方法,解决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典型性这两方面要求的矛盾,做到了既忠实于历史,又保证主题和人物性格的统一,两全其美。这个方法就是司马迁为达到传记人物典型化所匠心独创的“互见法”,《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等等,都成功地使用了它。
综上所述,我们又从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上论述了司马迁写《史记》确实不只用一般史笔,也不只是运用了一些文学描写手法,而是实实在在进行了严肃的文学创作。
四、然而,最能有力地表明《史记》的文学性质的,莫如实证。
我于1994年第2 期《语文学刊》曾发表《〈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一文,从《史记》及《史记》据以为素材的先秦典籍的比较对照中,举出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例证,说明:(1)《史记》不是单纯的历史编纂而是认真地进行了文学再创作;(2)《史记》不仅是为人物作客观实录,同时也在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概括进了更多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3)在组织结构上, 它不是把历史按其自然状态加以复述,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艺术加工,富有想象力地安排材料;(4)《史记》述史,允许有一定的想象、夸张乃至虚构, 《史记》的许多再创作,不仅有增润生发,也使用了移花接木,甚至移甲作乙等手段(详见该文)。
以上,我们从道理上和实际上两个方面论证了《史记》不仅是运用了一些文学手法,而且是从根本上具有了文学创作的性质。
如果这些论点能够成立,那么承认《史记》具有文学创作性质,是否会危及《史记》作为“实录”的信誉,以至动摇《史记》作为信史的地位呢?这是史学界同志所担心的。
其实,我以为不会。第一,我们说《史记》是文学,具有文学创作的性质,并不是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篇篇是文学,篇篇都有文学创作。其中《书》、《表》部分根本不属于文学,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其中有个例外,就是《封禅书》实际写成了难得的讽刺妙品),就是《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人物传记部分,也有很大数量的篇章(起码百分之五十以上)重在排比史料、叙事纪实,用的是一般史笔。象五帝、三王和秦本纪以及春秋战国时代大部分世家就是如此,只在涉及一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部分,间或有一些精采的文学片断。这些篇章,从总体上说,自然也算不得是文学。能够称得起文学作品的,主要是人物传记当中那些确实经过了文学创作,刻画了人物性格,真正把人物写活了的那些篇章(总共不过四五十篇)。就是这些篇章之中,文学创作成分的多少,艺术质量的高低,文学意味的浓淡,各篇之间也各不相同,那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二,《史记》再创作中有些脱胎换骨、移花接木、甚至移甲作乙的改动,这些属于或人、或事、或时、或地的改动,对于不允许虚构的历史真实来说,性质上当然是严重的。然而所有这类改动,一般都限于具体细节范围之内,而在重大事件的大关要节上,司马迁是毫不含糊,严格忠于历史的——《伍子胥列传》拒捕一段把原伍尚一个人说的话改成伍尚与伍子胥之间的对话,主角也由伍尚改成伍子胥,但拒捕这个大关要节没变,入郢复仇一段,把鞭墓、挞墓改为掘墓鞭尸,但入郢复仇这个大关要节没变。正因为这样,就象尽管《史记》有不少疏略抵牾,却并未妨碍它作“实录”的定评一样,一些个别的、细节范围内的虚构、改动,也动摇不了它作为“信史”的地位。第三,更为可喜的是,司马迁找到了一种解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矛盾,使之两全其美的法宝——“互见法”。互见法一方面使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被塑造成谦恭下士,好客为国,一身系魏国安危的理想化的光辉形象:一方面在《范雎蔡泽列传》又使读者如实看到他怯懦自私,不敢收留魏齐避难的很不光彩的一面;特别是在《魏世家》的论赞里,还向读者交待出历史的真象:“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所以,第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创作”与“实录”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以及如何处理“文学创作”与“实录”、“信史”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文学创作”是采取一般小说那样,“顺着笔性写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的办法,肯定要发生矛盾,而如果采取象《史记》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套适合传记文学特点的特有方法,矛盾便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也好克服。在此我们就越发感到金圣叹在把《史记》与《水浒》作比较时所作的那段概括得深刻。
本文于1995年6月10日收到。
注释:
〔1〕《汉书·司马迁传赞》。
〔2〕《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
〔3〕《晋书·张辅传》。
〔4〕《昌黎先生集·答刘正夫书》。
〔5〕《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6〕《史记评林》引。
〔7〕《水浒全传会评本》之《读第五才子书》。
〔8〕《水浒全传会评本》第二十八回回首总评。
〔9〕《尺牍新钞》释通盛《与某》。
〔10〕《史记菁华录》项羽本纪条下。
〔11〕《史记札记》项羽本纪条下。
〔12〕《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3〕《〈史记〉的特质》,《天人古今》,1994年第3期。
〔14〕《关于〈史记〉的性质及其他》,《语文学刊》,1994年第2期。
〔15〕《归有光·方苞评点史记》例意。
〔16〕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第276页。
〔17〕《司马迁是怎样写人物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语文学习》,1956年第8期。
标签:文学论文; 史记论文; 司马迁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魏公子列传论文; 读书论文; 伍子胥列传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