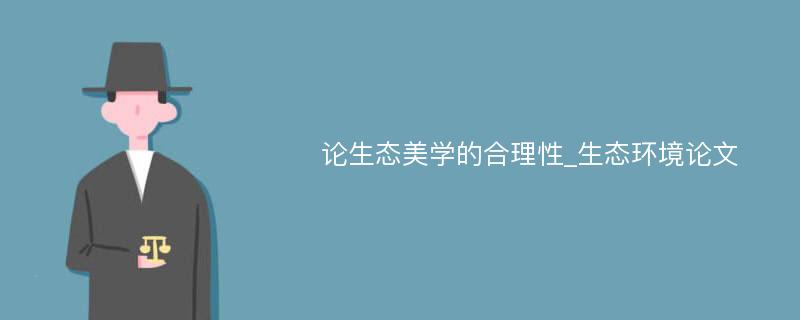
生态审美合理性论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需要把自己的生存活动不断升华为审美活动,人类从事审美活动的最终状态应该是和谐的。和谐性的生存应该是人类的终极存在,人类生态性存在的最终状态也应该是和谐的,生态系统的和谐与人类存在的和谐状态应该是一致的。
一、生态觉醒的必然性
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与人类存在的和谐状态应该是相通的,是双向互补的。生态系统处于和谐的状态必然会带来人类存在的和谐,而人类生存活动中对和谐自由的追寻更需要生态系统结构的和谐,即如果没有生态系统的和谐,人类需要本质意义上和谐性的生存活动,将是极为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后果,所以生态觉醒就成为改变现实人类生存活动的一个逻辑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追思自己和谐性终极存在的前提。这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又是生存论问题;既需要认识论的把握,又需要后天的教化。从存在论的视域透视,这既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不论是伦理性的,还是审美的,其关注的应该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由关系,或者说是,生态觉醒的有效性首先应该认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其出发点都应该是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合理性的基础上,通过人的精神生态存在的和谐与圆融,而解构人类不断增殖的欲望性需要和消费指向。
伦理性地把握人的生态觉醒和构建生态合理性,主要是通过“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的互动与交触,从观念与实际存在的环节认同自然存在价值的合理性,并合理地调适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存在价值的关系。生态伦理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伦理关系,因为人际伦理关系往往是属人的,主要是通过善与恶,“应当”与“不应当”的价值判断与评价,来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求在规范、约束等理性意识的制约中,使个体的活动不断地符合社会的规范与要求。生态伦理关系拓宽了人类认识自身的视野,是把自己放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把自己视为生态系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意识到如果自己这个环节出了问题,生态系统的和谐性循环结构就会受到破坏,那么人类自己的生存也必然处于危机状态。维护生态伦理关系的和谐性存在,除了外在自然力的推动,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人类对自身生存行为的约束和规范。
审美地把握人的生态觉醒和构建生态合理性,不只是要伦理性地承认人类生存价值与自然存在价值的关系,更重要地是从体验性和生命活动的意义上将这种生态关系认定为人的基本存在关系,甚至认定人的存在就是生态性存在,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是人类自身的,实际上是生态性活动。它首先需要肯定与直接体验自然的存在,并且必须认定自然的存在状态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前提,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归宿不是回归于人类自身,而是回归于自然。人类的发展必须推进自然的生成与发展,或者说,是推进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因为人类的肉体之身实际就是自然之身,更重要还在于人类作为系统性的存在,是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一个分支,人类对终极自由的追寻,必然是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中生成。从认同和肯定自然的存在,到人类的生态性生命的活动,都必然是在生命的体验性和活动中完成,人类生态关系存在的和谐性、平衡性、全面性,以及生态自由性,就使得人类的生命活动状态实际表现为审美的活动状态。审美活动本体的存在应该表现为和谐性、关系性、个体性、体验性,其终极的追寻是自由性;审美活动的对象性存在主要在于自然性,从对自然的审美对象性关系中人们建立起了社会审美与精神一艺术审美的参照,唤起了人们的生命价值的理解。审美活动调动了人类肌体的全部生命机能,在生命激情的涌动中,在汪洋恣肆的情感迸发中人们去体味着生命的存在价值。
伦理与审美召唤人类的生态觉醒,构建人类生存的生态合理性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伦理性的觉识注重理性与价值论意义上促动,它是由外在的关系性,即人与自然的伦理性关系的构建,而走向人类伦理性自觉意义的内在性;审美的觉醒更是人的生命体验的感悟与理解,是对自由生命的觉识,它可以从伦理的自觉的走向审美的自由,从而在现实的生命实践中展示人类的生态觉识,并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外在性,而促动人类对建立生态合理性的理性自觉,同时,我们还可以称这实际是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的过程。
二、生态亲和的包容性
人的生态性存在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必然存在状态,在生态性关系中生存的人,需要以一种生态亲和力认同对现实自我的态度,解构自我中心主义。所谓亲和力就是指人与自然、人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亲情与共生性的交往互动,而不是以占有性、侵犯性为目的的欲望性交往。
生态亲和力的本义应该是在情感、意志体验下的互通性,即人与自然都能够在主动性的生态交往中,情感性的体验对象。但由于在人类意识地支配下,这种生态性交往的主导方面又往往是在人类一方,即生态亲和力的构建主要在人类自身,因为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情性的关系中,人往往是处于主导性地位的,人对自然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种亲情性关系的和谐程度。生态亲和力的构建就应该将人类对于自身生态性存在关系的亲和力视为中介,由此而延伸及深化到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亲和,但同时还需要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存在关系是人的生态性存在现实基础。
生态亲和力需要产生一种“生态人”,建立以生态精神为主导的主体意识。生态主体意识不是二元对立意识,但它首先应该是人类的自觉意识,它包括人类要不断地确立自身价值存在与价值意义的意识,不断地确立对象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意识,不断地沟通人与自然生态世界和谐融通关系的意识。从生态合理性的角度讲,对象性的存在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这就表明生态主体意识中必须建立认同作为对象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自觉意识。不论是人类的自觉意识,还是认同对象存在的自觉意识都需要肯定“人本性”的存在,即肯定人存在的价值本位。这里所说地“人本性”的存在,不同于“人类中心”,也不同于“自然中心”;它所强调地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本位性,而不是排他性;是融通性,而不是解构性;它表明人类存在不可能不思考和把握自身的存在,但它又必须深刻地思考与把握人类存在的合理性、人类在生态系统的位置性,以及生物世界的多样性。人类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是生态合理性,它所促进地应该是人类自身与生态世界的共生与和谐发展,实际上只有在这种共生性的发展行程中,才会有人类发展的未来性,人的生态性存在才会有合理性。
生态主体内在地蕴聚着和谐、融通性功能,就表现为生态包容性意识。生态包容性意识以生态亲和力为内在价值和动力,它不仅需要人类自身的亲和与亲情性的交往,更需要人类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吸纳对象世界,认同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份子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成中英先生将这种包容性意识称为“包容性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意识规范下的人类,应该是“作为自我转化及转化外在现实世界的主体”,由此“人及自然二者相互依附于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这个同时包含人及自然的现实整体必须被视为一个能容许人及自然能在其中相互转化的动态的创造的转化过程”,[1]生态包容性意识实际就可以是整体意识、融合意识和转化性意识的合体,它所表征的人类精神是“一种转化权力意志成为仁爱精神的朝向和谐的意志”。[2]
然而,人类生存活动中的欲望性滋生人的占有性,以及不断张扬的“权力意志”阻隔了这种转化性,并使这种“仁爱精神”的朝向成为艰难与曲折的过程。弗洛姆称这种占有为“侵犯”,弗洛姆曾经分析了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侵犯性”,其第一种是人与动物共有的侵犯性,他称之为是“防卫性的‘良性的’侵犯”,是指当人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攻击性(或逃走)的冲动,这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冲动”。这种“侵犯性”是属于自我保护性的,是生存适应性,一旦威胁消失,它也随之消失。第二种是“‘恶性侵犯’,亦即破坏与残忍。这是人类特有的侵犯性,大多数别的哺乳动物都没有;这不是种族发生史演化出来的,也不是生存适应性的;它无目的可言,除了满足凶残的欲望之外,别无意义”。“‘恶性的’侵犯,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真正问题,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真正的威胁。”[3]尽管弗洛姆在那里所说地这种“恶性的侵犯性”无目的可言,其实人类对自然生物的“侵犯”必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或者是说,不同的时代中人们只是满足当下人的生存,而很少顾及后代人,更无需去考虑自然生物的生存与繁衍。因此,弗洛姆指出这种“侵犯性”对人类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也是具有警示性的。很显然,这种占有性和“侵犯”性又随之形成了排他性,并使人与人之间具有了隔膜、疏离和占有,同时也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那种“永无止境”的占有。我们不可排除人与自然可能是亲近的,并且是具有永远无法抛离的亲近感,但这种亲近是否就是真正和谐与亲情式的亲近,是否是在占有、征服、改造意义上表现的亲近。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人们都会沾沾自喜地声称是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却似乎很少去思索获得成就与“胜利”的行程中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副作用。同时人们还会声称某些自然灾害的发生因为是我们还没有掌握战胜它的手段,却很少考虑人类对这些灾害的发生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自然世界对人类的占有欲和“侵犯”性的报复。
包容性意识的存在就旨在解构这种占有、疏离和“亲近”,它要不断地构建那种转化意识,因此,包容意识的动态意义就表现为和谐状态下的生存转换。在生态世界中,人类的生存是万物存在的中介,自然的存在既成就了人的生命,又可以通过人类的活动而使生命的机能富有活力。包容性意识的基本行为模式和道德意义上的行为准则就是把对象包含在和谐关系之中,采取一种自我关怀和互为关怀相统一的存在状态。人类生态意识的确立产生于人对于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定和反思,而这种包容意识则是从本体存在的意义上反思人类的生存状态,首先就需要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改造和占有性的关系,人不能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自然进行无尽地掠夺。
三、绿色追寻的功能性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1992年6月4日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就表明,“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4]应该看到,《宣言》所讲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心”,以及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都是以人的存在为立论的中心,这应该是人类为解决自己的“健康而富有”的生存活动的基本权利,用当下已经破人们泛化,乃至过于庸俗化了的“绿色”而言,这可以被称之为“绿色权利”。
绿色的思维为生态审美合理性的研究视域提供了活性机制,它提示我们不论怎样谈绿色,或者说谈“绿色权利”,都必须是关系性中的绿色及关系性中的“绿色权利”。所谓关系中的绿色和权利的基本存在状态就是《宣言》中指出的,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所表现的关系性存在,也是诗性存在。绿色是生命之色,是诗性之色,它表征生命的勃发,生命的郁郁葱葱。审美视域中生命的绿色,是对感性存在的绿色的超越,是不断诗意生成的审美色彩。人类的诗意生存应该是不断地向绿色的世界吸取生存的智慧,同时又不断地向审美的绿色回归,回归绿色不仅是回归生命的本色,更重要的是生态审美性的体验人类的不断生成。
绿色是生态之色,绿色之地也是生态之地。生态文明的世界是绿色文明的世界,人类对自身的关怀实际也是绿色的关怀。从绿色本身的功能性角度讲,作为生态审美之色,它那强大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它对人类生存情感的巨大的冲击力,就可以将人的生命活力奔腾在生态关系的亲和力中,这种生态亲和力同时体现了一种巨大的对绿色的祈望性和绿色亲和力。这不仅因为色彩斑斓的自然万物是以绿色作为主色调的,更在于自然万物走出严冬的主体之色,走向生命与审美活力之色就是绿色。从色彩的形式功能来讲,绿色还是一种合成色,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成为天与地交触的中介,康定斯基说“黄色是典型的大地色”,“蓝色是典型的天空色”,“黄色和蓝色的等量调合产生了绿色”[5]为此,绿色成为永不歇息的生命旅程的主色调,它向太阳转换了能量,滋养和辅助着万物的生长。绿色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它掠过严寒,昭示着生命之春的来临;它铺设在大地上,使人与万物有了生命的暖床;它甘于寂寞,甘做陪衬,辅佐火样的花朵,为人类的栖息铺设着温柔的地毯,如此种种,绿色是自然的象征,绿色是生命永恒存在的象征。
当代西方的绿色哲学也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绿色哲学实际“是一种环境科学,用逻辑思维来研究一切有关人类环境及其存在的有关事物的科学,这种事物可以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也可以是抽象的思维或信仰。”[6]绿色哲学可以给予我们一种思维方法,为我们建立一种绿色思维和信仰。但这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应该时时体现在现实的人类活动中,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的生命体验活动中,因为我们所把握的绿色作为自然之色、生命之色,是生态审美之色,它伴随着人们的生命活动,深蕴在人们的精神生态结构中,更时时通过人们的精神活动表现出来。
四、自然审美的基础性
当人开始与天地自然在一个共荣的生态和谐圈中交往与互动之时,人就对自然产生了无尽的依恋情结。从原初的人类对自然存在模仿与依赖之始,在自然产生的无限的崇敬之情中就同时引发了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自然审美意识由人对自然的情感性关注与情感体验而产生了自然的审美体验,不仅使自然现象成为最早的审美形态,同时对自然现象的体验而产生的审美意识也成为人类最初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生存意识。
自然审美对人类生存来讲具有先在性、本源性、基础性,是激发人类情感想象活动,蕴聚生命体验活动的前提,它不同于后天发生的人工审美。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解决生态存在的最为一般性问题,就是解决环境问题。自然审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环境的审美,环境审美是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的统一。人类的生存环境实际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两大方面,自然环境是基础,人工环境是人类的后天创造,自然环境的必然性是人工环境所无法替代的;人工环境按照人的审美意识所创造,它含有自然美的意蕴,也含有艺术美的意蕴,但与人工环境无法替代自然环境一样,人工环境的审美也无法替代自然的审美。
任何对环境的美化都是人为的,尽管人类创造这种人为环境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但环境的制作往往又处于一种悖反的状态,即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破坏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形态,反过来又创造人为的环境去装点自然,而为人类服务。不管怎样说,人类是这样做了,并且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如果是做,那么人为环境的设置起码应该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以不违背自然生态为基础。人类以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的环境设置实际是为自己生存付出的代价,这是非自然性的,更是非生态性的。罗尔斯顿在评述这种现象时说:“如果自然景观的美化是要用推土机削平半座山峰,在上面修起高楼,又以带了伤痕的自然景观为背景,种上人工灌木丛,那就是非自然的。”[7]其次是符合激发人的生命机能,创造人生态性生存活动的前提。人为环境的设置有时是刻板的、主观的、随意的、功利的,尽管有时它确以自然景观为参照,同时也可以不同程度地弥补自然环境的杂乱与无序,但它往往是以打破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以及剥离自然与人生存的和谐为代价;或伴以由于物种生存环境的位移,而打破生物多样性的规律,破坏生物存在的和谐状态;或伴以对气候、湿度等规律的紊乱。显然人为环境往往使人难以找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温馨,难以与自然景观激发人的生命活力的魅力相匹敌。
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8]马克思从人化自然界的视域论证了人类赖以存在的两种自然界,两者都是属人的。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讲是“无”,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并且是不断向人生成的自然界才是有意义的自然界,所以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9]从马克思对自然界的意义性论述中我们可以把握,对于人类的存在说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在向人的不断地生成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就使得自然史与人的发展成为一致的。我们从人类的审美活动中体验这种自然历史与人类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似乎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与我们朝夕相伴的自然界,我们所感受与体验的自然美给我们带来的是实体性的生存感受,还是什么?
自然美给予人类的主要不是实体的存在,而是生命的存在,是生命的机能;自然生态循环与和谐也是向人类表征生命存在的机能。生态美实际呈现生命的美,生态审美必然显现生命的审美。人类应该在生态审美活动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发,体验着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生命存在。生命活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起始于自然生命力。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力超越自然生命力,可以改变自然生命力的欲望性存在状态,使之具有理性意识支配的。人还可以把生命力的存在作为追寻自由存在的中介,同时人也把自由的存在视为生命的存在,使生命的存在始终处于“新”的状态。因为人在审美的体验活动中,实际是在体验生命的活力,感受生命的韵味,而不是简单意义地去把握“生”,去认识生与死,更是在全新的意义上去体验新的生命存在。
自然审美面对的是实体性自然存在物,但他把握的却是内蕴的无限的生命机能。生命是自然界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自然审美是人类审美活动的基础,审美活动是人类体验自身生存价值的终极展示。审美活动中,艺术审美作为人类高级的审美体验方式,是最能展示自然审美的精神品格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审美以自然审美为前提,并从自然审美中汲取了无尽的滋养,艺术审美和自然审美的融通是最能体现人类生态存在的生命机能。
五、文艺审美的启示性
人类是天地自然化育出来的一个精灵,他既能仿效自然而繁育自身,又能仿效自然而润化万物的生长,并且又在“心师”、“模仿”万物的生长中润化自身。人在润化自身中,既能创生新质,能感性的驱动生命力的再生,又能理智性地朝向生命的未来,人就是在这特殊的灵魂境界中体验生命的灵性。这种生命的灵性之境,可谓生态之境,亦为审美之境;其繁育和润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人类的生态体验过程,亦为审美体验过程。文艺审美的生态之境最能启悟人之生命“性灵”的创生,以“心源”培育人的精神生态平衡。从而在人类生态系统的和谐性体验中感悟人类生存对自然的力量。
人在文艺生态审美的灵性之境中体验生态之“性”,并以强烈的情感亲和力去践履由“知性”到“尽性”、“体性”的过程。“性者”,本于自然,始初并无所谓“情”,但要“成于心”就必融聚“情”;聚“情”、“成心”,并配以“至诚”之理,方可提升人的精神品格;平衡人的精神生态,方可化育万物。《中庸·尽性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并列而成三才,禀赋天地之本性,发抒生态之灵性,极尽融通“人之性”和“物之性”,从而以“赞天地之化育”,“造化”生态审美之境。郑玄解其说:“赞,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10]人之生必依天地之生,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只有使天地归位,万物化育,方可以有人之无限的生,充满灵性的生,此即为“中”,是“天下之大本”;亦为“和”,是“天下之达道”。所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天命章》)
天地人三才,万物化育,于是《易传》就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11]。作为生态智慧,这种“化育”机制,必然成为生态审美体验的肌理。在生态审美体验状态下的人,必然是以强大的生态亲和力包容天地,化育万物,呈现对以自然事物为主要审美对象的肯定与确证。其亲和、包容、化育必然会遵循生态系统的构成节律,从而使生态循环的和谐链条成为可能。审美活动本应是体验人类自身的终极存在,而终极存在不是远离自然界而孤立的品味自己,而是在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走向人类的未来。生态循环和谐链条的运转就指向人类在对未来世界的追寻。文艺活动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方式,也是审美的最高形式。在文艺审美活动中人可以消除现实的功利性,而消融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使自己成为“知性”、“尽性”、“体性”之生命的生灵,从而参天地,以化育万物。人类追寻生命自由的历史,也是审美的历史,文艺审美活动的历史,也可以映衬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细致地品味人类文艺审美活动的历史,足可以启悟到一个生态体验的历史,尽管它更偏于精神生态的体验。因为在文艺审美活动中,主体面对自然对象,剔除功利,而“心师自然”,化育自然,在和谐圆融的精神境界中从事生态体验。事实上,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以及人的多种存在状态中,只有两种活动和状态是弱化现实功利的,一是文艺审美活动,一是生态状态。
在文艺审美活动中,“心师自然”,往往是主体消融在对象世界中,在对象是我,我是对象的情境中而“得其心源”。心与自然宇宙的生态性关联,首先表征着人与宇宙自然本是两个实体性的存在,是“在场”者,但在情感的撞击声中,两个“在场”者迸发出生命激情的火焰,遮蔽在幕后的隐蔽者便会粉墨登场,于是乎宇宙搏动着人心,人承载着宇宙,一种生态创生的魅力在那种“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中生成,在那种澄明世界中创生的审美人格便是生态性的人格。他启示着四时、日月富有生命节律性的更迭运转,作为天道化育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在节奏与韵律的音乐叠合中使生命勃发,创生着那种被儒家先哲们称为“至善至美”的生命境界。为此孔子便发出慨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尽管孔子未必是出于审美的目的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他对自然世界的领悟,对自然、宇宙的存在之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意义地领悟却是极为深刻的,因此,他绝非从占有性的意义上去理解自然与人的存在,这实际也是孔子的和谐论存在观。孔子曾深切地赞誉尧禅让王位给予舜而有的《韶》乐之美,并视为是至善之乐;批评因武王伐纣而有的《武》乐虽为美,但由于这是武王通过战争这种不和谐方式取得的统治权,所以孔子认为这是不善之乐。孔子的那种以“仁爱精神”为核心的和谐论存在观不仅是对人,就是对自然物他也强调需要有爱的存在。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孔子在钓鱼时,不用大网,在射猎时不射击树上栖息的鸟。作为“在”者,这表现了孔子对弱小生物的仁爱与尊重,同时作为隐蔽在“在”者之后的“不在场”者,更是他对自然存在物的生态关注。由孔子所导引出的这种“知性”到“尽性”、“体性”思想,已经表现了极为深刻生态智慧,其内蕴即为《中庸》所论“赞天地之化育”的“至诚”思想。
由天与人的合一而引申出的,自然物格与人格的合一也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们创造生命灵性境界的主要方法,实际是一种文艺生态审美活动。儒家先人所奉行的乐教,即强调从自然万物循环—和谐结构所内蕴的生命存在的生态关联性中,通过自然审美体验汲取人格存在的精神美感,以自然存在的活性动力之美感滋养和陶冶人的生命灵性。在中国古代人那里,“天”除了具有本体之“一”,以及“大”的存在性之外,同时还具有清明、空灵之态;以乐和天而产生的人的志清、聪明、血气和平,致使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尚清”品格就处于一种生态美感状态中;“清”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还包含有静气、平静心态之意,这些都具有“去欲”、“消累”的功能,以表现自然生态体验和精神生态的整合。
六、人文智慧的关怀性
人文智慧的核心在现实视域中应该是人的存在,其未来性视域就是关怀性。关怀性不是脱离于人的现实存在,其内在意义应该是从整体性、未来性、目的性上,由对人现实存在的关怀,而导向对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而生态审美的生命境界就表现了这种关怀性品质。
人的生态性存在之于生态审美的合理性,首先是在关系性的存在中通过对自然世界的人文关注,而指向对世界未来的关注。不论是关注形而下的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还是形而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都应从对人及自然生物的现实关注,或者说是对自然界的生物性关注,而导向对人的精神灵魂的关注。从人文智慧的存在论与关怀论的整一性意义上看,人的现实的存在往往是异化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由对人类自身的特别关注而走向了异化。解决异化困境中的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呼唤人类的人文生命智慧,创造人的生态审美存在之境。人文生命智慧的存在是逻辑的动态过程,它是由人对自然的积极态度而表现的和谐状态下的关系存在,实际这是一个由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人化”过程,也是审美化的过程。因为人文精神品格的基本存在样态,首先就是这种“人化”,是人作为“类”的精神的体现,由“人化”的精神活动表现为精神生态和谐,而精神生态的和谐必然是生态审美活动中的和谐。
人文智慧是不断地超越人的现实“在场”的存在,而去感悟、理解、寻求,以至于澄明被现实遮蔽的“不在场”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从本质上讲就是“真实”的理想世界,也是未来的目的性世界,是人文追寻的终极世界。意义的终极澄明应该是在人与对象世界共同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得到展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应该是生态性的世界,是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共同构建的生态世界。《易传》中有一段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论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这里的“人文”应该是天地人共在的人文生态世界,既是自然之人化的创生性的结果,也是人之于天地共存的生态性感悟,由此而表现出人“化成天下”的生命智慧。在现实存在中人文智慧与生态智慧是一体化的,其基本意义可以表现为:其一是生存智慧。这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形而下认同和体验,其首先关注人的生物性的、个体性的存在状态,以探寻、追索现实人的生存方式和方法为自觉。其二是理性智慧。这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和人的存在本体的解析,同时展示人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形而上思索;既探悉人的原始存在,也表现人的终极实在。其三是生成智慧。这是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角度中,把握作为类存在的人的生命活动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把握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并且将人类的历史视为由自然向人不断生成的历史,从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视为生态转化和生态和谐的关系史,同时也把人类的生成史视为以生态创生性品质为精神构成的生成史。其四生命智慧。生命智慧首先是要肯定生命的个体性存在,凸显个体存在的生命活力和丰富多彩性。生命体验不是凝定的,而是在不断地体验创生性。人类只有在创生性体验中,才能把握生命的智慧,并将人的自然生命化成为精神的生命,使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合体“气聚”而生,以创造生命的价值。其五是审美智慧。审美智慧首先内蕴着人的生命智慧,是由对个体的、感性的生存智慧的体验而理性的生成人精神审美品质,是对人的自由品质的构建中来认同人的现实生命活动,因此,它是从整体性、关系性、系统性的生态关联中体现与澄明人的存在。
西塞罗称苏格拉底之所以倍受尊敬,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即把哲学真正带给了人间。并且在之后的人文主义者那里也不断强调“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13]的确“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应该是人类存在的永恒性主题,这既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切关怀,也是人类在生态性的生存状态中关注自身的现实与未来。人文关怀作为生态性的关怀,还表征着人必须在与自然的生态一体化中走向自己的未来,昭示着人类的未来必然是审美的、多重自由的和谐性存在,是生态审美化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