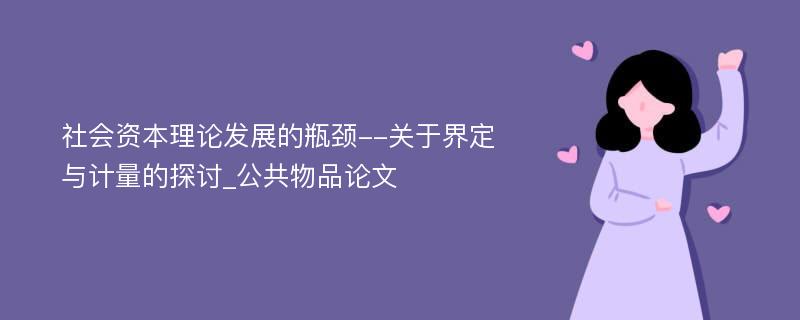
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瓶颈:定义及测量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瓶颈论文,测量论文,定义论文,资本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2—0102—05
目前,社会资本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它不仅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还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分析范式,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加强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对于研究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然而,社会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诸如定义宽泛、难以直接测量与比较等理论难题,这些理论难题若得不到解决,将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其理论价值。
一、社会资本的界定问题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资本已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最近几年,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已经从社会学理论领域进入日常语言领域,散布于许多政策性期刊和普通杂志之中。但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甚至相互矛盾,尤其是目前的一些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存在着对社会资本概念和有关理论认识不全面、不统一,社会资本概念模糊不清或片面理解等问题。而且由于社会资本被应用到众多的事件之中、诸多的背景之下,社会资本失去了确切的含义。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资本指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在一些情况下,社会资本又指社会关系网络本身或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资本又指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有时,社会资本指普遍信任;而有时,它又指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或包括其他东西,如个人声望、地位、文化规范、信任等;有时它还指个人成长时期的一些社会、社区和家庭等环境因素;在极端情况中,社会资本甚至包括除经济资源之外的一切东西。那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作为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分析工具,关键的一点是无法有效区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所包容的诸多不同含义。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确切的含义,社会资本遭到了许多批评。例如,林南对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中的严谨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社会资本研究迅速发展,其文献扩展到无数研究及应用领域时,这个术语成为包罗万象、能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危险性亦随之增加。布朗也批评说,虽然这个术语很快成了社会科学和决策圈内的常用词,但明确的含义却并不多见。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很少详尽地阐述过社会资本的理论细节。学者们开始批评这个概念的理论层次过低和用法过分简单化,但大多数人通过自己对社会资本的不同解释来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资本的概念过于不明确,而又被用于解释几乎任何一切东西,其遭到滥用的事实使人很难产生研究上的信心。
另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还表现在它发挥具体功能过程中的不明确性。社会资本既然是一种资本,就必须直接构成生产要素的一部分。但社会资本什么时候构成生产要素,什么时候又不构成生产要素呢?关于这一点尚无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任何一项经济社会活动,都会牵涉到经济要素之外的很多社会资源,但这些社会资源并不一定能够构成资本。在什么情况下社会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本呢?这一点也并不明确。从目前来看,社会资本已接近处于尴尬境地和受到类似嘲笑的地步了:那就是一切获得成功的事实都是因为有社会资本在后面予以支持,如果某项事物能给某事带来好处,那它就是社会资本。鉴于当前社会资本概念泛化的问题,若不能尽快确定它的精确含义,限制它的使用范围,将大大影响社会资本理论的说服力及其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有葬送这一理论的危险。
笔者认为,要改变当前社会资本概念泛化的问题,首先要严格区分以下几个概念:
1.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
社会关系网络是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强关系、弱关系;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等等。
社会资源是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所嵌入的各种资源,包括各种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例如权力、保障、资金、信息、机会、劳力、决策、情感支持、合作等。它是个体或组织所掌握和控制的资源之外的所有能够联系到的资源。
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只是社会资源的载体,社会关系是调动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渠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成分等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存量。
2.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是否能够被使用。上文已述,社会资源是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资源的总和,而社会资本则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那部分社会资源。一个组织或个体所拥有的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资源的存量可能很大,但能调动和利用的资源即社会资本却不一定很多。
3.社会资本与情感、信任、规范
当前,许多研究者把情感、信任、规范等同于社会资本,加剧了社会资本含义的模糊程度。虽然社会资本与情感、信任、规范等有着紧密关系,但并非是一回事。情感、信任、规范等仅是衡量或判断社会关系双方关系密切程度的指标,社会关系双方情感的密切程度、相互间的信任程度、规范的有效程度、相互服务程度等决定着调动和利用所拥有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的多少,情感、信任、规范本身并非社会资本。
4.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与宏观社会资本
一些学者按社会资本的主体把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微观社会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嵌入其中的情感、信任、规则等;中观社会资本指企业、社团、社区等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宏观社会资本指一个国家、区域的特征,包括和谐、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权威关系以及合作性的社会组织等。
社会资本分为三个层次的初衷是为了使社会资本的概念清晰化,但由于宏观社会资本的概念中含有太多的文化、道德、心理等因素,背离了布迪厄、科尔曼等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最初含义,即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而产生的资源,也使社会资本的概念更加模糊化。因此,社会资本的主体应严格限制在个人和组织层次,而国家、区域的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本)可构建另外一个概念来代替它,以有利于解决社会资本概念模糊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的定义应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嵌入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资金、保障、信息、机会、劳力、决策、合作等等。一个个体或组织所能够调动和利用的社会资源即社会资本是影响其发挥作用、实现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
如何精确地测量和比较社会资本的数量也是制约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一个问题。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已有很多,许多学者皆有论述。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e Bourdieu)认为,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1] 詹姆斯·科尔曼提出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这几个方面的值越高或越多,其社会资本的个人拥有量就越多。[2] 林南(Lin Nan)认为,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有下列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具体说来,就是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3] 边燕杰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的特性是影响其社会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特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主要指关系网络所涉及的人数的多少。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其中可能蕴涵的资源就越多;第二是关系网络顶端(简称网顶)的高低。关系网络顶端是指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地位、身份和资源最多的那个人的状况。每个社会关系网络的顶端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同的,高度越高,这个关系网络中所蕴涵的资源也就越多;第三是关系网络位差(简称网差)的大小。是指关系网络顶端与底部落差的大小。社会关系网络的顶端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同的,同时关系网络所能到达的底部也是不同的。两个关系网络如果其他方面均相同,那么落差大的网络要比落差小的网络蕴涵的资源更大。原因是位差大的网络可以更多地克服关系网络资源的重复性。[4] 韦恩·贝克采取首先测量个体社会关系网络,进而评估个体社会资本的方法,提出了测量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四个指标: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成分、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侧重点。
上述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特征以及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测量,但这些测量方法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虽然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但关系网络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它仅是社会资源的载体,是调动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渠道。因此,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特征的测量是间接和定性地估计,其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
其次,关系网络中嵌入的社会资源并不等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能够调动和利用的社会资源,而能够调动和利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即社会资本,还取决于关系双方情感的密切程度、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规范的有效程度、相互服务程度等因素。因此,对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测量,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本的真正存量。
第三,对关系网络中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权力、保障、信息、机会、劳力、决策、合作等的测量,存在难以操作化和定量化的问题。任何经济资本都可化约为一个统一的尺度——货币,并通过货币数量的大小来加以衡量。对于社会资源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权力、信息、机会、劳力、决策、合作等难以精确定量化的变量,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加以衡量,谁能准确说出某人的这些资源值多少钱呢?这限制了社会资源的可比性与量化能力,不具有可操作化,这大大加深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定量化分析问题的难度。
除上述在中、微观层次上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外,还存在几种宏观层次上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如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5] 另一种方法是基于对人们彼此有多相互信任的度量。[6] 这一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World Values Survey”,它是通过对40多个国家的不同人询问“一般来说, 你可以说出你所能信任的人的最大数量是多少或者你不需要特别提防的人有多少”来进行测度。再有一种方法是利用人们可观察的行为及市民参与等来实现对信任或社会资本的度量。例如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中,就使用了投票人的投票参与、报纸的读者群、非盈利性联盟中的会员数等来度量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的大小。[7]
暂且不论宏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是否符合社会资本的最初含义,是否属于社会资本。即使属于社会资本,对它的测量则更难以操作化和定量化。如对能动性、信任、安全感、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等主观和文化因素,如何确定测量指标,怎样才能精确地定量测量?这使得在实际研究中,在具体的测量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如果说社会资本概念在微观层面上加以测量存在一定难度的话,那在社会宏观层面上困难就更大了。例如,要准确计算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某个社会在特定时间内的社会资本总量,更谈不上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到目前为止,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仍然没有形成共识,也远未达到可操作化和精确定量化的程度,这也致使社会资本理论缺乏较强的说服力。笔者认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定义,即个体或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嵌入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那部分社会资源。其次,由于社会资本包括如权力、信息、机会、劳力、决策、合作等难以精确定量化的变量,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也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测量,因此,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可采用比较法,即一个个体或一个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在没有动用其社会资本时所付出的总成本额减去动用了其社会资本时所付出的总成本额的差就是社会资本的数值。也就是说,动用其社会资本时所节省的成本就是社会资本的数值。这一方法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并在实践中检验。
三、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特性、不可转让性及可转化问题
除了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问题制约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外,关于社会资本的特性,如公共物品特性、不可转让性及可转化等问题的模糊不清、众说纷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
1.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特性问题
国内外许多学者尽管对社会资本的表述不同,但都承认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一系列特征。其中,公共物品特性就是社会资本区别于其他资本的一个重要特性。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因此人们尽力创造这种资本。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对于收益者来说,它不是一种私人资产而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只能存在于两个人以上的人中间。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区别。
但是,尽管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资源,但对于以自我本位和个人主义价值为取向的人而言,社会资本这种“公共物品”的性质就不一定确切了。这些人作为自我支配、个人奋斗、自我实现的行动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往往靠自己去主动建构、塑造于己有利的社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可以完全为行动者自己所掌握而获得相应的收益的,尤其是对于不同关系网络的行动者来说,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共性”问题。这时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对个人来说更多地是一种私人物品而不太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这在某些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表述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8];布迪厄认为“……这种‘体制化网络关系’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9]
等等,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个人所有。因此,社会资本是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还值得进一步探究。
2.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问题
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社会资本的不可转让性,就是社会资本对受益者来说不可能由拥有者依主观愿望转让给另一个体而使之受益。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10] 因为每个人的社会资本都是独特的、与他个人紧紧依附在一起的,无法转让。社会资本的这种不可转让性对西方人来说可能是正确的,其个人本位的传统文化和基本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标准和人际交往方式。而在基本价值取向是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很多社会资本是可以借用、转让甚至继承的。例如,如果行动者甲拥有对行动者乙的社会资本,那么甲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让与自己有着亲密联系的另一行动者丙找乙,要求乙直接把义务偿还给丙,这时甲对乙的社会资本就转让到丙了。[11] 比如,妻子利用丈夫的社会关系谋职,丈夫的社会资本就借给了妻子。再比如,父亲持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如果他愿意,儿子可以通过父亲的关系来获得社会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社会关系正是像滚雪球一样由此延伸和扩展开来的。而在具有先赋性(ascribed)特征的社会当中,社会资本的可转让和可继承性就更为明显了。
3.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问题
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是大家所公认的,社会资本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其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实质性价值,社会资本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从而成为个人财富和企业经济发展的有效资源。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虽然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但这个转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经过许多周折。例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就认为,“经济资本可以轻易、有效地转化成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本,而社会资本虽然最终可以被转化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化却不是轻易的和即时性的”[12]。而在中国,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却容易得多。例如,通过对海外华人在中国内地投资过程中和我国引进外资中社会资本功效的研究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可以轻易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就海外华人投资内地中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收益来看,正因为海外华人与中国内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的关系,他们在投资内地过程中才能够得到亲朋好友协助,准确、及时地获得有关投资信息,比较容易地找到合作伙伴,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大大降低进入内地市场的成本和进入风险;其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减少了企业内的委托—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降低了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和管理成本。所有这些使他们迅速开拓并占领国内市场,获得巨大的经济利润。再从我国引进外资中侨乡的发展情况看,正因为侨乡与海外的华侨华人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侨乡在引进外资中才不断地得到海外华侨华人的捐助和投资,从而使侨乡的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和快速腾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就是说,在中国这种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可以轻易地转化为经济资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理论目前还尚不完善,诸如社会资本含义、测量与比较、特征等理论难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也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但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彻底解决社会资本理论的这些难题,完善社会资本理论,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标签:公共物品论文; 社会资本理论论文; 社会网络理论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