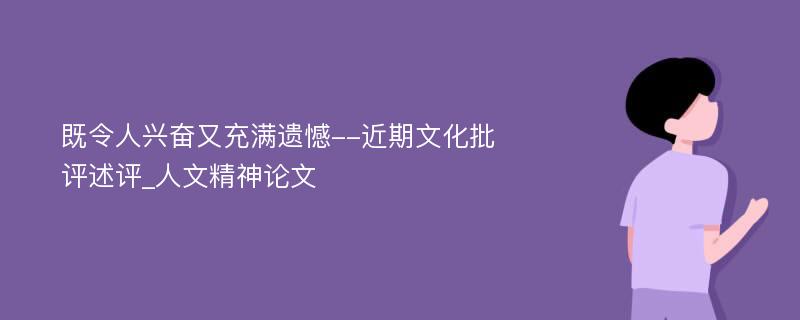
既令人兴奋 又充满遗憾——近期文化批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令人兴奋论文,遗憾论文,批评论文,近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的1995年,对于评论界来说,是空前活跃的一年,又是多少有点无聊的一年。尖锐的批评终于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派热热闹闹的混战;问题依然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但有深度的回应却甚少。
这是一个让人无比兴奋,又充满遗憾的年头。
90年代的精神背景
1989年以后,评论界曾经一度陷入沉寂。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使得整个社会迅速世俗化、实利化,原先以崇高使命为己任的知识阶层开始走向分化。然而,在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迫下,无论是坚守文化岗位的,还是匆匆扑向市场的,可以说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都显得有点匆忙应对,缺乏理性的自觉,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而已。
经过两年的震荡、分化和改组,知识界新的格局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90年代初期的沉默状态期间,伴随着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省,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暂时处于某种过渡性的“失语”状态。几年的闭门读书和潜心思考,使得大多数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开始亮出旗帜,尝试表达自己新的思想理念。
这样,自1993年秋后,随着结构分化的形成和知识范式的调整到位,评论界走出“失语”的阴影,开始了日趋激烈的思想交锋。先是关于王朔、《废都》和顾城的争论,随后是1994年起始的人文精神以及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大讨论。尤其是人文精神的讨论,使得一度零散的评论界重新找到了众所瞩目的公共话题,涉及面之广、争论之热烈,足以与80年代文化热期间的公共话题“传统与现代化”讨论媲美。这自然与90年代知识分子面临的语境有关。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化人如何自处,如何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如何看待这个变化了的世界,这些问题成为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公共境遇,早已分化的不同群体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旦找到人文精神这一冲突焦点,自然掀起争论的狂澜。
95年知识圈的精神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展开的。严格说起来,去年的评论界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话题,小说、散文、影视乏善可陈,缺乏闪光的兴奋点。话题的焦点继续停留在人文精神上,然而,讨论不是往问题的深度开掘,而是横向拓展开去,牵出一连串的人与事,从而带有表面热热闹闹、骨子里空空洞洞的戏剧化色彩。
在去年的文坛上,比任何戏剧、影视和小说更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关于“二王”(王蒙、王朔)、“二张”(张承志、张炜)的争论了。这一争论的中心话题可以说是人文精神讨论的续集,即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背景下,如何看待现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问题。因为“二王”和“二张”这几年异常活跃的言论和引人瞩目的姿态,被世人分别视作现世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人格象征。去年的文化论争一反已往的“问题中心”方式,而更多地聚焦在对具体人物的评价上,尤其是“二王”和“二张”身上。
批评规则的匮乏
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争论,自然有其便利之处。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以来的大分化,如果从世俗和精神这两极来说,“二王”和“二张”无疑有其代表性。以一种风格异常鲜明的感性主张或人格形象作为批评的文本,容易将问题挑得比较鲜明,但也有可能纠缠于具体人物的个人人格、品质的褒贬,反而遮蔽了真正的、有深度的普遍性问题。
95年的文化批评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许多批评不再躲躲藏藏,闪烁其词、不管批评的对象是文坛泰斗,还是无名小卒,大多直呼其名,拎到前台。如此具有针对性的批评可以说是大陆文坛多年来所未见。以前在历次运动中有“点名”的说法,那是政治策略中的威慑伎俩。而如今的点名批评基本不具有政治的、权势的背景,属于在没有外在压力的语境下知识分子内部自由讨论的性质。比起80年代以来形成的那种“某人”、“某说”之类照顾情面、闪闪烁烁的批评,当然要真诚坦荡得多。不过,在自由的批评环境下,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如何构建文化批评的游戏规则。
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之间最直接的思想沟通。沟通的行动,总是通过一定的对话方式进行的。尽管在思想多元的时代,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一种超越于所有不同话语之上的、提供相互交流最一般基础的“元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可能建立对话和沟通的形式化的元规则。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行动理论时,提出过一个普遍性的有效性假定,即“三真(正)原则”:一是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二是真诚性,说话者不是想有意欺骗听众;三是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的语境中特定的规范。〔1〕无疑,这也是文化批评应当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元规则。
也许是一种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污染的自由批评刚刚开始,我们的批评家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批评规则的重要性——就象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起步时,商人们也顾不上起码的市场规范一样——的缘故,偷换概念、故意曲解、混淆问题、带球撞人等现象几乎成为当前文化争论中不无普遍性的时弊。在这方面,作为文坛知名人士的王蒙,在争论中的一些表现是不敢让人恭维的。他先是在批评人文精神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抽去90年代提出人文精神的具体语境,将之曲解为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态势的不满和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留恋。随后,在对“小人物”王彬彬的反批评中挖苦后者是假批评名人而图谋出人头地的“黑驹”。自然,类似的犯规则不止王蒙一人,他的一些论战对手以及其他批评家也有相似的毛病。所谓的“二王(王蒙、王彬彬)之争”后来因刘心武等人的加盟而延伸为“高长虹评论之争”,更是一场观点模湖、“敌”、“我”难辨的大混战,好看虽是好看,却不见多少有价值的问题提出,仅显示出文坛的无聊而已。
由于批评多针对具体的人与事,所以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弥漫着一股相当浓郁的道德气味,无论是对“二张”的颂扬,还是对“二王”的抨击,更多的兴趣不是以一种理性的智慧解读对象,而是从道德的立场出发作春秋褒贬。文化批评自然不同于学术研究,可以有批评者自身鲜明的道德立场。何况中国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度,世俗信仰系统的疲软,人们更要求文学或文化批评能够承担一部分道德说教、人生教化的使命。然而,道德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批评的道德,这一道德按照理查德·罗蒂的话说是“容忍、尊重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2〕
95年文坛争论最激烈的话题之一是所谓“不宽容”问题,即对社会的某些现象是否要持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不宽容”立场。本来,讨论这一问题,在思想预设层面也许必须厘清两个区分:其一是价值与道德的区分。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是合二为一的,有价值的东西必定也是道德的。但在现代多元社会里,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二者发生了分化,有些问题(比如文人经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并非道德层面的问题。价值的问题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加以讨论,而不能用道德审判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二是美德与正当的区分。即使在道德领域,也有高调与低调之分。正当问题涉及到人的基本道德义务,比如不能欺骗、伤害别人、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财产权以及遵守各种游戏规则等等,这些低调的义务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须普遍履行的。而美德问题比如乐于助人、富有教养、反抗邪恶等等可以是个人自勉的高调理想,而不能作为苛求他人的道德律令。可惜的是,在关于“不宽容”的争论中,这些区分虽然已有论者涉及,但并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的注意。持有激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张承志、张炜和王彬彬等人再发生“道德观念的误置”,将本来属于价值观或美德领域的问题作为基本的正当问题加以讨伐。由于道德审判对象的扩大化,反而放过了真正应当谴责的邪恶势力和不正当行为。文化批评中“道德观念的误置”屡屡发生,表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和思想预设仍然受控于前现代的一元化知识结构,而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代多元社会。
效果意识压倒清明理性
中国文人的宗派问题一向是难愈的顽症,在95年的文坛之争中又一次暴露无遗。由于众多的批评明显地指名道姓,而且针对具体的人与事,使得本来就隐性存在的宗派矛盾表面化。某一圈子里的盟主受到了批评,圈内的兄弟哥儿们会齐心协力,拔刀相助;某青年学者在论战中发表了一篇观点平和的分析文章,就有人猜测作者貌似中庸,本意在为某某解围;人文精神的讨论首先由上海发起,于是上海的学者、评论家似乎都被认为是“人文精神派”,而且还要妄猜背后究竟谁是盟主……如此做派颇类似过去的袍哥会党或“阶级分析”路数,最关心的不是是非对错,而是究竟属于敌、我、友何方阵营。一些批评者不是严肃地探讨问题本身,而是以一种“打擂台”的狭隘心理介人论争,唯恐别人占据了话语的中心。本来,知识分子最要紧的是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他首先是作为个人的存在,而非依附于哪个地域、哪个帮派或哪个利益集团。然而,一旦宗派的情绪在论战中占据了上风,就会使正常的文化批评染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色彩,从而更显得庸俗无聊。
批评界的无聊化趋势,同媒介与出版业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这几年大量报刊的创办、改版,电子媒介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扩张以及图书市场的部分复苏,使得文化消费的需求被大大刺激和释放出来。本来纯粹属于知识圈内部的文化批评,在90年代的语境下突然具有了某种市场消费的价值,可以满足知识大众观赏的欲望,提供他们茶余饭后以助消化的谈资。多元化的文化市场的确是一头温柔而又厉害的的怪物,它可以容纳任何激烈的、偏激的声音,使之在市场上成为某种畅销的文化消费对象,从而消解它们的批判内容,变为无伤大雅的高级牢骚。以“精神圣徒”形象出现的张承志在95年的命运就是如此。尽管他一再地自我放逐,远离俗世,宣称“反正今天比昨天更使我明白:我只有一小批读者”,〔3〕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与另一位以反抗媚俗自居的张炜一起,成为95年图书市场上最具卖点的作家之一,他们所有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大红大紫的畅销书。命运就是如此残酷地捉弄着他们:当他们还是自己的时候,他们并不为公众所了解,而一旦被市场所接受,他们就不再是自己。拥有一册“二张”的书籍,谈谈“反抗媚俗”、“抵抗投降”,竟然成为95年大陆知识大众群体中最为时尚的媚俗。“走近张承志”的含义是那样地暧昧,以至于其真实的内涵不过是“消费张承志”而已。在90年代的语境之下,一个知识分子假如不甘寂寞,希望参与社会,反抗时弊,只要他取得些微的成功,都可能是一种异化的胜利,最终沦为所反抗的对象本身。
应该说,这样的结局并非当事人的初衷,但市场的逻辑却远远强于他们自身的意志。一些传媒编辑和出版界的策划人,为吸引读者和观众,不惜小题大作,故意制造焦点、热点和卖点,热衷于组织论战,制造出一种“阿庆嫂和沙老太婆打起来了”的戏剧化氛围,从中坐收商人之利。而一些文化人为赢得市场的效果,也不惜放弃理性的原则,专挑刺激的、煽情的和尖刻的字眼做成标题、编织文章。一时间,什么“抵抗投降”、“学会憎恨”、“文化冒险主义”、“时代内部的敌人”一类久违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术语,再度在文坛复兴。文化批评的概念工具是否真的已经如此匮乏,以至于不得不借助于政治的或准政治的语言才能流畅地表达,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热衷于这类话语的批评者不是看中了它们的市场价值,就是自己的文化思维方式还不曾“清洁”,依然残留着过去岁月意识形态的污痕。
由于圈内圈外过于注重批评的市场效果,以至于95年的文坛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似乎谁的姿态最鲜明、观点最尖锐、语言最煽情,谁就拥有最多的听众,成为最红的文化明星。在95年文坛上,替代严谨、具体的理性分析的,是一种卷土重来的机械化思维模式。类似这几年时兴的激进/保守分类方法,一些批评家以所谓的理想主义/现世主义、人文精神/痞子精神等二元式的思维模式将复杂的知识群体加以简单地分类排队,似乎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赞同“二张”的必定属“二王”一党,呼吁人文精神的就统统等同于张承志式的“神学询唤”或道德理想主义,甚至还张冠李戴,将余秋雨列入“抵抗投降”的“文学英雄”行列,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不重思想、只重立场的时代似乎重新降临。人们所偏好的多是那些立场分外坚定、而思想相形见绌的文化明星。而在理想主义与现世主义之间执着地探索着中间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持论比较理性平和,态度不那么极端固执,因而受到人们的忽视和冷遇,甚至面临着为对立的双方都不能理解和容忍的尴尬局面。公平地说,这些仍然保持着清明理性的、在“夹缝中奋斗”的自由知识分子,比起那些风头十足的对阵双方,往往具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他们充分理解市场经济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但对工具理性在生活世界的扩张保持着一份警惕;他们反对以道德理想主义粗暴地解读这一日趋复杂的世俗社会,又积极希望以多元的、开放的文化阐释赋予生活世界以人文的意义。不过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些立场极端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曾边缘化过,无论在政治舞台上、还是文化市场中,都是万众瞩目的中心角色,不是扮演悲剧,就是出演喜剧。而真正边缘化的倒常常是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具有独立性格的自由人士,95年的文坛不幸又一次重现了这一被时间反复验证的历史景观。
上海《文汇报》记者在评述1995年文化批评的专稿中,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过,热闹是热闹了,大大满足了看客们的消费欲望,却让“内行”们越看越糊涂,不知道论争的门道究竟在哪儿。这一年留下了许多热闹的话题,却没有留下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年太多才子气十足的急就篇章,却甚少深思熟虑、真正有份量、经得起时间玩味的心血之作。
注释:
〔1〕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2〕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3〕张承志《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