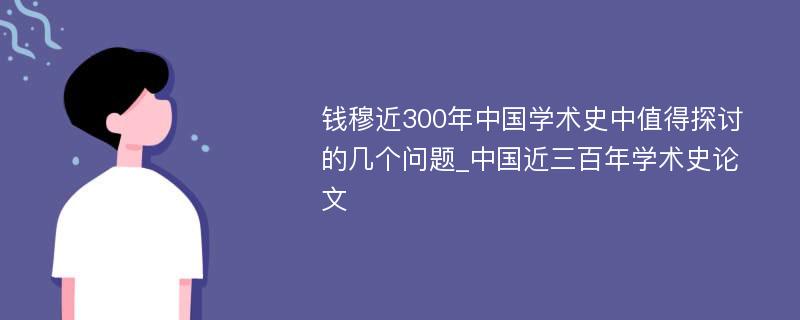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论文,三百年论文,学术论文,钱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而言,有略胜梁启超同名专著一筹之处。但钱氏之评史论事亦每有容商榷处。今试指其瑜中小疵数点,此亦不为尊者讳之意。
1.从谋篇布局上看,钱著之体例编排最容商榷处,是他漏列了崔东壁(述)。崔述集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考信录》一书,堪称我国古代疑古史学的集大成之作。以顾颉刚为首的现代“古史辨”疑古思潮,亦因藉对崔东壁的介绍和《崔东壁遗书》的标点刊行而勃兴发达。关于崔述对当代思想界的影响,钱氏一九三五年为《崔东壁遗书》作序时曾说:
“初,胡君适之自海外归,倡为新文化运动,兴世奔走响应惟恐后。胡君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为作长传,曰《科学的古史学崔述》。流布仅半篇,未完稿,然举世想见其人,争以先睹遗书为快。胡君友钱君玄同,读东壁书,自去其姓而疑古,天下学人无不知疑古玄同也。而最以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盖有进,为《古史辨》,不胫走天下。”
钱氏此《序》与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撰于同一时期。《序言》所论东壁对于现代思想界之影响,颇中肯綮。从中也可知崔东壁对于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钱穆原也是承认的。但钱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竟不列崔述,原因何在?这是否与钱氏在总体上对疑古思潮不以为然甚至反对有关?此不得而知。但崔东壁及其对当代思想界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一部反映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总体发展的学术专著,钱著漏列崔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陷。这与梁著的所列崔述相比,后者所列虽然简短,其论亦浅,但比起钱著的漏列崔述来毕竟要好。钱著之失是显而易见的。
2.钱著之论戴东原。戴震这个人,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坚持反对宋儒,力排程、朱,对于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以理杀人”,戴震的批判尤其不遗余力。因此之故,胡适于一九二五年写了一部《戴东原的哲学》来表彰他。胡适在该书的《引论》中说:
“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到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注:《戴东原的哲学》第1页。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下同,不另赘。)
胡适的这个论点,与梁启超的“反动说”相似,即都认为宋明理学到清代就中断了。胡适的这个论点,与梁启超的反动说也同样名闻遐迩。二人之说是当时持此种论调最有代表性的两家,一如钱氏绝对不能同意梁启超的“反动说”一样,钱氏亦绝对不能同意胡适的“消歇说”。与此相关联,钱著之评价戴东原,便多有针对胡适所论而发者。例如,胡适认为,“我们为他(戴东原)的两部哲学书——《孟子定义疏证》和《原善》——不能不疑心他曾受著颜李学派的影响。”“我个人推测起来,戴学与颜学的媒介似乎是程廷祚。”“我们研究戴震的思想变迁的痕迹,似乎又可以假定他在三十二岁(一七五五)入京之后。”(注:《戴东原的哲学》第22页。)针对胡适此说,钱著谓:“戴望为《颜氏学记》,尝谓乾隆中戴震作《孟子绪言》,本习斋说言性而畅发其旨,近人本此,颇谓东原思想渊源颜李”。这里的所谓“近人”,即指胡适。钱穆认为,胡适之说并无确据。“东原与绵庄(程廷祚)虽相知,而往来之祥已难考。”东原思想之最要者,一为自然与必然之辨,一为理欲之辨。此二者“虽足与颜李之说相通,而未必为承袭。”“思想之事,固可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相视以莫逆,相忘于无形者。”(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5页。)钱穆指出,东原游扬州而结识惠栋,此后东原论学宗旨即由徽学之尊宋述朱一变而为近于惠栋的反宋诋朱。因此,结识惠栋当为戴震思想转变之至要者。钱氏又指出,惠栋的《易微言》言“理”字与戴震甚近,故云“惠戴至近,何必远寻之颜李耶?”(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7页。)
今按,胡适、钱穆二人所考戴震《孟子定义疏证》及《原善》之思想源起,从思想内涵分析的角度看,似以钱氏所论差近实耳。但胡适据段玉裁《年谱》所论戴震与程廷祚之交往,而谓东原受绵庄影响,此亦并非无稽之谈。问题在于,厘清戴震的思想渊源固然重要,但如何评价戴氏的思想似更为重要。我们看胡适从分析戴震的天道观入手,绵延而及戴氏的性论,并时时以之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以及从中引发出来的“天理人欲之辨”相对比,胡适的要旨,在于伸张戴震所批判的“以理杀人论”。戴震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以心,因此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为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法救矣!”胡适据此批评宋儒道:
“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譬如一个人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分明是一个人的私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竟害死了无数无数的妇人女子。又如一个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又分明是一个人的偏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遂使无数无数的儿子媳妇负屈含冤,无处伸诉。八百年来,‘理学先生’一个名词竟成了不近人情的别名。理与势战时,理还可以得人的同情;而理与势携手时,势力借理之名,行私利之实,理就成了势力的护身符,那些负屈含冤的幼者弱者就无处伸诉了。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遂渐渐成了父母压儿子,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注:《戴东原的哲学》第56页。)
胡适据戴震的“以理杀人论”所作的发挥,是符合戴震的原意的。胡适所抉发的戴震思想中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内容,是戴震思想中最具价值、最为光彩的部分。对此钱著却每从方法论的层面加以指责。方东树《汉学商兑》诋戴震谓:
“程朱所严辩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谓以意见杀人,此恒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钱著整段引用了方东树此论后指出,“方氏之论虽底毁逾分”,但却得宋儒论“理”之义的一面,“植之则谓宋儒辨理欲,本亦为立言从政者之心术言之也。惟其如此,故东原辨理欲虽语多精到,而陈义稍偏,颇有未圆。”(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9页。)
宋儒严格辨理欲,其关注的重点到底在上还是在下?即是说,宋儒之辨理欲到底是为了抑制统治者的贪欲呢?还是要抑制百姓的欲望?此不可一概而论,两方面容或均有之。问题在于,宋儒即或有意以理欲之辨来抑制在位者的贪欲,其效果究竟如何?靠读书人讲两句“存天理,去人欲”的话,就想杜绝在位者的贪欲,这可能吗?我们之所以说它不可能或基本上不可能,那是因为贪官污吏手中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恩赐,而皇帝的权力来自于老天爷。权力的来源者才可能成为权力的制约者。也就是说,只有老天爷才能管得住皇帝,凡人不必去动这个脑筋。所以,单单讲正心诚意修身,再添上几句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对在位者的贪欲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或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假使在位者拿了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来对付“在下”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正如胡适所说“理与势携手时,势力借理之名,行私利之实,理就成了势力的护身符,那些负屈含冤的幼者弱者就无处伸诉了。”所以,宋儒的理欲之辨,其所造成的社会实效,就成了或主要成了在位者在对在下者压迫和奴役的口实。戴震揭示了在位者、尊者、长者利用“理”所造成的结果,总是卑者、幼者、弱者的“失理”,这才是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精华所在,也是戴震《孟子定义疏证》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钱著何以不对戴震批驳宋儒的“以理杀人论”深论一番,羽翼之而强化之,有如胡适所为者?为什么他却要抓住戴震的论证方法不放?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戴震排宋斥朱的立场是钱氏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戴震在排宋斥朱的立场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钱氏也就不能嘿然无语而必要加以申斥。实际上,对于戴氏既褒又贬,这早在章实斋即已为之。一方面,章氏称赞戴学“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博雅考订以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文史通义·朱陆》。)这里,实斋对戴学的推许,是因为章氏认为戴震的治学能以实证虚,以考证明“道”,这既弥补了宋明理学论道的空泛,又比乾嘉诸学人龁龁于名物典制的考据高明了许多。但章氏对于戴震排宋斥朱的立场又极为反感,认为“戴氏……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注:《文史通义·朱陆》。)章氏又讥戴震之斥朱乃数典而忘祖。今试以钱著之论戴氏,与章实斋之论戴氏相较,二者又何其相似乃尔!钱氏对于戴震之赞,亦因戴学路径渊源于朱学,戴氏未躭躭于名物典制之考据,而以明道为职志。此宋学气象也,故钱著谓戴震与实斋为“乾嘉时最高两大师”,原因在此;而钱穆之斥戴氏,亦全因戴震之斥宋排击朱熹而起,认为戴氏此论实为对宋儒之大不敬。然而平心而论,程朱的理欲之辨,造成历史上在位者、尊者、长者以“理”压迫卑者、幼者、弱者,戴震对此加以批判,我们正当礼赞戴震,因为这正是戴震的卓越处。如果因为戴震出自朱学体系就认为他不可以反对朱熹;因为推许宋明理学,便把理学划入批评不得,议论不得的“禁区”,这不是把理学变成了一种钱氏自己也一贯反对的门户之学了吗?
3.钱著之抑戴震,申焦循。钱氏对焦循之学极为推崇,谓焦氏足以与章实斋、戴东原相鼎足,其论“颇若时兼东原、实斋两家之长。”(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7页。)然钱著又每发为抑戴申焦之论。钱氏认为,焦循论性善之要义,一曰义之时变,二曰情之旁通。钱氏以焦循此论与戴东原的“能蔽”、“去私”说相比较,认为焦氏之说“似较东原尤完密焉。”(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0页。)又说焦氏论性分之不同,亦“非东原所及”。(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66页。)但我们注意到,钱穆之赞焦循论学,多取证于焦氏的《论语通释》。《论语通释》同时也是钱穆对焦氏著作中最为推许之一种。而在《论语通释》中有焦循评论吕坤的“理尊于势”说。焦氏说:
“明儒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时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礼,未闻持礼以与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按焦氏之论迂腐不堪,与吕坤之识见其相距真何啻天壤!焦氏抑且不及戴震识断之万一!钱穆一定细读过焦氏此论,何以竟然对此不置一喙,轻轻放过?何以不合焦氏此论与戴震批判宋儒的“以理杀人论”作一番对比?且戴震批判“以理杀人”,正是理势之争的绝好例证,钱氏亦向“以师道自尊”,认为“不为相则为师”是“宋明学者之职志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而钱穆对焦氏之迂腐却嘿然无语,此何以服膺人心?钱氏之申焦抑戴,非为抑戴而抑戴耶?非为对戴震之成见所致耶?
4.钱著对清代今文经学的评价。道咸以降,外侮渐作,国势日见凌替,文化思想的发展亦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乾嘉朴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晚清今文经学初甦复苏而渐次壮大起来。晚清今文经学独好《公羊》,他们既不满意标榜为“汉学”的乾嘉朴学之琐碎鲜有议论,乃欲由汉而返诸宋。而西汉公羊学既有“汉学”之名,而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又足以附会为经书义理而与宋学灵犀相通。晚清今文经学乃高举起公羊学旗帜,一可以以七十子后学所嫡传之“汉学”与清代的“汉学家”相角,又可以今文经说之微言大义与宋学通。是故晚清今文经学家皆不反宋,或取汉宋兼采立场,其根源在此。但晚清今文经学家仅以说经为端由。他们的治学方法虽亦由考据(因经说有此需要)一路而来,其旨意毕竟是落在用附会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以经说干政上的。因此之故,晚清公羊学多窳陋。钱著从学术本体的立场出发,于此一点的抉发最为深切而著明。钱氏谓“晚清今天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32页。)因此,“近人乃认晚清今文学为清代经学考证最后最精之结果,则尤误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8页。)书中指责康有为、廖平的治经:“若康、廖之治经,毕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52页。)钱氏此说确实是康、廖辈治学方法的根本缺陷。为了拔除公羊家通三统之说的根基,钱穆更谓:
“治公羊通三统之说,固必求其制度,而尤有一更要义焉,则帝王非万世一姓,及其德衰,必则贤禅让是也。此汉儒自董仲舒以下皆言之,极于王莽之代汉,亦自公羊通三统而来。长素盛尊公羊而力诋莽歆,高谈改制而坚主保王,则义不条贯,非真能知汉儒公羊家精神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60页。)
这里,钱氏用“入其室而操其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深深地刺中了康有为一派今文家治学的理不符实,“知”、“行”相分的要害,足令康有为辈为之掩口无对。又如钱氏讥弹康有为倒填《大同书》著书年月,称此为“篝火狐鸣”,“所谓国师公(指刘歆)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正不啻其自供状也。”(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01页。)所论极酣畅淋漓。语虽尖刻,理却平实,康有为辈确是有可讥弹之处的。
然而,钱著从学术上对晚清今文经学所论者多,从政治上对晚清今文经学派的批评却嫌不足。而晚清今文经学派恰恰是著眼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基本信条,以学术干政的。即是说,若仅仅或主要从学术本体出发,对晚清今文经学进行评论,而忽略了晚清今文经学的社会政治效果,那是有失全面的。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似乎比钱穆看得要准。梁著论龚自珍谓: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这就是完全从政治宣传而非学术的角度对龚氏进行的评论。而龚氏之价值,亦恰恰是在或曰主要是在政治宣传而非学术的一边。又如梁氏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这也是主要从政治而非学术对康氏所作的评价。而当时反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人,无论是最早提出毁禁《新学伪经考》奏劾的余联沅(1894年),还是王先谦、叶德辉,(注:见《翼教丛编》卷四、卷六王先谦、叶德辉文。)他们也主要是著眼于《新学伪经考》的政治效果而非学术优劣立论的。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主要价值确实是在政治而非学术的一边。从政治效果来看,康氏借《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找到了宣传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在经学上的根据,维新变法运动亦缘此而起,对此当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公允、全面的评价。钱著在这一方面所论甚少,表现了钱穆对晚清今文经学认识的不足。
如所周知,钱穆对“疑古”思潮报着否定的态度。因为他看到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潮的兴起,实与疑古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健将,亦确实都对晚清今文经学派,都对康有为报有相当的好感。他们的理论根据,也多从晚清今文经学而来,多从康有为而来。因此,钱著主要著眼于学术的价值而非政治的意义,揭示晚清今文经学派治学的武断难据,此亦“拔本塞源”之举。然而钱穆虽然著眼于“学术”论晚清今文经学,而其底蕴实乃亦仍然由“政治”而起,此与晚清今文经学之以学术论政干政,非貌异而神同者耶?
标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文; 钱穆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康有为论文; 戴震论文; 宋儒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