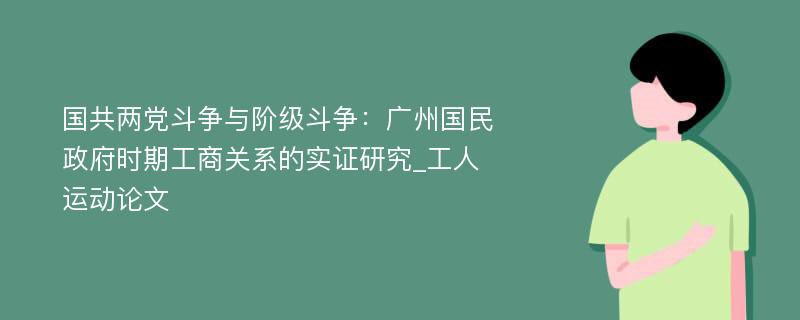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国共论文,实证论文,广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劳方、资方与国民党政权的互动为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劳资问题,近年已为国内学界所注意。然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仅有两篇②,笔者读后颇受启发。而与本文相关的成果多是从工运史“阶级对抗”的理念模式来分析的,显然,这与“党史的框子,工运史的例子”的传统研究取向密切相关。因而,过高地估计国民革命时期劳资阶级的分野程度似乎成为目前我国工运史论著的共同语境,这无疑对全面解读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颇为不利。而深入、系统地考察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工商关系,却为我们客观评估国民革命阵营中的阶级变动提供了典型例证。
一
1924年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劳资政策就已显现“袒工抑商”的特点。对工人运动要“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同时还将“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列入其政纲③。可见,国民党维护工人利益的政治决策是与其需要工人大力支持以实现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而各地商会为了维护眼前经济利益惧怕甚至反对革命的情况,当时却相当普遍。这一情况使国民党对商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信任,认为商会“稍一驾御失法,则在在足为革命之障碍”④。这是当时国民党劳资政策向工人倾斜的主要原因。而1926年1月, 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工人运动决议案》更是明确指出:“工人群众在各界民众中最为重要,若舍此不图,则所谓民众基础必无从巩固,甚至无从取得。……对此受压迫最深、革命性最强之工人群众,一方面宜加以深切的援助,使其本身力量与组织日臻强大;一方面须用种种方法取得其同情,与之发生密切的关系。使本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伟大的革命基础。”⑤ 与此“袒工”相比,国民党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却“洋溢”着“抑商”的意味。“对于旧式商会之为买办阶级操纵者,须用适当方法,逐渐改造”,“使一切商团成为真正小商人之武器,而不可使变为资本家所利用以成压迫革命民众之武器”,“对于商民运动与农工运动之关系,须令两方明白各阶级在国民革命工作中有联合战线之必要,处处须以国民大多数利益为前提,须以为被压迫的民众而革命为目的,以防止两方冲突之发生”⑥。
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实施,却为中国共产党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1925年1月,中共四大已适时地提出其工运策略:“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资本家)决不让步地斗争”,“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⑦。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首次引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指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之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无论工会组织的形式有各种的不同,但工会组织的性质是阶级的,工会工作的内容是阶级的,工会教育同样也是阶级的”,“工会组织必须有坚决的阶级行动”⑧。同时,还成立了以林伟民为首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至7月,广州国民政府的诞生更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先机。“国民政府成立,予人民种种政治自由,并扶助工人组织的发展,广州工人得到此种助力,而发展自然格外迅速。”⑨
然而,随着“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发生,国民党右派势力渐趋抬升,使得广州工界的党派政治分化骤然加速。这主要表现为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的对峙与冲突⑩。针对中共工会的强势竞争,一些国民党右派工会并未急于势力的扩充,而是更注重其内部的重组与巩固(11)。尽管这些右派工会组织自身控制严密,却也无力阻止中共系统工会力量的浸润与渗透。不过,共产党人在渗入铁杆右派工会时并未获得很大成功。但两大阵营间的工会斗争则随着国共党争的发展逐步升级为公开的暴力,“械斗、绑架、甚至谋杀成为1926年夏的惯例”(12)。仅据不完全统计,自1925年7月至1926年6月,广州就发生此类战斗54次,“也就是说每周至少一次,而且很少有不死人的”(13)。广州工界高度的党派政治分野无疑产生了严重后果,它使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陷入了艰难的境遇:一方面,为了共同御敌——国内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需要劳资双方的合作与结盟。另一方面,工人经济权益的获取往往是以牺牲其雇主利益为代价的,这确实被视为劳资斗争。国民政府审慎的努力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抑制商人的利益必然会激起商人团体的怨恨,这些商人团体自1924年商团事变后已遭受了相当的损失(14)。
二
至少在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 因国民政府“袒工抑商”而造成的“工强商弱”格局一直是此时期工商关系的最显著特征,这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表现尤为明显。尽管国民政府的成立赋予工人相应的政治权益,“然尚未得生活上的改善”(15),于是,“罢工已成了广州工人生活的基本特征”(16)。为更好保障罢工,1926年4月,广州工人代表会通过《经济斗争决议案》,决定设立经济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各工会的经济斗争,各工会罢工前“应先行报告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征得同意,以便通令各工会一致援助”(17)。这标志着经济斗争由过去的各自为战向工代会的统一管理转移,此后广州工界罢工的威力大增,集体行动便成为其向商界开展经济斗争的最佳选择。也正是在政府的袒护和工界势力的威慑下,劳资间的经济斗争往往以商界的妥协而告终。据1926年5月的《中外经济周刊》统计,自1925年6月以来的半年中,广州发生工潮百余起,但就既成事实的罢工而言,“工人所要求之条件,莫不完全胜利,于此可见工人今日在广州之地位与势力矣”(18)。这与政府的“袒工抑商”颇有关联。针对时人指摘政府在劳资争执中的“袒工”行为,国民党机关报特发社论辩驳:
许多不明经济原理和社会生活趋势的人们,他只是以浅陋浑噩的眼光批评劳资争执。他说起工人之要求加薪或罢工风潮,便切齿痛恨,以为这是政府故意维护工人,挑拨工人与资本家的恶感。更有些诋政府为实行共产主张劳工专政之征兆。他们不知道这些劳资争执,并不是由于政府之偏袒与行甚么共产而始发生,这个完全关系于物价问题,这个完全是由于物价趋于高涨所发生的一种影响(19)。
不过,将劳资争执完全归于物价问题,不免有失偏颇,而政府的“袒工抑商”恐怕也是事实。此时工界的一些经济斗争还呈现出过激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要求过高及封锁商店上(20)。如1926年初,广州石印工人在提出要求后,不待东家磋商便罢工,还派纠察“携木棍分赴各店威迫”(21)。4月,车衣工人亦为改善待遇而罢工。车衣工会不仅连日派队巡行,勒逼工伴离铺,还分向各商店“逼令盖章承认”,否则“咆哮侮辱,备极难堪”(22)。而此时,西关土洋匹头行店员工会也与东家发生争执。东家因要求过苛而“不敢开市贸易”,该工会遂纠合工人百余名各持刀棒,将行中最大的大光、南方两公司占夺,“强踞店账货物及店员行李”,“全行均极震恐”(23)。针对工人的“据铺骚扰、入屋拿人、触犯警刑各律”,农工厅特发布告:“商人固不应存破坏罢工之阴谋,工人更不应有骚扰秩序之暴举”,“对各工会工人之犯法行为,应依法专责办理。”(24) 但禁效甚微,工界扰商仍迭次发生。如6月,酒楼茶室工人要求东家将年中所有炮金、杂钱等项归其专有,
东家遂以生意冷淡为由拟歇业抵制(25)。后被工人侦悉将店没收,并派纠察“威逼各号承认”。各店多畏其凶悍,“弗敢与较,答允承认者不下三四十家”(26)。旋经农工厅调处,令东家不得罢市,“工人亦不得派纠察出而骚扰”(27)。但工人纠察仍连日“骚扰如故”(28)。其实,中共也力图纠正这些弊端。1926年4月, 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经济斗争报告就明确指出此缺陷,“但由于工人群众不了解,在他们之中引起了许多反感”(29)。
不过,此时工界的强势并未能驱使商界就范。相反,却使自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时就已显现的工商阶级分野日趋激化。针对中共工会阶级斗争攻势,广州商界更是勉力筹谋,使得此时工商关系的阶级对峙特征愈益浓厚,这在双方对工会的争夺上尤为显著。尽管国民党“袒工抑商”的政策不许商界“高度压迫”,但广州工界的党派政治分化却为商界留下了应对空间。这样,“利用工人分裂工人运动”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商界而言,不啻为其进行阶级抗争的理想路径。因而,“凡是工人组织起了工会的,资本家也就利用少数不觉悟的工友组织御用工会与真正的工会对立”(30)。“在广州工业界,这种状况非常普遍。结果工会非常分散,麻烦很多。”(31) 而这“表面上是工会与工会的纠纷,实际上是东家与工人的纠纷,此例太多,简直数不胜数。”(32) 如广州土墨工人成立工会后,1925年7月,东家则组建广东来墨总工会“冀图取巧”立案(33)。此外,广州酒业工会、药材工会、土木建筑总工会、经纶店员工会、革履工会、糖面工会等亦相继分别遭到东家暗设的酿酒工团、熟药工业研究会、建造联合会、绸缎职工会、革履劳资协进会、经纪工会的抵制与破坏(34)。同时,也应看到,此时工商间的工会纠纷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尤其在一些具有浓郁行会背景的手工业中。这可谓是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行会理念交锋的真实缩影,折射出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胶合的复杂面相。诚如国民党苏联顾问达林所言:
在广州,企业主和工人都参加的那种中世纪式的旧行会力量还相当强大。阶级斗争的发展使行会陷于崩溃。它们像肥皂泡一样迅即破裂。工人们纷纷退出行会,建立自己的工会。不过行会已有多年的惯例,有长期以来牵制工人的办法。各行业都有自己崇拜的宗教偶像,因而工人退出行会时,还得同这种偶像决裂。……中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有时就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过广州的工人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了。行会的祖师爷如何看待工会的问题已经难不倒他们。行会还用其他办法使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收入较多的上层工人,同商人接近。一旦罢工使行会垮台而工人参加了阶级工会,旧行会的商人便立即吸收上层工人、失业工人和工贼另行组织自己的工会(35)。
据统计,广州商人共组成26个雇主工会,拥有会员28000名。 这些工会参加了广东总工会,“这个组织由来已久,而且各种行会和同业公会都在其中”(36)。应注意,此时的“工商合作”不仅限于商界与国民党右派工会之间,中共所属工会为进行省港罢工也采取了“工商联合”的策略。不过,短暂的“联合”并未能延缓、阻滞渐趋明朗的工商阶级分野。随着国民革命后期国共党争的激化,及国民党“袒商抑工”政策的蜕变,广州工界内部两大阵营间亦展开了更加剧烈的角逐,而这为商界改变“工强商弱”的政治格局以新的契机。
三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主力相继北上, 留守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执秉粤政。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亦随之黯然蜕化,“袒商抑工”的倾向渐露端倪,而抑制工人运动的发展便成为其北伐期间“巩固后方治安”的首要举措。7月中旬,粤省当局宣布广东进入战时状态,所有产业、贸易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活动,都置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准发生违令之行为”(37)。及后,为“抑工”而颁布的“条例”、“布告”,更是变本加厉。8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决工界纠纷仲裁条例,规定工人“无论何时,各方不得聚众携械斗殴,或有违犯警律,或危害公安之行动”,“无论何方违反此条,所有损失归其直接负责。”(38) 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以蒋介石名义发布告:以武力制止工人结队持械游行,并扣留没收其械具;而后又令广州市公安局对工人法外行动“务须切实防范”(39)。
须承认,为维持战时后方秩序,当局禁止工人械斗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些禁令的颁行并未真正起到稳固社会治安的作用。国民党右派袒纵雇主工会分裂工人运动,致使北伐后广州工会间的争斗比以前更为剧烈,亦更加组织化与军事化。“平行工会之间进行巷战,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会同行会或企业主组织的工会之间进行巷战,在广州几乎是屡见不鲜的现象。”(40) 至1926年下半年,“殴斗更加频繁。殴斗完全按兵法原则,而且是在宽阔的太平街上进行。敌对双方举着旗子走来,激战开始。许多工人死去是因为当局虽然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雇主的工会。”(41)
也正是在当局的庇护下,此后国民党右派工会与雇主更加“亲密接触”,从而联袂上演了一幕幕旨在摧残中共系统工人运动的流血惨剧。如1926年9月, 广州菜栏工人罢工,就遭到雇主工会的袭击,结果工人被打死5名,重伤3名(42)。10月,广东药材工会派员征收会费,亦惨遭惠福路太元堂、仁德堂东家与广东总工会体育部的截击,当场杀死药材工人1名,伤者数人(43)。11月,广东织造土布工会工人因生活困窘举行统一工资底价运动。不料厂东策动东家工会“买嘱强徒地痞”,“各持短枪向土布织造工人轰击”,而被刀棍伤者30余人,其中2人“行将毙命”,“其争斗之剧烈可见”(44)。
除暗设御用工会分裂工人运动外,资本家还以武力直接渗入劳资纠纷,而此时政府的态度则明显偏袒资方。“工商界感情,因纠纷不已,日趋恶劣”(45);“(劳资)畛域之界既分,斯水火之见益烈。意气所中,感情所伤。于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剂酌调和之术,无从而施;寻仇报复之风,相继而发。”(46) 为消除劳资争斗,1926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仲裁会,处理劳资争执。该会以“所谓超阶级性和貌似公允掩饰自己”,“实际站在雇主一方,用围困法对付工人”(47)。事实上,“广州的罢工就是这样进行的。罢工常常处于病态的情况之中,时间拖得很长,而政府的仲裁更是十分软弱。如果工人不同意作出让步,仲裁委员会的会议就延期三天,然后一再拖延,直到工人因毫无收入而不得不退让为止。企业主则在这个时间内策划谋杀工人领袖。”(48)
针对劳资纠纷中商界与国民党右派联合镇压的逆境,中共所属工会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自然会尽其可能设法防御或抵抗”(49),“或是罢工而不离铺,否则封锁商店及工厂不使营业,或作铲除东家工会运动”(50)。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广州每一个工会都有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这类武装工人纠察队保护罢工工人不受企业主策划的袭击,保护他们免遭工贼的破坏。”(51) 工界的顽强抗衡,亦迫使商界与国民党右派在社会舆论上大做文章,致使各种诘责、诽谤工人运动的论调在北伐后“盛极一时”:“工人太猛进了,不能不加以取缔”;“阶级斗争破坏了联合战线”;“工潮是共产党捣的鬼”(52)。
1926年10月,广州总商会、广州市商会、广州商民协会、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等四商会不仅更起劲地散布“工人恐怖”论(53),而且派总代表郑耀文、谭棣池、余厚庵、黄旭升等就加薪、封锁与罢工、征收佣金、作工时间、任免职工、工会征费、征求会员、劳资协助等八项问题,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请愿,痛言工界的“停工要挟、封锁店铺以及私擅逮捕”等事,并要求当局速颁劳资待遇法规,“以免除工商间日后之一切纠纷”(54)。11月3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就商界的劳资纠纷意见逐项予以驳复,并上书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认为商界“故耸听闻,殊失其平”。同时提出五项请命:(1)积极改善工友生活;(2)保障工人职业及救济失业;(3)帮助工人铲除东家工会及工贼;(4)切实保障工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罢工之自由;(5)严禁东家利用土匪民团摧残工人(55)。然而, 这并未引起国民党的高度重视,此后广州工运的政治环境愈加恶化。
11月12日,以李济深为首的粤省政府重新改组成立。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北迁武汉。此后广东政局的态势顿时逆转,国民党“袒商抑工”的劳资导向亦日趋鲜明,对工人运动的限制也更为严厉。1927年1月5日,粤省政府正式颁行《广东省暂行解决工商纠纷条例》,其“袒商抑工”的政治倾向隐然可现:如对工会除规定不得擅自拘人、持械游行、封锁商店与工厂等项外,还对其征收会员、会费及基本金予以严格的限制;而对商人最严厉的规定亦不过是“不得阴谋搀设工会”和“不得指使或贿买别行工人或闲杂流氓参加,以增重纠纷”而已(56)。这对商界而言无疑达到了其遏制“工人恐怖”的预期目的。1月11日,广州商民大会正式通过拥护该条例的提案。而工界也只有工人代表会对此有异议,“请政府修改”,最后也全然接受(57)。工代会态度的“温和”,显然与中共工运政策的调整密切关联。国民政府北迁后,至少为在形式上维系革命统一战线,避免与国民党右派发生公开的决裂,中共此时开始降低工人运动的激进程度。诚如中共广东区委所言:
现在已经到了民众与政府对抗的时期,我们要使工农的势力不孤立,就要拉拢学生与商人,要学生、商人都不反对我们而与我们一致的反对政府。因为这个时期的政府,固然不会能代表资产阶级,不会使商人满意,所以此时还可以拉拢商人。但因此我们的口号就要低一点,乃能适合学生、商人的口味。特别是商人应注意,因为商人在经济上十分重要,如果他站在政府一方面我们就危险;站在工农群众一方面,就是一个相反的情势。所以现在为了我们整个的工作,有时应当妥协一下,对于广东劳资的冲突,现时就要小心的工作。广东的工业不能维持其成本,一来是因为工业不发达,二来是管理不好。政府的工业因为管理不良(职员扒钱太多等),都弄得要倒闭的样子,我们应设法使这扒钱的弊端减少点,而以增高工人的生活。对于私人工业则要很小心的,要使工人的要求能够适合以工业利润所能供给的限度,即不要工厂因工人的要求过度而关门,把工人与商人的关系弄得太恶劣了,结果在整个工人阶级与政府对抗的形势上陷于孤立,或竟使商人结合在政府方面来压迫工人。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要打倒资本家而与政府对抗,所以我们不能敌人树得太多了。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后的敌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需要与他们站在绝对的冲突地位以孤立我们自己的势力(58)。
可见,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对峙已为国共党争的主要矛盾所淹没。就中共所属工界而言,其工运政策的调整并未能缓和来自商界的敌意,相反却使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显复杂而激烈。也正因工界策略上的“温和”及国民党“袒商抑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国民革命后期商界的政治地位相对凸显,“工强商弱”的阶级格局亦随之渐然消逝。
四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当然,此两种类型劳资关系模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当时因革命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波动。不过,其变动的基轴还是工商两界与国民党政权三方利益格局之异趣所致。
国民革命兴起后,“无论是忠于三民主义还是忠于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下”(59)。因而,工人在革命中的政治地位愈显重要。与之相比,自辛亥革命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主体就处于严重脱节状态。至大革命初期,这种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疏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走得更远。商团事变的发生,可谓是商界对国民革命的认同降至冰点:“商民在各阶级民众中似较早有团结,然一察其内容,则大多已腐败不堪,大多数之旧式商会不独不参加革命,且为反革命。”(60) 本阶级主体的缺失,迫使国民党只得寻求其他阶级力量的支持,而作为能有效制衡商界的工人便成为国共两党合力革命的首要选择。这样,因国民党“袒工抑商”政策的实施、中共对工人阶级斗争理念的宣传及缺乏正确引导,就必然促使革命统一战线中工商间的阶级分野愈趋明显,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工人运动“左”倾情绪的滋生,加剧了劳资关系的紧张,而这却与国民党“劳资协调”进行全民革命的一贯宗旨不免相悖。其实,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所以热衷于扶助工人运动,为的是依靠其更好地开展国民革命,并不希望工商交恶的阶级斗争的产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产业幼稚,“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并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61)。故“本党民生主义,非着各工团以罢工为要挟能事,系欲劳资互助,农工合作,从事于谋联络一致。”(62)
国共两党“劳资协调”、“阶级斗争”理念的歧异,使得此时期广州工商关系亦相应呈现出“合作与对抗”的主题特征。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后期国共党争的日趋激烈,广州工会间的派系纷争与工商间的阶级对峙相互激荡,更加势同水火,这就使得革命统一战线存在着分裂的险象。因对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抱有本能的恐惧,加之广州商人因受商民运动的党化控驭,其革命性已有明显提高,而更重要的是,日益紧迫的北伐军事行动,需要稳定的后方和税收来源。因此,国民党政权对其“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予以调整势在必然。而《国民政府组织解决雇主雇工争执仲裁会条例》和《广东省暂行解决工商纠纷条例》等劳资法规的相继出台,可谓是对工人运动中过激行为的直接否定。尽管这些条例对劳资双方的约束尚似平允,“体现了在国民革命中照顾各联合阶级利益的原则”(63),但其所蕴含的“袒商抑工”的政治倾向却不言而喻,而这则与国民党“劳资协调”的基本政策一脉相承。国民党劳资政策在“袒工抑商”与“袒商抑工”之间的游移,恰好表明其“劳资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
最后,应指出,尽管此时期因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宣传,广州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就总体而言,其分野程度毕竟有限。这与广州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关联。从清末至民初,广州的社会经济结构基本上仍以传统行业为主,如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 新式的商业行业也不多(64)。这种以传统行业为主导的工商业格局的持续存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其行会势力的消退,并使之有可能在遇到适宜的“光合作用”而“枯木逢春”。与此相应,广州工界的社会构成亦呈现出以传统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特征。据邓中夏对1926年20万广州工人的社会分析,产业工人仅占8.5%,而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水上工人、店员为主体的传统行业工人却达91.5%(65)。这就不难理解,“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理念依旧在许多行业工会,尤其在以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工人团体中还相当盛行。诚如国民党工人领导者所承认的,“多数(并非全部)国民党工人组织起源于行会,但其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传统行会实践的影响”(66)。这或许道出了其所奉行的“劳资合作”工运路线的真谛。事实上,共产党的阶级动员一直遭到这些“劳资协调”型工会的顽固抵制。而在产业工人中更是这样,诚如1926年夏中共广东区委所承认的:“我们对重要的产业工人没有注意”,“仍不能领导工人群众去瓦解机器工人总会”(67)。可见,“劳资混合”的传统行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中共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而这似可从另一侧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注释:
① 文中“工商关系”指工人与商人间的互动关系。
② 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2页。
④ 参见徐思彦:《20世纪20年代劳资纠纷问题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⑤⑥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127、136—137页。
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284页。
⑧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页。
⑨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⑩ 因党派政治的渗入,此时广州工界主要分为三大派别:(1)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1924年5月成立,为广州实力最大的工会;(2)广东总工会,1921年3月成立,是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旧式手工业行会和新式工团的联合体,其行会色彩甚为浓厚;(3)广东机器工会,1926年1月,由国民党右派工会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改组而来。据1926年9月的一份共产国际报告所称:“现在广州地区有130个工会,工代会所属的有100个,会员数达15万左右。广东总工会所属工会有30个,会员数达3万名,机器工会所属工会有8个,会员数达7000名左右。”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年9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11) 自1926年初起,国民党新、老右派就已不断插手工人运动。 如被国民党势力影响的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改组为广东机器总工会,采用委员制,将其所属俱乐部改编为各支部、分部,把原来的10科扩大为20科。参见李伯元、任公坦:《广东机器工人奋斗史》,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5年版,第112—116页。
(12) 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75,P231.
(13)(16)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323页。
(14) 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232.此外,还须指出,清末民初的广州是近代中国商人团体发轫较早的区域之一。1926年,广州仅已注册的各种商业公会就有140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个复合型、颇有影响力的商会组织,它们构成粤商的主体:(1)广州总商会,1905年成立, 是广东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人团体。其主要代表大商人阶层的利益,是广东政治势力最大的商会。商团事件后,广东革命政府下令重新改组总商会,清除了一批把持总商会的买办分子及大商人,使其在商会中的势力大大削弱。其代表人物为邹殿邦、胡颂棠等;(2)广州市商会是1924年9月广州一部分中小商人因不满总商会的控制而组设的。其代表人物为梁培基、杨公卫等;(3)广州商民协会1924年12月成立, 以“互相协助谋广州工商业之发展,并协助政府以谋商民之利益”为宗旨,由国民党中央商民部领导。最初,以加入国民党的商人为主体。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各地中小商人亦纷纷参加。其代表人物为黄旭升、蒋寿石等;(4)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是1924年成立的全省各城镇商会的联合体。其成员多为高利贷钱庄,买办亦起着重要作用。广州总商会作为其主要成员,许多活动与商联会密不可分。其代表人物为林丽生、李镜峰等。参阅《广州的商人》,[苏]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202页;温小鸿:《省港罢工与广东商人》,《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市商会立案之批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4日;《市商民协会章程》,《广东七十二行商报》1924年12月18日。
(15) 冯菊坡:《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广州工人运动之现状》,《人民周刊》第33期,1926年12月,第4页。
(17)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02页。
(18) 《广州最近工潮调查表》,《中外经济周刊》第162号,附表,1926年5月15日。
(19) 孚木:《物价问题与劳资争执》,《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9日。
(20) 诚如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所言:“工人们的经济要求太高:产业工人和一些主要几种体力工人已实现了八小时工作日。因此各种体力工人都普遍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个要求当然不能接受;另一个要求是不上夜班。由于小商店缺乏钟表,不可能决定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要求灯亮之后就下班,关于增加工资,有时他们甚至要求增加百分之百。在广州举行罢工很普遍,在每次武装冲突中,封锁商店成为必要的措施。”参见《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年)甲6,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第343—344页。
(21) 《局令制止石印工人骚扰行店》,《新国华报》(广州)1926年1月27日。
(22) 《请制止工人纠众骚扰》,《公评报》(广州)1926年4月29日。
(23) 执中:《广州工人以暴力占领商店》,《晨报》1926年4月30日。
(24) 《农工厅严禁工人骚扰之布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7日。
(25) 《酒楼茶室行今日罢市》,《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19日。
(26)(28) 执中:《广州酒楼茶室风潮》,《晨报》1926年7月18日。
(27) 《农工厅调解酒楼茶室停业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1日。
(29)(31)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年)甲6,第344、343页。
(30) 罗浮:《陈森事件之真相》,《向导周报》第169期,1926年8月29日。此外,刘尔崧亦指出,“多数工友仍囿于旧行头之习惯,资本家方面眼见在政治上不能制止工人之结合团体,乃别用阴谋,利用工人破坏工会组织。以致派别纷歧,一行之内,常有几个工会,工友间工会间常因职业上之争执及小小问题之误会,发生了许多纠纷。”参见刘尔崧:《最近广东工人运动之形势》,《广州工人代表会会刊》(1926年),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A1—21,第15页。
(32)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第334—335页。
(33) 《广东各界工人反对奸商工贼摧残工会、迫害工人举行罢工情形》,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9(2)—182。
(34) 详情可见《训令公安局遵照省令将广州酿酒工团解散具报由》,《广州市市政公报》第193号,1925年9月7日,第363页;《广东农工厅公函第65号》,《广东省政府公报》第13期,1925年9月10日,第30页;《广东各界工人反对奸商工贼摧残工会、迫害工人举行罢工情形》,广州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19(2)—182;《工代会请取缔冒牌工会》,《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22日;《办理广州革履劳资协进会及劳工协会案经过情形》(1926年),《职工运动》(下),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A1—20—2,第106—107页;《革履工人赴农工厅请愿》,《公评报》(广州)1926年4月29日;《广州糖面工会已批准立案》,《工人之路特号》第362期,1926年6月29日。
(35)(40)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27—328、329页。
(36)(41)(42) [苏]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91、196、195页。
(37) 参阅禤倩红、卢权:《北伐出师后的广东工人运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8) 《劳工仲裁条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42号,1926年8月,第3—4页。
(39) 《总部严厉制止工人斗殴》,《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10日。
(43) 《东家惨杀工人之第二幕》,《广东工人之路》第7期,第6页,1926年10月15日。
(44) 《河南土布厂东走狗大杀工人》、《公安局封闭东家工会》,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9、16日。
(45) 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3编劳动法令),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版,第252页。
(46) 简琴石:《设立劳资仲裁机关之必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22日。
(47)(53) C.A.达林著、侯均初等译:《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192、194页。
(48)(51)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第323—324页。
(49)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第331页。
(50)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紫金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刘尔崧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5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54) 《四商会议定劳资法规之内容》,《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2日。
(55) 参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驳复四商会对劳资纠纷意见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8—152页。
(56) 《商民代表大会之第二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57) 参见《广州工人代表会总代表会议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232.
(58) 《中共广东区委政治报告(二)——国民政府迁移及省政府改组后广东政局与我们的政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年)甲6,第437—438页。
(59) [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6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2页。
(61)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2、369页。
(62)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63) 饶东辉:《试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南方政权的劳动立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7期。
(64) 邱捷:《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业与店铺》,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3期,2001年4月15日。
(65)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邓中夏文集》,第349页。
(66) Ming Kou Chan,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P258.
(67) 《广州工会运动的报告》,《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1—1926年)甲6,第346页。其实,此时中共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还存在着社会基础薄弱的潜在危机。对此,中共广东区委不无讳言:“由于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国民党省委工人部、农工局工人部的领导人员是我们的同志,任何工会的成立都得通过他们的检查,这些工会不得不加入工人代表会,因此工人代表会不是由于我们工作的结果而成立起来的,而是靠我们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结果,如兵工厂工人工会、灯泡公司工人工会、自来水公司等一些强大的产业工会没有加入工人代表会。如果国民党右派分子掌握政权,工人代表立即会被赶走,我们指导工人代表会的权力也会立即丧失。”参见上书第345页。
标签:工人运动论文; 中国工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广州国民政府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工商论文; 武汉国民政府论文; 经济学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国民党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