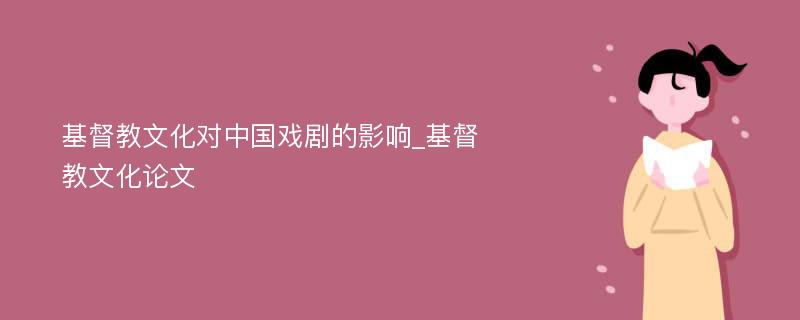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话剧论文,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4;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1999)05—0051—(06)
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成为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历史因素。由于不断受到时代思潮的严峻挑战与颠覆,基督教文化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时代的挑战与颠覆。因而,它也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系统,固守着自己,发展着自己;在西方文化中,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思想家、文学家,注视与解读的所谓西方基督教文化,实际上比它本身更复杂——既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文化,也包涵有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西方反基督教文化的各种因素。而且,这二者时相伴随、时相纠缠。正是这种难以言述的复杂体、混合体,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话剧发生着关联。所以,本文涉及的所谓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注视与解读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历史上反基督教文化思潮,时相伴随、时相纠缠的复杂体、混合“物”。
就外来文化影响而言,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也是一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尽管它不像传统的儒、道和佛教深深潜入作家们的心底,却也诱发了一部分话剧作家,在话剧意识方面的转化,并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多种影响。
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早期话剧
中国早期的话剧艺术,明显地包涵着基督教文化艺术。西方戏剧在我国演出,最早是从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开始的。“上海的学生演剧最早是受了欧洲人办的教会学校在圣诞节的恳亲会上演戏娱乐的影响,开始搞起来的”。“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学生演剧最早的记载大约只有两则”,其一即“是汪仲贤(优游)在《我的俳优生活》里讲到的1898年圣约翰学校演出的《官场丑史》”[1]。宗教剧,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戏剧”;起码,不是本世纪中国话剧所主要借鉴的西方戏剧。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从主观动机来看,依然和传教与娱乐有关。以致,在演剧“内容”得到重视时,演剧艺术相对受到轻视。欧阳予倩在谈到此事时曾批评说:“从那些戏的编排来看他们并不懂得分幕的方法,他们还是依照章回小说那样,把一个戏分成若干回——其实就是场。”这也就是说,新中有旧——引入新的戏剧形式,却“依照章回小说”的方式“分成若干回”——因为忽视艺术而造成的亦新亦旧[2]。由于此时倘属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第二个历史时期, 人们对基督教文化,往往采取有意“忽视”与回避的态度。故而,此番演剧未能超越学校的圈子广泛进入中国社会。但从客观效果来看,演得“新中有旧”的西方宗教剧,因其具有以世俗生活为对象、以讽刺为特色等话剧艺术因素,却使渴求变革的中国文艺家感到新鲜,在“意外”中,对中国早期话剧产生了较大刺激。所以,西方宗教剧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主要也在这两个基本方面:话剧形式的影响——只说不唱的演法;话剧观念的影响——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而非传统戏曲那种象征的、虚拟的表演观念与方法。
真正揭开中国话剧史序幕的,是20世纪初,一群由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春柳社首演的是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三幕,其后上演了根据林(琴南)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这个戏,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认为可以看作中国话剧第一个创作的剧本。因为在这以前我国还没有过自己写的这样整整齐齐几幕的话剧本。”[3]该剧于1907年首先在日本演出获得成功。“辛亥革命后, 春柳社回国演出,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使得传统的戏曲长时间被称为‘旧戏’,也使得传统戏曲的编剧方法与表现形式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戏剧的影响。”〔4〕林译小说本作《汤姆叔叔的小屋》, 是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代表作,问世于1852年。斯托夫人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她自幼受父亲影响,虔诚信仰基督教,关心道德、宗教和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传播福音的愿望。在美国,最早反对奴隶制的,是基督教的魁克派(即教友会)。斯托夫人痛恨南方奴隶制度的残暴,怀着“基督教‘仁爱为怀’的伟大宗旨”,用小说揭示社会的黑暗。《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被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林肯总统也曾把斯托夫人称为“发动南北战争的妇人”〔5〕。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不少有志之士为着挽救国家的命运,为着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或奔走呼喊,或投身运动。林琴南、魏易翻译此书,也意在唤醒国人,反对外族的侵略和奴役。根据欧阳予倩在《回忆春柳》中,提供的当时的节目单上的分幕简介,可以看出,改编后剧本的主要情节大致符合原作。但是,有两个明显的改动,首先,抹去了原作中的基督教立场与颂扬、传播福音的印迹。使既是一个深受压迫的黑奴,又是一个具有虔诚信仰与美德的基督徒的汤姆,简化为一个深受压迫、性格善良的黑奴的汤姆。随着他身上宗教色彩的减退,他所代表的种族色彩更加浓烈。受难的背后,全失基督徒主动“承担”的宗教意味,转为强化性地象征着一个弱小种族整体受难的命运。其次,改变了原本是悲惨的结局。使不肯出卖难友、被毒打致死的汤姆,“和哲而治一同逃走了”;使原作中极度悲惨的结局,变成“中国化”了的“悲喜交集”〔3〕式的结局。对此, 欧阳予倩阐述得很清晰:“照斯托的小说着重在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极力描写汤姆信教的虔诚。在春柳这个戏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涉及宗教思想。还有一点就是原书的结尾是解放黑奴,而这个戏的结尾却是黑人杀死几个奴贩子逃走了,以战斗的胜利闭幕”。“编者的心理,是愿意汤姆也一同逃走,在当时也可能以为这样做使戏比较容易结住,同时也让观众舒一口气,不致过于压抑。”〔3〕与中国早期话剧的先驱者们, 对待教会学校所演出的宗教剧的方法,基本上一样。“放送方”弘扬宗教的愿望,被按照“强国保种”的需要所涂抹、所删除。“放送方”所传递的西方悲剧精神,被视作“巧于叙悲”的技巧,为“宣传”的需要、也为观众的习惯,理所当然地被“淘汰”。在与基督教文化艺术相遇时,“接受方”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意图,以“外在”于基督教文化的方式,“拿来”基督教文化艺术中的“养分”。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西方悲剧观念,并没有对中国早期话剧形成实在的冲击。其实,这也是中国早期话剧,对待、接受基督教文化艺术的启迪与影响的基本方法。它既由当时“强国保种”的政治取向所决定,也与对基督教文化进行抨击、抗拒为主调的文化取向密切相关。
二、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比较广泛、深入。中国现代话剧,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方式,也是各种各样。这种深入的影响与多样的接受,可以在对中国现代剧作的考察中,看出一些端倪。
陈独秀将基督教称为爱的宗教,和促使欧洲文明的主力,并将基督之“爱”的内涵作了扩展。这种说法推动了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注视与解读基督教文化的步伐;也预示着,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文学时期,被解读、被接受中的复杂化趋势。中国现代话剧剧作在发展历程中,就反复出现过这一复杂化趋势。
翻译剧、改编剧,曾是中国现代话剧剧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首先表现在翻译剧、改编剧的翻译、改编、上演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改编者,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过渡到注视上一时期教会学校所看重过的圣经题材剧。但是,他们注视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教,而是“意在教外”,别有所图。
其一,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从王尔德的《莎乐美》被翻译、上演,到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等剧作的问世,都反映着这一动向。王尔德取材《圣经》的《莎乐美》,较早被介绍到中国,并对现代话剧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21年3月, 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发表于《少年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田汉亲任导演将该剧搬上了中国舞台,并引起了较大反响。田汉并不想去追究,唯美主义的王尔德是要光大基督精神,还是要大作自己唯美主义的文章。他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借用经典,去发挥、演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善恶观念的艺术方式。所以,与其说,田汉关注的是《莎乐美》中的圣经故事;不如说,他关注的是王尔德讲述圣经故事的方式,和支撑这种方式的思想。而这种取自“经典”,又背离“经典”的创作取向与精神,正是“五四”新文学所赞赏与渴求的。这种取向和精神,很快便具有了为新生的现代戏剧鸣锣开道的意义。如南国社曾专注于用这种“精神”,解构中国文学中的“圣书”——《水浒传》。并且,选取了一个莎乐美式的女性——潘金莲进行试验,产生出有名的“翻案剧”,即欧阳予倩的《潘金莲》,为以潘金莲为代表的女人正名。欧阳予倩的《杨贵妃》,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以及向培良的《暗嫩》,都蕴涵着王尔德通过《莎乐美》所传递的精神与艺术表现方式。
其二,他们的“所图”乃在于: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这一意图,清楚地表现在茅盾译介的一些客观上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的圣经题材剧及小说中。1934年3月,著名的左翼作家茅盾, 翻译了比利时著名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耶稣与淫妇》,并刊载于《文学》杂志第2卷第3期。莫里斯·梅特林克出生于比利时,从小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耶稣与淫妇》,是他的三幕剧《抹苔莉的玛丽》中的第一幕。梅特林克的《耶稣与淫妇》一剧,直接取材于《圣经》,宣扬着基督的伟大,弘扬着基督教“爱”的精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中,有如下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住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可见,通过如何对付“文士和法利赛人”,如何对待“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既显示出耶稣的智慧与耶稣之爱的伟大,也显示出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卑鄙、无耻。茅盾翻译的梅特林克的《耶稣与淫妇》,分为四场。剧中写抹苔莉的玛丽,因诋毁耶稣和为金钱出卖肉体,犯下了双重大罪。耶稣并未嫌弃抹苔莉的玛丽,用著名的“八福”感化了她的心灵,使她有了悔改和皈依之意。在她受众人围攻时,耶稣发出了拷问灵魂的声音:“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耶稣的威严声音,使围攻者畏惧于自己的罪,终于羞愧地放下了石头。抹苔莉的玛丽也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比较《圣经》与剧作,梅特林克仅作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改动。如剧中的“她”,由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当场“拿住”押来,改为“她”在耶稣传播“八福”的那充满柔和又威严的声音中,受感悟而自愿走来。这样的改动,主要是为了方便剧情的连贯和发展。不仅未损伤《圣经》称颂耶稣的原意;相反,在传达《圣经》中耶稣的智慧与行迹的同时,以艺术的方式,渲染、强化了耶稣的宽宏、仁慈、威严,强化、突出了“八福”对世人的巨大感化作用。
翻译、发表《耶稣与淫妇》这部圣经题材戏,尽管它“客观上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非但不能说明茅盾信服基督教,甚至亦不表明他比前一时期更欣赏基督教文化。茅盾的主观意图,乃是为了以西方之神击东方之鬼,以西方基督教文学来曲折地表现,自己需要表达又无法直接表达的心声。
不论取材于经典、背离经典,还是借西方之神、斥东方之鬼,其目的都不是为了传教,而显现出一种宗教之外的复杂:或者从中学习“精神”,或者将其作为隐喻。但是,从客观方面来看,各种译作的出现,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有助阐明或宣扬基督教精神的文学作品。
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话剧的关联,也表现在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汲取中。由于主观意图的变化,现代话剧文学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既输入西方的文艺,又钻研基督教的《圣经》。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开创者,也曾是一个《圣经》的钻研者,一个对基督教文化持“容忍”态度者。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出现过几次“非教运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宗教——不论是何种宗教,都在检视与批判之列。1920年至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对宗教批判较为激烈。1920年8月,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评议部曾拟通过《拒绝有宗教信仰者入会》一案。当时身在日本的会员田汉,去信反对通过此案,并引发了一场争论。最后,此提案被取消。改“拒绝有宗教信仰者入会”,为“不妨用极慎重的方法,暂且容忍入会”。田汉似乎不止于满足这种争来的容忍,在给友人的通信中,进一步表明过自己对基督教、基督教文学从容忍到钻研,甚至到“有好些喜欢”的态度:“弟近又研究Biblical Literature,有好些喜欢的地方, 并且有点爱Christ那种伟大崇高的人格呢。”〔6〕有趣的是, 这时候的田汉,正在忙于译介悖离《圣经》之道的唯美主义的戏。他曾这样记叙:“(1929年7月28)《莎乐美》一剧,因是反基督教, 金陵大学校长陈先生再三再四拒绝我们借该校的大礼堂,……我们感觉得艺术与宗教的冲突了。”〔7〕田汉向中国的读者、 观众展示出了他的复杂性:对圣经有“好些喜欢的地方”,且“有点爱耶稣那种伟大崇高的人格”,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译介、上演反基督教的戏剧的积极性。与之类似的还有向培良等剧作家。向培良熟识《圣经》,但他的《暗嫩》,有意打破了《圣经》完整的叙述结构,使以劝戒为目的的“例证”孤立起来、独立起来,产生因断章取义而出现的歧义、反义。与早期话剧家相比,这时候的话剧家,以更主动的方式对待基督教文化。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解与发挥,使基督教文化变得非常复杂,其中充满了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反基督教文化因素。
中国现代话剧界的这种局面,由于曹禺的出现,发生了一些变化。曹禺以一部《雷雨》震惊了文坛,为中国戏剧史写下了新的一页。曹禺坚持着“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两大基础理论基本主题: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他在学习西方、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对基督教文化也很留意。他说过:“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8〕在基督教文化中,找社会的出路、 找个人的出路,这种明确的说法,在中国现代剧作家中,还不多见。虽然,这不说明,曹禺在其中找到了什么出路;但是应该可以说明,他不想用基督教文化来装饰某种思想,或者演示某种艺术,而是想看清楚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真实面貌。在创作中,他也受到他所认识的基督教文化影响。田本相在《曹禺评传》中写到:“1934年暑假”他回天津,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外文系”。“是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要讲《圣经》学,因此更多地接触《圣经》。《圣经》中的故事自然引人入胜,而它漂亮的文笔,特别是其中的箴言,更给他以深刻印象,也引起他的兴趣。他不但选择其中片段教学生,而且在后来写《日出》时,在前面引用了若干段,并精密地加以编排,借以抒发他难以直接表达的思想。他说,他从小说接触过《圣经》,但对《圣经》却‘懂得不多’。基督教的经典的确给他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9〕曹禺未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文化对他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度。 但是,在这个有限的限度之内,曹禺的“兴趣”,不仅在基督教艺术,也在基督教思想。1936年7月, 曹禺在《日出》跋说:“……我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我读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我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些孤独的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驮负着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路。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这一类的动物。他们偏若充耳无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避开阳光,鸵鸟似地把头插在愚蠢里。……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诚如《旧约》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我观看地,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烦躁不发’,我眼看着要地崩山惊,‘肥田变为荒地,城邑要被拆毁’,在这种心情下,‘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我要写一点东西,宣泄这一腔愤懑,我要喊‘你们的末日到了’!对这帮荒淫无耶,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10〕可以看出,这时候的曹禺仍然在寻找社会的出路:旧的必须推倒,新的是什么又不明确。被陈独秀视为穷人的宗教、而又为他所熟悉的宗教——基督教思想,对他自然发生了一些影响。也许可以说,在观照社会、拟定主题时,他不仅仅是借用了《圣经》中的某些语言,还借用了《圣经》中的某些思想。而且,他的这种借用,不同于田汉、向培良的借用,即不同于前时期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借用。
此外,基督教文化中,一些重要的观念、意识,也不时潜在于曹禺的作品中。如在《雷雨》与《原野》中,周朴园之罪与仇虎之罪,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上帝”面前,他们都是“罪人”。周朴园有“意识地”进行着忏悔,仇虎被潜意识驱使着忏悔。
在《原野》中,意欲复仇的仇虎,冲突的对象显然是整个黑暗的社会。他坚定不移地活下来,就是为了血债血偿、命命相抵。就此而言,他的目的达到了,起码是部分地达到了。复仇后的仇虎,冲突主要发生在自己的内心——因而,被称之为心中之狱。朱栋霖在《论〈原野〉一文中说:“要正确解释仇虎的‘心理谴责’,必须弄清‘这《地狱》里的魔鬼’是什么?导致仇虎失败的悲剧根源何在?”答案是“仇虎‘心狱’中的魔鬼是‘愚昧与迷信’……而造成愚昧、迷信,控制这一切的则是封建统治势力,这就是仇虎悲剧性内心冲突的本质。”〔11〕“心狱”中的魔鬼,是“愚昧与迷信”的说法,不能说不对。但是有点失之笼统。幻像、鬼怪因为仇虎陷入“心理谴责”,而出现在舞台上。这说明仇虎头脑中,确有愚昧与迷信思想因素。其实,血债血偿、父债子还、命命相抵的复仇行动,早已显示了仇虎的愚昧与迷信。因而,“愚昧与迷信”早已潜在于他的心底深处,关键问题是要追究:仇虎到底为什么在这时候会产生幻像、害怕鬼怪、迷失方向?实际上,也就是要直接叩问:仇虎为什么在坚定不移地完成了复仇任务之后,又“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心理谴责”的路途?所谓的“心理谴责”到底是谴责什么?
马佳认为“这一切又都仿佛在寓示着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一双盯牢仇虎灵魂的眼睛。所以实际上仇虎一直笼罩在无法摆脱的矛盾纠缠中,一面是他的意志、他的精神、他的理智,另一面则是神的追问、神的意志和神的审判,‘两个鬼’在他心中用力地打架争执”。“在仇虎的心目中他其实是一直把焦氏作为焦阎王的象征和替身来对待的,他对大星残酷的异化行径正是想让焦氏得着极深的苦痛和欲罢不能的煎熬,是想最大程度地刺激焦氏,使自己有面对阎王复仇后一样淋漓尽致的快感,但小黑子的惨死,一个更脆弱的更赢小的纯洁的生命却不幸地等于死在他刻毒的设计中,于是,即使得到快感也一时间彻底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忏悔、辩白、申述、祈求,当所有这一切举动都无法平息自己‘心’的罪恶时,他只好选择死亡!”〔12〕可见,马佳认为是“两个鬼”在他心中用力地打架争执:一面是他的意志、他的精神、他的理智,另一面则是神的追问、神的意志和神的审判。如果,仇虎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农人,马佳所认为的“两个鬼”,十分可能。但是仇虎只是一个生活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农人,马佳所说的前一个“鬼”,存在于仇虎心中,十分可能;后一个“鬼”,则较为牵强。如果说,后一个“鬼”是“神的追问、神的意志和神的审判”,倒不如说是仇虎在实现了复仇计划,手刃了好友——焦阎王的替死者焦大星,与客观上造成了小黑子的惨死之后,心灵的自责——对为了复仇而造成的滥杀无辜的行为的内心自我谴责。有了这种强烈地、如同复仇行动中坚定不移的自我谴责,仇虎心灵又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次升华。曹禺写道:“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逐渐消失,正如花氏之在半夜的折磨里由对仇虎肉体的爱恋而升华为灵性的作家心中。”〔13〕所以,与其说是仇虎心中有了一个“西方的神”,不如说是作家心中有了一个“西方的鬼”。是作家按照“西方的神”的理念,在仇虎心中安排了具有灵魂升华性质的忏悔——强烈的自我谴责。作家的如此安排,不仅使仇虎的心灵陷入极端的矛盾与分裂,而且也使仇虎的性格在失败显得伟大。雅斯贝斯说:“人不是神,这使人渺小和走向毁灭。人的伟大在于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端程度,自己知道会因此走向毁灭”。“悲剧主人公,即抬高了的人,无论他本人是善是恶,是满怀善心还是渺小丑恶,作为生存两次都由于坚定不移而失败,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无条件性。他的反抗、他的固执、他的狂妄促使他成为‘伟大’的恶。他的坚忍、他的受又提升他到善。他总是通过体验极限境遇而被抬高。”〔14〕曹禺通过悲剧主人公——仇虎,与社会及自身的两次冲突,以及在冲突中“都由于坚定不移而失败”,使仇虎的性格在失败中显得伟大起来——一种充满现代悲剧色彩的伟大。
曹禺展现的仇虎这种坚定不移地复仇与被潜意识驱使着忏悔,使得《原野》在悲剧艺术与悲剧主题上,都显得更加复杂。尽管许多批评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或者进行了否定。但无疑,《原野》展现出的新的悲剧内容,与批评者对新悲剧内容的批评,都为中国现代戏剧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有陈独秀的鸣锣开道,“西”有王尔德的成功范例;前有春柳社的早期话剧家,继有“唯美派”的田汉、欧阳予倩,后有“里程碑”似的作家曹禺;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汇合”的局面,既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收稿日期:1999—03—20
标签:基督教文化论文; 基督教论文; 圣经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艺术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莎乐美论文; 耶稣论文; 日出论文; 戏剧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