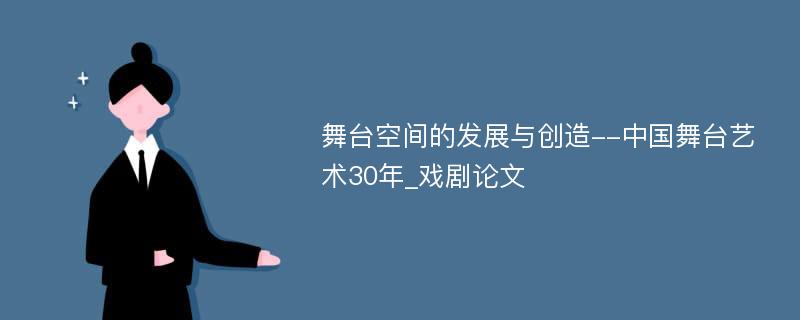
舞台空间的开拓与创造——中国舞台美术3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台论文,中国论文,美术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现代舞台美术,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踏过的是风风雨雨的历程,谱写的是值得自豪、令人感怀的篇章。经过几代艺术家艰辛的努力、无畏的探索和脚踏实地的实践,现代舞台美术已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成为戏剧文化中一面独特的旗帜。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戏剧舞台经过10年的劫难之后,重新踏上复苏的征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舞台美术的创作也获得了新生。作为戏剧艺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创作部门,它在创作上显得格外瞩目,显得更有活力。舞台美术是直观的外在形式创造,容易放开手脚,容易接受外部新的事物和新的观念,也容易显现出自己的创造成果来。
正是由于戏剧观念的解放,艺术视野的开阔,主观意识的强化,舞台美术的园地上呈现了百花争妍的态势。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上一代舞台美术家的艺术理想没有能够实现的话,那么,80年代之后的当代舞台美术家,已经逐步地在实现他们前辈艺术家的梦想,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打开了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一)
舞台美术的整体创作,走向了多元化的态势,打破了长期以来狭窄、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手法,也对现实主义作了重新的审视、调整和界定。开放初期,舞台美术界进行了“推墙破框”讨论,就是推倒只承认现实主义的“墙”,破除只有镜框式舞台才算正宗的“框”。也就是说,推倒旧的创作观念,破除旧的创作框框。舞台美术的创造主要是让外在的、直观的形式“说话”。形式的多样化才能接纳更多的戏剧内容,倾诉更多的舞台意蕴。所以,在新时期的舞台上,戏剧观念是多元并存的,舞台风貌是千姿百态的,有写实的和写意的,有再现的和表现的,有具象的和抽象的,有模仿的和象征的,有逼真的和变形的,有幻觉的和非幻觉的,有心理空间的和物化空间的等等,既有强化一个方面的样式,也有两者兼容的形象。它不死守一种创作手段,更多的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戒律。而今,创造的走向更具有挑战性,更认同戏剧的舞台属性,能动地去组织、调动有意味的戏剧动作空间。这是新时期戏剧创作宽容、包容、大气、成熟的表现。
由于有了这样内在和外在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舞台美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话剧舞台创作走在前列,创造了多元化的舞台画廊,如有《陈毅出山》、《天下第一楼》、《地质师》、《死水微澜》、《“厄尔尼诺”报告》、《父亲》、《十三行商人》、《秋天的二人传》、《立秋》等一批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力作,又有强化写意、变形乃至怪诞的创造,如《再见吧,巴黎》、《WM(我们)》、《天边有一簇圣火》、《中国梦》、《赵氏孤儿》等。然而,更多的戏剧舞台的创造焦点,是投向两者之间的最佳位置,也就是说兼容虚与实、表现与再现、幻觉与非幻觉等。这样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红鼻子》、《阿Q正传》、《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商鞅》、《荒原与人》、《秀才与刽子手》等,在舞美创造上都有其代表性,很难将它们简单地归属于一种模式之内。特别是近五年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舞台剧,就舞台美术而言,它的多元化态势较为明显,成为了一个亮点。
可以说,是舞台形式的多元、多样化,使戏剧面貌绚丽多彩。有此成绩,舞台美术家功不可没。
(二)
由于观念的突破,舞台美术创作更具有了综合性理念,更注重体现全局和整体的意识。舞台美术家也更为主动地参与了整体的创作。
当代的戏剧舞台,传统呆板的“整一性”被打破,舞台的节奏加快,时空的跨度加大,包括人物心理时空的变幻、调节等,都已超越了常规。同时,物质材料、器具的丰富性和舞台科学技术的进步,观众审美价值等的变迁和更新,无疑要求舞台美术家重新调整自己的方位、视角和心态。在创作形式的“结构”中,也必须具备“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节”,才能组织成自己的艺术体系,赢得自己的艺术生存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强化参与和介入意识,即舞台美术家的“导演意识”,才能够驾驭和把握整体舞台形象。
在新时期舞台上,凡成功或较为成功的演出,可以说都是“参与”有效或较为有效的创作。这已经成为共识。以话剧舞台为例,《桑树坪纪事》、《钟山风雨》、《关汉卿》、《生死场》、《万家灯火》、《白鹿原》、《立秋》等就是代表性的作品。它们无论是偏向“实”或倾向“虚”,都张扬着设计者的“导演意识”,与导演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导演艺术家焦菊隐始终认为,舞台美术家扮演了“半个导演”的角色。舞台美术家薛殿杰也认为:“不纳入导演构思的舞美创作,越是创新,越失败得不可收拾。舞美创新的成功,首先在于它准确而有分寸地找到自身在综合艺术中的位置。”他自己的创作,都遵循着这条原则,如《和氏璧》、《生死场》乃至小剧场戏剧《死无葬身之地》,都打下了整体介入的鲜明印记,展示了主动的、积极的、参与的创造精神。
(三)
对戏剧假定性和非幻觉因素的认识和实践,也使舞美创作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舞台创造中的假定性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能回避的艺术门槛。除了传统戏曲舞台固有的假定性创造之外,话剧等其他舞台上假定性的确立,使舞台的表现性得到了强化。在我国的传统戏曲舞台上,与程式化的表演相匹配的舞台空间格局,以“一桌二椅”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假定性理念,早已约定俗成:舞台就是表演的场所。它从艺术形式到表现手法,早已是程式化、虚拟化、节奏化的了。它完全打破了任何摹拟生活的幻觉,升华到假定的表演场所,承认舞台是假定的表演场所。
话剧,包括现代戏曲、歌剧、舞剧等舞台上的假定性,恰恰是艺术形式的特性和表现,只有正视艺术的假定性才能发挥艺术的特点。因而,舞台上大量中性景观的运用,不作更多的舞台包装,使用的材料、器具裸露无遗。也就是说,明明白白地告诉台下的观众舞台原貌,不捉迷藏,不故弄玄虚。演戏就是演戏,给予观众更多的“间离”因素和思考。梅耶荷德认为:“假定性戏剧喜欢新旧因素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新旧因素的结合”已获得认同,有了鲜明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戏剧家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的舞台,让人看到了假定性的魅力。它突破四堵墙的幻觉,设计一堂中立的布景。灯光也不复杂,但大小道具和门窗做得精致,服装、服饰要求真实。总之,凡是与演员直接接触的东西就特别严谨、细致,不得马虎。它又将舞台演出置身在一个较为轻松、超脱、自如的氛围里,如在半截幕中进行场景的迁换,不让舞台神秘化,歌舞的串场、连续,使演出节奏更趋和谐、流畅和更具娱乐性。装置性和装饰性的布景,不使人们陷入幻觉性的思考。通过这一系列的假定性的音符,达到了布莱希特“要使观众尽可能地有惊奇、批判和审查的立场”的要求,也符合他“间离”的目的和陌生化的效果。我认为这是我国话剧应用假定性的开山之作。
进入本世纪以来,强化假定的舞台更为普及,更适合当代观众的口味。血流成河的满台红砖砌成的《赵氏孤儿》,一堵土墙最后才打开或者说推倒的《生死场》,倾斜的、白色的北京四合院的《北京人》等等,它们的舞台,完全摆脱了对生活环境的摹仿和复写,造成了假定性极强的空灵感,既突出了演员的表演,又净化了整体的舞台。加上表演者虚拟化、舞蹈化、形体动作化的表演,更蕴含和隐喻了种种舞台环境,诉诸于观众以丰富的感受力和自由的想象度。
由于舞台假定性地位的确立,新时期舞台出现了不同戏剧观念和体系相糅合的演出舞台。曾被认为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再现演剧体系受到了挑战,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和我国传统戏曲的演剧观相继登上了话剧的舞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与舞台美术家一起参与创造的一道风景。
(四)
新时期以来,舞台美术民族化的倾向愈来愈鲜明,有了一派新的面貌,也与写实的现实主义一样,随着时代的步伐,有了新的发展。我国传统戏曲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但在新编历史剧或故事剧的舞台上,我们的传统美学诠释得更为精到、极致,如越剧《陆游与唐琬》、川剧《金子》、京剧《华子良》、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都凝聚着传统的情结,又焕发着当代民族文化的色彩。
近几年在歌剧、舞剧舞台上,也在外在形式上追求、运用民族的艺术语言,如《大漠敦煌》、《妈勒访天边》、《野斑马》等的创造。如果忽视我们民族的创造元素,必将会失去自己的根基,失去自己的观众。尤其大量“音舞诗”的舞台,少数民族的舞台,如《云南映象》、《家在长江边》等,舞台设计,包括服装、化妆的人物创造,其舞台美术更倾斜于民族文化的张扬上。
至于“舶来品”话剧的民族化,可能是个比较长期的创造课题。上世纪60年代以《蔡文姬》为代表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辉煌;80年代以来的不少演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作了民族化的尝试。就其形式来说,舞台美术家的审美视角是我们民族所能接受的,喜闻乐见的。不少写意性的舞台设计,如《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黄土谣》等,从不同的切入点,注入传统艺术的血液,浸透了民族文化的意蕴。
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我们的舞台上已成无孔不入的态势。双脚踏在养育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与自己息息相通的观众,继承、发扬、创造、表现自己民族的戏剧文化,当是舞美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应成为一种创作的主流。其实虚实、黑白相济,情景交融,或以一当十,边景一角,去繁就简,留有空白和余地的审美原则,更符合中国观众的观赏习惯和情趣。
(五)
新时期戏剧的改革开放,使小剧场戏剧异军突起,也给舞台美术家既提供了机遇,又引起了舞台美术家的关注和兴趣。小剧场戏剧的演出要求并不苛刻,况且我国长期没有专门的小剧场舞台。80年代初北京人艺的小剧场剧目《绝对信号》,是我国小剧场戏剧的开先河之作。就其舞台美术来说,就是将演出的时空,放置在首都剧场三楼的休息厅里。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营造起让人信服的戏剧空间。之后,便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小剧场演出,其设计者都是利用各种不规范的场所进行创造,同样展示了戏剧空间的诱人魅力。
从《绝对信号》撩开的小剧场戏剧帷幕开始,小剧场的舞美已走过了一段探索的道路,经历了一段起伏跌宕的舞台实践和观众的检验,现在已经走向了初步成熟。代表性作品《火神与秋女》、《留守女士》、《同船过渡》、《思凡》、《陪读夫人》、《死无葬身之地》、《足球俱乐部》、《原野》等,都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五花八门的戏剧空间。这些小剧场戏剧的舞美创作,把握了灵活、敏锐、富有弹性的实验性,寻求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最佳生命状态,检验并展示了自己在开放性的舞台上的适应和生存能力。正因为实验性,从而使不同风格、题材、流派的剧目搬上了舞台。
小剧场戏剧舞台方兴未艾,也将从实验和前卫中走向文化市场空间,其舞台美术创作仍大有作为。新时期戏剧既然孕育了小剧场戏剧,也必将迎来自己的发展,包括舞台美术的创造。
(六)
现代舞台的直观形象,已愈来愈令人耳目一新,美不胜收。这里包括大型电视晚会、文体晚会的演出,更包括今年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超大型的演出,人们愈来愈感受到舞美创造的惊人魅力!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舞台科技的进步和参与,它大大地增强了舞台等演示场所的艺术表现能力。舞台美术的创造,是非常物质化的创造,也含有很强科技性的艺术创造,可以也应该利用声、光、色、形等物理因素,使舞台的景观生动、鲜活和流动起来。
当前,舞台利用的科技成果是多方面的,如各种机械舞台、新型的电光源及其电子控制设备、先进的音响器具、物质材料、化妆用品,乃至紫外线、激光等。而且,运用的门类越来越广泛,技术手段越来越精良。不少新建的剧场,配置和使用转台、升降台、移动台等机械舞台,极大地改观了舞台的节奏和空间的表现力。试想,当年如果《桑树坪纪事》、《南街北巷》不使用转台,就不会那么流畅、精彩了,更谈不到舞台的意蕴了。
因此,现代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在舞台上的广泛应用,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潜在的、灵活多变的创造力量,越来越强化了戏剧审美的价值。捷克的舞台美术家斯沃博达曾预言:“利用灯光和投影代替颜料画的布景就是未来。”这在当代科技面前,已成现实。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场景,便是舞台上舞美创造的放大、延伸和集成。
总之,当代舞台美术已跨入“三十而立”的黄金岁月,既留下了值得自豪的足迹,也留下了不能回避的课题:一是舞台美术创造的实践大于理论,实践与理论相互之间还不能协调和适应,因此还存在着盲目“大制作”以及滥用豪华的、贵族化的包装、滥用科技手段等现象;二是舞美工作者应更加发挥主动、积极的参与整体艺术创造的精神,勇于参与恰恰是舞台美术家成熟的表现;三是稳定舞台美术的主流队伍尤其重要,抵制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干扰和介入。舞台美术家的个人艺术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上述的课题,无疑需要“综合治理”。然而,有一点可以相信,舞台不会回到过去一统的、固守的局面上去了,不会重新缩回到原来的狭隘的躯壳中去了。多元并存,综合发展,是舞台美术创作发展的总趋向。排斥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是一种自我禁闭。任何一种创作手段只要与“这一个”的戏剧舞台相匹配,那么,任何一位舞台美术家,就有可能创造出自己的精品。
“三十而立”。只要有戏剧存在和发展,舞台美术也将存在和发展,舞台美术的绿叶也将永葆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