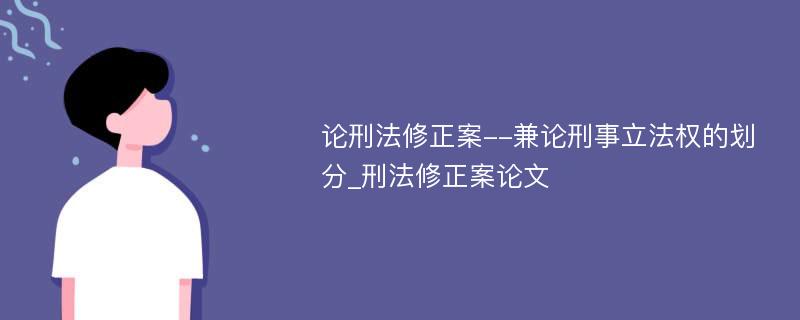
论刑法修正案——兼谈刑事立法权之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法权论文,修正案论文,刑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注:本文的刑法修正 案具有两个含义,没有书名号的,则作为法律形式使用,有书名号的,则作为法律文本 使用。并且,除明确其含义之外,本文所有的法律文本一律使用简称,即标题省略中华 人民共和国,如《婚姻法》。),在新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采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和补 充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虽然有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先例,在刑事法律上却是全新的,因此 ,必将对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立法者、理论界以及司法部门并没 有意识到此种形式带来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使未来的刑事立法更趋 于理性化、合法化。
一、刑法修正案之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之替代关系
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以及附属刑法,虽然都是修改和补充刑法典,但是具有明显不 同的特点:内容上,单行刑法基本上是对普通刑法有规定的事项,重复做规定,是刑法 典中同罪名的细化或者补充,其罪状通常既符合单行刑法,又符合普通刑法,形成法条 竞合的现象。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刑事政策的要求,因此,功能上,恰恰是附属性的,立 法政策上,单行刑法可以不要,因为法秩序的建立,普通刑法已经足够。而附属刑法是 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其罚则规定通常是属于增加补充刑法典罪名的内容,其依附的 法律,则自成体系,与普通刑法无关,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保护某种特殊的文化价值、经 济价值或者社会价值,功能上,和其附属刑法的名称相反,是独立性的,立法政策上, 附属刑法必须保留(注: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属于散在型立法,有三种形式:一是概括 式,即规定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典型的表达是:“违反本法规定,依照法律追究刑 事责任”,或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缺点是刑法典的规定如果不 明确或者没有,则难以执行。二是明示式,即明确规定如何处罚,典型的表达是:“对 于……行为,依照刑法第×××条处罚或者按照××罪名处罚”,这是较好的立法模式 ,缺陷是如果刑法典没有这样的犯罪条款,则无能为力,并且如果刑法典或者单行刑法 加以修改,其条款顺序发生变化,则使得二者出现错位。需要修改法律,造成立法上的 烦琐和司法上的混乱。三是比照式,即仅仅规定罪名和罪状,而其法定刑比照刑法典或 者单行刑法。由于其内容的独立性,在立法技术上,无法完全将附属刑法的罪状全部纳 入刑法典。)。形式上,单行刑法一般是对具有相关性的内容作系统的规定,立法技术 与刑法典无异,因此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法规体系。附属刑法在立法技术上,既可以形 成依附于刑法典的罚则规定,也可以单独具有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在前者的意义上, 具有附属性(我国刑法属于此种情况),在后者的意义上,完全是独立的。1999年修改刑 法采用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和原因是:国务院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了《关 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惩治期货犯罪的决定(草案)》,其他部 门和一些人大代表也提出立法建议,立法机关认为:1)立法建议的内容与刑法典的内容 许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并且各个建议的内容关系不大;2)一部统一的刑法典不仅便于 司法机关适用,同时便于广大群众学习和掌握,不宜再单独制定两、三个决定或者补充 决定;3)不论修改或者补充多少内容,均可一次或者多次修正原有规定,增加条文的, 可以在内容相近的刑法条文之后,作为某条之一、二。如果修改条文,就直接修改,其 优越性在于不改变刑法的总条文数,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完整和稳定。(注:黄太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理解与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1辑。)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在内容上是替代关系,因此,刑法修正案通过和实施 的时间实际上也是其灭亡的时间,换言之,刑法修正案一旦通过,立即完成它的使命, 而被纳入于刑法典中,原刑法典的内容立即被新的内容所替代。举例而言,1997年《刑 法典》第180条是证券内幕交易罪的规定: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 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 ,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而《刑法修正案》第四条:
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 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 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 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如同计算机执行替换命令一样,1999年《刑法修正案》代替了1997年《刑法》第180条 的内容,而成为1997年《刑法》第180条的新内容,即证券、期货内幕交易罪。其他条 文也是如此。因此,可以对没有任何相关性的内容修正,无须采用刑法典的立法技术, 换言之,可以作纯粹的内容规定,无需使用条款的表达方法。(注:关于刑法修正案的 立法背景参见后文,另外,我国目前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并没有任何不同,都使用 条款的表达方法,在单行刑法中,也出现直接对刑法典条文的修改,诸如“将刑法第× ××条修改为×××”的表述即是如此。)总之,由于内容上的替代关系,形式上,刑 法修正案与刑法典是同一的。
(二)刑法典之重新公布
纯粹从形式的角度出发,对于法典的任何一次修正,意味着由有权机关重新颁布一次 法律,实践中也是如此操作的。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律师法》作如下修改:
1.第六条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 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 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 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2.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进行大规模修改的法律更是如此,这清楚的反映在《婚姻法》、《著作权法》、《工 会法》、《商标法》等法律文本的修改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改决议和决定成为修正 法律的前置工作,而其最终的成果是重新公布的法律文本。
例外的是宪法和刑法,宪法的修改一直采取修正案的方式,1988年《宪法修正案》并 没有规定宪法需要重新公布,但在1993年的修宪说明中指出:宪法修改,继续采用修正 案的形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照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99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再次重申此点。(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1993年第2号和1999年第2号,第74页和第100页。)如果这样,就意味着需要重 新公布宪法文本,由于公布法律的权威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没有按照修宪说明 的要求重新公布宪法,如此要求出版社,实在有些勉为其难。(注:修宪说明是否具有 法律效力也是值得思考的。)因此,1993年修改宪法之后,大多数正式出版的宪法文本 都只是收入了修正案,并没有将修改的内容替代进去,而是采取公布法典和修正案的方 式,将修正案附着于法典之后。(注:出版法律文本较为权威的机构,如法律出版社、 中国法制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等等,都是如此,笔者目前看到的例外是八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秘书处编,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代世界出 版社出版的《常用法律法规选编》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如此,其标 题题注(1982年通过,根据1988年和1993年《宪法修正案》修订——略写,笔者注),即 是以替代的方式汇编法律,这并不是突发奇想,而具有一定的根据,奇怪的是,后者对 于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并没有替代进去。)因此,修正案和法典的关系,是 值得研究的,一是仅仅公布修正案,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法律修改的内容如果不 公布,等于没有修改;二是将修正案附着于原法典之后,二者并存;三是将修正内容替 代原内容,而重新公布法典。我国立法的实践是第一种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仅仅 公布修正案,而有关出版社出版法律文本,采取第二种方法。笔者认为,采取附着式和 直接替代的方式各有优劣,前者原法和修正案形成一个既依附又相对独立的形式载体, 有利于了解修改的内容,但对于原法容易产生误解和形成错误的第一印象;后者有利于 学习、掌握新内容,但无法通过法律文本本身了解修改的内容。有的学者建议采用二者 之结合,即公布原法典,但在修改之处加以注释,标明修改内容和时间。这种做法的缺 点是如果修改规模大和次数多,则非常烦琐,笔者认为,采用什么方法,并不是绝对的 ,应该符合该国的法律规定和习惯,根据《立法法》第53条第2款的规定:法律部分条 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注:当然《立法法》是根据宪法制定 的,此条规定对于宪法没有约束力。)因此,直接替代的公布方法是合法的。
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刑法典必须重新公布。(注:《刑法修正案》通过之时,《立法法 》还没有通过,可以说不存在违法问题,但是《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 三)则是在《立法法》通过以后,那么,应该考虑到立法法的规定,重新公布刑法典, 并且,宪法可以作为《立法法》的上位法,而无需受其约束,但刑法不能例外。)并且 ,刑法修正案所使用的立法表述,在现行法的框架之下,是不科学的。如《刑法修正案 (三)》第四条规定:
《刑法》第一百二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 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刑法修正案(三)》第八条也是如此规定的。现行法的体例和用语是按照编、章、节 、条、款、项的顺序排列的,第120条之后如果增加一条,意味着刑法典条文顺序的依 次变更,因此,上述“条”的使用是不规范的,只能使用诸如“第×××条中增加一款 或者两款”的表述方法。如果立法者有意为之,而作为刑法修改体例创新的一个契机, 刑法修正案是对刑法体例形式的完善:即在不改变刑法条文数目和形式的情况下,变更 刑法典的内容。那么,刑法典就必须重新公布,使内容和形式获得统一。在这个意义上 ,刑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刑法典重新公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立法缺陷。因此,笔者认为 ,应以此为契机,冲破刑法典的现行体例和框架,确定一个崭新的体例,重新公布刑法 典并相应修正司法机关确立的司法罪名。两高根据三个修正案和一个单行刑法,相应修 正了罪名,于2002年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法释2002[7]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93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 委员会第10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3月26日起施行。),其采用的方式(见下 表)是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并列的方式。罪名的实施时间应该和法律文本的实施时间一 致,两高的修正罪名可谓是亡羊补牢,相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刑法典的重新公布,也 应该提上日程,如果考虑到每次修正后都需要公布,造成立法成本的浪费,那么,在达 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重新公布。
刑法条文 罪名
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投放危险物质罪
(《修正案》(三)第1、2条) (取消投毒罪罪名)
第115条第1款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
(《修正案》(三)第1、2条)(取消过失投毒罪罪名)
第120条之一 资助恐怖活动罪
(《修正案》(三)第4条)
第125条第2款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
(《修正案》(三)第5条)(取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罪名)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相比较,笔者认为,刑法典之重新公布,应该采取和其他 法律相同的方法,即刑法修正案需要规定“根据本修正案,刑法作相应的调整,并重新 公布”,并且在标题的题注写明修正的时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3月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根据×××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 案》修正,……);对于条文的顺序,由于刑法修正案的数目排列是刑法修正案、刑法 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三),相应的,条文排列顺序应该是第×××条,第×××— —2条,第×××——3条等等,如同意大利、日本刑法典的形式,《意大利刑法典》第 374条规定的是诉讼欺诈罪,而第374—2条是根据1992年6月8日第356号立法性命令增加 的,规定的是在向司法机关提供的文书中进行虚假陈述和证明罪。(注:黄风译:《意 大利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日本刑法典》第197条是 受贿、受托受贿何事前受贿之规定,后条是197条之二,向第三者提供贿赂之规定。但 从修正案所使用的表述看,应该采取台湾地区刑法典(2001年修正)的形式,如该法典第 224条规定:对于男女以强暴、威胁、恐吓、催眠术或者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而为 猥亵之行为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24—1条规定:犯前条之罪而有第22 2条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两高的罪名补充规定 ,笔者认为,具体条文之排列,应该采取“第×××条之一、之二”的表达方法。
(三)刑法修正案之司法适用
审判实务中,能否以及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作为判决的根据?学者通常只注意到后面的 问题,以1999年《刑法修正案》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将《刑法修正案》第1条作为刑 法典的一条加以援引较为合适,其理由是:其一,从刑法分则科学化的趋势看,一法条 一罪名是正确处理罪名与罪状关系的方法,1979年刑法典在罪名和法条的关系上存在一 法条数罪名和数法条一罪名的混乱情况,1997年刑法典虽一定程度上协调了这种关系, 但仍不完善,刑法修正案注意到了这一点;其二,修正案规定的是“条”而非“款”, 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文的援引应当是:“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注:蒋 熙辉、徐全兵:“关于刑法修正案适用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9期。) 有的学者没有明确如何适用,认为修正案的方式,其优越性在于有利于维护刑法典的完 整和稳定,法律文书也可以直接援引修订原条文款项内容。(注:黄太云:“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理解与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第1辑。作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成员的意见应当是较有权威的,但这个意见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如 果没有曲解他的观点,应该是直接引用刑法典的条文作为判决的根据。)理论上也有学 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罪名适用图解》中对罪名的阐释,即根据刑法修正案的内 容而将刑法典的内容改变,(注:李永利著:《罪名适用图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年版。)也有的学者采用修订刑法的概念解释罪名。(注:周其华著:《中国刑法罪名释 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换言之,必须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内容已经 发生变化,而形式是古老的。
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和单行刑法不同,因为单行刑法内容上和形式上都独立于刑法 典,因而,在司法判决中,可以直接作为法律文本单独或者和刑法典一起被引用,如贪 污罪需要引用1979年刑法典和1979年之后通过的单行刑法(如《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 的补充规定》等等)。而刑法修正案,无论是否规定重新公布刑法典,都仅仅是一个法 律规定的问题,从实定法的观念出发,意味着刑法典的再次公布,以修正后的新面孔出 现,刑法修正案被同一化为刑法典,因而,刑法修正案无法直接作为判决根据的法律文 本,只能是内容上如何被引用,即形式上作为刑法典的一条加以援引。(注:这个结论 如果建立在刑法典重新公布的前提下,正确无疑,但由于修正案并没有规定刑法重新公 布,也不排除司法实际引用刑法修正案作为判决的法律文本,这是否妥当,值得立法者 和司法部门慎重考虑。)虽然两高罪名的补充规定是并列规定罪名(见上表),但是作为 判决的根据如果同时引用二者,即刑法典第×××条(刑法修正案第×××条),是重复 的工作,也毫无意义。如期货内幕交易罪,只需要引用1997年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证 券、期货内幕交易罪,而不需要引用《刑法修正案》,作为其定罪量刑的法律文本。
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是:
1)刑法修正案仅仅具有立法史的功能,只有研究刑法理论的学者才会关注,对于司法 者来说,无需考虑,而且客观上致使修正案本身所确立的实施时间等同虚设,如《刑法 修正案》第9条规定:“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即1999年12月25日;刑法典附 则第452条规定:“本法自1997年10月1日起实施。”刑法典的生效时间是1997年。(注 :修正案和法典的生效时间,法律的规定通常是不一致的,因为修正案一般规定自通过 之日或者通过以后多少日实施,如《婚姻法》的修正时间是2001年,但是重新公布后的 《婚姻法》附则第51条规定:本法自1981年1月1日起实施,其他法律也是如此。)如果 形式上作为刑法典的一条援引,则引起法律文本内容的实施时间和形式上的实施时间的 错位和脱节。
2)刑法修正案混淆了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效力关系。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特别 刑法,因此,其内容规定如果不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则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如果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则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刑法典之通过主体是全 国人大,而单行刑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排除其效力,即在刑事法的体制之内可以解 决矛盾。目前,刑法修正案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刑法典的通过主体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二者的通过主体是错位的。(注:同样更大错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198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20 01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增加15条、修改22条、删除1条,未改动的 只有14条,虽然修改经过广泛的公民讨论,但是在程序上没有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立法。)这和宪法修正案以及其他法律的修正不同,宪法以及 宪法修正案都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商标法》以及《著作权法》等法律的修改和通过 主体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从表面上看,刑法修正案作为修改和补充刑法的一种形 式,不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但由于二者是形式上的同一和内容上的替代 关系,因而结论全非。刑法修正案在法律形式上是作为刑法典出现的,取得了刑法典的 效力,具有普通法的地位,同样是修改刑法典,其效力却高于其他的修改形式。如果刑 法修正案的内容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注:刑法修正案在内容上是替代关系,因此 ,逻辑上不会出现矛盾。)无法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虽然其通过主体是全国人 大常委会),排除其效力,唯一的可能是通过再次修正解决,或者在刑事法的体制之外 ,通过违宪审查的方法排除其适用。(注:根据宪法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 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决定,解释上,当然有权改变和撤销全国人 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的内容。此方法在目前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先例,其前提是具备 完备的违宪审查的制度。)
因此,刑法修正案的通过程序,必须不同于其他修改形式,换言之,应该具有更为严 格的通过程序。即刑法修正案程序上应当和刑法典的通过程序一样,由全国人大代表大 会审议和通过。换言之,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修改和补充刑法典,但无权采用刑法 修正案的形式,只能采用传统的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形式。
二、刑事法修改之合宪性:立法权限
刑法修正案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合法性问题,笔者以为,并不是修正案本身的问题, 反思刑法修改的历程,则揭示出一个隐藏更深而在固定知识背景下被忽视的根本问题: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刑事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其核心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事 立法权限的划分。
(一)宪法意义上的一般考察
1954年《宪法》第2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的权利;第3 1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法律和制定法令的权利,1975年《宪 法》和1978年《宪法》同之。其特点是区分了法律和法令的概念,并明确法律制定权仅 仅属于全国人大,根据拥有制定权即拥有修改权的原则,全国人大当然有权修改和补充 法律,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和补充法律则没有明确,这也无法通过立法实践 求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修改和补充过法律的实证,因为54年到78年之间的立法史表明 ,全国人大除1958年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之外,没有制定过任何法律,全 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修改和补充法律的机会,因此,合理的结论是否定具有修改和补充法 律权。这种集中性质的立法权限,是历史的必然,客观上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 时间较短,需要解决的事情非常之多,要求其制定和通过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调整显 然不利,因此,授权立法早在1955年就开始,1955年全国人大《关于授权常委会制定单 行法规的决议》,在此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大约通过了30个左右的法律,1959年又再 次授权常委会有权在人大闭会期间,适时的对有关法律加以修改和作出新的规定,但基 于共知的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行使此授权。78年到82年之间,即双轨制并存的时 期,大部分的法律仍然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除几个带有过渡性质的法律(试行)之外, (注:如《森林法》(1984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环境保护法》(1989年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食品卫生法》(1995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不可思议的是《民 事诉讼法》(1991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也在其中。)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商标法 》、《文物保护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1955年和1959年的授权立法在1978年 《宪法》中并没有得到承认,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是违反宪法规定的,但由 于相对比例较小,因而并不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适宜的法律迫切需要修 改,国家和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求迅速增加,单一的法律制定主体显示出无法容忍的滞 后性,1982年《宪法》对立法权作了较大的改变,趋势是下放法律制定权,适应快速立 法的需要:该法第62条第(三)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 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一)……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 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其特点是:1)概念上明确区分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而取消了法律和法令的区别。2 )使用“制定”、“修改”和“补充”,明确了制定权、修改和补充权之权属。由于198 2年《宪法》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制定权和修改基本法律权,82年之后的法律 ,除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外,几乎全部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例外而 且恰好是和全国人大开会同时,则由全国人大通过。(注:1982年《宪法》本身没有规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程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中也 没有非常明确其立法程序,2001年《立法法》第7条对其立法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而对于基本法律的修改,甚至是宪法性法律,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如《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一次修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 第二次和第三次修正全部由人大常委会进行,各种《组织法》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立 法特点是全国人大的立法主体缺位,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明显增强其立法权。
(二)宪法学意义上的刑法考察与评析
如果从宏观上的立法活动而言,制定是指从无到有,修改是指改正有,补充是指在有 的基础上增加新内容,这样则意味着一旦全国人大制定出某个基本法律,就可以躺在功 劳簿上高枕无忧了,余下的工作,即使超大规模的补充、修改,也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完成,客观上就会存在以修改和补充基本法律的名义而使基本法律面目全非的危险,换 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以“合法”的途径架空全国人大的制定基本法律权。刑事立 法的实践表明了此点,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82年 《宪法》之前,就已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几个单行刑法,(注:1982年《关于严 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1年《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 人员的决定》和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在 表面合法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飞快的速度通过了20几个单行刑法,因此,刑 法的修改和补充全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司法实践表明了这种状况的不正常:实行 法典化的国家,而刑法典在现实中被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架空和虚置,刑法典分则成为 高悬的剑,只具有功能上的威慑意义。理论界的批评直接导致了1997年刑法的修订,废 止了几乎全部的单行刑法,而附属刑法的规范也尽收其中,使刑法典成为一个包罗万象 的宝囊。但是,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通过一次修改就可以一劳永逸的,由于立法者认识 能力的非至上性和立法水平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文本相对于变动不居 的社会生活来说,其滞后性是无法避免的,这部法典暴露的弊病在实施后的不久开始出 现,修改和补充刑法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97年之后,又通过一个单行刑法和三个修正 案。(注:即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 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9年新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和 补充,目前,我国已经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2001 年有关土地犯罪的《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12月29日有关恐怖活动以及相关犯罪的 《刑法修正案(三)》。)看来,真正引起批评的原因并不是法律修改本身,因为法律完 备而不需要任何修改的技术神话已经破灭,相反,应该重新研究修改的形式、内容和程 序。
我国修改刑法的实践形成一个认识上的盲点,即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基本法律修改和补充,这种惯常性导致我们忽视:制定权和修改权不仅在理论 上应该是同一的,(注:制定权如果不与修改权同一,意味着上位法和下位法效力的倒 置,因为修改某法律实际上等于废除制定法的内容,根据一般的原理,全国人大常委会 根本无权废除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而现实是相反的。我国台湾地区《法规标准法》第 20条规定:法律修正之程序,准用本法有关法规制定之规定。参见周旺生主编:《立法 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第578页。)即使按照《宪法》的规定,也是如此。第62条 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 有权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其含义是:修改基本法律原则上应当由全国人大完成,仅仅 是作为例外(即闭会期间),而且仅仅能部分修改和补充,而且其内容不得违背基本法律 的基本原则,因此,部分修改和补充决不意味着可以对基本法律推倒重来,也不意味着 旧瓶装新酒,而目前全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刑事法的修改导致了根本上违反宪法 的结局,更加可怕的是,我们对此竟然熟视无睹。(注:这属于宪法学的常识,并不是 笔者的惊人发现,并且,刑事法理论界可能并非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则问题更严重 ,这是群体对违法的漠视。)
(三)现行体制下的权限划分
在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部分修改和补充基本法律的权力前提下,除程序上是例外的 进行之外,必须研究和明确其有权部分补充和修改的内容,而不是如《宪法》所规定的 几乎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原则性限制。(注:虽然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律的 内容有所限制,即不得违背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则,但这种原则性限制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如婚姻法的修改即是如此。)因此,必须注重制定、修改和补充三者微观的含义,对 其概念重新诠释,确定各自的权限划分。笔者认为,从刑事法的角度而言,制定是指确 立新罪名,而修改的对象是已经确立的罪名,补充在立法活动中本来没有其独立的地位 ,所谓立法,是指废、改、立的活动,《立法法》中只有第7条使用了“补充”的概念 ,第53条规定的“修改”显然是广义的,不仅意味着对现有条文直接修改,也包括增加 和删除条文。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并没有直接删除某条文的例子,但其他国家的立法例 可以证明,如日本刑法第二条第一项等。也许恰恰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表述上,使用了 补充和修改的概念。因此,补充一部分属于制定的范畴,另外一部分属于修改的范畴, 只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分别窃取了制定和修改的部分内容,而取得独立的地位。(注: 台湾地区刑法典修改使用的词语是“增订、修正和删除”,根据修改的内容分别使用不 同的词语,如“增订并修正中华民国刑法条文”(2002年1月30日)中规定:“兹增订中 华民国刑法条文第334条之一及第348条之一条文;并修正第328条、第330条至第332条 、第347条及第348条条文,兹公布之。”参见www.law.paochen.com.tv/b-law/index.h tml。区别了制定和修改,并没有补充的概念,相比之下,较为科学。)
我国修改和补充刑法的内容一般包括:
1)纯粹属于解释论的范畴,如对刑法典使用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国家工作人员”等概念的明确化,这是解释权的立法化。
2)属于修改的范畴,即对刑法典条文的直接修改,具体包括: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 单纯修改法定刑的幅度;基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对罪状进行的修改。
3)属于补充的立法,一种情况是本属于修改的范畴,即在条文基础上的明确化补充, 如《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114条的修改,“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实质是对“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立法明确,另一种情况是本属 于制定的范畴,即制定新条文,增加新罪名的立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和刑法修正案 中都存在。例如1999年刑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规定是增加新罪名的立法:
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 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这样的内容在刑法修正案中也可以看到。(注:凡是刑法修正案中使用“在×××条之 后增加一条”的表述,如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条和第八条,都属于增加新罪名的立法, 属制定法的范畴;使用“将×××条修改为……”的表述,本应属于修改刑法的范畴, 但存在增加新罪名的嫌疑,如证券、期货内幕交易罪的规定,是一个选择性罪名,如果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期货内幕交易,只构成期货内幕交易罪,在内容上可以认为是增加 了新罪名。)那么,反思过去的修法,真正应该引起批评的,是增加新罪名的补充部分 ,这部分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改和补充的方式进行,而应当属于制定权,属于 全国人大的权力。即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中已经存在的罪名,也应该慎重对待 ,不能频繁进行,否则,赋予其修改和补充基本法律的权力而不对其修改内容进行限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修改权侵蚀全国人大的制定权就成为必然。但上述区分“制定 ”、“补充”和“修改”的观点立即会遇到最有力的挑战,如果增加新罪名属于制定权 的范畴,那么,如何解释附属刑法的现象?因为附属刑法显然属于增加新罪名的立法, 通常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是否属于修改权和补充权侵蚀制定权。1999年9月1日实 施的国务院制定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许多附属刑法规范,作为犯罪处罚,明 显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因为《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而 根据狭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立法法》的规定,形式上只有法律,才能设立有关的罪刑 规范。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纳入刑法典,其功能和目的也是出于解决其合法性的考虑 。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宪法》对基本法律和法律的制定权的划分,(注:这种 划分的不科学,许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成为宪法学上的常识。)因为不仅事实上难以区 别什么属于基本法律的范畴,什么属于法律的范畴,而且理论上认为规范性文件的效力 层次,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排列顺序 ,《立法法》也是如此规定的。换言之,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还是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和补充的基本法律,效力都处于同一位阶中,从这个角度出发,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刑法典的任何修改和补充,无论其形式是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与 刑法典之间的效力是等同的,即使违反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无法通过上位法优于下位 法的原则,排除其适用之可能,相反,对相同事项和同一位阶的法律,应该根据后法优 于前法的原则,排除刑法典的适用,(注:理论上认为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是特别刑法 ,应该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也证明如此。)因此,在刑事法本身的体制内, 无法否决其效力。唯一的途径是提起宪法诉讼,而目前是不可能的。
总之,如果基本法律和法律在效力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那么,就不应当区别其制定 权。未来宪法的修改,合理的做法是应该在立法权下放的趋势下,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制定基本法律权,全国人大行使复决权,改变和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 法律。
未来刑法的修改,在现行法的体制下,需要向两个方向运动,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概括 是:加强两头,削弱中间,这恰恰与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相反。(注:有学 者批评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了,错位的行使权力,一方面越 权行使立法权,一方面对其固有的法律解释权疏于行使。表现是从来没有进行过宪法的 法律解释,刑法方面也很少。)详言之,相对于其修改内容的第一部分,全国人大常委 会应该加强行使法律解释权,对刑法进行合理的、科学的解释;相对于其修改内容的第 三部分,肯定其制定法律权,但是基本法律的修正案,程序上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和批准,使之纳入到基本法律的范畴,这也符合《宪法》的规定:第六十四条:法 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注:这个条文,内容上 好象和其他相互矛盾,因为如果法律必须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其实是否决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法律制定权,因为通过权和制定权是同一的,但这个条文的含义可以理解为 :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没有必要如此,因为本条的数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之前,而处于全国人大的 职权规定,按照系统解释的方法,可以如此解释,而且,这样的条文也有立法的背景, 因为82年宪法之前的规定是区别法律和法令制定权,82年宪法区别基本法律和法律,因 而忽略了此条的“法律”的含义。因此,此条的法律应该作限制的解释,即基本法律, 如果不如此理解,则我国的大部分法律都违反了宪法,并且,《立法法》也是违反宪法 的。)相对于第二部分,纯粹的修改,应该例外的行使。而1997年之后的刑法修改,已 经有了坚实和良好的开端,尽管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仍应该为之馨馨祝福。(注: 表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法律解释,即2001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和2000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三个修正案虽然和刑法典,具 有制定主体错位的弊病,但形式上更加科学。)
标签:刑法修正案论文; 法律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 全国人大法工委论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立法权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有期徒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