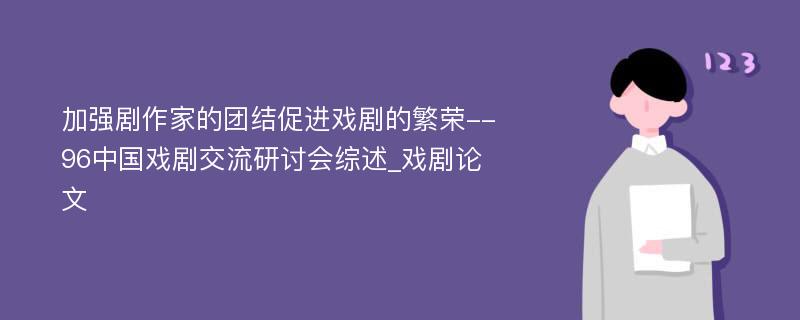
增强剧人团结 促进戏剧繁荣——’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繁荣论文,戏剧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团结论文,中国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的夏末是美丽的,如火的骄阳渐渐隐遁于秋凉之后,浓浓的绿意依然笼罩着京华大地,和煦的清风在红墙碧瓦与华屋广厦之间嬉游,为都市勾勒出一派飒爽英姿与祥和之气。
值此美妙时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广东省文化厅、香港辉煌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96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于8月23日至8月28日在京隆重举行。古老的都城张开双臂,热情迎接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日、美等国戏剧人士数百名,大家欢聚一堂,坦诚以待,相继展示了各地戏剧创作的最新成就,认真总结了中国戏剧既往的成功经验,共同探讨了现阶段戏剧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相互磋商剧场技艺,并对中华戏剧发展趋势做出了初步阐示。
这次盛会,是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戏剧交流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更是一次中国与海外同胞相互了解、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盛会,同时也是一次明证中华民族血脉相连、文脉相通之基本事实的盛会。正如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言,“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可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众所周知的原因,把我们隔离了这么多年,致使我们各自的文化面貌、文化气息有了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快走上一条共同的大路,也就是在新的时代中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优秀艺术的大路”。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杨世彭先生说,他此次能带团赴京演出,感到“意义非常重大”,“与国内一些历史悠久、成就卓越的剧团相比,我们只是资浅的小老弟,但由于香港环境特殊,也建立了一些独特的色彩,正是我们可以和内地剧坛互补共享的”。台湾中华戏剧学会会长杨万运教授则盛赞此次大会,实际是“‘知识’与‘心灵’的交流之旅”。
为期一周的会议,共安排了内地、港、澳、台地区共13台戏剧参与交流演出,召集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共计19位专家学者宣讲了学术论文,组织了戏剧主创人员与与会者进行面对面的探讨与交流,对参演的10部戏剧做了专题性研讨。会议规模之大,节奏之快,成效之好,影响之大,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戏剧交流活动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此次活动中上演的13台戏剧,显示着各地戏剧的地域风格和精神风貌。其中由香港话剧团演出的《次神的儿女》,是译自美国的一部名剧。它表现了健听人李兹先生与哑女罗门小姐之间一段蕴含哲理意味的情感纠葛。当李兹做着种种努力,教罗门唇读,鼓励她发声,直至缔结他们之间的婚姻时,恰恰是将罗门与自己都带入了一种彼此无法认同、无法勾通的尴尬之境。也许李兹的世界与罗门的世界各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一种存在取缔另一种存在,不仅很难成功,而且会使各自丧失原有的内在平衡,导致出现一种混乱、茫然的无序之境。扮演哑女的龚小玲女士,在全剧中不着一句有声台词,仅凭流畅、优美的手语动作和生动表情,塑造了一位情感细腻、个性鲜明、不合流俗的哑女形象。她的出色表演几可乱真,让人怀疑她原本就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直至座谈会上她微笑致意,缓缓谈吐,才让众多好奇者了解了她的谜底。
香港演艺学院演出的《少女梦》,是一部多场次的歌舞剧,取材于我国古典名剧《牡丹亭》,但在再创作的过程中已完全打破了旧的结构框架,改制成了一部载歌载舞、别开生面、充满创造力的艺术新形式。
香港沙田话剧团演出的《苦山行》,是此次戏剧交流中唯一的一台小剧场戏剧,该剧取材于香港同胞为内地贫困地区捐资助学而进行的一次远行活动——苗圃行动,导演有效地采用了格罗托夫斯基贫困剧场的方式,充分运用肢体语言的丰富表现力,以虚实结合、加字幕、演绎东西方神话故事等手段,化熟悉为陌生,化陌生为熟悉,强化戏剧意象,加大表现力度,创造了一台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剧场前卫戏剧。
来自台湾绿光剧团的《领带与高跟鞋》,是由内地出资特邀参演的一部音乐剧,1949年以来台湾戏剧在内地舞台的首次亮相。演员们对这次演出很重视,也很担心演砸了会令内地同胞失望。然而大幕一拉开,随着一群上班族情态各异又颇多风趣的戏剧情节的展开,伴着演员们百老汇式的夸张舞步和嘹亮歌喉,观众席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和开心的大笑——对于台湾戏剧界机智幽默的搞笑手段和轻松自如的表演,内地观众完全领略了其中的奇趣并产生了心理共鸣。
作为东道主的内地剧坛,也为交流演出奉献了9台形式不同风格各异的戏剧,充分展示了从国家级剧院到省、市、县级剧团的编演水平。蜚声海内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与会代表演出了颇能显示人艺风格的拿手好戏《北京大爷》,展现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北京一座古旧四合院里一家人的心态情感。围绕着祖传老屋卖与不卖的矛盾,演绎的决不是守成与破败、保守与创新的简单道德故事,而是揭示着处于社会转型期内的两代人,他们各自具有的茫然复杂的心理意绪。只图知足常乐的德大爷晚年却面临着家道衰落、子辈不孝、无可奈何的事实,当德家一家人的寻宝美梦破灭后,收购此宅的商人已手拎巨款昂然走入德家大门。这结尾中无声的一幕,真比《樱桃园》中三姊妹谛听砍树的斧声更来得惊心。一些台湾戏剧界人士观看了演出之后,不禁啧啧称奇,深深钦佩内地戏剧表演艺术家的深厚功底。
另一台由文化投资公司组台,由人艺老演员演出的戏剧《冰糖葫芦》,也造成了近年来在戏剧舞台上少有的轰动场面。这出反映老人们晚年生活中苦辣酸甜的戏剧,表现着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但却内含着向上、进取的时代气息。于是之、朱琳、吕齐、牛星丽、李婉芬等年事已高却风采依然的老演员们登台献艺,再次在首都观众中掀起了对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敬重之意以及对其舞台艺术的留恋之情。这台戏的演出为此次戏剧交流活动敲响了开台锣鼓,也许是它敲得早了一点,故而使是一些稍稍来迟的港台人士,因未及观看而内心颇有不甘。但他们也提出一些看法,认为是否因为这些老艺术家即将告别舞台,才在观众心目中掀起了这股热烈的情感狂澜?观众是否抱有一种观看易碎古董的心态相与往观?笔者认为,观众的热情恰恰表现了对于一种表演水准的认同,这种认知性的欣赏方式,倒是颇令人感动而赞叹的。
来自山东省话剧院的《布衣孔子》,以恢宏的气势,严谨的舞台风格,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中华民族的先哲孔丘的光辉形象。戏剧时空在古代与现代之间自由移动,从一位中国学者与一位日本女士对历史的观照视角出发,表现了一位忧国忧民,志向远大,胸怀高略却报国无门,性本高洁却屡遭困顿的先贤古圣的胸襟,并从中反思着普通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的命运。这台戏尤为海外人士所看好,美国长江剧团的艺术总监陈尹莹女士甚至说:“《布衣孔子》这个剧的水平可以拿到国际上去比一比。”
来自广东的两台戏《火红木棉花》与《新居》,前者是一部历史剧,反映了日本侵华期间在广东对中国百姓实施人体细菌试验的滔天罪行;后者是一部现实剧,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所发生的崭新的变化,以及普通农家步入小康之后寻求新的发展的故事。前者庄严、凝重,于血泪般的历史叙述中,展现着民族的不屈之志,不朽之魂;后者欢快清新,于富有水乡色彩的通俗画卷之中,展现着新时代的农民新的生活与新的追求。广东戏剧界既凝望历史,不忘过去,又展望未来,探索明天,这两台戏在表现手法上皆有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为大家所公认。
由大连话剧团演出的《勾魂唢呐》是一台独角戏,表现了一位老年妇女对其一生中印象深刻的几个生活片断的追忆。偌大的舞台,只有女演员一人参与表演,时空跨度很大,表演难度颇高,但却节奏紧凑,满场生辉,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艺术效果。此外,武汉话剧院的《人生一台戏》,以其生动感人的艺术魅力,为首都舞台带来一片生机;由经济人自行组团,来自北京的正喜剧《别为你的相貌发愁》,于喜剧的轻松幽默之中,加进了某些沉重的生活内容,引起了广泛争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流演出中出现的一台军旅戏剧。由总政话剧团编演的《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以轻松活泼的风格,再现了军营生活中年轻女性们善良、纯真的天性。舞台上的小女兵可爱极了,以致于使得那些对内地军队一向隔膜,而今才一睹真容的港台人士大为激动,演出结束后,他们纷纷跳上舞台,与小女兵合影留念。台湾国光话剧团艺术总监贡敏先生激动地紧握住总政话剧团团长郑振环先生的手说:“看了你们的戏,我知道我们为什么到台湾去了,知道你们军队为什么打胜仗。”他甚至设想邀请这台戏到台湾去演出,“教育教育我们那儿的部队”。当然,要把这一设想付诸实施,还需要我们做不懈的努力。
本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学术研讨活动,海内外近百名戏剧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京城,带来了他们各自潜心钻研终有发现的最新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就其研究对象与性质而论,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
一,对于中国戏剧宏观发展态势的理论探索。这一问题的提出总是牵连着中国戏剧传统的“守”与“破”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文化的发展不过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递进着,它是累积的过程的结果,自身又处在过程之中,无法超越历史与现实的可能。田本相先生对中国现代戏剧所经历的二度西潮,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发表了一些独到的理论见解,他坚决反对照搬西方,反对跟在洋人屁股后头亦步亦趋地翻花样,而主张“中华文化应当进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格局之中”,这样一来,“它不但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赢得新的地位,也必将在总格局中获得新发展”。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探索剧的得与失,认为探索剧本身存在着“形式外观的丰富多彩与思想内涵的单调苍白的矛盾”,有些戏看起来颇有“哲理”,其实精神上是贫弱的。“西方反传统的现代派戏剧,是在现实主义已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我们这里,现实主义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发展,”因此他提出了深化中国戏剧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的问题。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谭霈生先生则认为:“在新时期戏剧曲折行进的路程上,时时可见一个‘幽灵’出现,它的名字就叫‘传统’”,“内地戏剧在求取进步的路程上,传统的重压导致举步艰难,步履蹒跚,甚至成为停步回转的路标,”因此他取一种伽达默尔式的开放式的传统观,主张中国的戏剧同仁“不能把‘现在’看作只是‘过去’的延续,现在的工作只是对以往形成的东西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努力创造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先生认为,中国戏剧应当在奋进中寻求自救,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经验,创立中国的“现代艺术语言”。他提出这一新的学术概念,认为“现代艺术语言是世界流布的一种潮流,是人类智慧的共同产物,中国的人文观念必须更新,进行大胆的艺术探索,不能因为这类探索代价太大,难度太高就放弃努力,放弃尝试机会”。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士仪先生则通过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关系的分析,来论证中国传统戏剧独特的美学意义,并澄清西方人士对东方戏剧传统的误读。他将通常所译的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的“陌生化效果”改译为“非寻常化效果”,认为布氏所理解的中国戏曲传统的美学旨趣与实际情形存有差异,他形象地比喻中国人的艺术是酒酿,酒里有米,米里有酒,形象创造中不存在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划分。王士仪先生的比较分析与学术发现,对于我们辩析传统的内涵,思考现代戏剧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二,关于港、台地区戏剧发展之历史与现状的学术报告。随着九七临近,内地与香港戏剧同仁之间的交往频繁,近年来该地区的戏剧出现活跃局面。香港戏剧学会副主席麦秋先生介绍了香港戏剧的现状。他说香港戏剧注重理论探讨和艺术批评,经常开展学术交流,演出活动频繁,业余与专业剧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戏剧教育发达,培养了不少戏剧的有生力量。香港剧作家张秉权先生谈到中港关系与香港戏剧,指出“香港戏剧”的真正成立,是六、七十年代之间的事,70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事件的发生使得香港戏剧界的民族情绪增强,演出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中国改革开放,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对香港影响很大,此后出现了一些反映港人回归心态之复杂意绪的“九七戏剧”。随着中港关系的深化,香港进入“后过渡期”,其戏剧中的“中国”,逐渐从认识上的“客体”内化为创作元素中的“主体”。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冯梓勋先生,分析了香港话剧与流行文化的关系,指出香港话剧的使命感强,对艺术的追求也很执著,然而流行文化的渗透是无所不在的,处身于票房的压力和市场主导社会的困境,香港戏剧所采取的措施一是不回避通俗文化,甚至强调娱乐性以吸引观众,然后在嬉笑怒骂之中,结合教育于人生哲理的因素,二是利用某些流行文化的题材为原料,加以艺术化的演绎,以图雅俗共赏。
80年代以来,台湾小剧场戏剧发展迅猛,为台湾剧坛带来生机。台湾戏剧理论家、著名剧作家马森先生撰文对此予以分析,指出80年以来,台湾产生了反写实的新戏剧,不过与此同时,在更大层面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又恰巧赶上了本土意识的回归,但这种回归未能阻挡台湾现代主义戏剧。1980年举办的实验剧展中出现了《荷珠新配》这样的戏,明显受益于西方现代剧场的训练方法,其中又是传统剧的翻新,带有浓厚的本土成分。多半的小剧场戏剧倾向于前卫剧场的演出,没有剧本,全靠演员之间彼此切磋,戏剧强调反叙事结构,强调肢体语言的声响、意象符号等,同时也有一些半职业化的剧团演出西方化与本土化交融的戏剧,至于80年代末出现的对实事政治进行关注的“政治剧场”,其大胆程度不能不说是二度西潮鼓励的结果。贡敏先生则介绍了1995年台北剧场的风貌,指出“台湾的大型舞台剧,似乎仍然好整以暇地在‘搞笑、政治与性’的基调中漫步。惊世骇俗的题材大都走进了小剧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则经常反映于多元化的传媒”。这一年的剧场很难说是景气还是不景气,剧团都在活动,一些新戏被推出,也都创造了票房纪录,但在艺术上的进展却有限。
总览港台戏剧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其大都深受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前卫的色彩明显,探索的方式多样,整体上出了五彩斑斓的特点。
三,关于各地区戏剧团体运作模式的经验交流。以前由于旧的体制的原因,内地专业剧团的管理一直处在一种闭锁状态,规模庞大,人才积压,造成种种弊端。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种打破旧有模式的新型经营方式,即由经济人出面,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另外组团,排演戏剧,呈现出一种运转灵活的民营性质的运作模式。《冰糖葫芦》、《别为你的相貌发愁》等剧组皆属此类性质。当内地戏剧界人士将此种情况介绍给海外同行时,他们颇感兴趣,并将其视作内地戏剧在新的时期出现的新态势。
杨世彭先生介绍了香港话剧团的运作情况,指出此为市府属下的艺术团体,成立于1987年,现有成员不足60名,全员实行聘任制,每年演出七部戏共计100余场。在过去的19年中,演出中外剧作140多部,常能邀请内地与国外的戏剧专家指导其戏剧实践,仅本年度其经费预算就高达2500多万港币,是目前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职业剧团。香港学者邓树荣先生还介绍了香港独立专业剧团的创作概况,指出这类剧团的产生深受后现代理论中自我意识的影响,相对传统的以故事、人物、情节为主的演绎性的戏剧艺术而言,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剧场艺术,将舞台还原为零,在开放空间下,利用各种各样的舞台元素创造多元化的风格。
澳门学者周树利先生介绍了澳门话剧团体的运作情况,他说,80年代初,澳门的戏剧团体只有三四个,迄今向政府立案注册的业余话剧团体连同附属于学校或社团的话剧组织,在这个人口总数只三四十万的城市,大大小小已达20多个。各个剧团每年都有公开演出,而规模较小的话剧组织亦开始尝试联合公演,近年来活动式样很多,由政府主办或赞助或由民间团体举办的各类戏剧比赛,促进着澳门戏剧的开展。
杨万运教授还谈到了台北戏剧治疗研习营的运作情况,他们邀请纽约的蓝迪博士来台,主持旨在进行心理治疗的即兴演出的戏剧活动。研习营成立于去年,有学员30名,通过学习制作面具,展开联想等方式,不断实验傀儡、面具、化妆及梦幻等在戏剧方面的投射力量,以及对人的内心的影响。
此次研讨会,还安排了“院校活动日”,以中央戏剧学院为龙头,串连港、澳、台各艺术院校,共同磋商了如何开展戏剧教育,教养戏剧新生力量等问题。与会者深感加强联系与合作的必要,并初步拟定了一些交流意向。
为了使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活动在今后走入一个有序化、规范化的前景,此次会议还制定了今后每两年为一个周期,在大陆、港、澳、台地区易地轮流举行华人戏剧交流与研讨活动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