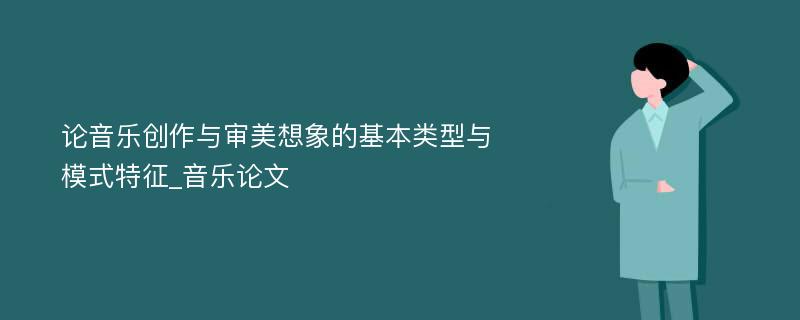
论音乐创作与审美想象的基本类型及其模式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创作论文,特征论文,类型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音乐审美想象是指音乐创作与欣赏者在直接观照客体对象的基础上,积极调动主体的情绪记忆、情感体验,借助于原有的表象和经验创造出新的音乐完型(格式塔完型)的心理过程。音乐审美想象是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最活跃的心理机制,在音乐思维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美学家、音乐家都特别重视艺术创作中的想象。马克思曾指出:“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创造了不只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文学,并给予人类以强大的影响。”[1]舒曼也说过:“音乐家的想象力愈是丰富,对事物的感受力愈是灵敏,他的作品也就愈能鼓舞人、吸引人。”[2]可见,想象力是音乐家艺术才华的一个重要标志。
音乐审美想象按其表现形态的不同,大致可归纳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有意想象;二是无意想。请参见下例图表:
音乐审美想象的基本类型
有意想象无意想象
再创元梦
造造意幻
性性遐想
想想想象
象象
一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意想象的特点。有意想象是一种由创作与审美主体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方向,运用自己以往积累的音乐经验,在审美中主动自觉展开的想象。比如,在音乐欣赏中,人们常常把优美的旋律译成生动的情节或是鲜明的形象和图画。以舒伯特的进行曲为例,舒曼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一天我和我的朋友弹舒伯特的进行曲,弹完后,我问他在这首乐曲中是否想象到一些非常明确的形象。他回答说:“的确,我仿佛看见自己在一百年以前的塞维尔城,置身于许多大街上游逛的绅士淑女之间。他们穿着长裙,尖头皮鞋、佩着长剑……。”值得提起的是我心中的想象居然和他完全一样,连城市也是塞维尔城!”[3]在此,舒曼和朋友的想象显然是一种有意想象。在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有意想象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科林伍德认为,艺术家是通过有意识的想象活动使情感得到表现,日常的粗糙的情感经由有意想想,变成了“理想化的情感”即审美情感。审美情感又不是直接表露的,它在有意想象中和感知材料熔为一炉,成为受意识统辖的“想象性经验”。科林伍德所说的“想象性经验”,就是鲍桑葵所说的“审美表象”。
有意想象可以促使音乐创作、审美主体与客体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得被想象的客体往往失去了独立性,成了主体情感的投射对象。这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线消失了,达到物我融合的程度,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移情”或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Einfuhlung),意思为“把情感渗进里面去”。[4]据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惕庆纳的研究证明,一切认识活动都多少涉及外射作用。艺术家在观察外界事物时通过有意想象的作用,使自己设身处在客体对象的境地,把本无生命的客体,想象为有生命的客体,本无情感的事物,想象为有情感的。洛兹(Lotze)对有意想象的移情现象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们的想象每逢看到一个可以眼见的形状,不管那形状多么难以驾驭,它都会把我们移置到它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这种深入到外在事物的生命活动方式里去的可能性还不仅限于和我们人类相近的生物,……而且还能把这类情感外射到无生命的事物里去,使它具有意义。”[5]艺术家想象中的移情对于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高尔基曾说过:“科学工作者研究公羊时,用不着把自己想象成一头公羊,但文学家则不然,他虽慷慨,却必须想象自己是一个吝啬鬼,他虽毫无私心,却必须觉得自己是个贪婪的守财奴,他虽意志薄弱,但却必须令人信服地描写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6]这说明艺术家必须根据创作需要体验各种人的各种情感,通过想象把情感移入到被表现的对象上。在有意想象中,移情作用不仅把创作与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到客体对象上去,而且在投射过程中也获得极大的享受,亦即是说,有意想象中的移情作用,是主体的人格在和客体对象完全融合一致或心与物相默契的冲动中,充满了审美的愉悦。不言而喻,有意想象中的移情作用,既有很大的审美功能,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在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有意想象是最多、最常见又最有效的想象形式。这类想象形式具体又可以划分为若干类,在此,我们仅取两种类型分析之。
(一)再造性想象
在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音乐家与欣赏者根据已有的特定对象的启发和暗示,在创作与审美意识中形成的相应的音乐表象的过程叫再造性想象。我们可将再造性想象大致分为三种:其一,音乐家对自然界音响进行再造性想象的摹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有一部分自然音响本身就比较谐和悦耳,或者是与某一特定的生活形象、情绪情感体验有密切的联系。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便把这些自然音响进行直接或近似的再造性艺术摹拟,以此来唤起审美主体对相关生活形象和意境的想象。李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野蜂飞舞》,就是通过对野蜂飞舞时所发出的嗡鸣声进行再造性的艺术摹拟使欣赏者仿佛目睹到野蜂在空中高低远近翩翩飞舞的形象。自然界的许多音响都可以成为音乐家进行再造性想象的对象,仅以鸟鸣为素材,借助于再造性想象而创作成功的作品就举不胜举。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百鸟朝凤》、《荫中鸟》、《鸟投林》、《小杜鹃》等等。其二,音乐家对音乐内容与形象的表现,不是由自己直接构思创造出来的,而是借鉴别人的描述和想象进一步加工整理,再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整体构思之中去。如对历史题材、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音乐遗产的改编与移植等。其三,再造性想象更多的是指二度创作(声乐和器乐的舞台表演)和三度创作(欣赏)。二度创作是演奏和演唱者,根据词曲作者在音乐语言符号中所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再造性想象。三度创作则是在原作品和舞台表演提供的全部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化再造性想象。
再造性想象的运行一般遵循两条规律:第一,音乐审美的再造性想象受创作、欣赏主体旧有的音乐表象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因为音乐表象是想象的基本材料,创作与审美主体大脑中储备的音乐表象材料愈多、愈丰富,再造性的内容就愈充实饱满。再造性想象不仅依赖创作与审美主体旧有的音乐表象的数量,而且还依赖于旧有音乐表象的质量。具有不同生活经历和文化素养的人,由于储存的旧有音乐表象在质和量上都是不同的,因而他们的再造想象也不尽相同,因此,音乐思维中的再造性想象具有个体差异性。第二,由于再造性想象更多指二度创作和三度创作,因此,音乐表演和欣赏者必然要受音乐文本(一度创作)的意向性和指向性的影响。就是说,音乐表演与音乐欣赏中的再造想象,是由音乐的构成形式和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所引起的,必须在正确地理解、把握音乐文本的真实内涵和确切意义的基础上进行再造想象。只有如此,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想象。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再造性想象是主体根据客体对象所提供的信息,运用自己已有的审美经验、情感体验、情绪记忆等而展开的,从这一意义上看,再造性想象也仍然具有创造性成分。
(二)创造性想象
创造性想象,主要是指创作主体(音乐家)在脱离开眼前的知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艺术想象。它的基础是无数次的感知和丰富的经验积累,通过创作主体积极的情绪、情感记忆的联想活动将原有的音乐表象调动、开掘、升华并有所补充或重新加工组建,从而创造出新的音乐完型,以此来丰富和深化审美对象的内容。音乐思维中的创造性想象与再造性想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其感知觉为基础,都是在原有的表象基础上重新加工改造,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创造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再造性想象虽也有创造成分,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往往是在原词、曲作者的描述或暗示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创造性想象却不同,它不是依据任何现成的描述,而是运用记忆表象按照自己的创见独立创造出的音乐完型。因此,创造性想象具有首创性、独立性和新颖性的特点,它比再造性想象更复杂、更困难。音乐家的创造性想象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一种严格的构思过程,它有赖于创作主体思维的积极活动,受思维活动的控制调节和支配,这就要求音乐家对已有的感性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只有通过积极的、正确的音乐思维活动,音乐家的创造性想象才能按照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
音乐家创造性想象的心理机制,是在大脑皮层已形成的暂时联系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分解与综合的,从而形成新的音乐格式塔。正因为创造性想象离不开旧有的暂时神经联系,离不开原有的音乐表象的存储和启发,所以不管它提供的音乐形象如何新奇独特,归根到底不过是对大千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超越认识、组合建构而已。“乐圣”贝多芬在双耳失聪的厄境中,还能创作出不朽的音乐佳作(如“第九交响曲”),一方面是靠平日的积累,另一方面是靠他的丰富想象。音乐家丰富的生活经验是创造性想象的基础,是想象的动力所在。创造性想象的动力,不是某种极力想把某些经验恢复或复制出来的愿望,而是音乐家所体验和领悟到的人类的种种情感。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记忆能够使创作主体敏锐、充分、及时地抓住和利用那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暗示线索和时机(音乐动机)。可见,没有丰富的情感作为中介和动力,音乐家的创造性想象活动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种作为中介和动力的情感,并不是日常生活中那种只对个体有意义的即时性和偶然性的自然情感,而是经过了音乐家深刻体验,细腻了解和不断升华之后的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人类情感。可以说,音乐家的思想越是深刻,洞察力越是敏锐,他的情感就会越远离偶然性的个别性,这种情感一旦在音乐家的内心成熟,便会通过想象极力地去寻求一种相应的表现形式把它呈现表达出来。
二
以上我们对音乐创作与审美中的有意想象的特点和类型进行了分析,下面再具体分析无意想象的特点和类型。
无意想象是一种不自觉的,即创作与审美主体没有主动要自己想什么,而自发的不自觉地展开的想象活动。普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系统”,它是由横向的知、情、意与纵向的意识无意识、超意识这两大方面六个因素复合而成。音乐创作与审美想象的“无意识性”,正是由创作主体纵向心理结构的这种多重性所决定的。无意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引起许多艺术家、心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康德曾指出:“知性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起作用最大……,在模糊中能够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并认为“想象的能力就是自生性”[7]。瑞希特也说过:“无意识是我们心灵中最大的一片区域,这种无意识,这片内在的非洲,它的未被认识的疆界是伸得很远的。”无意想象往往是在意识活动被抑制的状态下才能显现其存在并发挥作用。可以说,想象愈是没有意识的干涉和控制,就愈能发挥其想象的效能。正如叔本华所说:“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好多事情,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的更好些。”[8]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就是这个意思。人的本质、本性是潜在的不自知的,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也是不自觉的,唯其不自知与不自觉才能更深更真地表现其本性、本质和更深层的心理内容。艺术想象亦是如此。清代的张浦山对书画中的气韵问题有过这样的描述“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9]。显然张浦山把从无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气韵视为上乘,即真气韵。同理,在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想象只有进入无意识状态,才能引发更多的创作灵感。
当然,我们充分肯定无意想象在音乐创作与审美活动中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就否定意识、否定理性。无意识理论之所以遭到一些人的非难,原因就因为它被认为是反理性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何为理性,何为非理性,这需要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是永远存在于理性形式之中”。[10]无疑,无意识之中有潜在的理性,只是没有被意识到,没有意识到有“理性”,并不说明就没有理性或反理性。所以我们强调音乐创作与审美过程中想象的无意识性,决不等于就是要反理性。
由于无意想象的发生深植于创作与审美主体的无意识深层,因此,它的表现形态更为复杂、神秘、奇特。在此,我们试初步将无意想象分为两种类型:
(一)无意遐想
无意遐想作为一种特殊的想象形式,在音乐创作与审美活动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曾用相当形象的语言描述了无意遐想的发生过程,“某一天的早晨朦胧中预感到一个印象,正苦于如何设法将它表现出来。他试用种种不同的字句,来捕捉他倾心追求的那个表象对象。他试用文字组合M,但是觉得它不恰当,缺乏表现力,不完善,丑,就把它丢掉了。于是他再试用文字组合N,结果还是一样……经过许多尝试,有的似乎接近了那个目标有的却又远离目标而去,均难尽如人意。可是突然间(几乎不求自来的)他碰上了他所寻求的表现方式,刹那间由扑朔迷离转为水到渠成。”[11]翻开中外音乐史,不难发现,许多著名音乐大师创作的音乐精品,就是由无意遐想而发现创作灵感的。贝多芬自幼酷爱大自然,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想象和灵感,常在郊外、田野、林间散步,以便领悟大自然的奥秘和真谛。从晨熹初露的黎明到夜色阑珊的月夜,他走着,遐想着,随身带着笔和谱纸,不失时机地把无意遐想中偶然萌发的乐思记录下来,他的不少名曲的主题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一次,贝多芬和他的学生散步,一路上不停地哼着什么,忽高忽低没有确定的调子。……忽然他停下来不继续散步了,转头就往他的住所跑去,进屋后连帽子都没摘就坐在钢琴旁弹奏起来,这就是《热情奏鸣曲》的最后的快板乐章的主题。从表面看,这一创作过程似乎带有偶然性和突发性。这并不是作曲家忽略了艺术想象这一过程,而是将这一过程以不自觉的想象形式淡化,同时又是深化积淀到无意识层中进行的。
无意想象与有意想象相比,前者要比后者更自由、更开放。有意想象由于受到创作与审美主体传统观念和常规思路的束缚,往往受理智的审查与限制。因为主体的自觉意识活动,很容易受制于旧的成功经验和思维模式,所以,在意识控制下的自由想象,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尽管创作主体自以为按照越轨思维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和自由组合,其实有时这些组合,并没有超出暗中起着制约作用的常规思维,因而,想象并不真正具备反常规的创造性。而当创作主体从有意想象转入不经意的无意想象甚至是随意的遐想时,却有可能产生超常的信息组合,引发真正可贵的创造性灵感或顿悟。有不少带有突破性的音乐创作尤其大量的华彩乐段,往往就是由无意遐想诱发的。总之,音乐家的想象要有成效,不仅需要真正“放”得开——由有意想象、无意遐想展开的艺术建构的最大的独创性、自由度;而且还要“收”得往——由理性和美感造成最敏锐的审美判断力。
(二)梦幻想象
梦是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在睡眠时脑中出现的一种下意识活动。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梦是一种无意识想象,是一种潜意识活动。睡眠时由于大脑皮层中的局部还未完全抑制,因而外在刺激在大脑皮层中的残留痕迹会重新活跃和再现。此外,睡眠时机体内部的某些刺激也会使大脑皮层形成某些暂时的联系而产生梦。梦尽管是一些混乱的、无规则的无意想象,艺术家往往会从这种想象中引发出创造性的灵感。正如阿恩海姆所说:“睡觉在所有的人身上唤醒的创造性想象力,都会使人惊叹不止。”[12]19世纪中叶,法国医师A莫里在对3000例梦的回忆叙述进行研究之后,认为梦是由外界刺激所引起的,这种特殊的无意识想象活动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剑桥大学胡钦森教授也曾对各学科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进行过调查,发现有70%的科学家谈到过从梦中获得的创造性成果[13]。许多作家、音乐家亦是如此,如柏辽兹、瓦格纳、帕格尼尼、海顿、莫扎特等,都从梦这种想象形式中获得过创作灵感,柏辽兹创作的《幻想交响曲》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是一部自传色彩浓厚的作品,全曲除了“幻想”这一标题外,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片段。”作者曾对《幻想交响曲》的创作进行过解释:“一个青年音乐家有着病态的敏感和热情的想象,由于失恋而服用鸦片自杀,但因麻醉剂量不足,未能致死,而昏昏入睡了,在睡梦中出现了奇异的幻想,当时他感觉到感情和回忆在病态的脑海中变成了音乐的形象和乐思。他所爱的女性本身也变成了一支旋律,如同一个‘固定的乐思’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14]对此现象弗洛依德在《梦的解释》一书中曾作过分析,认为“梦由于摆脱了思想范畴的束缚,它就更为柔顺、灵活、善于变化,它对于柔情的细微差别和热烈的感情有极为敏锐的感应,而且还能迅速把我们内心的生活塑造为外界的形象或艺术形象”[15]。梦里的想象是缺乏概念的语言的,梦者的思想情感活动必须用相应的感性形式才能表达出来。
由于做梦的时候,人们不象清醒状态那样按通常的逻辑程序思想,正是这一差异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机会。在梦中储存在大脑中的各种信息,可不受自觉意识的制约自由地组织成各种表象,这种想象也许99%是荒唐的,但也可能有1%是打破常规的思维程序,而带有独特的信息组合,给艺术家带来有益的创造性启发。那么,艺术家在梦中出现的自由的无意想象,是不是毫不受理性制约呢?恰恰相反,它所以能为艺术家带来创造性的灵感,正是与创作主休“有准备的理性头脑”巧妙结合的产物。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是如此。由于艺术家白日所进行的艺术构思,造成了大脑优势兴奋中心或强或弱地制约着睡梦中的想象内容。心理学试验证明,人的梦八九成都出现在“眼动睡眠阶段,”此阶段的脑电波与清醒状态的脑电波相似。心理学家猜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对平时大脑接收的信息进行回顾、整理、选择、淘汰的过程。其二,人在梦中的想象尽管受潜意识支配,但潜意识中的潜知、潜能和潜在的逻辑——生理结构积淀着大量客观信息,具有理性因素。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说:“如今,我还常在梦中跳新的舞蹈,排练新的节目。”有的心理学家认为,作梦也是人的大脑的一种活动程序,它可以为大脑中储存的信息进行去芜存菁的筛选,能使创作灵感彼此交汇,通过梦重新安排已经感受或认识过的东西,使“新”与“旧”的认识合理地沟通和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更多、更深,甚至是更新奇的认识。由此可见,梦这一特殊的无意想象形式所激发的创作灵感,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它往往是显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们用控制论的方法来说明音乐创作与审美中的想象作用,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迪。人的大脑是一个黑暗的箱子,它隐藏着全部复杂的心理结构和微妙的心理活动,音乐家要想洞悉这个黑箱的秘密,就必须靠想象这一艺术才能。人的大脑与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信息不断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化的开放系统,而不是静态的封闭系统,音乐创作与审美主体就是根据其输入输出的信息来想象这个黑箱的秘密的。如果没有想象,这个“黑暗的王国”之门是很难被打开的。有些高明的音乐家往往能从其富有特征的音乐符号中,想象出连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说不出来的秘密。我国著名诗人艾青曾说过“想象是经验向未知之出发,想象是此岸向彼岸的张帆远航。”[16]这里的“未知”就是心灵的黑箱,而想象就是从“经验”和“彼岸”的信息特征出发去打开黑箱的一把钥匙。可见,在音乐思维中想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可以使音乐创作和审美主体充分发挥原有经验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艺术想象,就没有艺术世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2]《世界音乐家名言录》第165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3]戴里克·柯克著《论音乐语言》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4][5]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第603页;第6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6]《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7][8]转引自吕骏华著《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第129页、第150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9]《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425页
[10]转引自《康德传》第92页
[11]转引自陶柏华、朱亚燕著《灵感美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觉》第636页
[13][15][16]金天诚主编《文艺心理学术语详解词典》第2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西洋百首名曲详解》第67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