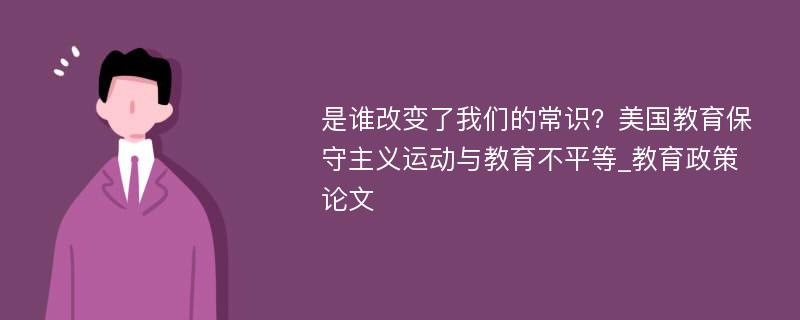
谁改变了我们的常识?——美国教育保守主义运动与教育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不平等论文,常识论文,改变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6)04-0001-13
我们正处于教育思潮的“反动”期,到处充斥着“教育失败”的言论,诸如高辍学率、读写能力的滑坡、教学纪律的散漫、教育标准的缺乏、不能教给学生“真的知识”和就业技能,以至于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太差等都成为对学校进行抨击的理由。而所有这些又被认为是导致生产率低下、贫穷失业乃至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根源。于是抨击者呼吁,教育应该回归“共同的社会文化”、对私领域负责(指个人和公司等——译者注),并提高学校的运作效率。只有这样做,以上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对平等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抨击。这些抨击虽然隐藏在各式各类的话语之中,然而批判的主旨并不难洞悉,其实质就是把美国经济和文化的滑坡主要归因于文化上和政治上“太过民主”。类似的倾向在其他国家也有,例如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教育科学大臣肯纳斯·贝克尔在评价近10年来的教育“右倾”风潮时认为,这标志着“平等主义时代的结束”。① 他说这句话时如释重负,远非忧心忡忡。
由于这些对平等目标的抨击都隐藏在“提升”竞争力和就业、“提高”质量和标准这样的话语之中,因此其真实面目反而变得模糊。这些话语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英国“新工党”的教育政策中,事实上美国的教育政策也同样出现趋向保守的趋势。
然而,如果把教育政策出现这样的转变仅仅归因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精英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教育政策,无疑是过于简单的理解。尽管教育政策中许多针对公平价值观的抨击确乎有把教育政策和经济体系保持一致的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考量是教育政策唯一的出发点。事实上,文化冲突以及种族、性别冲突都与阶级联盟和阶级权力相关。②
教育是一个充满斗争和妥协的场所。大而言之,教育是不同群体围绕制度目标、群体利益和最终决策进行斗争的中介机制。小而言之,教育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所,在这里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以及意识形态的竞争导致了不同的教育政策、教育财政、课程、教学法和教育评估方式的出台。因此,教育既是导致社会形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教育既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是被决定的因素。③ 这其中的复杂性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穷尽的,本文所要做的只是勾勒出美国教育在迈向保守趋势时所引发的主要冲突和斗争。值得指出的是,我认为美国教育政策所趋向的保守性其实是多元的,在教育路线“右”倾的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取向,有的取向彼此之间还是相互矛盾的。④
虽然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美国的问题,但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无法离开宏观的国际背景。因此,在强调更高的教育标准、更严格的考试制度、强调教育为了就业,以及教育要更多地和经济保持一致的背后,是美国对国际竞争失利的恐惧、对资金和就业转移到日本和其他“亚洲虎”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地方的担忧。⑤ 同样地,美国目前国内所呈现出的重拾(当然是有选择性地)“共同社会文化”的社会压力,比如对“西方传统”、宗教、英文语言的强调,其深层次还是体现出对拉美文化、非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的恐惧。这便是我在本文中所要展开讨论的大背景。
当然,美国教育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现右倾,最主要还是得益于右倾阵营成功地实现了广泛联盟;而这个联盟之所以获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却得益于它对常识的成功改造。⑥ 事实上,它创造性地把不同的社会取向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就社会福利、文化、经济以及本文所要揭示的教育问题的应对上达成联盟,我姑且把他们在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上所要达成的目标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
在这个联盟中包含了四股主要力量,它们是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和一个正处在上升阶段的由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每一支力量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和发展历程;然而每一支力量又都融合到了这场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中去了。本文将侧重探讨前两支力量,因为这两支力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在改造美国教育的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另外两支力量就不重要,事实上我在我的新作中对此有详尽和全面的阐述。⑦
一、新自由主义:学校教育、选择和民主
应该说,在美国所出现的这场保守主义教育运动中,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它的主导思想便是倡导“弱政府”。因此,凡私必优,凡公必劣。公共机构,比如学校,被认为是吸钱的“黑洞”——经费投入了却看不到实效。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理性是最优理性,那就是经济理性。在这种理性支配下,效率、成本——收益的考量是两条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是要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这背后所隐含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假设,即所有理性行为人都是这样行动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对社会动机客观中立的描述,而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围绕自己的价值观形成的主观建构。
隐藏在这个立场下的是一套视学生为人力资本的观念。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激烈竞争,学生作为未来的劳动者必须获得相应的技能和习性,使之能有效地参与竞争。对学校的任何投入,如果不是直接和经济目标相关,就都值得商榷。目前的公立学校无论是在组织模式上还是监控方式上都存在缺陷,它既没能把美国的下一代培养成适应未来要求的劳动者,还大量消耗着公民们的纳税,而出现这样状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者攫取”(producer capture)——学校的建立不是为“消费者”,而是为教师和国家行政人员,因此只反映后者的需求,却忽视了真正的教育消费者需求,这样的公立学校应该进行私人企业化的改制。
在这里,“消费者”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消费者选择”便是对民主根本的诠释和保障。教育不过是和面包、汽车和电视机一样的产品,只要通过教育券和教育选择计划等方式推向市场,它就会开始自我调控。在这样的计划中,公民的概念被偷换为消费者;民主的概念被偷换为消费者的选择性。于是,民主从一个政治概念被转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概念,而作为消费者的个体也被抽象并原子化为无种族、无阶级、无性别的纯粹“数”的概念。或许,这种政策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被称为“唯数论”。
不过,这个“消费者和超级市场”的譬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贴切的。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可以去超级市场在一堆相似或不同的产品中挑选自己想要的;不过也有人只能进行“后现代”式的消费,消费那些琳琅满目的产品图片和介绍(此处为作者的调侃——译者注)。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本质就是统治集团将自己对公共决策过程的不满转嫁于国家和穷人的过程。因为,资本流动和工厂外迁不是政府的决定(工厂越来越被迁往那些没有工会或工会组织很薄弱的国家、那些有强制政府的国家、那些没有环境保护条约的国家),穷人也不会自己选择失去工作、失去工厂,让社区和学校齐齐陷入困境,生活失去指望。因此,既不是政府也不是穷人“选择”让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而真正让他们失业的是资本集团的公司兼并和融资收购行为。
由于新自由主义强调“消费者”甚于“生产者”,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也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抨击。以教育领域为例,新自由主义者便对教师工会抨击不断,认为它太强大、太花钱。也许不是出于本意,但类似的抨击却可以被视为人类攻击女性劳动者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教师主体都是女性。
尽管在这个新的文化霸权阵营中,教育政策背后的考量不尽相同,不过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是围绕促进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另一个则是要把学校直接推向市场。加强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教育政策动议,体现在一系列“学习为了工作”和“教育为了就业”的动议中,以及要求缩减“庞大政府”开支的舆论抨击中;把学校推向市场的教育政策动议则体现在了全美以及各州纷纷推行的教育券和教育选择计划中⑧,还包括引发激烈争议的以公共财政支持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的动议。事实上,所有这些政策动议背后的逻辑就是要让学校服从市场竞争的规律。这些“教育准市场化”的政策动议在全美引发了巨大的分歧和争议,尤其是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是否可以经由教育券制度而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这方面的官司正受到全美上下广泛的关注。
一些支持“教育选择”计划的人辩称,只有加强家长的声音和选择权,少数民族的家长和孩子才能最终得到“教育拯救”。⑨ 例如,莫伊就认为对于穷人来说,他们要想“离开差学校而寻求进入好学校”最现实的途径莫过于采取“非正统联盟”的策略,即与共和党和企业联盟,借助这两个最强大、有最强烈的教育改革意愿的社会力量,实现穷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⑩
正如我和许多人在很多时候所说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教育的“准市场化”已经激化了目前围绕阶级和种族所出现的社会分化。(11) 有研究表明,虽然教育券和教育选择计划表面上是要给予穷人离开公立学校并选择自己心宜的私立学校的权力,然而从长远的结果来看该政策只会加速白人离开公立学校进入私立和宗教学校,并最终导致富有的白人阶层拒绝为支持公立学校系统纳税,这将使得已经饱受州政府财政危机、教育经费连年不足的公立学校系统的生存雪上加霜。最终的结果只会出现更严重的教育种族隔离。(12)
英国教育政策学家杰夫·惠蒂对美国轰轰烈烈发生着的教育改革十分关注。他认为,强调消费者选择的政策动议者认为竞争会带来学校的办学效率和办学责任,也会给社会不利阶层带来新的教育机遇,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没有与之配套的根除社会和文化不平等的宏观政策体系”,这样的教育政策目标现在无法达到,将来也无法达到。他还论述到,“在一个高度阶层化的社会,原子化的决策似乎是给了每个个体平等的机会,但是这种将公共决策的责任转而移交私领域的做法,最终会削弱集体行为的努力。”(13)
对此,赫尼格大表赞同,他也说“目前教育运动一个令人悲哀的讽刺就是,由于过度认同学校选择计划,那些试图通过激进改革解决社会问题的良好初衷,也许会最终演变为对集体商议和集体应对机制的瓦解和动摇”(14)。事实上,当这样的取向在实际中会导致阶层、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激化时,就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省。
新自由主义还存在着另一分支。和上文中把学校推向市场的观点不同,该分支认同对学校(不论是私立还是公立)的投入,但前提是学校必须达到资本的要求,于是将教育与增强经济竞争力挂钩的改革和政策在资源上得到了保证。对此,笔者试举两例加以揭示。在全美很多州中,都通过了针对各级学校旨在加强教育和经济联系的法令。以威斯康星州为例,所有的教师教育方向都必须对其未来教师的培养强调“教育为了就业”方面的教育实践;所有的公立小学和中学都必须把“就业教育”因素纳入正式课程体系。另一个例子看似不如上面的那个例子鲜明和重要,但事实上它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更强的宣示,这就是“第一频道”(Channel One)。第一频道是一个盈利性的电视网,目前全美40%左右的中小学生所在的学校被纳入了该传播网(当然其中很多学校是迫于财政压力才加入的,虽然事实上很多州的财政明明是有盈余的)。在这样一项“改革举措”中,一家私人媒体公司免费向该传播网所覆盖的每一所学校提供一个碟形卫星天线、两台播放器以及为每个教室配备电视机。他们还为这些学生提供免费的新闻节目。作为回报,所有参与该项目的学校都必须签一个三到五年的合同,保证他们的学生每天都收看该频道的节目。这听起来相当宽厚。事实上并非如此。不但该套设备在硬件上被设计为只能收看第一频道的节目,而且和新闻节目一起强制学生们收看的还包括一些诸如快餐和运动装备产品的广告。学生被作为强制观众被学校卖给了公司。由于美国法律强制学生必须呆在学校,美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将年轻一代作为商品出售的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倡导和影响下,不仅美国的学校被改造成为了市场中的商品,连学生也不能幸免。
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出的,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我们常识的偷梁换柱,比如什么是民主,我们是不是视自己为“消费者”,以及我们怎样理解市场的运作。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背后是对市场公平性和公正性坚定的信仰——市场会按照个人的努力而有效并且公正地进行资源分配;市场会创造所需要的就业机会;市场会保证所有公民(消费者)获得一个光明未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问一问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经济模式到底是怎样的。新自由主义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光明前景,似乎只要我们放松对学校的控制,让市场更多地发挥调控功能,那么最终技术性工作将取代劳役性工作,目前所饱受的不完全就业和失业之苦也会得到纠正。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却表明市场在人们的生活中既是强大的建设者,也是强大的破坏者。
试举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例为说明,新自由主义者不是一直敦促教育要和劳动力市场保持一致吗,然而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是,虽然劳动力市场中的高技术工作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大多数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将要从事的工作都是非技术工作。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将越来越为零售、贸易和服务行业中的低薪、重复性工作所主宰。这种趋势鲜明地体现于一件事实——截至2005年,收银员的工作总数将超过计算机科学家、系统分析员、物理治疗师、操作分析员以及应用辐射技术人员的数目总和。事实上,就业市场新增的95%职位都是在服务业领域,它们包括个体护理、家庭健康助理、社会工作、饭店和住宿工作、餐馆侍者、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和办公室服务人员。而且,未来10年之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作中,排行前8项的分别为零售员、收银员、办公室职员、卡车司机、侍者、护理助手/勤务兵、餐馆中的配菜员以及看门人。显然,这些职位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高层次的教育。这些工作中的很多都是些低薪水、无工会、临时和兼职的;而且是和劳动中的种族、性别和阶层分化相关、并对其加以强化的。(15) 这便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实景,而不是一如新自由主义所勾勒的浪漫前景。
新自由主义者辩称,因为市场是社会价值的最终裁判者,因此应该将政府的非理性从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决策过程中剔除出去,让效率、成本——收益分析成为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发动机。然而“节约成本”和“去政治化”的措施必然会加深社会中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关于去政治化,弗雷泽有如下论述:
“在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政治性’的界定往往和‘经济性’、‘本土性’以及‘个体性’的界定是对立的。从此,我们就可以导出两类‘去政治化’的制度架构:其一便是家庭制度,即目前的现代男性主导的核心家庭制度;其二便是正式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制度,如付薪工作场所、市场、信用机制以及私营企业和公司。家庭制度通过将事务‘个体化’和‘日常化’,从而形成‘家庭隐私’和‘个体日常’的概念以区别于公共和政治性的概念,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而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制度却通过‘成本节约’的概念来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因此被转化为宏观的市场推动力、私有财产所以权以及管理规划者的技术问题,和政治无关。这两种去政治化策略,把基于个体需求的诠释刻意拉近,从而让人迷失掉整体森林的概貌;而且通过对该诠释因果链的刻意删减,制造出‘家庭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概念鸿沟。”
这样的去政治化过程使得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居于劣势地位的群体需求很难作为公共问题出现在公众面前,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这在弗雷泽看来,就是因为“需求的(政治性)话语”被转化成了“市场的(经济)话语”以及以“个体”为导向的政策。
为了本文的继续展开,我们需要在此讨论两种不同的“需求话语”。其一是反抗性(oppositional forms)的需求话语。这类话语产生于自下而上的需求政治化的过程,是被统治群体反抗性特征的反映。以前基本被认为是“私”的事务被纳入了广义的政治范畴。比如,性骚扰、种族和性别隔离、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反歧视行动都是此类例证,即“私”问题已越过个体和家庭的边界而上升为社会问题。
另一类是与反抗性话语相对立的重新私有化(reprivatization)的话语。它们是应反抗性需求话语的产生而产生的,目的就是要把反抗性话语试图将个体问题社会化的意图压制回个体私领域。他们力图瓦解或压缩社会服务,解除对私营企业的调控,终止那些“过分”的社会需求。因此,重新私有化者试图把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内部事务,认为使用政治性话语(比如权力和性别平等——译者注)是毫无必要的。或者他们认为,关闭一家工厂是私有制保障下无可指责的行为,是客观的市场行为,而不是什么政治问题。(16)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重新私有化论者的目的就是要压制可能爆发的“逃逸性需求”(runaway needs),并将其去政治化。
在美国的教育政策中,这两种话语对抗的例子并不罕见,加利福尼亚州便是其一。加州的重新私有化话语者花大笔的钱做广告,向公众宣称过去在反抗性话语压力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平权法”是政府对“个体才能”的不当干预,是失控性政策。在宏大的宣传攻势下,禁止加州政府使用该法案、禁止加州大学的录取工作使用该法案的公民复决被高调通过。加州的行为引发了其他州出台类似充满争议的教育动议。教育券计划便是另一个试图对公众教育需求进行“去政治化”的例子。该计划的提出者认为谁的知识应该被教、学校应该由谁控制乃至学校的经费状况如何,如此种种都应该交由市场来决定。通过把“工作技能”的最终界定权交由私领域,重新私有化论者把“工作”还原为一件“个体”的事,而且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选择,以此杜绝任何针对工作组织、控制以及薪酬体系的分析和批判。以上例子向我们展示了重新私有化话语的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的案例,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价值”合法化和“理性”合法化。这两种策略都是强势社会群体和州政府对其权威进行合法化时所采用的策略。在价值合法化策略中,合法化过程是通过给人们所想要的来实现的。比如,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州政府为了得到民众的继续支持,可能会为其民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服务,虽然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因为反对性的话语在社会领域越来越有影响力从而重新界定了公私领域边界的结果。
相反,在理性合法化策略中,强势社会群体和州政府并不给人们所想要的,而是试图改变社会需求的理性意义,使之完全异化为其他事物。比如,假如弱势群体要求政府更负责任,并在决策过程中增加民主,那么强势社会群体和州政府并不给予人们所要的民主“价值”,而是改变“民主”的定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中,民主被界定为不受限制市场体制中的个体选择权。从其本质来说,就是政府的退出。而人们对改头换面后的需求以及需求话语的广泛接纳程度,体现了重新私有化论者成功地重新界定了公私边界,同时它也表明在一个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时期,人们的常识是可以沿着保守主义的方向发生逆转的。
二、新保守主义:教学生“真”的知识
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领头羊,笔者认为它事实上还有其他三类同盟者,其中紧随其后的便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弱政府不同,新保守主义强调强势政府,尤其是在知识和价值的问题上。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如雷蒙·威廉斯所称是一个“形成中”的意识形态板块,那么新保守主义则来自其他的剩余部分。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建立在对“过去”的一种玫瑰色的看法上,在它看来“过去”的时期里知识和道德居于无上地位、人们各守其位、社区稳定而且社区中的自然秩序使人们免受现代社会的摧残。(17)
基于该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教育政策包括如下:强制统一的全美或全州课程计划、全美或全州范围的标准考试、重新强调“高”的教学标准和“西方传统”的回归,以及在性格教育中对爱国主义和其他保守特征的养成。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隐藏在新保守主义教育和社会政策之下的考量并不仅仅是“回归”,更核心的是对“它者”的畏惧。这种畏惧在新保守主义对全国统一课程的强调、对双语和多元文化的攻击,以及对提升教育标准的执着之中都清晰可见。
新保守主义对回归传统和道德的强调已激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近十年卖得最好的书便是威廉·贝纳特的《美德书》。贝纳特曾出任共和党教育委员,长期以来他都在批评,“我们的教育根本是在不务正业,无视对知识和道德标准的攻击”。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我们应该“重新强调对卓越、品德和原则的追求”(18)。贝纳特的书通过道德故事,力图恢复孩子们对传统美德的接纳和追随,比如爱国主义、诚实、道德人性以及企业家精神。这样的立场不仅成为社会常识并且影响深远,而且成为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运动很重要的推动力之一。特许学校是一类得到特许可以游离在国家要求之外,根据自己客户的需要而自行开发课程的学校。然而在理论上这类学校仍存在很多可以质疑的地方,比如很多的研究都表明大量的特许学校成为保守的宗教分子变相攫取公共财政经费的手段。按照原来的公立教育法,宗教学校是不能得到政府财政经费的,但是通过特许学校制度,它们做到了。
显然,在新保守主义背后隐藏着的是深深的失落感——对信仰的失落、对想象中传统社区的失落、对有着共同信念且“西方传统”至上的田园牧歌式理想的失落。这和玛丽·道格拉斯对“纯粹”和“危险”的讨论十分类似,想象中存在的都是神圣的,对“污染”的担忧则是首当其冲的。我们/他们的对立两分以及对“他者”文化的恐惧主导了该类话语。
这种对文化污染的担心在教育的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对教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对是否应该为“非法移民”的孩子提供学校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的质疑,有些地方连合法移民的孩子也受到了质疑,此外它还体现在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唯英语”运动以及试图将课程和教材朝向西方传统的重构运动中。
为此,新保守主义者哀叹传统课程的“衰微”、哀叹传统课程中所传载的历史、文学和价值的“衰微”。而在这背后的是一套关于“传统”的历史假设,和对确乎存在着合法性知识和文化优越性的社会共识的假设。然而,我们不能忘了那些为新保守主义者所深刻哀悼其“衰微”的“传统”课程,却极大地忽视了构成美利坚民族的绝大多数群体如非裔、欧裔、亚裔、拉美裔和北美土著的文化。它所关注的只是那些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社会群体,而全然不顾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事实上是一个更广的光谱,它有着“更广泛和复杂的社会和群体构成”。然而,这样狭隘的道德和文化却被强加于所有个体成为“传统”,不仅教给所有的学生,而且以优越的身份教给所有的学生。(19)
正如劳伦斯·莱文提醒我们的,是一种狭隘的和错误的历史观支撑并助长了新保守主义者的怀旧情绪。事实上,无论是经典、还是课程都是历史和变动的,它们总是不断地被调整和修正,虽然这样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愤怒的捍卫者们的坚持”,认为“变革会带来传统的崩溃”。在美国,即使是把诸如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纳入课程也总会引发一系列漫长和激烈的斗争,即谁的知识应该被教的争论。因此,莱文认为当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批判者要求“回归共同文化和传统”时,他们犯了过于简单化的错误,以至于扭曲了事实的真相。目前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所发生的合法性知识的扩张和变更,“完全是正常的现象;它绝不是对课程史中一般模式的背离,即课程与经典的内容总是在不断争议中扩张、改变的,并且始终伴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就该扩张和改变应该是什么性质的持续斗争”(20)。
显然,如此保守主义的立场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在“改革”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中,为保持自身在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不得不作出某种妥协。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历史课程中不断浮现的话语体系,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在这个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特征的话语体系中,美国历史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移民,从最初跨过白令海峡并最终在北美、中美和南美扎根生存下来的“本地人”,到继之不断涌入的墨西哥、爱尔兰、德国、斯堪地那维亚、意大利、俄罗斯、波兰等地的人,以及稍后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涌入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移民。虽然这个关于美国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个体所构成的国家的结论是真实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它在文化上具有丰富和活力特征的原因所在,然而这样的话语却不知不觉地把历史给抹煞了。因为,这些人的移民模式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戴着镣铐来的,来之后又被国家宣判为被合法持有的奴隶,并遭到几百年的隔离;还有的则遭受了身体、语言和文化上的摧残。(21)
这表明,虽然新保守主义迫切地要改革全美的课程和考试制度,但他们也常常以妥协为手段。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对新保守主义教育计划和政策最坚定的拥笃者也同意新的课程体系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要承认“他者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能掌控全局的教育部,而且素有各州和地区掌控学校教育的传统。于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成了每个学科自发地生成自己的全国性标准(22)。笔者在上文所举的历史学科的例子便是这些自发达成的标准之一。
由于开发这些全国性标准的是全国的专业性组织,比如全美数学教师顾问委员会,因此标准自身往往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比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显得多了一些弹性。应该说,学科标准出台的过程本身就起到了对新保守主义知识控制政策的平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对美国整体教育政策的走向过于乐观。事实上,全美学校改革的话语越来越为保守主义力量所掌控,多围绕着“标准”、“卓越”、“责任”等而展开。而且,由于课程标准中的弹性部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很高的花费,因此关于课程标准的讨论,不过是为新保守主义力图加强“合法性知识”的中央控制以及“提高学业成就水准”,无形中增加了话语上的说服力。由此政策将带来的学校在学业成就上的分化,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心。
然而新保守主义的教育政策推动力并不局限于合法性知识的领域,它的强国家理念还体现在加强对教师队伍的调控方面。教师的工作出现了从“许可的自主性”向“调控的自主性”的转变,因此变得高度地标准化、合理化和政策化(23)。在“许可的自主性”下,一旦教师获得了教师资格认证,那么他在课堂上基本是自由的,当然这种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过这限度也由教师自己判断。这样的权力模式是建立在对专业判断力的信任基础上的。然而,随着教师权力越来越变成“调控性自主”,教师的行为无论是在过程还是结果上都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事实上,美国的有些州不仅对教师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定,甚至对教学方法也有唯一的规定,教师如果不遵循规定的教学法便会有行政处罚的危险。这样的控制权力模式不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教师行为动机和能力怀疑的基础上。对于新保守主义而言,这是一个和“生产者攫取”相类似的概念。不过,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市场,而是一个强大的干预性政府,由这样的政府来规定并强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在全州或全美推行教师和学生的统一考试的政策。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样的教育政策取向必然会导致教师技能的削弱、教师工作量的强化,以及教师自主权和尊严的丧失。这其间的道理不难想象,因为在这股保守主义的社会冲动背后,弥漫着的是对教师的不信任,以及对教师能力和教师工会的不满和攻击。
虽然支撑新保守主义教育政策的是对教师的不信任,以及对文化控制权力和文化“污染”的担忧和假想,然而如前文所提到的,隐藏在该立场之下的根本还是文化种族主义,甚至是生理种族主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赫恩斯坦和默雷的“大作”《钟型曲线》。在这样一本销售量达几十万本的著作中,两位作者堂而皇之地为种族基因决定论做论证和辩护,有的地方还有性别基因决定论的色彩。对该书作者来说,冀望社会政策来削弱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浪漫但不实际的想法,因为智力和成就的差异根源于基因遗传,而不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差异;对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来说,最佳的方法便是接纳这样的事实,不要再向那些穷人和智力不济的人群提供“虚假的希望”,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黑人而言的。显然,这本书强化了在美国教育和社会政策中早就存在了的种族决定论的思想。
事实上,种族是一个社会分类,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群体对该分类概念的使用和理解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赫恩斯和默雷的大作不过是为传统的种族歧视思想贴上了一层科学的遮羞布。而该书作者接受了新保守主义基金会一大笔经费的事实,则不仅向世人透露出新保守主义的种族偏见的政策取向,还使得新保守主义势力试图把这样的政策观点带到公众面前的意图昭然若揭。
这样的政策立场并不仅见于教育政策之中,事实上它还见于许多和教育政策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中,并十分强大。他们认为穷人所欠缺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恰当”的生物遗传以及纪律、勤奋和道德等关键的价值观。所以,他们推动了一系列的“改进学习”、“改进工作”运动。如果孩子缺课若干天,则父母的若干福利将被取消;或者如果不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则相关社会福利被取消,当然他们才不管工作的性质究竟如何卑微或者州政府根本不提供托儿和医疗福利。这样的政策不过是“济贫院(working house)”历史的卷土重来,虽然该政策曾在英美历史上盛行过,并带来巨大的破坏力。
至此,我描述了美国教育及其社会政策中的新保守主义立场。它已经和新自由主义创造性地结成联盟,该联盟在其他社会力量的加盟下有效地改变了政策的出台机制。下面,我将转向对威权民粹主义的论述。这是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的第三大力量。
三、威权民粹主义:上帝想要的学校教育
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如果不谈“基督教右倾”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的教育政治生态。(24) 这一股势力对美国的媒体、教育、社会福利、性及其身体政治学,以及宗教等领域的公共政策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远超过其群体范围自身。它影响的根源来自多方面,这包括其广大成员的忠诚、雄厚的经济实力、民粹主义的修辞学,以及对目标追求的不断进取。“新右倾”的威权民粹主义者把自己对教育和社会政策的一般原则,建立在圣经中关于基督道德、性别角色和家庭的权威信念之上。例如,这些新右倾主义者们将性别和家庭视为一个有机、神圣的统一体,它最终解决了“男性的自我中心和女性的自私自利”的缺陷。正如亨特尔所说:
“由于性别是神圣和自然的…所以社会不应该允许(这方面的)合法性的政治冲突…如果不是因为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干扰,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地——都是处于一种和谐状态…‘真正的女人’,比如她们了解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是不会为了追求自我而威胁到家庭的神圣性的。当男人和女人对自己的角色内涵进行挑战时,他们实际上是背离了上帝和自然属性;当这些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及世俗人文主义者不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已经危害到我们社会存在所依赖的神圣和自然基础”。(25)
在这群人的观念中,公立教育自身便是无穷危机之渊薮。用保守主义运动家蒂姆·莱希耶的话来说,“现代公立教育是儿童生活中最危险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在宗教、性、经济、爱国主义以及生理方面都会带来危险的影响。”(26) 这和新右倾主义者围绕学校教育和家庭现状所感到的失落直接相关。
在过去,正如新右倾主义者所看到的,学校不过是家庭和传统道德的延伸。家长们之所以对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感到放心,是因为这些学校都是由当地控制的,而且直接反映了圣经中以及家长们的价值观。然而随着学校的权力为一群外来的、精英势力所掌控之后,学校现在成为横在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一道障碍。很多人都感到,以往存在于家庭、教会和学校之间的统一关系破裂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控制,孩子乃至整个美国也同样失去了控制。事实上,新右倾主义者认为家长对于教育的控制起源于圣经的界定,因为在上帝的蓝图中,对年轻人的教育职责首当其冲的是家庭,尤其是父亲。正是这种“外来精英的控制”、与圣经教义的割裂以及“上帝所给予”的家庭和道德结构的瓦解,带给新右倾主义者强烈的失落感,并成为他们致力于教育变革的不懈动力。威权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重要社会力量,这不仅是指它的话语影响,更重要的是它的经费支持,以及它在学校应该做什么、如何使用经费以及由谁掌控等问题的社会冲突中的影响力。当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性别、性和家庭,事实上还涉及到一系列和“什么才是学校教育的合法性知识”相关的问题。在对宏大的学校知识体系的思考中,保守主义活动家对课程的开发商施加不小的压力,以改变课程的内容以及州政府关于教学、课程和评估的政策。这点至关重要,因为美国不存在国家课程,课本都是商业化运作,由各州政府自己采买,所以威权民粹主义对课本开发商以及州政府的政策游说行为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以课本开发商的“自我审察机制”为例,威权民粹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当强大的。例如,在保守人士的压力下,许多课本出版商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稿收录到文学人类学课本中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把文中关于美国严重种族歧视的部分删除。(27) 在国家课程政策层面的,比如课本立法,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就规定课本中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服从权威和反对“行为出轨”方面价值观的传递。由于绝大多数的课本开发商都着力于课本的内容和组织方式能为人口大州所接纳,以便达到全国推广的目的,这就使得诸如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人口密集的州在“什么是合法性知识”的问题上有相当的决定权。
因此,和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新自由主义因素彼此呼应和强化,威权性民粹主义的宗教活动家在课程政策和实践中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只有使权威、道德、家庭、教会和“优雅”等价值观重新回归社会核心,学校才能从目前包围着我们的“道德败坏”中被拯救出来;只有在学校中重新强调圣经教学的常规性和重要性,我们的文化才能得到拯救。
虽然许多州和学校已经建立了对抗这方面压力的机制,但是正如我在《文化政治和教育》以及《国家和知识政治学》中所阐释的,由于学校系统的官僚本质,加之当地和州政府的诱导,使得许多家长和社区成员也许并不认同新右势力的意识形态,却仍然参与到了对现行学校教育的攻击和批判中来了。
虽然威权民粹主义试图影响课程和课本的努力不断升级,但是这种弥漫着的对现行学校教育的不满,使得威权民粹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券和教育选择计划给予了有力的呼应和支持。虽然由威权民粹主义者所构成的新右势力对资本的动机和经济计划也持有保留和怀疑的态度,毕竟他们自己是企业裁员和经济重构的亲历者,但是他们却认同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教育政策取向,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利用这样的“改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学校税率的减少,还是税收或公共财政的重新分配改革,都使得这个群体可以谋取更多的经费来创建符合他们道德信念的学校体系,以找回他们认为“失落了的社区”。
这种社区重建运动,无疑受到了教育政策较量中的“重新私有化”取向的影响。在否定对手立场的同时,重新私有化话语事实上采取了一种更“政治化”的处理,即把问题上升为公共问题。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重新私有化的讨论却带来了更多的关于“逃逸需求”的公共讨论。不过,这样的讨论却并不是以其反对势力的得胜而划上句号的,相反它们带来了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界定,把“逃逸需求”重新纳入经济的、家庭的和个体的领域中去。如此,新的保守联盟最终形成。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现实——一套威权民粹主义式的重新私有化话语体系,创造性地把社会中的不满分子团结在了一起,使他们的希望和恐惧连接成了一体,并因此成为教育重新私有化运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者。(28) 如果不是因为右倾群体成功改变了诸如“民主”等一系列关键概念的内涵,基督教右倾势力是不可能在保守阵营中谋得一席之地的,而重新私有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
四、新的专业与管理中产阶级:更多、更频繁的测试
我会用相对简洁的文字来描述新的专业与管理中产阶级在保守主义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因为它的影响虽然不断增加却还是有限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在这场政策运动中确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是一个新的专业中产阶级,他们基于自己的技术优势得以在国家和经济体系中实现升迁。他们大多拥有管理和技术的背景,因此为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化政策和新保守主义的中央控制政策的几个核心理念——政策透明、政策估算、“产品控制”和政策评估——提供技术的和专业的支持。
这群实现了社会升迁的专业及管理人士也许并不信奉保守主义阵营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们也许是观点温和的,甚至在政治上还有点“自由”色彩。然而,由于他们是效率、管理、测试和审计方面的专家,因此为保守主义的政策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他们自己的个体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类技术的推广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强调“控制”、“测量”和“效率”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常常支持“中立工具主义”的政策,即使该类政策被用于其他政治意图。(29)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学校对更严格的测试、责任和控制的强调仅仅归因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事实上,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政策压力来自学校的管理者和教育部门的官员,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样的控制是得到授权的而且是“有益”的。这些控制形式虽然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是更严格的控制、更高标准的测试和责任回溯的方法为这些管理者们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提供了支持。这使得他们能够以全面的形式加入到教育改革的运动中去,并强化了他们的专业地位。
而且,在一个学历和文化资本竞争日趋激烈的年代,重新进行社会分层的机制,比如强制性的标准化考试制度,使得专业和管理阶层的孩子和其他孩子相比,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因此,引入诸如标准化考试这样的措施对人群重新进行分层无疑会强化文凭的价值,而文凭是新中产阶层最容易获取的,因为他们是文化资本的掌控者。笔者在此并不是说这都是一些有意识的行为,但是这样的政策却在客观上有利于新中产阶层的前进,因为新中产阶层不掌控经济资本,他们所握有的只有文化资本。
基于以上的境况,我相信这个群体对意识形态的右倾不具有免疫力。考虑到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抨击,这个群体难免会对其子女在一个不确定的经济世界中的社会前景感到忧虑。因此,他们也许会很容易地被新保守主义阵营的立场所吸引,尤其是新保守主义中对“传统”内容的关注、对考试制度的重视以及对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分层机制的大力强调。这可以从很多州的家长对强调传统科目学业成就的特许学校的支持中得到反映。而且他们今后在类似的教育政策上还会达成一致。即使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和“右”倾集团存在不一致,但他们仍可能会为其所驱使,因为他们对工作和孩子前途的考虑是压倒性的。
五、结论
由于美国教育政治的复杂性,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论述了对美国教育政策并在社会领域中有着深刻影响的保守主义运动。这场教育的保守现代化运动是由一个社会力量联盟推动的,虽然该联盟内的不同社会力量在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
重要的是该联盟的性质。该联盟克服内部的分歧,赢得这场教育政策和实践变革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尽管新自由主义的诉求是弱政府而新保守主义的诉求是强政府,这么两种看似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诉求却创造性地走到了一起。目前出现的教育标准、教育内容和教育控制权力出现的集中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经由教育券和教育选择计划而实现的。
一旦全州或全美的课程和考试制度就位,那么学校之间的比较就成为可能,也许美国也会出现类似英国的学校排行榜。当然,也只有存在标准化的内容和评估,市场才能够变成“自由”的,因为“消费者”才能获得哪些学校是“胜出者”的“客观”数据。建立在消费者选择基础上的市场理性才能最终导致所谓的好学校学生盈门,而差学校关门了事。
关于该类政策对现实中学校的负面作用我已经在我的书里进行过详细阐述。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重申,一旦穷人“选择”把孩子留在内城或郊区那些没有经费并且破败的学校时,那么他们就是为自己“错误”的选择唯一负责任的人。然而,事实是他们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机会,很多时候他们经济困局、每天疲于奔命、对学校状况一无所知,加上城市公共交通拥挤而且昂贵,他们也只能如此“糊涂了事”地选择。于是,结构性的不平等被重新私有化的话语一笔抹杀,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策、威权民粹主义和新专业管理中产阶层政策,这两对看似矛盾的政策流派却相互应和起来,并结成了最终的联盟。(30)
虽然我认为教育政策的领导权握在保守主义阵营手中,但我并不想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构成这个阵营的四中力量是铁板一块,而且无往不胜。这不是事实。在美国的地方层次,掀起了大量的反抗文化霸权的运动,并带来很多不同的改变。在面对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和压力时,许多的高校、中小学和学区都表现出相当的对抗能力,也有很多的教师、学者和社区活动家创造出许多在教学和政治属性上都具有“解放”特征的教育运动,或者正在捍卫具有类似特征的教育项目。
我们已发现保守主义阵营开始出现缝隙,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的学生正在积极抵制各州所颁布的强制性标准考试。这样的行为得到了不少教师、学校管理者、家长和社会运动家的支持。显然,有些社会力量开始浮出水面。
话虽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对创造有益于进步主义政策的宏观社会环境的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我们要牢记,美国是一个没有强大中央教育部的国家。教师工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又十分微弱,而且其所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总是促进进步主义运动的。而且,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进步主义教育政策的日程表,人们也莫衷一是,毕竟推动教育进步主义的社会因素是纷繁复杂的,比如种族/民族、性别、性、阶级、宗教、“能力”等,有时这些不同因素的社会诉求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很难在形式上得出一个全国性的“进步主义”教育政策和实践运动。
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反文化霸权的工作都是在当地和地区范围内进行的。虽然目前也开始出现了建构全国联盟的努力,对此我们姑且称之为“分权统一体”(decentered unity),如“全国教育运动者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Educational Activists)及其其他围绕“反思教育”而形成的组织已经在全美范围内出现,但是这些运动中没有一个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威权民粹主义那样有背后的经费和组织方面的支持。也没有一个有能力如保守主义运动那样通过媒体或基金会等方式把自己的主张带到“公众”面前。也没有一个有能力或资源迅速地在全美范围内形成一个力量联盟,提出或支持某个政策动议。
不过,在这些结构、经费和政治的多面性中,我们也可以乐观地看到,还有这么多的社会群体没有被保守主义的文化霸权所整合,而且创造出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反抗运动,并在地方层次带来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社会事实以鲜活的形式向我们表明教育政策和实践永远不会只有一维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些鲜活的事实表明,保守主义政策的成功也不是必然和无懈可击的。这点对于我们身处已经忘记什么才是真正需要的教育的年代,尤为重要。
Translated by LUO Yan
( Institute of Education,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罗燕,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4
译者简介:罗燕,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注释:
①Madeleine Arnot." Schooling for Social Justice," unpublished paper.University of Cambridge,Department of Education.1990.
②Michael W.Apple,et al.,The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New York:Routledge,2003.)
③同上.
④Michael W.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2[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
⑤William Greider,One World,Ready or Not.(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7.)
⑥Michael W.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6) ; Michael W.Apple,Official Knowledge,2[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0.)
⑦Michael W.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2[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
⑧John Chubb & Terry Moe,Politics,Market and America' s Schools.(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 ; Ernest House,Schools for Sale.(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8.)
⑨John Chubb & Terry Moe,Politics,Market and America' s Schools.(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90) ; Ernest House,Schools for Sale.(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8) .另参见,Geoff Whitty," Creating Quasi-Markets in Education" in W.Apple,Revi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ume 22( Washington: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1997) .
⑩Quoted in Whitty," creating Quasi-Markets in Education" ,17.
(11)See 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 Lauder and Hughes,Trading in Futures.
(12)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especially Chapter 4.
(13)Whitty,Creating Quasi-Markets in Education.58.
(14)Henig,Rethinking School Choice,22.
(15)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Greider,One World,Ready or Not; Christopher Cook," Temps Demand a New Deal" ,The Nation,March 27,2000,13—19.
(16)Fraiser,Unruly Practice,171.
(17)Allen Hunter,Children in the Service of Conservatism; 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
(18)William Bennett,Our Children and Our Countr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 .
(19)Lawrence Levine,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Boston:Beacon Press,1996) ,20.
(20)ibid.,15.
(21)Howard Zinn,A People' 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9) ; Howard Zinn,The Future of History( Monroe Maine:Common Courage Press,1999) .
(22)Diane Ravitch,National Standards in American Education( 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95) .
(23)Dale,The State and Education Policy.
(24)更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参见Apple,Educating the" Right" Way,The Subaltern Speak.
(25)Hunter,Children in the Service of Conservatism.15.
(26)Hunter,57.
(27)Delfattore,What Johnny Shouldn' t Read,123.
(28)Fraser,Unruly Practices,172—173.
(29)Basil Bernstein曾对国家中的新中产阶层和私领域中的中产阶层作出区分。参见,他的专著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30)Apple,Cultural Politics and Education,22—41.
标签:教育政策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