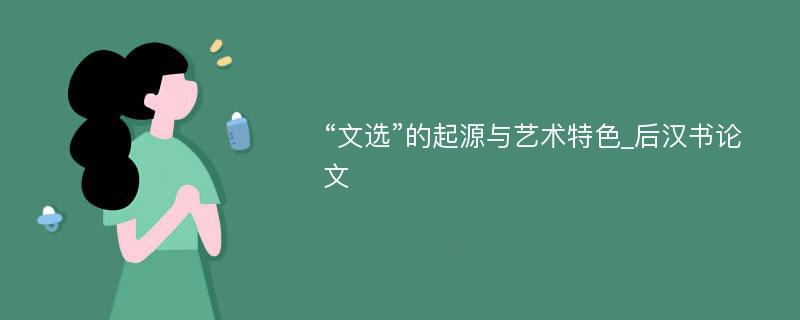
《文选》策诏文源流及艺术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特色论文,艺术论文,文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文选》的37种文体中,除赋、诗、骚、七四体为文学作品外,余下的33体均属于实用性的文章。文章以“诏”起,其后继之为“册”、为“文”。册选文一篇,文选文三篇,即《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和《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它们分别是齐武帝萧赜、梁武帝萧衍策试选拔秀才的策诏文,由当时的大手笔王融和任昉代作。
作为文体的策和文虽然都属于皇帝的命令,但因使用的性质不同,其作用也不一样。册,为册书,产生于商周,兴盛于两汉,其作用,一是“册封王侯”[1],二是“诸侯王三公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三是“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2]。纵观两汉册书,用于“册封王侯”的少,用于重臣擢拔与罪免的多。这种现象之产生,反映了两汉治国的重心已由初期的封王建国转向了对重臣贤才的依赖和使用。高帝曾说“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3]哀帝亦云“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4],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他们对贤大夫、三公的重视。正因此故,他们常用册书的形式将那些尸位素餐,“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5]的庸臣从重要的位置上罢免下来;同时又将那些有德有才能直言极谏之士从草莱之中选拔出来以登朝位,这样便出现了皇帝亲自主持策试之举,便产生了为策试所需要的策诏文。策诏文虽缘起于对贤良方正的征用,其性质作用有别于册书,但其书之于册的外在形式和表达皇帝旨意、命令这一根本属性,则又表明它同册书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是册书的一种演变或创新,具有“尊显”的意义和作用。
策诏文之作,始于汉文帝。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说:“汉文中年,始举贤良”。徐师曾《文体明辨》说:“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均认为汉文帝是其创始人。考之史籍,亦如二人所言。《汉书·文帝纪》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此处所说的“傅纳以言”,是指被策试者要“敷陈其言”而文帝要“纳用之”,既然要敷陈其言,亦自有对策文之产生。由此观之,完整的策试是由策诏文和对策文组成的。它们如同联璧玑珠,相互生辉,共同展示策试的全过程,为我们以下的考证提供了依据和方便。文帝此次策诏贤良文学,《汉书·晁错传》也有记载,说:“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其景况之盛,亘古未有。晁错本传全文录入了文帝的策诏文和晁错的对策文,文帝的策诏文是这样写的: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
这是一篇陈政的策诏文。文章以“起年月日,称皇帝曰”[2]发端,行文简捷明快,遒劲有力,不失为一篇佳作。如果说,晁错的对策可称为“蔚为举首”[6],那么文帝此策亦可誉为“开山之作”。自文帝之后,历代欲有作为的君主无不“踵其事而增毕,变其本而加厉”,以至一次策诏连下数首策文,将策试的范围和内容引向了开阔的境地。比如汉武帝建元元年策诏贤良[7],就明确表示要“垂听而问焉”,后策试董仲舒,真的连策了三文,由一策的“求天命与性情”,到二策的“求帝王之道”,再到三策的“求天人之应,治乱之术”,一问一答,步步紧追,将策试引向了深入。董仲舒的对策文,刘勰用“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奥者,事理明也”[6]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现有文献记载,汉魏晋宋齐梁,有策诏文和对策文可考的篇目并不很多。西汉,武帝的策诏文,除上述一篇三首外,还有《元光五年策贤良制》一文。这次策诏,《汉书·公孙弘传》记载说:“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第一。”该传全文录入了武帝的策制文和公孙弘的对策文。武帝的策制文与前篇相比,重点仍放在天文地理人事上,设置的问题其容量之大,可谓无所不包,既令人目不暇接,又让人跃跃欲试,以展才智风采,学术风流。其设置之妙,亦可垂示千古。而公孙弘的对策以简要著称。刘勰称之为“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6],也是一篇光照千古之作。有魏相的《贤良对策》,此为残文,见于《汉书·韩延寿传》,说:“是时昭帝富于春秋,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以‘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昭帝的策诏文史无记载,故不可考。有杜钦的《举贤良方正对策》、《白虎殿对策》和谷永的《建始三年方正对策》。杜钦的《贤良方正对策》和谷永的对策为同时之作,《汉书》两本传都作了记载。建始三年是汉成帝的年号,成帝本纪有此次策诏贤良的诏书记载,而无策诏文的记录,两对策文亦只字未提,故成帝此策亦无从考寻。杜钦的《白虎殿对策》,其本传全文录入。成帝的策诏文亦见于对策文中,说:“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在?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可见,这也是一篇残文。杜钦的对策文,刘勰用“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6]予以称赞。
后汉,有申屠刚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后汉书·申屠刚传》云:“平帝时,王莽专权,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卫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书秦,莽令元后下诏曰:‘刚所言僻经妄说,违背大义,其罢归田里。’”再细披原文,则知此策为疾世愤恶之辞,与常规的对策文相比,另具特色。而平帝的策诏贤良方正亦成为王莽收买士心,玩弄权术的一种手段,其策诏文失而不可考。有鲁丕的《举贤良方正对策》。《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鲁丕附传》云:“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丕之对策文,《后汉书》本传不载,而严可均《全后汉文》依据袁宏的《后汉纪》收录了全文。刘勰称此文为“辞气质朴,以儒雅中策”[6],认为是后汉对策中唯一一篇可肯首的文章,肃宗章帝的策诏文因对策文只字未提,现也不知其所云了。有养奋的《贤良方正对策》,此策不见于《后汉书》,《全后汉文》依据《续汉五行志三》注补引《广州先贤传》作了收录,同时又据《广韵》引《孝子传》叙其生平说:“奋,字叔高,郁林人。永元六年举贤良方正。”永元是汉和帝的年号。《后汉书·和帝纪》记述了永元六年策举贤良的诏书,并说帝要“亲临策问”。和帝策诏文,养奋的对策文只录用了一句话:“策问:阴阳不和,或水或旱。”余者无记载。有皇甫规两篇《举贤良方正对策》,二文均见于《后汉书》其本传,并说:“冲、质之间,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曰……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弟,拜郎中。”“永康元年,征为尚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规对曰……对奏,不省。”这里说的“冲、质之间”,是指冲、质二帝之间。冲帝是建康元年八月即皇帝位的,时年二岁,第二年便去世了。质帝即位,年仅八岁,然第二年被梁冀鸩杀。据《后汉书·冲帝纪》记载,建康元年曾进行过策举贤良方正,故皇甫规的第一次对策应在此年。永康是汉桓帝的年号。《后汉书·桓帝纪》说:“壬子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时间与本传合。然二次策诏文既不见于二纪传,又不见于二对策文,故其面貌不可知。有荀爽的《延熹九年举至孝对策》,《后汉书》本传收录了全文,并叙其事云:“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后汉书·桓帝纪》也说:“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二纪传所叙相同,然策诏文均无记载,今亦不可考。
魏晋,有挚虞的《泰始四年举贤良方正对策》,见于《晋书·挚虞传》。这次诏举贤良方正,《晋书·武帝纪》略有记述,说:“泰始四年……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而武帝的策诏文,因二纪传无记载,不可知。有武帝的《策问贤良却诜等》、《策问贤良阮种等》、《策问秀才华谭等》三篇策诏文和却诜、阮种的《策贤良对策》、华谭的《举秀才对策》三篇对策文。这六篇文章均见于《晋书·却诜阮种华谭列传》。列传分别记载了三人举贤良秀才始末,如说却诜,“泰始中,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举诜应选”,“以对策上第,封议郎。”说阮种,“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之士,于是太保阿曾举种贤良”,“时种与却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虽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策奏,帝亲览焉,对擢为第一,转中书郎。”说华谭,“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曰……又策曰……又策曰……又策曰……时九州举秀才,策无逮谭者。”对于却、阮二人对策的时间,二本传,一说是“泰始中”,一说是“是时”,严可均辑校的《全晋文》却将时间定为“泰始七年”,不知何据。但据阮传说的“俱上第”,则又可以肯定二文作于同时。此外,还有陆机的《策问秀才纪瞻》和纪瞻的《策秀才对策》。《晋书·纪瞻传》说:“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曰……”详细记载了二人一策一对的情况,其时间大约在元康年间。《晋书·陆机传》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又说:“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朗。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吴王晏出镇淮南在前,赵王伦辅政于后,其时大约在元康年间。元康是晋惠帝的年号,晋惠帝是个白痴。白痴不能策问,执政的贾后不便策问,于是,只好由尚书郎陆机来策问了。
刘宋,有颜延之的《策秀才文》,《宋书》、《南史》均无记载,仅见于李善注任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说:“颜延之《策秀才文》曰:‘废兴之要,敬传良说。”这首策诏文作于何时,今无从考知。刘宋以后至《文选》结集,这段时期除见于《文选》的三篇策诏文外,其他的无从知晓了。
总之,自两汉至梁,今天能见到的策诏文和对策文,就是这么一些,这显然不是它们的全部,它们的全部应该比现在见到的要多。这可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贤良方正》见其大概。该卷考稽此时段各代君主诏举贤方良正共34次,其中西汉17次,东汉14次,魏晋3次。诏举上第授官者除上述贤良外,西汉还有严助、朱云、王吉、贡禹、盖宽饶、孔光、杜邺、何武、辕固、黄霸、朱邑等11人,东汉还有苏章、李法、崔骃、周燮、刘瑜、荀淑、张奂、刘源、刘焉等11人。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不难发现诏策文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伴随着朝廷政治运作和治国需要而产生形成的一种特殊文体。象公文而又非纯粹的公文,似命令而又非地道的命令。由于它的功能主要是作用于对贤良方正的策试和选拔,因此它仅使用于策试者与被策试者之间,是策试者用来考察人、了解人的一种重要媒介和手段。它俨然象一架端庄的天平,既能给测试者上架测试的机会,又能让测试者在它那严正的砝码下测试出各自的份量。它既是秘密的,又是公开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作为现实的举措,历史的经验,它给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以莫大的启迪,为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提供了一个灿烂的平台,因此历来为读书人所看重。或许正因此故,《文选》才将此类文体选录出来以飨后人。由此可见,选录者的眼光是远大开阔的。
(二)
《文选》选录的3篇13首策秀才文,与两汉以来的策诏文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欲论述它们的艺术特色,既要考虑它们自身的特点,又要考虑它们同两汉以来策诏文的联系,这样论述才能全面。基于此,笔者认为其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立意上高度体现了治国之要道。谭献曾对王融、任昉三文之妙用了一个“意”字来进行概括,说永明九年策“纯以意运”,永明十一年策为“意胜”,天监三年策为“有主文谲谏之意”(《骈体文钞》)。这一评价大体是对的。然此“意”指什么,前二评未加申说,后一评仅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个“意”主要是指君主之要道。傅玄《傅子·治体》说:“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袁准《袁子正书·用贤》说:“治国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赏功,四曰罚罪。四者明则国治矣。”傅、袁所说的治国之柄,与汉文帝提出的“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的治国之道是有所不同的。傅、袁之说是站在为臣为民的角度对君主提出的希望,文帝之说是站在为君的立场对手下贤臣提出的要求。因此,前者理想的成分多,后者实践的意味浓。理想的成分多则显得空泛而稍欠实际,实践的意味浓则显得实在而切中政要,所以自文帝创这种策诏之意,立这种策诏文体之后,各代策诏文无不加以承袭并根据国中情况进行适当的变更,如晋武帝三策,策问却诜,旨意在治国之道是尚礼乐还是重刑罚,及如何“建不刊之统,移风移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兹?”策问阮种,旨意则在陈述“王道之本”,策问华谭,一策边事,谋求弭息边患之术;二策治理内乱,索求“绥静新附,何以为先”,三策武备,以破轻敌之想;四策法令,理顺无为与律令之关系;五策求贤,弄清“未获出群卓越之论”的原委。策试的内容如此林林总总,然仍未超出“三道”之樊篱。王融、任昉之作,因顺的也是这个传统。其永明九年策五首,一策治国之“三道”,这是对文帝策的直接沿用;二策兴农之术,三策狱事,四策财贷,五策天文阴阳,均是对“国体”之道的细化。其中策狱事,与晋武帝策法令有着某些联系;策天文阴阳,又与汉武帝策董仲舒有着某些相似。其永明十一年策五首,一策布政,意在谋求安民之术;二策简政,旨在索取整治游堕之方;三策吏治,意在得网络人才之道;四策文治教化,欲辩王道治理之得失;五策边事,以识武备与辞辨之是非。这五策之旨意仍然未超出国体、人事之左右。又与汉代以来各朝策诏文有某些相似之处。其天监三年策三首,一策赋敛,欲从“三道”之理;二策求贤,欲开弘将之路;三策直言纳谏,欲扬弘长之道,依循“三道”之迹尤为显著。
历来文家提倡为文须立“主脑”,称“意者,帅也。”从上所析,可以看出意也是策诏文制作的灵魂和核心,是它的主要艺术特色所在。策诏之作,只要以意为主,它就能将制作者心中之块垒,古今治国之事理统于一端,熔于一炉,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否则,也会成为一盘散沙,不知所云。王融、任昉之作之所以被《文选》所收录,就因为它们立意明确,得治国之要道。这虽是因袭前人,无甚新创,但它们的出现,为我们了解齐梁时期策诏文的制作情况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具有美的欣赏价值,是策诏文苑中迟开的三朵鲜艳之花。
二是审美上给人以智慧之启迪与愉悦。一首杰出的策诏文实际就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能给人以审美的情趣和愉悦。然而,要达到这一步,关键在于策诏者是否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目光,囊括四海、气吞宇内的浩大气魄和深谙经籍、渊博精通的学问;在于策诏文是否具有深广的信息含量和启人智慧、开人疑窦的问题设计,而这些则又是由策诏贤良的主旨所决定的。从上述的策诏文中,可以发现它们都具备了这两个要素。这些文章在行文上有一套陈陈相因的程序和模式,即开端引述相关的史实,继而转向联系现实,阐述二者相通点,然后再提出问题和要求以收束全文。这种三段式之建构,便将制作者对经史的了解,典故之掌握,学问渊博之程度,以及对国家政况存在弊端之分析和对治国方略谋求全都囊括进去了。篇幅虽小而含量很大,再加上制作者行文的变化,令人读后并不感到陈陈相因,生硬呆板。因此,这是制作者高度智慧的结晶。王融、任昉的这三篇文章,无不具备了这些特征,试看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其二:
又问:昔周宣惰千亩之礼,虢公纳谏;汉文缺三推之义,贾生置言。良以食为民天,农为政本。金汤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无迁。朕式照前经,宝兹稼穑。祥正而青旗肃事,土膏而朱纮戒典。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甽泠风,述遵无废。而释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贫擅富,浸以为俗。若爰井开制,惧惊扰愚民,舄卤可腴,恐时无史白。兴废之术,矢陈厥谋。
全文134个字,囊括了多少内容!从典故方面来说,几乎是一句一典,字字有来历。从引用的经史子集来说,据李善注,有《国语》、《礼记》、《汉书》、《尚书》、《泛胜之书》、《范子计然》、《吕氏春秋》、《盐铁论》、《风俗通》、《周礼》、《史记》等十余种。从涉及的国事政要之弊端来说,有“释耒佩牛”的堕农问题,有“兼贫擅富”的差异问题,有“爰井开制”的耕作制度的变更问题,有“舄卤可腴”的土地改良问题。这些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纷繁沓来,奔辏荟萃,交织互鉴,将要策试的重点,需要解答的问题,通过优美的语言,便如花似锦地呈现在秀才们的面前,令他们去思考,去回答。这与其说是皇帝对秀才的策试,毋宁说是秀才同秀才的学问智力的较量,这种较量的最终美感就是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愉悦。
三是语言上给人以匀称、整齐、流宕之感。西汉时的策诏文,语言多用散体,如前引汉文帝的策诏文,其语言就是长短句错落参用,自然流畅;亦间或骈句俪语者,如汉武帝的《元光五年策贤良制》就基本上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试看第一部分: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番,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鱼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无郊止,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作者一开笔就连下了12个三字句,接着用了3个五字句稍作改变后,又连用8个四字句加以承接,致使这段文字一气贯注,音节短促而琅琅上口,偶句迭出而整齐流宕。范文澜曾经说“魏晋以前篇章,骈句俪语,辐辏不绝者此也”(《文心雕龙·丽辞》注),于斯观之,所言极是。魏晋时期,语言更趋向骈丽化,“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7],几成魏晋群才一大嗜好。作为此时期的一种文体,策诏和对策二文的制作亦染上此风。如陆机的《策问秀才纪瞻》六首其二:
庶民亮采,故时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用。故《书》称明良之歌,《易》贵金兰之美。此长世所以废兴,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千载恒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
全文从头至尾,皆由偶句组成,显得匀称、工整,是首典型的骈丽之作。齐梁之世,仍然是骈体文兴盛发展的时期,故王融、任昉的三篇策文,也是用骈文俪句写成的,如任昉的策文其一:
问秀才:朕长驱樊邓,直指商郊,因籍时来,乘此历运,当扆永念,犹怀惭德,何者?百王之弊,齐季斯甚,衣冠礼乐,扫地无余。■(原文不清)雕刓方,经纶草昧。采三王之礼,冠履粗分;因六代之乐,宫判始辨。而百度草创,仓廪未实。若终亩不税,则国用靡资;百姓不足,则恻隐深虑。每时入刍槁,岁课田租,愀然疚怀,如怜赤子。今欲使朕无满堂之念,民有家给之饶,渐登九年之畜,稍去关市之赋。子大夫当此三道,利用宾王,斯理何从?伫闻良说。
文中除了一些关联词外,凡34句,其句式分配,前十二句均为四字句,中二句用上五下四字句,又中二句用四字句,又中二句用上四下五字句,又中四句用四字句,又中四句改为六字句,末四句用四字句。这种句式安排,给人于匀称之中以长短错落之美,于整齐之列以跌宕变化之感。其对偶形式,无论短句,长句,均两两相对,字无雷同,句无错杂,大都对得工稳妥贴;同时,作者用正好典故,这些典故一经编织成对句,便于腐朽之中顿生神奇之美,于陌生之中给人以亲切之感。总之,这种对句的大量使用,给这类庄重的文体带来了某些勃勃生机,着上了一层“文”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