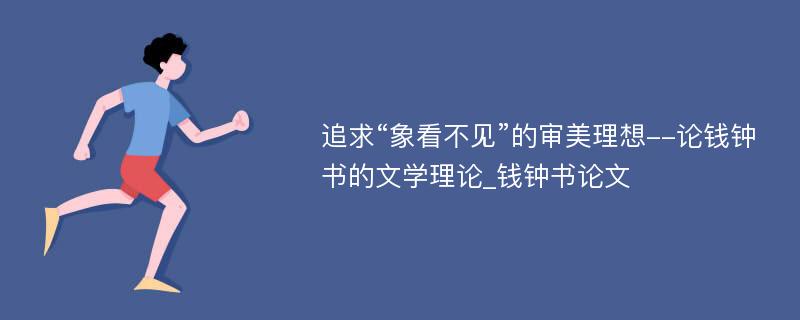
追寻“大象无形”的美学理想——关于钱钟书的文学理论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美学论文,大象论文,理想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642X(2000)01—0041—07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有一种“大象无形”的观念,表达了一种超越形迹的美学理想。从整个中西文艺理论发展过程来看,交流作为一种空间的扩展,并不是在扩大中西文化的距离和界限,而是在化解和消融其所造成的隔阂和距离,使理论创造进入一种“大方无隅”的境界,即文学思考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分,无古今之分的世界,这时,不仅中西文艺美学理论的分别变得模糊了,而且其地域文化属性也不再显得明显和突出了;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创造又都熔铸了多种文化的意识成果,表现为一种人类性的思想发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西文艺交流中,无形迹的现象更引人入胜,因为它隐藏着更多和更深的秘密,包括文化的和个人的。就20世纪来说,一种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和视野的拥有和建立是最基本、最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理论工程。这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一个超越本身传统思想观念的、更为广泛的理论价值体系的确立,人们不再仅仅从本民族和本地域文化传统出发去理解文学的意义,而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理想中寻求沟通和理解。在这方面,钱钟书的学术活动无疑体现了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方式。
一、从感通到通感
在钱钟书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中,通感是一个最为人所知的观念。尽管钱钟书在论述它的时候,主要所涉及的是文学创作和欣赏现象,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但是仅仅局限于此来理解其意义是不够的。实际上,通感也是打开钱钟书整个文学理论世界的一把钥匙,它表现了研究和理解各种不同类型文学的一条思路和方式,即用细读和文本比较的途径捕捉和理解不同情景中人类共通的艺术感觉。可以说,这是融汇了古今中外许多文学理念,特别是文艺心理批评学派和新批评学派观念的一种方法,特点是把感受批评与文本分析研究紧密结合,化为一体,寻求一种理解和贯通艺术创作的“理论之眼”。
要把握通感的理论含义也许得从“感通”入手。感通在西方文学和心理学中一直受到重视,很多理论家都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柏克莱在《视觉新论》就注意到人的各种感官在生理上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所以在感觉上是可以互相沟通的。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借光和色的媒介,别的与此十分差异的观念也可以暗示在心中。不过听觉也一样具有此种间接的作用,因为听觉不但可以知其固有的声音,而且可以借贷它们为媒介,不但把空间、形相和运动等观念提示在心中,还可以把任何借文学表示出来的观念提示于心中。”显然,这里的“暗示”就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感通现象。柏克莱认为它是在人的感觉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是由人们习惯地观察到两种或两种以上观念一块出现的恒常现象所决定的。休谟(David Hume,1711—1776,钱钟书很熟悉这位西方哲学家,特别关注过他的感象论(注:参见《休谟的哲学》,原载《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0期,1932年11月5日。 ))对此似乎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我们如果考察物体的各种作用和原因之产生结果,那我们就会看到,各种特殊的物象是恒常地会合在一起的,而且人们借习惯性的转移,会在此一物象出现后,相信有另一物象。”(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83页。)这也就是说,人们在感知世界事物的过程中,各个感官之间是互相联系的,一方面能够以综合感觉的形式获得对事物的总体观念;另一方面在认识事物过程中,个别的感觉是在感官的相互联系中获得它的实在意义的。所以,某一性质的感觉可以同其他性质的感觉构成某种或同一,或相似,或补充,甚至替代的关系。一个人在认识客观事物过程中,愈能沟通各个感官领域之间的关系,感觉就会愈丰富,判断就会愈灵敏。不过,对于柏克莱或者休谟来说,这种“暗示”或者“习惯性转移”最终只能被理解为一种观念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观念是最后唯一具有综合感觉能力的心理形式。尽管人的感觉可以排列组合成无限的结构形式,不断扩大它们的感知范围和深度,但是如果没有观念的综合,它们就不可能形成对事物相互关系的把握,在人的感觉领域内构成对事物的整体反映。
对于人类感觉可以感通这一特点的认识,自然影响到了对艺术的认识,因为文学艺术最终是离不开感官和形象的,艺术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其感性力量,这正如李斯特论肖邦时所说:“艺术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咒语;艺术家想把感觉和热情变成可感,可视,可听,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触的东西,他想传达这些感觉的内在的全部活动,而艺术的各种各样的公式正是供在自己的魔圈中唤起这些感觉和热情用的。”(注:见《李斯特论肖邦》,第2页。 )对于这种艺术魅力的理解和追求,无疑也促进了对人的艺术感通能力的认知和开发。一些西方艺术理论家开始从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去探讨各种不同感觉形式的贯通性,并以此说明由此一美感引起彼一美感的艺术效果。美国音乐理论家G·黑顿曾指出:“听感觉具有某种触觉的性质”, “内耳的器官和外侧性感官以及皮肤感官,从种系发展来说可能都是‘触觉结构的某种最普遍的形式发展而来’。”(注:G —黑顿:《生理学与心理学与音乐的关系》,见《音乐译丛》第四集,第229页。 )奥地利的汉斯立克还提出一种音乐审美中的“替代”观点,指出:“通过乐音的高低,强弱,速度和节奏化,我们听觉中产生了一音型,这个音型与某一视觉印象有着一定的类似性,它是在不同的种类的感觉间可能达到的。正如生理学上在一定的限度内有感官之间的‘替代’(Vikaricrcon ),审美学上也有感官印象之间的某种‘替代’。”(注: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第28—29页。)而莱辛在《拉奥孔》中曾举霍加兹的绘画《愤怒的音乐家》为例来说明,一个画家是怎样用诉诸视觉的符号来描绘听觉和其它感觉的对象的。
当然,倡导“直觉即表现”美学观念的克罗齐也意识到了艺术中的感通现象,他在谈到绘画中形象的整体审美效果时说:“又有一种怪论,以为图画只能产生视觉印象。腮上的晕,少年人体肤的温暖,利刃的锋,果子的新鲜香甜,这些不也是可以从图画中得到的印象吗?假如一个人没有听触香味诸感觉,只有视觉器官,图画对于他的意义如何呢?我们所看到的而且相信只用眼睛看得那幅画,在他的眼光中,就不过像画家的涂过颜料的调色板了。”(注:见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第7页。)绘画是如此,其它各门艺术何尝不如此呢? 哪一种艺术形象不是艺术家用全部身心去感受和体验的结果呢?因为艺术形象和艺术画面要获得自己完整的生命力,达到闻之有声,视之有像,触之有物,呼之欲出的效果,就必须有艺术家全部生命的投入,能够激发欣赏者的所有感情和感觉,才能实现。而文艺美学理论的最终价值就是探索,理解,发现,揭示和传达这种艺术的奥秘。随着人们对于人的心理活动的深入而更为全面的认知,也愈来愈注意到了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感通现象。应该说,在审美活动中,无论是外在的直观形式和内在心灵的艺术表现,都离不开人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反应的沟通及综合现象,艺术审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人的生命能够全部投入的,能够从某个方面透彻的意识到自己的、高级的综合行为过程。如雪花飘落,骏马奔驰,红日东升,小鸟歌唱等等,这些现象可以用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各种不同的艺术方式表现,并诉诸于人们不同的感官世界,但是都可能把人们引导到一种充满艺术活力的艺术境界中去——尽管它们各自有自己独特的展现和回味方式。这时,艺术给与人们的绝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的视觉或听觉形象——尽管它们有可能是用某一种媒介直接诉诸于人们感官的,但是其目的却是调动人的整体生命状态,给与人们一种动人的完整的艺术感觉。我们还可以说,所谓人的艺术活力和能力,就在于是否能够通过运用或欣赏某种艺术媒介,最大限度的沟通和综合自己生命的各种感觉,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状态和境界。所以,人们的艺术感通能力发挥得愈充分,艺术活动所呈现的生命感就愈广阔,愈鲜明,愈具风采。
二、“以海测蠡”的秘密
钱钟书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理论家对感通现象的关注及其论述,并把它应用到了文艺批评领域。《中国画和中国诗》就是一篇以新的理论视角重新评估诗与画的艺术价值的论文。从心理美学上说,它所涉及的就是不同媒介和感官互相沟通的程度及其差异问题。钱钟书之所以对此感兴趣,正如文中所指出的:“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上的异同,是美学上重要理论问题。”[1]因此, 这篇论文虽然题名为“中国画和中国诗”,但是却是从中西文论的广泛对比中寻求解释的;他所具体关注的是诗与画的关系,而潜在的意味还包含着沟通中西方文论以及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努力。他在文中所谈到的圣佩韦(Sainte—Beuve )、克罗齐(Croce)、柏格森、休谟、达芬奇、鲁本斯、 康德等西方人士的观念,都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点产生了某种沟通和对比效果。也许为进一步加深对文艺中感通现象的理解,钱钟书还专门写了《读“拉奥孔”》一文,把诗与画,也是视觉与听觉之间的审美关系,引申到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关系中去探讨。显然,这里的“读”是一种比较的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读,才能“读”出一番新的意义来。由于中国诗论、画论的对比,莱辛所讲的“诗歌的画”和“物质的画”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时空的限制上,更由于人的各种不同感情感觉的参与而显得格外突出。这时,通感问题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它作为一种诗歌无与伦比的“画不就”的品质而受到钱钟书的偏爱。因为语言文字不但能写出有形的、可捉摸的物体,而且能表现出“笼罩的,气氛性的景色”,“寥阔,流动,复杂和伴随着香味、声音”的景物;能够“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彩色碟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刻划的形状可能使造型艺术家感到凿刀和画笔力竭技穷。”[1]
由此说来,《通感》是钱钟书对中西文论中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多少有点偶尔得之的味道。所谓偶尔得之,一方面是钱钟书在探讨大问题——不同艺术领域的异同的时候,对小问题——关于语言文字艺术的表现力——有了新的发现和感触;另一方面则是从对于小问题——通感效应作为诗歌表现艺术的特殊优势的比较分析中获得了大发现,认为这不仅是中国诗文中“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的一种描写手法,而且也是中西文论中相当薄弱,但是又有非常价值的一个话题。就后者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以天窥管,以海测蠡”的过程,关键在于钱钟书拥有一个中西学问的广阔天空和古今文学的汪洋大海,所以能够赋予“通感”特殊的理论价值。在对通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钱钟书一方面很熟悉西方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对于这一心理现象的论述;另一方面很清楚在这方面理论上的薄弱和匮乏。
正如我们上面已说过的,对于通感这一人类心理和艺术形象,从亚里斯多德到克罗齐,都曾有过论述,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而到了近代,有更多的理论家和艺术家对此类的现象感兴趣。除了克罗齐对直觉及其综合心灵的论说之外,波德莱尔(钱钟书经常在文论中提到他)及其象征派的诗歌理论也曾引起过人们对于通感的注意。例如,朱光潜在《诗论》中就指出过:“有又一派诗人, 像英国的史文朋(Swinburne)与法国的象征派,想把声音抬到主要地位,魏尔伦(Verlaine)在一首论诗的诗里大声疾呼‘音乐啊,高于一切!’一部分象征诗人有‘着色的听觉’(Colour—hearing)一种心理变态,听到声音, 就见到颜色。他们根据这种现象发挥为‘感通说’(correspondance),(参看波德莱尔用这个词为题的十四行诗),以为自然界现象如声色嗅味触觉等所接触的在表面上虽似各不相谋,其实是遥相呼应,可相感通的,是互相象征的。”[2]但是很显然, 波德莱尔的感通说在理论上并没有深入的探讨,甚至没有超出克罗齐的感性直觉范畴。因此我们宁愿把它称之为艺术创作中的感通现象,而并不是通感的理论发现。
事实上,朱光潜对通感的评价似乎与燕卜荪有点类似,后者曾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谈到:
在这类情况下,用一种感觉去进行领悟,却是根据另一种感觉进行描绘,或者在与另一种感觉的比较中得到描绘的。人们称之为通感,有时候他无疑是有效的。他把读者引向混沌不清的感觉状态,而这种状态为所有这类感觉所共有;它也许还会将读者引回幼儿时候分不清各种感觉的混沌状态,引起一种初步的感觉紊乱,有些类似如头晕,癫痫或麦斯卡尔一类药物造成的感觉。服用麦斯卡尔的人有“纯诗歌”的读者所共有的感受,自己看到了非常悦目但又从未见过的崭新色彩,正是了解非常重要而又有趣的某种东西。不过他们就是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不过这种失调对读诗的人究意有多重要,却很难说清楚,我们也难确定它什么时候产生。它常常只是肯定第一类朦胧的手段。[3]
可以看出,也许由于一种潜在的理性的偏见,燕卜荪尽管突破了克罗齐的审美直觉说,把通感引入了修辞领域,但是并没有从审美感觉和艺术欣赏方面真正接受和理解通感的艺术价值。在这里,通感似乎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现象,全然没有了钱钟书所传达的那种艺术魔力。朱光潜虽然比燕卜荪(也许出之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熏陶和欣赏习惯)更能接受甚至欣赏波德莱尔的这种艺术感通意识,但是还是把它列入“变态”的范围。
真正从理论上发现通感的艺术意味的是钱钟书。我们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钱钟书从中西文论两方面看到了在这方面的理论缺失,是自觉的把通感引入到了文艺美学领域。对此他在论文开始不久就指出:“通感很早在西洋诗文里出现。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论》里虽提到通感,而它的《修辞学》里却只字不谈。”[1 ]这说明钱钟书是有意识把通感从内在感觉领域导引而出,赋予其艺术传达和修辞学的意义。这似乎有转向燕卜荪或新批评派的嫌疑,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燕卜荪并没有真正接受和理解通感的艺术意义,过于倾向于理性和分析的思维方式使他不能够同时把艺术表现中的心理色彩和修辞方式融为一体。因此,修辞成了一把理性的利刃,割舍了艺术创作中某种不确定的感性色彩。就此而言,钱钟书不仅走出了克罗齐拘泥于“执心弃物”的误区,使通感能“得手应心”,得以艺术传达和表现的阐释和理解(注:关于钱钟书对克罗齐的态度,可参见郑朝宗所编《〈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何开四《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中有“对克罗齐唯心主义美学观的批评”一节可供参考。);同时又从艺术创作的实例出发,肯定了通感作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艺术表达和表现方法的心理意义,因此避免了燕卜荪的偏颇。
三、从比较到契合
从钱钟书与燕卜荪的比较可以看出,燕卜荪尽管在思路上对西方传统思维方法有所超越,开始关注文学中不确定的因素和状态,但是到了对具体问题和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上仍然非常注意所谓的普遍性和理性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新批评派”在理论上的形式主义价值取向。特别是与中国的钱钟书相比对,燕卜荪的理论思路和论述方法仍然是不可救药的推理性的、逻辑化的,而没有钱钟书那种感性的,品味性的色彩。具体来说,燕卜荪在评价通感现象的时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尺度,但是潜在的仍然拥有某种理论观念的限定,随时可能把某种不合标准的现象排除在外;而钱钟书则更多的是从一种欣赏的角度切入,首先从作品中获得美感,甚至沉醉于具体作品的艺术感受之中,然后从中领悟到某种理性的理趣。对于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中文学状态的区别,钱钟书自己或许有最贴切的感触,他曾说道:“这种现象并不稀罕。习惯于一种文艺传统或风气里的人看另一种传统或风气里的作品,常常笼统概括,有如中国古代隽语所谓‘用个带草(怀素)看法,一览而尽’(见董说《西游记》)。比如在法国文评家眼里,德国文学作品都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古典主义也是浪漫的,非古典的(unclassical );而在德国文评家眼里,法国的文学作品都只能算古典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至多是打了对折的浪漫(only half romatic)。德, 法比邻,又同属于西欧文化大家庭。尚且如此,中国和西洋更不用说了。”[1]
当然,这种区别并不能阻止在文学领域里通感现象的发生,除非研究者过于拘泥于概念和名词,而不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甚至是描写中寻求沟通的感觉。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钱钟书的文学比较往往是从文本的细节开始的,其结论也是从具体的文学鉴赏和批评中生发的。其实,所谓通感理论的发现和延展也是从古今中外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生发出来的。在《管锥编》中,钱钟书从《列子》皇帝“神游”谈起,涉及到老子、庄子、佛家典籍、《朱子语类》、《新唐书》等多家学说中的看法,勾勒出了通感理念的由来和潜在意义,然后指出了它和西方象征派文学家波德莱尔(Baudelaire)有创作上的某种沟通:“西方神秘宗亦言‘契合’(Correspontia ), 所谓‘神变妙易, 六根融一’(O metamorphose mystique/De tous mes sens fondus en un!)。 然寻常官感,时复‘互用’,心理学名曰‘通感’(Synaesthesia);证之诗人赋咏,不乏其例,入场说《山夜闻鼓》:‘听之如可见,寻之定无象。’盖无待乎神之合无,定之生慧。”[4]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同一个词语Correspontia的两种译法——通感和契合。也许这两种译法各有所侧重,通感和契合——就波德来尔诗中的意义来说原本就有相通之处:神秘的感通是达到与万事万物契合的最理想状态,而契合则是一种消除一切隔阂的艺术状态的实现,这原本是一个共同的艺术过程。然而,对钱钟书来说,通感和契合的这种相通之处不仅在于一种感性的创作心理状态,而且是一种文艺美学的理论境界。他曾如此说道:
一家学术开宗明义之前,每有暗与其理合,隐导其说先者,特散钱未串,引弓不满,乏条贯统纪耳。群言岐出,彼此是非,各挟争心而执己见,然亦每有事理同,思路通,所见遂复不期而同者,又未必出于蹈迹承响也。若疑似而不可遽必,毋宁观其会通,识章水之交贡水,不迳为之谱牒,强瓜皮以搭李皮。故学说有相契合而非相授受者,如老,庄之于释氏是已;有扬言相攻而隐相师承者,如王浮以后道家伪经之于佛典是已。[4]
可见,钱钟书是有意识追求一种契合的理论境界的。但是,何以能达到一种契合的境界,却是钱钟书一直在探讨的。其实,就一种理论体系而然,钱钟书并未有“一家学术开宗明义”的打算,但是很看重“观其会通”的效果。所以,他不但很欣赏庄子“齐物论”中的思想,也迷恋过中国特有的“拟人化”批评方法。1937年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专门提出了“人化文评”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作我们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有《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骨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钟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哪里举得尽呢?我们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换作“texture”, 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在意义上, 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的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 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批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5]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在这里所谈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特点,但是仍然不断引用西方有关论述作为对比,以说明西方并非没有人化批评,只是在“规模”上没有如此突出,并指出:“西洋谈艺者稍有人化的趋势,只是没有推演精密,发达完备。”[5 ]“而且在说明人化批评的意义和根据时,依据的又正是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观念, “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 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力为taste, 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他还认为:“人化批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于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似乎人化批评又和西方的“移情”观念合而为一了。有人认为,后来钱钟书自己放弃了“人化批评”的提法,只是仍然坚持了“近取诸身”的意见,其实并不确切。(注:可见陈子谦先生“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辩证法探要”一文。《〈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郑朝宗编。)与其说钱钟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如说他更侧重于发现中外古今文论中的契合之处,而不是强调中国文论的固有特点。因此,有关“固有特点”的文章,钱钟书也没有再做下去。(注:钱钟书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评还有其它特点,本篇只讲人化”,但是后来没有再刻意写此类文章。就这篇文章的写作,当时也是为了满足别人的要求而进行的。)
我们的这种看法可以从钱钟书后来的文学论说中得到证明。《谈中国诗》(1945年12月6日)就是一篇重要文章, 其中所谈的侧重点就是“中国文学跟英美人好像有上天注定的姻缘”,“中国诗不但内容常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他还指出:
所以,(给)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它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注:原载《大公报》综合第19,20期,1945年12月26,27日,是在上海美军俱乐部的讲稿节译。)
可以说,钱钟书在这里所关注的“姻缘”或者“暗合”,就是中外文学的契合之处,但是要想得到它就须有一种比较的眼光,因为:“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其像外,得于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
所以,几乎和朱光潜一样,钱钟书也对王国维“隔”与“不隔”的说法很感兴趣,很早就写了《论不隔》(1934年7月)一文, 就一个偶然的发现——由安诺德(Arnold)挪用柯尔津治的诗为翻译标准而联想到王国维的“不隔”——而感到如此欢欣鼓舞:“多么碰巧,这东西两位批评家的不约而同!”而这种兴奋又正是与这种理论发现连在一起的:“这样‘不隔’说不是一个零碎、孤独的理论了,我们把它和伟大的美学绪论组织在一起,为它衬上了背景,把它放进了系统,使它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而我们认为,钱钟书当时对于“不隔”的理解就已传达了他对理论的某种思考:“‘不隔’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是一种状态(state), 一种透明洞彻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的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作者的艺术的高下,全看他有无本领来拨云雾而见晴天,造就这个状态。”[1]还有一种说法是钱钟书1988年9月写到的:“我的和诗有一联‘中州无处皆同壤,旧命维新岂陋邦’;我采用了家铉翁《中州集序》和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诗的词意,像说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可以贯通与中国旧诗的研究。”[1]
所谓“透明洞澈”的“无遮隐”,所谓“贯通”,都与一种契合的理论追求相连。这和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言“造化之谜,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是相通的。李洪岩在《钱钟书与陈寅恪》一文中曾称“这是一种超越中西,南北,体用等等界限的文化观”,我们很赞成,要言之,如同钱钟书先生自述,就是“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乎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之所有,沛然觉肺肝中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6]无疑, 这种契合的学术追求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著名学者王佐良1985年出版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集《论契合》(DEGREES OF AFFINITY),就把契合看作是一种文学发展的重要法则,他说:“契合表现在文学的所有方面。除了超越世纪之外,它不受任何时期的限制。对古代作家的兴趣的契合会显示在不同时代的作品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契合是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的:在两种拥有完全不同语言和传统背景的文学之间。”[7 ]至于他对于中西文学在诗歌和戏剧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现代诗在中国40年代演进情况的考察,则为中国文艺批评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收稿日期:1999—12—28
标签:钱钟书论文; 文学论文; 美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通感论文; 西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