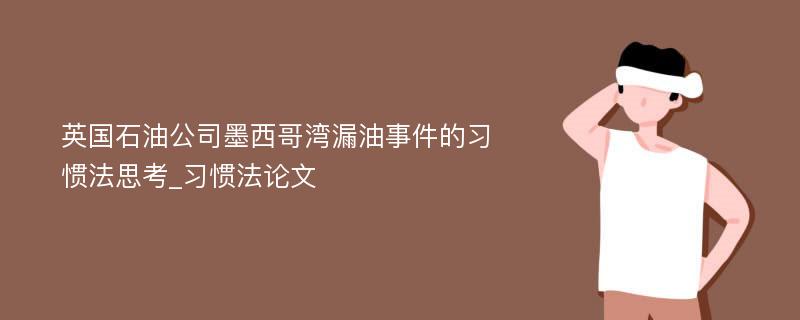
对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国际环境法思考——从习惯法的角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湾论文,习惯法论文,漏油论文,英国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发生在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漏油事件把国际社会对跨国环境保护的关注推向了高潮。如同滥捕海洋渔业资源,如同擅自在大气中进行放射性核试验一般,原油泄漏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且不可恢复的损害,这些损害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评估:(1)受害者个人遭受的生命以及其他人身损害;(2)受害者个人遭受的财产损失;(3)原油污染的清理、预防以及其他应对措施的成本。除此之外,还应当认识到,钻井平台的海上漏油事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影响范围较小的环境侵权事件,从国家关系的层面看,至少还可以从受到漏油事件影响的国家的产业损害来计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公海水体及其蕴含的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保护,不仅关系到沿岸各国的利益,同样也涉及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由此将会引起国际层面的法律问题。
联合国国际法院对环境的权威解释为:
环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代表了包括未出生的人在内的、人类的生活空间、生活质量以及健康。国家总体上负有保证在其管辖和控制的范围之内尊重他国环境或超出本国控制之外的环境的义务,这一点已经成为了与环境相关的国际法规范的一部分。①
上述定义反映了在国际法院这一全球最为权威的国际司法机构看来,跨国环境问题的分析不应当仅仅是以主权为导向的,而且还应当包括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尊重的方法论指导。②在国际法院后来审理的多瑙河大坝案件中,上述观点再次得到了重申。③因此,分析受到原油污染直接影响的国家遭受的损失以及人类共同利益遭受的损失和污染起源国之间的关系,是国际环境法深入的切入点。
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达成总额为200亿美元的赔偿安排,并协议将赔偿款项分批注入由独立第三方监管的基金账户之中,用以支付受害者的赔偿请求。美国政府强调,200亿美元的赔偿额度并不是封顶数额。这一安排似乎考虑到了在多方利益的格局中如何艰难地取得平衡的问题:一方面要尽可能让受害者取得适当的赔偿,同时尽量避免环境侵权诉讼的冗长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对环境风险的引入者和污染的制造者既苛以责任,又不至于让其今后的发展背负过于沉重的包袱。大规模的跨国环境污染案件中,对污染者在国内法的体系下追索赔偿对于受害者而言,是难度颇高的事件。历史上处理类似污染的实践表明,处理进程的缓慢使得受害者通过传统司法途径追索赔偿的努力往往陷入“迟来正义”的僵局。以1989年埃克森·瓦尔德茨号油轮在美国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发生的原油泄漏事故为例,1100万加仑的原油泄露进入大海,受害者由此向油轮的船东埃克森货运公司以及船东的母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提起了超过200起诉讼。任由环境诉讼自然发展而不加干预对于受害者的救济而言效率低下,此事直到1991年美国政府与埃克森货运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达成赔偿协议才算了结。④两相比较之下可见,行政力量在污染产生的第一时间介入,对于解决受害者追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程序繁琐冗长的缺点。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明确,跨国原油污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系,抛下污染起源国本国受害者在国内法意义上的求偿不说,外国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风险因素:(1)跨国追偿司法成本高昂;(2)本国起诉可能面临起源国主张豁免的抗辩;(3)申请本国政府给予外交保护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跨国原油污染的求偿问题,如果仅仅关注于起源国国内法层面的法律问题,通过冲突法规则的运用在追究污染者民事责任方面做文章,对外国受害者是极为不利的,必然需要从污染起源国和受到影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污染起源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关系上考虑问题,必然涉及国际环境法的具体规则的运用。
国家责任的基础
追究污染国的责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认的国家责任规则是,国家仅在存在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行为且该行为可以归因于国家的情况下承担责任。⑤但在与跨国环境污染有关的国家责任问题中,引起环境污染的行为往往是国际法并不禁止的行为。环境法中国家责任的基础在早期判例特雷尔冶炼工厂案中得到了阐述。特雷尔冶炼厂是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特雷尔的一家北美洲最大的冶炼工厂,是加拿大一家私人的冶炼厂。该厂从1896年开始冶炼锌和锡,由于提炼的矿物质含有硫黄,烟雾喷入大气中成为二氧化硫。到1930年,每天喷入大气的二氧化硫约达到600到700吨。这股气体随着上升的气流南下,越过特雷尔以南约11英里的美加边界,在美国华盛顿州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该地的庄稼、森林、牧场、牲畜、建筑物等均受到大面积的损害。该案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美国华盛顿州的环境污染是特雷尔工厂造成的,却没有证据表明加拿大自治领与特雷尔冶炼工厂之间的某种支持关系。两者之间的唯一联系是特雷尔工厂的地点在加拿大境内。对于特雷尔工厂给美国造成的损害,加拿大自治领政府是否应该承担国家责任?如果应当承担责任,其依据是什么?加拿大对损害负责的前提条件是,在国际习惯法上国家承担某种不作为义务,即国家不得允许其领土被利用从而对别国环境造成污染。对于确定这种义务,仲裁庭论述到:
根据国际法以及美国法律的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这样的利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以致让烟雾在他国领土或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造成损害,如果已产生严重后果并且那已为确凿证据证实的话。⑥
以特雷尔冶炼工厂案为发端,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中,站在更高的角度从一般性规则的层面论述到: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义务,不在明知的情况下允许其领土被用于有损他国权利行为。⑦
从起源国和受影响国之间关系的层面考虑问题,这一模型的核心因素是,国家之间主权的平等性,因为主权平等性的存在,才导致了一国承担了不得利用领土损害他国权利的义务。然而,随着对一切义务(erga omnes,或称“对事义务”)理念的兴起,环境方面的国家责任存在另一个方面的解释:因为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此,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数量有限的国家之间相互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层面,从而进入到一国针对构成国际社会之所有国家承担义务和责任的阶段。对一切义务概念的合理性已经为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公司案中确认。⑧这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个体对整体依赖加深的必然反映。
此次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的泄漏事件表明国际环境法下的责任问题的复杂性。英国石油公司开采原油,是在美国近海进行,依照美国国内法展开,但是造成了跨国性损害。海洋水体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剧了对墨西哥湾沿岸各国乃至公海水体及海底区域的污染,沿岸受到影响的国家针对美国有权主张其承担国家责任。但现实的问题是,英国石油公司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或代理人,英国石油公司开采海底石油的行为属于根据特许权协议展开的商业行为。因此,沿岸受害国追偿必然面临可归因性方面的问题,即只有依照一定的法律规则证明英国石油公司的行为在此类情况下可被视为美国政府的行为,沿岸受害国才取得了向美国政府索赔的权利。毫无疑问,国家需要对其本身及其国家机关的行为负责⑨;同时,功能主义理论的观点又为国家责任的一般原理所接受,当国家将政府公共权力委托给个人或其他实体行使,亦可视为满足了归责的必要条件⑩。从一般意义上看,国际投资法的基本规则确认,领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因此私人公司和国家之间就投资达成的特许权协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私人公司管理自然资源的公权力。尽管国际法委员会承认,此类归责仅仅涉及政府将公共权力明确授予实体的狭窄类型(11),但是国际法委员会同时也确认,什么样的授权属于政府公权力的范畴,应当根据各国不同的历史和传统来决定(12)。
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一个较为艰难的问题是,如果跨国污染是纯粹的私人主体造成,不存在任何政府的授权或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起源国是否还应当对此负责。针对要求起源国在任何情况下均承担责任的主张,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在加拿大要求美国政府对大西洋瑞奇菲尔德炼油厂造成的跨境污染承担赔偿责任一案中。(13)果真如此追究,似乎会不恰当地任意扩大起源国的责任范围。有学者指出,在跨境污染发生的前提下,起源国寻求受到影响国减轻损害的行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的决定而非纯粹基于法律考虑。(14)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责任规则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在此框架下讨论起源国是否应当就本国境内不被国际法禁止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严格的国家责任,那么政治因素决定论无疑是有道理的。但除此之外,也存在一种合理的解释:造成污染者的行为本身不被国际法禁止,当跨国损害产生之时,起源国在习惯法上承担了相应的帮助预防、排除污染的义务,这一义务并非隶属于责任规则而是属于行为规则。如此解释,起源国的责任并不在于是否要对污染者的行为负责,而在于在跨境污染产生后是否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排除之。
求偿诉讼资格和采取反措施的资格
前文已经阐明,污染起源国承担责任的基础在于两个:一方面,因为污染直接侵害了受影响国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于污染损害了环境这一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侵犯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受影响国依据第一个理由求偿乃至采取反措施,就其根本而言都是为己诉讼,国家的求偿资格自不待言;没有受到直接损害的国家基于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理由,要求污染国承担责任或对其采取反措施,是为他诉讼的问题。罗马法对后世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体制方面产生的一大影响便是群体诉讼(actio popularis)问题,即为了公共利益允许与案情无关的第三人进行公益诉讼。(15)
结合国际环境法上的责任问题考虑,国际法委员会在2001年《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中似乎为没有受到跨国污染直接损害的国家代表他国、国际社会求偿或采取反措施提供了依据。这个责任草案把国际义务分为三个类型,第一,国家对国家承担的义务;第二,国家对一定数量国家组成的集团承担的义务;第三,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违反上述三类国际义务,均会引起国家责任。国家如果违反上述第二类、第三类国际义务应该如何承担国家责任,国际法委员会在该条款草案中提出了框架性方案:
第48条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
1.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权按照第2款在下列情况下对另一国援引责任:(a)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务;或(b)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
2.有权按照第1款援引责任的任何国家可要求责任国:(a)按照第30条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和(b)按照前几条中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根据该条款草案的价值取向判断,国内法意义上的群体诉讼在跨国环境求偿方面隐约地显现出端倪。这一取向似乎可以这么理解:群体诉讼的问题与实体法层面的对一切义务问题是挂钩的——如果在反措施、诉讼等程序体制中不允许群体诉讼存在,那么即便实体法层面对一切义务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在缺乏监督实体的情况下,也等于没有对国家进行任何约束。然而,在国际权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面前,非为本国利益的诉讼一直受到否定。西南非洲案是较早的一个案例。该诉讼中起诉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主张南非在西南非洲地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有悖于其在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下承担的最大限度提高该区域居民的安宁生活的国际义务,因而需要承担国家责任。案件实体判决部分指出:
(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国的主张请求相当于这么一个诉讼:国际法院应允许“群体诉讼”(actio popularis)的存在,或者是法院应该肯定国际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权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虽然上述权利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国际法发展的现阶段来说,却是未知的事情:本法院不能认为这一权利是由法院规约第38条第一款第三项所指的“一般法律原则”。(16)
国际法院对群体诉讼制度的否定,因为其管辖权制度得到了加强。东帝汶案(葡萄牙诉印度尼西亚)中,国际法院再次否定了进行群体诉讼的可能性。该案件中,东帝汶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当时被联合国列为非自治领土。东帝汶自1975年以来就被印度尼西亚占领,并且在1976年作为印尼的第27个省并入印尼,但是这一事实从来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肯定。相反,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肯定东帝汶人民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和独立的权利,并且要求印尼最终从东帝汶领土上撤军。1989年,当时作为东帝汶托管国的葡萄牙在国际法院以澳大利亚为被告提起诉讼,称澳大利亚与印尼就开发、利用东帝汶领土所属大陆架的资源达成的协议,不仅严重侵犯了东帝汶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而且也侵犯了当时作为东帝汶托管国的葡萄牙在托管制度下的权利。国际法院在程序法层面上还是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
某一条国际法规则的对世义务的特点和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不同的两码事。不论所涉及的义务的性质如何,如果本法院的判决将会对一个非本案当事国的行为的合法性暗示某种评价,那么本法院就不能对一个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即便所涉及的问题是国家的对世权利,本法院也不能对此作出行动。(17)
在涉及跨国环境污染的案件中,核试验案件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法院的否定倾向。本案涉及法国在南太平洋上空进行空爆核试验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是否侵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权利的问题。澳新两国申请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在诉讼期间暂时禁止法国进行核试验。澳大利亚对此要求的解释是,空中核试验严重侵犯了人类的环境,而澳大利亚是这一整体环境的一部分。(18)国际法院应澳国要求指示了临时措施,但该临时措施并非根据国家对一切义务的法律基础做出,国际法院反而强调法律依据在于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主权,而非为了保护澳国的其他权利。(19)
由此可见,国内法中的群体诉讼并不能简单地在国际层面的求偿诉讼中被克隆。但非直接受害国向污染起源国主张国家责任,并非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展开。反措施作为一种遏制正在发生违法行为的自力救济的工具,得到了习惯法意义上的认可。国际法委员会将通过诉讼主张国家责任和反措施的展开进行了区分,反措施是否必须由直接受到损害的国家实施,似乎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至少国际法委员会没有任何限定,在理论上是可以探讨的问题。(20)
污染起源国的谨慎注意义务
《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第21规定:“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编纂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的条款草案案文》中则以《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第21条为蓝本,其第3条规定:“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预防重大的越境损害或随时尽量减少这种危险。”与特雷尔冶炼工厂案件中观点略有不同的是,在国际法委员会看来,国家的不作为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主要表现在国家不仅仅要对其领土内进行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而且也应该对其管辖或者控制下的其他地方进行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负有预防性义务。(21)
习惯法上国家负有不允许本国领土被利用导致他国环境损害的规则必然在逻辑上导致这么一个问题:国家对于在其境内可能造成他国环境污染的活动,应当承担谨慎注意的义务。对于谨慎注意义务自何时开始,归责似乎很模糊。但是具体到可能引起跨境环境污染的事件来看,从性质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类,突发性跨境环境污染事件,如运输化学药品车辆车祸导致跨境污染等;第二类,非突发性跨境环境污染,如前文提到的特雷尔冶炼工厂案。从法理上推测,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国家的谨慎注意从事故产生污染并为国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开始。对于非突发性的可能造成跨境污染的工程,国家应该从这类工程开始修建之时就负有谨慎注意义务。
关于谨慎注意义务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应该注意到什么程度。国际法委员会观点是:
第一,谨慎注意的程度应该和所进行的活动的危险性相称。(22)例如,运送一般化学药品和运送放射性核材料,国家应该给予的注意的程度是不同的。通常危险性越高,谨慎注意的程度也越高。第二,谨慎注意的程度应该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23)通常情况下,没有理由去要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对境内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像高度发达国家那样承担谨慎的监控义务。
对谨慎注意义务的解释,可以更为宽泛。事实上,不论对于突发性的还是非突发性的跨境污染事件,习惯法的编纂工作已经显示,起源国应当在危险活动的核准(24)、风险评估(25)、与可能受跨境污染影响的国家资料交换(26)、紧急应对灾害(27)、通知紧急情况(28)等各个方面均采取合作态度。谨慎注意的义务可以被理解为已经渗透到了起源国与可能或已经受到影响国家之间合作的各个层面。
启示和建言
美国政府应对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钻井平台漏油事件的策略,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污染起源国的责任问题、污染起源国和受影响国之间在谨慎注意基础上的合作关系问题,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跨境石油污染乃至范围更大的跨境污染损害问题,带来的法律难题是复杂的,对此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准备充分的应对策略。我国是资源大国,海洋大国。针对东海、南海的资源开发,在充分考虑国际环境法制度的基础上完善本国的应对策略,是此次美国墨西哥湾污染事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的重点在于论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法律障碍。正是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等到跨境污染事件发生之后再试图进行弥补,是下下策。站在习惯法的角度,站在代际公平的角度,站在保护全人类共同财产的角度,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我们都发现现行的国际、国内法律制度重责任承担、轻视风险控制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出于建言本国环境法律制度和应对策略的目的,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来构筑跨境污染的应对策略:
第一,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管理规范等各级法律文件应当全面重视风险控制。共同开发争议区域的资源在可见的将来极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本国的法律制度应当不分开发主体属内资还是外资,不分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一视同仁地对资源开发等有可能造成跨境污染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风险监控和管理。
第二,跨境污染事件发生后的应对策略方面:(1)针对本国为起源国的情况,法律制度应为跨国合作预留充足的接口。(2)针对别国为起源国的情况,应当更积极主动应对,一方面审慎考虑以外交保护的方式切实保证我国国民、公司的权益;另一方面应当针对起源国的不作为,保留采取与其严重程度对应的反措施的权利,并积极运用。
注释:
①The Legality of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Advisory Opinion,at para.29.
②Anotonio Cassese,International Law,2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89.
③Case Concerning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Judgment,at para.53.
④(13)(14)Xue Hanqin,Transboundary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5~26,p.78,p.79.
⑤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2001,Art.1.
⑥"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Tribunal:Decision 1941",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684.
⑦ICJ Report 1949,p.22.
⑧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Second Phase,I.C.J.Reports 1970,p.3,p.32.
⑨ILC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Art.4; 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or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ICJ Reports 1999,p.62,p.87.
⑩ILC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Art.6; Xue Hanqin,Transboundary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77.
(11)(12)ILC Commentary On Draft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Commentary on Art.6,para.7,para.5.
(15)Malcom D.Evans,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496.
(16)South West Africa Case,Second Phase,judgment,ICJ Reports 1966,p.3,p.47.
(17)East Timor Case,Judgment,ICJ Reports 1995,p.90.
(18)Request for the Indica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 of Protection Sub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ICJ Pleadings,Nuclear Test Case,Vol.1,p.42,pp.44~45.
(19)Nuclear Test Case,ICJ Reports 1973,p.98,p.105.
(20)Malcolm D.Evans,International Law,2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517~521.
(21)ILC 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Harm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adopted in 2001,Art.1.
(22)(23)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Commentaries to the 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harm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Commentary to Art.3,para.11,para.12.
(24)(25)(26)(27)(28)ILC 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Harm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adopted in 2001,Art.6,Art.7,Art.12,Art.16,Art.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