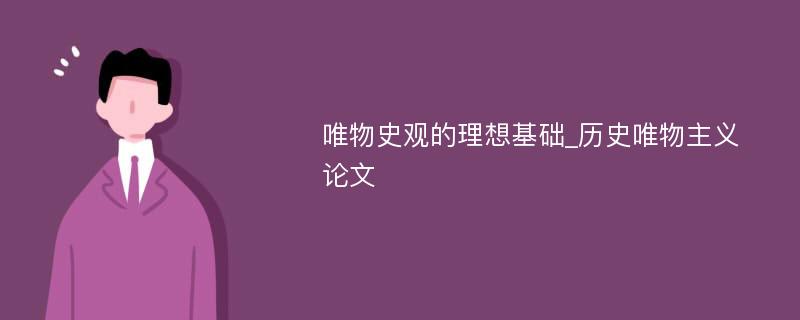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理想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尚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以至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之争论,无不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当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理想价值问题,建立与“历史科学”构成互补的“价值科学”,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解决规范性问题等①。总体说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条件的,把理想价值落实到个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上,而在社会历史层面则强调超越个人的客观必然性。个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空间中,而社会对个人的现实规定性中常常不存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人作为非自由的定在或者非本质的存在,意味着现实社会很不理想,理想被迫成为个人的事情,甚至是非现实的“主观性”的事情。作为个人与社会之统一的“社会主义”是超越个人主观性的社会理想,那么社会主义如何与历史科学统一起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此可知实际的社会理想如何在阶级社会中以分裂的方式存在着。 一、历史科学的革命性意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直觉。这一违背肇始于第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马克思不算原创。但是把这一反抗彻底化地发展为科学,以实现对现实的真实的把握则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 恩格斯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意义。阿尔都塞认为,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③。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形态》,发生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总问题转换,又叫做“认识论断裂”。《手稿》中的核心概念“类本质”、“人性”、“异化”、“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历史科学的崭新概念所代替,如社会形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类本质”观点被指认为抽象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哲学人本学也是作为“思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相对立④。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意味深长地进行了反映现实的科学话语与想像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比较与置换。 解剖市民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帮助马克思走出了哲学家的意识形态世界,发现了建立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基础上的现实社会。其中,经济基础是“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把握的部分,这是现实的基础部分,现实生活的另一部分是建筑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⑤。上层建筑部分可以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精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不能成为科学的“思辨部分”,这部分与现实经济结构相适应,并能为其所说明。科学以有限者为对象,即科学所把握的对象是规定性、限定性或者说定在。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物质性是定在的意思,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只有在成为“受动”的时候,即成为它的现实存在方式生产关系的固定规定性时,才表现出它的客观物质性。科学所能把握的人的存在是其经济活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无限即对限定的否定,即非限定、非规定与超越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现实生活既包括科学所能把握的部分,也包括意识形态部分。历史成为科学、成为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以现实的定在部分为标尺,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为出发点,这些个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⑥,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⑦,从而破除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必然性与决定性的外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归源于经济基础,正如现代哲学让无限性以有限性为基础。“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⑧。马克思把天国埋在尘世中,指认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高贵意识形态的分裂性与异化性,异化的崇高是以等级压迫与阶级对立为补充的。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历史科学的革命性意义源自资本的力量:资本消灭了等级,世俗化了基督教,瓦解了形而上学,把诗人、学者变成资本招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消灭了宗教、形而上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在不能消灭它的地方,就把意识形态变成赤裸裸的谎言⑨。 与消解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必然性与决定性相伴而行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个人的“扬弃”与消解。科学所能把握的那个经济的人,是劳动与交往相统一的人,即社会的个人,也就是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从《手稿》中的具有类本性的自由自觉的个人,如何成为“现实的个人”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人的自由本质在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中成为现实的定在,即社会关系的固定的规定性。社会关系的异化使现实的个人变成了非个人的现实,因为个人只是承载一种固定的规定性与外在的强迫性的容器,所谓社会的个人就是把个人消融在他无意造成又不能占有与驾驭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的客观性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个体意志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面前是无效的,个人的能动性被社会的必然性贬低为主观性,从而“能动”成为“受动”。人的能动性之沦为主观性是以阶级对立为条件的个人与社会的分裂造就的。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出色地论述了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消融,他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11)。历史的类自然性,是与人的物化相对应的,历史的内在一般规律是以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为材料的。 到底在社会中存在着什么神秘的炼金术使个人消融了,而且还要把这种牺牲颂扬为个体对类的贡献?个人的能动意志在社会交往(冲突)中沦为偶然的私欲,社会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客观性是个体私欲的偶在借助社会历史无意识地超越了有限意图所达到的更高的理想价值。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被斯密与黑格尔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内在奥秘,但这只“手”的“看不见性”却被马克思视为人的不幸与灾难,即阶级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的不自主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形而上学的神秘颠倒的根据在于社会关系的异化。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个人在历史中是无名的偶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认为,历史无主体,不能把历史还原为活动,如同不能从个人去解释社会。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活动与历史、个人与社会处在不同层次上,个人只有献身于与其相排斥的超人的社会存在,才有科学与唯物主义。但人们仍可追问,难道历史不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吗?社会不是人的交往活动的结果吗?说社会历史中看不到人,不是指看不到“活动成为受动”的、受苦的、忍受着固定的规定性的无个性的、“偶然的个人”,而是指看不到科学拒绝将之作为出发点的“想像的个人”。这种“想像的个人”、“理想的个人”就是有着生命的整全性与内在必然性的自主个人。 结构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界定割裂了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关于历史科学与社会主义的统一问题,我们常常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然道路。卡尔·洛维特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12)。“自由人的联合体”被认为是某种类目的性的价值预设,“人的解放”被认为是在未来某一时刻到来的正义,社会主义再次从科学变成了空想。但是,如马克思所说,“解放”不是理论预设,而是一种“历史活动”(13)。“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4)。人的解放现实地存在于生产劳动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冲突即阶级斗争中。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是抽象反思的理论结果。“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自由的类本性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是未完成的,这正与阶级社会对人的现实规定性相补充。“抽象”,从理论的观点看来,是一种非现实的构想,而从实践的观点看来,则是“未完成”的意思,即以分裂的、异化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超越理论的实践观点,可以使我们破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界定,澄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形象。 二、社会历史作为大写的人 结构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界定确立了人与社会历史的抽象对立。当然,结构主义者并不认为存在这种对立,因为个人与社会历史不处于同一层次上。个体意志在相互冲突的“历史合力”中,是作为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存在的。个人的现实性是作为社会的规定性而存在的,在社会对个人的规定性之外的部分是非现实的,不具有客观有效性的。个人的目的、意图、理想、意志之所以沦为“主观性”,是因为它没有被阶级社会对个人的现实规定性所识别。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个体理想的能动性是作为质料存在的,而社会历史的形式则在更高的层次上,人的能动性自身在利用它、规定它的更高形式中是一种盲目的存在。人的理想价值在社会现实层面被消解,说明社会现实是非个人的和不理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人的自主的联合,是对人的个性在社会层面的恢复,这个社会是人的理想的实际性(现实)。社会主义的理想在阶级社会中并不仅作为一种幽灵只在人的头脑中存在,而且以未完成的和分裂的方式现存着。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极力避免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解,是因为经济决定论不但不是社会存在的真理,而且代表一种极端的社会状况,社会现实对人的稠密规定中已经丧失任何自由空间,这是社会有机体僵化与行将解体的表现。可以看到结构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界定阉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 社会作为超人的存在,是人的不自主的现实表现。社会历史更清晰地反映了人的现存状况。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说明社会现实中的个人存在没有证得人的“类本质”。人与人有着极高的差异性,个人也是难以认识的黑箱,以至于“认识你自己”已经成为德尔斐神庙的神谕。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心”与“理”的层面上,极为不同的人又都归属于它的“类”,人们的交往形成“社会”。个体意志的冲突扬弃了个人的次要的、偶然的品质,把一个时代之为一个时代的人的“同心”、“同理”的本质保留下来、“聚集”起来,“历史合力”是人的放大镜。社会历史是作为“大写的个人”而存在的。当然,“作为社会的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存在,而阶级社会则是人的类本质的分裂存在。 “根据柏拉图的看法,人类本性就像一篇困难的文章,其意义必须靠哲学来译解。但是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中,这篇文章是用非常小的文字写成,因而很难辨认。哲学的最初的工作就是必须放大这些文字。哲学只有在已经发展了一种国家的理论时,才能给予我们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的理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在国家这里,这篇文章的隐含意义突然显现出来,原来看上去暧昧含混的现在变得清晰可辨了”(16)。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讨了人的本质,我们可以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进行对比,其间有重要的对应性。 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与欲望,分居于身体的头胸腹三个部位。理性的美德是智慧,意志的美德是勇敢,欲望的美德是节制。智慧、勇敢与节制的协调统一才能实现完满的人格——正义。完满的人格分裂地存在于国家不同等级的人中。国家的统治者对应人格的理性部分,其美德为智慧;国家的保卫者对应人格的意志部分,其美德为勇敢;国家的生产者对应人格的欲望部分,其美德为节制。唯有国家的三个等级各得其所,各适其性,各美其美,才能实现协调统一的理想国,成就国家的正义。“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17)。成就理想国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哲学王,而哲学王的统治活动就是哲学教育。哲学王不仅使自己成为智慧的朋友,还用智慧浇灌存在的另外两个层次,使国家的保卫者具足勇敢,使国家的生产者实现节制。哲学王的智慧不是观念性的理论存在,而是教化性的实践存在,必须深入、落实到不同的存在层次,点化、超升出各自的美德。理想国的正义成就了哲学王的智慧。意志听理性的话节制欲望,同样,政治也成了由上而下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由下而上层层制约的社会结构构成了“必然王国”,这个“必然王国”是颠倒的“理想国”。经济基础大约相当于理想国中的生产者,政治上层建筑相当于城邦的保卫者,而意识形态则接近于哲学王。 柏拉图的城邦虽然分为三个阶层,但要成就城邦的正义,就必须有哲学教育的智慧浇灌,各阶层的交互作用与协同运作。城邦的哲学家是从洞穴中走出,又回到洞穴的,哲学家作为智慧的朋友,对智慧的热爱必然成为对人类的热爱,爱智慧必将表现为对城邦的服务。智慧成就于城邦的正义中,城邦的正义作为完成了的智慧是完美人格的表现。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在阶级社会中分为三层结构,其中的界限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因为界限只是分裂与异化的表现,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有机体之所以为有机体,就在于各部分的交互作用与相互渗透。对于这种作用,马克思在不同地方有两种把握:或者是决定与反作用,或者是制约性与相对的独立性。还有一种作用是相关性,相关性远离实体性,最具包容性。作为阶级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现实的反映,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的把握也是知性的、实体化的、“地形学”的。三层结构的实体化甚至是相斥性是反生命有机体的,这与阶级社会的自我分裂及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相对应。阶级社会的现实中暗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人们的“灵魂”中还保持着对完满性的“回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人与人的交往不再受自然的、自发的外部力量的支配,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自愿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体中,社会的同时成为个人的,被安排、被规定的转化为个人自主的,每个人中包含着一切人、包含着社会。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自由自觉的联合,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作为“至心若镜”与其他一切人交融互摄、相互包含。因此,社会有机体的三层圆融、平等无碍地存在于每一个自由人中,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扬弃了它们的分裂的、对立的形式,“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20)。在人的自由个性中,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显现出它们的本来面貌。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形象 “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形象中的重新阐释,就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这些对立面包括:物质与精神、能动与受动、外在与内在、偶然性与个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必然与自由等。 探讨“物质生产力”概念之前,重新清理“物质”概念是必要的。尽管马克思除了埋怨霍布斯等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物质”已经丧失了唯物主义的始祖培根的“物质”概念中的生命力与诗意光辉外,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物质”概念,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以其他方式更深刻地使用着“物质”概念。“物质”被剥夺了内在生命与诗意光辉,变成能被数学严格规定的广延,是霍布斯的伟大创造。“物质”违背了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的感性直观,同样可能让霍布斯感到不舒服,但“物质”不正是个人生命的现存状况吗?当马克思说,“物质生活”应当同“自主生活”一致起来时,他正是用非自主的、无生命的抽象规定来指认“物质”的。何为“物质”?两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最清楚:贝克莱说,“物是观念的集合”;黑格尔说,“物质”是一个最抽象的概念。“物质”是存在的现实规定,因为在资本的逻辑中,物与人的个性生命早就丧失了。概观“物质”的概念史,唯物主义者是在大体一致的倾向中使用“物质”概念的。“物质”是具有或承载各种规定性的基质、质料,基质的无限定性只是各种固定的规定性的集合的补充,也可以说,这种无限定性是用来固化、聚集各种规定性的。“物质”意味着固定的规定性与外在的强迫性。机械必然性正是撞击、推动所造成的外在必然性,当然这种外在必然性对于那个作为自由精灵的“偏斜原子”而言,又叫外在的强迫性、被规定性。能被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规定的“物质”,处于“精神”的对面,除了是这些规定性之外,“物质”不再是什么,大约类同于与理性相对的“知性”概念。“物质”理解不了“生命”,除非“物质”与“精神”抽象对立的现实被消灭。人与自然在资本的逻辑中成为数学的对象。如果不是把“物质”作为决定性的本原,而是当作抽象的现存状况的概括,“物质”是一个有用的、深刻的概念。当我们在日常话语中指责某人很“物质”的时候,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指,他丧失了作为内在必然性的个性生命,不能包容、涵摄其他的可能性,失去了自主性、否定性、超越性等“精神”特质与形上本性。 就此看来,生产力的客观“物质”性其实就是生产关系的意思。生产力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共同活动的方式,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存在方式。我们一般认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这种改造是由人们结成一定的关系才是可能的,但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关系不是平等的,不是自愿、自觉的自由联合,而是一种自然、自发形成的超人(或曰外在、异化)力量。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处于一定的地位,这个地位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从前代继承的,也可以是沦落的或自力挣得的。这种关系或地位常常失去其他的可能性,变成固定的规定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活动一般丧失了自主活动的特点,成为强制性与必要性的活动。整个活动如果变成了外部规定性的纯粹加减,就失去了作为内在必然性与整体性的个性生命,成为毫无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物化”活动。使用工具的人变成了工具的延伸,“活动变成受动”,生产力从能动的本质力量变成客观物质力量,成为“物质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的客观性,正是作为历史活动之结果的给定性、条件限制性或现实规定性,而非来自自然的物质性。“物质”作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不是自然的独立性或中立性,而是现实社会对人的固定的规定性与外部强迫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人的活动无意造成的他不能支配的力量。自然的“物质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当代社会压迫人的并不是自然的物质性,而是造成了自然的物质性并不断利用自然的物质性实现自身增殖的资本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揭示在“物与物的关系”下隐藏的“人与人的关系”。 生产力的“物质性”是由生产力的存在方式,即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构成的。社会生产力是个人活动的大写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21)。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或共同活动方式)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其实是指,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交往形式与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旧交往形式之间的冲突,而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旧交往形式的集中表现则是政治上层建筑,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交往方式对旧交往方式的反抗必然具有政治的性质。 已成为桎梏的僵化的交往方式是作为新交往方式的背景存在的,“偶然的个人”与“有个性的个人”共在于分裂的社会活动中。社会形态的转换,打破桎梏的政治革命总具有一定的社会解放的性质。进行革命的阶级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而出现的(22),其思想的普遍性还不完全是抽象的。新生的社会有机体破壳而出,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人们作为主人翁发挥出历史首创精神,一切存在者被带到历史的开端处,完成了一次关于存在的本质的“灵魂的回忆”,政治解放可视为人类解放的摹本。社会新生命尚未僵化为三层结构,社会关系对生产的规定与普遍的理想价值对生活的范导(引领、超升)还交融在一起。可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被社会现实的稠密规定所封闭,具有向上的开放性,从而构成了意识形态起作用的空间。新的交往形式与活动的个人的现实局限与片面存在相适应,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23)。生产力除了具有一种物的形式之外,还表现为与个人结合的个人所有的力量。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过程成为生产者的生命表现,生产的生命活动把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从外部给予的经验材料转化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存在。自主活动具有一种“似乎先验”的结构,把外部材料生产为内在自我的生命。自主活动的人还保留着关于本质的某种记忆,对劳动者而言,自主性是他的活动中的现实内容。 与现实局限和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自主活动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而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中,社会有机体已经僵化,紧张的阶级对立中不再存在共同的理想空间,统治阶级的思想丧失了革命时期(上升时期)的“具体的普遍性”,生产活动被剥夺了想像力起作用的能动空间,从而失去了活动者的现实内容(除了谋生的手段),在必要性与强迫性之下成为“受动”的活动。存在与本质相分离,劳动成为生产者的非现实。生产力成为一种与个人相分离的物的形式,生产者受制于固定的规定性与外部的强迫性,成为生产资料的资料,生产的先验结构变成了结构的经验制造,劳动中的物不再具有生命的意味,而生命则具有了物的形式。中世纪的手工业者之间没什么分工,每个人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从而“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24),而现代工人则完全受物的力量所支配。 有局限性的交往形式即使作为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时,仍然是人们无意造成的外部关系。阶级关系总无法摆脱物的性质,还不是人自身的关系。在“代替那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生产力摆脱了物的形式,成为人的自由个性与本质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扬弃了物化的外部形态,成为人的自觉自愿的自由联合。意识形态失去了被分裂出去的天上王国的角色,回到了个人的创造性活动中,也深入到“物质”中,恢复了事物的个性。理想价值不再是阶级利益的幻想形态,成为每一个人的现实活动(自我实现的活动)。所有人的成为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成为所有人的,个人与社会实现了统一。在人的本质性存在(类生活)中,阶级社会分裂的三层结构,恢复了其本来面貌,统一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四、意识形态作为“想像的真实”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形象进行概观之后,我们才冒险进入对意识形态的探讨。根本说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就是意识形态。出于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现实进行真实把握的历史科学的需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对意识形态的消极使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6)。当意识形态家意识到社会的冲突与分裂,力求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其克服的时候,精神意识形态从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并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其独立性已经被压抑,沦为了消极的欺骗。当新生的社会有机体的矛盾尚处于隐蔽状态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还有着具体的现实性,我们还不能怀疑意识形态家的真诚性,此时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尚未被压抑,它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具有范导性。马克思在《形态》中主要批判了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普遍性,即给狭隘的利益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这是消极的意识形态,有时被叫做“精神鸦片”、“锁链上的花朵”。消极意识形态处于收缩状态,其独立性是被压抑和锁闭的,并被归根于现存条件下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对人与现实的关系、现存条件与现实状况的想像的把握,物质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反响”。在他们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6)。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当作意识,这种意识是对现实的“颠倒反映”或“倒立成像”,从而很容易把意识形态与现实及作为对现实的真实把握的科学区分开来。可是,一旦把意识形态想像从社会现实及历史科学中剥离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丧失了理想基础。因而有了后来的一系列补充: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订,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问题,历史决定论的困境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再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中对其追本溯源,以求克服消极意识形态与积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表观与本性的对立。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克服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虽然是对现实的想像的把握,但也作为社会分裂的三层结构之一的精神生产部门而存在,因而意识又化身为较为客观的固化形态,如概念、理念、思想、艺术、宗教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从社会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去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27)。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决定性外观是由它的相对的独立性造成的。它是对现实的想像,这种想像力在消极的意义上被称作“颠倒反映”、“倒立成像”,在积极的意义上就是能动的超越性。对意识形态的想像力的评价应当超越利益对立的世俗视角,相对的独立性说明意识形态有着不同于经济基础的现实规定的另一来源。意识形态“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8)。意识形态作为想像力是自动的而非被推动的,是能动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如同康德所说,知识始于经验,但并非源于经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意味着知识有着基于理性自身的内在构成。经验无法告诉我们,如何把经验的外部给予转化为内在自我的生命,经验无法提供的内在必然性来自哪里。所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是把材料的相关性当作了本质决定性。意识形态的生产活动当然使用它的时代的经济基础与现实的生活过程所提供的材料,或者说相关于现实状况和现存条件,但它是自身本源的。纯粹的理论、神学、艺术、哲学虽然有着民族性的风格、时代性的内容和阶级性的局限,但又有着永恒的人类性意义,从而是一种“相对的绝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艺术的独立性困惑: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9);“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0)。希腊神话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不受“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能摆脱阶级社会的现实桎梏,完成超越性的跳跃,以“灵魂的回忆”实现对永恒与绝对的模仿,从而持有对类本质的记忆。当然,现实就是马克思的“罗陀斯岛”,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新城。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共产主义不光有经济的性质而且有哲学的性质,扬弃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分裂,消灭哲学与现实的对立,使其更为深刻更为直接。 如果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或反映,“想像的真实性”必然被“对真实的想像”所取代,它的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是深刻的。之所以把意识形态当作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与反响,是因为把意识形态活动的结果(产品)当成了意识形态本身,把意识形态的表观当成了它的本性。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指认为意识、观念、概念,或者是精神生产部门中的宗教、艺术、形而上学等。如同从内容上说,思维中所有的一切无不在经验之中,意识形态生产所用的材料无不来自于现实生活过程(经济基础的现实规定)。但意识形态活动是想像力对经验的超越性构造。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石斧子与铁斧子的材料虽不同,但成就斧子的智性却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表观追溯到其本性的话,意识形态不是意识、观念、概念(这些当然不是本源性的),也不限于作为《神圣家族》的精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实的“想像的把握”、“颠倒的反映”、“倒立成像”,而是一种生产,意识形态生产着分裂的阶级社会的整全性。它是不同于能为数学的精确性所把握的现实经济基础的另一种真实。这种想像的真实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尽管我们可以被必要性与强迫性剥夺了任何意识形态生产的空间,成为物化的存在,但我们仍然被意识形态的生产性所占据,即使它没有活动、没有起作用,意识形态的生产(创造)本性是不灭的。它比自我意识更为寂静,比逻各斯更为深刻。想像的真实不是指想像创造出的产品,而是说想像是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即使不活动、未起作用,也不能被否认的真实存在。如同我被资本所迫,没有一点自由时间,或者我只是一个懒汉,你却不能否认人的能动的超越性、精神的否定本性与创造本性,也不能因为人的现实局限而不承认人性的绝对性与完满性。因为如果没有后者,你就不能确定异化与桎梏、或者我是一个懒汉的事实,也不能做出有限理性的断言。想像不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机能,而是其能动性根源,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存在层次。它可以通过人的自主活动显现,也可以不显现。想像的真实是一种与规定性的现实不同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是非规定的、无限的、否定的。想像与现实之所以是不同的,是因为二者是分裂的,或者说是未完成的。无限性与否定性的现实表现就是能动的超越性与自主的创造性。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虽然只是一种分裂与异化的表现,但我们仍可从其本性上使其超出精神上层建筑的范围,在生产力的活跃性中或者生产劳动的自主性中保持其存在。想像与现实之分裂的整体表现,是阶级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时间为代价。 五、想像与现实的否定性统一 从整体上说,或者对社会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1)。“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32)。这种整体的概观与洞见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是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生命经验不相契合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整体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领域与阶级那里以分裂的方式存在着的。“物质”与“精神”、历史的前提与结果、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在生活世界中并没有直观的存在。回归生活世界,我们只有从想像与现实的结合去探究自主活动的秘密。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3)。在个人占有生产力之前,他首先被生产力所占有,环境也还不是人的环境,而人只是环境的附属物。社会现实对个人的规定在成为他的生命的内在丰富性之前,是人的重负与压迫。人必须要接受的或必须得达到的是与他的生命相异在的,或者说,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是不相契合的,其存在是非本质的物化的存在,而其本质是受压抑的或尚未存在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作为前人历史创造活动的结果,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但在实体性的结果中并未保存历史创造活动的全部意义,或者说后人并未通过与其存在条件或环境的相遇,而共享自主活动的真实意义。实体性结果作为社会现实对个人的规定已经丧失了人的本质,人必须通过重新“从头开始”才能再次成为本质性的存在,生产力只有如此地被人占有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力量。“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真实意义是人的理想价值延伸、充实到他的环境、条件与对象上,人与世界共享了人的理想价值,原先作为活动对象的外部规定性失去了固定的、分裂的知性特征,似乎具有了一种内在必然性,成就了整全性的个性生命。而这个物的个性生命也是人的同一个个性生命,在存在的本质性维度上,人与物(现实对人的规定性)都丧失了固定的僵化的界限,成为交融互摄、相互包含的存在。人在对象或异在中同时成为在自身中,人在对象中看到自己,因为物已经成了人的生命之镜,不只物成为人的,人也成为物(社会)的,人与物(社会)成为一种感性的共在。 自主活动作为想像对现实的否定性统一,以往人们过于注重对现实的实体性改造,即创造新的规定性,把自主性当作人的目的、意图、意志的实现。有限的目的、意图本来就是自我意识的剧场假相,表面上是自我的、我要的,其实“假名我”做不得主。创造新的规定性并非真正的否定性与超越性,创新所携带的无限性的讯息消失在了新的规定性之中。苏格拉底曾论及哲学一创造的本性,他指出:“在同一天之内,他时而茂盛,时而萎谢,时而重新活过来……丰富的资源不断地来,也不断地流走,所以他永远是既不穷,又不富”(34)。新的不一定是重要的,而本质性的创造活动确实实现了人的自主本性。但我们不应把创造新的规定性这种表观当作自主活动的本质,因而可以抓住创新所带出的其后其外的存在,直奔主题,存留无限性之意味。社会现实对人的规定性作为前人创造活动甚至是自主活动的结果,未能把自主性存留于物中,直接交与后人。物化的结果既作为支配人的物的力量,又作为人实现其自主活动的印迹、路标与入口处。社会现实对人的规定性首先作为“知性—物质”,与人构成了一种外部反思关系,从而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想像对现实的否定性统一,是一个既充实化又空灵化的过程。想像穿越了物化现实的表观,把其带回本质性层面,召唤回现实规定之后之外的生命一精神。可以说再现了原创者在“灵魂的回忆”中所带来的关于永恒的意象与绝对性的讯息,恢复了物的个性生命与创造的真实意义。想像对现实规定的充实,把存在者带回了开端处,回到事情本身,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达到具体的普遍性。想像对物化现实的充实又是对它的消解与扬弃。前已述及,想像的真实是非规定性的、无限的、否定的。想像力应化现实规定的活动,消解了现实规定的固定性外观,使其在真实意义的层面上与其他的可能性交融互摄、相互包含,也就是在现实的规定性中存放、涵摄、保持住其他一切可能性,从而成为精神,富于辩证性。想像把现实带回真实意义的层次,也就是消灭了物质,并转化为精神。 自主活动所实现的是人与自我的统一。人与自我之关系的完成是对人的异化或人与自我之疏离的克服。马克思专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但异化存在于深层的人性结构中。异化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涵义,哲学上指主体活动的结果变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构成了人与他物、人与他人的关系,所谓异化就是人在异在中不能保持自身,对象化是人在对立面中丧失本质的过程,这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阶段。其后则是扬弃异化,实现对立面之统一,达到更高的概念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否定之否定所肯定的就是人与自我的统一,即人在异在中就是在自身中。黑格尔辩证法有着天才的洞察力,但是“回到自身”、“对立面的统一”、“发展”(达到更高存在)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5)。因而,现实的人正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他人的交往来实现人与自我的统一。在实现人的本质的自主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根本上都是人与自我的关系。自主活动不是一个人对他物、人对他者的对象性、意向性的单向度主体性过程,而是一个人与他物、人与他人的循环往复的创生过程。无疑“人—对象—自身”的循环往复的创生结构是对对象性、意向性的主体性结构的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把这一循环往复的结构称为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模式,但还需要更为深刻地揭示其真实意义。从对象“回到自身”的过程并非是对第一个对象化、外化过程的“颠倒”,而是如黑格尔所说,对立面的统一是在更高的存在层次上实现的发展。“回到自身”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把人失去的关系归还给人的过程,“归还”必须是一个本质性的活动,或者说实现人的本质的“复性”活动。所回归的“自身”不是自我,而是比自我更深层的自性,“回到自身”是主体自我的自性化过程,它实现了生命的整全化与人格的完满化。我们所谓的“异化”、“人与自我的疏离”,是指人在自我意识的剧场假相中丧失本心、不明自性、不见本体。“人与自我的统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生产劳动)、人与他人的交往(社会关系)带到了人的“类本质”层面上,正是在人的“类生命”中,人在异在中才能同时是在自身中。“人与自我的统一”、“回到自身”是借助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他人的交往的暗示所实现的“灵魂的回忆”,因此自主存在具有绝对性、无限性与永恒性品格。人在异在中就是在自身中,意味着人与他的对象交融互摄、相互包含,人在对象中的活动与对象在人中的活动是同一个自主活动,人与对象具足同一个性生命,共享绝对性的理想价值。而这一自主存在也涵摄其他一切可能存在,这种涵摄与辉映正是想像的无限性在现实规定的当下即是。 马克思批判了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普遍性,主张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克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分裂,实现想像对现实的否定性统一的自主活动。这正是倒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注释: ①郗戈:《规范基础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③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2页。 ④王南湜:《“历史科学”何以可能: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7页。 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5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248页。 (1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3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0页。 (17)《柏拉图全集》第4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7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67、68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44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7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5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6~1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2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2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36~37页。 (34)转引自《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6页。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