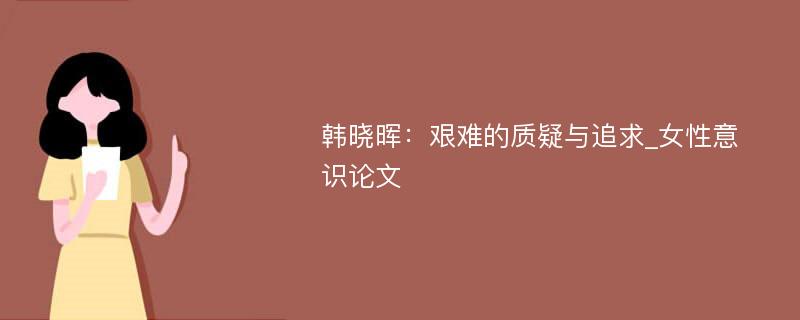
韩小蕙:用力追问与求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力论文,韩小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我和韩小蕙,还有许多“文化大革命”后有着特殊经历的大学生,终于有了自己象征性的历史命名。当大家说“新三级”的时候,就如同中国人跟中国人说“右派”,说“知青”,或者“老三届”一样,在无意识中迅速掠过一个彼此不言而喻的时代背景,达成对其中内涵与外延特别的心领神会。
在“新三级”的历史命名下,我同韩小蕙,一个七七级,一个七八级。可是,史无前例的半年入学时差,竟使不同年级的我们在一个大阶梯教室里,几乎天天打头碰面却没有说过一句话地同学了好几年。那时,在我们两个年级的一百多号人中,有诸多才子才女,被统称为人物,韩小蕙就在这之列为老师和同学另眼相看。七八级的墙报上经常赫然贴着她的大作,这使得喜欢混迹在最后一排的我,每每用双眼拨开那些已经做了父亲的大男生们老农似的喷烟吐雾,从后向前闲望的时候,总是会格外注意人物们,自然也没有放过韩小蕙。在我的印象里,这个看上去是温柔敦厚的“七八女”,总是沉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好像总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那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事。与我们七七级几位勇于积极在讲台前亮相或具有叛逆倾向的人物相比,韩小蕙确实是太安静了,她永远是不出风头的,是慢条斯理和慢声细语的,也是严谨正统和尊师守纪的。我甚至能够想象,她的书本和宿舍也绝不会像我那样可以是漫不经心和乱七八糟的。
毕业后,一切也便随着已为人父的大男生们的烟消雾散而淡忘。重新唤起并印证我在阶梯教室里对韩小蕙这种感觉的,是她写于1991年的散文《生命总不成熟》。应该说,让我惊异和感动的,并不是文章中那些纯粹技巧上的东西,而是当时已经三十六岁的韩小蕙,面对着自己从少先队员到记者生涯的十八张照片,竟挚切单纯得如同一个沉浸于理想主义情怀的女中学生,始终紧紧地抓住人生的正面要义,不顾一切地用力追问,用力求索。我特别注意到,她在慨叹自己的生命为什么总不成熟的同时,又在用力拒绝着一种世俗意义或反面意义上的成熟,这使得韩小蕙一直在理想信念与现实处境的矛盾状态中苦苦挣扎,挣扎的结果,不是向现实投靠与妥协,而是坚定了自己于不成熟中的生命理想保持。她因为自己种种在世俗意义上的不成熟,用力地向所谓的“成熟”追问,求索到的却是心灵对所谓“不成熟”的认定,于是获得了自我激励。这种用力,不仅让我惊异,让我感动,还让我心疼。因为我知道,只有一个曾经是十分听党的话,听老师和家长的话的好孩子(女?!),好学生(女?!),才可能有这样的心灵或信仰基调的命定,才可能在一个精神匮乏的时代进行这样的追问与求索,才可能陷入这样的自我挣扎并舍得如此用尽心力。我在其中看到的,是一种与骨血融在一起的不可更改的生命颜色。我还知道,与其说这种信仰基调和心灵色彩的命定是韩小蕙的,不如说它也是属于“新三级”中许多许多用力活着或作文的人的。他(她)们这辈子根本不可能真正享有玩世不恭或玩文学一类的轻松,他(她)们在命定中被框定,很难成为对抗正统信念的逆子与逆女。
所以,多年前的一个深秋,当我在渤海边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意外地碰到穿着咖啡色毛裙温良恭俭让地坐在那里的韩小蕙,特别提到了这篇散文。等我闭上嘴,韩小蕙慢条斯理地说:是么?
2
是的。
不管人们用过多么深刻,多么美妙,多么玄奥,多么科学,多么这样或那样的话语,说明散文的本质,它在我的眼里都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暴露性文体。所以,我在散文的字缝里,看到的常常是一扇扇通向作者情感或心灵极深隐处的幽门。无论是坦率真诚的挥洒自如,是尽诉愁肠的长歌当哭,是老奸巨滑的滴水不漏,是矫揉造作的炫耀卖弄,是道貌岸然的虚情假意,那散文字缝里的东西都瞒不过人,仿佛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不可能是水一样货真价实。最高层次的阅读是什么?就是与这样的东西真正接通。如果在感觉上短路,你阅读的便不是作者,而是你自己。
我不敢说,自己都能够进入对韩小蕙的这种最高层次的阅读。但是,《无家可归》使我感觉一下子就与她字缝里的东西接通了,我读出了韩小蕙在无比的用力中,在无尽的追问与求索中,情感的深在绝望和心灵的不停滴血。这使我心痛和心疼。一个非常能干的编辑和记者,虽然能以她十几年如一日为他人作嫁衣的勤恳奉献,为报社撑起一方亮丽的文化小天地,却不知到哪里为自己撑住哪怕豆腐干大的能够挡风遮雨的生存空间。她拉着女儿甜甜的小手,在高楼林立仿佛天上人间的北京大街上流浪,无家可归!她在流浪中对人生的追问,因为太用力,而明澈透底地指向绝望:
虽说是社会进步了人人平等了谁都可以去购买这些可爱的小楼,可是钱呢?以我工资条上286元(其中还包括女儿的独生子女费、副食补贴等等)的财力,敢去想入非非那些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高档楼?假如我能借得神人一口仙气,活个五百一十八岁,不吃不喝不花费不养家糊口,光干活一天到晚脑不停手不停脚不停,也许临死之前能买上一座?可是到那时连我女儿的女儿的女儿……也都早就老死了,我还守着一座空房子干什么用?
房子是为人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君不闻古猿人从树上刚一走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觅洞穴而居?君不闻成者王侯的帝王将相,哪一个不是大兴土木修宫殿,造了地上的再修地下的?君不闻世上最牢靠最赚钱最常胜不败的最长荣不衰的生意,就是房地产生意?君再不闻世上最摧人心碎的,不就是因了空间的困窘而使情人反目夫妇成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显然,这样的绝望里已没有深渊,韩小蕙的一番用力追问已经穷尽和洞穿了它的深底。让我心痛和心疼的是,一个临逼着被自己洞穿的绝望深底的人,只是“因为有女儿在,还不得不留在人间”,她一方面用力追问着“我们真正的家在哪里呢?”一方面又以母亲的眼光重新打量那种生存的绝望,最终求索到的竟是“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精神的家园”,那是她以母亲的一颗心用力为女儿撑起的家——“女儿张开小手搂住我的脖子,乖乖地靠在她的‘家’上……我就是她的房子,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可以为她除病去灾,可以为她赶走黑暗的压迫和坏人的欺辱,可以为她创造一个人文意义上的最温馨的家”。
这就是韩小蕙。身处现实困境时,并不满足于只凄凄惨惨戚戚上几句,她非要通过自己的用力追问,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说得明明白白,看个底儿掉。然后呢,绝不就此偃旗息鼓,对于她来说,那支握在手中的笔不只是为了揭露,为了批判,为了宣泄,还为了求索。那种命定的信仰基调,使她不能完全陷入对自己来说是“走调儿”的现实里无力自拔,当她在生存的困境中仿佛身陷囹圄似的不能主宰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用尽气力分身出一个精神的自我,释放出另一个她来“自我实现”。于是,这个她,再用力踏着那种命定的信仰基调去求索,直到把自己完全送进理想的归宿,为走了调儿的现实立好一个参照,一个价值目标,才算了事。
说到自我实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一个前提:一个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已得到很好满足后,才开始进入自我实现的王国。自我实现的人的生活是由“存在的价值”——真善美就属于这种价值——支配的,它也叫“超动机”(metamotives),就是超越需要的存在价值。可是,在马斯洛的估计中,只有1%的人能够自我实现,原因是由于这种超越需要的存在价值,处于人类需要等级的顶端,与所有的比如生理、安全、归属等需要相比,它是最嫩弱的,最微妙精细的,因而很容易在习惯、文化压力以及对它的错误看法下受到阻抑。那么,为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metamotives偏偏没有被阻抑住呢?马斯洛认定,这样的人,有一种靠着个人信仰(价值的)“内引导”,去抵抗消极文化或环境同化的品格。按照我的理解,能够自我实现的人,也是牢固地踏着主体生命的信仰基调,并以此主宰或指导自己生活的人。可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并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韩小蕙,之所以照样自我实现不误,就是因着她能用力排除各种阻抑,调遣出那个叫metamotives的家伙,让自己分身有术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用力的结果。对于这样的用力,我虽然很难一语道破,但是在我看来,它起码标明了主体对框定在生命骨子里的一种信仰(信念)的痴迷或执著程度。理想主义教育(也包括宗教),造就的就是这样一类人。
因此,你别看韩小蕙在《我家的烦恼》里,扯开话题大谈生存空间狭小的一大摊烦事,到了最后,她才不让自己陷进烦恼的现实场景里肠断不止呢,所以,牢骚能够蓦然打住,作为走调儿现实参照物的理想世界在精神上拯救出了韩小蕙——“祈求的是,我的单位光明日报社快快富起来,多盖房子,盖好房子,赶快人人三室一厅、五室一厅、八室一厅,使我赶快实现自己的诺言……让女儿……小小的心眼儿里获得大大满足,享尽人间天伦之乐”。在那篇叫做《体验自卑》的文字里,她虽然对着走了调儿的现实发尽自卑的牢骚,甚至动用了“嘁”这样的字眼儿助长牢骚的势头气,但是“愤世嫉俗、嫉恶如仇、浑身冒着复仇的火焰”过后,韩小蕙突然温良恭俭让地掉转过身来,丢下走了调儿的现实,把脸朝向美和善,将一个精神的自我立马送进人与人互助友爱的理想现实,把完全不同意义的自卑体验送进“升华到新的一重天”的境界。于是,这个分身出来的韩小蕙告诉人们:在“神圣的善良与爱面前,我感到一种自己不及的自卑”。
如果说,散文是在为书写主体塑像的话,那么,韩小蕙的散文形象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追问的她,虽然面对着走调儿的现实恶狠狠或不依不饶地穷追猛问,但是却始终是在她命定的信仰基调上沉浮跳跃;求索的她,虽然把分身出来的自己送进一个理想的境界,却不是为了悬浮(超然?)于走了调儿的现实或一个猛子扎进白日梦里不再出来,而是要认认真真给现实立下一个参照,一个“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目标。
这样一个痴迷或执著地想把理想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人,让她不用力,能行么?
3
不行。
我还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除非韩小蕙改变或放弃她被框定在生命骨子里的那种信仰基调,面对她认为走了调儿的现实,从此接受“世界可以是这样子”或“世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认知方式,换一种说法或者想法,否则,让她在追问与求索的时候不用力,是不行的。我说过,这样的用力标示着一种命定的痴迷或执著程度。
那么,一旦走出个人的生存困境。在《兵马俑前的沉思》,或看《苏州街涅槃》,韩小蕙是从哪里获得的走进历史的资格凭证,使她在对历史追问与求索的时候,用的偏偏是那样一种力呢?比如,站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威武之师塑像前,她要为自己弄个底儿掉,向读者说得一清二楚的,是兵马俑们为什么会成为埋葬——为什么会笑——笑什么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秦墓陪葬阵势是空前的兵马俑?这是因为秦始皇想要保住他的“万世江山”。为什么这成千上万个兵马俑非要以活人作模特儿?这是因为秦始皇在死后也要继续奴役他们。为什么兵俑们的脸上不是悲愤反而堆起恭顺的微笑?这是因为秦始皇强迫他们作此笑脸,使之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我终于弄懂了,兵俑们在笑什么。
……
他们在笑崩溃、笑灭亡:不可一世的秦帝国,倏忽一瞬就被埋葬掉了。
他们在笑贪婪、笑妄想:越想做万世的皇帝,越是短命而亡。
他们在笑虚弱、笑无能:在历史之簿上,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长久地奴役人民。
同样,颐和园里仿照清代原貌重建起来的新苏州街,使韩小蕙迫不急待要搞清楚的是康乾盛世的真谛,是“为什么历代的封建帝王,这么重视大修宫殿园苑呢?”终于,通过一位老学者的一家之言,她求索到了苏州街“虚假繁荣”的意义:乾隆盛世已显露出的转衰端倪,使假造出的一条苏州街,重现了令皇帝依依不舍的昔日江南的繁盛,通过怀旧情绪的寄寓,补偿了这位一国之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于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求索下去,韩小蕙交付给读者的是透彻得底儿朝天的揭示——“说苏州街是一曲挽歌极是准确无误,它的主旋律是无可奈何的悲凉,表面上的富丽堂皇,不过是封建文化到了烂熟阶段的一种回光返照,是一种极度贫弱的旧文明的象征”。如此,徜徉在清代文化腹体内的韩小蕙,感受到的只能是《哀江南》的感伤基调无处不在,因而“痛也切切,恨也深深”着从此“中国从世界第一流强国迅速沦落为屈辱的半殖民地”,“导致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面倒退,导致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乘虚而入”。
我想,如果换一个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大文化的角度?军事家的角度?时代审美崇尚的角度?……),多元而非一元论地观照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兵马俑也好,新苏州街也好,可能会与韩小蕙迥然有别的。
这再一次证明,韩小蕙对历史文化的追问与求索,同样是极其用力地踏在了主体的信仰基调上。这是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被框定在个体生命里的一种信仰基调,它直接通向融化于唯物史观与阶级论的历史范本,脱胎于主导意识形态下早已被永恒与绝对化了的历史教科书的教义。韩小蕙正是从这里获得了走进历史的资格凭证,也就是说,这个凭证规定了她的思想行走于其间的只能是这样的路线,而不可能是别种路线,就像一个人拿着楼上的电影票,不可能从楼下的检票口进去,从楼下飞到楼上的座位,而须先爬上楼梯,在楼上的票口检了票,才能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在这一点上,所谓的历史信仰基调对人的框定,并不是韩小蕙一个人的。因为:无论曾经作为权威性的历史范本,还是作为一元论及政治化、简单化的历史课本教义,它的影响,统驭的是整整一个时代,只要你没有走出那个时代,所读的就只能是这样的范本,所接受的就只能是这样的教义。实际上,在这两篇文字中,韩小蕙通过她近乎“天问”似的追问,以及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痴迷或执著,让人看到的正是这种历史范本的深入与具象化,这种历史教义的延伸与对象化。
在这里,信仰基调确实规化出了一道无形的神圣门区,韩小蕙便仿佛一个“守门人”。
4
有位叫怀特的老外,就提出过一个叫做“守门人的模式”。这个模式,后来在大众传播过程的研究中经常被使用。记者,便因此在西方传播学中获得了“守门人”之称。
怀特的守门人模式想告诉我们,在大众传播中的新闻流动渠道“门区”,“守门人”是干什么的?在怀特的眼里,这些人的使命或责任,就是根据特定意识形态的要求,或依照自己所理解的新闻受众者的兴趣和需要,或依据个人的意见(其实,这个人的意见也是信仰基调使然),对大量涌入“门区”的社会信息——无论是人物的,还是事件的——能否进入新闻渠道或继续在新闻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及选择。在我看来,这样的角色使命,规定或注定了记者——特别是我们的党报记者文字操作的特色。
韩小蕙是记者,这意味着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守门人。因而,她的一些散文或随笔,完全可以当作“守门人的艺术”来读。
“周五茶座”是韩小蕙在报纸上开的一个专栏,她之选择《道德·文化》、《呼唤绿色》、《记者自省》、《为人着想》、《予子以德》这样的议题进入媒体,是因为作为一个“守门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人文关怀,更加严肃正统地对走了调儿的现实给予匡正,并从正面的意义上更加直奔主题地为它立下一个参照,一个自我修正的价值目标。在韩小蕙的意识求索里,你会发现,能够涌入她的信仰基调所规化的门区的,大多是用力系牵着传统的观念:她认为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仁者之风”、“君子情怀”等应成为今后恢复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教化内容;她渴望建立一个人际间和谐与理解的世界,为此提出每个人都应学会为他人着想;对于记者现状的省察,使她寄望于以“记者学者化”的目标,带来新闻界的自戒自律;面对城市建设对花树绿意的摧毁,她发出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绿色的呼唤,指出人类尊重了自然就等于帮助了自己……
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长忆河源》与《鳌江深处》中,韩小蕙虽然对着河源之水、鳌江之变,用优美的语言或写景或状物或记事或抒怀了一番,但是她所有的“不遗余力”,都没有超离一个记者的使命与责任。她用力讴赞河源人民的顾全大局与自我牺牲,是因着记者的责任使她满怀激情地要为一种民族精神代言;也正是记者的使命,使她在鳌江深处发现的,是托起和托住那里经济起飞与生息发展命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作为守门人,她最知道“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文化遗产,永远是我们安身立命、发展前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这样的意义提升,流入“门区”后的作用。
在韩小蕙呈示的一系列“守门人的艺术”中,《文坛新伤逝》是我所看到的最出色的记者文字,她准确地触摸到了新时期最辉煌的时代与作家的脉动。面对着屡屡新伤逝的文坛,她不仅在用真诚的文字,而且是用一颗灼热的心,呼应着它,表达着它、慰藉着它,干预着它,提升着它,超越着它。所以,这篇文字传导出了时代的温度,人(作家)集体心象的温度。今天,说这是韩小蕙以记者的责任,为八十年代的文学与作家所作的一次耐人寻味的文字祭奠,并不为过。
因为:九十年代,虽然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文坛再也没有了那种情怀那种温度的伤逝。
5
韩小蕙的性别意识,就喷发于九十年代。
此间,她关于女人话题的散文有,《愿我们不再苦涩——给我所有的女同胞》(1990)、《不喜欢做女人》(1991)、《欲休还说》(1993)、《女人不会哭》(1993)、《说不尽的男人和女人》(1993)、《为你祝福》(1995)、《男人也爱,女人也爱》(1995)、《一日三秋》等等。在这些文字里,韩小蕙继续着她散文所特有的用力追问与求索,可是,问来求去,从根本上想弄明白和说清楚的不过是两个问题:女人和男人应该是什么?实际上又是什么?
在这些文字中,韩小蕙出示的是一种非常自觉与鲜明的女性意识。说到女性意识,在这里有必要对这样一个已被广泛使用的概念给予澄清。我曾经在一些评论文字或女性作者的发言中,看到和听到有关女性意识自觉与否、有无与否的说法,而且经常是把女性意识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和具有积极价值判断意义的语词加以运用。实际上,就我国目前女性作者的创作实践来看,女性意识并不是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女性主义(意识)的代称或同义词,女性意识不过是作为女性性别个体的一种意识存在,而女性主义(意识)则是女性性别共体的政治利益的一条阵线(这个在许多人心目中比较吓人的字眼儿),并不是所有的女性作者都能接纳它。所以,女性意识和过去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专政的特定时期,全民口中言及要增强的“阶级意识”——其实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而是指代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同的。可以说,女性意识仅仅是一种性别身份的强调,由于女性意识本身有五花八门,无论从积极社会实现的方面,还是从消极社会实现的方面看,它都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因而并不构成价值判断的意义。所以,有或者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并不一定给写作带来积极的价值判断意义。澄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意识自觉且强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一不渗透书写主体性别为女的信息,可作品所呈示的恰恰是一些反女性价值的东西。
韩小蕙虽然有着自觉而鲜明的女性意识,但是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顶多能算半个(?)女性主义者。在她的内心里,一直虔诚地树立着一个被神化的理想男性的偶像,这使她认定“优秀的男人应该是沉稳的山岳,挺起大山的胸膛,为女人挡住风,挡住雨,挡住虎,挡住狼,挡住一切艰难困苦、流血牺牲、崎岖坎坷”,优秀的男人“应该是宽广的天空”,“应该是无垠的大地”,“应该是奔腾的江河”,“应该比女人更无私……更多优点、更少缺点……更聪明、更博学”——总之,在好的方面都应该高过女人,坏的方面都应该少于女人。在这样的男性神话面前,女人应该是什么呢?是“可以无怨无悔地任心爱的男人踩着她的身躯去奋斗,也不愿躲到平庸、胆怯、愚蠢、苟且、低俗的男人那里金屋藏娇”,是“哪个女人都希望她所爱的男人比她强大”(《说不尽的男人和女人》),是“每个女人其实都在企望一座长城,能够安全地靠在上面”(《不喜欢做女人》)。而韩小蕙在《男人也爱,女人也爱》中树起的理想女性的偶像,则是“德”的绝对化身——“她们靠的是——内心的善良本质,高贵的人格修炼,和由此而来的外表的优雅气质”,就是这样的在她眼里非常杰出的女性,也把生命的最高价值实现寄望于爱情或男人,她们“不求功名利禄,不要荣华富贵。这辈子所求只一事——但求能有好男人来欣赏我,爱我”。
认真追究起来,框定着韩小蕙性别意识的这种信仰基调,其实是源于作为男权文化遗业的男性神话,或者说是对这一男性神话的现代复写。我曾经谈到过宗教与神话中的男性本质及文化迫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关于父亲的神话(国王的神话),英雄的神话,白马王子的神话,无一不是在布设关于理想男性偶像的无尽无休且不知疲倦的诱惑,构成一种固定不变的启迪。可以说,自从理想男性的形象嵌入神话,便被永恒化,并作为一种文化遗业而永世不灭。看一下中国宗法社会的古老典籍与文学,就可以知道它们是怎样千方百计强化着这种男性神话的信念:那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说卦》);虽“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敬慎》);是“我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再看一看“基督为男纲,男为女纲,上帝为基督纲”的基督教义,同样是在塑造关于男性的神话。所以,当西蒙·波伏娃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先躯者站立起来,她的《第二性》首先打碎的就是男性神话的偶像。她是在男性神话的偶像已经倒塌的基础上,指出女人的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所谓天生且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正是女性受压迫的产物,是个谎言。
我说韩小蕙顶多算是半个女性主义者,就是因为神话般理想男性的偶像至今依然树立在她的精神深处,使她仰视、信赖和渴望,使她并不因为无处找寻那个男性之神,而放弃自己对他痴诚的柔情与无尽的希冀——“不知道你在哪里,有话对你说”,“我托过风,让风吹遍茫茫天宇,找你……可是,不知道你是故意铁着心,还是真的没听见,我怎么到处也找不到你?”“我想找的,只是心心相印的你”(《有话对你说》,当然,并不排除这个“你”中也有能心心相印的理想女性偶像)。当她踏在这样的信仰基调上,向着现实人生求索的时候,对男人的失望,使她不能不用力追问:“什么时候起,男人们变得这么孱弱这么矮小这么虚飘这么全无责任感这么失了丈夫气这么没了男人味儿,令女性想做奴隶都不得?”(《不喜欢做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应该是什么”的理想信念,便不会有“男人事实上是什么”的失望。实际上,并不是男人让女人失望了,而是女人本不该沉醉于理想对男人寄托那么高的希望。于是,韩小蕙的某些文字再一次成为她在理想信念和现实情境之间惶惑与痛苦的载体。在韩小蕙的意识求索里,面对男人的那一半,算不上女性主义。
我之所以又在韩小蕙顶多是半个女性主义者的评论前打上一个“?”号,是因为她对现代妇女的困境有着自觉的意识与批判,比如《愿我们不再苦涩》就是对现代妇女的内务角色(家庭角色)与外务角色(社会角色)的疏离之累和超载之苦的发言,《女人不会哭》就是在为不以弱为美的自尊自立自强的妇女代言。在她这一半的意识里,可以看到与女性主义意识的合谋。我打下的“?”号及“顶多”二字的保留性说法,是因为韩小蕙在她女性的信仰基调中,确实表现出对传统的某种亲和力,她认可“女人天生来是男人的阶梯”,以为“只是因为女人们越来越寻找不到可以为之献身的男人,她们才自我奋斗起来”(《说不尽的男人和女人》)。这样的看法,实在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目标,相距甚远。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在现实处境与观念上两性的不平等,妇女革命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源于漫长的男权文化已经将对女性的仇视与歧视内化在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这一切的出发点,无论落在男/女二项对立的中心或者边缘,女性要恢复的都是她们被压抑和排斥的主体性,绝非是因为寻找不到可以为之献身的男人。
在为这篇文字画上句号前,我想说明的是,从我们目前的现实处境出发,我并无意召唤所有的女性或女性作者都成为女性主义者。即便是我本人,也只说过从此不再拒绝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我承认,我的思想或意识,总是大大地走在我行动的前面,我的写作自然也常常大于我的行为,这使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对文学发言的时候要有所保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批评韩小蕙的同时,也深深地理解她。对于我来说,理解一个古典的和理想的女性,也许比契合一个现代或后现代的女人更容易。
韩小蕙无疑是理想的和古典的。她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着,追问与求索,那么用力。她需要思考的恰恰是如何才能不失之这种用力。
1996年12月20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