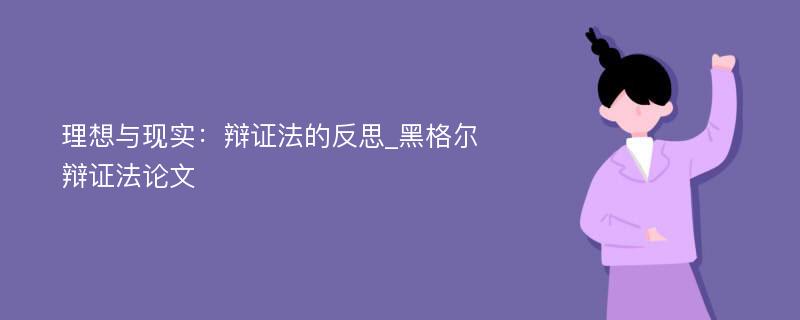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辩证法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01-07
在当前我国的理论界,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命运是十分奇特的。抽象地说,它在理论界(甚至在理论界以外)的地位很高,但是在全国每年的科研成果中,却很少有关于辩证法理论的新探索,似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了。偶尔有一点相关的讨论,却又常常不易看懂,弄不清它是从什么角度来规定的,为什么这样规定。更有甚者还向我们传达了一种信息:现在还来讨论辩证法,不过是不学无术的表现罢了。之所以导致这样的局面,可能是历史上的某种浊流造成的恶果。
过去我发表过一些反思辩证法的文章。我认为,辩证思维不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弃儿,恰恰相反,这个时代在理论思维上,正是由于缺少了辩证法才陷入了一系列的困境。例如,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肯定是由于人类自身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前进了呢?不能,还要前进,而且是更快的前进。那么,我们能不能期望找到不再产生矛盾的更快前进的道路呢?不可能,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二重化的存在。没有这种二重化,人就不会走上文明前进的道路。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忽视辩证法,无论是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还是时代提出的辩证法的新问题,都应大力去研究。我正是根据以上这一点,谈一下近期的想法。
一、辩证法是为解决认识的客观性而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哲学理论
大家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第一个系统阐发了辩证法理论。他在阐发这一理论时,是把它作为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理论提出来的。这种形而上学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亚里士多德说:“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窃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地为某种本性所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的原因。”[1](P84)又说:哲学是研究永恒、不动但可分离的东西的,即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实体的。因为这种存在是我们的感官不可能直接把握的,所以,后人把这门学问称之为形而上学。但在思维方式上,人们是按直观中有限对象似的来研究它的。
到了近代,由于实验科学和为之服务的数学在西方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中世纪曾被抬高到上帝地位的作为存在的存在,受到了强劲的冲击。法兰西斯·培根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时说:“它所作出来的与其说是给真理开辟道路,毋宁说是确立和传播错误。”[2](P6)在这种背景下,号召大家研究自然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认识论理论发展了起来。对认识论的研究代替了对本体论的研究,成为了当时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有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相反,近代认识论却使原来孕育于形而上学的一套思维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和系统化。后来人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方法的便是这些。
如果对这套思维方式略加整理,可以归纳如下。(1)认识对象是先于认识就给定了的。(2)认识方法是独立于认识的一套认识工具。(3)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4)认识的结果或者是错的或者是对的,不可能有第三种。上述诸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因为,它意味着主体和实体的对立是绝对的,这样认识的客观真理性便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证明。
当然,这些方法论的原则并不是某个思想家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在实验科学的发展中往往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把它们总结出来,推广到哲学中去,便不一定行之有效了。例如,物理学是研究物理现象的特性、规律等等的,可是它并不追问客观上是否存在物理现象。对物理学而言,物理现象便是给定的。但是,哲学所要研究的,无论是古代形而上学中的实体,还是近代认识论所要研究的自然,其存在与否都要被追问。所以,按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原则,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是实证的科学。
正如科学的方法不能取代哲学的方法一样,哲学的方法也不能取代科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在研究辩证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种简单化的错误,以为辩证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其他一切方法都是错的。其实,这种理解恰恰就是反辩证法的。起码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把辩证法当成了可以包医百病的仙丹,这正好是对辩证法的否定。
即使在哲学的范围内,由于时代的不同,哲学在具体内容上的差异,也不可能要求它们都必须臣服辩证法。辩证法有它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说一点辩证法之所以会出现的历史背景。
从旧形而上学到近代经验主义,理论上始终存在一个隐患,而后,这在大卫·休谟那里被揭示了出来。休谟在批判经验论时说,如果人类的知识全部来源于经验,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能提出在经验之外有没有某种独立于经验的东西存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请教于经验。但是,经验在这里沉默了,而且也不得不沉默。人们从这段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把认识对象理解成先验给定的,在理论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困难。
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比较清楚地理解了休谟所提问题的革命意义。他说:“自从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休谟并没有给这一类知识带来什么光明,不过他却打出来一颗火星,如果这颗火星遇到一个易燃的火捻,而这个星星之火又得到小心翼翼的护养并且让它着起来的话,从这个火星是能得到光明来的。”[3](P5-6)他又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3](P9)经过了几十年的思考,康德对休谟提出的难题给予了一个极有启发性的回答。这就是他所说的:“意识的综合统一是一切知识的一个客观条件,不仅是我们自己为了认识一个客体而需要这个条件,而且任何直观为了对我成为客体都必须服从这一条件。”[4](P92-93)如果把康德的话说得简单明白一点,那就是: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个条件即意识的综合统一。显然,在这里,康德提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即他否定了历史上把认识对象当作先验地给定的观点,提出了在主体能动性的前提下,认识和认识对象同时成立的观点。这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从逻辑的层面说,没有认识,又何谓认识对象;反之,没有认识对象,又何来认识。正如历史上争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两者是在相辅相成中演化过来的,若问谁在先,即把发展的现状当成发展的起点,完全把问题弄错了。同样的道理,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分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人类不改造客观世界,人类和其他的自然动物一样,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便无所谓认识者和被认识者。
问题在于康德虽然提出了“同时”成立的思想,但却没有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他仍然认为,认识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先验地给定了的。其一是物自体。只不过他暂时抛开了他的经验实在性,变成舍弃了它与主体的一切联系,仅就其自身而言之物。其二是先验的自我。康德说它在和经验材料接触以前只具有先验的观念性,不具有经验的实在性。其实这两点,一个是尚不成其为对象的对象,另一个是尚不成其为主体的主体。因此,康德的认识和认识对象同时成立的思想,是一朵有启发性的“花”,却没有能结出有启发性的“果子”来。
黑格尔在批判康德在逻辑上的不彻底性时曾指出,物自体既然舍弃了与主体的一切联系,它便不过是关于物的极端空洞的抽象,完全是多余的假设。至于说到纯形式的自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形式即内容。思想的对象就是它自身。例如一个人若不会说“我”,便不可能真正成为思维的主体。所以黑格尔说:“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思维形式的批判,必须在认识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各个思维形式必须自为自在地加以考察,它们既是对象又是对象本身的活动,它们自己考察自己,必须在它们自身由自己规定自己的界限,揭示自己的缺陷。这就是往后作为辩证法而加以特别考察的思维活动。”[5](P103)按照黑格尔如上的分析,他是克服了康德的不彻底性,不过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即在他看来,物自体是不必要的,思维要认识的就是它自身的矛盾运动。
到此为止,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之所以要提辩证法,是想在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前提下,来克服以往对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僵硬对立的理解。但是,由此获得的认识却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此,辩证法所要讨论的矛盾,并不是任何一种矛盾,而是在肯定主体能动性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与认识对象、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如果把辩证法所讨论的矛盾扩大到一切直观中的矛盾,这是思想中的混乱和理论上的错误。以为只有辩证法才承认矛盾,其他的思维方法都是否认矛盾的,那是无知。例如,机械力学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大概不会有人认为是辩证的,但是,它并不完全否定矛盾,相反,它认为没有矛盾,机械运动便不可能。
正是由于这种任意夸大辩证矛盾范围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等量齐观,似乎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是直接的。这就形成了对辩证法的经验主义理解。其实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正如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样,是互为中介的辩证的关系。因为两者的表现形式是相反的,在主观上是一般蕴含个别,反之,在客观上却是个别蕴含一般。所以,它们的一致不是落实在一个最后结论上,而是落实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中。正是由于用经验主义观点来理解辩证法,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宣传辩证法的名义下,形而上学猖獗了起来,甚至便于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
二、辩证法的根源是实践
按照上面的解释,可能有人仍然会问,这样理解辩证法合理吗?有什么客观根据呢?我以为,这个客观根据就在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中。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但归结起来说,无非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反思。总体来说,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二重化的存在,人只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但是,他却天天在为超越现实的理想而奋斗。我常常说,现实之所以叫现实,永远不可能成为理想;反之,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在实践中,理想和现实的确又在相互转化,如果不能相互转化,理想就成了空想,现实便成了世界末日了。所以,这是一对典型的辩证矛盾,抽象一点说,这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这便是辩证法的客观根据。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人类生存发展中特有的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这个矛盾,人类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人和其他动物的对比中便能清楚地看到。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从自然界中发展来的。但人以外的其他动物都是在适应外部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人则不然,他是在通过实践要求自然环境适应自己的前提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所以,前者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而人却超越了自然界,把自然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部分,并组成了自己特有的世界,即人类社会。
由于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在人和自然界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为我关系。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6](P81)所谓为我关系,从主观上说,即被我意识到了的关系;从客观上说,是我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为我服务的关系。一句话,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按我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当然,这种建立不是任意的,而是历史性的。但是,无论如何人不是自然的奴隶,相反,他从自然界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这就产生了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特殊关系问题。
要实现理想,首先就要认识现状。正如法兰西斯·培根所说,想要驾驭自然,首先就要服从自然。但是,经验主义者所说的认识,还停留在直观的水平,说得好听点,是要反映对象的原貌,就像食草动物似的,要知道此草(对象)正是它可以食用的草。但是,上面所说的认识是要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服务的。严格地说,仅适应自然便无所谓认识。所以,它不能停留在简单肯定此物(对象)上,而是要充分认识了此物(对象)的原貌,目的是改造此物(对象)。即不能停留在甲就是甲,而是要达到甲既是甲,又是非甲。也就是说,要从肯定中看到否定,通过否定来达到新的肯定。这种思维方式,便不是传统形而上学(以本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旧哲学)中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
所以,上面所说的辩证法并不是个人的任意规定,而是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也可以说,辩证的方式就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主观上看,它都是如此。
从客观上看,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具体点说就是他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说:“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P68)生产不仅从生活资料的供应方式上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了开来,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消费的性质。
供应方式上的不同很好理解,其他自然动物都是靠自然界的直接供应而生存的,人则不然,他主要靠自己的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正因为如此,人才能超越自然界,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即组成了社会,开创了文明发展的历史。从积极的方面看,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大,那么,人从自然界争得的自由权便越大,越是能独立创造人类的文明史。但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大,改造越深入,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就越严重。甚至一些科学家呼吁说,人类的生产方式若不改变,那么人类在地球上可以生存的年月,将是屈指可数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人类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也越来越小了。
所谓改变了消费的性质,是指本来消费是为维持生命,所以是生理性的。例如,不吃便会饿死,吃饱了便不吃了。所以,它不会变成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人的消费因为主要靠生产来满足,结果便产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生理性的消费变成了社会性的消费。例如,现在社会上的请客吃饭,主要不是为了吃饱,而是某种社会礼仪的需要。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金钱似乎是人们最大的需要。你可以说用它能满足生活上的一切需要,也可以说,它什么实际需要也满足不了,它只是满足了积累财富的需要。第二,满足原有需要的过程,变成了创造新的不满足(新的需要)的过程。例如吃不饱的时候,人们只期望能吃饱,等吃饱有了保证时,人们便期望能吃好。有限的需要在这里变成了无限的奢求。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大道上,迈上了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它也为人类招来了无数的麻烦。例如,许多没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甚至有害的消费品也发展了起来。对自然,我们提出要保护,难道对人自身就不需要保护了吗?难道说文明的发展必须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吗?到底什么叫美,违反自然的能叫美吗?文明一定要超越自然,但超越自然就是要反对自然吗?
但是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只能向前进。要前进,人类便不应该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面临的困难。在矛盾和困难中前进,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
从主观方面看,思维活动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内容。它的活动方式也和生产活动的方式相似,是在辩证矛盾的斗争和转化中前进的。
对思维最简要的称呼可以名之曰“我”。一个人能以“我”称呼自己,是正常思维能力的必要条件。大家都熟悉,学说话的幼儿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说得出“我”来。“我”就是“自我意识”,是思维能力的核心要素。思想和感觉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就在于:感觉以感官以外,并与之并存的东西为对象。例如,眼睛是看眼睛以外的东西,它不可能看到它自身。思维则不然,它在形式上是以自身为对象,其实是以自身为中介,才能以外界为对象。例如,我意识到“我”看到了什么。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思想的纯概念当作全部逻辑推演的主体,就是错误地理解了思维在形式上的独立性。其实,感觉和思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互为中介的。如果感觉和思维相互独立,都满足于自己的直接性,那么它们都等于零。用逻辑的语言说,它们都是纯存在。不过,这两个纯存在是不能等同的。感官直接把握到的纯存在是一个还没有被规定的个别的存在,相反,思维直接把握到的纯存在,是舍弃了同类诸个体的特殊性以后剩下的一个抽象的共同体。黑格尔的所谓逻辑推演,实际上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纯存在。
按照经验主义的习惯,人类似乎是先有感觉经验的积累,然后才有思维。其实,没有思维参与的感觉是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反之,没有感觉经验的参与,也就不可能有思维活动。所以上面我们说,感觉和思维是互为中介的。而且,这种中介是一个无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像大家熟悉的鸡生蛋蛋生鸡一样。
认识中除了感性和理想的矛盾以外,还有一个基本矛盾,即如实反映直接对象还是超越直接对象。按照传统的观念,人们总以为,认识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反映自己的直接对象。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是说只有和对象直接打交道了,认识才可靠。即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反映对象的原貌。但是,认识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实践的目的恰恰是要超越原有的对象,创造新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如实反映原有的对象上,那怎么能指导实践的创新活动呢?
中国有句古语,叫“实事求是”,很多人以为,这句古语很好地反映了认识的根本目的和本质。在我看来不一定。关键在于对“实事”如何了解。如果仅仅作给予意义上的了解,那么对“求是”的了解便完全可能是经验主义的。正如法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所说的那样:“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此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过此,他既不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2](P8-9)如果人的认识真的只能是如此,那么,不必说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甚至可以说,人根本上不可能超越自然,走上文明发展的大道。
“实事”和“求是”是一对辩证矛盾。人的认识主要从事实中求得规律性的看法,以便保证认识有预见性,对实践起到指导的作用。但是,这里所说的“实事”,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静观中给予的存在,更应包括为“求是”而主动设定的动态中的存在。而且,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和认识的越来越深入,根据“求是”的需要而设定“实事”的比例便越来越大。反之,由此而获得的认识也就越全面越深刻。
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认识的能动性已经是一个人们可以直观到的事实了。如果说,在古代,人们认识能力的标志是认识的结果,现在却发现,这种能力的真正标志是对认识对象的设定。
三、辩证法的实质是要探索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便重视理性,重视逻辑,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到近现代甚至产生了用科学来否定哲学的时髦思潮。中国古代哲学则重视德行、重视心性修养,比较倾向于人文主义思想。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片面的。从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看,恰恰是要求把两种倾向统一起来。
所谓人的特殊存在方式,就是上面所说的理想与现实二重化的存在方式。正如俗话所说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这些任何人也活不了。这也就是说,人和其他动物相似,都依赖于实存的自然界,只不过其他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是直接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间接的。因为人是通过自己对自然界的改造而依赖于自然界的。因此,我们常说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满足于现实的世界,总想按照头脑中理想的模型来改造现实的世界。正是由于这种改造活动,人才超越了自然界走上了文明发展的道路。所谓理想的模型,就是一种价值的尺度和原则。这种模型、尺度和原则,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不过这种尺度和原则既然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尺度和原则,也就是人类所特有的尺度和原则。因此改造自然的进程,也就是弘扬人性的进程。在这里价值和事实统一了起来。只不过这种统一是历史性的。正如我们常说的,理想之所以叫理想,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现实;因为一旦理想变成了现实,它也就否定了自身成为理想的现实根据,而不再是理想了。同样的,现实之所以叫现实,它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理想;因为,一旦现实等同于理想,那就等于现实抛弃了它成为现实的品格,成为没有个体性的抽象的一般原则了。这不等于世界末日到了吗?所以,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只可能在它们互为中介的矛盾转化中。这种历史发展,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越来越广泛深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性的光辉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发扬。这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文明的历史。
哲学中的价值,既不同于经济学中的价值,也不同于伦理学中的价值。经济学中的价值可以用一个商品在生产中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计算,而且因为它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商品的占有者可以通过出卖它而盈利。所以,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本质上仍是个形而下的概念。哲学中的价值,是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形而下的实物的,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就如实体,作为存在的存在等等概念似的。它标志着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展开和提高,即人的尊严和自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哲学中的价值概念与伦理学中的价值概念也是不同的。伦理学中的价值概念总是和人的行为规范相联系的;哲学中的价值概念是与人的存在方式相联系的,指的是人不仅生产了实存,而且生产了它自身(即人的尊严和文明)。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人们产生过一种误解,以为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的权利。实际上,他们把历史发展的某种结果,当成了历史的起点。他们无非是想把这种结果当成永恒的原则,来证明某种狭隘私利的政治理想是天然合理的罢了。历史上曾经时髦一时的这种幻想,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欣赏了。
我常喜欢以长城为例,来说明哲学中的价值概念。当年长城是为防御外族入侵而修建的。为此,中华民族不仅在财力上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人力上也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经过了千年风雨,万里长城已经所剩无几了,当然不可能再起到防御外来入侵的作用了,而且,即使它完好如初,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上的使用价值了。但它却留下了一句永远鼓舞着华夏子孙的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因为,从长城的断垣残壁中,华夏子孙看到了勤劳勇敢、不怕艰苦、威武不屈、不畏强暴、排除万难、一往直前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保证了华夏文明几千年来从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的诸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今天,它仍在鼓舞着我们振兴中华,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这就是万里长城断垣残壁的真正价值。
一般说来,人类所创造的东西,都蕴含着实存和价值这样一对辩证矛盾。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生产原来是为满足人的生计而进行的,但这种满足却改变了人,使人超出了自然,超出了自然动物,走上了一条独立的人的发展道路。人类的生产活动或实践活动,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人性展开的历史性标志。因此,人类所创造的产品,既是有实用价值的实存,又是这种实存所显示的人性的展开,即价值的进步。
实存和价值在形式上似乎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说到实用,人们想到的便是某种实存,只有在它几乎要丧失实用性时,人们才会想起它的价值。如果这种实存真的没有任何使用价值,那么人类便不会生产这种东西,当然也就无所谓在人性化的道路上有所前进了。但在这种一致中的确潜存着矛盾。当人类的产品真的改变了人类消费的性质,由生理性的消费变成了社会性的消费,由有限量的消费变成了无限量的消费时,有害的消费便可能发展起来,完全有可能把原来对人性的弘扬变成了对人性的毒害。例如,鸦片作为药品时,它在帮助人类战胜病魔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但是人们一旦把它吸食过量,便是对人性的毒化了。又如对核能的利用,它的确帮助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迅猛前进,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杀人的强大武器来生产时,便不一定是在帮助人类前进了。所以,认识这种潜在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人类真的就要犯自我毁灭的错误。
不过,人们也不要以为哲学中所说的实存与价值的统一就是宗教中所说的尽善尽美的天堂。尽善尽美的就是不现实的,真实的东西是在不断发展中的东西。就像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的无限发展中一样。尽善尽美的现实,不过是更善更美的无限发展的过程。正如上面指出的,经过人们在实践中的努力,理想不断地在向现实转化。但理想不是一个给定了的常数,当它不断地在向现实转化时,也就不断地变更着自己、发展着自己,即向现实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这也就是价值和实存的真正统一。价值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实存,实存也永远不可能等同于价值。价值和理想是人们永远要追求的目标。
人的这种无限发展的过程,被人们归结为人的存在的一个根本特点:它永远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所以,人和自然动物相比,后者是一种有限的存在(是这个不是那个);人却相反,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不过这种无限存在,却仍然以活生生的个人体现出来。正是这种活生生的人,成了事实和价值统一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