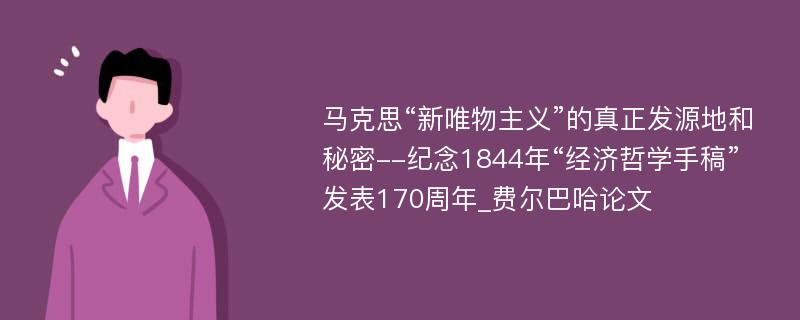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纪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17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诞生地论文,唯物主义论文,手稿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写于170年前。由于该文本的独特性及其特殊的历史境遇,所以它成为争议最大同时也是误读最严重的文本,从而构成哲学史特别是哲学文献诠释史中的一道风景线,乃至这一现象本身也成为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笔者在多年前曾经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赫斯与马克思思想关系的角度对《手稿》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解读,澄清和阐释费尔巴哈、赫斯对《手稿》的实际影响。①本文拟从另外的视角,结合哈贝马斯、阿尔都塞、阿伦特、海德格尔等人的相关评论,对《手稿》的性质、地位特别是有争议的主要问题进行某种再释和讨论。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手稿》的一种辩护和正名,这是基于对《手稿》中表述的劳动观的基本肯定以及相关争议问题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 在笔者看来,将《手稿》之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意义同《精神现象学》之于黑格尔哲学的意义相比拟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手稿》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发源地和秘密,正如马克思称《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②一样。这集中体现为马克思通过《手稿》对“劳动”概念的深入探索、分析和阐释,初步而系统地创制了自己的新实践观(其形式是仍带有经济学特色的劳动观),从而为整个“新唯物主义”体系大厦奠定了最初、然而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据相关考证,德语中的“劳动”(Arbeit)一词来源于希腊语kopos和ponos,拉丁语labor和molestia,在中古高地德语中意指奴役活动(Knechtstaetigkeit),在困苦、劳累、艰辛的工作意义上被使用。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中,这一含义几乎无实质性的改变。阿伦特在其1953年的讲座手稿即《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曾反复强调这一语词的古老的、传统的或所谓正统的意义:劳动这种营生性的活动,是具有消费性质的、发生在生物学领域里的、属于动物功能的、与必然性相联系从而具有强制性的、私人领域里的行为。概言之,它具有动物性、消费性、私人性和强制性等一系列特征,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完全动物性的“非人行为”③。如此看来,可以想见,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要素,置于自己新哲学的核心,是何等地反传统、何等地具有颠覆性了。 在《手稿》中,“劳动”概念居于中心地位。它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作为经济学概念,它具有“特殊劳动”和“一般劳动”双重属性,是创造财富的手段,是一个现代范畴,被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称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④,并且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才具有了最成熟和完善的形态。作为哲学概念,它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劳动”的一种哲学转化和升华形式,实际上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的表述。不仅有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概念所具有的特点,而且还有更为一般的哲学存在论的特点,即它是人及其历史运动的现实基础和本质规定。此外,就其作为哲学范畴而言,在《手稿》中,“劳动”概念也是一个“具有双重蕴含的范畴”:“它既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规定,又是一种人的存在的规定,……一方面,……是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的本质规定,即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劳动是产生生命的活动或人本身的生产,因而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决定因素。”⑤ 为了全面展示马克思在《手稿》中初创的作为其实践观雏形的劳动观,以及便于后面展开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我们不妨首先对其略加赘述。 马克思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劳动的本质、内在结构、主要特征以及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劳动的本质和结构,与黑格尔所看重的精神劳动以及费尔巴哈所看重的理论活动不同,马克思肯定和确立的是以往西方文化传统所贬斥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劳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劳动作为“实践的人的活动”,首先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本身,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⑥。而“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即体现为“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⑦。它的横向结构隐含在马克思有关劳动产品、生产行为、类本质、与他人关系等“异化劳动”规定的分析中,主要体现为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同生产行为以及同他人的关系;它的纵向结构即完整劳动过程的诸环节,隐含在马克思所撰《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所摘引和直接论述的对象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项要素中⑧。关于劳动的主要特征、作用和地位,马克思提出并阐明,劳动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和动物相比,人的劳动是“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从而人能够将其与自身相区别;劳动是“全面的”、不受人的“直接的肉体需要”支配的、“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可以运用“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以及“按照美的规律”进行⑨;劳动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中介和手段,通过劳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⑩;劳动是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和艺术等社会诸政治和精神现象的本质,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前者普遍规律的支配;(11)劳动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劳动一方面使人成为“类存在物”或“人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使自然成为人的“作品”和“现实”,成为“人化的自然界”或“人类学的自然界”(12);劳动是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基础,人类历史是劳动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3);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首先作为存在论范畴出现,并全面展现出其存在论的内涵。 需要特别论及的是《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及其特性的界定。基于对“劳动”概念的理解,马克思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人的社会性,并进而初步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新见解。他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4)这是因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5)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出重新规定,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他的生产。“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6)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人是社会存在物的实质,在于他首先是劳动、实践的存在物。 与此相关联,从新的劳动观出发,马克思对构成劳动即物质实践的内在矛盾的主体、客体的关系作了与以往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界说和阐释。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个体的人理解为主体,把现实的自然界即作为“劳动对象”和“提供生活资料”的自然界理解为客体,而把这两者的中介和现实基础理解为人的劳动活动。在他那里,主体与客体通过劳动相互扬弃而一体化,成为一个有机的密不可分的整体:作为主体的人是通过他的活动被自然化了的人;作为客体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的活动而被“人化的自然界”;而作为自然与人的中介的人的劳动本身,其现实的表现形式和完成形式则是“工业”。因而工业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开”,是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的钥匙(17)。据此,马克思既否定将主体原则绝对化的抽象的“主体主义”(Subjektivismus),同时也否定客体原则绝对化的抽象的“客体主义”(Objektivismus),认为扬弃两者及其对立“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有可能。(18) 由于马克思把人的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从而也就把人的劳动理解为整个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这样,就从根本上扬弃了西方既有的将世界二重化的传统形而上学,扬弃了在感性世界之外和之上去寻找整体世界的终极和最高的统一性的思维传统,这种思维传统曾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一直延伸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中。正如马克思所阐明和表述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19) 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确立的劳动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彰显出其重要意义:在理论方面,它为整个“新唯物主义”大厦奠定了最初的决定性的基石,开启和提供了人类对自身及其社会和历史认识的一个新的视域;在实践方面,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异化劳动批判,将私有财产归根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并最终归根于“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深入阐释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初步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现代形式——资本的本质、根源和内在逻辑(20),并为其最终扬弃提供了哲学论证。 不难看出,《手稿》体现了马克思在通过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实现从“新唯理论”(21)向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决定性转向之后,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这是“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最重要的酝酿、准备和前奏。在随后不久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系统地拟定了他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要点。在某种意义上,《提纲》是对《手稿》的概括、提炼和升华。没有《手稿》,就不会产生《提纲》,当然也不会产生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与《手稿》所表述的劳动观相联系,国内外学界对《手稿》的争议和批评主要聚焦在“异化劳动”以及“人的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问题上。在此方面,代表否定性意见的“人本主义”说、“唯心主义”说、“虚无主义”说等都影响颇大,甚至有的观点迄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些判断不仅曲解了《手稿》文本,而且还在客观上遮蔽和贬低了《手稿》的价值,损害了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理解,故而值得重新提出并深入探讨。(22)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说为人们所广为熟悉并不同程度地接受。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断裂时期”前的著作,表明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立场,(23)从人、人的本质或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因为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为理论人道主义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就是人和人的本质构成了他的哲学和全部理论的中心。阿尔都塞认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解释社会和历史的理论。阿尔都塞还断言,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的经验主义和本质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24) 为什么阿尔都塞如此讳言人的本质,如此反对以人为出发点来解释社会和历史呢?他的回答是:这是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的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25)。但是,以人为哲学的出发点、对象和中心本身与唯心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不构成理论错误和理论灾难的必然前提。现代哲学的第一甚至最高对象就是人。古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就其对象来说就是从自然转移到人。黑格尔在构建自己哲学理论体系之初为自己哲学规定的任务就是“从自然迈向人的作品”(2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规定的现实“出发点”、“前提”和最终价值归宿也是人,即“现实的个体”(27)。其所以如此,因为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历史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价值主体。因此,问题的关键显然并不在于是否以人为出发点、对象和中心,而是在于到底如何理解人。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批判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形态,并非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谈论人,而是因为它抽象地谈论人和谈论“抽象的人”,即“精神的人”(鲍威尔)、“自然的人”(费尔巴哈)和“利己的人”(施蒂纳)。也就是说,是因为它把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变成一种普遍的一般的抽象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强调的:“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28)因此,是否以人为出发点、对象和中心,并不构成一种有关人的理论正确与否、合理与否,乃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标准。能够构成这一标准的是对人、对人的本质的界说是否合理或科学。阿尔都塞陶醉于自己所创制的基于“只看到”和“没有看到”双方面的“症候式”阅读法,但是,恰恰在此问题上他却完全背弃了自己的这一方法。因为他一方面“只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谈论了人、人的本质和人性,而另一方面却“没有看到”或视而不见马克思对其是如何界说的,这就使他势必“失察”和遗落马克思理论的“深层结构”和“总问题”。 那么,马克思在《手稿》中到底对人的本质是如何理解和界说的?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基于社会物质关系在社会历史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理解,马克思就指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soziele Qualitaet)”。(29)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30)。在与《手稿》同期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专门就人的本质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所以人通过他的本质的活动(Bestaetigung)创造和生产人的共同存在物、社会的本质(das gesellschaftliche Wesen),而这种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个体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个体的本质,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精神,他自己的财富。……人,不是抽象物,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诸个体(Individuen)。”(31)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人是现实的诸个体;他的社会本质的规定性就是作为他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活动的劳动;人的本质不是某种先验物、预定物和预设物,而是人自己通过他的本质活动而生成的创造物和生产物。正是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本身,生产生活本身”(32),而人作为“特殊的个体”和“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具体而言就是从事生产、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的“工人”:“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的人的特性只有在这些特性为异于他的资本而存在时才是人的特性。”(33)不仅如此,在《手稿》中,马克思甚至还基于自己的劳动观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直接将费尔巴哈所主张的人的精神本质即“理性、爱、意志”和自然本质即“人的自然”(34)归结为劳动的产物,对费尔巴哈关于抽象人的议论进行了委婉的批判:“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5)这无异于公开昭示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基本立场上的分歧和对立。 《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理解无疑迥异于费尔巴哈的观点,从根本上超越了后者。就实质而论,费尔巴哈人类学主义的根本缺陷并不在于它以人为中心,而是在于它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其具体表现在,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劳动活动,只承认理论活动和诉诸“感性直观”,将人的本质理解和界定为自然本质或精神本质,从而将人变成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将人类历史变成了自然史和宗教史。由此可见,在《手稿》中,基于劳动观的确立,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这一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类学主义、从而也与以往各种人道主义理论彻底划清了界限。 诚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将自由与劳动相联系,称劳动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然而,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假定了一种抽象的理想的劳动吗?事实上,只要仔细注意一下语境,就会发现,马克思之所以称劳动这种活动是一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决不是出于一种理想的抽象,而仅仅是指人的这种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在于,人的这种活动是一种具有意识性、意志性的活动,人能够将它变成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对象,并藉此将自己的这种活动同自己的生命本身区别开来。正如马克思在文中所阐明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6)二十多年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当马克思谈到建筑师与蜜蜂各自活动的区别时,又表述了同样的见解:“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7) 阿尔都塞还指责《手稿》以“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的本质的复归”这一逻辑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一理论逻辑是从现实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还是出于主观杜撰而从外部强加给现实历史的?笔者以为,当然是前者,因为这一逻辑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基于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及其运动的初步分析得出的(38),正如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所申明:“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39)因此,马克思基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出的这一理论逻辑,其实是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找到一种哲学的思辨的表达。 总之,阿尔都塞将《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归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从而归于本质上是“主体的经验主义和本质的唯心主义”的一般人道主义,无论在哪方面均难以成立,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臆断。他将“断裂时期”前的马克思思想冠以“人道主义”而加以否定,不啻于宣布人道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将“断裂时期”后的马克思思想冠以“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则不啻于将马克思哲学改制成一种敌视人的学说。 哈贝马斯在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重建》)一书中,也提出了与阿尔都塞的观点相类似的论断,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中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种“唯心主义概念”(40)。另外,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质疑,即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生活的再生产特征,只能作为区分原始人与动物的标志,而不能作为区分人(非原始人)与动物的标志。哈贝马斯之所以提出这一论断,是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只是一种遵循工具和战略行为规则的目的性的工具活动,反映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关系,它不包括遵循主体相互间公认并得到习俗保障的行为规范的交往行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如果要使劳动这一尺度具有普遍性,必须补充体现交往行为的“家庭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的组织原则”。据此,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断言,作为社会进化的一种标志,社会劳动结构只是与古老的人类进化阶段相联系,而交往中的“角色行为结构”则“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41)这意味着,社会劳动最多只能构成原始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不能构成此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此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主要是交往活动。 笔者以为,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et)的理解,充分强调和揭示人的交往活动的作用,特别是道德-实践规范结构的作用,是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的。但是,他在《重建》一书中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上述解读以及对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的关系的理解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偏差。 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表现为经济学形式的物质实践概念)理解和诠释为单纯的目的性或技术性的工具和战略行为,将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排除在劳动概念之外,是对马克思的严重曲解和误读。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特别提出和反复重申了他的这一原则性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42)由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是通过劳动者与自身的关系即劳动活动本身连接起来的,所以这一命题意味着:劳动中所发生的、所结成的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是劳动者与自身的关系,从而也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的实现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一命题,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时明确指出:“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43)我们也看到,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内涵即劳动者同劳动对象、生产行为、类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的四项规定中,实际上涉及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即人与劳动产品、对象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后者,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文中将其具体表述为“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44)。而在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中,已经以某种形式蕴含和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交往关系。因此,显然不能将交往行为排除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之外,将其视为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而且是单个的、孤立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单向度的关系。如果作这样一种理解,无疑是对马克思劳动、物质实践概念的狭隘化和片面化。 哈贝马斯似乎也意识到他的这种片面解读对于马克思来说过于牵强,于是也退而承认:“当然,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不仅是一个个的个人的工具行为,而是不同的个人的社会协作。”(45)但是,出于其理论建构的需要,他又转而片面解释社会协作的内涵,强调社会协作“是根据战略行动的规则形成的”(46)。言外之意,它不是根据道德-实践的规则形成,因而也与交往行为无关。这样,社会协作就被作为完全不同于交往活动的东西而被排除了。其实,社会协作就已经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一种物质交往活动。而哈贝马斯所谓的道德-实践规则和工具-战略规则,在现实性上是融汇于物质交往活动中的,前者在一定意义上还服从于后者,两者只能在人们的理论思维中才能被区分开。 这样,就物质交往活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而言,或者就一般意义上的交往活动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应该说,前者是内在于后者之中的,并不是独立于或脱离于后者而存在的。它就是后者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的一个方面。换一种表述,就其哲学底蕴而言,哈贝马斯所诉诸的、体现为交往活动的主体间性本质上也是一种主体性,只不过是同抽象的单一主体的主体性(Intrasubjektivitaet)相对立的一种主体性。作为一种现实的主体性,它内在于实践的内在矛盾——主客体矛盾之中,体现真实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并没有脱离和超越主客体矛盾的框架。它实际上否定的只是抽象的单一主体的主体性以及主客体关系原则的绝对化的形式。 阿伦特同哈贝马斯一样,也否定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她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由于只有一部分人直接从事劳动活动,如此用劳动来定义人类,“没有表达人类共同生存的全部经验”,势必会将劳动者以外的人变成“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导致“不能称为人类的人”的存在。(47) 笔者以为,阿伦特过于强调了劳动这种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只看到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于劳动仅是从其特殊形式、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去理解,而未看到劳动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实践活动,即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等其他社会活动的活动,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本质。 阿伦特还特别强调劳动具有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会丧失其强制性。因此,在她看来,马克思对劳动的赞美,“隐含着对强制、自然的必然性的赞美”,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攻击”,而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的说法,实际上却是从以往传统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绝望的结论”(48)。阿伦特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基于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的二元对立而得出的。在她那里,自由是外在于“自然的必然性”和强制的。如此一来,自由始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而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由是从“自然的必然性”中、从强制性的劳动中赢取和获得的,故而马克思在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9) 如果将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劳动观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质疑,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基于西方文化中传统劳动观的立场。 就现代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作出的回应而言,海德格尔的评论是尤其值得重视的。这些评论围绕马克思哲学同虚无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展开,其内容集中体现在这一核心论断:马克思哲学“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对此,既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果。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之虚无主义的评判是在存在论之维即所谓“存在之真理”的视阈提出的,因此,也理应和必须在存在论之维来给予回答和辨析。 在《路标》中,海德格尔肯定,“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其历史观比其他历史学说都要优越,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却未能认识到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从而未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高度。海德格尔还肯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表达了“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50)。但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在该文中又认为,包括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在内的一切人道主义本质上都是一种遗忘了存在的形而上学。这表现在,它们对人的本质的规定都以对存在之真理不加追问的存在者解释为前提,即它们在规定人之本性时不仅不追问存在与人的本质的关联,甚至还阻止这个问题(51)。在二十多年以后,在《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明确提出,鉴于马克思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一必须被视为形而上学的命题,以及接纳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所得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最后结论,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人来说不再存在”,表明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52)。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哲学为虚无主义”是根据他对虚无主义的基本界定即所谓对“存在”的遗失这一标准作出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存在之真理失落了,它被遗忘了。”(53) 那么,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一判定能够成立吗?马克思哲学与“存在”到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究竟是如何看待和解决存在问题的?笔者以为,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有必要先行追溯、考察构成海德格尔之虚无主义标准的若干前提,即:究竟何谓存在?存在存在于何处,或存在与人之“此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的统一性体现在哪里?在既有的通常见解中,这些问题似乎已经被海德格尔阐释清楚了,因而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实际上,如果彻底深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有关“存在”的这些问题并未完全被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之光所照亮,有的还处在晦暗不明甚至某种黑暗之中。 何谓“存在”?因其不可道说性,海德格尔似乎刻意回避对其作出直面的明晰的回答。但是尽管如此,因其道说的不可避免性,在某些场合他也对其作出了一些描述。举其要者,例如:存在是“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54)的那种规定者;“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的存在不是存在者的种,但却关涉每一存在者。……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一切可能的具有存在者方式的规定性之外。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dens[超越]”(55);“存在是存在本身”(56);存在(该词因其不可道说性而被打叉——引者注)“是指示着(天地神人)四重整体那四个区域,以及它们在打叉位置上的集聚”的“符号”(57);存在是其被遗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对象、起因和标志,因而可以被命名为“事件之在”(Ereignis)(58);“存在已经……自行预示”(59);等等。 我们可以得到的界定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基本规定和超越,是由天、地、神、人四大区域构成的整体世界的统一性,存在是自在自为者。但是,这种有限的界说显然并不能够令人感到满足。因为即便我们得到上述界说,我们还是不甚清楚和了解:存在到底是一种实体还是一种属性?是一种实存还仅仅是一种思维抽象,抑或同时是两者?存在作为自在自为者,是存在于存在者之内还是存在于存在者之外?等等。 对“何谓存在”的进一步回答显然必然关涉到存在在何处、它与存在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何关联等问题。对此,海德格尔当然也给出了一些论述和说明,这里我们不妨尽量完整地列举其要点:其一,人在其存在中对存在具有存在关系,人存在论地存在,人的存在者状态结构包含存在之领会的规定性。海德格尔认为:从存在者状态上来看,此在“这个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者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于是乎,此在的这一存在机制中就包含有:这个此在在它的存在中对这个存在具有存在关系。……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此在作为存在者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存在论地存在。”(60)“此在本质上就是:存在在世界之中。因此这种属于此在的对存在的领悟就同样源始地关涉到对诸如‘世界’这样的东西的领会以及对在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了。……此在的存在者状态结构包含着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之领会的规定性。”(61)其二,人内立于或置身于存在的敞开状态之中。海德格尔说:“人是这样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是通过在存在之无蔽状态中保持着开放的内立——从存在而来——在存在中显突出来的。”(62)海德格尔明确地说明,他之所以选用“Dasein”这个语词,就是用其来意指人置身于敞开的存在之中(63)。其三,“人不仅被包含在存在之中,而且,存在需要人之本质,存在依赖于对自为(das Fuer-sich)假象的抛弃,因此它也就具有另一种本质”(64)。其四,“存在之本质于自身中就是那种与人之本质的关联”(65)。其五,存在是包罗万象者,人是特殊存在者,人之本质中已经包含存在与人两者的关系。海德格尔着意指出,“如果我们以为存在是包罗万象者,同时仅仅把人表象为其他存在者(植物、动物)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并且把这两者置人关系之中,那么,我们对存在也就言说得太多了;因为在人之本质中已经包含着那种关系,即与那个通过关联——在使用或需要意义上的关涉——而被规定为‘存在’、并且由此而从其所谓‘自在自为’中获取的东西的关系”(66)。其六,“人在其本质中乃是存在之记忆”,人之本质属于存在。其七,“人参与构成了存在之区域”(67)。 综括海德格尔的以上论述,我们或许可以清晰得到海德格尔眼中存在与人之间的某种同一性关系:存在包含人在自身之中,或者反过来说,人被包含在和参与到存在之中;存在是包罗万象者,人是特殊存在者,无论在存在之本质中,还是在人之本质之中,都含有存在与人两者之间的关系;领悟存在是人的状态结构规定和天然使命。但是,即便海德格尔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我们仍不免有问题要追问:如果说,无论在存在之本质中,还是在人之本质之中,都含有存在与人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含有是由什么决定和赋予的?或者说,是由何者使然,来源于何处?领悟存在这一人的状态结构规定性特别是可能性,又是由谁规定和植入的?诚然,海德格尔明确地肯定:人存在于存在之中;人之本质包含存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人存在于存在之中,并不等于存在存在于人之中;人之本质包含存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等于人之本质包含存在本身。那么,存在究竟是否存在于人自身之中,抑或完全存在于人自身之外?恰恰是在这一最具有实质性的问题上海德格尔没有给予明晰的回答。根据海德格尔的相关思考,或许我们有理由断言,尽管他将存在与人的关系看作包罗万象者与特殊存在者的关系,以及反复强调在存在和人的各自本质中都含有存在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他那里,实际上存在本身依然存在于人自身之外而不是存在于人自身之内。换言之,存在并没有真正被人这一“此在”所分有。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解读中获得证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7卷中通过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讲述了一个洞穴人在洞穴之中和洞穴之外所必然遭遇的不同境遇的故事。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的这一“洞穴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柏拉图关于真理即“无蔽”的学说。他通过对柏拉图的这一“洞穴隐喻”的再解读强调,无蔽者及其无蔽状态在人的任何居留区域内总是公然“在场”的,尽管它可以以不同程度或等级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场化就是存在的本质”(68),其基本特征就是无蔽状态。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无疑确实表明了柏拉图对存在者与作为理念的存在两者关系的一种理解。这一比喻也能够有力地说明存在作为无蔽者,在人这一具体的存在者的居留区域里总是在场的。但是,问题在于,存在在人的居留区域里的在场,说到底仍是存在在人之外的一种在场,而并不是存在在人自身之内的在场。因此,它只能用来说明人存在于存在之中,而并不关涉也不能说明存在也存在于人之中。可见,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与存在(“可见者”与“光源”)、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已经被分离开和二重化了。存在无论如何无蔽地在人的居留区域里显现,都是在人自身之外发生的,而非在人自身之内发生的。鉴此,有理由说,柏拉图是将存在与存在者相分离的始作俑者,而海德格尔则一开始就追随柏拉图而步入了一种二重化的陷阱。实际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并非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在于对存在的遗忘,而是在于将存在与存在者特别是“人”这一特殊存在者相分离,将其二重化。这样一来,存在就只能在存在者外部发光,从而至多使存在者显现其外观,而不能在存在者的内部发光,使存在者本身得以透察。 在我们花费许多笔墨澄清海德格尔对马克思有关虚无主义之评判的前提之后,就可以较为容易地对这一评判本身即“马克思将人的根本(人的实践活动)归结到人”,以及“用物质实践概念来取代‘存在’概念”到底是否虚无主义了。 马克思诉诸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劳动、物质实践,并由此出发来看待对象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提出人的劳动、物质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要求“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将以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感性世界视为超感性世界的根源,用物质实践取代了以往哲学家们的抽象的“存在”,用人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取代了以往哲学家们的抽象的“整体世界”,从而彻底否定和扬弃了感性世界之外、之上的超感性世界的“存在”,克服了西方传统思想中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二元对立。就此而言,特别就彻底否定和扬弃了以往传统形而上学中脱离“人”这一“此在”的“存在”而言,马克思的主张无疑是一种虚无主义,而且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但是,这是一种合理的虚无主义。 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而言,即就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物质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现实基础,是“人”这一“此在”与自然、与整体世界相统一的现实基础而言,特别是就马克思具体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资本统治的根源及其扬弃路径而言,那么,马克思的主张恰好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彻底的反虚无主义,不仅反理论的虚无主义,而且反实践的虚无主义,即反资本的虚无化。因为他找到和指出了“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物质实践,通向和不断接近整体世界、接近终极的“存在”的真实的、现实的道路。如前所述,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作为自然存在和自然界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这样,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意味着: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为一体的,人的存在是整体自然存在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整体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因此,整体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彼此交融、密不可分,整体自然存在之奥秘就存在于人的存在之中,存在于人的劳动、实践之中。 当海德格尔断言“其他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69)时,其实他所表达的是与马克思相同的思路。也就是说,他对“存在”的追索所采取的从“此在”着手的路径,与马克思通过“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来观照进而把握整个世界历史这一路径,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对存在的真实把握只能通过一定的存在者,特别是人这个特殊的存在者,舍此别无他途。即使以往哲学家们直接关注和研究的都是存在者,看上去似乎遗忘和失落了存在,然而实际上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涉到存在,甚至也可以说都是对存在的一种研究。所以,海德格尔关于以往“一切哲学都沦于存在被遗忘的状态中”的断言未免夸大其词、危言耸听。 ①⑤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97-119、147-177页等;第241页。 ②⑥⑦⑨⑩(11)(12)(13)(14)(15)(16)(17)(19)(28)(32)(35)(36)(39)(42)(43)(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1页;第160、162、163、205页;第157页;第162-163页;第163页;第186页;第211、163、191、193页;第196页;第188页;第187页;第162页;第193页;第196-197页;第528页;第162页;第170页;第162页;第111页;第165页;第165页;第164页。 ③(47)(48)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25页,并参见第11-15页;第25页,并参见第18、17页;第28、4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页。 ⑧马克思后来在1857年撰写的《〈政治经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将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归结为生产本身的内在要素。另外,关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写作时间,学者们意见不一。日本学者中川弘、苏联学者拉宾等主张《摘要》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这一观点近年来受到国内学界一些学者的关注。本文仍持《摘要》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之前的观点,但在总体上将这两者视为一个在内容上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2页,译文有修订。对于抽象主体主义和抽象客体主义的具体表现和主要代表,马克思在文中并未具体论及。笔者以为,似可以以费希特哲学作为前者代表,而以旧唯物主义作为后者代表。 (20)马克思在《手稿》中特别说明,所谓私有财产,其历史形式就是地产和资本。“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1-182、187页。 (21)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当时所持哲学立场的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52页。 (22)笔者在拙作《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曾对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诠释的主要代表奥伊则尔曼的有关《手稿》的评论进行过讨论,批评其将马克思言说的人的本质解读为不变先验物和“预先给定物”,并称其未能同人本主义和启蒙学说划清界限,是必须加以放弃的“本体论倾向”的观点。见《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44-246页。 (23)在汉语中,费尔巴哈的哲学通常被译为和称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事实上,费尔巴哈使用的称谓自己哲学的概念只有Anthropologie和Anthropotheismus这两个语词。Anthropologie在汉语中通常被译为“人本学”,与此相适应,Anthropotheismus通常则被译为“人本主义”。但是,这种译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也在某种意义上歪曲了费尔巴哈的原意。在德文中,Anthropologie意为“人类学”,并无“人本”的涵义。与此相类似,Anthropotheismus也无“人本”的涵义,应译为“人类学主义”。另外,马克思在《手稿》中使用的“彻底的人道主义”或“完成的人道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一词,不是费尔巴哈使用的Anthropotheismus,而是Humanismus。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语词已经表达出他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人类学主义的超越。 (24)(25)吴晓明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学者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503、498等页;第503页。 (26)Christoph Jamme und Helmut Schneider,(herg.)Mythologie der Vernunft,Hegels aeltestes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Frankfurt am Main,1984,S.11.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3、11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70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4页。 (3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4-25页;第170页。译文有修订。 (34)参见笔者《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第58、61-70页;《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振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2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 (38)马克思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手稿》中[笔记本II][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的概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2、177页。 (40)(41)(45)(46)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52页;第140-147页;第140页;第14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926-927页。 (50)(51)(56)(57)(59)(62)(63)(64)(65)(66)(67)(68)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401页;第376以下各页;第389页;第483页;第435页;第442页;第439页;第483页;第471页;第479页;第484页;第252、259页。 (52)费迪耶等:《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53)(58)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269页;第263页。 (54)(55)(60)(61)(6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第8页;第47页;第15-16页;第17页;第17页。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文; 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