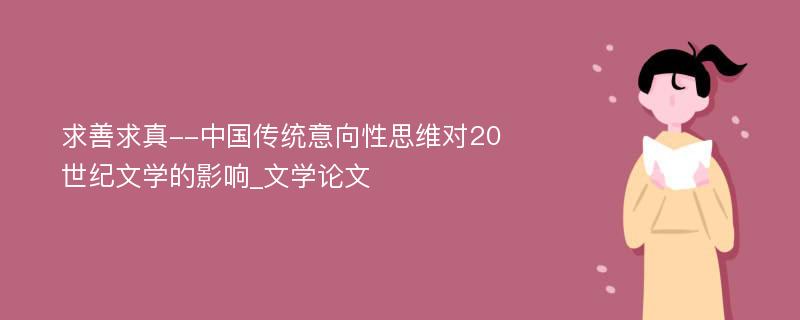
向善与求真——中国传统意向思维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意向论文,世纪文学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4-0026-05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历史的演变中也具有更大的稳定性。20世纪初,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然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部分受到了荡涤,但是其中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是保存了下来,并对20世纪新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儿,我们主要探讨一下中西思维在认知追求上的差异,即意向思维与求真思维的差异特别是前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善与真:中西思维追求的差异
中国传统思维中有一个很有特点的方式就是意向性思维。所谓意向思维是指主体更倾向于用情感判断代替认知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传统宇宙观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看来,人和宇宙万物都来自于道,主体自身就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因此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就不必求之于外在的探索;只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不被小我所蒙蔽,就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能反身而思,便能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中国人宇宙观的这个特点内在地决定了传统思维不可能是一种以求真为目的的外倾思维,而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内倾思维。
另外,在传统哲学中人和万物都被认为具有一种道德、伦理的本性;而后者既是人的本体也是宇宙的主体,这样人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无往而不具有道德、伦理的特点。因此古人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将情感意向和认知放在同一个过程中;思维本来应当是一个逻辑运思和推理的过程,但是古代中国人受特殊宇宙观、世界观的影响,让主观情感较大地影响了思维进程;思维更多地表达了主体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表现了主体情感的好恶,它所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一位研究者指出:“传统思维的特点,则是把认知和情感融和在一起,知、情、意处在合一未分化的状态,其中,情感因素起重要作用。这就使传统思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情感需要所决定的方向而发展。”[3](P29)中国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泛道德化的宇宙观,对其认知方式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古人看什么都是道德的,一些平常的自然现象也被与某种道德行为联系起来,例如人们常将地震和日食看作上天的某种警示。当知、情、意被混淆在一起后,一方面人的认知就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了,另一方面,既然道的本体就存在于人自身中,人也就没必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认识自然的过程中。
西方哲学在很早就设立了一个人与自然二分的意识,即将自然作为与人不同的对象,去认识它、了解它、改造它和征服它。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哲学在很早就表现了强烈的求真诉求。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大部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观测星象,研究数学,探讨数的比例与谐音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原则。其后西方哲学家像层层剥笋一样将这个思考不断地深入,提出了一系列的范畴和理论假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这种思考最终都是以探讨和认识世界为目的的。西方文化正因为有一种强烈的认知渴求,因此它在思维中优先考虑的总是认识和把握对象的特点,而不是急于让主体作出评判。
中西哲学和认知方式的这种差异对美学和文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学上,西方美学更多地表现为美真相兼,而中国美学则是美善相兼。所谓美真相兼,就是将真看作美的必要条件;西方作家总是突出强调“真”的价值,这个“真”不仅是与生活的相似,它还提示了文学的认识价值,即文学作品要能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如果说人们在自然科学中了解科学知识,那么在文学中就可以认识社会方面的知识。“美从属于真,这个思想支配西方文艺界直到19世纪,‘写真实’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最心爱的口号。”[4]而“美善相兼”则是将“善”作为美的必要前提。《论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据郑玄解释,《韶》是赞美大舜的乐曲,舜从尧的禅让取得天下,以文德致太平,所以得到孔子的高度赞许;《武》则是歌颂周武王的乐曲,武王以武功定天下,在孔子看来,不及文德之值得推崇,所以说它美而未能尽善。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物即便被非常逼真地刻画出来,而如果他没有善的品性就不会受到人们的赞美。
中国传统的意向性思维对古代叙事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价值判断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作家不是全力地认识自然与社会,客观真实地反映它,而是习惯于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要么急于表达某种观念和认识,要么追求一种教化的目的;作家不是让作品像镜子一样地反映生活,而只是要在生活中选取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古代作家还特别注重从道德的角度切入生活,其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泛道德化倾向。
1.突出关注文学的教化功能。这种倾向在中国文学的源头上就已经表现出来。孔子曾有“兴、观、群、怨”说,汉儒要求文学要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王充要求文人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曹丕则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那种以教化为目的的故事就已经相当常见了。如董永卖身葬父、郭巨埋儿、楚僚为事后母卧冰求鱼、浪子回头的周处以及宁自刎而死誓不从盗的乐羊子妻等等。在宋元拟话本小说中,一些作家更是非常自觉地承担起道德说教的任务。
2.作家观照生活的视角比较多地限制在道德与伦理中。文学作品本来应当像生活一样丰富。但是在古代,意向性思维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作家在创作中无意深入地认识生活、挖掘生活,而是急于说出对生活的某种认识,作出某种评判,特别是作出某种道德评判,这样作家观照生活的视野就大大地收缩了。古代作家特别喜欢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切入生活,他们的作品也写到爱情和婚姻,但是关注的并不是爱情、婚姻本身,他们不会用很多笔墨去写青年男女在爱的等待中的痛苦与焦灼,得到爱情后的兴奋与狂喜;或者通过爱情展示人的生命本能在灵与肉、爱与欲冲突中的凸显与爆发,而更多地侧重于对爱情、婚姻的道德评价,即男女双方是否遵守了一定的道德原则,作家热衷于抨击那些负心汉和薄情女。古代作家也写到战争,但是他们更关注的是战争双方道德定位,即哪一方是“替天行道”,哪一方是皇室正统,双方的主帅的行为是否符合“忠、孝、仁、义”的标准;而作者的同情往往完全放在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一方。古代作家从道德、伦理切入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这种视角的单一性决定了古代文学不可能多角度的反映生活,即便它涉及了多方面的题材,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非常狭隘的。
3.人物道德面目的两极化。在生活中人的道德表现是非常复杂的,好和坏往往混杂在一起而且常常发生变化;而古代作家由于受到意向思维的挟制,突出关注的往往是主体对对象的情感态度和道德评价,他们不能虚空心灵、藻雪精神,不带任何偏见地观照外物、摹写外物,这样他们从主体的需要出发,夸大人物的某些道德特征也就在所难免了。
西方作家没有意向思维的传统,他们不是急着评价对象,对人和事作出道德评判,而是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注视着生活,诚心诚意地写出他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心态是放松的,即便对所谓反面角色他们依然能依平常心待之,实事求是地既写出他们的缺点也写他们的优点,表现出了一份在我们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大度和宽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拿破仑是发起者,他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也是作者的敌人,但是托尔斯泰写到拿破仑时并未把他写成一个恶棍,而是很客观地描写了他的行为和心理。
二、意向思维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意向思维在20世纪的文化转型中,受到了强调理性和逻辑的西方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它也出现了面向现代的变化与转换,但是,思维方式具有更强的历史继承性,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意向性思维并没有在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中消失,相反它与来自西方的求真思维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有时,它还会在文学中顽强地呈露出来,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强大与威势。
“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开放的时期,西方文化大量引进,中国文化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于是传统的意向思维受到某种抑制,文学显示出客观化的倾向。在现代文学史上,即便像茅盾这样政治倾向上十分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生活仍有相当明显的客观性;作家希望表达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是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不是作者把它特别指出来的。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他们一边面临着官僚、买办资本的追逼、压迫,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工人的造反,在各种力量的前后夹击下,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中。小说没有特别丑化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家,而是把他写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的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他在经营上的强干和内心的空虚;作者有意把他写成“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但是他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又确实是生不逢时,时代不允许他成为民族工业的英雄。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定步履维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必将充满困难。茅盾的创作与西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20世纪上半叶,不利于克服旧思维方式的因素也不少。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充满了内忧外患,中国人在大梦醒来看世界时,发现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于是中国作家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一些作家或承担起启蒙教化民众的任务,或面向邪恶大声疾呼,希望借文学之力行一些干预之作用,其中自然也有旧的思维方式在发挥作用。总的来说,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倾向于在创作中表达主观感受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特点。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文坛上最流行的是“问题小说”,这种小说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特点;其作家大都是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西方的观点看中国社会,从中发现了种种问题;他们急于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唤醒民众,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于是他们的作品广泛地涉及了婚姻家庭、妇女贞操、卫生习俗、阶级压迫、劳动者权利等多方面的问题。“其时因问题的尖锐性是第一位的,相应便减少了对小说形象化的要求,造成许多‘问题小说’比较概念化,存在着文笔空疏、人物成为作者某种‘主义’的传声筒等弊病。”[6](P62)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虽然有茅盾、老舍这些倾向于客观描写的作家,但是也有像蒋光赤、洪灵菲、楼适夷、钱杏村、郑伯奇等一大批作家,这些人大都兼有革命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而“自觉地运用文学来为革命呐喊,在急剧的变革年代里,以特殊的热情,写出‘思想大于艺术’的具有重大社会效果的作品,是他们的共同特点”[6](P295)。1937年,抗战爆发后,以往具有不同主张、倾向的作家开始自觉聚集在抗战的旗帜之下,文学自然又向时世和政治靠近了一大步。“‘救亡’压倒一切,文学活动也就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始终关注的启蒙主题,包括‘个性解放’或‘社会革命’的主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也都暂时退出了中心位置。”[6](P446)
在从1949至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30年中,相当奇怪的是,中国文学旧的思维定势在新文学中又非常强劲地突显出来,而且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文学重新以教谕作为自己的主要功能,而把审美功能挤向了一边;人物忠、奸分明,在取消了中间的过渡以后,人物完全两极化了,好则极好,坏则极坏,已经类似传统戏曲中的脸谱人物,好人被塑造成英雄,塑造成神,坏人则被漫画化,脸谱化。
实际上,建国伊始文坛上就出现了能不能写中间人物的讨论,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其后,理论家们就热衷于讨论如何塑造英雄人物。茅盾率先提出可以以真人为基础,然后将“一切优秀品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光未然认为未能塑造出英雄人物主要是过分拘泥于现实主义手法,本来可以适当地加一些浪漫主义。周扬则提出可以使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他说:“现实主义者都应该把他看到的东西加以夸张,因此我想夸张也是一种党性问题。他所赞成的东西,他所拥护的东西要加以夸大,尽管它们今天还不很大;他所反对的东西尽管是残余了,也要把它夸大,而引起社会对新的赞成,对旧的憎恨。”[7]他认为,作家为了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的品质,应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一个现实主义者作家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到了新时期,文坛上重又出现了类似于“五四”时期那种有利于作家克服旧的思维模式的创作环境。主要原因是:首先,政治、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文革”结束后,以往流行的那种“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二为”方针,即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要求相对要宽松得多。国家放松了对作家的统制,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文坛开始三分天下,即除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外,还存在着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文学创作相对有了一块自己独立的天地,作家可以亲近政治,也可以疏离它,二者的关系变得比较随意和正常了。同时中国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那种积贫积弱的情况,不再动辄受到列强的欺辱,总是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作家也多少超脱了“国家仇,民族恨”的缠绕,在创作中有了一份难得的平常心。其次,在1980年代初,中国作家继“五四”之后又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文学,主要对象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新的引进文学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规范,当中国作家依照这些规范进行创作时,他们旧的思维方式必然受到某种抑制。事实上,在1980年代初人们谈得最多的也就是要恢复真正的现实主义,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人物性格的二元组合和多元组合。
当然在新时期,新旧思维方式仍然处在胶合状态,呈现为一种较复杂的形式;在不同时期,它们也有一个彼消此长的起伏。事实上,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新时期创作中那种倾向于说教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作家的情况看,此期在文坛上打头阵的是一批被称为“五七族”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丛维熙、刘绍棠、陆文夫、高晓声等等。这些作家1957年后被打成右派,随之被赶出文坛,沦入社会下层,许多作家备受煎熬几十年;这样当他们再次获得创作权利时,他们多年的积怨和对世事的不平会骤然喷发出来,使他们处在一种高度激动和亢奋的状态;他们所讲的故事大都充满了鲜血和眼泪,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他们平平静静地叙事那是很难想象的。其次,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作家一方面要总结历史,另一方面,他们还担负着继往开来和设计新生活蓝图的重要使命。如果说回首历史,痛定思痛会使人积愤难平,那么在一个饱受磨难的民族重新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之时,瞻望未来同样会使人心潮澎湃。概括地说,这是一个慷慨抒情的时代,而不是冷静叙事的时代。一位研究者指出:“详细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的‘叙述’方式,不难发现其‘一般’特征:情理驾御着叙事。叙事动机是表达理知、抒发感情。”“叙事在文学创作中常常被作为表现认识、抒发情感的‘手段’出现,无论是‘叙’,还是‘事’,都没有真正体现出它们本身的独立价值。”他随后解释说:“这一时期文学从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以说理与抒情为价值支点的叙事特征,是特定历史处境对文学的一种需要,也是时代对文学的一种规定。因为这是一个经历了大灾难、大幻灭之后的历史转折之际,人们有太多的感慨要抒发、有太多的问题要回答、有太多的见解要表达,悲泪与喜泪交流、幻灭与憧憬共生。”“就在这样一个噩梦初醒、人们重新获得了掌握自己乃至国家、民族命运的时候,怎能不喜出望外、心潮滚滚?怎能不激情澎湃、思绪翩翩?”[8](P266-267)
到了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时代的激情逐渐趋于平息,一方面,“文革”离人们越来越远,它逐渐成了一个模糊的记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影响也大大增强了,于是,作家在创作中的评价与说明的倾向明显在减退,他们的叙事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趋势。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199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小说都代表了这种倾向。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新时期虽然政治开明,国家大的外部环境也相对比较平稳,然而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毕竟刚刚起步,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同时又面临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许多事情并没有理顺;人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社会积攒的深层矛盾比较多,因此现在还远不是那种作家可以远离尘嚣,在纯艺术的象牙之塔中恣意逍遥的时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一方面文坛上涉及政治,揭露政治弊端的作品仍然非常多,政治仍是相当一部分作家突出关心的话题,而在这一部分作品中,作家关心“问题”胜过客观性描写的情况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另一方面,即便在新写实、新生代这样的群体中,作家也并不是纯客观地写实,中国作家那种倾向于说明与评价的本性在他们的创作中仍然是时有表现,同时他们离现实政治也并非像想象的那样远。
事实上在每一个时段中备受关注的小说主潮之外,现实主义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多数,这一点只要打开当今的各类杂志就可以看出来;现实主义作家反映来自生活的各类问题,也正是这类作品在当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改革小说自1980年代初发轫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这类作品或者直接切入改革的进程中,反映改革的必要性,也揭露它带来的许多弊端;或者从侧面表现改革对现代生活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像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菩提醉了》,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李佩甫的《学习微笑》、《无边无际的早晨》、《画匠王》,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都可以属于这个系列。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提倡作家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生活的主潮、时代的主潮,近年来中宣部搞的“五个一工程”对现实主义创作无疑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位研究者在1990年代指出:“处于我们这种政治色彩比较浓的社会,小说创作自然对政治比较关心,而生活也大量提供了这一方面的内容。由批判‘四人帮’、歌颂老干部,到揭示多年来各种政治运动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灵和肉体的创伤,由欢呼社会改革,到表现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包括选择新干部这些十分具体的政策问题,都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而一直延续到现在对‘改革家’、‘企业家’及对个体工商业者的表现。普泛点说,一切新出现的社会事物,往往都被创作者纳入‘政治’视点的程式而加以认真地表现。政治,不说永恒,起码也是我们十多年来小说创作不厌倦的中心话题,至今,已经历了好几个阶段。”[9]
[收稿日期]2002-10-10
标签:文学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