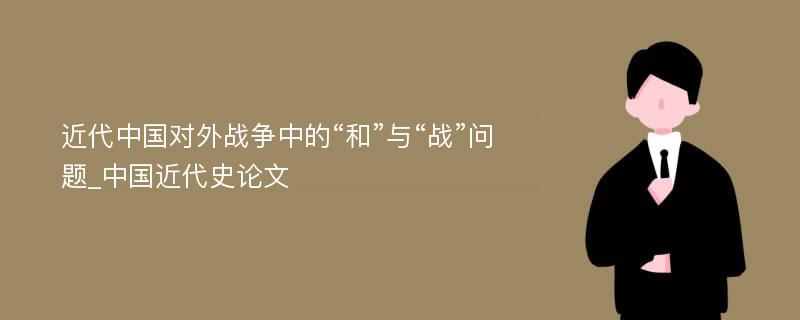
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和”、“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4)-02-0092-06
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主和”、“主战”之争。其间是非问题,史学界历来意见不一。曾在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认为:反抗近代强敌,固然极其艰难,但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誓死抵抗,不应屈辱乞和。中国虽弱,但地广人众,只要前仆后继,坚持到底,最终必能胜利。中国在近代屡屡战败,原因不全在于敌强我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苟且偷安、昏庸无能之徒当道而坚持抵抗、有胆有识之士横遭排斥,每次抵抗均不能坚持到底。若由杰出的抵抗派人物主持战事,战局应可改观。这种观点认为坚持抵抗的林则徐等是民族英雄、先进人物,妥协乞和的琦善、李鸿章等是卖国贼、反动人物。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胡绳等。
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以落后的中世纪的中国抵抗先进的近代强国,“战则必败”,最后仍需求和。“不战而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第130页;第133页、第11页;第132页。)。林则徐等坚持抵抗实为不智之举,于国于民有害无益。琦善坚持屈辱求和,不但并非卖国,反而是他的“超人处”,表明他在“知己知彼”、“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方面“远在时人之上”(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第130页、第133页;第11页;第132页。)。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蒋廷黻。蒋氏观点的理论核心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第130页、第133页;第11页;第132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面前的根本问题、根本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至于抵抗侵略,则不是当时能做和应做之事。
表达蒋氏上述观点的代表作有《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和《中国近代史》一书,二者分别发表于1931年11月和1938年,即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和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民众抗日呼声高涨之时。蒋氏那套先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然后再徐图反抗的理论显然与当时形势和民心格格不入。在许多人看来,这套理论不是书生迂腐之见便是政客欺人之谈。在史学界自然也受到冷遇。
20世纪50-70年代,反抗帝国主义仍是舆论宣传的主题,蒋氏观点几乎无人提及。但实际上,蒋氏强调学习西方的观点已被一些学者批判地吸取。对林则徐的赞扬中,“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内容日益突出。林则徐逐渐被塑造为把反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典范。
70年代末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成为舆论宣传的主题。史学界潮流随之而变。在一些“创新派”的史学著述中,反帝反封建这一传统主题被学习西方、走向近代化所取代。蒋氏著述受到一些著名学者青睐,重新出版,蒋氏对“和”、“战”问题的观点广泛流行。这时,赞扬主和派的学者把力量集中用于主和派最重要的代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一些史学论著、通俗读物和文艺作品中的形象由卖国贼一变而为忧国忧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开拓进取的一代伟人。将这一时期“创新派”有关“和”、“战”问题的论述与蒋氏对照,不难看出,其中大多数人所做的主要是循着蒋氏的观点和思路对更多的事件、人物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评论,并无观点上的创新或重要补充。大约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都对蒋氏避而不提。
这一时期,在“和”、“战”问题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少数有一定创新精神的学者,他们既不囿于传统观点,也不囿于蒋氏观点,而是从扎扎实实地弄清史实真相入手,进行独立思考,认真吸取双方观点中自己认为合理的成分,批判自己认为不合理的成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就我十分狭隘的见闻所及,我以为茅海建和他的成名作《天朝的崩溃》(以下简称《天朝》)可算其中的佼佼者。
《天朝》一书绝大部分篇幅用于对鸦片战争中一系列重要事件(包括战事和谈判)和人物进行细致考证和具体剖析,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众多学者对此书的赞赏大多集中于此。
和蒋氏一样,此书对鸦片战争中“和”、“战”问题的研究首先从为琦善洗刷卖国罪名入手。但此书对琦善的进一步分析却与蒋氏颇有不同。此书对琦善及其他“主和派”重要人物在战争中和战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指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页。)琦善在谈判中曾千方百计企图诱使英方让步,但都失败了,他自己则在英方压力下步步退让,“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蒋廷黻说,琦善与义律签定的《川鼻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川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4页;第130页、第133页;第11页;第132页。)。《天朝》一书则指出,义律提出的《草约》的确没有《南京条约》那么苛刻,但这并非琦善谈判的结果,而是义律从一开始就自作主张对英国外相巴麦尊预先拟订的条约草案进行了修改,阶低了要价(至于义律为何这样做,此书表示尚待查考)。尽管如此,这个《草约》对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仍有严重损害,琦善知道道光帝此时绝不会接受,因而未敢签字。后来,巴麦尊也拒绝承认这个《草约》。此书指出,既然《草约》并未成立,“又何从称之为外交胜利?”(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
此书对“主和派”其他重要人物如伊里布、耆英等等也逐一进行了扼要而细致的考察,指出他们都是在战事失利后心生畏惧才一意乞和,并非有什么“超人的”见识。他们在谈判中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道光帝和英国两种反方向的巨大压力下尽力敷衍、蒙混,以求自保。由于英方十分骄横,毫不让步,他们实际上所能做的只是对道光帝百般哄骗,把战败谎报为“获胜”,把英方的骄横说成是“恭顺”,把英方强迫中方接受其侵略要求说成“向大皇帝乞恩”,把英方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侵略条件说成“并无大碍”,竭力诱使虚骄而又无知的道光帝接受英方条件。道光帝在对战事完全失去信心后也就接受了他们的诱导,以阿Q式的姿态宣布同意对英国“施恩”。这就是“主和派”在外交中取得的成绩!此书在考察伊里布时指出:“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4页。)在考察琦善时指出,琦善在战后复出的11年中,“未为中国的变革做任何有益的事”,说明“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61页。)。这些评沦显然也适用于其他“主和派”人物。
总之,此书通过对琦善等人求和活动的具体考察和剖析,有力地批驳了蒋廷黻对主和派的赞誉。在这方面,此书与那些对蒋氏观点亦步亦趋的著述相比,显然要高出许多。
另一方面,此书对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给予林则徐等主战派的过高赞誉也进行了反驳。此书列举事实说明,林则徐虽在了解西方方面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他本人对西方的认识仍很肤浅,甚至有一些严重错误,如以为英军毫无陆战能力等。他的御敌方案仍是旧式的、落后于时代的,在实战中必然失败。人们常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林则徐首先提出的,此书对此也表示怀疑,认为此说无直接证据,也不能从林则徐的活动得到证实。从林则徐关于建立水军的设想看,他所设想的船炮并非仿造西方新式船炮,而只是对中国旧式船炮略加改进。他还打算雇用福建“民商之船”充作战船。此书认为,林则徐设想的水军即使建成,也“只是传统水师的强化,并非近代海军”(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25-427页。),不能起到“制夷”的作用。此书还提出,林则徐在战后复出期间,也并没有学习西方、改革现状的建言,更没有这方面的行动。此书的结论是: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64页。)。此书对关天培、陈化成、定海三总兵等被传统观点高度赞誉的抗英将领也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他们誓死抗敌的精神固然可敬,但他们那套陈旧的作战方式在近代强敌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把他们的战败完全归咎于主和派的破坏是牵强附会的。
《天朝》一书对鸦片战争中一系列事件和人物的考察,无论在史实考证上还是在具体分析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赏。但是,此书作者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厘清鸦片战争中的一些具体史实和对一些具体事件、人物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评论,甚至也不仅仅在于研究鸦片战争本身。(尽管此书副标题为《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对鸦片战争的具体考察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不仅用以指导对近代战争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用以指导人们应对今天和明天可能遇到的重大国际冲突。作者在“本书的主旨”一节中首先联系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提问:“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页。)接着回答:“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页。)接着,作者又针对当前的现实提醒人们:“历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我们面前的一切,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中国依旧落后。我们还经常面对着那些曾困扰前几代人的老问题。”(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页。)作者希望人们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得出结论:中国落后和保守必然失败,当时中国人的使命是致力于近代化而不是进行徒劳无益的抵抗。作者还进一步提醒人们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现实问题:既然现在“中国依旧落后”,如遇强敌入侵,我们应如何应对才不致重犯一百多年前的错误?“主旨”一节中这些简短而意味深长的话,乃是全书点睛之笔。作者还在其他一些章节多次就落后国家反抗近代强国的战争能否取胜和是否应该抵抗作了一些理论性论述,作为对主旨部分的补充。不少学者对此书的赞赏集中于此书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具体考察上,对此书主旨却很少涉及,这恐怕难免使作者有“买椟还珠”之憾。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奇怪。此书对事件、人物的具体考察确有不少超越前人之处,足以引人注目。其理论性论述却在观点和思路上基本沿袭蒋氏,只是论述更细、与事例结合更紧而已,对读过蒋氏著述的人自然缺乏影响力。
鉴于蒋氏关于“和”、“战”问题的观点近年来颇为流行,而《天朝》一书对蒋氏观点的阐述和论证特别详尽,这里不妨对《天朝》一书的主要理论观点讲行一些讨论。
《天朝》一书提出的理论性问题主要有二:一、落后的中国是否有可能战胜先进的侵略者?二、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
此书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首先就战争的实质发表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尽管现代人已对战争下了数以百计的定义,但是,战争最基本的实质只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页。)依据这一见解,此书认定: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并由此认定:“鸦片战争是清军与英军的军事对抗,要判断清王朝能否获胜,首先就得考察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并参照英国远征军的力量,进行评估。”(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页。)随后,此书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三个方面进行评估,指出:清军武器装备远比英军落后,军事制度又极不合理,而且从上到下“已经腐败”。结论自然是:清王朝的军事力量远不如英国,抗英战争必败。这一系列论述如此合乎逻辑,似乎无可置疑。但值得考虑的是,其大前提——对战争实质的判断是否正确。
人们在观察战争时,首先看到的自然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但是,事物的实质并非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的,而是深藏在事物内部,否则,揭示事物的实质就是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轻易做到,无须深入的理论思维了。德国杰出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实质的看法显然与《天朝》的作者大不相同,他在《战争论》这部名著中反复强调:“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1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页。)克劳塞维茨反对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战争,而《天朝》一书却主张只从军事角度看战争,二者究竟孰是孰非呢?
再就战争的具体内容而言,是否仅仅是“两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呢?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力量有“军队[直译为‘战斗力量’]、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页。),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如果我们稍稍考察一下中外战争史,就可看到,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力量还不仅限于克氏提到的三种,至少还应包括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等,而且,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之间又常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有时相互助长,有时相互削弱。正因为如此,战争进程才常常复杂多变,难以预测。如果单凭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评估就能判断战争胜负,那么,预测胜负的任务只需交给一些稍具军事知识的统计工作者去完成,而无须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和一批专家去反复研究、论证了,历史上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家因预测失误贸然发动战争而自食恶果了。
就军事力量本身而言,它也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常在其他多种力量影响下发生变化。战争开始时军事力量占优势的一方到战争后期有可能转为劣势,反之亦然。同一军事力量在不同条件下所能发挥的作用往往也有很大差别。如:在战争得到民众坚决支持时,军事力量往往能超常发挥,在战争受到民众坚决反对时,军事力量会受到很大遏制。
在评估军事力量时,也不能单从正规战的角度来评估。有的军队长于正规战而不适应游击战,有的军队则相反。
总之,战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绝不能把它简单化、公式化。战争的胜负受多种因素影响,绝非单凭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评估就能判断。在美国与越南的战争、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中,美苏的军事力量均占压倒优势,但他们都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被迫撤军,灾际上是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于越、阿领导者和民众不甘屈服,坚持长期的游击战,而美苏民众反战情绪却日益高涨,政府无法把这种旷日持久、代价高昂、丧失民心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
《天朝》一书在分析鸦片战争时,不仅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了评估,还对历次重要战役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对关天培指挥的虎门之役、葛云飞等三总兵指挥的定海之役、颜伯焘主持指挥的厦门之役作了详细剖析,指出:尽管关天培、葛云飞等备受传统观点赞扬的爱国将领率领士卒浴血奋战,直至壮烈牺牲,尽管颜伯焘对厦门防务“事先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构筑了“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与伦比的”防御工事(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8、336页。),战时又亲自“坐镇督战”,但都未能避免惨败的结局。此书由此得出结论:“清军拒战必败。”(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8页。)“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43页。)这些结论是从一个个战役中总结出来的,似乎极具说服力。但是,问题在于:对战役的分析并不能等同于对战争的分析。
战争与战役分属不同的层次,其运行规律不尽相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比战役复杂得多。在阿苏战争中,落后的阿富汗部族武装绝不可能在正规战役中取胜,但却可以用长期的游击战迫使苏军无功而返。同为反侵略战争,阿苏战争与中英鸦片战争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这显然不能简单地用落后与否来解释。事实上,阿富汗部族武装与苏军的差距远远超过中英差距。阿富汗能免于失败,主要是由于阿富汗部族首领虽然落后,却尚有不甘屈服、坚持反抗的斗争精神,并在民众中有颇大的号召力,能领导民众坚持长期艰苦的抵抗,而腐朽的清朝当权集团既不愿承担长期抗战的艰苦和牺牲,又与民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不敢让民众武装起来,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民众进行持久抵抗。《天朝》一书把中国战败单纯归因于落后,不仅不谴责清政府屈辱妥协,反而认为清政府根本不应抵抗,似乎欠妥。
下面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个问题的前提——注定要失败——不能成立,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讨论的价值。但我想,既然有不少人认同落后者“拒战必败”的观点,那么,对由此引申出的这个问题仍不妨加以讨论。
《天朝》一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4页。)“清王朝此时最为明智的策略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应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才可与英国较量。”(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页。)“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军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7页。)“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9页。)
这些回答显然不能算是什么创见。几十年前,蒋廷黻早已作过同样的回答。一百多年前,李鸿章也早就作过类似的回答。归纳起来,他们提出的方案有二:一、放弃抵抗,尽早与侵略者“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二、暂不抵抗,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再战。《天朝》一书认为,这乃是“最为明智的策略”。
但是,这些“策略”果真有效吗?先看第一方案:放弃抵抗,争取一项“相对有利的和约”。蒋廷黻曾以《川鼻草约》为例,企图证明这个方案是高明的,有效的。但《天朝》一书用史实驳倒了这个例证,指出:战前,英外相巴麦尊“就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06。)。义律在与琦善谈判时擅自降低了一些要价,迅即遭到严厉斥责,并被撤职。《川鼻草约》也从未得到英政府承认。此后的谈判中,英方始终坚持巴氏预拟条件,从不让步。看来,以放弃抵抗来换取“相对有利的和约”只是一种幻想。中外战争史中,被侵略者以顽强抵抗迫使侵略者降低侵略要求的事例并不少见,以放弃抵抗赢得侵略者让步的事例却闻所未闻。蒋廷黻举出的唯一一例已被《天朝》一书驳倒,《天朝》作者虽熟悉中外战史,却也未能另行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
再看第二个方案:“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再战。这似乎是十分稳健的做法。但他们似乎忽略了:战争何时开始,并非由被侵略者决定,而是由侵略者决定。侵略者总是把对方的虚弱视为发动战争的良机,岂会按照对方的意愿等待对方“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发动侵略?而且,李鸿章、蒋廷黻和《天朝》的作者对“充实武力”的要求非同一般,他们都认为,落后国家必须先努力赶上西方,才能具备抵抗近代强国的实力。然而要赶上西方谈何容易。就中国而言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时间。难道西方列强会在这么长的时间“暂停”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耐心地等待中国赶上他们以后再与中国“较量”吗?那么,在赶上西方之前,中国就只能在外敌入侵时始终坚持不抵抗了。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只能是加速殖民地化而不是近代化!
蒋氏著述和《天朝》一书都把日本当作放弃抵抗、全力搞近代化的成功范例,以此证明不抵抗是“明智的选择”(注: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9页。)。日本在被迫签定不平等条约之后,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这的确值得称道。但这并非不抵抗政策的胜利。明治维新的发动者并非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幕府,而是主张“攘夷”即抵抗侵略的倒幕势力。其中的骨干力量长州藩、萨摩藩都曾在1862年对侵略者进行过武装反抗。他们的改革主张与反侵略的宗旨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把改革图强与反抗侵略对立起来而把它与不抵抗硬拉扯在一起,是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未进行过大规模反侵略战争,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是日本对西方侵略战争放弃抵抗,而是西方并未对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西方列强的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有很大不同,其中原因有待熟悉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进行研究。这里姑且尝试着谈一点粗浅看法:直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跨越重洋到远东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一直很有限。他们在远东的战略意图只能集中于两点:一是侵略中国,二是应对沙俄。中国地广人众,又是落后国家中的“首富”,是西方列强掠夺压榨的主要对象。它们在远东的军事战略主要指向中国。沙俄虽比西方列强落后,但差距不太大,又兼地广人众、兵力雄厚,且占有地利,西方列强无力在远东与其兵戎相见。有的西方强国遂希望能在远东找到某种助力牵制沙俄。日本地狭民贫、资源匮乏,非西方列强掠夺重点,而它邻近中俄,又有武士道传统,倒可供西方用作侵略中国和牵制沙俄的助力。西方强国在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后,便不再劳师远征对日用兵。有的强国还愿意帮助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强大起来。于是,日本得以在和平环境下变革图强。而中国却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西方列强为了在中国夺取更多利益必然还要对中国用兵,更不可能帮助中国强盛起来,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对手。认为中国不抵抗侵略就可实现变革自强,是不切实际的。
日本在败于美国后不久就锐意维新,中国却长期止步不前。蒋廷黻把罪责加在林则徐等抵抗派头上,指责林则徐对敌强我弱的现实避而不谈,并坚持抵抗,给时人以误导,使中国的变革被长期延误。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抵抗的要求本应是变革图强的动力,抵抗的实践本应使人们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到中西差距,看清学习西方、变革图强的必要和变革的目标。但腐朽的清朝当权集团并无抵抗侵略的决心,也就没有发愤图强、改弦更张的欲望,而是苟且偷安,不思振作,与日本幕府如一丘之貉。而中国却没有像日本那样强大的足以推翻腐朽旧政权的“攘夷”势力。腐朽的清政权继续维持,变革也就无从实现。中国未能及时变革,本应由清政权承担罪责,蒋氏却把抵抗派当作替罪羊来指控,实在令人难解。
《天朝》一书指出:“以鲜血赢得的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这里,既肯定了抵抗提供的“血的教训”应有的价值,又抨击了清政权不能“认真思过,幡然变计”,与蒋氏观点大异其趣。由此,本应得出结论:中国要变革图强,必须反对冥顽不化的清政权。但此书并未作此结论,而是坚守蒋氏观点中最基本的一条:在强敌入侵时应放弃抵抗,一心一意学习西方。试问,有了抵抗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国尚且未能“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致力于学习西方,变革图强,难道放弃抵抗,索性连“血的教训”也没有,中国倒能更快地觉醒?
[收稿日期]2004-2-20
注释:29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60页。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天朝的崩溃论文; 林则徐论文; 蒋廷黻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茅海建论文; 战争论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