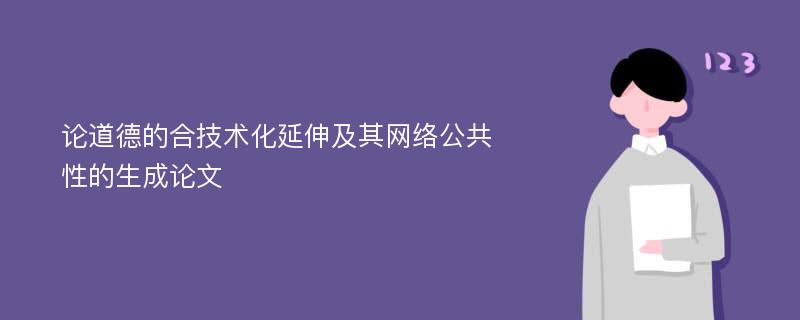
论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及其网络公共性的生成
杨嵘均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620)
摘 要: 当前网络道德和现实道德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断裂,由此造成了人们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中的道德紧张关系。> 这是现代社会人们道德生活的一个根本问题。> 它不仅涉及现代技术性社会中道德本身的聚合力问题,也涉及未来技术化加速发展进程中道德能否提供超验的终极意义以及人们能否对日常道德生活满足的问题。> 本质上,网络道德是现实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现实道德是网络道德生成的基础和条件,网络道德则是现实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的结果。> 基于此,必须面向现代技术性社会实现道德根基的公共性转换,在坚守人类共同“善”的基础上,把自由、开放、平等、包容、理性等现代性的要求作为网络道德生成的根基,从道德教育、建章立制以及技术创新等方面加速生成网络道德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从而提高网民自律能力,强化制度约束力以及弥补技术所造成的道德脱域,建设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 网络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网络公共性;技术性社会
当前,人类已经生活在由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现代通讯通信技术以及智能科技等支撑的虚拟社会。显然,我们所谈论的虚拟社会是技术性的社会,它具有技术的先验性特质,而正是技术的先验性导致了现代人在网络空间中生存的异化。这正如马尔库塞分析人的需求与技术发展的内在关系所指出的:“尽管我们可以把一台机器、一个技术装备看作是中性的、纯物质的,但是,这台机器、技术装备并不外在作为技术的整体单独存在的,而只能作为‘技术性’的一个基本元素而存在。这个所谓的‘技术性’的形式就是作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方式的‘世界的状态’。海德格尔强调对这个用具世界的谋划领先于、也必须领先于作为手段的技术装备、作为操作技术的技术员之前。事实上,这种先验的知识包含着社会需求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满足这些需求的社会的无力感。”[1]由此,所有技术,不管是农业社会的技术、工业社会的技术还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都是人类生存的“策略”;人类发明和使用这些技术根本上是为了让人类活着、活好而且要活得更好。而不管是“活着”“活好”,还是“活得更好”,人类的存在和生活都应该是道德的。因而,涂尔干针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社会指出,“当代社会仍然是一种道德体制(moral order)”[2]109。然而,时至今日,当面对技术性的虚拟空间或者虚拟社会时,这一道德命题却遭到了挑战,人们对人类的虚拟存在是否应该是道德的这一问题产生了困惑、迷茫乃至怀疑。客观地说,网络虚拟空间道德和现实道德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断裂,而且这种道德裂隙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不管是在网络虚拟社会中还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都疲于应付这种紧张关系。这不仅涉及现代技术性社会中道德本身的聚合力问题,也涉及未来社会加速技术化发展进程中道德能否提供广泛的或者超验的终极意义以及人们能否对日常道德生活满足的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网络空间道德与现实空间道德之间的关系。
1 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的基础和条件:现实道德
作为文化的道德,它是有根的,因为文化是生成的[3]41-46,所以作为文化的道德存在是一种有根的存在。就此而言,网络道德本质上就是现实社会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的结果,因而网络道德具有合技术化延伸性。也就是说,网络空间道德与现实空间道德之间的关系就是:网络道德的生成与发展是由于现实空间道德适应网络信息技术环境而发生的技术化变异。
湖北倍丰农资有限公司的唐杰也表示,近几年农民种地收益极低,以至于很多农民转型搞起了小龙虾的养殖,传统复合肥的需求量正在逐年降低。据唐杰介绍,公司现有复合肥库存1000吨左右,已经把政策报给了下游客户,但是下游观望情绪浓厚,不愿意打款,只有极少的客户打来了一小部分预付款。他说:“考虑到传统复合肥的生产成本过高,市场也正在逐渐缩小,在消纳掉现有库存以后,将有可能采取随进随销的方式,而不会再大量备货。”当记者问及对今年冬储价格的预测时,唐杰表示:“预计会比去年冬储的报价上涨300元/吨左右。”
人类文明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类的存在都是某种形式的道德化存在,文明社会的生活也是与此道德形式相适应的道德的生活。这是因为,虽然道德最本质的社会需求是“爱”和“善”,但是“利益是道德的基础”[4]221,所以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利益的表现形式而已,它是附着在利益、权力乃至权利之上的“爱”与“善”,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德性获得的普遍性,而德性正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5]241。因而,无论在何时何地,也无论在何种语境下,利益都是最现实的存在。这表明,在当今的技术性(或者技术化)生存的社会,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仍然没有超越其现实性,技术只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技术化的生存环境而已。所以,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6]37。就网络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技术而言,从其诞生以来,它只不过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没有超越追求现实利益的根本目标时,就道德实践的利益性追求而言,网络空间道德事实上就必须是现实社会中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
所谓“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笔者认为,它是指包括道德目标、道德规范、道德约束、道德权利、道德义务、道德实践等道德体系适应于技术环境而发展或者重新生成的技术化道德体系。事实上,人们发现,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现实社会生活中原有的道德目标、道德规范、道德约束、道德权利、道德义务、道德实践等道德体系已不能满足网民们的心理、感情和交往需要。也就是说,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秩序、道德功能以及道德凝聚力等在网络空间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实践在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时间与空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道德空隙,这样便产生了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中的道德脱域、道德失真以及道德失范。正因为如此,人们突然发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人类已经进入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时空环境,并不断追寻着有关人类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人类为什么会如此的更深层的哲学解释。就网络空间道德而言,人们在寻求与现实社会中的“不变”要素——即网络空间道德的现实延续性——“不变”是现实社会道德向网络空间道德延伸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网络空间道德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道德之外的,它是现实社会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体现为现实社会道德的虚拟延续性。从网络道德合技术化延伸性的基础和条件而言,其“不变”之处体现在:
自律性是道德的唯一原则,也是最高原则[16]61。在现实社会中,道德是一种自律行为,是道德个体的自我立法与自我遵从,它是灵魂的善。在网络空间中,现实中人的生存场域已经转化成网络数字化的生存幻象,而幻象是没有真实对应物的东西,它只是一种图景,因而是虚拟的现实。“在幻象中,真实的或者原初的东西被模型或者编码所替代。这样的模型或者编码是根据能够使再现发生的要求而构造的,是使完全相同的副本再现的模板”[17]100,而这种模型只是“相关物的能指”[17]101,它并不指称任何真实的存在。这是人类在网络空间中虚拟存在的状态。此外,从网络社会交往角度来看,人们主要依靠社交媒体进行彼此交往,而“社交媒体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18]7,这时,“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的信息”[19]597。因而,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具有的身份、地位、工作、家庭环境、收入状况等都统统被隐匿起来,交往的对象由此而成为不确定的、未知的和虚拟化的想象图景。这样,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迫于各方面的道德压力而不得不潜藏起来的本性便会在虚拟空间中以一个“面具人”的身份得以爆发。这种双向的不确定性和隐匿性特征让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脱离了社会身份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监督,如此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自律意识便容易弱化甚至消失殆尽。于是,在网络空间中,我们看到一些在现实中彬彬有礼的君子可能成了满口污言秽语的痞子,平时怯懦的人可能忽然变得个性张扬起来,等等。这样的失德言行,不一而足。此时,人们在网络中已经失去了道德法律等社会禁忌令人紧张恐惧的犯罪感,模糊了罪与非罪、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自我陶醉在虚拟化的完美幻象中。“虚拟化的现实变得越来越完美,真实和表象、已经发生过的和有可能发生之间的界线将会消失无踪。”[20]175由此,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因技术化的生存环境而发生蜕变。
第二,不管是在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社会中,道德的本质没有变。道德是一种被整个社会所认可的规范体系,是关于人们社会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性规范,因而它是“一种生活的社会体系,但它是能在自己的社会成员中促进理性的自我指导或自我决定的一种生活体系”[8]14-15。虽然上述是针对现实物理空间中的道德所做出的判断,但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我们仍然应该在道德伦理的语境中去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如果用其他的态度去研究网络信息技术,既没有意义也容易误入歧途。事实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在网络社会中同样应该被认同。因为网络空间中的“人”,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道德规范和调节的内容和对象仍然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和利益关系”。只不过,在网络空间中,人们的道德行为因技术而被虚拟化了,人们的言行被技术编码而体现为数字化的幻象存在。然而,“由编码或者语言形式所产生的幻象并不真正指涉存在,而仅仅是对存在的模拟。幻象是某种想象物或者复制品,在后现代中与幻象对应的指涉物是不存在的”[9]181。因此,人们的言行因技术而虚拟为信息化的存在,表现为人们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交往,是一种信息文明。而“作为道德形态的信息文明,也即信息文明时代的道德伦理观。信息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活动空间和新的行为方式,从而也形成了新的道德空间和提出了新的行为规范即道德伦理要求,这是先前的活动空间所未曾遇到的”[10]80-85。如果我们把网络看作是技术理性建构起来的装置,那么,在这个装置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机械和规范化的世界装置中脱离出来”[11]46。因而,“人们必须学会把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调整到和他人同步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和秩序。也就是说,只有根据那个可以确保这个装置正常运转的标准来行事,人们方能确保自身的生活。”[12]62-67这也表明,网络道德是现实社会道德的延续。
网络空间道德认同属于虚拟认同。“虚拟认同是指人们对自身的虚拟生存活动及其特点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选择。”[24]74-89当在虚拟空间中实现的价值认同与现实生活状况不一致时,人们很容易丧失对现实社会的归属感并进而造成个体与整个社会的分离。众所周知,互联网是一个面向全世界开放的信息分享和大众传播平台。互联网传播打破了地点、民族、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职业等的限制,使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网络空间传播变得既容易又便捷。显然,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比以往更为充分地利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更为充分地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功能,已经逐步构建成一个手段开放、对象广泛、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社会交流系统[25]5。然而,通过在虚拟技术提供的逼真场景中的活动来实现的虚拟认同很容易使虚拟的价值观念被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而被固定下来,并沉溺于虚拟的境域从而模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造成虚拟认同对现实认同的僭越,并进而弱化主体现实社会交往乃至割裂与实际社会关系的联系,最终导致现实社会归属感的丧失和个体与社会的分离[24]74-89。这样,在网络空间中,多元价值观所内蕴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知识水平、生活方式等通过舆论传播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很容易使人们走入道德迷途乃至走向道德歧途,其结果是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极度分化,从而在整个社会内部出现多元化、分层化的格局,这样就极易导致行为主体“道德选择的摇摆不定,现代人在享有前所未有选择自由的同时,又被抛入了一种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26]165。这时候,最易产生的社会心理就是从众心理,从众心理的社会风险在于:“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者绝对谬误。”[27]25此外,从众心理也是道德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在道德民粹主义看来,“多数者有着道德上的权利决定所有人如何生活”[28]76。我们看到,在网络空间中多元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让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甚至迷失自我,而此时选择“从众”的策略可以免遭危险、伤害乃至毁灭,因而“从众”就意味着安全、便利、无责任和效益最大化。这样,网络空间中存在着的多元价值观不仅冲击着主流价值观,而且导致人们对网络道德难以形成共识,最终必然会解构现实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并形成价值真空和道德失范。
本文认为,网络道德的本质特征和现代根基是网络公共性。公共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从本原上来讲,‘公共性’是一个哲学范畴”[29]45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较直接反映“公共性”的词语是“公”,甲骨文中“公”指的是古代共同体祭祀场所的平面图。关于中国传统的“公”观念,我国台湾学者陈弱水将其分为五个阶段[30]5。然而,中国古代社会却是“公私不分”的,“有私德而无公德”是中国古代伦理本位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梁启超是最早把道德划分为公德和私德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想建设一个新国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31]33。梁漱溟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人过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为公共服务,就不讲求”,而其原因就在于“缺乏集团生活”[32]162。因为“缺乏集团生活”,所以就产生不了“公共性”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即“公共观念”。梁漱溟还尤其指出中国人特别缺乏国家观念,认为造成公共观念缺乏的原因在于中国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环境。
显然,信息是构成网络空间有组织的社会的“神经系统”,正是通过信息交流和交互整个世界才被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信息最大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和共享性。事实上,当前人类已经生活在由信息科技建构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糅合而成的“虚-实”交织缠绕的浑然一体的空间中。以互联网科技为核心的信息科学技术,“正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使我们逐渐放弃了内心的抵抗心理,接受现实的生存环境”[38]95-110。因而,人类既是现实世界的主体也是虚拟世界的主体,人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的物理空间中,而且也生活在现代科学技术搭建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人们不仅能够以“谦谦君子”的道德形象在现实的物理空间中彼此交往互动,而且能够化身为漂浮闪亮的符号化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空间中彼此交流互动。在很多情况下,似乎现实空间中“谦谦君子”的道德形象已荡然无存,网络虚拟空间似乎失去了“道德君子”的生存根基。所以,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力发展为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人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39]95。这是因为,网络不仅成为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网络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网络虚拟空间的形成,人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获取信息、交流、购物、娱乐,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建立起一个个虚拟社群,并逐渐形成网络社会,即所谓的虚拟社会。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需求,已经逐步发展到依靠网络虚拟平台或者各种电商平台来满足。现实的社会和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被虚拟化了。事实上,“虚拟化就是心灵、身体与互联网和谐同一的社会影射及文化表达过程”[40]28-32。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既然“人的本质并不是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18,那么也就是说,个人只能在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一旦生成了这样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有适应和维护这种社会关系,并要求个人遵守的社会准则和道德法则。因此,既然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人们一片新生的生活领域与交往领域,那么现实社会中的公共道德就必然会延伸到网络社会中,并结合网络本身的特点而形成网络社会公共道德来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人们必须要面向现代社会实现道德的公共性转换,同时要坚守人类共同的“善”,以自由、开放、平等、包容、有序等现代性的要求为网络空间道德生成的根基。这是道德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顺应时代发展的一种能动表现,也是对自身内涵的一种新的延伸和补充。
1.2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抗感染,平喘,祛痰,适当强心,利尿,纠正水、盐、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等综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另外给予低分子肝素钙4000U皮下注射,2次/d,再给予前列地尔10μg静脉注射,1次/d,总疗程10d。
2 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的诉求与结果:网络道德
以上是对网络空间道德是现实社会道德合技术化延伸的基础和条件所做的论述,这是从网络空间道德与现实社会道德“不变”角度论述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变”——“变”是网络空间道德适应网络信息化技术环境发展而重新生成的新道德诉求。就此而言,网络道德就是适应网络信息化技术环境的发展并以现实社会道德为基础和条件而重新生成的新道德。
随着网络媒介的全球性、虚拟性和自由性等特征导致网络社会的道德运行与传统社会道德运行存在的法律制裁、社会舆论、利益机制等外在力量约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使得道德约束对网络行为的调控作用和约束力大为降低[15]73-77。因此,网络空间产生道德脱域就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现实社会道德已经有相当部分的成分不适应网络运行的新环境而形同虚设,道德约束力随之大为减弱。这样,网络空间道德就对现实社会道德产生了革新的诉求和需要。既然网络空间道德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形式,那么其革新诉求就必然以网络言行作为调整对象,以构建与网络信息技术以及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相适应的规范体系与伦理准则作为道德目标,其与现实道德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网络空间道德自律意识减弱
第一,网络空间道德和现实空间道德的作用对象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人们通常会认为,“网络社会”是网络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似乎网络道德的生成根基单纯在于由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所独立引发或造就的。然而,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网络社会始终是附着于现实社会的,是现实生活通过网络信息技术载体的某种实现形式,是人们依赖于网络信息技术而追求现实利益的技术化环境或者虚拟化空间。因此,只有在网络信息技术存在的意义上网络社会才可以相对独立于现实社会,而涉及道德这种社会内容就只能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也就是和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活动结合起来。可以说,网络不但生于社会、长于社会,而且它还要融于社会、回归社会。在网络社会中,虽然人以“符号”的形式虚拟化存在,但是“符号”的行为背后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人的行为以及现实社会中的利益诉求,这没有也不可能违背马克思恩格斯“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87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网络社会或者网络空间中的道德体系所规范的对象必然还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其发挥作用以及实现利益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仍然是现实社会。因而,人们只有立足于现世人生,通过道德修养、德性修炼与道德践行,才能实现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并在网络空间中体验莫大的感性愉悦与精神自由。就此而言,网络空间道德是现实社会道德在网络信息技术新平台中的一种现实化、技术化和虚拟化延续的结果。
结合设计咨询工作,在一些咨询项目中已应用了开发的部分软件,现在选择了上海·中骏世界城、苏州绿地中央广场1#地块项目作为软件应用的示范工程,开始在工程中应用软件,如图12和图13所示。
2.2 网络的虚拟性使得道德约束与道德权威消隐
在西方,“‘公共性’作为一种比较规范的理论叙述概念,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出现的”[29]47。尽管从概念发展史来看,西方社会公私之分起源比较早。在“公共性”理论研究方面,汉娜·阿伦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作出了很大贡献。20 世纪,汉娜·阿伦特将社会区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阐释了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所蕴含的公共性内涵和意义在于:“一是‘公开展现性’,二是‘差异共存性’。”[33]38哈贝马斯则将“公共性”看作是一种理想范型公共领域的价值属性,而这一理想范型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公共性意味着“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无障碍的开放性、公众在公共领域内对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的批判性,以及遵循自由、民主、正义原则进行理性商讨所达成的可以促使独立参与者在非强制状态下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识”[34]6。可以说,公开性、批判性以及理性化是哈贝马斯这一公共性的显著特征。从总体上来说,在西方道德伦理思想史上,西方崇尚“符合于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35]385,因而理性主义是作为其基本脉络的,虽此消彼长,但自始至终一脉贯穿。然而,到了16 世纪末,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随着上帝的祛魅化发展,人性和理性得到张扬,因而近代思想家转而从人本身、从人性和理性出发来寻找道德的依据。近代理性主义思想始祖笛卡尔认为,道德内容和道德评价标准取决于人的理性,主张人用理性来约束所追求的目标。而斯宾诺莎认为,“道德的原始基础乃在于遵循理性的指导以保持自己的存在”[36]196,因而他认为人的理性是德性来源。黑格尔把道德定义为主观意志的法,并把理性主义的主体中心转换成社会中心,认为人们只有摆脱了个体的主观性才能适应社会要求,而“道德的基本内容要求人们在内心规定着善恶标准,从而在行动中扬善抑恶”[37]108-109。然而,自20 世纪以后,西方伦理思潮转向贬抑理性主义而崇尚非理性主义。
2.3 网络空间多元价值对现实社会道德认同的侵蚀
喉源性咳嗽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耳鼻咽喉科疾病,主要是指因咽喉部疾病引起的咳嗽,临床症状以阵发性咽喉干痒、咳嗽无痰为主,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且随着空气污染加重、饮食结构改变而出现发病率增高趋势,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3-5],且由于喉源性咳嗽容易与其他感染性疾病混淆,导致其误治,西医治疗尚无有效的方法[6,7],因此,临床上需针对喉源性咳嗽的病理特点进行明确,再针对其中医辨证分型特点进行针对性治疗。
3 面向现代技术性社会实现道德根基的公共性转换
第三,从道德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来看,网络道德并没有超越从属于人类道德的一般范畴体系,它仍然具有现实社会道德的一般性特征,比如承载着一定的善恶取向并以此指导人们的行为判断。既然道德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那么作为新的技术工具的网络不仅在加速创造和重塑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在加速重塑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因而它被视为当前“整个世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13]22。就道德生成环境的一般性规律而言,网络道德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网络虚拟空间所特有的,因而网络道德势必会因为技术本身的特点而被赋予一些和现实社会道德不同的特点。但是无论其如何不同,网络信息技术不可能也不会实质性改变道德的社会根基,所以在网络空间中,基本的人类道德的规范体系并没有因网络信息技术而发生改变。事实上,在网络空间中,个人从来都不只是孤立的个体,总要生活在特定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都是在情境中被树立起来的或被建构的;而且,这是在社会制约下的自我建构”[14]48。道德以规范的形式表现着人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本质,它是以指导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正确的行为方式为内容的精神修养。因此,在网络空间中,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必要的道德修养,才能为他人所认同、所接纳,并取得扮演特定交往角色的资格,从而成为一个具有“人之为人”的道德的人。就这一意义而言,作为人类精神和社会角色存在的人,其道德存在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网络道德是现实道德的合技术化延伸。
网络的虚拟性消弭了时空的差异,使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原本的道德规范、道德权威和伦理秩序等失准、失却乃至消隐。事实上,公共权威的关键性职能是增加在全体社会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相互信任[21]123。在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交往靠的就是相互信任,这让人们形成了强烈的道德意识、道德觉悟以及道德自律,从而维护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然而,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经常是彼此陌生的,因而网络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人们彼此之间以某种需要或者兴趣组成各种虚拟社群。而在这样一种没有熟人甚至感觉不到“人”的存在、感觉上只是在和机器打交道的虚拟网络社会中,人们的言行异常自由,现实道德约束力的防线变得异常脆弱。由于人的大部分行为并不起源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起源于情感[22]3,所以,一般来说,起源于情感的言行很容易散发并滋生个人的劣根性,极易导致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蔓延,最终结果就是在无拘无束的网络空间走向无法无天的深渊。而且,这种虚拟的网络环境很容易导致人的虚无感,并使人沉浸在道德虚无状态而无法自拔,其结果就是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与戏谑娱乐风气盛行。有些人完全将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约束、道德规范、道德权威、道德监督、伦理秩序乃至法律规制等抛诸脑后。由此,总是在个体存在的外在状态、个体本质存在的内在状态和个体存在的想象状态之间游离,并不断地进行着角色的切换。因而在网络空间中,“无论在何处,每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种角色”[23]17,而这种角色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虚假性、隐匿性、欺骗性和伪善性,并从而导致行为主体更加迷恋这种道德虚无状态,更加沉醉在任性妄为的“快感”之中。而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约束、道德规范、道德权威、道德监督、伦理秩序乃至法律规制便等由此失准、失却乃至消隐。
综上所述,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从本源意义上来说,道德是通过人类想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类之所以要利用想象去创造道德,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人们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维系个体以及群体的道德感知和道德存在,并通过爱憎与善恶的评价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道德心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而迫使个体与群体维持一种有秩序的道德生活。这是人类能够承续至今的根本所在。从这一意义来说,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始终的。然而,有关于道德的公共性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却是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才逐步彰显出其重要性的,因而,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也具有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与“私德”相对照,“公德”更显著的特征在于道德的“公共性”,因而公共性是判断道德是否是公共道德的首要标准。
(2) 在三点弯曲试验中,花岗岩和大理岩脆性试样变形破裂过程会产生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在线弹性阶段花岗岩有较强的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大理岩的电荷感应信号和微震信号强度则较弱;而在破裂发展阶段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幅值都达到了最大值,花岗岩试样变形破裂过程产生的微震和电荷感应信号强度比大理岩试样的大且事件数也多。
4 现代技术性社会网络道德公共性的生成路径
如上文所述,随着现实社会道德向网络空间的合技术化延伸,人们对于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中是非善恶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反差,现实中被公认的道德标准出现了偏离甚至歪曲。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仅任由网络空间道德荒漠蔓延,而且对于许多网络失德言行的性质与后果也表现得很淡漠乃至麻木。其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技术便捷性、隐匿性以及虚拟性等特征为所欲为,对诸如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网络欺诈、黄赌毒信息传播等触犯法律底线的行为不以为然,对自我的网络道德要求普遍很低,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我道德约束性的失准、失却乃至失效。产生这些道德失准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空间中各种价值观与道德观并存、交替、更迭,造成道德规范内容的矛盾与现实社会道德衔接的脱钩。这已经对现实社会道德生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加速网络空间道德规范体系的生成,实现网络空间道德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4.1 从现实道德教育入手,提高网民自律能力
康德认为:“自律原则是唯一的道德原则,而道德原则必须是一个定言命令式,但这个命令所要求的,却不多不少,恰恰是这种自律。”[41]552因此,真正品德的养成来自人们自觉自愿地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而没有内心的道德自律就难以获得高尚的德行。事实上,无论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凡是漠视道德自律意识、忽视道德自律能力淬炼而放纵自己行为的人,最终都会受到应有的报应和惩罚的。要知道,“互联网推崇自由、促进自由,但并不存在绝对自由”[42]43-46。“绝对自由”是网络空间道德公共性和共享性生成最大的思想观念障碍。所以,网络空间道德公共性和共享性生成的最牢固根基是教育网民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自律意识。道德规则应该是现代社会人们首要遵循的规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43]43。为此,一是必须加强网络道德教育。这是因为,网络道德的主体仍然是现实的“人”,网民是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共同的行为主体。引导网络主体自我塑造、自我约束,通过反省克服自己的恶习,在实践中改造自身,躬行、践履道德规范,增强自我对网络不良道德行为的识别警觉能力、自律抵诱能力。二是必须注重培养网民的道德责任感,增强网络道德认知和规范网络道德言行,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事实上,“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价值评价问题,而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价值评价与人的道德境界息息相关”[44]162-171。以正确态度面对信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和整合,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与诱惑。三是增强网络个人道德修养。其要旨在于“养德”,同时还要提倡网络空间道德主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信息的时候,应该努力做到坚持主体间性原则,坚持“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充分考虑其他主体的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四是引导网民树立保护人格尊严的意识。人格尊严“既是对网民个人行为的规范,也是对他人尊重和保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要求”[45]100-109。因此,我们需要把自尊和他尊有效结合起来。如果每个网民能够主动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并同时尊重他人的尊严,那每个人的人格都会得到自我和他人的双重尊重,这样道德失范现象就会大大减少,最终必然会建立起一套以网民道德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心性修炼达到网络道德规范体系。
4.2 建章立制,加强制度约束力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所以国家必须从法律制度上强化道德的约束功能。一般而言,道德对人的调整方式往往是由内而外的,这种作用方式决定了道德规范只针对那些认同此种道德规范的人才能发生约束力。所以,网络道德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个体的道德自律,还要积极发挥法律、法规、制度、条例等的约束力。目前,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很难保障网络道德健康有序发展。为此,一是要立法到位,建立健全网络法律法规,保证网络法规的权威性、系统性和全面性。首先是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立法研究和立法程序把充分反映了国家和人民意愿的政治道德、经济道德、家庭道德等一些公认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文本,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其得到贯彻实施,并进而强化网络道德的普遍约束力。其次要明确划分网络行为的法律界限,推动网络空间针对各个领域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建设,对诸如网络资源的管理、网络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政府组织和个人在网络中的权利义务等做出明确规定,为网络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要建立健全网络道德激励与道德约束机制,加大对网络犯罪的惩处力度。当前,立法部门要根据网络道德问题尽快制定相应的道德激励与道德约束机制,对于网络道德失范者实施必要的惩处,如经济制裁、限制其网络使用权等,严厉打击网络不法行为,加大犯罪代价,从而保证网络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三是要加强网络立法的国际合作与司法监督,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提供国际法保障。
4.3 加强技术治理创新,弥补技术造成的道德脱域与道德裂隙
网络是一种新兴的技术,而“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因此,我们“在认识论上和精神上必须和技术拉开距离”[46]111。很显然,网络信息技术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道德漏洞。一方面,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网络信息技术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非真实的事件或者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不仅遮蔽了真实而且也吞噬、消解甚至摧毁了意义。正因为如此,网络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浩如烟海,难辨真假对错,这会给一些网络事件的制造者有机可乘达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传播赋权”。众所周知,网络信息化时代是一个群体传播时代。虽然传播赋权强调人通过多样和有创造力的方式积极地、有意识地形塑媒体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但是客观地说,在网络空间中,不乏对诸如黑客技术、人肉搜索等网络技术盲目崇拜的网民,他们一味追求高科技所带来的刺激与满足而罔顾伦理道德的约束。这些技术漏洞的存在对个人安全和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有一定的威胁性。因此,为了弥补网络信息所造成的道德脱域与道德裂隙,一是创新网络不良信息过滤技术,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以及垃圾邮件、病毒邮件、泄密邮件和网络聊天等进行过滤,从根源上最大限度地限制和删除带有欺骗、煽动、色情等负面性质的信息,阻止和降低不良信息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侵害,坚决杜绝低俗、颓废乃至反动的言行。二是对于技术部门来说,要创新纠治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方法,针对网络技术自身的缺陷创新发展弥补网络道德缺失的技术手段。三是加速关于网络信息自控技术的研究,努力克服目前网络信息数据冗杂性和难以捕捉的动态性的难点。
根据调查,绿色食品在大中城市市民中的认知度超过八成,绿色食品标志已在多个国家成功注册,多个国家的企业和产品也正在使用中国的绿色食品标志。
5 结语
网络信息技术在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带来负面影响。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13]8。不仅如此,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也塑造了适应此技术发展的道德伦理、法律规范以及社会文化,因为“技术这一最实在的物质产品,从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47]8。新的交往方式不仅打破了现实社会中原本的人与人之间道德实践的方式,而且也打破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当现实道德合技术化延伸到网络空间中时,网络主体由于在双重空间中的道德环境不同就极易产生伦理道德观念上的“错位”和道德实践上的“失范”。因此,在网络“失德”行为与日俱增、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下,必须认识到在网络时代塑造公民道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网络道德失范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确保网络空间秩序和谐,网络伦理道德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MARCUSE H.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rial society[G]/ /KELLNER D,PIERCE C.Herbert marcuse:philosophy,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New York:Poutledge,2011.
[2]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3]林剑:论民族文化的创新[J].江海学刊,2015(6):41-46.
[4]黄瑚,钟瑛.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威廉·K·弗兰克纳.伦理学[M].关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9]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0]肖峰.信息文明: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5(1):80-85.
[11]MARCUSE H.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G]/ /KELLNER D.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New York:Routledge,1998.
[12]黄璇.技术控制及其超越:从海德格尔到马尔库塞[J].国外社会科学,2016(2):62-67.
[1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4]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5]胡玉璋,易鹏.中国网络媒介社会责任建设探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3-77.
[1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BAUDRILLARD J.Simulations[M].New York:Semiotext(e),1983.
[18]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9]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0]马克·斯劳卡.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M].汪明杰,黄锫坚,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21]JOUVENEL B.Sovereignt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22]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兆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4]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治理[J].学术月刊,2017(5):74-89.
[25]郎劲松,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6]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7]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8]H.L.A·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智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9]张雅勤.公共性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0]陈弱水.中国历史上的“公”观念及其现代变形[G]/ /刘擎.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1]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32]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33]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4]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6]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7]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8]杨嵘均.网络暴力的显性歧视和隐性歧视及其治理——基于网络暴力与网络宽容合理界限的考察[J].学术界,2018(10):95-110.
[39]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40]唐魁玉.心、身与互联网——一种虚拟世界心灵哲学的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0):28-32.
[4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2]范玉刚.新媒体与网络空间的文化表达[J].探索与争鸣,2012(3):43-46.
[4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4]邓晓旭.试论建设网络强国的价值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62-171.
[45]杨嵘均.人格尊严保护:网络文明和网络伦理建设的价值内核[J].道德与文明,2017(5):100-109.
[46]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7]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Multi-technological Extension of Morality and its Generation of Publicness in Cyberspace
YANG Rongjun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
Abstract: The current morality has been shown as differentials both in virtual society and real society,which has resulted in people's moral tension both in the cyberspace and real space.And so,this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eople's moral life in modern society,which concerns not only the cohesive force of morality itself in modern technological society,but also morality how to provide transcendental ultimate significance in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eople how to satisfy their daily moral life.In essence,morality in cyberspace is the multi-technological extension of morality in real space:morality in real space is the basis and condi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morality in cyberspace and morality in cyberspace is the result of the multitechnological extension of morality in real space.As the reasons given above,we must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s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ness of the moral foundation in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society.On the basis of adhering to the common “good” of mankind,we should take the requirements of freedom,openness,equality,tolerance and rational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neration of morality.In order to do it well,we can take the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generation of the moral publicness in cyberspace from the aspects of moral education,establishment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 order to build comfortable cyberspace with common beliefs,symbols,morals and spirits,we should enhance the self-discipline of netizens,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binding force and make up for the moral dislocation caused by technology.
Key words: morality in cyberspace,multi-technological extension of morality,publicness in cyberspace,technological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2-0171-10
收稿日期: 2018-1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及政府协同治理研究”(14AZZ016),项目负责人:杨嵘均。
作者简介: 杨嵘均(1973—),男,博士,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 超
标签:网络道德论文; 合技术化延伸论文; 网络公共性论文; 技术性社会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