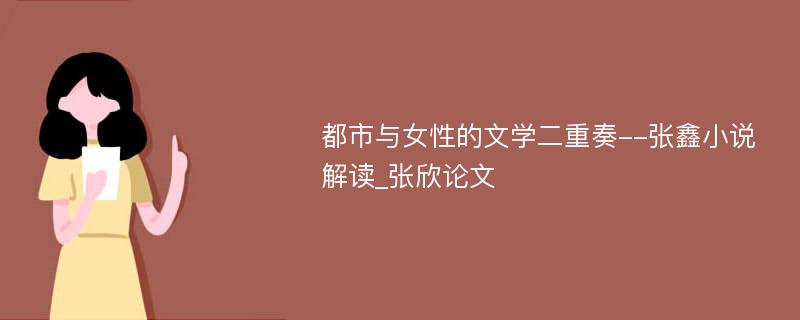
都市与女性的文学二重奏——张欣小说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小说论文,张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广东女作家张欣走上文坛是在1978年。10多年来,她的作品频频见诸《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国作家》、《小说界》、《十月》、《上海文学》……多次荣获广东、全军乃至全国的文学奖。早期结集出版的有文学新人单人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短篇小说集《初次尝到寂寞》等。在新近面市的“风头正健才女丛书”(王朔主编,华艺出版社出版)中,张欣的小说集《城市情人》榜上有名;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当代著名女作家“红罂粟丛书”(王蒙主编)中,张欣也有一席之地。此外,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都市平安夜》等影视作品,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被评论界赞为“挖掘都市新意的佳作”。不容置疑,张欣的创作已经成为了文坛注目的对象。
对张欣创作的定位,评论界以曾镇南的评述最为贴切而全面:以现代都市女性为主人公,以她们在事业、爱情、友谊上的追求和失落展开故事,旨在揭示“都市女性的误区”,也写出了“生活层面的丰富和新颖”〔1〕。这同张欣自我定位的创作谈《女性误区》简直契合无间。
看来,要评析张欣的创作就离不了都市、女性、情爱、误区。探索当前都市中女性的情爱误区——这既是张欣的创作焦点,也是她的作品在都市文学和女性文学双重题材领域内的特色和价值所在。因而,如何分析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及其身陷的情爱误区,如何评价张欣在呈现都市、探索女性误区的过程中的得与失,便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
张欣从文10多年来,始终在写都市和都市人。此间,中国的城市演进充满喧哗与骚动,而张欣又一直生活在广州这个日新月异的都市新贵中,但她对“新都市”的体察却很有些灯火阑珊处的淡然。早在1988年,张欣便在创作谈《永远不说满意》中指出,某些都市文学作品过多地注意到浮光掠影,好像发生在这当中的故事永远不会像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那么沉重和郁闷,其实“病态的都市恰恰隐藏着最复杂怪异、最不为人知的人物关系,隐藏着让人辛酸和哀怨、感慨和心悸的插页,也有着与农村中易于暴露出来的一模一样万古不变的自私、势利、守旧和黯淡。只不过它的生活多了一层鲜釉罢了”。1992年,张欣又在创作谈《记录生活而已》中进一步强调,香车美人不夜天也好,满嘴时间效率也好,只是都市“一层极薄的包装纸”,都市真正的内核常常是火树银花掩盖着的心酸与悲苦。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欣的作品虽然描绘了都市的“鲜釉”,但不拘泥更不沉溺,与那些崇尚奢华,以香软甜媚为都市标签的作品大相径庭,有着剥开“包装纸”的自觉与清醒。
那么,剥开包装纸后的都市又是什么样的呢?张欣的表达与众不同,她说:都市“是一个大误区”!
在张欣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都市蓝图和全景,商战的风雨和开拓的激情也都淡淡的,凸现的只是些“身陷红尘,重拾浪漫”的都市女性,在“人生无处不沧桑”的慨叹下,为爱情、友谊、事业和家庭奔忙着、苦恼着……这样的都市图景既有别于南翔、钟道新等外来作家的“南下奏鸣曲”——热衷于写新、写开拓、写经济为轴心带来的变化以及内地和沿海的反差,也不同于刘西鸿、黎珍宇等南方作家的“带露摘枝”——充满“你不可改变我”的自信和商界驰骋香江沉浮的豪情。同样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都市生活的底层,去揭示严峻的生存中理想道德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张欣的笔墨何以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张欣的“都市情结”始终是以“女性情结”为内核的。“都市很大,我没有能力面面俱到”,而“女人永远是文化、文艺的主角”,“是一种色彩,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出现”。女性有永恒的魅力和无穷的新意,况且,作为感受型的女作家,张欣很容易与都市女性达成命运的认同和灵魂深处的共鸣。这样一来,张欣的作品在都市文学中以女性的情爱为标识,在女性文学中则以都市的冲撞和误区为特质,奏响的其实是都市与女性的文学二重奏。因此,所谓“都市是一个大误区”的界定,实乃都市女性对人生的误区慨叹的放大。张欣的笔就这样沿着都市的血脉进入到了都市女性的世界。
三
张欣对都市女性情爱的演绎与当代其他一些女作家有息息相通的地方:精神上的超越指向(张洁)、行动中的从俗选择(池莉)、感受上的心理真实(姜丰)、事业中的个体独立(莫然)。但张欣自有一副独特的笔墨,她自称为“女性误区”,即都市女性在事业与爱情的双重线索和爱情——友情的平行交织中面临的“困守还是出击”的选择。“出击需要勇气”,而“困守需要耐力”〔2〕。
张欣的女主人公多是处于转型期的3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不单从职业、而是从智商和心态方面而言的),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清高和对精神生活理想化的追求。在传统与现代的新旧对峙中,她们一方面淡泊名利,慎待婚姻,孝敬父母,笃爱孩子,一方面又关注自我,对无爱的婚姻不苟且,对价值的认定不含糊,似乎追求着一种“新旧合璧”的人生。然而,在“你需要什么,就没有什么,这就是生活”的现实中,她们真纯、强烈的情感呼唤迟迟得不到应和,爱的理想在比比皆是的失恋、婚变中一次次失落了,她们也因此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困扰和自我拯救的努力中。
都市女性情爱理想失落的原因何在?张欣在作品中作了如下分析。其一,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使她们与男性在情感体验上不尽相同。男性观察重整体,认知多定向于物和外部世界,他们的感情体验是粗线条的,总是喜欢寻找刺激,寻求不重复的、新的刺激,即使追求失败了也还留存着追求时的美感和与挫折伴生的成就感。而女性不同,她们重细节,多注意人和内部世界,感情细腻,心智敏感,仿佛为了感受并接受爱而生,因而她们往往最易感知到内心情感的灾难,又最易在灾难的打击下肝肠寸断。其二,女性面临事业与爱情的冲突。这冲突不仅在于时间、精力、情绪上难以两全,也不仅是因为和丈夫、情人在同一事业领域内竞争而伤了和气,而是一种深层的两性心态错位。其三,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这是女性个体最难以改变的。女性的这种失落心理在中篇《首席》中突出地表露出来。吴梦烟和欧阳飘雪这对才貌双全、心高气洁的女友,在众人眼中风光得很,但她们的苦衷却是无法调和与淡忘的。飘雪说:“女人真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爱,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吴梦烟也慨叹:“一个女人,刚烈又怎样?好强又怎么样?抵不住别人一句话,就能叫你的工作、名誉、自尊和清白统统泡汤。”她们都曾以为自己是好琴手,对知音(广义)充满自信和期望,不料现实中,女人似乎“仅是一个音符,人家把你拉成流氓小调也未可知”。悲哀、无奈、挥之不去的女性误区,又何尝不是整个社会的误区呢?
有失落,就会有不甘失落的救助。面对“爱又如何”的诘问,张欣用“真纯依旧”作答。“真纯依旧”既是女主人决不从俗的人格与灵魂,也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爱情空白、支撑爱情理想的珍贵友情,这便是自救与他助。这两种救助都带有纯化美化的理想色彩,但在精神的层面上的确体现了对失落的不屈和超越。
先让我们来看看自救,这当中凝聚着张欣的人格理想。《真纯依旧》中的赵亚超,承受着病痛与婚变的双重压力,却依然睿智、勇敢地在选美比赛中担当着美的评判者、支持者,对前夫的女友、参赛选手崔菁菁也给予了真诚的理解和无私的帮助。对于生活中的美、爱和真纯,赵亚超是永远的信徒、永远的卫士。《城市爱情》中,林默兰在绝症的折磨中接到留学异邦的男友为生计而变情的绝交信,在情感与生命的双重危机中,她仍坚守自己的信念:“爱不是靠契约维系,也不是靠高尚的取舍达到,而是一种生命的交融,一种绝不能失去对方的信念。”这在死神威胁下也不败的花朵,无疑是对爱的理想最美的祭奉。
与自救之路并行的,是友情至上的他助之途。张欣笔下对女性之间情感的倚重是与对男性的失望互为因果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中达弟的丈夫虚伪而蛮横。《永远的徘徊》中林子的男友是诗人和导演,从事着看起来超凡脱俗接近性灵的职业,然而却懦弱、自私得“连做朋友都太过肤浅”。《首席》中稳重能干的江祖扬,是飘雪和梦烟这对出色女子共同的初恋对象,也许还是终身的情人,却也是对名利虚张清高、对情感怯懦逃避的角色。
和充满欲望、功利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相对照的,是真诚、无私、患难与共的女性伴侣,如《无雪的冬季》中的夏媛蓓与宋菲,《永远的徘徊》中的林子与忆蝉,《爱又如何》中的可馨与爱宛。最具代表性的是《首席》中的飘雪和梦烟。她们的关系经历了亲——疏——亲的过程:同江祖扬的三角恋和由此产生的误解,使她们由密友变成路人,作为外贸业的竞争对手,她们又长期在商战中狭路相逢,但心智和情爱追求的默契却使她们始终在意识深处同病相怜。当商战和初恋情结一同沉入“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留住”的疑惑时,她们再次为友谊举起了酒杯:“Cheers(干杯)!”这无疑是用友情抚慰爱的伤口,分享风雨人生的誓言。
当然,友情再浓再美也无法替代爱情,面对困守还是出击的爱情难题,对友情的趋近终不过是答非所问,误区并不能因此释然。同样,执著于自我的选择也只能达成精神上的些许安慰而不是解脱。救助的局限性深化和加重了失落的悲哀,这恐怕是女性误区的死结所在。
张欣笔下的女性对爱情难题的确是有所出击的,但她们又困守着自己先前认同的道德范畴和做人准则,这使她们不得不奔波于梦境和现实、行为和动机的反差中,出击得苦,困守得累,可她们却不作别样的选择。这就是误区中的女性,可爱又可怜,无奈又坚强。
张欣对她笔下的女性是既钟爱又同情的,因为她们身陷的误区很大程度上正是张欣对切身命运的感悟和投影。“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因为生活在一个开放城市,无形中被许多新观念包围,所以自己常常会成为一个矛盾体”,“停留在一片纷乱的冲撞之中”〔3〕。看来, 张欣不仅是女性误区的探索者,也是误区中的挣扎者,她用笔写下对女性误区的了解和点化,也用心与误区中的女性相伴。双重的身分既使她的感悟格外真切,又决定了她的探索需要更大的勇气,而突破则面临更大的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十年来张欣对女性误区坚持不懈的探索格外难能可贵,她那与心路起伏相呼应的笔下世界也有着突出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
四
近年来,张欣的创作越来越顺,一是产量大增,二是质量均匀,每年都有多篇作品被收入《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这当然与张欣的勤奋分不开,同时也得益于她创作切入点的选择。张欣选取了都市女性情爱误区这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和多样发展可能的生长点,并用色彩斑斓的人物、变幻莫测的事态将之充实、扩展开去,以情节化、动作化结构作品,有着较浓的戏剧意味和影视风格,言情不媚俗、谈爱不龉龊,没有脏字眼儿,也不人为地设置语言障碍,有着雅俗兼备的特色和优势,因而从阅读角度来说,张欣的作品轻松好看,引人入胜,可谓当前言情小说的成功之作。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综观张欣的作品后便会发现,在成功与顺畅、好看与轻松后面,也有着旧有言情小说模式化的痼疾和时下文学作品缺乏透视深度与批判精神的流行病。这势必成为妨碍张欣创作实现自我超越的隐患。
张欣创作的模式化体现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两方面。
从内容上看,一是人物形象类型化。张欣将女性按年龄分为“上一辈”、“转型期”和“下一辈”三代,从老到少分布于由旧到新的发展轨道中,一方面将“转型期”的女性置于新旧夹缝中,以“困守还是出击”的两难选择凸现其形象的丰富和复杂,一方面又将“上一辈”和“下一辈”放在非旧即新的两端。“上一辈”都是婚姻、家庭旧有观念束缚下的“传统”的奴仆,“下一辈”则都是以我为圆心、世界为半径的“现代”的主人。张欣解释说:“上一辈困守得甘心,而下一辈几乎已经有了与生俱来的冷漠,无论对得到和付出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4〕这种类似“进化论”的安排概而言之不无道理,但忽略具体的性格 成因、取向动机和个体差异,在多篇作品中都笼统地以“与生俱来”注释“甘心”与“冷漠”是无法令人信服的。用上下两辈人的简单化和类型化来衬托“转型期”这代人的丰富性和典型性,的确达到了鲜明突出的效果,但难免会造成肤浅和失真。
再让我们来看看“转型期”的女主人公们。她们单个看确实丰富多彩,但聚成群却仿佛成了孪生姊妹:骨感美人,洗尽铅华,模特般的身材,贵族般的气质,聪慧能干,独立自强,敬业却又为尊严、情感等非功利的因素辞职,重情却又为“痴”和“纯”饱尝精神的挤压。人物间彼此复印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内容方面的模式化还体现在情节设计上。家庭不幸,病魔入侵,多角恋爱和永恒友情是最为显著的四大模式。这种框架模式有时使张欣的新作也给人以老相识的感觉,减弱了阅读中的悬念和期待感。
模式化在人物情节上表现为类型化和雷同,在语言风格上则表现为缺少变化。将张欣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对语言的驾驭虽然越见熟稔老辣,但叙事技巧,表达策略,语汇选择方面仍是惊人的一致,历时的更新与共时的多向尝试都极少,不免有惯性书写之嫌。在这点上,张欣的创作比起张洁、张辛欣、毕淑敏等女作家就显得单调沉闷了些,不能不说有些遗憾。
张欣创作的模式化其实并非主观臆造和任意简化的产物,在对纷繁的现实生活的观照中,她确实体察到了某些惊人相似的人、事、情感和观念。忠实地传达这些生活模式是可以的,关键在于如何传达。文学对生活的超越正在于它在感性真实的基础上还有理性的概括与提炼,在平面的拓展中还有纵深的掘进,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张欣创作的模式化就会发现它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核心正在于缺乏一种透视的深度和批判的精神。就普遍而言,都市文学与都市现代化进程和都市人的观念嬗变几乎同步,与丰富多变的描写对象之间难以形成充分的距离,这就给作家增大了全面把握和冷静反思的难度。从作家的个性气质看,张欣不属于“站在人生边上”看人生的哲思型作家,她多次在创作谈中称自己是感受型作家,生活的读者。对笔下误区中的女性,她充满认同;对现实中的世俗人生,她总是“投入”。这影响了她艺术视野的开阔和思想上的高屋建瓴,眼光容易拘束在生活中周围人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向度上,也使她对个人感悟、自我体验的表达有铺陈和固执的倾向,难以进入一个更高的无我的境界,以实现批判后的认同和超越后的投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番肯綮之谈对张欣也应该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张欣创作中的局限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就都市文学而言,早在几十年前,评论家杜衡就不无焦虑地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这一焦虑至今仍有深刻的参考价值。面对都市文学作品大多满足于描摹世态,感性淹没理性的现状,有识之士呼吁要直面都市的灵魂,深刻思考人的境况和发展问题,切实探索与现代都市的内涵合拍的表达方式。就女性文学而言,个人经验范围内的女性意识和理想化、梦幻式的独白是不足以与深厚的历史,剧变的现实对话的,美善真情之外,还需要力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眼光。
有论者指出:我国70—80年代进行的文学变革是属于观念与思潮,方法与文体方面的,而90年代文学面临的变革则是生存方式,生存能力,生存气象方面的,需要对时代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大关心、大钟爱与大悲悯。〔5〕张欣正面临这样的挑战与召唤。 面对女性的误区和误区外的都市,张欣的文学二重奏会传出怎样的新声呢?
祝所有误区中的都市女性好运!
祝张欣在审视女性误区时,取得突破自身艺术局限的成功!
注释:
〔1〕曾镇南:《’93年中篇小说创作情况概述》,《当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5期。
〔2〕〔4〕张欣:《女性误区》,《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2期。
〔3〕张欣:《但愿心如故》,《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1期。
〔5〕徐剑艺:《论新都市小说》, 此文系《新都市小说选》绪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