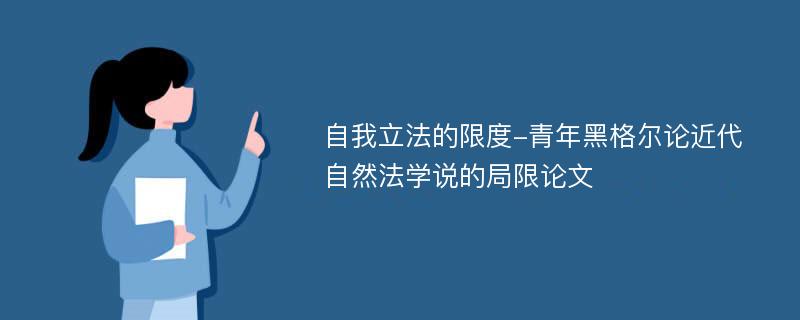
自我立法的限度 *
——青年黑格尔论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局限
罗 久
内容提要 在耶拿早期的“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通过对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种近代主要的自然法学说的批判,表明其自身的法哲学思想具有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不同的哲学基础、研究进路和论证方法。黑格尔指出,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研究虽然表面上彼此对立,却共享同一个前提,即它们都是从对自然的否定出发,以主观理性的自我立法为基础重新构造人的实践经验,使其符合主观理性的确定性和抽象统一性。在这个意义上,霍布斯式的经验主义恰恰是理性主义政治的始作俑者,而康德和费希特的形式主义不仅促进了理性主观化进程的完成,并且从根本上拒斥了超越主观理性的客观之道。
关键词 黑格尔 法哲学 自然法 经验主义 形式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格尔被视为是复辟哲学家和普鲁士威权政治代言人,人们甚至从这位“德意志民族哲学家”身上看到了纳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子。然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却使人们忽然意识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对于我们反思基于个人主义的抽象的法权观念、促进现代法制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建设以及普遍自由的实现,仍然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注] 罗久:《诠释镜像中的黑格尔法哲学》,《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而要想利用这一宝贵的资源,首先必须将黑格尔重新纳入到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之中去。就像英国学者佩尔钦斯基(Z. A. Pelczynski)力图证明的那样,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在研究进路、论证方法和理论化的水平上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梭的政治理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注] Cf. Z. A. Pelczynski, “Introductory Essay,”in Z.A. Pelczynski, eds., Hegel ’s Political Writings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p.135.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经过几代西方学者的努力,[注] Eric Weil, Hegel and the State , trans. by Mark A. Cohe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cques d’Hondt, Hegel in His Time :Berlin 1818-1831, trans. by John Burbidge, Nelson Roland and Judith Levasseur, Peterborough,Ont: Broadview, 1988; Z.A. Pelczynski, Hegel ’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Shlomo Avineri, Hegel ’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rles Taylor, Hegel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黑格尔的负面形象似乎已经得到了成功的扭转。基于这种新的研究范式,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显然既不是普鲁士国家的写照,也不是极权国家的一种预兆。相反,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法制国家(Rechtsstaat),黑格尔试图在他的法哲学中将法国大革命宣传的那些人权和公民权现实化,而市民社会的解放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石。
然而,这种将黑格尔重新纳入西方政治理论主流的做法有可能会导致另一个黑格尔被我们忽视掉,那个黑格尔对从霍布斯到费希特的西方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毋庸讳言,黑格尔的确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拥护者,他也试图在他的理论中吸收现代自由主义的成果。可是,黑格尔为自由和权利奠基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和近代自然法理论对此所做的努力。他对于将前政治状态(自然状态)的原子式个人作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起点深表怀疑,同时他还批判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理论,还有合法性与道德性的严格区分,以及康德或费希特意义上的自律的自由等等,这些现代政治试图达到的目标却被黑格尔视为知性反思的抽象产物,这些政治理论对人类精神和现实的理解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是片面的。由此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并非如佩尔钦斯基所说的,在研究进路、论证方法和理论化的水平上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梭的政治理论没有根本性的区别,相反,黑格尔与他们的区别是根本性的。黑格尔非但不是近代主流政治哲学的同路人,而且他的法哲学恰恰是在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
实际上,在耶拿早期的一篇重要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探究方式》(Ue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 ,1802-1803)中,黑格尔就已经通过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批判,表明了他关于法哲学的思考与近代主流政治哲学理论在目标、原则以及方法上的根本差异。正如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所言,这篇连载于《哲学批判杂志》(Kritisches Journal der Philosophie )的论文,已经具备了《法哲学原理》的基本轮廓,黑格尔在其成熟的法哲学中只是通过一个更加精致的体系性结构使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所有基本概念得到更为清晰和详尽的再现;而早期论文的“不太成熟的形式”则在这些概念的提出方面具有更高的原创性,并且给予它们以“更加美丽、新鲜和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的”表达。[注] Karl Rosenkranz,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Leben , Berlin: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olt, 1844, S.173ff.在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法哲学中,由于体系性的表述所带来的一些限制,无法完全阐明他的意图、立场和方法,而这一缺憾正好可以通过将这篇早期论文中黑格尔的观点与他所批评的其他自然法研究方式的对比来弥补。可以说,如果忽视了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传统的批判和吸收,人们就无法真正思考他的法哲学。[注] Norberto Bobbio, “Hegel und die Naturrechtslehre,” 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 Bd.2, hrsg. Manfred Riedel,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5, S.81.本文将以“自然法论文”为中心,透过青年黑格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局限,进一步理解黑格尔对自己的法哲学思想的独特定位。
一 、近代自然法研究的两种类型
黑格尔将近代自然法的研究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分别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和以康德、费希特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研究方式似乎是完全对立的,前者跟其他所有经验科学一样,通过对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多样性的观察、归纳和反思,赋予某些比较通常的、普遍的经验内容和日常信念以概念的形式,从而在科学的体系中将它们提升为基本原则;也就是通过对人们在面对不同情景时普遍表现出来的喜怒、好恶等情感或其他一些心理活动的抽象来确定哪些事情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哪些是应当的,哪些是不应当的。而后者则是不依赖于经验内容和感性或病理学因素的形式科学,它在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要求规范的确立是完全出于理性自律的无条件的先天立法,而不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来获得,因此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在建构自然法的科学时就与经验关系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完全对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两种自然法的研究方式的原则,一个是诸关系以及经验的直观与普遍物的混合,而另一个是绝对的对立和绝对的普遍性(GW4:420)。
双乙烯酮中控分析中样品含高聚物较多,且聚合物的聚合度不同,水解性能差别也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滴定分析的结果判定,所以双乙烯酮的手工滴定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方法所得双乙烯酮的含量能准确反映样品的真实情况,但所得醋酐的含量因受方法的限制存在明显偏差。所以,双乙烯酮的中控分析中,若要准确反映样品中醋酐的含量,仍需结合色谱分析,为防止样品中的固态物质堵塞色谱柱,应对样品进行必要的蒸馏预处理。
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分别从两个方面来批判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研究:在涉及到统一性或规范的普遍必然性方面,他主要通过批评康德对实践理性法则的演绎来揭示这种形式立法的空洞性和实定性;而在涉及理性法则要求在经验中达到一种的总体性或者说在要求从主观理性出发将世界作为一个合乎理性必然性的系统来建构方面,黑格尔则通过对费希特的法权体系的批判来表明这一形式法则如何在它的执行中导致理性自身的异化和形式同一性的暴力。[注] Jean Hyppolite, Introduction to Hegel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 p.46.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形式主义自然法学说。
二 、经验主义自然法研究的实质与限度
近代自然法学说分享了古代自然法传统对普遍必然的政治秩序的诉求,它们都认为,正当性和规范性本质上不能化约为那些仅仅是令人愉快的东西,或者说,存在着一种不为任何特殊的人类约定或习俗所制约的自然法,它之所以是普遍必然的乃是因为它合乎自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自然’是它原属的事物因本性(而不是偶性)而运动和静止的根源或原因”,[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构成了事物的本质或形式,它是所有运动和变化的根源,也是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所谓善的或好的就是与事物自身的存在或普遍的本性相适合的,古代自然法学说试图将人类共同生活的规范性基础建立在不以人的主观性和有限性为转移的事物客观的本性之上。
对霍布斯来说,这样一个分解-重组的程序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将自然法学说改造成一种像物理学那样具有确定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经验科学,是因为霍布斯认为通过这一分解的过程,他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普遍的要素,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一纯粹的自然情感完全像物理学中的力那样具有机械的必然性和数学的可计算性,将理性的法则和行动规范建立在这样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激情之上,使理性与激情结合起来,规范的客观有效性才能得以实现,也正是这种通过抽象和还原而得到的可以量化的激情使政治科学成为可能。因此,不同于古代自然法传统从人在整体秩序中的位置,即他的本质和目的出发来规定人的义务,近代自然法学说作为一门理性科学必须从自我保全的欲望中推演出法的内容,求生与畏死乃是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来源,那么,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确定不移的自我保存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公民社会或者国家的职能和界限必须以人的自然权利而非自然义务来界定。[注]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pp.180~181.在霍布斯看来,虽然他自己也是将德性和规范的形成归根于人的自然天性和激情,但是并不会因此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相反,由于这些激情依赖于数学模型的先天构造的产物,所以它们无一例外地遵循那种理性的无矛盾的确定性;普遍的数学作为一种认识的理想创立了这样一种理性的关系体系,它能把合理化了的存在的全部形式上的可能性、所有的比例和关系都包括在内,借助它能把所有现象都变成精确计算的对象,[注]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Neuwied : Luchterhand Verlag, 1968,S.307.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的自然法,并有效地预测、控制和征服人的激情。可以说,政治的技术化、人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国家由共同体变成了一种机械装置、一种人们为了实现彼此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而相互妥协所形成的契约性社会,这些近代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主张实际上都源于他们对理想政治秩序和自然法学说的科学性与确定性的追求,法的普遍必然性和有效性被建立在可以通过数学公式进行计算的合理性概念之上,理性与自然的源初统一的分裂也正是这一追求的必然结果。
亚里士多德基于他关于潜能与现实的存在论洞见,特别强调习惯、经验和过程对于人之本性或自然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却正是霍布斯的不满之处。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法的科学追求绝对的统一性,必须尽量避免矛盾和力求精确,而亚里士多德对经验的包容和他的目的论自然观恰恰使他无法向我们提供任何确定的知识,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掌握和调节我们的公共生活,甚至有再次陷入相对主义和战争的危险。正是出于对确定性和统一性的渴望,对矛盾和不确定的厌恶,促使霍布斯试图像伽利略将数学方法带入物理学研究那样,借用数学的分析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法理论,由此促成了古代自然法到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根本性转折。
西克(SICK)于1946年创建,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活跃于全球的集团公司,拥有近5 800员工,2011年销售业绩达到9.03亿欧元。西克中国成立于1994年,为SICK在亚洲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包括包装、汽车、物流和钢铁等行业。目前已在广州、上海、北京和青岛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并形成了辐射全国各主要区域的机构体系和业务网络。
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将数学方法应用于政治哲学,意味着政治第一次被提高到科学的高度,使得政治学能够具有像分析判断那样的普遍必然性,由此成为理性知识的一个门类,[注]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7、164页。 进而从根本上规避了激情和意见对政治活动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自然法的科学必须从对人的本性和对自然的否定(die Privation der Natur)[注] 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Hegels Reohtsphilosophie , Stuttgart, Klett-Cotta, 1982, S.86~87.开始。根据近代理性主义的观点,自然事物本身不具有那种可以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的规范性秩序,相反,我们只对那些我们就是其产生原因,或者其构造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或取决于我们的理性和意志的东西,才能获得绝对可靠的或科学的知识。[注]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p.173.近代哲学不再把世界视为独立于认识主体的东西,而主要地把它把握为自己的产物。由此,数学的方法,即从一般的对象性(Gegenstβndlichkeit)前提中设计、构造出对象的方法,就成了把世界作为总体来认识的哲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标准。[注]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 Neuwied: Luchterhand Verlag, 1968,S.288;另外还可以参考[美]维塞尔:《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贺志刚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60~67页。霍布斯将统一性的根据追溯到数学,并且按照这样一种理性的先验形式结构来重塑我们的经验,使人为构造的科学的经验(wissenschaftliche Empirie)能够按照一种统一的、可量化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摆脱自然的或日常的经验常常带有的那种含混、不确定和多义性(GW4:427),从而能够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经验知识,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可以用来指导人类政治活动的自然法的科学。
末次给药当日下午禁食,禁食24 h后,CO2吸入处死,开腹,结扎幽门和贲门,摘取全胃,向胃内注入2~3 mL 10%中性福尔马林固定液,将胃浸入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5 min,取出,沿胃大弯剪开(避开溃疡部位),轻轻洗去胃内容物,将胃平铺在展板上,测量溃疡面积(溃疡面积S=长径/2×短径/2×π),拍照,图片记录。然后将胃浸入10%甲醛溶液中保存。根据溃疡面积计算溃疡抑制率。
在《论公民》(De Cive ,1642)一书的前言部分,霍布斯提出了他的自然法科学的基本方针:对国家的认识就像对钟表的认识那样,只有将它拆开,分别研究其部件的材料、形式和运动,才能弄清楚每个部件和齿轮的作用。“在研究国家的权利和公民的义务时,虽然不能将国家拆散,但也要分别考察它的成分,要正确地理解人性,它的哪些特点适合、哪些特点不适合建立国家,以及谋求共同发展的人必须怎样结合在一起”。[注] [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 根据这种被称为“分解-重组”(resolutive-compositive)的方法,[注]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霍布斯首先从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制状态(Rechtszustand)中抽象出那些任意的、偶然的和时间性东西,人被抽去了一切在后天的文化教养中形成的各种质的规定,成为完全无序的、混沌的自然状态(Naturzustand)中一堆受制于机械因果必然性的同质的原子式个体;通过对现象的多样性的消灭,简单的统一性在这一无序状态中浮现出来。为了让这些杂多的、无规定的原子重新整合成一个规范有序的整体,就需要在其中引入一种必然能够贯穿于这些原子之中并将它们联结起来的力,在霍布斯看来,这种力来自于人类求生存的欲望和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最强大的激情引发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中只有遵循因果律的事实性而没有规范性,因而也就没有善恶可言,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而放弃自己对善恶标准的判断,通过相互妥协达成一个根本性的契约,将判断的权利让渡给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统一的规范必须由主权者的普遍意志和命令来赋予,由此才能重新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政治秩序、一个反映在经验多样性中的肯定的统一性和绝对的总体性(GW4:424-426)。
暗信号非均匀性的变化规律如图4所示,其随电子注量的变化趋势与暗电流的退化趋势类似。为了更加明显地给出暗信号非均匀性的退化趋势,图5绘出了辐照前后暗电流谱呈高斯曲线分布的情况。
当然,绿色印刷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局部的改变,应从印刷所需原料的采购,到印前、印刷、印后的全过程着手,进行绿色改革。比如在原辅材料采购上,盛通印刷采用通过国家环境标志认证的纸张、油墨和润版液等,选择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施环境保护措施的材料供应商合作,要求供应商提供材料的绿色认证,并在使用前进行环保测试。盛通印刷的纸张供应商均通过了FSC、PESC等认证。
不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像火总是向上运动那样是“由于自然或按照自然”的,它运动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像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人的伦理德性并不是自然直接赋予我们的,我们达到这些德性的方式毋宁是“经由习惯”;没有任何自然的事物可以改变自然赋予它的存在方式,但人的伦理德性却完全不是这样。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将伦理德性视为与自然完全没有关系,情况倒是“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注]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页。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人的伦理天性与他的自然禀赋不尽相同,它一开始是以潜能而非现实的方式存在着。所以,相对于自然事物,人的德性并不是先天的和普遍必然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培养他的能力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的养成并不是通过像服从先在的自然法则那样服从一成不变的规范就可以实现的,我们不是先知道什么是“公正”的概念然后才去做公正的事,相反,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而使他们变好,我们总是在现实的城邦生活中践行着那些因循我们的本性而形成的法律和习俗,才成为一个公正的人,这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和从潜能到现实的内在合目的的过程。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充满了对具体的德性和城邦实际生活状况的研究,在他看来,普遍秩序的寻求作为政治哲学和自然法理论的主题,不允许运用像数学那样严密的方式来处理,而应当同关于正义和善的种种观点意见达成和谐,同政治经验达成和谐。[注] [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7、164页。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并不因为没有事先对公民的行动规范进行规定,人们的行为、爱好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甚至是不一致,就会损害城邦的秩序,相反,普遍的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哲学所特有的那种确定性恰恰是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中逐渐生发出来的。
然而,将数学的方法引入自然法学说,通过对自然的解构和否定自然本身的规范性来建构自然法的科学,其代价是,从一开始这门新的科学就放弃了对那些根本性问题的探讨。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霍布斯的自然法科学只是一种“解释现实”的反思活动,他所关心的不是实在本身的规定,而是解释规范性形成的条件,即为了保证法则的有效性,实在应当如何被构造出来。因此,这种自然法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二元论,“以这样的方式,那种在一个方面被宣称为完全必要的、绝对的东西,同时在另一方面被承认为某种非实在的东西、单纯想象中的东西和思想物,在前一种情况下是虚构,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单纯的可能性,这是最尖锐的矛盾”(GW4:424)。在这个分解的过程中法的形式和内容被分离开来,而数学的自明性(Evidenz)只在形式上保证了法的确定性,却无法给予其内容的必然性以充分的证明,结果,为了超出量上的多数而达到一种统一性,只能把一些后天的、事实上行之有效的或普遍认可的规范作为主权者的意志片面地加以强调,以作为普遍立法的内容(GW4:426)。所以在霍布斯那里,那些经由抽象程序所设定的“人的本性和规定”与“能力”等等其实都是任意地被挑选出来作为自然状态的先验原则,因而:“在此分解过程中,经验主义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标准,以区别偶然与必然的东西的界限,并区分何者应该被保留在混乱的自然状态以及人的规定中、何者应该被排除其外。在这里,引导性的规定只能是为了叙述在现实中被找到的东西而同样地需要保存下来;在此挑选先天规定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则其实是某种后天的东西(das Aposteriorische)”(GW4:425)。为了说明法的内容方面的必然性,经验主义的自然法研究只能采取一种循环论证,将后天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当做人固有的社会性任意地添加到人的先验规定中去,而未能阐明规范本身内在的必然性,规范性的法制状态作为某种偶然的东西是外在地赋予自然状态的。[注] Jean Hyppolite, Introduction to Hegel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p.42.
某变量贡献率是指敏感系数与该变量多年相对变化率的乘积,即为该变量对ET0的贡献,若贡献率大于0,则称为正贡献;反之则为负贡献(Yin et al.,2010)。其计算公式如下:
一旦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作为自然法研究的目标,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古典自然法学说向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近代自然法理论的转变就在所难免了:一方面,人的所有关系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自然科学概念结构的客观形式;另一方面,行为主体越来越对这些人为抽象了的过程采取纯粹观察的态度。[注]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Neuwied : Luchterhand Verlag, 1968, S.310.换言之,我们应当也能够像研究物理对象那样来研究人类的规范性行为,在此基础上得出如自然的铁律一般普遍有效的规则以调节人的行为。当我们将求生畏死这样一种人为构造的经验归为人的本性,并且从人的自我保存这一自然权利出发来理解自然法时,基本的自然法就成了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并且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由此可以推出第二条自然法,即“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注]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8页。 换言之,对霍布斯来说,什么是自然正当的在于看一个原则是否有助于人类的和平共处,而这一普遍原则的达成取决于人们彼此放弃和让渡相应的自由权利,从而对彼此的自由任意构成限制。可是我们发现,霍布斯在这里提出的自然法理论只涉及法的形式条件,而根本不涉及内容本身的必然性;我们可以在彼此互不妨害的基础上订立各种理性的法则,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阐明这些法则就其自身而言必须被遵守的必然性,只要我们的共同利益改变了,法则的内容也会随之而改变。这样一来,政治就被还原为人的权利、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分配问题。这样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的政治和道德,以人的动物性自利和自保为基础来理解人类共同生活的本质,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并不可靠的底线伦理,使我们满足于免受他人的侵犯、摆脱对暴死的恐惧。然而,以满足自利为目标的知性技艺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和规定的形式合理性,自利本身又被抽象为一种没有目的和规定的机械活动,所以,当一种规范和约束阻碍了某一群体对自利的要求时,它的规范性效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而我们的底线也因此可以越拉越低,直到没有底线可言。
霍布斯对传统自然法理论的这一改造恰恰开启了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先河,黑格尔对霍布斯的批判主要也是着眼于这一点。正是霍布斯对传统自然法学说的改造首次“排除了一和多的绝对的统一性”,而代之以“抽象的统一性”(GW4:426-427),在人类政治事务中用数学的形式合理性取代了实质的合理性。尽管同样是从人的经验出发来理解规范性的根据,但这种通常被看作是经验主义的自然法研究实际上已经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经验主义大相径庭,而更多地灌注了近代理性主义的精神气质。恰如黑格尔所言,“古代科学将自身的活动限制在观察(Beobachtung),因为唯有观察能够就对象之完整的和未分裂的状态来吸收对象。而采取孤立隔绝的方式,通过人为设计的结合与分离来观察自然,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GW4:274)。这一转折从根本上颠覆了古代自然法传统,通过在经验科学中引入数学的模式,霍布斯用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神圣理性而完成了又一次创世,形式理性从混沌和无序中先天地创造出一个如钟表一般合乎数学和逻辑规则的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国家机器,在此基础上,自然法的科学才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有效性,但也正是这一转折将人置于客观的宇宙秩序之上,成为世界的主宰,而霍布斯也由此成为人本主义政治的先驱。
说实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一半是因为吴小哥对于三十年前那个古家庄的清晰程度,一半是源自我那未泯的良心,我不想欺骗一个生活在自己村庄幻想里的老人,也不想欺骗自己。
三 、形式主义自然法研究的悖论
近代的合理化进程绝对不会止步于霍布斯式的经验主义,相反,经验主义的自然法科学要想真正实现它的初衷,成为不受特殊性和偶然性影响并能够对人的实践活动进行预测和控制的科学,就必须依赖于形式主义所达到的一个“实定的组织”(positiven organisation)(GW4:421),即通过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将有限的经验内容转化为一个不允许有例外存在的实定的法权体系,赋予其“绝对”的形式,以克服经验主义中隐含的怀疑论的威胁。虽然康德的实践哲学是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研究与其说是霍布斯的自然法科学的对立面,毋宁说是它的真正完成。因为正是霍布斯对人之本性或自然的分解-重组,将人的现实的感性存在化约为纯然无本质的抽象(wesenlose)(GW4:432)和与规范性相对立的杂多的、无序的质料(自然状态),而康德和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同样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且以理性自律的名义将理性与自然、一与多的对立绝对化了。所以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对自然的否定”作为17世纪自然法学说的基本特征,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中达到了顶点。[注] Manfred Riedel, Zwischen Tradition und Revolution Studien Iu Hegels Rechtsphi -losophie , Stuttgart, Flett-Cotta, 1982,S.87~88; see also Ingtraud Görland, Die Kantkritik des jungen Hegel ,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66, S.166~167.
综上所述,《综合英语》系列教材文本的空白并不单独存在于某个层次中,而是贯穿了所有的层次。所以,《综合英语》教材文本的意义并不单独存在于某个层次中,而是多层次的复合体现。这种体现势必会导致其解读模式也是多层次整合的解读过程。
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经验主义没有在“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导致普遍立法的原则受制于偶然的经验内容,无条件的理性法则被遵循机械因果必然性的条件序列所消解。因此,经验主义的自然法研究不仅无法将自然法学说改造成一门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反而会使其暴露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攻击之下。真正的实践理性法则不能取决于行动者的偏好、特殊的情境或者行动的效果,而必须采取定言命令的形式,它是出于理性自发性的无条件立法。揭示出“法和义务的本质与思维着和意愿着的主体的本质完全是合一的(schlechthin Eins sind),这作为无限性的更高的抽象是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伟大方面”(GW4:441)。观念论哲学试图从理性意志的同一性而非特殊的偏好和自然的多样性出发来演绎法和义务的规定,康德的理性自律和费希特的实践自我是这一学说的最高表达。就此而言,自然法意味着理性法(rational right),[注] Jean Hyppolite, Introduction to Hegel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es of Florida, 1996,p.44.法的根据在于理性的纯粹自发性,它不受时间和地点等偶然条件的制约,而是以自身为根据具有内在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只有出于理性自身的无条件立法才具有无可置疑的天然正当性。
可黑格尔发现,康德和费希特通过知性反思所达到的那种同一性并没有忠实于他们最初的原则,因为对于反思的知性来说,同一性意味着对多样性和差异的否定,这样一来,“当它尽管把作为一的存在(Einsseyn)承认为本质和承认为绝对的东西时,它同样绝对地把分离放入一和多,由此使两者获得同样的地位。因而,同一不仅不是肯定的绝对的东西(它构成一与多的本质,并在其中两者是同一的),而是否定的绝对的东西或绝对的概念,因而那必要的同一成为形式的,并且两个对立的规定性被设置为绝对的,因而在它们的持续存在中落入观念性,这观念性就此而言是两者的纯然的可能性”(GW4:441-442)。既然现实的存在被先验哲学作为有限的和非理性的东西排除出意志的规定根据,那么,法的确立只能依赖于主体思维和意志的无矛盾性,这种抽象的同一又与那充满着矛盾和变化的实际存在相对立,因而实践理性法则作为一种出于理性自发性的定言命令必然只是作为思维中无矛盾的观念物而非现实。可是这样一来,无序的、杂多的现实反而比理性自身更加真实和优越,理性不是绝对者,而只能将合乎无矛盾的形式法则的理想世界作为理性信仰和“应当”设定在现实的彼岸。这种反思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本体与现象、理性与感性、自然与自由的二元对立。
但是黑格尔敏锐地发现,这两种表面上迥异的学说在它们的成分和处理这些成分的方式上却是一致的:为了达到科学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和普遍必然性,近代自然法学说都力图摆脱非理性的自然的影响以及多样性对统一性的制约,而从主体自身的先验理性来进行立法并且使人为构造的经验成为符合理性法则的统一性的总体,这一转向最终导致了理性与自然、概念与直观的分离。就像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指出的那样,自然(Natur)与法(Recht)的对立实际上是事实性(Faktischen)与规范性(Normativen)之二分的一种表现,自然在这一区分中被当作是价值无涉的事实领域,而与其相对立的法或规范则被归属于价值的领域。这样一来,自在存在就被理解成无序的和无规则的杂多,规范作为秩序的原则不是表现为存在(Sein)而是表现为效用(Gelten),[注] Karl-Heinz Ilting,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Aristotelischen Politik,” G .W .F .Hegel :Fr ühe politische Systeme ,hrsg .Gerhard G öhler , S.761.绝对者或存在本身失去了其作为规范性的终极根据的意义。可以说,正是由于对法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客观有效性的追求,使得近代自然法学说满足于对主观理性所构造的有限经验进行收集,并用知性概念加以整理和系统化,而不再承认也无法再认识那因其自身的缘故就是善和正当的绝对者(GW4:417),对本然之理和形而上学的拒斥成了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标志,如此一来,自然法的科学在法的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就变得缺乏“完全内在的必然性”(eine vollkommene innere Nothwendigkeit)(GW4:417)。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研究方式的确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是互为表里的:经验主义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将经验放入概念的形式统一性中来保证权利和法的绝对性或有效性(GW4:427),而形式主义则将有限的经验材料片面地加以形式化,从而把有条件的东西转化为理性无条件的自我立法的内容(GW4:429),二者实际上都是近代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在实践哲学领域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研究方式的批判正是想揭示在这些以自我立法和行动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为目标的实践哲学背后所隐藏的矛盾,以及它们为了达到这种完美性和理想性所付出的代价。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法则的演绎充分体现了形式主义自然法研究的反思性特征。对康德来说,应当之为应当就在于它不受制于因果必然性法则,所以必须将一切有条件的经验内容排除出规范性的领域,从无条件的理性自身出发来确定意志的规定根据。可是通过对感性的或病理学因素的排斥,康德就从根本上回避了所有涉及原则的内容的问题,他所关注的不是法的内容的必然性,而是如何确保法则在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这样一来,定言命令就变成了纯粹空洞的形式同一性。“纯粹意志和纯粹实践理性的本质是舍弃一切内容,因而产生如下自相矛盾的事情:因这理性必须具有一个内容,就在这绝对的实践理性中去寻找一个伦理立法,由于这理性的本质就在于没有内容”(GW4:435-436)。可是,法则毕竟是必须有内容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无法从理性自身演绎出它的内容的必然性,因而只能借助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来将某个特殊的准则提高为普遍立法的原则。
不过在黑格尔看来,经验主义从可量化的欲求和情感这一经验事实出发来确立自然法的研究方式,在面对形式主义时仍有它的优势。因为在经验主义那里仍然保留了对对象之客观性的意识,事实对于规范的形成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不可能彻底地否定自然、变化和多样性,像形式主义那样要求事实完全符合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而且,如果将经验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它就不可能停留在某些片面的规定上,理论对错综复杂的经验事实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不会让某一规定具有压倒其他一切规定的优势,或者认为客观有效的法则必须在所有时间地点都严格遵循,相反,对法则之有效性的判断总是随着情境和效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由于不一贯性,把诸规定性吸收到概念中的做法能够得到纠正,并且能够取消施加给直观的暴力,因为不一贯性直接消灭了从前被给予一个规定性的那种绝对性”(GW4:428)。这就使经验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具有了自我修正的可能性,并且在这种自我修正中自然与法、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统一仍然以一种歪曲变形的方式保持着。
康德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表达为:“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立法的原则”(KGS5:30)。可是,这样一个原则就像形式逻辑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任何真理一样,它根本无法阐明到底哪些内容、以及何以这些内容可以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则,相反,如果按照康德的想法来推断,任何规定性其实都能够被吸收到概念的形式中,并被设置为一个质,完全没有那种不能以这种方式被变成一条伦理法则的东西,只要它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普遍地、无矛盾地加以执行。但是,这种无矛盾性并不能消除这些规定本身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当有一个与一般认同的普遍法则相对立的规定出现时,两个规定中的每一个都有资格被考虑或者被提升为普遍的规定,因为理性自身并没有判断何者必须被保留、何者必须被抛弃的标准,它的根据倒是后天的(GW4:416)。在康德那里,道德和法的命令的演绎总是依靠将有条件的内容与无条件的形式混合起来,却从来没有从理性自身演绎出来。判断正当与非正当的标准在于看人们的行动中是否有矛盾出现,他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够将一个特殊的准则转化为普遍的法则而不使自身陷入矛盾,他就建立起了法则的正当性。[注] Georg Lukács, The Young Hegel ,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5, p.293.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实际上,纯粹实践理性的崇高的立法的自律能力真正说来只是产生同义反复(Tavtologie);知性的纯粹的同一性,在理论中被表达为矛盾律,在转向实践的形式时是一样的。如果向逻辑提问:‘什么是真理?’并让它来回答,给了康德一幅可笑的景象,一个人给公羊挤奶而另一个人拿筛子去接。那么实践理性追问:‘什么是权利和义务?’并让它回答,是一样的情形”(GW4:435)。
对康德来说,我们不能占有别人寄存在我们这里的财物以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是一条普遍立法的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旦违反了尊重他人的财产这样一条定言命令,把占有别人的寄存以增加自己的财富的这样一条准则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寄存本身就会因此而被取消,这条准则的普遍化必然会遇到矛盾。对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而言,外在的目的和所谓病理学上的和经验性的理由在定言命令中不应该被援引,而是必须由概念的直接形式来决定这一法则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寄存之所以不能被占有,或者财产之所以不能被侵犯,只是因为寄存是寄存或者财产是财产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分析命题,除此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理由规定我们的义务。实践理性法则不能违反矛盾律,或者毋宁说,在康德那里,无矛盾的就是正当的,他试图——至少是消极地——在无矛盾性原则那儿找到那个形式上,同时是规定内容和创造内容的原则。[注]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 Neuwied: Luchterhand Verlag, 1968,S.303、292~293.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财产必定存在,“财产是财产”作为主语和谓语的同一(A=A)是某种绝对的东西,但作为形式的同一性它对内容A本身毫不涉及,对形式来说,这个内容是某种完全假设的东西。所以,这个同义反复的判断并不能够为财产本身的正当性提供任何在内容上具有必然性的根据。在感性的内容对于理性的、预测的知性形式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上,理性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理性立法在内容上的这种非理性正是由近代的知性逻辑和在实践领域追求数学科学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所产生的问题;尽管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可以保证法则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它在内容上就是合理的,相反,在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中法的内容的存在和存在方式(das Dasein und das Sosein)仍旧是一种完全不可溶化的既定事实(unauflösbare Gegebenheit)。[注]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 Neuwied: Luchterhand Verlag, 1968,S.303、292~293.所以黑格尔说,“唯一关键性的东西是在纯粹理性的这种实践立法的能力之外的东西,即决定对立的规定性中的哪一个必须被设置;但是,纯粹理性要求这已经事先发生,并要求对立的规定性中的一个预先被设置,只有这样,纯粹理性才能够实现它的现在多余的立法”(GW4:437)。
黑格尔对形式立法的批判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康德的演绎中,应当的必然性(die Nortwendigkeit des Sollens)和应当之物的偶然性(die Zufälligkeit des Gesollten)之间的对比显得尤为触目。根据康德对实践理性法则的演绎,法则的内容并不以某种实体性的在其自身规定的存在(Insichbestimmtsein)为根据,而是奠基于准则的主体性,而且命令的必然性并不同时是它的物理的现实性,只是准则的普遍有效性。因此,恰如黑格尔所言,康德式的定言命令“通过绝对的形式与有条件的质料的混合,形式的绝对性意外地被偷运到内容的非实在的东西、有条件的东西上,而这种颠倒和戏法则位于纯粹理性的这种实践立法的核心”(GW4:438)。在这里,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特点,那就是建立在分析命题或同义反复基础上的自明性,通过这种形式使一些并非天然正当的东西在人们的日常信念中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主观理性的形式立法使偶然的东西和外在的经验的必然性成为绝对的法则只要以数学真理的自明性、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为样板的合理化模式这一基础没有改变,人类就会始终将非理性的因素保持在形式合理性当中。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他们对那种在一切时间和地点都有效的普遍立法的追求,关于什么是“善”和“正义”,以及什么是一个理性行动者应当去做的等等规范性的要求被作为自明的“理性事实”直接给予我们,并且要求我们的情感、意志和欲望全部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规定。这种隐含着非理性因素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学说所留下的是哲学的独断论,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把它的思维形式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由此,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不仅比经验主义更彻底地陷入了经验的必然性,而且在普遍意志的名义下更进一步地加固了理性与自然的分裂,产生了新的不自主,这在费希特的自然法学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通过知性反思所得到的形式法则必须在现实中有效地实行并由此建立起一个合乎理性法则的共同体,才能证明这种自然法学说的科学性和法的绝对性。可是,费希特的自然法学说就像他的知识学一样未能真正贯彻同一性的原则,反而是预设了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对立,在他看来,与普遍意志的合一不可能从特殊的、个别的意志中产生,而是必须作为应该通过外在的关系或强制而产生的东西(GW4:443)。黑格尔将费希特的合法性体系称为强制的系统(Zwangssystem),对费希特来说,通过强制使个别意志服从普遍意志的统治,是使人摆脱自然的机械必然性,实现理性立法和自由的唯一方式,[注] [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43页及以下。 可是这种强制的系统却把国家本身和它的统治变成了一种没有生命的机械活动(GW4:58)。
因为主观观念论哲学通过知性反思的方式将同一性等同于确定性和无矛盾性,对同一性的坚持就产生了非常吊诡的结果,即为了证成世界合乎理性的统一性,在尘世间实现至善,实践理性的无条件立法应当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得到严格执行和坚决贯彻。可这样一来,合理化所坚持的那种知性的同一性就变成了一种强制和异己力量的统治,理性之法(Vernunftrecht)作为一种自由的因果性实质上就变得与机械的必然因果性无异了。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形式主义用这样的方式不仅放弃了在它称之为经验的东西面前的一切优势,并由于在有条件物与条件的联系中,这些对立物被设置为绝对存在,形式主义本身就完全陷入经验的必然性,并通过形式的同一性或否定的绝对者(形式主义靠这个把对立物集中起来)给予经验的必然性以真正的绝对性的外貌”(GW4:423)。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将自由和正义等同于排除了一切差异和变化的知性的同一,它热切地渴望实现一种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说的“完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fection)或“齐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uniformity),[注] [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希望人类可以按照出于理性的普遍必然性的法则而非自然的偶然性来建立一个普遍按照法权来管理的公民社会,能够通过将自然置于自由、多样性置于统一性的统治之下来消除怀疑与纷争。然而,这种合法性的体系只是“形式上的无差别(这无差别在自身之外有有条件的差别物),是无形式的本质,无智慧的力量,无内在的质或无限性的量,无运动的静止”;“在靠机械的必然性而进行的活动中的最高的任务是用普遍的意志去强迫任何个人的活动”(GW4:443)。也正因为如此,法律的执行就变成了一种强迫,犯罪与惩罚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是一种机械关系,而不是自由的实现。在这样一种法权体系中,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由于触犯他人的权利或未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应当接受的惩罚都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来,惩罚就像一种商品,而犯罪就是它的等价交换物。所以黑格尔才不无讽刺地说到,“国家作为法官的职权,在于举行一个带有诸规定性的集市贸易,这诸规定性叫做各种犯罪,并出售以交换得到其他诸规定性(各种惩罚),而法典就是价目表”(GW4:449)。
尽管理性立法的绝对性和现实合乎理性的统一性本是主观观念论的实践哲学的最终目的,但是这一目标却不可能通过对抽象的形式同一性的坚持和对自然或多样性的否定来实现。首先,因为形式主义的实践哲学将对自然法或规范本身之合理性的认识变成了对实践法则的形式条件的认识,将自然法的科学变成了实践理性批判,这样一来,无矛盾的确定性就取代对法的内容及其内在必然性的探究成为自然法科学的最高目标,理性的统一性满足于一种主观的、形式的统一性。黑格尔批评这种理性法则是空洞的和形式的,这并不是说道德或法在它那里没有具体的内容,而是说,这种内容缺乏出自理性的内在必然性;理性的统一性在内容上受到外在于理性自身的现成存在和偶然的感性因素的制约,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理论的工作只是将一些历史形成的或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信念与准则加以整理,使其具有合乎理性的外形。因此,尽管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强调了理性的无条件性和普遍必然性,但由于这种普遍性只是形式的普遍性,它的内容并不是出自理性自发性的产物,所以它在实质上仍然是经验主义的或有条件的。其次,对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理论来说,只有不受一切经验条件制约的定言命令才是以理性自身为根据的无条件的法则,所以,真正的绝对者即合乎理性统一性的世界必然要按照定言命令来运行。可是,道德行动和法律作为无条件的理性立法的实施,在形式主义的实践哲学体系中必然表现为为法律而法律、为义务而义务的行动(das Gesetz um des Gesetz willen,die Pflicht um der Pflicht willen)(GW4:402),这种排斥一切感性因素影响的实践,将权威对个人的统治这种外在的异化,转变为人自身的异化,表现为知性同一的形式法则对杂多的经验内容、理性的方面对感性的方面的统治,理性的自我立法和理性行动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最后,这种出自形式合理性的规范性要求一方面排斥自然和经验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又需要在与多样性的对立中来保持自身的同一。因此,这种否定的道德和法权体系只具有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整个实存的领域都处在理性的统一之外;而为了证明实践理性法则的绝对性,理性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转而通过压迫和强制的手段来维护形式立法的绝对权威,或者求助于对道德的世界秩序(moralische Weltordnung)的一种非理性的信仰来激发行动者的伦理动力以保证理性法则的有效性和现实性(GW4:270),在无尽的“应当”和“公设”中满足自己对完美秩序的渴望,普遍与特殊、自然与自由的对立就在这一主观理性的统一中被永恒化了。[注] 罗久:《理性信仰的悖论——青年黑格尔对康德实践理性公设学说的接受与批判》,《基督教学术》第16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261~288页; Geor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tsein , Neuwied: Luchterhand Verlag, 1968,S.302~303; Heinz Kimmerle, Das Problem der Abgeschlossenheit des Denkens, Bonn: Bouvier Verlag, 1970,S.211~212.
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及其所有后果都与它自身的原则即理性的绝对性和理性自律相背离,它将自然与理性、实然与应然的分裂和对自然的否定推到了极致,事情本身的规定性或本然之理与主观理性的形式法则之间完全对立,人的自我立法取代事情本身的必然规定成为规范性的来源。正如黑格尔所言,“自然法应当阐明伦理自然是如何达到其真正的法(Recht);反之,如果否定的东西(不仅本身而且作为外在性的、形式的道德律、纯粹意志的和个人意志的抽象),以及这些抽象(例如,强制,普遍自由的概念所限制的个人自由等等)的综合表达了自然法的规定,那么,它可能是一种自然的非法(Naturunrecht),因为通过把这种否定作为基础性的实在,伦理自然将陷于绝对的毁灭和灾难”(GW4:468)。由于成功地将普遍性与每一个特殊的经验规定分离开来,形式主义的自然法研究把反思性的论理发挥到了极致,[注] Jean Hyppolite, Introduction to Hegel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6,pp.42~43.它通过援引形式逻辑的抽象的同一性来确定意志的规定根据,用知性的相对的统一性取代了理性与自然的源初统一,使理性自律最终走向自身的反面,而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在它的执行中异化为一套实定的、压制性的法权体系。
四 、黑格尔自然法批判的意义
方法论意识的优先性和普遍数学的理想构成了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基本特征。数学所具有的这种抽象的、普遍的自明性帮助人类征服了自然,我们充满信心地利用数学的工具将这个变化无常的自然界置于理性那整齐划一的统治之下;精确性、可重复性、可预测性成了科学的标志,不论是霍布斯还是康德和费希特,他们都希望这种合理性与科学性可以在人类实践的领域中被复制,由此催生了近代自然法学说的诞生。然而,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批判却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即涉及到人类行动的规范性领域不可能有完美的立法,但并不是由于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使这一完美的立法不可能,而是因为以数学为样板对人类的本性与实践活动所进行的还原和重新构造并不能真正把握人类经验的复杂性。真实存在的东西由于它自身的复杂性而不可能还原为数学真理的自明性,但这复杂性和多样性背后又并非没有它的合理性与合法则性,在黑格尔看来,真正永恒的和绝对的理性之法就其本性而言恰恰是在各种特殊、差异和矛盾中展现自身的规范性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批判,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回避之前的研究过分地依赖于经验或神秘的猜测的做法,“使自然的、特殊的意志服从属于普遍意志而成为理性立法的目标和标志”。[注] 邓安庆:《论黑格尔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他更进一步从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自然法研究的表面对立中,揭示出二者共同的基础。形式主义的自然法学说借助分析命题的同义反复将特殊的规定转化为绝对的法则,并且要求在公民社会中毫无例外地服从这个普遍法则的统治,将这一强制视为自由的表现,由此固化了理性与自然的对立。而霍布斯式的经验主义研究虽然看上去是从人类普遍的求生与畏死的情感出发来确立意志的规定根据,但是这种所谓的普遍情感经验却是理性反思和对真实的人类经验进行解构与重新建构的产物,而对经验的理性重构是霍布斯将政治哲学改造为一门数学科学的重要环节。这样一种经验主义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底色,它对直接的感觉经验和日常信念的不信任,与康德、费希特的形式主义自然法研究是一致的,这两者在黑格尔眼中都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这种理性主义在实践领域中越是追求合理化、坚持数学式的确定性和抽象的同一性,反而越是拒斥了真正的绝对者、越是导向主观主义和非理性。因此,黑格尔对近代自然法研究的批判延续了他耶拿早期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注] 罗久:《从启蒙的教化看黑格尔的康德批判——以耶拿时期的〈信仰与知识〉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罗久:《论黑格尔对费希特主观观念论的批判——以耶拿时期的“知识学”为中心》,《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 对确定性的执着追求,使得特殊与普遍、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在反思中完全对立起来,最终导致了理性自身的异化和实践中对客观之道的拒斥。对黑格尔来说,人类行动的法则及其正当性的根据当然不能是因人因时因事因地而异的,立法的普遍性是自然法学说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法的普遍有效性并不等于无矛盾的确定性,而近代自然法的探究方式恰恰是基于这种无矛盾的确定性,制造了自身同一的理性法则与特殊的、矛盾的现实之间的对立,消解了理性自身的现实性。因此,只有突破反思哲学的非此即彼,使理性不再是为了避免差异和矛盾而以设定对立物的方式来保存自身的主观理性,而是作为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源初统一被把握时,理性之法的绝对性及其内容上的必然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注] 罗久:《黑格尔法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第2卷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6~216页。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德国早期浪漫派政治哲学研究(1797-1802)”(17CZX038)
〔中图分类号 〕B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9)04-0061-12
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责任编辑 :王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