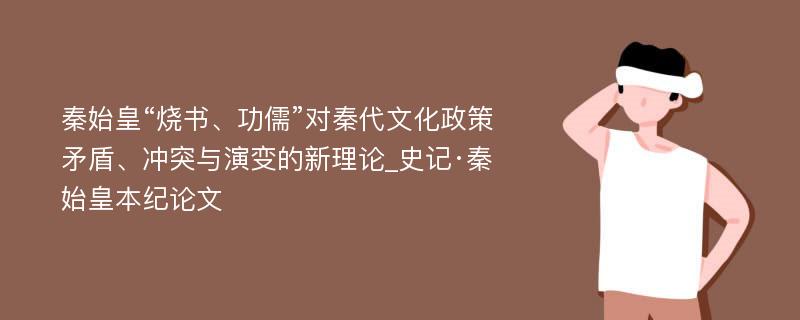
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论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矛盾冲突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王论文,焚书坑儒论文,新论论文,冲突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4)06-0024-06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重大政治、文化、学术公案。从汉至今二千余年,对此的评说不绝于史。有秉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亦有对此存疑或疑为夸大其事者。细研史籍,我认为始皇“焚书坑儒”是与秦统一之初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极大差异的。它标志着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政治、文化取向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亦是秦始皇本人帝王心理失衡的个性心理特征在政策上的反应。
一
秦统一六国,除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有着一以贯之的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政策、措施外,还在文化一统政策上有着细密的思考。从当时形势看,地处关中,久处戎、狄的秦与关东六国、尤其与东方滨海的齐鲁之地相比,其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上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秦地处关西一隅,其风格“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表》)。而关东诸国,尤其是齐鲁之地,是周以来的“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孔孟之徒、缙绅之士播及远近。且不论战国时齐稷下学宫之盛,邹鲁之士谈仁说义,靡然向风;仅就《汉书·儒林传》所载继秦不久之西汉著名文士地域分布看,齐鲁士林上承东周,文风之盛,亦在全国首届一指。《儒林传》所载文士212人中,有籍贯可考者191人。这191人中,鲁国人最多,达31人;其次为琅邪郡19人,东海郡17人,齐郡12人。此四郡共占有籍贯记载之文士的41.3%,而鲁一地则达到16.2%之多。可见,在西汉山东滨海一带仍是全国重要的人文渊薮,名士辈出之地,也说明了齐、鲁在全国占据的文化与学术优势。
秦统一前夕,应该说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有着初步的估计,这就是秦的武强文朴。秦挟“虎狼之师”,横扫六合;但它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却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诸夏耻与之,这不利于它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从史籍记载看,秦在东周以降,其学术、文化著作之质与量实与关东六国不能抗衡。《汉书·艺文志》等书所载目录中,我们所见标识秦国卿、相与士人所著的仅《史籀》、《商君书》、《秦诗》、《由余》、《田俅子》、《秦谶》、《尸子》、《张子》、《吕氏春秋》等书之目,这其中大部份还是由六国士人仕秦时所著。而其书中内容主要涉及兵家、法家、农事、历法、小学、占卜等实用与“中用”之学:如《史籀》系文字之书,《秦谶》系阴阳卜筮之书,《商君书》取自法家,《田俅子》取自墨家。这正与秦由来已久的农战论与功利观相一致。而关东六国与秦相比,则人文藩滋,文学之士比肩。基于这种武强文质的情况,早在六国统一之前,始皇帝的“仲父”、秦相吕不韦便召集六国士人,作《吕氏春秋》一书。《史记·吕不韦列传》记: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从这段记载看,吕不韦作《吕氏春秋》,乃是利用六国辩士,兼容六国学术智慧,对即将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进行的一种文化“自立”行为。从吕不韦居官之尊及他对此书所任之重,可视为一种统一前夕所给出的对未来帝国的文化导向与政策暗示。《吕氏春秋》被后代史家文人公认为杂家之学。而《汉书·艺文志》评论杂家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从班固所论来看,杂家之学在当时被看作涉政类书籍是无疑问的。它的优点是合儒、墨、名、法之教,以知国体,资王道,“贯”王治;其不足处是荡者为之则散漫而寡要。关于此书内容,亦是遍及诸家思想。如《吕氏春秋》序高诱注曰:“……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高诱见解受后代儒学影响,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可是指出该书综罗百家,试图“经天纬地”的观点却是持平的。这可与吕不韦在该书其它内容相互发明。因此,吕氏著书,其用意深刻。该书从体例到内容的最大特点,便是广涉诸子,遍引诸学,揉合道、法、儒、名、阴阳、兵、农诸家,试图为帝国奠定新的则天法地的“大圜”“大矩”。而却绝无商韩“燔书”“禁学”之文化专制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吕不韦对于秦统一后文化政策上表现出的一种倾向。
但是,西秦及吕不韦的悲剧在于,这种文化的“自立”行为,竟然只能采撷六国之学,“使其客人人著其所闻”,对六国文化与学术实行大规模的剽窃与综罗。这从某一方面,亦可以看出秦文化底气的不足以及文化内涵的单薄。《吕氏春秋》意欲成“帝王”之言。它虽然未能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但也似乎发出了一个政策信号,即文化上的统一主要以融合与吸收为主。这也正是文化力低下的民族在对文化力较高的民族在武力征服过程中所遇的障碍及其通行的规则。因此,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庞大武功帝国后,它并未采取自穆公以来所实行的商、韩厉行禁止“文学之士”的文化一律政策,而是对关东六国尤其齐、鲁之士实行了开放、容纳及礼遇的对策。据史载,秦开国时置博士员甚众,基本上是齐、鲁之旧儒生。“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史记·封禅书》)从史籍看,七十人大约是秦宫廷所置博士员定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博士七十人未对。”(《说苑·至公篇》)在中央官吏职能中,博士乃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北堂书钞》:“秦博士,典教职,礼仪之所寄也。”(《北堂书钞》引晋中书郭璞语)各书大多称秦置博士70人,而始皇即帝位三年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说明博士来源乃是以齐、鲁之地为主。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下,这应当是一支庞大的在秦宫廷服务的东方文化队伍及文化势力,也是一股言论力量。从史籍可考的秦博士所持学术来看,主要是来自于齐、鲁儒家者流之习研经术文学礼仪者。如“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漯水又东迳汉微君伏生墓前,碑碣尚存,以明经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隐。”(《水经·河水注》)“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此外,散见于史籍有姓名可考的秦博士还有周青臣、淳于越、黄疵、桂贞、沈遂、茅焦、羊子、高堂生等;亦有汉初“四皓”为秦博士之说。故而郑樵评论秦时儒风未衰时说: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秦时未尝不用诸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后,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通志·校雠略一》)
秦始皇在帝国广置博士员,任用齐鲁儒生的同时,还不断地向东巡游,封禅泰山,挟武威以宣其文治。据史载,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多年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出巡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滨海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上泰山,“并渤海以东,过黄、月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遂之琅邪”;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并海上,北至琅邪”,由之罘“西至平原津”。
在古代舟车极为不便的情形下,这么频繁的出巡,驱车而东,其有关国是的重大目的是不难想像的。始皇每到一地,都要刻石留念,以志秦威。如《峄山刻石》《琅邪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等。而刻石内容,不外于“颂秦事,明得意”“表垂于常式”“垂著仪矩”“光垂休铭”。尤其在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的《琅邪刻石》中,有这样的内容: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与议于海上,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始皇好于刻石,无疑是颂扬帝德,炫耀武威。但东巡刻石中倡扬“道”“德”尤甚于宣染其武功,这不是偶然的,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士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说明秦上层统治者是深知文治武功之互补的。而其“道”和“德”的内容也包含了儒家礼仪及孝、贞的伦理规范。例如泰山刻石有:“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史记·秦始皇本纪》)会稽刻石文:“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同上)峄山刻石有“孝道显明”等提倡孝道的话。故顾亭林在《日知录·论秦刻石》中道:“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顾氏之言,应见秦文化政策之一端。
在始皇所立“博士”中,既有邹鲁儒学之士,也不乏齐之阴阳方术之士。如位列七十博士之中的卢生、侯生,便是始皇引为“以鬼神事”“求芝奇药仙者”的方士之流。秦始皇多次巡游滨海之域,其深层心理,还有接近并探求神仙世界的期望。《史记·秦始皇本纪》曰:“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自此开始了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求仙运动。求仙运动是帝王对权势欲求无限的放大,是对永生的追求。这之中包含了他个体心理上对权势的自信、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滨海之域神仙文化的一种迷信与希冀。这种个人心理的因素,始皇在位时间越久,就越强烈地反映出来。“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道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史记·封禅书》)这种至死不渝的追求神仙及长生之药的行为,说明齐之滨海文化对秦上层统治者思想影响之巨。这也可以从始皇“行礼祠”齐之八神得到说明:“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史记·封禅书》)。根据《史记》记载,太山梁父、之罘、成山、琅邪都为始皇所亲历,说明祠齐之八神确有其事。中国古代由于从史前社会过早过渡到阶级社会,各诸侯国统一的宗教神尚未确立。以各部族神为代表,而沿袭史前遗风的“泛灵论”,在古代为各国君王所重视。尤其承戎狄之俗的西秦,质朴的关西鬼神文化不能满足统治者之欲望。因此,始皇多次巡游东方,行祠齐之八神,既有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对滨海之“齐”的文化尊崇,又有对神仙芝药的梦想。这应当是研究秦宗教与文化政策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战国末期秦国研究一统文化政策时以法家思想为主,兼及儒、道、阴阳诸家的一种余绪吧。
但是,在秦帝国武强文弱条件下制订的对关东诸国的“文化怀柔”政策,却因东西二域两大文化系统的差异与冲突而迅速遭到挫折。
秦以军功立国,骨子里尚力轻文、重利而鄙道德。《荀子·议兵》:“秦人其生民以狭厄,其使民以酷烈。”郝懿行《荀子补注》云:“狭厄犹狭隘也。”《史记·刺客列传》有“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的说法。而关东六国,尤其居东的齐、鲁一带,自古多说士墨客,其行止多“宏大不经”,士林承稷下之风,多有恣荡自由之谈。这就使两种文化系统及社会心理的融合不是短期可及,一蹴而至的。更重要的是,秦帝国的上层统治者并未深切理解吕不韦的良苦用心,没有认识到文化融合问题对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们骨子里迷信以“力”取天下,治天下,将文化怀柔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工具。正如秦始皇本人所谓:“(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里提到的“兴太平”之术,实际上表达了始皇帝对经术文学之士和方术之士的两种异中有同的认识:经术文学之士欲以兴太平,是一种治国之略;方术之士欲练以求奇药,是帝王个人求仙长生的需求。这两种需求都是“兼”的内容,也是帝国武功的延伸。在统治者看来,它们都是附冀于帝国专制独裁与军功这张皮上的毛,是粉饰文治武功和帝王延年益寿的需要,不涉及帝国的“力”治的基础与统治的根本。这种以文学方术之士粉饰太平的作法,是对文学方术之士一种骨子里的轻视,它表现了秦人重武轻文的狭隘性、功利性与短视性。这样下去必然会使帝国初期执行的耀武兴文,以齐、鲁之经术文学礼义补帝国之治化的政策受到破坏。
事实确是如此。早在始皇二十八年封禅泰山,秦始皇及其僚属就与齐鲁儒生在祭拜礼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
从秦之官僚体制看,“天下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量,不中量不得于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今遇有邹鲁古风、宏迂不经的儒生不识时务的“各乖异”议,虽仅涉及到封禅的交通等小事,但它是对以武恃强的秦专制君权封建体制对关东文化容纳限度的考验。可惜的是秦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了“绌之”即排斥的方法,这便引起秦、齐重“力”重“道”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儒生博士在初始兴致勃勃,而后“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这种奇耻大辱后,借始皇遇风雨亦反“讥之”,由此揭开其后冲突的序幕。
始皇三十四年,即秦山封禅事件六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政体与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爆发。“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紧接着批评始皇不师古、不分封子弟功臣,不是久安之策。于是在师古与分封问题上产生争论。丞相李斯以法家立场否定了淳于越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请禁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便是名著史籍的李斯焚书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即秦代文化政策的取向与如何对待儒生代表即博士员的问题。从秦代文化政策看,当时正面临原关西秦域与关东诸国地域两种文化的冲突。秦虽然采取了文化兼容的政策,来解决重“力”与重“道”,武强文弱的矛盾。但是,在王朝短短八年的实践中,秦欲以经术文学之士“兴太平”,带来的却是与秦的专制、皇权、秩序、服从以及相应的文化禁锢政策相反的结果,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的官僚体制及其影响的文化制度正受到广泛的社会批评,这可以从“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看出其中实情。而这种社会层面的文化批判是本之于先秦诸子之学、本之于与法家相异议的各学派。这种“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战国百家争鸣、“处士横议”风气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武功帝国专制政体的批评,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帝国的“官学”以及法家为本的意识形态,即所谓“非法教”。面对这种挑战,如果以一种涵容的、宽怀的眼光去看待,处理,历史将可能会导向另一种结局,秦王朝将会走向另一种未来,即以“道”“德”为本的长治久安。因为仅从当时强大的武功帝国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实力看,是不会被这承先秦余绪的百家“私学”的区区议论所击垮。可是,历史进程在这里显出了它的必然性。既然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能取得赫赫功勋,君临天下;那么面对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上的差异,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来。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这也就是李斯所主持的“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
平心而论,任何政权在刚建立时,都有统一思想、意志的需要。这是巩固政权的基本条件。但对秦帝国而言,面对关东诸国曾经历的诸学杂陈、诸子争鸣的巨大文化遗产、文化余绪、文化现实,应当如何对待,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探索、对待并涵融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秦相吕不韦在大统一前夕对吞并六合后秦帝国文化取向的深邃眼光以及以诸子杂取作为大规大矩的思想。
秦帝国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采用极刑对待敢于街谈巷议、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者。这就将西秦的文化专制主义施向全国,将帝国的专制、服从、秩序、等级、军功引进文化领域。从这时起,帝国初始的文化怀柔政策被原西秦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文化禁锢政策所取代。它也宣告帝国初期企图以怀柔文化而“兴太平”,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取向的彻底破产。但李斯进言中,对东方文学经术之士还留有一丝“关照”的缝隙,这便是位居博士员的经术文学之士还保留持有与议论《诗》、《书》的权利,即“非博士官所职……”。但在全国焚诗书的高压氛围下,这一权利又能延续多久呢?它的实际价值何在呢?果然,“焚书令”实行后不到三年,秦宫廷又爆发出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这就是“坑儒”。其实,早在实行“焚书”“禁书”令后,帝国的文化取向就十分显明,而文学经书之士(包括朝廷上聊作粉饰的博士儒生)的命运也被早早决定了。这就是导致“坑儒”事件的方士侯生、卢生所说的“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侯生、卢生以始皇“贪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的理由逃亡。这下子引爆了始皇早已久忍在心的怒气。“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段话看,始皇大怒的原因一是涉及个人心理因素,即耗巨资遣方士求长生仙药的愿望落空。根据史籍,前有徐市、后有卢生等人赴海求药,但“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成为世人讥笑的把柄。这使权势欲无限放大的始皇在求仙的精神追求中遭受挫折,不由他不大发脾气。二是方士的逃亡再度引发他对儒生的怨恨,积怨由此爆发。本来,在秦帝国上层对关东文化的认识中,儒生与方士处于同样地位。儒生谈经书,方士则秉承战国阴阳家学说,而日益世俗化、神仙化、闲散化。两者在秦初俱是滨海文化的主流。但一是学术,一是卜筮。从当时观念看,学术以道德、文章干政;卜筮以求仙、遁世营造另一人生极致。这对秦帝国统治者来说,俱有利于饰太平,求神境。这种将儒生与方士相同看待的观念,可能正是重实用、讲功利的秦人对东方文化理解上的错误,也可能正是他们对儒生、经书、《诗》、《书》、礼乐加以轻视的深层心理原因。不论怎样,方士的逃亡,引起始皇对儒生方士群体的忌恨,于是残酷的株连与镇压拉开了帷幕。史载“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
对于始皇实际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看法。如《盐铁论·利议篇》引大夫语曰:“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史记·儒林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后汉书·陈蕃传》注则具体指为在汉新丰县温汤之处以视瓜之名皆坑之。被坑的人数亦有七百多人至四百六十余人不等的说法(《文选·西征赋》注作四百六十四人,《论衡·语增篇》作四百六十七人,《诏定古文尚书序》作七百人)。但不管怎样,坑儒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诛杀儒生多少或手段如何,而在于向天下昭示秦帝国文化政策的取向,昭示帝国以“力”制文的既定政策。正因如此,在“坑儒”并“使天下知之”后,帝国内部一片禁文肃杀之氛。连公子扶苏为“诵法孔子”的儒生辩护进谏,也被视为大逆不道,贬边远上郡,远离政治中心的京城。至此,秦虽然仍保留了“备员弗用”的博士官一职,但其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自此湮灭。秦宫廷中聊以备员的“博士员”即经术、文学代表的士群体,自此沦落为聊备皇帝顾问的吏员,而中国帝制下的文化定位由此有了“独尊一术”的取向。其后叔孙通以“园滑”著称于世,是士群体在权势高压下对专制政体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也开启士群体在专制政体下儒学价值观与承意顺命,“道义”与威权二者谁寄于谁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其后儒家再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禁锢专制政策的产生以及文化专制的延续,应是这一专制理念的延伸。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秦帝国建立之初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定位与其后采取的极端的文化禁锢举措有所差异。应该说,帝国初始时的文化定位乃是试图融合关东关西两大价值系统文化,实行文化怀柔与文化融合政策。不希望引起关东关西文化冲突大约是秦帝国最初的文化政策取向与文化目标。这和《吕氏春秋》以“百家”贯以王治的意图应是切近的。
2.秦帝国的文化怀柔,乃是用长期在西秦行之有效的商韩法吏文化,去兼融关东地域文化,尤其是齐、鲁之地的儒、道、阴阳之术。初始的帝国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这几者在本质上的重大区别,对其“兼”“融”的严峻性估计不足。这也导致其后极端文化政策的出现。
3.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东西区域文化价值系统对立并冲突的结果,亦是始皇求仙受挫后偏激的个性心理因素所致。它是秦帝国横扫六国、君临天下、崇尚以“力”统“道”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对主观力量无限自信的一种表现。从根本上说,它是西秦商韩法家文化专制内涵所确定的必然性。
4.“焚书”“坑儒”,并公示天下,是秦帝国文化专制政策的确立,它标示了大一统君主制集权的官僚体制系统在文化定位上的价值观内涵,即等级、秩序、服从、功利等。此后,承秦之制的汉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唯儒独尊的文化形式,以及以专制主体的官僚体制价值系统为内涵的“新儒家”大一统学说的学术与理论体系,都正好是秦帝国文化禁锢政策的承继。它的变通之处在于其内容上吸取秦亡教训,注意到中国宗法社会的性质,由此将强调宗法血缘的道德礼仪的邹鲁儒家文化兼融性地标贴在法家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表面,互为表里体用,完成了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学说的转型。这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先河。
收稿日期:2004-10-20
标签: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秦灭六国之战论文; 秦始皇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史记论文; 吕不韦论文; 焚书坑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