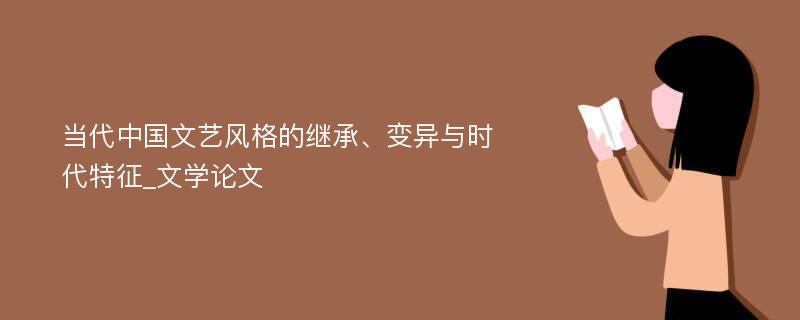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风格的传承、变异与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艺术论文,中国当代论文,风格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就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当代风格。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风格都在变化、发展,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都应继承、创造,没有继承便没有创造。民族性——时代性,这是测量中国当代文学风格传承、变异轨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发生了一次空前苦痛而剧烈的大裂变。那时,以其“超稳态结构”持续二千数百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轰而破。然而被轰破的不仅是国门,还有那一度光辉灿烂而又自给自足的古代文化(文学)体系,以及它那同样“超稳态结构”的雍容典雅、中庸和美的艺术格风。但东方睡狮在文学的田园美梦中毕竟酣沉得太久,文学嬗变的阵痛长达数十年。近代文学在思想意识上想打破旧文化传统,又因过于软弱而冲不破旧传统的藩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可以概括这一无可开解的症结);在艺术形式上既想图新谋变,又因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参照体系而苦闷不堪(“我口写我心,古岂能拘牵”其表达形式恰恰是受到“古”之“拘牵”);这打上特定时代烙印的双重矛盾使文学吹奏出悲凉的调子(“万马齐喑究可哀”。“秋风愁雨愁杀人”即是其中的凄厉音符)。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文学革命突破知识分子小文化圈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展开。中国文学的新生儿发出了响亮的啼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就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反帝是为了救亡;反封建是为了科学和民主。这两者也许不无相互抵触之处,但它们在一个交叉点上却达成了共识。即:无论是救亡还是民主,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列宁语),都必需启蒙。新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作为了自己的核心主题。“改造民族的灵魂”,一方面是无情批判因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保守、麻木,一方面是热情歌颂“中国的脊梁”、热烈呼唤“美的中国”。这一主题的双重奏,在后来的文学中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具体化、丰富化和延伸。
百余年来的中国史,外患内乱不绝。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伴随着痛苦和血污的历史“分娩”。“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经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际黑暗”(鲁迅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于是便有“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有“荷戟”的“彷徨”;有“凤凰”的再生,也有“沉沦”者的呼号;有“幻灭”、“动摇”与“追求”;有“雷雨”与“日出”;有“春”,也有“秋”……这些“大合唱”响彻着悲凉与激昂交织的旋律,悲凉中不是没有激昂,这样的战士举起了“投抢和匕首”;激昂中也不是没有悲凉,“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女神》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郭沫若语)但毕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注: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样地,中国当代文学风格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风格的传承和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学实践中,当代文学风格呈现出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传承启发演变,演变植根传承的特点。
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权早在解放区已具规模。因此,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把《讲话》指出的文艺方向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这使中国当代文学一开始就明显以解放区新文学的艺术风格为特色。事实上,建国初年最活跃的作家本来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一批作家。再加上新涌现出了一批充满生气的文学新兵,解放区的艺术风张这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热烈歌颂“美的中国”和“火热的建设”,以自豪心情回忆往昔峥嵘的战斗岁月,反映翻身农民在合作化康庄大道上焕发出的活力,成为文学最普遍的主题。文艺为工农兵,但劳动人民在政治翻身后还需文化上的翻身,要“学文化”,因此,“普及”仍然是摆在首要地位的问题。为了让文学“为工农兵所利用”,单纯直观的结构,中国传统的白描、比兴手法,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成为文学的普遍形式。由此,乐观、单纯、明朗、朴素,成为凯歌行进年代艺术风张的了基本要素。
1956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阶段。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表明历史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的题材要扩大: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写知识分子;文学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一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二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这当然就要求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即此前风格不够多样化)。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用很通俗的比喻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注:毛泽东:1956年8月24 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在此“大气候”下,当代文学风格出现了明显变化:歌颂“光明面”的同时也出现对官僚主义这类“阴暗面”的潮讽,除描写工农兵外也揭示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因而带来细腻文笔,大众化、民族化进入更高层次的形式和语言追求,在表达时代主题时也展现出个性化的不同色彩。
这种艺术风格深化、多样化的趋势不幸被接踵而至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阻遏。但失误的“运动”尽管可以一时阻碍、延缓文艺的发展,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发展的规律。由于双百方针仍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加上1961年初文艺政策的调整,我们看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村题材和民主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抒情散文和杂文、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历史题材的话剧,文学意识比过去更为复杂,主题显得更为深刻,尤其是作家视野较过去开阔,作品形态更为成熟,语言较过去更为精致。不少作家的风格较过去更为丰富,还有的作家给文坛添加了过去极罕见的悲凉、沉郁色彩。如方纪的《来访者》、陈翔鹤的《广陵散》、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以及老舍的《茶馆》。
1963年后,当代文学被迫卷入更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题材只能“写十三年”,主题必须是“反修防修”,“中间人物”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不准“深化”,文学的艺术风格骤然大大褪色。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农民对人民公社开始丧失信心,加之文学界“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注: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作为一种曲折透射,当代文学失去了当年的那种明朗和乐观,调子显得分外严峻,风格变得有些乖张、浮泛。当时几乎所有文学作品言必称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切生活现象都生硬地注入了阶级斗争的含义。任何平凡小事也无不“升华”到革命理想、五洲风云。如写“钢”,动辄就是“钢啊,钢!一身豪气一身光;巍然战斗在火热斗争的前线上”,“很快,钢不再是钢,它成了无所不在的‘精神’”(注:谢冕:《历史的沉思——建国三十年诗歌回顾》,载《当代文艺思潮》1982个第2期。 )这恰恰是文学风格变得有些乖张、浮泛的明显表现。
有人说,50年代是颂歌的年代,60年代是战歌的年代。这句话大致可以概括十七年文学艺术风格的总体变化,即由“颂歌”的乐观、明朗、朴实演变为“战歌”的热烈昂扬与冷峻沉郁杂糅。激昂则是其中的总基调。但也应注意,不论十七年文学如何激昂,既然有冷峻糅含于其中,也就并非没有历史、时代涂抹上的悲凉色彩。这只需把农村题材前后期的作品,把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作品作一比较即可见出。这甚至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如柳青)、同一部作品中(如《山乡巨变》)也可看到。
随着《五·一六通知》发表,揭开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悲剧的序幕。“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在文革前期,文学被打入死牢,长达五年的时间,偌大中国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公开发表;在“文革”后期,占“正统”地位的“左”倾文学经过极左政治的残酷“过滤”,异化了的文学表现的是表面上“豪情满怀”,实质上千篇一律的“政论”格调。风格是一种真诚的东西,“瞒和骗”必然导致艺术风张的沦丧。
惨痛的代价,终于换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期。仿佛历史又回到了1956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党的工作着重点大转移,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等等。但这决不是历史的轮回。历史根本无法重复:毕竟经历了一场中华民族的大劫难,毕竟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毕竟有改革开发的基本国策……新时期的文学,开始似乎也站到了1956年的起跑线上:重申双百方针,讨论人性、人道,揭示社会阴暗面,突破题材禁区,“五七战士”重新“回归”等等。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她与五四新文学有了更多的认同。思想意识上,批判封建、倡导启蒙、呼唤科学、呼唤民主、人的觉醒、人的苦闷等,成为文学创作的普遍倾向;创作题材上,章永璘(《感情的历程》)、白音宝力格(《黑峻马》)们似乎又在经历知识分子“幻灭”、“动摇”、“追求”的三部曲;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写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格分裂,似乎是当年同一题材的升华;而女性文学(无论是道德观念上的“新女性”还是“东方女性”)、历史风俗(如《受戒》、《芙蓉镇》之与《边城》)又成为“热点”;作品主题上《班主任》重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陈奂生拖着阿Q的影子, “落后是要挨打的”(《西线轶事》)是“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沉沦》)的巨大历史回声;艺术形式上,现代派手法的借鉴,新形式的铸造,象征主义风行,唯感觉小说再现,古怪诗使人联想到当年遭到冷遇的李金发,而艾青则重新提炼他在30年代使用较多的印象与象征手法,还有那同样富有张力的狂放不羁的语言;尤其是艺术格调,新时期文学弹奏出的还是因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带来的激昂与因历史因袭太重,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全方位改革“阵痛”带来的悲凉的双重奏。还是:激昂中不是没有悲凉——“沉重的翅膀”,使改革难于起飞,改革者不能不品味着一种孤独感,历史投下了过重阴影;悲凉中也不是没有激昂——章永璘们终于恢复为男子汉,陈奂生最后以“包产”“大团圆”,年青一代骑着“黑骏马”,用黑夜造成的“黑色眼睛”“寻找光明”。还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内,由于改革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历程要走,中国还在谋求达到小康,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空前劫难“文化大革命”给新时期投下的巨大历史阴影,以及经历了深刻痛苦的觉醒后必然具有时代性的民族忧患意识,悲凉的色调暂时会比激昂的色调更浓重。
新时期文学的这种艺术风格既是十七年文学风格的传承,也是五四新文学风格的变异;既是十七年文学风格的变异,也是四五新文学风格的传承。
和十七年一样,新时期的文学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文艺民主这一历史趋势的天然刻度。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是1956年就已经形成的一种时代要求,所以才有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到新时期,人民群众的构成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老一代工农兵文化水平有所提高,新中国第一、二、三代文化人成为社会主体,尤其是经历了文革后,中国人民不是通过“学文化”而提高了知识水平,而是通过痛苦经历而把文化提高到了观念意识的高度。根据这一时代特点,如果说当年“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精神需求,为满足人民不同心理层次的精神需求,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天经地义。于是便有文学风格由单纯到复杂、由明朗到深沉、由乐观到悲壮、由单一到多样的历史性变化。这就是新时期文学风格对十七年文学风格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风格在艺术实践过程中的发展。
新时期文学也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时期进步文学的艺术风格。这是在被历史阻隔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以文学发展规律承接上的。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更主要地是继续解放区文艺的艺术风格,这是历史时代的需要。但也并非没有历史局限,如过于忽视了五四新文学中的进步文学风格的继承。这一偏颇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补救。当然,这也是历史时代的需要。因此我们才看到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那么多的相似。但相似并非相同。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当它处于发展的某一阶段时,自然会与以前的某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它已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文学的发展、艺术风格的发展也是如此。尽管新时期作家中暂时还没有出现像鲁迅那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风格大师,但毕竟一批当年“革命文学”的过来人经历了相当长的艺术实践、探索,发展、丰富了自己的风格(如巴金、艾青),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经过人生痛苦体验,终于锤炼出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曾以幼小的心灵承受灵魂裂变的痛苦,他们起点甚高,风格早熟;还有“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他们较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天然地有些“现代派”,给文坛带来了风格的新质、异质。因此,从整体而言,新时期文学比五四新文学在文学意识上深沉得多、艺术形态上完善得多、艺术手法上丰富得多,艺术风格上也更为多样、更为鲜明、更为成熟,同时也更为凝重。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时代的文学。从历史的大背景看,新中国是在经历了漫漫长夜的封建社会,又经历了“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才崛起的;从时代的大背景看,新中国是在世界经历了两次空前的“大地震”后,国际上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性的对峙、国际共运出现大波折而我国自身还有完成历史遗留任务的情况下而屹立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为这一历史时代的以生产力为水准的经济基础所制约,并必须与这一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相适应。她表现的是这一历史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满足的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审美需要。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势必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势必会显示出自己的时代特征。
大众化与多样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风格的时代特征之一。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尺度;文艺民主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长期以来,文学成为少数人享受的特权之一,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人的本质力量得不到充分的显示,文学创作才能、创造性的欣赏才能被限制、扼杀。封建士大夫阶层是文学创作、欣赏的主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到了近、现代,这一情势有了很大变化。但即使是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文学,更多地还是知识分子在忧虑民族危难、争取个性解放时抒发苦闷,广大劳动人民并未成为文学的主人。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与文学的直接结合才能实现。于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大量涌现,平民百姓成为作品的主角,大众化的语言运用蔚然成风,作品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出中国文学史上从不曾有过的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然而,“大众”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一个个音容相貌各不相同、心理状态彼此有异的个人组成的。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不同人生经历和个人感受、不同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不同个性特征和审美趣味的活生生的个人都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他们有的人欣赏“大团圆”式的喜剧,有的人欣赏“不团圆”式的悲剧,还有的人则欣赏悲喜交集的正剧;这群人喜欢阳春白雪的高雅,那样人喜欢下里巴人的通俗,又有一群人更喜欢兼容两者的亦雅亦俗;你留恋明朗、单纯、乐观、情节,他沉醉沉郁、复杂、苍凉、心理,我偏爱朦胧、荒诞、戏谑、形而上;阴柔、阳刚、优美、壮美、滑稽、崇高、典雅、怪异,空灵、朴实,白色幽默、黑色幽默……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都可以找到产生心灵感应的读者群。没有风格的多样化就没有风格的大众化,就象没有风格的大众化就不可能出现风格的多样化一样。大众化是多样化的根基,多样化是大众化的生成。
民族化和现代化,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风格的时代特征之二。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信息交流的迅速和频繁,“世界文学”成为一种历史趋势。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的尊严,表达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强调自我选择和个性自由成为各国文学的共同主题;摒弃旧的文学传统,创造新的文学形式,探索新的艺术手法,实验新的艺术语言成为各国文学的共同观念。百年来,久经屈辱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就是民族的现代化,因而中国文学一直有汇入世界文学、在汇入过程中谋求文学现代化的强烈冲动。五四时期的文学通过“别求新声于异邦”开始具备现代意识,“借用外国良规”开始具备现代形式。(鲁迅语)这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中国当代文学也曾出现过一段与世隔绝的可悲时期,但它终于开始走向世界、大致形成了现代化的格局,并正努力进一步发展、完善自己的现代化。文学的现代化要求文学具备现代思想意识。中国当代文学由于主体意识已经觉醒,它对周围世界、对历史面貌、对社会现实、对自我人性有了比过去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清醒而真切的认识。文学因之越来越具有历史意识、变革意识,反思意识、忧患意识,忏悔意识、自省意识,比较意识、哲学意识。这是当代文学现代化的一个明显标志。文学的现代化要求文学具备现代观念。今天,传统的“文以载道”已被“文学是人学”所取代。既曰“人学”,人所具有的一切,无论思想、感情、感觉、潜意识,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文学的内容,而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具有如此广阔的空间;既曰“人学”,文学的功用就不仅是“载道”,它还可以“载认识”、“载审美”、“载陶冶性灵”、“载净化感情”,乃至“载娱乐消遣”,而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兼具这多种功用。现代的文学观念、现代的感知方式势必“物化”在文学形态中。中国当代文学在创造、建立表达现代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掌握外部世界的新方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的结构形式、新的艺术手法、新的语汇排列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文学观念、文体观念的自觉性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向现代化的又一个明显标志。
如果说“风格即人”,那么也可以说“风格即民族”。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多经磨难而始终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处,靠的就是“国破无以家为”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充分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当代的作家们继承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充分地吸取了养份,其文学心态中随处可见民族文化遗传的基因。如对民族兴衰的强烈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热烈执着,以及民族个体化、个体民族化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比如同样是忧患意识、危机感,在西方文学中往往植根于个体的人生体验,对个性沦丧、人性异化、自我分裂的恐惧;而中国文学则始终以“家亡”的悲哀表达对“国破”的忧虑,以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明民族的兴衰,即使是“我是谁”式强烈忧患,忧患的其实并非个人性的“沉沦”,而是民族的劫难。另方面,西方文学的现代表达方式或依托于极为具体的个人的生理、心理层次,或寓意于极为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层次;而中国新文学的现代表达方式则以显现明晰可感的政治、伦理、文化层面为特征。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流淌着民族意识、具有独特的民族形态、表现出民族特有的艺术格调。在当今形成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民族化的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激昂与悲凉交织,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风格的时代特征之三。一个备受欺凌、贫苦落后的旧中国,今天终于成为独立自主、处于发展中日益强盛的新中国;一个因“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而显得有些愚昧、麻木、保守的民族,今天终于焕发出聪明才智、勃勃生机;一个个过去睡着的、躺着的中国人,今天成为醒着的、“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我们毕竟是个历史悠久、有着古老的文明传统的国家,我们是一个有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国家——每当中国当代文学在表达这一心爱的历史主题时,一种明朗、乐观、自豪的感情便油然而生,“激昂”自然而然成为文学风格的一种基本色调。而只要回忆起中华民族那屈辱的岁月、辛酸的往事;只要想到国际上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仍有复辟的危险性;只要“睁开眼”看到中国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因袭、重载,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善,我们的经济、科学、工业、文化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相差一大截——每当中国当代文学直面这同一主题的变奏,往往就使她不由自己的流露出焦灼、痛苦、忧伤、烦恼的情绪,“悲凉”无是理智的还是潜意识的就成为文学风格的另一种基本色调。由此,激昂与悲凉交织,成为最典型的中国当代文学风格特征。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激昂与悲凉的交织在不同的时期因两种色彩的比重不同而呈现出主色调的变化。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的主旋律更多激昂,而新时期的文学显得悲凉更为浓重。有意识的是,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好相反,同样是激昂与悲凉交织,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风格走向,是由更多的悲凉转为更多的激昂。但若把两者衔接起来,中华民族的文学在20世纪则正是走完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风格也是激昂与悲凉交织的特征,中国当代文学风格本来就是其继承和发展。但两者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激昂是谋求民主独立、渴求中国新生,今天的是民族已经独立、新中国已经建立,因而激昂中带有更多成份的自豪;过去的悲凉相当程度上是外国列强强迫我们“睁开了眼”而产生的;今天的悲凉是我们自己“睁开了眼”,在看到历史成就时,也不能不直面自身深刻的矛盾——如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时,民族的自我反省总是使得这悲凉显得更深沉。我们深信:激昂与悲凉的交织,会激励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更加鲜明、更加丰富、更加成熟。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艺术特色论文; 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