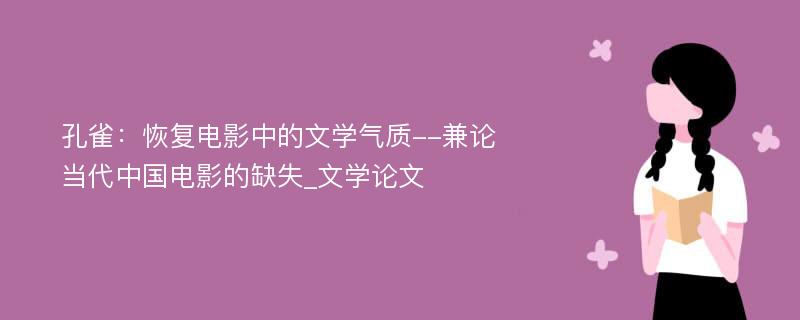
《孔雀》:找回电影中的文学气质——兼评当代中国电影的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孔雀论文,当代论文,气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孔雀》找回了丢失的气质。这种气质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 万家灯火》《早春二月》一脉相承的,是与欧洲艺术电影传统相互贯通的。
《孔雀》在适时时候的出现,扛住了中国电影下滑的危机,庆幸的是,《孔雀》没有 被中国电影日益上涨的市侩之气、庸俗之风裹挟而去,它对电影艺术本质的坚持与寻找 ,使它获得了人们的真实的尊重,它是电影圣殿上一块当之无愧的阶石。在这阶石的背 后,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来自文学的强大支撑。在《孔雀》那残酷、温暖、辉煌、美艳的 影像中,我们感受到久违了的浓郁的文学气质的复苏。
一,再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谁没有过“孔雀开屏”的梦想?姐姐、哥哥和弟弟 无一例外,而姐姐更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姐姐一心想当伞兵,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姐 姐动用了她当时能够想到的一切手段。姐姐的所作所为有着骇人的目的性,但在这目的 性中,恰恰透露出姐姐对于理想的执著。尽管姐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理想的幻灭,但理 想的炭火始终未曾在她的心底暗淡,即使处于灰烬当中依然会星火燎原,依然追求着燃 烧。伞兵没有当成,姐姐就自己做了一把伞,呼啸着穿街而过——这是影片中最富华彩 的一段浪漫影像,所有的光芒都集合在这一瞬间,它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灿烂的“孔雀” 开屏。当她狂躁的举动被家人用药物制止后,她没有颓败下去,继续在生活中寻找暖意 ,主动与艺术馆的老馆员接近,寻找精神的慰藉。她主动选择婚姻是为了减轻家庭的负 累,但择偶的条件却是摆脱原来的生活圈子,姐姐始终寻找着超越的生活。少女时期青 春梦想,总是与爱情同在,与爱情合一,彼此难分难解。姐姐对理想的爱恋或者说对伞 兵军官的爱恋贯穿全片,在影片接近结尾时,一个盲人从姐弟面前横贯而过,隐喻命运 的提示。姐姐看见一个庸常的中年男人正在街边狼吞虎咽,此人正是姐姐心中的偶像— —当年那个军官,这一场景真正体现了造化弄人的意味。姐姐回来却对弟弟谎称,对方 永远爱着她。姐姐有一个不变的品质,就是把幻想当生活,最终她找到了一个来自孔雀 家乡云南的爱人。
在各自经历了有一番人生的痛苦磨砺之后,面对冬天公园里的孔雀,姐姐、哥哥和弟 弟分别表现出对待现实的不同人生态度——姐姐对女儿说,爸爸的老家满山遍野都是孔 雀,依然怀抱着浪漫;哥哥比较务实,等挣足了钱,自己盖个动物园,住在里面天天瞧 ;弟弟消极而超脱,反正冬天孔雀不开屏。
编导站在影片中人物的态度之上,通过坚实的影像,给了观众一个自信的说法:孔雀 最后还是美丽地展开了翅膀,显示了编导的精神倾向,在理想与现实的角逐中,理想是 最终的胜利者。
二,对人物性格的深度挖掘。这是一部以人物为核心的影片,如果让我们复述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不会很爽快地回答上来,因为它讲述的不是一个故事。它 讲述的是人物的追求、浪漫、失落、沮丧,乃至于坚韧,它传达的是由人物的命运转述 给我们的一种阻塞的情绪。
编导在刻画人物的性格方面,注重人物内部的冲突感,通过自身的反作用,彰显人物 性格的张力。姐姐代表着理想,她的妥协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抗争,一方面她在现实的 泥沼中下滑,一方面她却执著于梦想,坚忍不拔,越挫越勇。哥哥代表着现实,他看似 混沌,其实每到关键环节,都保有一份过人的清醒:当他的工友因为他的原因被打,他 知道买一只烧鸡前去慰问;当他看中别的姑娘时,他知道如何巧妙地说服妈妈;当昔日 的工友朝他借钱,他爽快地答应,却搬来一箱积攒的烟盒来对付。编导着力刻画一个愚 人性格的反面,愚而不笨、大智若愚的人生智慧。弟弟代表着超脱,特殊的经历,使他 盼望着一觉醒来,已是60岁老人。他渴望过一种退休的生活,他的激情甚至不如下棋的 老头,他似乎把一切看透。年轻与世故在弟弟身上体现为一种悖论。
刻画出人物的双重性,标志着《孔雀》在人物塑造上所抵达的深度。
三,缜密精致的故事结构。《孔雀》让我们想到了杨德昌在《轱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等影片中冷静的叙事控制。对比其它中国电影,我们发现《孔雀》尤为注重故事的结构 ,以及如何进行合情合理的讲述。
影片采用三段式的复调结构,犹如小说中的三个章节,是文学上巴赫金理论的充分实 践。每一章故事集中一个人物,以人物带出事件,推动情节的发展。一家五口人在走廊 上吃饭的场景,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家庭一个典型的仪式化象征,构成了影片的总 体旋律,造成了影片结构上的间离效果。
首尾呼应使《孔雀》具有文学作品结构上的精致之美,它不仅体现在第一个镜头和最 后一个镜头呈现的是同一景观——俯瞰城市冬天的大全景,还体现在中心人物姐姐在其 中发挥的贯穿作用。三个章节虽是独立的,但姐姐在整体结构中既是起点人物,又是落 脚人物。
编导很好地解决了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与留有艺术空白之间的关系。凡是影片中发生 的事件,都有事先的铺垫或事后的暗示和交代。姐姐为了当兵花钱送礼,弟弟拿出两元 的积蓄暗中资助。两元钱是远远不够的,当姐姐看见军官与另外两个姐妹打成一片之后 ,失望地将烟酒丢到桥下,影片紧接着插入一个场景,姐姐沮丧地回到家,妈妈正絮絮 叨叨哭诉自己丢钱的经过。很显然,钱是姐姐偷的,但影片在此处点到为止。完整的交 代与含蓄的表达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几近完美的辩证处理。
那么,由此反观当代中国电影缺失在哪里?
缺失之一,疏离深度的人文表达。与近几年韩国电影丰富的景观相比,中国电影的处 境普遍令人失望,它们或者用技术上的虚张声势,掩饰内容的空泛,充装好莱坞大片之 状(《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或者用低劣平庸的趣味,包装一个思想 极其浅白的主题(《和你在一起》、《手机》、《天下无贼》)。它们不像是一个有生命 、有呼吸的活人拍出的作品,更像是木乃伊似的产品,它们缺乏现实的痛切之感、撕裂 之感,无法调动起人们心中深层次的审美快慰。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电影这几年真心的 创作很少了,任何艺术创作一旦与人的心灵不再发生联系了的时候,我们能期待它去感 动人、打动人吗?而《孔雀》唤起了我们对自身生命的审视,对他人梦想的尊重。这不 正是社会进步迫切需要的一种人文基础吗?
缺失之二,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自第五代导演以降,我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种电影 定式,观看一部电影等于赏玩一本厚厚的精美画册,观赏的过程就是愉悦视觉的过程, 除此之外,它不再负担提供更多的审美积淀。作为承担着演绎主题、推进故事等主要职 能的人物,在其中却只是没有血肉的机械人、被偶然因素牵扯着被动行走的古怪的影子 。陆川的《可可西里》展现的是中国西藏雪域高原上的奇观和奇人,护猎队员的事迹惊 天地、泣鬼神,但是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队员没有任何报酬地从事这项不被人理解的工 作,他们的心理动机是什么?陆川在本该交代的地方,反倒避重就轻玩起了空白。人物 的行动没有支撑点,其原因是编导对人物性格缺少必要的认识和挖掘。
像《孔雀》这样精心地刻画人物复杂性的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中是不多见的 ,尽管他们有的仰赖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但一旦进入导演的实践过程,他们 通常就不由自主地偏离总体的控制和把握,把人物丢在一边,陷入一种单一的角色当中 ,丧失了创作的基础和根本。
缺失之三,缺乏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的能力。电影接力棒传到第六代导演手里,几乎 只剩下了一堆精美的碎片,这些碎片甚至不能粘连起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有必要提醒 中国电影导演,如何通过影像讲明白一个完整的故事。同样是陆川的另一部作品《寻枪 》,本来具备了一个很不错的电影开头,一个警察因为失误把枪弄丢了,戏剧张力不可 谓不饱满,但是接下来他没有把这个故事运作好:什么人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冒着让一个警察担责任的危险,非要连杀两条人命?这个人的心理动机是什么?谜底揭开 后,我们看到这个锲而不舍的犯罪嫌疑人追杀人的原因,是愤慨于对方制售假药贻害社 会。很明显,电影的最大败笔是这个人物的动力线不足。
造成上述缺失的最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中国电影放弃了由蔡楚生、费穆等老一代 艺术家开创的人文主义传统,一味地追求电影的物质化,把技术化的视觉冲击力奉为至 上,漠视文学剧本的创作,轻视文学的气质,把手段当成目的,致使本末倒置,影响了 艺术的整体水平。
《孔雀》扭转了中国电影的风习,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味。
